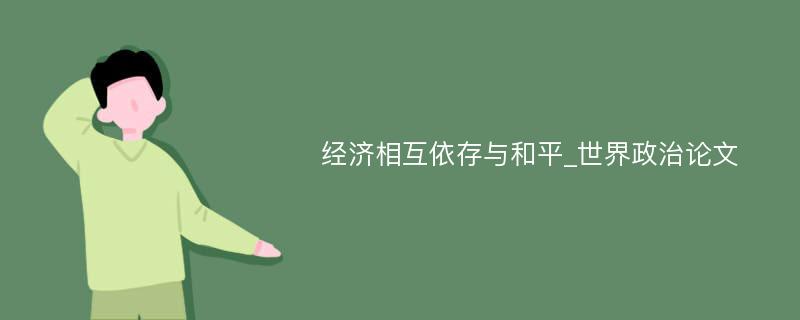
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平论文,相互依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乎所有有意解释战后的长期和平之源的人都把战后空前增强的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经济相互依赖列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注:"Interdependence"常被译成“相互依存”,但还是译作“相互依赖”更符原义。)固然,一般来说,相互依赖有着加强有关国家间的共同利益纽带、从而加强它们为国际纠纷或冲突寻找非暴力的解决方式的趋势。但进而认为,倘若各国间存在着相当的相互依赖,国际和平也就有了保障,那就不适当了。最多,“不使用武力不是相互依赖的一个本质特点,而可能是一个经常的特点”。(注:Peter Willetts,"Interdepe-ndence:New Wine in Old Bottle,"In James N.Rosenau and HylkeTromp,ed.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Aldershot:Avebury,1989).p.206.)
一
一般的,只有国家才能合法地有武装力量,国家也就成了国际武装冲突的主体。只要世界仍被分割为几十个、上百个国家,军事冲突就不会消亡。一些学者认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概念趋于抽象。为此,不妨记住这点:国家的最直接、最重要的体现是一块疆土上的一整套政治体制,尤其是政府。
在一些人看来,技术进步和相互依赖的增强使跨国经济活动大大增加,而这将使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散失其传统的意义。有观点认为,“跨国的资本与货物流动已使一国政府更难以独立自主地管理本国的经济。决策者们控制不了的国际交往可能会令一国的政策毫无效果。”(注:参见Richard Cooper,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NewYork:Mcgraw-Hill,1968).)哈佛大学教授出身的首届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赖克则走得更远。他声称,相互依赖和跨国经营要求人们放弃一个国家的所有国民是同一艘经济大船上的乘客的观念。国民的经济利益已经国际化和分散化了。今天,政府的政策也许只对某一两个大公司、某一小部分国民甚至相当一部分外国人有利,而并不能让多数人获益。(注:参见罗伯特·赖克:《国家的作用: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更有不少人在津津乐道大型跨国公司在国际事务中的新兴作用。
相互依赖的确将使国家趋于衰微么?至少是在经济生活中?我不这样认为,理由是:
1.即使国家散失了在经济方面的职能,它依然能在其他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生活在同一个居民小区的人们很可能供职于各不相同的公司、企业、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有着各不相同的经济利益来源,但他们依然有着基于共同的居住区域的共同利益,都会希望所居住的小区有着清新的环境、良好的治安、便利的服务设施甚至较高的道德水准。同样,即使一个国家在经济上被相互依赖扯得四分五裂,其国民依然可能对稳固的国防、良好的生态、较低的犯罪率、周全的大众福利、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等有着共同的要求,而这正为政府开辟了大有可为的空间。
2.实际上,相互依赖很难使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不再构成一个经济主体,很难剥夺一个政府的经济职能。使相互依赖程度上升的一大因素是技术进步。它通过改善交通、通讯和信息传播状况等降低了跨国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使之能更广泛便利地得到开展。可是,技术进步所促进的不仅仅是跨国的经济联系,它同样也降低了国内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刺激了一国疆界之内的经济交往。因此,相比于国内经济活动,“国际流动在今天是否比一个世纪或更多时间以前更为重要尚不清楚”。依据托姆森和克莱斯纳提供的数据,全球出口值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880年是11.4%,1980年才达到16.9%;对外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840年是19%,到1970年只有12%;美国的对外空中运输和国内空运的比例在1930年是11.4%,在1980年降到了8.8%;全球国际邮件数和国内邮件数的比例在1928年至1929年是7.2%, 到了1975年至1977 年才升至9.3%。(注:Janice E.Thomson and StephenD.Krasner,"Global Transaction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Sove-reignty."In Ernst- Otto Czempiel and James N.Rosenau,ed.,GlobalChanges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Approaches to World Politicsfor the 1990s(Lexington:Lexington Books,1989),pp.199~205.)因此,各国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依然在自己的疆界内进行,我们所认识到的相互依赖的空前增强只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跨国经济活动远未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断定是否会出现这种局面。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除了交通、通讯之外,还有劳动力价格、比较技术优势、原料来源、市场分布与政治状况等等。就它们而言,并不能得出进行跨国经济活动是商人和企业家们必然的优先选择的结论。与此相联,政府由于本国疆域之内的经济活动的大量存在依然会具有强大的经济调控职能。这个职能也延伸到了国际经济活动身上,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经济世界上,各国间的协调和合作管理必不可少。另外,也极难想像除了国家,还有其他什么权威能为产权和经济秩序提供切实的保护。
3.一群国民和另一群国民之间最基本的区分在于他们各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民族团体感。它们分别升华于成百上千年的共同生活经历,比现实中共同的经济生活更能够有效、长期地赋予某一片疆域上的居民以团体意识和自我精神。在当今世界,作为一种精神的民族主义依然充满活力。姑且不论新兴的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在相互依赖程度最高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世界中,民族主义也依旧是一面夺目的旗帜。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淹没在了美国民族主义的喧嚣中。目前,这般情感丝毫不为相互依赖所左右,后者反而常常是国家自我意识的催化剂。
所以,各个国家作为各个不同的社会单位、经济单位和文化单位依然积极地存在着。美国人还不能像用自家钱那样随意动用日本人的外汇储备,欧洲人也不会把克林顿看成自己的总统。我们目前也看不清有什么道路将人类引向天下一统。只要这种局面依然明显地存在,各国就各有其独立的基本利益,各国间的利益分立就仍是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国际合作就只是参与者实现各自需要的一种手段,而使用强制和暴力仍旧是国家在必要时的有意义选择。
二
相互依赖不仅根本不会消弭国际冲突的根源,也不充分地具有维护和平或合作的能力。有人说:“在相互依赖的情形下,战争变得非理性了。因为它会危及并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会损害的不仅仅是敌手,也包括一国自身的利益和投资,它不会有助于任何理性的目标”。(注:Hylke Tromp,"Interdependence,Security and Peace Research." In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p.9.)可是,战争本身作为一种非理性的解决分歧的方式,并非一直是理性思维的产物。荣誉感、无休止的贪婪、冒险精神、领导人的偏执等等都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从一般的理性出发,希特勒就不会在1941年进攻苏联,萨达姆也不会在1990年出兵科威特,而今天的某些日本人则会为偷袭珍珠港而惋惜不已(因为否则的话,日本或许还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有中国东北和朝鲜)。即使决策者本人有严谨、缜密的头脑,面对着一种普遍存在的、要求显示实力和决心甚至不惜使用武力的公众情绪(这种情绪大都不是“清醒的实用主义”性质的),出于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或其他原因,他们未必不会多少屈服于舆论压力。在危机时刻,决策者也往往缺乏足够的时间和意志来进行全盘思考。
即使战争决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相互依赖带来的庞大利益也不必然是和平的坚实保障。既然如前所说,一片疆域之内的经济活动依然构成了一国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那么对外经济联系就不是万万不能割舍的。如果一国认为它从战争中得到的收益要比付出的成本多,或者是战争给敌国造成的损失要比己方遭受的要大(比如有人说日本在30年代频繁掀起对华战事的一大目的是打乱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在中国出现的稳定的现代化进程),战争对它就是可选择的。而且,统治阶层出于自身的眼前紧迫需要常常不惜让大众的整体利益因战争受损。为解决自己的统治危机,阿根廷军政权在1982年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以图转移国内矛盾,使自己成为随着战争的到来而高涨的国内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认同对象,尽管战争会损害与西方的贸易关系,恶化阿根廷经济。与此相联,如果将对外政策放在国内政治的框架内考察,那相当多的时候它不过是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要求相互竞争或妥协的结果。既是如此,某些群体系于对外经济联系的利益有时就不会得到保全。
对一国来说,相比于经济利益,就性质而言更加重要至少同等重要的是政治和安全利益。在一个国家林立、民族主义盛行的世界上,这方面的利益被普遍地认为比经济上的好处更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和荣誉,因而也更能令公众敏感。对几乎所有的国家来说,政治和安全都是经济利益的必要先决条件所在。对其中的一些国家来说,经济发展的主要好处就是增加国家的实力和政治威望。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利益也是各国军队所服务的首要目标。为此,一国将经济上的实惠置之一边,毫不回避战争可能是常有的事。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特雷奇克甚至声称,无论何时国旗受到污辱,都必须立即要求彻底赔偿。如不能得到满足,“就必须立即发动战争,不管引发的事端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注:转引自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第218页。)假如台湾宣布独立,相信中国政府不会不采取断然措施,虽然这即使不会招致美国或西方的武力干预,也完全会严重影响到中国与西方的经贸关系。
相互依赖的类型也影响着有关国家间的合作可能的大小。罗瑟克兰斯认为,“两国之间互利的贸易关系也许不能约束它们的政治立场和政策,尤其是如果所交换的商品能从其他地方获得的话。金融上的相互依赖可能无甚意义,倘若所牵扯的只是对某家外国公司证券的购买。只有在另一个国家拥有相当的固定资产才表明对该国的政治和经济前景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为此,直接投资比有价证券的投资包含有更大的利益相关性”。(注:Richard Rosecrance,"War,Trade and Interdepende-nce."In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p.52.)不过,建立在直接投资基础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否意味着政治关系的牢固也得取决于其他因素。
相互依赖可能导致有关国家进行经济政策方面的协调,对国际经济进行合作式管理,这在现实生活中不乏其例。但是,“国家(特别是大国)开始广泛地利用政治和经济杠杆,来增加他们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的相对利益。经济相互依存和国家自主之间的矛盾,经常是用有利于自主而不是有利于相互依存的方式加以解决,各国既希望从相互依存中获益,同时又谋求限制它对国家自主的影响。他们要求得到自由贸易的集体商品和维持稳定的货币秩序,而又不致损害他们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经济的能力”。(注: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第440页。)另外, 增进国内福利已成为各国政府的优先目标,国内经济压力使今天几乎每个国家都执行出口导向性发展战略和进攻性扩大出口的政策。这样,国际政策协调并不建立于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我们不能指望它能一次又一次地取得成功,也不能断言这方面的失败不会引发政治冲突。
相互依赖本身也不是完全有利于和平。理由是:
1.相互依赖的增强意味着有关国家间接触面的扩大。而客观上讲,接触越多,发生碰撞、摩擦的可能性就越大。从古至今,大多数冲突或战争都不是发生在有甚少联系的国家之间。今天,美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赖。顺理成章地,美日两国之间的纠纷数量也远远超过它们和诸如尼泊尔之类的小国间的纠纷数量。因此,相互依赖绝不会减少冲突数量。不管这些冲突能否通过妥协、调和而解决,冲突的增多至少不会有利于和平。
2.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每一种分工都意味着依赖,因而也包含着一种政治关系。相互依赖的政治性不仅表现在它有可能促进有关方面间政治关系的协调上,也表现为它有可能促成冲突。基欧汉和奈把依赖的中断对某方造成的影响程度称为敏感性,把该方“获得可替代选择”的能力叫做脆弱性。那么,如一种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一方的敏感性或脆弱性较大,这种相互依赖就不是对称的。显然,这类相互依赖屡见不鲜。而“在行为体交往中,最有可能为行为者提供影响力的是依赖关系中存在的不对称状况。依赖性较少的行为体经常可能把相互依赖关系作为在某一问题上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或者影响其他问题”。(注:罗伯特·基欧汉和小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4页。)这样,冲突或政治冲突就极易发生。上个世纪末,美国对夏威夷的吞并就是一个例子。美国成功地利用了夏威夷对美国蔗糖市场的严重依赖,通过大幅限制夏威夷蔗糖的进口造成了后者国内的经济混乱和政治动荡,并乘机攫取了这个群岛。1941年美日间爆发战争的一个导火索也是美国中止向日本供应后者严重依赖进口的燃料、钢铁等战略物资。战后以不对称相互依赖为武器的典型例证是70年代阿拉伯产油国向西方的叫板。若不是当时的世界正处冷战僵局之中,也许早已有了另一次“海湾战争”。
对称的或几近于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也有被利用的可能,就像战争并不是总发生于两个强弱分明的国家之间一样。决定一国在以相互依赖关系为杠杆的游戏中能否获胜的不仅是这种关系客观上的对称状况,也包括有关各方的主观承受能力,而这不一定与前者相称。相互依赖常常促使一些国家为寻求自主或保证基于对外依赖的利益而使用武力。当年日本推行南进政策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想摆脱在战略物资的获得上对美国的严重依赖。美国对第三世界的依赖也是它对该地区不时采取武装干涉的一个原因。
相互依赖理论的一位先驱、英国的安吉尔爵士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向人们证明,战争已变成不可思议的东西,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对立面,有百弊而无一利。(注:参见Norman Angell,The Great Illu-sion: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of Military Power to National Advantage (New York:Puntam's,1911).)可现实表明,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国家间竞争依然强烈地存在的背景下,贸易是国家增加财富、增强实力和安全的工具,这样我们就不能指望它总是维护和平,总是促成合作。
三
迄今为止,最高程度的相互依赖其实仅存在于发达工业国家和若干发展中国家间。历史上相互间多有紧张和战事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在二战之后已享有五十余年稳定的和平,人们对相互依赖的和平作用的乐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可是,早在一百年前,欧洲和北美就已经构成了一个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世界。前后的不同使人要去寻找更多的原因,也大可找到不少缘由来解释战后工业世界的和平。
头一个自然是冷战。它使西方国家有必要处理好相互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以服务于联合对抗苏联这个共同的首要目标。在我看来,冷战是战后西方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的首要原因或第一推动力。美国之所以原意贡献“公共利益”,西方国家之所以保持持续的经济和技术进步都有系于此。由此,冷战后的西方国家间关系又会如何变化?斯特兰奇预测,“一旦柏林墙的崩溃减少了它们安全上的受威胁感,美国的盟国有望会重提它们推行与美国不一致的政策的权利”。(注:Susan Strange,"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Cambridge:Pohcy Press,1995),p.159.)
第二个原因在于,在战后西方世界处于超强地位的美国担当了军事安全方面的主要角色,并为维持多边的经济调控体制付出了相当代价。这不是在肯定“霸权稳定论”,因为“只有随着主要矛盾的出现,霸权国面临更强有力的外部挑战,才能些微收敛其高压政策,容忍他国某些歧视以谋结盟,争取战略优势。战后西方多边自由货币体系得以投入运营是以整个国际体系的不稳定即冷点为前提”。(注:王在帮:《霸权稳定论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考察》,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我们发现如今美国变得愈发斤斤计较了。
第三个原因是,在战后西方,诸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经济管理体制得以建立并发挥积极作用。这种机制的存在有利于改善信息的传输,规范参与者的政策选择,增加某一方的行为及其结果的可期望性,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便利了合作的开展。30年代初之所以经济民族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大行其道,不是客观上不存在合作的机会,而是普遍机制的缺乏使各国在紧迫局势下难以心平气和地达成妥协。当然,机制不是解决任何矛盾的灵丹妙药。而且,如前所说,战后美国为上述机制的正常运转确实付出了一定代价。
第四个原因是技术的进步。它对冷战后西方世界的积极作用主要在于两点:1.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使人的智力素质成为了决定经济财富增减的最重要因素,而使用军事手段并不能使你方便地获得能为你工作的熟练技术工人、专业人员或科学家,他们更适合于用和平的方式来培养。另外,技术变革也相当地降低了对于天然原材料的依赖。2.战后空前的技术革命带来了空前的经济增长,使发达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空前加强,增加了它们相互协调的趋势。而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有利于缓和各国的经济压力和在政策协调上的难度。相反,一个技术停滞、增长缓慢的世界必定动荡不定。
另外,西方国家间存在着所谓“民主国家间不应打仗”的观念。我认为,在战后西方民主制在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的情形下,冷战促进了西方国家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亲近感,连同战后它们相互间长期的合作关系,造就或强化了上述观念。不过,需要澄清的是,我不认为“民主和平论”本身站得住脚,只是认为“民主导致和平”的观念在西方的形成是可解释的。我还认为,在西方国家眼中,“民主国家”仅仅是它们自己,它们对非西方的“民主”国家并无很深的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我感觉到,欧美的“民主”国家对于“欧美式民主”有一种强烈的自傲心态,这导致了这种矛盾现象:它们一方面起劲宣扬、推广自己的“民主”,另一方面又对非西方地区成为“民主的好学生”的能力百般怀疑和挑剔,连日本都未必被它们当成“自己人”)。
还有其他一些对战后西方和平相对次要的原因,如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战争费用的上升、上半个世纪两次大战的惨痛教训、战后和平运动等等。总体上说,相互依赖也是战后西方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它的作用和上面重点提及的几个因素相比,并不是第一位的,而且还有赖于其中的若干因素。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国际现实下,即使相互依赖本身在大多数情形下有促进和平的作用,但这种作用远不足以令人满意地抑制冲突和战争,相互依赖下的和平都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在现实中,相互依赖的世界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界的观点十分流行。这种观念的传播自然会有利于和平,因为人都是在观念下行动的。可是,这并不意味这种观念本身的合理性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因此它也不足以应付具体的现实,而持有该观念的人们面临具体的现实也不禁要对其打些折扣。比如,早先日本的政治家们认为促进中国与外部的经济交流与融合就能够防范所谓“中国的威胁”,而现在他们又觉得还是和美国人贴得更紧一些让自己踏实。(注:参见Michael J.Green and Benjamin L.Self."Japan'sChanging China Policy:From Commercial Liberalism to ReluctantRealism." Survival,Vol.38,No.2,Summer 1996.)
但是,“目前对经济的关注以及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强,也表明了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用和平变革的机制取代传统的依赖战争进行变革的梦想或许可以变成现实。使这一梦想成为现实应该成为当代国际事务管理的一个主要目标”。(注: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页。)这个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多个因素的组合。 虽然当前并不能把冲突和战争的根源从世界上抹掉,但使这个星球多些平静还是大有余地的。当然,单纯的和平不一定具有最高价值,公平地照顾到各方的合理利益的和平才应是值得我们去争取的目标,这样的和平也最有可能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