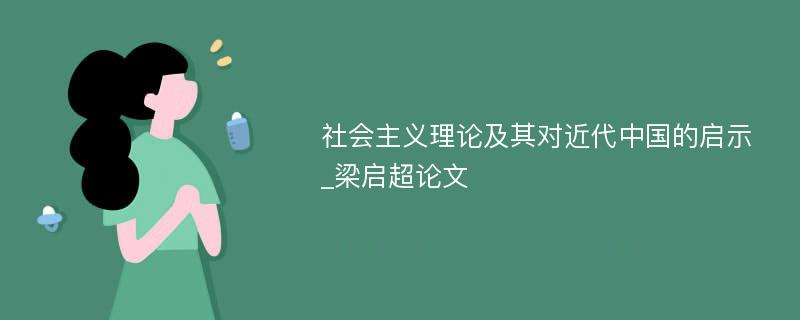
社会主义学说和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蒙运动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1)01-0029-07
启蒙运动是一种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知识而得到进步的运动。17到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因启发人打破中世纪的黑暗,当它传入中国时,有人译作“黎明运动”。在近代中国,正当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推动早期中国启蒙运动开展的时候,一些外国的社会主义著作被译介传入中国,首先在这部分思想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传入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而启蒙运动又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传介铺平了道路。
社会主义学说同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这种特殊关系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在西方,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是批判封建主义,而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则是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出现以后才开始。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不能简单地按照西方启蒙学者所指引的那条道路走下去,因为当时西方启蒙学者所讴歌的理性、博爱、自由、平等,此时变成了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尖锐阶级矛盾和工人运动高涨的严峻事实,使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一方面试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由于中国启蒙运动和西方启蒙运动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别,决定了它一开始就与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联系在一起。
一 戊戌变法的社会理想
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其代表人物的积极作用,主要并不在于政治改革的成效,而是在于思想启蒙。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某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同时又在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学说体系,即初步的资产阶级理论形态。由于他们对于世界环境和历史进程有一定的理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认识到帝国主义的腐朽的一面,能够清醒地看到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列强“即不尔而握全国平准界之权,已是使我民无复遗类。”[1]基于这种原因,他们对西欧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抱同情态度。当然,他们所要求保护的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把社会主义附会在进化论上,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原则运用于人类,使社会主义学说成为我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复活。他们在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项原则涂上一层浓厚的小农平均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作为戊戌变法运动领袖的康有为,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02年正式写成的《大同书》中。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即已萌芽,他在《实理公法全书》等著作中,初步提出了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开始把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念纳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19世纪末,他将前期的大同思想又进一步具体化,并吸收了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各种社会主义著述中的养分,使这种思想在保持批判旧世界的革命精神的基础上,又充实和丰富了内容。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回忆了自己的大同思想发展的历程。他说在《西国近事汇编》等书的影响下,他“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1884年,“始演大同之义”;1885年,“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86年,“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对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接触得更多一些了,因而其“大同思想”较前进了一大步,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大同书》所歌颂的,是建立在“独人”基础上的“大同社会”,即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理性王国。
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所讲的破除九界,包括取消国家和家庭,消灭阶级差别和贫富的差别,当然非常激进。但是,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像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一样,企图以社会全体群众的资格,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者出现。因而,他的大同设想,也就带来了不少问题:第一,这种“太平大同”经“待之百年”之后方可实行;第二,“九界”破除的方法,不是依靠阶级斗争,而是使大家明了天赋人权。他大肆宣传富人、贵人、帝王也有种种苦难,以此来掩盖劳动人民穷困和灾难的真实根源。他主张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和平共处,只要由“仁人”广为宣传倡导,即可使社会走向大同。例如说,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各为夫妻,只订岁月交好之和约。这样实行60年,无夫妇父子之私,无遗产可传,就可以进入大同世界。这种上天堂的门票自然是廉价的,但只能是一张空头支票。康有为所说的“无有阶级”“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是指废除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实行“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治”意义上的平等,是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基础上,建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社会,这客观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对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向往和歌颂。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石,就在于获得人身自由的个人,它把人从宗法社会中解放出来,而康有为强调“大同世界”建立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也具有社会的进步意义。
当然,《大同书》也想探求在今后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如何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它认为,“机器之在今百年,不过萌芽耳,而贫富之离绝如此。”那么,在今后数十年,贫富不均,则会远若天渊。而“工党之结联,后此必愈甚。恐或酿铁血之祸。”所以,要紧的办法,是使“人无私家,无私室,无私产,无私店,无家而禄厚,性美而教深,必无侵盗之心,自无侵盗之事。”这里描述大同理想所使用的语言虽然类似空想社会主义,然而其思想又是庞杂和模糊的。它可以说是以基督教的平等、佛教的慈悲普渡和孔子的仁爱为基础,杂采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新说,在“三教合一”的基础上形成他的理想与现实改革的主张,所以其中充满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正是在于既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却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2]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实质也是如此。
由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带有不少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所以,它在对未来的憧憬方面,虽然含有较多的虚幻和空想成份,但也预示了某些后来已经科学证明了其正确性的东西。比如,《大同书》中说,“太平之世”,工人阶级应该最受尊敬,劳动对人来说,不成其为一种痛苦。这说明康有为是受到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在他完成《大同书》时,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早已达到了高峰,西方之行,又使他有可能接触到傅立叶等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而在《大同书》中也确实提到了傅立叶,同时在某些内容上也有与傅立叶等人的学说如出一辙的地方。毫无疑问,康有为如果不是广泛地从当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著作中得到启示,《大同书》就不能达到如此的深度和广度。
从康有为写作《大同书》的主观原因来分析,是由于当时改良派所面临的是一个空前变动、万花缭乱的时代,原来固有的旧事物开始令人怀疑,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摆在面前需要解决,这就迫使他们冥思苦想,进行判断。如果说,康有为的《大同书》只是把西欧早期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揉合在一起的话,那么,近代社会主义思潮在他的助手梁启超身上却留下了深深的烙痕。因为,后来梁启超身居日本,对于国内译介社会主义著作热潮的出现,远比他居于印度的老师要敏感得多。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写了不少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当然,在他的笔下,社会主义也是被纳入改良主义的轨道的。如同对待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伟大原则所表现出来的双重性格一样,他在《新民丛报》十七号的《干涉与放任》中,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一方面又说“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生放任,其内质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他把古今中外的统治术,分为两大主义,“一曰干涉,一曰放任”。而历史的发展是走着否定之否定的道路的,中世纪的干涉主义时代,为18世纪、19世纪的放任主义所代替,而20世纪又将是干涉主义全胜之时代。社会主义之所以被说成为干涉主义,是因为它提倡集体主义,每个人都像一个螺丝钉,必须随着社会主义这部整体机器的转动而转动。那么,今日之中国,应该采何种主义,他认为,“其当操干涉主义者十之七,当操放任主义者十之三。”这是所讲的干涉主义,并不完全等于社会主义,而是集权中央,扩张政府权力,建立“有机统一与有力之秩序”。所以,在梁启超看来,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政治改良中的一种辅助剂。
在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使命就是进行思维,发现永恒的理性、正义与真理。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同样不懂得唯物史观,但是,由于现代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他们又开始意识到仅仅进行思想革命还不能根本解决社会问题,所以,还必须重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1903年梁启超撰文认为,社会要求进行变革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条件,他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的分析,然后指出:“自机器大兴,生产力骤增,而消费力(即买物者)岁进之速率不足以应之,于是生产过剩,特价下落,不知所屈。小资本家纷纷倒闭,而大资本家亦綦惫矣。”[3]资产阶级把这种经济上的灾难都要转移到劳动者的身上。由于物价下降,失业工人人数的增多,资本家“则不得减劳力者之庸率而延长其操作之时刻,或用妇女儿童,使之过度之勤动。”“加以小资本家力不克任,相次倒闭,弱肉强食,兼并盛行,于是生计界之秩序破,劳力者往往忽失糊口之路。”[3]这样,就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此近世贫富两极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起也。”[3]这种矛盾和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弊端。“据社会主义家统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九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此等现象,凡各文明国罔不如是,而大都会为尤其。纽约、伦敦,其最著者也。财产分配之不均,至于此极。”[4]因此,社会革命终将不免。这就说明他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从经济制度方面来寻找社会变革的原因,这是梁启超比西方启蒙的思想家进步的地方,而这种进步是与他接受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
梁启超虽然认为“社会革命其终不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从改良主义转变到革命民主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改良政治的附庸品,社会革命没有必要去发动一个阶级去推翻另一个阶级。为了说明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改良主义的一种方法,梁启超把这种崭新的学说说成是“中国固夙有之。”他把古代的井田制度,汉代王莽的复古改制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曾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5]而宋代苏洵对贫、富不均现象所表示的一些不满言论,也被当作社会主义思想,说“此等言论与千八百六十六年万国劳动力党同盟之宣言何其口吻之逼肖耶?”[5]在这里,社会主义不仅作为西方政治学派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而且遭到了歪曲和篡改。其实,反对贫富悬殊的思想,在中国早已存在。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如此严重的“不均”,又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没有料想到的。在中国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传统“均平”思想的熏陶,另一方面又骇怕在竞争中成为外国资本的牺牲品,所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平等的理想相差太远。但是,这种“均平”思想理论的空泛,常常是与实践活动的不足称道结伴而行的。所以,尽管梁启超把社会主义称为“分配极均,而世界将底于大同,此社会革命之真精神。”[6]但是一接触到具体变革的时候,又认为“万难实行”,把它拒之在千里之外。由此可见,改良派依着自己的理解和需要,介绍和罗列一些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事实,包括马克思的事迹及其学说,其目的还是逼迫清朝政府接受他们的一系列的改良主张,在某些方面按照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方法,来革除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某些弊端,以避免一场真正意义的社会革命。
二 取代戊戌思潮的民主主义
从1903年以后,戊戌思潮的高潮逐渐过去,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急速高涨。正是在这种关键的交替时刻,康、梁等维新派的政治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对以往只是作为新学派之一种的社会主义学说,也转而采取公开的反对态度了。梁启超的这种政治的退步,恰恰说明他对较为彻底并较富于战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格格不入。这种转变也使他自己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早期突击手很快地沦为这一运动的绊脚石。历史的发展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代替维新派推动近代启蒙运动向前发展的,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而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任务,也就历史地落在了这些人的身上。
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为了挽救中国的危亡,如饥似渴地寻求各种新的学说,以运用于社会的改造。但在这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它的腐朽本质已充分暴露出来。特别是生活在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直接感受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种种不合理的事实,而且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时时刻刻冲击着他们的思想。这就很自然地使他们在接受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同时,也从社会主义思潮中吸取一些政治营养,把社会主义作为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医疗术。
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先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是马君武。1903年3月2日,《译书汇编》第11期发表了他撰写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马君武在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时谈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他指出:“社会主义诚今世一大问题之最新公理”,它“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Saint imon)、佛礼儿(Fewine),中具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Blane、louis),布鲁东(Proudhon),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Ferdinandlassalle)、马克司(Kanl Marx)”(引文根据原译)。文章称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了在当时条件下较为详尽的介绍。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马君武不是像梁启超那样把社会主义归结为进化论的一种,而是把两者加以明确的区别,他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中说:“达尔文之所谓发达与社会主义之所谓发达,固不同也。达氏以物种竞争最宜者存;社会党人以为,人群当和亲利益均享,其异甚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在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以后,由劳动者共同掌握生产资料,然后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所以,“争利一事,固社会党人所诋为人间之黑兽(Betenoire)者。依达氏之说,则争利为社会竞争以致进步之鞭。由于马君武能够在思想上把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粗浅地加以区分,从而也就在政治上开始了从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然而,由于他并没有完全摆脱把进化论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所以,又往往把辩证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相混淆,认为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结论和生存竞争推动社会进化的观点是互相补充的。
但是,马君武是把现代的社会主义思潮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严格加以区别的,在这一点,他比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有很大的进步,因为他对那种把社会主义依附于古代的大同思想的说法是持明显批判态度的:“且近人已有托礼运之片字只义,演为大同条理,除设制度以期实行者,欲以一人为牧人,以众生为牛羊,而听己之指挥焉。”所以,这种大同思想,实际上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封建专制没有多少区别。他认为,作为启蒙运动倡导者的责任,并不是引导群众原封不动地固守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要使原有的思想文化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得以发展,把传统文化中没有的崭新学说介绍给人民群众:“以中国今日文化之程度,进而与之言社会主义,其不惊疑却走也几希。虽然欧罗巴之世界,既有此种奇伟光明之主义,而忍使吾国之人昧然不知其为何物,则亦非以输入文明为己任者之本心也。”[7]
马君武在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时还有一个可取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和批判。1903年5月10日,他在《新民丛报》第31号上发表的《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和《佛礼儿学说》,除了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学说做了简要的介绍以外,还指出了他们思想中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在《佛礼儿学说》中,他指出,傅立叶“全不知人类之有自利性也,欲不可纵,而自由必不可无界。徒务纵欲,而自由无界,是返人群于草昧之道也。是皆与政治及社会进步之理不合。虽然,读佛礼儿之书者,则必知专制政府之罪恶,而地方及个人之自由,不可不发达。此佛氏之所以为世所重,而后之谈生计学者,皆不可不研究其学说也。”傅立叶的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则是“感情的吸引”,而个人的自私自利,将融化于统一的合流之中。他离开社会关系的总和来抽象地谈论人的性质,这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这样的思想在当时确实能够激发人们对于平等、自由的追求,鼓励人们去从事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马君武虽然在当时不能这样去评价傅立叶的学说,但是,他在评价傅立叶这种社会结构的原则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时候,指出傅立叶反专制、争自由的必要性,和实现这种自由所采取的途径的不合理性,确实具有科学的成分,在某种程度上接近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三 具有激进色彩的宣传
1903年,由日本东京浙江同乡会创办的《浙江潮》,和由江苏同乡会创办的《江苏》,在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方面,都较为激进。
《浙江潮》是一个具有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的刊物,同时又受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永等人的影响,所以能够注意从经济上去分析当时中国存在的民族危机。该刊在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中,注意在某种程度上使之与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比如,它指出甲午战后,沙俄政府利用清朝统治者的亲俄倾向,登堂入室,巧取豪夺,把势力范围扩展到长城以北,使这些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商业、航运及其他经济利益都落入到沙俄资本家之手,中国人民对此再也不能置若罔闻。否则,“可萨克之殖民地将包山东、直隶而有之,而黑龙江、黄河之水将全赤,而我国民,且将望北九叩首以大呼顺民”了[8]。这种分析,在思想内容上比早期单纯的排外思想广泛而深刻的地方,正在于认识到外国帝国主义之所以侵略中国,从经济根源上讲,是要实行资本的扩张,通过这种扩张而实行政治控制。
在《浙江潮》的第6期上,刊载了《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作了比较。它指出,欧洲18世纪的革命,导致了西方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教育及物质文明的大发展。然而,物质文明的进步,并没有给人间带来多少幸福。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之额日众,社会之幸福日薄,百实业骤兴,而富者益富,贫者亦贫”。“多数人民仅得为资本家之奴隶,而独立性质乃全灭绝,自由生活乃全阻止。”这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和社会党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近世社会党蔓布列国,忽而同盟罢工,忽而集会学说,每年秘密出版之劳动杂志数百万册,抗贵族求平等自由血泪数百万斛,非有昔日之压制,安有今日之炸裂。吾视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纯乎社会主义之世界矣。”[9]从而,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还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问题。
当然,《最近三世纪大变迁史》的作者在当时是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理论的。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种现实矛盾的直觉又使作者称赞法国大革命,并要求中国要以此为榜样建立所谓平民社会。这种平民社会,是“各人皆以自己之力,生存竞争之社会也。平民的社会,能拆毁梯子,使上层主人公个个滚下与平民对立之社会也。平民社会,以天则及道德为基础之社会也。”[9]这种平民社会,实际上也是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理想的社会。作者希望用这种理想来反对封建制度,自然是进步的,但同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是不协调的。因为,用资产阶级革命的办法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这本身就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然而,对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主派来说,又只能设想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下来解决自己国家民主革命中的问题。
《浙江潮》的第8期,刊登了《新社会理论》,作者把共产主义基本原理说成是废除私有制而代之以国家所有制。他指出,地主、资本家掌握土地和资本而不劳动;劳动者从事生产而无生产资料,这是劳动者生活穷困、精神卑屈、政治上屈从的根本原因。作者还扼要地概述了剩余价值的原理:“劳动之结果,即天然之报酬。今日生产力益益盛,当使劳动者的报酬益益加,人益益幸福。”但是,资本家利用生产资料的垄断“坐而护其利”,于是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劳动者“其生计费以时匀计之,平均一日六时已足,今劳动者至十二时,十三时,尚不足担。是贫者富者,非关系的事,而绝对的现状也。”在克服劳动阶级这种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就“必废私有相续制而归于国存。”
《江苏》杂志在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批判改良思潮方面也是一个很激进的刊物。它在第六期的《中国立宪问题》等论说文和时事短评中,揭露了清政府推行“维新”、“新政”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嘲笑改良派一套保皇主张是“形同妻妾”的“柔声缓语”,号召知识分子,摆脱改良思想的束缚,选择革命的道路。1903年,俄国革命运动在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有了新的高涨。这一形势对处在民主革命运动前哨的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江苏》第2期的《俄人之自由思想》一文,着重介绍了1895年以来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简述了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活动和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经过及其早期活动情况,称赞它“范围之广,势力之大,出于意表,政府虽出而与抗,然终不能灭也”[10]。只是囿于见闻,搞不清民意党、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而笼统地把它们都称为“民党”。然而,它从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的启示中,树立了反专制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它指出:“专制政体者,侵害国民之公益,剥削国民之权利之利斧也。故人先当文明之世,公理既明,权利之观念既强,未有不求去专制政体者也”[11]。而推翻专制政体的革命,必须使用暴力手段,而暴力之能够实现,又在于把群众广泛地发动起来,并增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无团结之暴动,野蛮暴动也,虽日日暴动无效也,……盖天下事未有无团结力而可以成者也,是故欲言暴动则不可不言团结,俄罗斯之暴动有团结力之暴动也,……是可为我民族法者也”[12]。《江苏》当时所发表的这一番议论,其突出特点,是强调坚持革命的道路,反对改良主义,它在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潮逐渐被革命思潮所代替的关键时候,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
在当时的条件下,《江苏》杂志要沿着探索革命的道路前进,必然要表明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第五期上的《国民新灵魂》一文,分析了“上中二等社会”,指出“下等社会之困难于经济,类皆受上、中二等社会之压制”。并把利用资本进行剥削,“闭门高坐,如第二之君主”的人,称为“助独夫民贼以流祸”的“奴畜之类”,还称颂“共产均贫之说”为“人从所欢欣崇拜,香花祝而神明奉”的学说,宣称要用这种学说“铸我国民之魂”,并且准备“先献身破产,铲平阶级,以为因民倡”。这里,尽管作者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相当肤浅,但是,其追求和皈依真理的坚强决心却令人钦佩。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启蒙运动正处于初期阶段,作为这种启蒙运动先驱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是把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作为新思想的一种来进行介绍和宣传的。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学说和他们所讴歌的自由、平等结合起来了。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作为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曾经在“牖新知”的旗号下介绍过社会主义学说。而当他们由启蒙运动的发起者变为这一运动的绊脚石的时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便接过了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接力棒,开始探索和传介各种社会主义学说。这些人,大多又是侨居国外的知识分子和留学生。正如斯大林所说:“在学的青年,当他们还没有投身于人生大海,还没有在那里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热心地追求那号召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理想。”[13]因此,他们能够跳出改良主义思想的樊篱,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和传播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当然,因为在这个时候,去戊戌变法的时间尚短,知识分子思想上变法维新的希望还没有完全破灭,即便有一些人虽然没有赶上戊戌变法运动,但也受过改良思想的熏陶。然而,这些人尽管具有革命热情,但绝大多数尚处在由改良向革命转变的前夜。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中,一方面表现激进,如主张以暴力推翻旧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带有改良的色彩,如鼓吹地方自治,道德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们理解和宣传的社会主义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往往同一些不能相容的思想、观点和学说掺合在一起,从而不可避免地在自己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的各个部分之间,呈现出思想庞杂、瑕瑜互见的情况。与之相比,无论从其广度和深度来说都相差甚远。
尽管如此,但这种传介毕竟打破了局限于原原本本地翻译外国的著论的状态,开始了在中国的先进分子中间结合自己的思想认识来谈论社会主义的风气。这样,各种集团的思想家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所采取的态度趋于明朗,在中国是否应该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开始提出来了,社会主义学说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虽然还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意识,因而他们往往把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附在社会主义上面;但是,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总算在中国的思想界引起了反响。这种反响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普遍传播奠下了第一块基石。
收稿日期:2000-05-13
标签:梁启超论文; 康有为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法国启蒙运动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大同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傅立叶论文; 大同书论文; 新民丛报论文; 浙江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