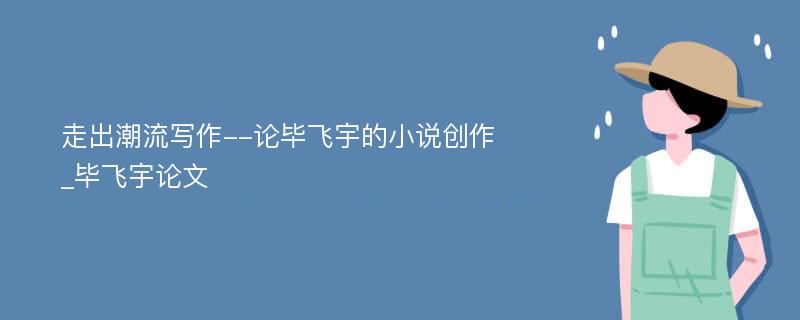
潮流外的写作——毕飞宇小说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潮流论文,小说论文,毕飞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毕飞宇从1991年在《花城》第1期上发表中篇处女作《孤岛》到2001年4月《人民文学 》推出其中篇力作《玉米》,他在小说创作道路上已经营了十个年头了。十年之间,毕 飞宇的生活几经变化,小说创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也“转了几个弯”:从最初狂热而执著 的历史叙事,转而对当下城市世俗生活的生动描摹,再到最近冷静客观的现实透视与社 会批判,毕飞宇经历了像蝉蜕一样难苦和令人振奋的艺术磨砺与突破。毕飞宇的创作基 本集中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而90年代引领文坛风骚的莫过于“新生代”小说群的兴起 。依据评论界对新生代作家的普遍界定,毕飞宇确实属于新生代作家,而且在已出版的 几种新生代或晚生代小说丛书中,都收录有毕飞宇的作品,但通观其创作,毕飞宇在题 材选择、主题确定、叙事方法及话语风格上却与新生代创作主流表现出了相当差异。而 且这种差异在他近期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大有与新生代这个称谓分道扬镳之势。
一
毕飞宇小说创作大体是在三个维度上展开的:一是对历史个人化的体验与传达;二是 对都市人生存环境与现状的观察与思考;三是对人性深层心理的挖掘与探视。“历史” 是毕飞宇早期小说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凭着对历史的偏爱,他用小说的艺术形 式对有关历史的话题做了大量深入的探讨与思考。这个过程延续得较长,从最初的《孤 岛》和随后的《祖宗》、《叙事》、《楚水》、《明天遥遥无期》等到1995年6月发表 的《是谁在深夜说话》,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话语在这些文本中四处流淌,它构建出 一个现代人对历史的深邃洞察和复杂情感。这可看作毕飞宇小说创作的最初阶段。
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敏感而慎重的话题。历史本身只是一种消逝了的存在,正因为这一 特性,历史的真实所指常常不为人所知。而强势话语的趁虚而入,使历史一向被当作真 理、规律、正义等的代名词。但是在《叙事》中,毕飞宇却通过对自己家族三代人血缘 关系地研究,轻而易举地揭穿了所谓的历史不过是一群人别有用心的叙事结果而已。“ 历史其实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兴之所至,无所不能。历史是即兴的,不是计划的” ,①(注:《叙事》:《收获》94.4)对历史的探寻,出人意料地竟动摇了人们长期以来 坚信不疑的常识。那么真实的历史又在哪里呢?就像奶奶在上海的神秘失踪一样,真实 的历史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理想和虚妄而已。在这篇小说中毕飞宇沿用了先锋小说以家庭 、性等原材料实施对历史解构的叙事策略,只是在小说意蕴上,理性的形而上的风格更 为突出。
在对历史进行话语解构并从中获得叙事快感时,毕飞宇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施展了一场 肆意的亵渎和语言狂欢表演。《明天遥遥无期》、《楚水》中书香门第的风雅文人在日 军入侵下显得多么孱弱,优雅的古典词牌名以一个个妓女放荡无耻的身体出现。其中的 颠覆意味不言而喻。随着对历史的深入掘进,毕飞宇对历史的态度也由先前哀切激愤地 揭露,变而为理智超脱地审视。《是谁在深夜说话》可谓毕飞宇历史叙事的一个代表作 ,也是他对此类写作的一个总结。小说中,哲学家最形而上的思考与妓女最形而下的物 质活动在黑夜中交织,相互补充又相互解构。建筑队对明城墙的修缮则进一步把这种对 立推向极致。“现在城墙复好如初,砖头们排列得合榫合缝、逻辑严密甚至比明代还要 完整,砖头怎么反而又多了出来?”②(注:《是谁在深夜说话》:《人民文学》,95.6 )历史的荒唐在此昭然若揭。毕飞宇的历史文本因历史本身的深厚博大与作家渴望穿越 历史迷雾和纷繁世相抵达通透澄明境界的主体精神特点而显出了一种深度与智慧之美。 但是,抽象的历史和理性的思辩从来不是文学的主业,加之90年代,后现代文化语境对 作家的选择,95年后,毕飞宇放弃了用小说对历史的直接叙写和形而上思考。但历史仍 以故事背景的方式时常出现在其小说中。如《武松打虎》、《白夜》、《手指与手枪》 、《阿木的婚事》、《怀念妹妹小青》、《蛐蛐,蛐蛐》、《玉米》等都选取了“文革 ”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作为故事时间。虽然新生代作家大多都如李冯所说是“文革童年, 高考少年,改革青年”,但毕飞宇表现出的超乎同时代人的强烈的“历史情结”和“文 革情结”却颇为独特。我以为除去先锋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对其的影响外,原因大致有三 :在他的小说和随谈中曾多次提到幼年父亲是下乡右派的事实,这大约极大地影响了他 的身心成长;另外,文革非常态的时代环境对于剖析人性、人心的隐秘世界是个得天独 厚的时期;三是毕飞宇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参与意识的作家。(这一点在后文会有专门 的论述。)“鉴古知今”“以史为鉴”或许正是毕飞宇追求的小说现实功能之一。
二
90年代文学经验的现实来源,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城市生活的经验,城市生活经验不仅 是90年代为文学传统注入的最为新鲜的血液,也是90年代标志性的写作方式。毕飞宇在 《九层电梯》、《卖胡琴的乡下人》、《生活边缘》等早期的文本中,就对现代城市生 活经验有相当的关注和描摹,随后《林红的假日》、《哥俩好》、《遥控》、《生活在 天上》、《睁大眼睛睡觉》等又对城市的生存处境和城市人的心灵有更为深入丰富的探 视。可以看出,毕飞宇沉迷于历史的同时,对当下社会最为活跃地城市生活图景也始终 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创作热情。
同样是写城市,但毕飞宇表现城市生活的切入点与邱华栋、何顿、韩东、朱文对城市 生活的处理明显不同,他更多的是以乡村和自然健康的人性为或潜或显的参照,观察、 思考在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可能对人的身心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因此, 城市在其笔下始终处于一个被观察、被审视的地位,他与城市之间也始终充满着一种紧 张感。当然这种紧张感的强弱前后有变化。
在毕飞宇对城市的书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城市的认识与情感态度有一个不 断发展深入的过程。早期小说《九层电梯》里女儿的宠物耶萝、布莱克的先后死去与女 儿令人心酸的乖顺在与“我”儿时乡村生活的对映下,寓示了城市生活对自然生命的围 困和压抑;《卖胡琴的乡下人》怀揣胡琴在风雪的城市中走街串巷的失意行程,则是对 城市中渐渐稀少的素朴优雅的古典情调的叹息和缅怀;《生活在天上》借助城市闯入者 的视角对城市进行了一番异己的打量。的确,城市的高速发展,不仅在城市景观、交通 、通讯等方面与乡土生活大异其趣,而且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也表现出对乡村 的某种背叛和抛弃。面对这种变化,毕飞宇在文本中流露出一种淡淡的隐忧与感伤色彩 ,对现代化的城市基本持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此后,在《遥控》中他又通过虚构一个 居住在公寓里身高一米七一,体重一百九且还在攀升的青年的日常生活,揭示出高科技 、现代化的物质,带给人全方位的体贴与照顾的同时,生命的体验性、丰富性正面临逐 渐被物替代和抽空的危险,并由此对都市日益加剧的物质化生活予以了尖刻的嘲讽和鄙 弃。虽然反讽的背后仍是无可奈何的痛惜,但反讽比感伤更为理智坚强,它不仅意味着 毕飞宇对城市生活的正视和对城市人生存状态的积极关照。也意味着他的城市叙事进入 了新的阶段。
尽管毕飞宇在小说中对商品化的城市里,金钱、物质的巨大刺激和腐蚀作用做了不遗 余力地揭露和批判,但他并未将自己的思考停留在城市发展带来的表层现象上,而是进 一步沉潜入人物内心,对城市人的意识、心理、感觉等层世界作了细致入微的剖析,这 也是现阶段城市文学发展的主要特点。中篇小说《哥俩好》通过殷家两代三人在乡村与 城市,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理智与情感之间的不同态度和选择,展示了城市对现 代人无以伦比的诱惑和同化力量,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灵分裂和精神悬浮。义无反顾地逃 离乡村背叛父志的图南图北,在城市的各种欲望中沉浮时,既未寻找到理想中的精神家 园,又永远地失去了乡村这块假想的灵魂栖息地。在此,毕飞宇已不再以城市边缘人的 身分打量城市,而是站在城市内部,设身处地为他的主人公感知城市的一切,真实地描 绘出现代人面临的生存困境。在《林红的假日》中他又将一个城市女性因刻板生活而迷 失本性的那种委屈、心疼、不甘、挣扎与徒然的心理过程,历历在目的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篇小说中毕飞宇将城市对人的影响日常化处理了,不再是那么突兀的情欲、物欲、 物化的尖锐对立,而以更为隐蔽地心理背景出现。我以为是值得高兴的事,因为它显示 出毕飞宇对城市生活的一种认同和正视态度。
在城市对人的物化中,“性”对人的物化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性与爱的分离甚 至对立在城市背景下上演得尤其剧烈。毕飞宇的性爱叙事对此也给予了足够关注。《孤 岛》中小河豚与旺猫的性爱单纯明净带有一种自然的原始的美;若冰与少兰疯狂而压抑 的性爱充满浪漫传奇色彩。性与爱相互渲染和谐一致是他们之所以动人的根本原因,但 这种古典时期的性爱形态在90年代的城市生活中已发生了某种分离与质变。乐果先迫于 经济窘况去做吧台小姐,到后来已分不清是被迫还是乐意为之(《家里乱了》)。新新人 类阿来最大的生活理想便是“每隔两三天摸一次麻将,每隔两三天享受一次稳定、持久 、高质量的性爱……这就是他的英特纳雄内尔。”此处阿来对于性的要求只是纯粹有益 身心健康的运动,丝毫没有更多有关道德情感的社会内容,二黑对于朋友夺走自己情人 无动于衷的反应,也表现出现代人对“性”前所未有的宽容和共享态度(《与阿来的二 十二天》)。即便有爱作基础的婚姻亦莫不如此。《故地》中推销员阿海与妻子梅朵两 年多的婚姻关系概括起来很简单——“不是他睡她,就是她睡他。”爱情不过是性的幌 子与美丽的外衣,它早已退化为一种策略和技巧,目标直指赤裸裸的性。“身体是爱情 的头号天敌”毕飞宇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喟叹。这的确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物质时代。性在 毕飞宇小说中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形态。它不仅承担着小说意义的言说功能,还常常作为 一种叙事元素和情节动力,完成小说文本的虚构。
毕飞宇对城市始终保持高度的清醒和理智,这不仅是他人性关怀信念下的必然结果, 也是一个习惯思考具有批判意识的作家的本色所为。他的城市叙事因其是对当下生活近 距离地书写,文本里充盈着许多感性的文字,叙述语调也轻松、机智还不时露出一丝幽 默。情节与故事也更落到实处,极富生活气息。他在城市文本中对世俗生活的描写也使 他前期作为“感性的形而上者”的形象得以补充与丰富。
三
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城市叙事,毕飞宇都对其中的人物性格和心理流露出强烈的探究 和表现的兴趣。特别是特定情景中的人物的特殊心理他更是着迷。对人物心理地耐心解 剖与展示,对其深层意识的细微体察,是毕飞宇出色的文学才能最淋漓尽致的体现,也 是他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
毕飞宇从一开始创作就显示了他在人物心理刻画方面卓越的艺术潜能。近期,《青衣 》、《玉米》颇受好评正是得益于他在这方面不懈地努力与积累。十年里他塑造的人物 不算少,若把他们集拢来,反复揣摩、体味,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人物的性格有某种 暗合之处。他们的心理在自身或外部的挤压和影响下,都处于一种压抑或缺失状态,并 由此不同程度的带上偏执、焦虑或疯狂的情绪。林康出游时没头没脑的怒吼是对自己在 前夫与现任丈夫之间尴尬心理的发泄(《五月九日和十日》);蓝田女人事隔多年后唐突 地向剃头师傅念叨“我就是展玉蓉。”是其潜意识里长期对豆腐西施展玉容艳羡与模仿 的曲折流露(《充满瓷器的时代》);若冰与少兰热烈而忧伤的偷情,是对名不符实的婚 姻的变相补偿(《明天遥遥无期》);小铃铛对弟弟血淋淋地残害是失宠后恶意的报复( 《生活边缘》);惠嫂母性勃发,林红蓄意出逃,图北对父兄的背叛等等,无一不是某 种性格心理近似疯狂的体现。这些人物身上有着旺盛的本能的生命力,在“疯狂”的举 动中释放出生命的强大意志,他们虽然沉默、不张扬,却并不软弱,萎琐,他们身上有 一种恣意的单纯性格之美和撼动人心的不经修饰与掩藏的朴素品格。
《青衣》与《玉米》即是这方面的佳作。《青衣》讲述了一个人与一出戏的命运。“ 化上妆这个世界就没有了,你不再是你,她不再是她……她现在不是自己,是另一个女 人,嫦娥。”筱燕秋现实世界里的种种失意,在穿上戏服站在戏台上时消失了,剩下的 全是演戏的痛快淋漓。结尾处筱燕秋雪夜街头边走边唱的痴态令人心酸,也令人叹服。 她以不顾一切地投入与执迷不悟见证着艺术、理想、人生的美好境界和人性的强大、不 可屈服。这注定是一种悲剧性格,一出悲剧人生。但它却正因为触及了人们心中对于传 统的优美、执着品性的温暖的回忆而显得卓尔不群。
《玉米》中的主人公玉米,在性格上仍继承了毕飞宇小说人物特有的压抑、执拗、疯 狂的心理模式。十四岁的玉米,在经历了父亲官败带来的种种牵连后,咬着牙让父亲给 她另说一个“手里要有权”的人,但是当她和人武干部郭家兴躺在床上,听着他告诉自 己其妻尚在病中还未过世时,却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筱燕秋、玉米的结局的确令人扼腕 ,她们如此执着于一个目标,拼其所有不顾后果奋力争取的所作所为,使读者感受到了 90年代文学少有的悲剧品格和悲剧震撼人心的力量。当通俗文学、流行文化以隔靴搔痒 的方式触及人们的生活和心灵,当新生代小说淹没于生活之流,随遇而安奉行相对主义 的处世哲学时,毕飞宇却以强悍率真的主人公对当下灰色生活表示了一种阻击和对抗。 姑且不论他们为之奋争的是否有意义有价值,这都给看惯了当下大多数新生代小说中那 些在现实的压力下变得圆滑而且麻木冷漠的灰色人物的读者,展现了生命与生俱来的鲜 活滚烫渴望圆满的一面。毕飞宇的小说总有一种尖锐的力量感,这样的阅读效果与其小 说人物的这种性格有不少关系。毕飞宇的人物不以丰富见长,而以人物性格的深度和强 度见长。
毕飞宇在《玉米》中对“官本位”意识的批判,在创作谈《我们身的鬼》中有更为直 接地阐释:“我们身上那个‘人在人上的鬼’……不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于平民、 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上。”③(注:《 小说选刊》:2000.6)这样有明确社会指向的话语不仅是毕飞宇多年来持有的知识分子 参与社会批判社会的精神的一次集中爆发,也是其在个人化日常化叙事占据文坛主流的 今天一次特立独行地表演。其实毕飞宇身上知识分子的气质一直很浓。早在《歪说李商 隐》的作家絮语中,就曾一面肯定李商隐的诗作成就,一面对其“缺少一种——用今天 的话来说——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与人格魅力”甚为不屑,并进一步发出这样的诘问“ 然而,一个诗人,除了做个诗人之外,真的可以什么都不是么?”④(注:《歪说李商隐 》:《小说家》95.5)这股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批判冲动经常成为其写作时的内在动 力,并在作品中酝酿出厚重的社会底蕴。这也是毕飞宇作品内容不显单薄的一个重要原 因。《孤岛》中权力的血腥争夺;《哺乳期的女人》中断桥镇狭隘的习惯势力;《武 松打虎》中队长不动声色的权威;《好的故事》里人心的自私与卑琐;《蛐蛐、蛐蛐》 中“九次”死而不已的威风,都使读者感受到了毕飞宇的用心所在。他的历史叙事之所 以持续那么长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亦是这种现实参与冲动的结果。尽管个体生命而今拥 有绝对不容置否的地位,但文学若不加区别地合谋似的对某些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加以 拒斥,这是作家的遗憾,也是文学功能萎缩的表现。因此放开视野面对现实,关注更广 大的人群,重提作家的批判意识,非但不显得“旧”,而且对于建立文学的公共话语空 间十分必要。
这样的写作定位和价值立场明显使毕飞宇与新生代主流创作拉开了距离,也是他独立 的艺术个性最有魅力的体现。毕飞宇以社会批判为主旨的创作在近来有增强之势,我们 不必担心他会落入空洞的宏大叙事的窠臼中,毕飞宇的笔感性而丰盈,他知道该以怎样 的方式切入他的写作中心。
四
与对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审视态度及作者理性的创作个性相适应,毕飞宇在叙述角度上 基本都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视角,这种视角在赋予叙述人一种开阔自由的运笔空间的同 时,也为作家和叙述者介入小说提供了某种便利。如果叙述人的声音过于强烈,势必会 破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愉悦感。这种状况在毕飞宇早期的历史叙事中表现得颇为 明显。所幸的是这一现象在毕飞宇的城市叙事和其他小说中有很大改观。他的小说故事 一般较为完整,情节的因果逻辑清晰,喜欢采用一些典型的情节和寓言似的深度叙述模 式,叙事话语也较为规整。基本可归入现实主义的创作落畴。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毕飞 宇小说的叙述人几乎都很敏锐和机警,叙事态度也出奇得冷静节制和内敛。最有代表性 的当推《怀念妹妹小青》、《蛐蛐、蛐蛐》等。
毕飞宇对小说语言一直有非常自觉的艺术追求,大约他在语言上花费的功夫绝不亚于 他在小说建构方面的功夫。在他看来,语言不仅是实用的,更是审美的。他的小说语言 首先是简洁、炼达。简洁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功力。因此,毕飞宇十分爱惜自己的笔 墨,倾心三笔二笔就见筋见骨、见精见神的传情达意的写作方式。特别是近年发表的小 说对文字的吝啬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力求“简洁”,毕飞宇爱用短俏的句式 ,干净利落的叙述口吻,这样一来,文字就有了金属般峭利的质感。在句与句之间的停 顿转折处却又意蕴丛生。的确,在新生代作家中毕飞于小说语言的中国色彩、文人气质 最浓。
虽然在语言的使用上毕飞宇力求简省,但文笔却并不枯涩。“大街上纷乱如麻,只有 冬雨下得格外认真,他们一丝不苟”。⑤(注:《婶娘弥留之际》)“阗静而又柔和的雪 夜里,响了玻璃破碎声,突兀、揪心、纷乱而又悠扬。”⑥(注:《白夜》:《钟山》9 5.6)像这样丰润而富于情味的句子在毕飞宇小说中并不少见。“周作人只是从故事的周 围绕了一圈,给了作品一种氛围或笼罩,这笼罩便罩住了我们的某个痛处,而痛便弥漫 了,无声无息,你找不到伤口在哪儿,故事完了。”⑦(注:《“硬说”周作人的“小 说”》:《作家》97.5)毕飞宇对周作人散文《初恋》小说式地解读,流露出他对情境 小说的心仪。因此在他早期的创作中我们多能读到一种诗意的东西。而这种诗意的东西 ,又常常借助意象化的方式散发出来:乡村雪夜白得发蓝的雪光(《白夜》);漫山遍野 如生命一样热烈火红的枸杞子(《枸杞子》);纯洁清新的栀子花香(《那个男孩是我》) ;风雪中悠扬凄伤的胡琴声(《卖胡琴的乡下人》)等莫不如此。意象化地处理增强了小 说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但同时也存在一个问题。小说毕竟是叙事的艺术。对小说意 境的过度看重会使小说在文体上发生变质。如把《婶娘弥留之际》、《白夜》、《哺乳 期的女人》、《是谁在深夜说话》等早期小说当作散文来读也未尝不可。毕飞宇随后也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弊病,于是在后期创作中刻意加强小说写实力度,在故事上狠下功 夫,《玉米》中,读者显然留心到毕飞宇将小说的叙事功能凸显到了第一位。
毕飞宇的创作才华因其选择了独立于潮流外的写作方式而迟至今日才引起了读者和批 评界的广泛关注,但这正证明了他是一位不趋时媚俗,执着于自己的创作个性的实力型 作家。写作作为他生活中与足球、音乐并列的三大快乐之一,相信他会坚定的继续下去 。而且以其严谨的创作态度,人物心理挖掘的出色才能,叙事节奏和语言上的良好感觉 我们有理由对他今后的创作寄予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