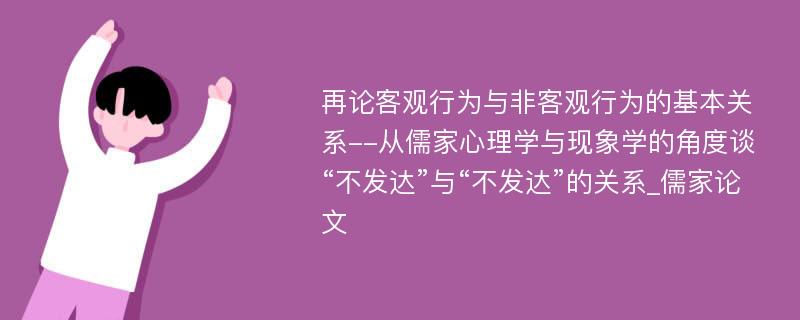
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的奠基关系再论——从儒家心学与现象学的角度看“未发”与“已发”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体论文,儒家论文,关系论文,现象学论文,角度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笔者在现象学与唯识学关于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关系的讨论方面,曾做过初步思考。(参见倪梁康,2008年,第80-87页)最近在翻译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一书时,受其讨论的心性现象学诸问题之启示,试图对该书中相关论述的脉络做一大致的梳理和可能的补充,同时也尝试着继续在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关系的标题下做另一方向的展开,即发掘和探讨在儒家心学中蕴含的对意识结构的分析把握与在心识发生方面的解释说明。
一、引论
如所周知,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进行的现象学早期意识分析工作已经清楚地表明:构造意识对象的是客体化行为,它们主要与意识的分辨活动与认知活动相关,如感知、想象、判断等行为;非客体化行为主要与意识的意愿活动与情感活动相关,它们并非是指没有客体、没有对象的意识行为——因为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意识都是指向对象的——而是指这样一些类型的意识行为,例如欲求、好恶、爱恨、同情等行为,它们本身不能原本地构造对象,因而只能以客体化行为所构造的对象为自己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非客体化行为是奠基在客体化行为之上的,即是说,情感行为需要以表象或认知行为作为自己的基础。与此几乎等值、但仍须进一步论证的命题就是:伦理活动以认知活动为其基础;实践活动以理论活动为其基础。
这个合乎欧洲哲学从古典到近代的思想传统的基本命题,在佛教唯识学的传统中可以找到知音与和声,然而在具有悠久心性学传统的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却很难引起共鸣。尤其是儒家心学,从一开始讨论的就是作为道德情感的“心”、“意”和“良知”。在唯识学那里得到强调的作为“了别”的“识”,在儒家传统中即使偶有涉及,也始终处在派生和次要的地位。中国哲学的思想传统,尤其是儒家心学,即使不是反认识论的,也是非认识论的。关于认知行为的讨论在中国哲学的思想脉络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也几乎被忽略不计。中国思想传统中没有认识论的历史,唯识学进入中土之后的发展实际上也是断多续少。
但是,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却可以发现忽隐忽现的超越论的不断延续的路径,首先是在儒家的心学传统中,同样也在佛教于中国的接受与发展的历史中,当然也可以在道家的心性论中。“超越论”在这里是指在反思的目光中对本己心性(心的本质)进行把握的学说;它既是康德意义上的、也是胡塞尔意义上的“超越论”①。这种学说之所以是“超越论”而不是“认识论”,乃是因为它仅仅以反思或反省的方式关注非客体化的情绪、情感、意愿的能力与活动,却不将客体化的表象、判断的认识能力与行为当作自己的主要探讨课题。与这种“超越论的”目光密切相关的,是儒家心学在“正心”、“修心”、“养心”、“明心”、“涤心”、“存心”、“放心”、“尽心”等方面的“工夫论”实践活动。
笔者在此所要讨论的正是儒家意义上的非客体化的情绪、情感、意愿等心性现象,以及与此相应的工夫或修持方法。
二、儒家传统中的“未发、已发”以及相应的修持工夫
儒家经典《中庸》的第一章中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之说。宋明理学家对此有诸多讨论。其中的“未发”与“已发”可以被理解为对两种心理状态的描述:“未发”是指情感活动尚未发生的心理状态,“已发”则是指情感活动已经发生的心理状态。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是《中庸》第一章中的另外一句。它可以视作对修行者提出的一个要求:对“不闻不睹”保持“戒慎恐惧”,也就是在自己不看与不听、即王阳明所说的“无思无为”(参见《王阳明全集》卷三,第63页)时,也保持警惕谨慎。②这里的“闻睹”,原则上应当理解为心的感知或表象活动与判断活动,当然也可以包括由感知或表象引起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行为。
将这两句联系在一起思考,我们可以将“不闻不睹”视作一种“未发”。在此意义上,“未发”不仅是指任何情感行为的尚未发生,而且也是指任何感知行为的尚未发生。而能否将“未发”进一步理解为任何意愿萌动的尚未发生,这个问题则要留待后面再作讨论。③
因此,我们在这里事实上已经面对三种心理状态:第一种是“未发”,即情感、表象、思维尚未发生的状态。用现象学的术语可以将它称作“前客体化行为”的状态,亦即“客体化行为未发”的状态。胡塞尔也会将它称作“前意向的”或“前现象的”状态。而第二种和第三种都是“已发”,即各种行为已经发生的状态。但这里主要有两种行为,其一是“客体化行为”,即作为“闻睹”、“思为”的各种意向表象行为;其二是“后客体化行为”,即各种作为“喜怒哀乐”的意向情感活动。后者之所以可被称作“后客体化行为”,是因为“喜怒哀乐”的情感活动如前所述必须奠基于“闻睹”的表象活动之上。所谓“奠基”关系是指,如果在A与B的关系中,A的存在与发生不需要以B的存在与发生为前提,而B的存在与发生却必须以A的存在与发生为前提,那么在A与B的关系中,A便是奠基性的,而B则是被奠基的。并非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而是在逻辑的奠基顺序上,必须首先有表象活动或客体化行为构造出各种对象或客体,而后才可能有对这些客体的喜怒哀乐情感产生。
宋明儒学家对“未发、已发”有诸多讨论,笔者这里主要关注朱熹与阳明学派的相关思想。首先是对“未发”与“已发”的理解,其次是对“中”与“和”的理解。前者涉及本体论,后者涉及工夫论。除了前面提到的“不睹不闻”与“戒慎恐惧”的解释之外,与此相关的本体论概念还有:心-性、体-用、静-动、寂-感、心-意、性-情、良知、念,等等,以及工夫论概念:涵养、体认、敬、定、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致良知,等等。事实上,对“未发”的理解,即对各种情感产生前的“心”是什么以及处于何种状态的理解,是整个问题的关键。这个理解基本规定着对“已发”的解释以及相应的工夫实践的理解。
朱熹最初从他的老师李侗那里了解到从二程、杨时、罗从彦传承而来的“以主静为宗”的修养论,即“于静中体认大本”的静养思想。由于《中庸》第一章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因此,“于静中体认大本”也就意味着:“未发之中”要通过静养来达到。李侗将“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理解为一种“气象”,并将相应的工夫称作“默坐澄心”,亦即“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宋史》卷四百二十八,第12746页)。虽然朱熹当时并未理解和认同这种学说,但他后来在其中和“新说”中还是对这个观点有所接纳和发展。
以后在胡宏与张栻的影响下,朱熹首先将“未发”理解为“性”,将“已发”理解为“心”,即提出所谓“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第3130页)易言之,情感未发生的状态被理解为“本性”或“天性”,而情感已发生的状态被理解为“心理活动”。与之相对应的伦理工夫或修养,要么是对道德心理活动的察觉、认识和纠正,即“省察已发”,要么是对“本性”或“天机”的领悟、把握与滋养,即“体验未发”。由于“本性”是由“天命”规定的,即《中庸》第一章第一句中所说的“天命之谓性”,因而修身的工夫理当更多运用在对当下行为的省察克制上。
但朱熹随后不久便在“未发、已发”的理解上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从而将上述观点称为“中和旧说”。他提出:“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反之为已发。(同上,第3130-3131页)他将“心”理解为“性”与“情”两种状态的统一或主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性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情也。子思之为此言,欲学者于此识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情性之德者欤。”(同上,第二十一册,第1403页)这里的“性”,不再是指“天命”,而更多是指一种未现实化的能力或性质。这也就意味着,“未发”和“已发”都是心的状态:前者是表象、思虑、情感未发生的阶段或可能性,后者是它们已经发生的阶段或现实性;或者也可以说:前者是心的前客体化行为阶段,后者是客体化行为阶段。朱熹于此倡导作为伦理工夫的“敬”,并认为要将它落实在这两个方面,因为,“何者为心?只是个敬。”“只敬,则心便一。”“无事时敬在里面,有事时敬在事上。有事无事,吾之敬未尝间断也。”(《朱子语类》卷十二,第209、210、213页)即是说,朱熹最终主张无论在“未发”还是在“已发”的阶段上,都要修持伦理的工夫:“敬在里面”为“涵养”,“敬在事上”为“察识”。就总体而言,朱熹在工夫论上重涵养甚于重察识,因此在“中和新说”中以其特有方式最终回到李侗等人“主静”的立场上。
三、王阳明的“致良知”及其所理解的“未发、已发”
王阳明倡导“致良知”,以“良知”为本体,以“致”为工夫。他在总体上主张“体用一源”、“无分动静”、“中和一也”,因而他原则上既不愿意同意朱熹的“中和旧说”,也不愿意完全附和朱熹的“中和新说”。他在“答陆原静书”中说:“‘未发之中’即良知也,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有事无事,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有事无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寂然感通也。动静者所遇之时,心之本体固无分于动静也。理无动者也,动即为欲,循理则虽酬酢万变而未尝动也;从欲则虽槁心一念而未尝静也。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动,然而寂然者未尝有增也。无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静,然而感通者未尝有减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又何疑乎?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则至诚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发在已发之中,而已发之中未尝别有未发者在;已发在未发之中,而未发之中未尝别有已发者存;是未尝无动静,而不可以动静分者也。”(《王阳明全集》卷二,第64页)因此,王阳明虽然用“体用”的概念来解释“未发、已发”,但同时强调“体用一源”,即“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者矣”(同上,卷四,第146页),“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同上,卷二,第17页)
与此一致,王阳明所提出的“致良知”学说既不偏重“未发”,也不偏重“已发”。他批评说:“只缘后儒将未发已发分说了,只得劈头说个无未发已发,使人自思得之。若说有个已发未发,听者依旧落在后儒见解。若真见得无未发已发,说个有未发已发,原不妨原有个未发已发在。”(同上,卷三,第115页)他在工夫论上也要求“惟精惟一”,主张“中和一也”。即是说,“未发之中”与“已发之和”,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中和是离不得底。如面前火之本体是中,火之照物处便是和。举着火,其光便自照物。火与照如何离得?故中和一也。近儒亦有以戒惧即是慎独,非两事者。然不知此以致和即便以致中也。”(同上,卷三十二,第1174页)这里所说的“后儒”与“近儒”,基本上是针对朱熹及其学派追随者而言。
王阳明对“不睹不闻”与“戒慎恐惧”的解释也强调本体与工夫的统一。既可以将“不睹不闻”理解为本体,也可以将“戒慎恐惧”理解为本体;反过来,既可以将“不睹不闻”理解为工夫,也可以将“戒慎恐惧”理解为工夫。例如他曾说:“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同上,卷三,第123页)但他同样也说:“此处须信得本体原是不睹不闻的,亦原是戒慎恐惧的。戒慎恐惧,不曾在不睹不闻上加得些子。见得真时,便谓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功夫,亦得。”(同上,第105页)
这里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被推进了一步:用“未发”或“不闻不睹”来描述心体,只是表明心体不是什么,即不睹不闻、无思无为;但如果用“戒慎恐惧”来描述心体,性质则完全不同。这个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果心体是“戒慎恐惧”,那么“戒慎恐惧”当然不是闻睹、思为,但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活动或心理状态呢?
《传习录》中记载:有人问:“当自有无念时否?”王阳明回答说:“实无无念时。”再问:“如此却如何言静?”再答:“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戒谨恐惧即是念,何分动静?”又问:“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又答:“无欲故静,是‘静亦定,动亦定’的‘定’字,主其本体也。戒惧之念是活泼泼地。此是天机不息处,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体之念,即是私念。”(同上,第91页)按照这个说法,王阳明不认为人在清醒状态下有全然无念(无意念)的时刻。“未发”只是喜怒哀乐的情感与闻睹的表象没有发生,并非完全没有任何心理活动发生。“静”乃是指情感与表象的不生起和不活动。即使在“未发”时,也有“戒谨恐惧”,而且这种“戒谨恐惧”是一种“念”,即“意念”或“念想”。它是“本体之念”而非“私念”。
事实上,类似的说法在朱熹那里也可以找到,他曾说:“人心无不思虑之理。”(《朱子语类》卷十二,第206页)“静坐而不能遣思虑,便是静坐时不曾敬。”(同上,第214页)“当静坐涵养时,正要体察思绎道理,只此便是涵养,不是说唤醒提撕,将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时,自然邪念不作。”(同上,第217页)因此,即便是“主静”的朱熹,也认为“静坐涵养”不是全然无思虑、无体察思绎。这里“静”的是邪念,“动”的是思虑、思绎、思量。即是说,即使在静坐、无事时,“敬”的心思仍然是存在的、活动的。
四、阳明后学对“未发、已发”的理解和讨论
在王阳明的弟子那里,王阳明和朱熹的这些心学思想仍然在起作用。我们至此已经看到,借助于儒家心学的论述,至少可以分别出三类不同的意识活动或“心思”类型:(1)“闻睹”一类的对象性表象或客体化行为,它们构造意识行为的对象并为情感行为奠定基础;(2)“喜怒哀乐”一类的情感行为,它们本身不是对象性的和客体化的,但因为奠基于“闻睹”一类的表象行为之上,因而本身也是有对象的和有客体的;(3)“念”一类在上述两类行为尚未发生时的意识活动,王阳明将它称作“本体之念”,朱熹将它称作“体察”或“思虑、思绎、思量”,后面我们还会看到,欧阳德用“意”来标示它。
第三类行为有对象或客体吗?它与前两类客体化的行为有何分别?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样一种意识活动,并非指心的全然寂静,而只是指“无欲”或无“私念”的“静”(王阳明),或者说,是“无事”或无“邪念”的“敬”(朱熹)。如果我们将“欲”或“事”理解为对客体的诉求与交涉,那么这里的“本体之念”就应当是非客体化的意识活动。但对这个假设还要借助阳明后学的讨论来做出更进一步的推敲。笔者这里主要关注在王畿与聂豹、聂豹与欧阳德、罗洪先与王畿之间与此问题相关的分歧与论辩。
王畿和聂豹在对王阳明的“致良知”问题的各自理解上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接受宋儒邵雍根据《易经》“先天、后天”说法所提出“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用它们来标示两种“致良知”的方法。用这里讨论的问题来标示:“先天之学”在他们那里相当于“未发之学”,“后天之学”相当于“已发之学”。④王畿一再强调:“正心,先天之学也;诚意,后天之学也。”(《王畿集》卷十,第10页;卷十六,第445页)但他在总体上偏重于先天上的工夫,认为先天与“良知”有关,后天与“知识”有关,得到“良知”便得到“中和”:“良知者,本心之明,不由学虑而得,先天之学也。知识则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假于多学亿中之助而已,入于后天矣。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发而中节之和,此是千圣斩关第一义,所谓无前后内外、浑然一体者也。”(同上,卷六,第130页)他也认可后天之学,只是认为它“繁难”:“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便是先天易简之学。原宪克伐怨欲不行,便是后天繁难之学。”(同上,卷十,第10页;卷十六,第445页)他将“先天之学”称作“天机”,并主张通过“顿悟”来把握它。(同上,卷七,第154页;卷十四,第393页)
聂豹也将“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理解为“未发”的“良知”与“已发”的“知识”,也注重“先天”方面的工夫,但他并不像王畿那样认为它简易直截,而是强调对先天心体的专心的“养”:“先天之学,即养于未发之豫。豫则命由我立,道由我出,万物皆备于我。”(《聂豹集》卷十一,第375-376页)他批评王畿将“良知”视为从一开始就“现成的”、“具足的”,因而忽略“致良知”的方法和工夫,“坐享其不学不虑之成,难矣!”(同上,第379页)聂豹本人主张通过“静坐”或“归寂”来存养良知,亦即偏重于在“未发”中的沉浸:“不睹不闻者,其则也,戒惧者,其功也。不关道理,不属意念,无而神,有而化,其殆天地之心,位育由之,以命焉者也。”(同上,卷十三,第534页)
欧阳德并不赞成聂豹在致良知方法上对“静”与“动”的区分以及对“未发”的偏重。他依据王阳明的主张反驳聂豹说,实际上未发已发、动静寂感是不能分的,因此在工夫上也不能做相应的划分:“夫喜怒哀乐,本无未发之时,即思虑不生,安闲恬静,虚融澹泊,亦有可名,名之曰乐。故未发非时也,言乎知之体也;喜怒哀乐之发,知之用也。”(《欧阳德集》卷五,第187页)即是说,“未发”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时间段,而只是心体的一种专一状态:“体用一原,显微无间。非时寂时感,而有未感以前,别为未发之时。盖虽诸念悉泯,而兢业中存,即惧意也,即发也。虽忧患不作而恬静自如,即乐意也,即发也。”(同上,卷四,第125页)欧阳德在这两句引文中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主张“未发”虽然是一种思虑不生、无客体化情感行为进行的状态,但并不是没有任何情感活动存在。“安闲恬静、虚融澹泊”就是在“未发”状态中存在的“情感”。他也将它称作“惧意”或“乐意”。因此,如果我们将“情感”视作有对象的,那么这种无客体的、非对象性的“惧意”或“乐意”也许应当被称作“情绪”或“心态”。⑤
这种“情绪”或“心态”的最主要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没有意识对象的意识。对此,在许多方面站在聂豹一边的罗洪先似乎给出了一种用来支持欧阳德所说的那种没有意识对象的意识或意念的解释。他认为,在“静坐”中的心绪可以用“视于无形,听于无声”来描述:“人情事物感应之于知,犹色之于视,声之于听也。谓视不离色,固有视于无形者,是犹有未尽矣。而曰‘色即为视之体,无色则无视也’,可乎?谓听不离声,固有听于无声者,是犹有未尽矣,而曰‘声即为听之体,无声则无听也’,可乎?”(《罗洪先集》卷三,第74页)
耿宁在其近著中特别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他的理解:“罗洪先用这个出自《礼记》的‘视于无形者、听于无声者’之表达所意指的究竟是什么?或许他是指一种在其视野中根本没有任何事物和形体凸显出来的看的活动,一种对全然黑暗的看,或者是一种对其它无分别的视域的看?他指的是一种集中在寂静上的听?如果这样,那么罗洪先用此‘视于无形者、听于无声者’的比喻所指的就是一种清醒的、然而没有对象的意识,亦即在‘静’的沉思实践中或在禅定中所追求的那种意识。”他认为:“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意识,大概它不会使意向性概念成为多余,但会赋予它以一个新的含义。”(Kern,S.788)
五、两种基本的道德意识与修行方法
回顾以上的讨论,我们已经至少涉及两种道德意识:第一种是作为“未发”的非对象的、无客体的道德意识。严格说来,一方面,它是一种“本原意识”,可以被称作“良知”,但不算是道德意识,因为在这个意识阶段上尚无善恶的分别;另一方面,它也不能被称作“意识”,因为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如前所述,王阳明将其称作“念” (“本体之念”或“私念”),欧阳德将其称作“意”(“惧意”或“乐意”),而罗洪先将它刻画为“视于无形、听于无声”。朱熹也曾谈及类似意义上的“听于无声,视于无形”。曾有人问朱熹:“‘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或问》中引‘听于无声,视于无形’,如何?”他回答说:“不呼唤时不见,时常准备着。”问者指着坐的地方又问:“此处便是耳目所睹闻,隔窗便是不睹也。”朱熹回答:“不然。只谓照管所不到,念虑所不及处。正如防贼相似,须尽塞其来路。”(《朱子语类》卷六十二,第1505页)王阳明也有类似的说法:“手指有见有不见,尔之见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骛,不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功。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实落处。久久成熟后,则不须著力,不待防检,而真性自不息矣。岂以在外者之闻见为累哉!”(《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22-123页)朱熹所说的“照管所不到,念虑所不及”和王阳明所说的“睹其所不睹,闻其所不闻”,都是这个意义上的无对象的道德意念活动。
这些说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谈到的基本情绪“畏”(Angst)或“烦”(Sorge)。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基本情绪是无对象的,而且是比意向性的意识体验(即客体化的表象行为与情感行为)更为原本的和本真的。⑥后来他所说的“无所期待的等待”(Heidegger,S.217),也可以做此方向的理解。这种意念也会令人联想到佛教唯识学中作为初能变的“阿赖耶识”和作为二能变的“末那识”。它们都是在作为三能变的前六识(即对象意识)产生前的心识活动。(参见倪梁康,2008年)
朱熹与阳明学派谈到的另一种道德意识是作为“已发”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因为奠基于表象之上,因此是指向或针对具体的对象或客体的,它属于意向的道德意识。王阳明也曾常常谈到这种道德意识。例如《传习录》记载:一友自叹:“私意萌时,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王阳明回答说:“你萌时这一知处,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23页)这里的“知”,就是指这个意义上的道德意识。耿宁将这个意义上的道德意识视为王阳明的第二个“良知”概念:在道德上直接意识到自己思想、语言、行为(意、语、身)的善恶,或者简言之:道德自证分。⑦
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在于:这个意义上的道德意识是否与舍勒所说的“伦常明察”(sittliche Einsicht)相一致?或者是否与孟子意义上的“是非之心”相一致?以及这个意义上的道德意识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合乎理性的道德反省与道德判断是否有根本区别?以及有何种根本区别?
但这里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相对于以上所说的两种道德意识,即作为“未发”的和作为“已发”的道德活动,王阳明已经指出两种不同的工夫或修行方法:“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此正《中庸》‘戒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同上,卷二,第66页)如前所述,朱熹也已经以他的方式继承了这个儒家双重工夫的传统:“体验未发”与“省察已发”,或者:“无事时敬在里面,有事时敬在事上。有事无事,吾之敬未尝间断也”。 (《朱子语类》卷十二,第209、210、213页)
笔者在这里主要关注朱熹与阳明学派在“未发、已发”问题上共同的本体论理解和工夫论理解,至于朱熹与王阳明之间以及王阳明学派内部存在的各种分歧,则被有意地搁置了起来。因为,这涉及对“未发、已发”(非客体化行为与客体化行为)之间两种基本关系的理解:究竟是对它们做发生上的、时间上的理解,还是做结构上的、逻辑上的理解;这个差异在现象学内部也存在,无论是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舍勒之间,还是在胡塞尔自己的早期和后期思想之间。当然,这是另一篇文章所要讨论的课题。
六、感言而非结语
本文对前人思想的理解与分析,都是在概念文字中进行的;无论是在东方的语言传统中,还是在西方的语言传统中。它们显然只能以现象学的描述分析或解释学的发生说明的方式处理本体论的问题,而无力和无权去谈论工夫论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关于工夫论的语言文字讨论都是哗众取宠的,因而都是无工夫的。
王阳明曾有言:“用功到精处,愈着不得言语,说理愈难。若着意在精微上,全体功夫反蔽泥了。”(《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15页)王畿也说:“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复欲因言以求其精微之蕴,抑又远矣。”(《王畿集》卷六,第778页;参见卷四,第734页)
此处显然会产生出有关笔者这里的工作是否合法的问题:如果道德意识方面的“学证”与“修证”不能达到一致,那么通过文字理解与分析来进行的学证究竟有何必要?
牟宗三对此问题似乎早有思考。他在撰写《心体与性体》时谈及王畿的三个层次的悟道:解悟、证悟、彻悟。(同上,卷十七,第494-495页)“解悟”属于“从言而入者”。牟宗三谦虚,甚至说他自己“今且未及言悟”,而是只从语言文字做“客观了解”。“了解”在他那里又有三个层次的康德式分别:感性、知性、理性。最高层次的理性了解对他来说是“会而通之,得其系统之原委”。(牟宗三,第1页)
笔者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借助语言文字进行的“理性了解”,以期达到“会而通之”的目标。耿宁所坚持的一种写作态度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个意义上的哲学家的工作态度,笔者愿意在此予以引述:“我在这里听凭一个直接的明见(直观)的引导,并且试图将它用某些语词表达出来并澄清它,以便能够诉之于读者的相应的明见。我对直接明见的信任要甚于对语言使用的信任,并且我试着在后者中指明前者。”(耿宁,第10页)
注释:
①胡塞尔在为《论〈觉者乔达摩语录〉》写的书评以及他的手稿“苏格拉底-佛陀”中,将佛教思想称作“超越论的(transzendental)而非超越的(transzendent)”,因为同样对于佛教而言,“世界仅仅是主体性中的现象”。(参见《唯识研究》第1辑,第36-154页,尤其是第136、150页)
②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别人看不见自己和听不见自己时也保持警惕谨慎。这个解释与《中庸》“君子慎其独”的要求相似。但这里不再进一步考虑这种解释的可能性。
③这个问题意味着:我们能否将“未发”理解为任何一种在康德意义上的“知、情、意”心理活动的尚未发生。
④王畿也说:“未发先天之学”。(《王畿集》卷十,第262页)
⑤这会让人联想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谈及的“基本情绪”问题。对此笔者会在下一节讨论。
⑥关于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对生存分析与意向分析之间关系的理解,可以参见笔者《现象学背景中的意向性问题》。(倪梁康,2007年,第165-167页)耿宁用“一种对本已此在的主动或被动的情绪”(Stimmung oder Gestimmtheit)来定义它(cf.Kern,S.563),不知是否与上述关于海德格尔的联想相关。
⑦耿宁区分王阳明所说“良知”的三个不同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心理-素质的概念”,第二个概念是“道德-批判(区分)的概念”,第三个概念是“宗教-神灵的概念”。(ibid,kap.1—3)
标签:儒家论文; 王阳明论文; 王阳明全集论文; 心学论文; 现象学论文; 读书论文; 朱熹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国学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致良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