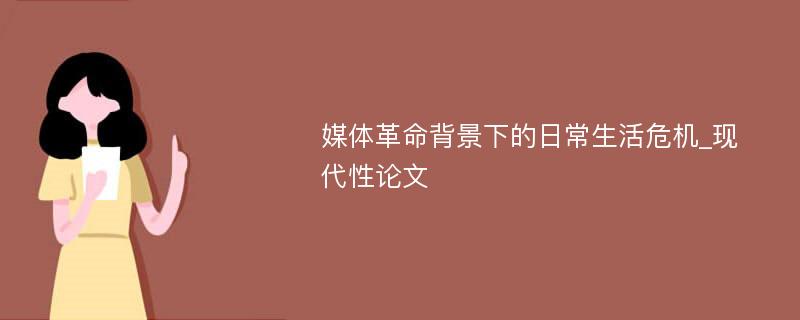
媒体革命语境中的日常生活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日常生活论文,危机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0257-5876(2006)06-0039-11
在西方现代性的道路上,科学和技术最终驱逐了上帝,使自然去魅而把人抬到神话的高度,但它却悖反地使日常生活世界成为一个空壳。海德格尔将现代性的这种状态诊断为“对存在的遗忘”。当“日常生活批判”渐成学术行话,我们也已经捡到那只海氏扔下的漂流瓶。在今天,如何解读内含在那一诊断中的相关讯息(如“人被隐去”、“日常生活的意义流失”等)呢?
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概括,“对存在的遗忘”描述了贯穿现代性全程的基本危机,但正由于海德格尔强调的时间视野的重要意义,对“对存在的遗忘”的探讨亦必须语境化。这将使我们注意近三十年来形成的一个独特难题:日常生活由于“内爆”(implosion)而成为一种不可能性。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这个问题是高度现代性的一个自然后果,它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作用,而是广泛地与科学、技术、资本、市场、国家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不过,20世纪下半叶以来逐步升温的媒体(信息技术)革命以异常的方式将那些因素高度地整合起来,并在经验层面上有组织地侵蚀了日常生活的基础。无论如何,这个难题的出现,对“对存在的遗忘”及其克服便不可能按照既有的现代性批判思路进行。亦因此,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现代性危机的再一次深化或转型。
一、媒体与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建构
日常性是在20世纪才被论题化的。对于许多人来说,它似乎是一个新近的“发现”。然而,我们不应当误读这个“发现”,仅把日常性视为现代世界的产物。因为,如果说日常性是我们的存在状态,那么,历史一旦开始,人类便浸泡在日常性之中——日常性既是他呼吸的产物,又是他的呼吸得以进行的氛围,这一点至今并没有改变①。正是由于这一点,日常性与存在问题始终联系在一起,并由这种联系进入历史。也正是在历史中,我们才能够理解:日常生活的论题化,作为一个自我反思事件,它见证了人类在日常性之外确立自身存在本质的做法是如此之久,以至于忘记了生活本身。这是近代欧洲造成的存在难题。
我们无须重复20世纪西方思想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部思考,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发现”日常生活之际,它已经失去了其原始性,在历史中变得难以辨认。在现代性扩张过程中,理性、科学、技术、工业、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使经济、政治、文化的边界日趋明显,维持着日常性/非日常性的严格区分,同时又将之纳入同质化的过程,使之晦暗不明。所以,日常生活引起人们注意的时间也不短了,但是对它进行严格定义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也就是鲍曼所描述的那种语言(和情感)上的矛盾性(ambivalence)②。
值得一提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列斐伏尔为解决这一困难(亦是一种历史理解的困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他强调,研究日常生活是希望改造它,改造它就是把它的混乱置于日光下和语言中,就是使其潜在的冲突表面化并因此击碎它③。从这一视角我们看到,无论是马克思、马克斯·韦伯、西美尔等现代社会理论的先驱,还是胡塞尔、卢卡奇、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不同的哲学探索,抑或米兰·昆德拉断言的四个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小说,不同的话语在离析现代性日常生活建构逻辑的同时亦干预着那种逻辑。现代世界的变迁经验表明,日常生活并不天然存在,而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场所,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争取的场所④。
本文的焦点是媒体革命对当代日常生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是在现代性日常生活建构逻辑上发生的。在根本上,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是通过与资本积累动态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创伤性的和冲突性的关系——而形成的。在现代日常生活中,个体既是资本生产以及以维持这种生产正常运行为己任的政治权力所规训的对象,又是抵抗力量的场所。大众媒体正是在这种双重斗争中发挥作用的,如媒体之“中介”这个原始含义所表明的那样,它既是匿名化了的权力施于个体的中介性工具,又是个体徒劳地自发反抗的手段。因此,对于媒体的作用,亦必须在此背景下进行分析。这意味着,虽然我们把媒体置于焦点位置,但并非简单地把媒体视为终结的原因。
媒体与日常生活,并不是两个孤立的事物,它们存在并纠缠在一起。只是在今天支持我们讨论语境的那种社会结构改变了它们各自存在的方式及其相互关系。人们早已认识到,作为一个人与他人从而与整个社会发生联系的那些信息工具,媒体的发生经历了从口头到印刷再到电子的转移,人们日常生活亦经历复杂的变迁。
以电子技术为支撑的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的泛滥,其结果并非仅仅形成了独特的大众文化或媒体文化。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日常性建构是借助媒体才得以完成的,并且日益强大起来的媒体不满足于自己的工具地位,它现在要求按照自己的逻辑和形象来安排世界。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在建构货币经济和契约政治(从而实现独立个人之间平等而自愿的联合)过程中,对于普遍的交换具有深刻的依赖性,而这最终形成了这样的事实: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⑤。在物的依赖性之中的“抽象”(即理性)统治(马克思)、“无人统治”(韦伯)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好是一种镜像结构——商品与商品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对照才获得自身的价值⑥。这种结构即是媒体作用的机制,它最终成为绝对权力的机制。
从上述逻辑看,媒体不只是一个技术的方面,而且是各种现代性建构因素的汇集点。只有在这个语境中,我们才能够正确地理解麦克卢汉的《机器新娘》⑦。虽然日常生活仍然是一个永远不会被彻底征服的领域,或如布罗代尔所强调的那样,作为整个社会的底层,在长时段中,它顽强地对抗试图组织它的市场和控制它的国家,并因此支撑着历史,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承认,经由现代性的洗礼,它成为一个“完美的体系”,成为控制消费的“组织化”社会的主要产物⑧。在那种“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结构强大的组织化过程中,“我们的小酒馆和都市街道,我们的办公室和配备家具的卧室,我们的铁路和工厂企业,看来完全囚禁了我们”⑨。
正是由于这样的作用,媒体不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媒体文化,而且为全部的文化提供了表演平台。现代性社会理论已经指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⑩。而随着媒体的一步步强大,我们现在将变成等待媒体捕食的动物。《图门秀》(Peter Weir,1998)这部电影的开头以隐喻的方式指出了这一现实:在打上“live”这个产权标志的画框中,人们表演着,这就是日常生活。在那种日常性中,虽然生活表面上也总是按照个体的意志、需要和能力展开的,但实质上界线早已划定。
二、媒体革命与日常生活的内爆
1964年,麦克卢汉断言:“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三千年的爆炸性增长,现在它正经历内向的爆炸(implosion)。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就我们这个行星而言,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我们正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和总体上得到延伸,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一样。”(11)麦克卢汉的这一断言,直接拓展了海德格尔有关“对存在的遗忘”的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是由媒体革命造成的。
从媒体角度来看,随着技术的突破,新型媒体(如计算机、手机)、整合性通讯方式(如多媒体、因特网)等的出现,媒体渗透日常生活的能力极大地加强了。当“无失真”、“零时滞”、“无缝性”、“虚拟性”等特征出现时,一方面,媒体不再是再现世界的中介性工具,而是世界本身的“在场”方式;另一方面,日常性/非日常性之间的界限被彻底打破,因为非日常性被强行灌注入日常性,使后者发生内爆,成为一种不可能性。
在媒体革命中,所有的技术性要素或许都需要认真关注。其中,始终处于焦点的问题是:由技术革新所造成的媒体的多样化增殖——不仅是通信技术和手段的多样化,而且包括由于生产成本降低而带来的私人通讯工具的普及,最终形成了一个由电视、电台、报纸、杂志、因特网、手机、固定电话等多种性质的媒体相互作用的全球信息网络。这一网络改写着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并指向那种终极的状态:当传播从广播发展到窄播的时候,巨大的信息(注意,不是媒体)构成了包围并轰炸个体的无缝之网,人变成嵌在这一网中的存在物,成为挂在其上并维持自我运行的一个个“要素”。主体的那种“在场”感被具象化为“在线”感,由此,他时刻担心自己像果子被从树上摘走那样“掉线”。
1.隐私被穿透,日常出现漏洞。个体主体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自不必言说,然而,虽然有关争论已经汗牛充栋,但是有一个问题却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既然个体依据其日常而存在,那么其日常实践的“我的” (康德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对主体性的描述)边界便具有关键的意义。后现代的生活政治立场(如吉登斯)虽然并不足取,但其对政治与个体身体以及自我之间关系的反思却直接指涉了这个问题。因为媒体革命所造成的日常交往和消费中的隐私问题清晰表明:在现代性的高点上,一方面,隐私已经成为自由个体的最后一个据点;另一方面,它成为最后一个被去魅而透明的假象。
我们已经观察到,电视进入家庭的时候,引入其中的绝非仅仅是一个物(传统意义上的家具),而是一个(群)真实“在场”的成员,甚至比户籍统计意义上的家长更具权威的成员,因为它指导着我们的衣食住行(以“今天你吃了吗……”、“……男人的世界”、“爱我就……”等这样的语气),也安排着我们生活其他方面的规划(通过“…现场”、“有请当事人”等场景示范方式),比如说恋爱婚姻家庭纠纷的处理等等。电视等媒体自其诞生起便倾向于成为一个比家长、教师和其他传统权威角色更具权威性的教育者,正因为如此,在奥威尔的《1984》中,它才成为“老大哥”的肉身。
如果说电视的上述问题几成常识,那么,下列问题则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私人通讯工具越发达,个体的隐私就越发不可能保留。拿固定电话来说,装上电话,你家屋子的墙上就出现了个洞,因为电话铃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敲门声,敲门声仅仅表明一个来访的请求,而当你应答电话铃声的时候,来访者已经“闯入”你的私人领地。移动电话则是一种更巨大的力量,因为人人都拥有手机的时候,也正是每个人都把自己全天候地交给他人的时候,此时,你的私人性便完全依赖于他者——亲朋好友、或许只见过一面的客人、无孔不入的广告商以及偶然拨错号码的冒失鬼等等——的“恩赐”。GPS(那种带GPS功能的手机)并非仅仅在急剧变化着的地球表面给我们提供一个确切的坐标,让我们感到自己存在的确定性,而是把我们放逐出自己的日常生活,那种机器的铃声像空中不可思议地出现的一只巨爪,把我们扔向一种无助的空间。在近七十年前,本雅明便表达了这样的感觉:“电话铃声把柏林市公寓中的恐怖放大了几倍。每当我摸摸索索穿越黑黑的过道,惊魂未定地去结束那恐怖的铃声,把头伸进两个像哑铃那么重的听筒之间时,我只有束手就擒,无望地听任于话筒里那个声音的摆布了。什么都无法减轻这个声音对我的控制,我无力地承受着它对我关于时间的思虑、我的计划以及我的义务感的摧毁。”(12)
在当代电影中,《夺命狂呼》(三部曲, Wes Craven,1996等)突出地表达了这种现代性的恐惧感。在电影中,始终纠缠着西妮的是电话,这构成恐怖达及其身的一个通道:在电话的那一头,出现的是一个了解你的一切但你所不知的匿名者。这使得你身边的一切人都成为嫌疑犯:父亲、老师、同学、朋友、情人等。在最真切的意义上,你被置于一个“一切人都反对你的战争”之中。电话是一位匿名“在场”者的标志,它首先隐去了信息发送者的形象,其次加之其他技术,亦可隐去声音特点,这使得送话者成为一个隐蔽的“上帝”——仅就其无性别、无形象而言。这个匿名者成为全知(全能)者,他知晓你的一切。由于这个匿名者的“在场”,你的隐私不再可能保留。
在电视、电话穿透隐私外壳的同时,隐私也借由媒体成为大众消费品。在当代文学、电影、电视这些娱乐场中,到处都有“原始而赤裸裸的东西”在蠕动着——情杀、仇恨、乱伦,卧室的门被打开、床被暴露在阳光下的现象早已为人们诟病,有关拨一个电话号码便可听到“浪漫技巧”、“性福声音”的广告亦争相出现在各种大众报纸上。
总之,私人生活不再是私人的事件,而成为媒体的公开表演和展示。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如何维持一种真正属于自身的个体再生产呢?正是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福柯断言的“主体的死亡”,因其“主体”仍然是指向笛卡儿“我思”之“我”的抽象观念,而没有达及对现代性批判的底部。拉康虽然保留了主体观念,但他出其不意地从精神分析角度穿透欲望主体的虚假性,这种批判要比福柯更深入,更代表着对当代的批判。
2.距离被消解,差异成为漫画。距离向来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矛盾,最低限度的距离是意义生成的必要前提,亦是人类个体作为差异获得在场感的基础,当距离足够大时便成为实现共同体团结所需要克服的空间障碍。现代性倾向于消灭空间,这种冲动在媒体世界中可以说已经实现。因此,在今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开始遭遇由于距离销蚀而产生的问题。
关于距离销蚀问题,早已引起20世纪学者的高度重视。例如,詹明信有关后现代主义核心特征的描述便是集中于距离——审美深度、历史感以及批评距离等——的消失(13)。在媒体泛滥的过程,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普遍问题。例如在《飞虎队》(王翼邢,1996)这样的主旋律电影中,崇高与低俗之间的距离被消解,革命亦成为暴力、野性、低俗的载体,更不必说大规模的“红色经典”被商业涂写,在弘扬人性的口号下,个性与差异亦被漫画化,化为同质的原始野性。
然而,距离问题不仅仅与审美或者艺术相关,它全面关联日常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能够得到维持这个根本问题。一方面,在媒体中极为明显地存在着哈维所言的那种“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作用。这种作用是由交通、通信等多种工具共同实现的,但在传播方面更为彻底。如哈维引证过的阿尔卡特通讯公司所做的广告,全球空间被压缩和还原于一个媒体之中。当然,就时间来说,便是一个当下(14)。2006年,中国电信推出“世界触手可及”这个广告词。之所以电信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就在于它将日常生活的时空两个维度压缩成无矢量的弥散性平面,或者说,一个点。在这种情境中,任何一个个体所经历的日常生活,都成为被无限多的信号所灌注的接受器,也因此产生“内爆”效果。另一方面,与这种压缩作用相反的是偶然性的个体被放大。如果说前一方面是一种聚集效应,那么这就是发散效应。 2005年,“芙蓉姐姐”事件成为一个典型案例,借助媒体,个体把自身投放到远比直接活动范围要大许多的未知空间中,并因此改变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媒体制造的事件,例如,李宇春,一个没有任何传奇的女孩,在2005年成为中国(俨然已经波及世界)最争夺眼球和话题的焦点人物,在《新周刊》的年度盘点中,她甚至压倒丁学良、李敖等人而占据“年度新锐人物”的位置。更大量的例子是,地方性事件和个体借助因特网以某种传统无法想象的力度直接影响着这个世界。
在以上两种作用中,都贯穿着吉登斯所言的那种“脱域”(disembeding)作用(15),这种作用正是马克思以及西美尔谈及货币时所指出的那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象征作用。就媒体来说,媒体穿越一切障碍而夷平一切,使一切人和物都暴露在其镜面上。借助于这种作用,媒体掌控了世界,它抽象为世界本身,这个世界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等质的。这不仅消除了个体经验的差异,而且把个体还原成同质性的“原子”。
从认知角度来说,如果在现代性早期,人们坚持需要科学是因为现象与本质之间存在着裂隙,那么在今天我们显然不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为,我们直接遭遇的世界是媒体构造出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形相与本质之间差异无可挽回地消失了。正是从这一角度,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人对媒体的信(依)赖远远大于对科学的信(依)赖。
从伦理角度来说,在今天,人们已经普遍抱怨,过度发达的媒体造成了对亲情、友情的疏离,人们对天外的兴趣似乎超过了对身边的兴趣。但这仅仅是一个现象,更真实的问题是:不是人们对自己的直接同伴丧失了兴趣,也不是因为极度发达的媒体让我们无意中忽视了身边的人或事,而是媒体所产生的那种“时空压缩”和“脱域”效果把世界还原为由弥漫着的无差异的“离子”所构成的平面,天外与身边的区分对于个体来说不再具有实质性意义。在这一背景中,人事实上是对世界失去了兴趣。在媒体的海洋中,他倾向于使用媒体报道式的客观眼光来看待世界,或者说,媒介替代了他包含情感和期待的目光,因此世界本身就成为数字那样的冰冷的事实。
战争、恐怖主义、灾难、凶杀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称为“悲剧”的东西,现在每天通过报纸、杂志、电影、电视、因特网等各种媒体像一日三餐的点心那样按剂量地定时喂给我们,转变成供我们消遣的无害点心。一方面,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反而感到不安。它们的缺失,就像更大暴风雨之前的平静那样威胁着我们,使我们处于焦虑之中。另一方面,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成为在媒体上展示的那种表演。最近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武汉某地青年交通事故受伤后发出的呼救声竟被邻人以为是“隔壁电视里的声音”,结果得不到及时救治而亡(16)。昆德拉问道:“我也想到每天在公路上发生的大量的死亡现象,那是一种既可怕又平凡的死亡。既不像癌症,也不像艾滋病,不是大自然造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那是一种几乎自愿的死亡。为什么这种死亡不让我们触目惊心,不搅乱我们的生活,不驱使我们去进行重大的改革?”(17)这一质问所指向的事实见证了那种包含着莫名冲动的日常生活的死亡。因为那种冲动是日常生活特有的属性,而现在,它开始沉寂。
3.实在被虚化,生活失去质感。20世纪 60年代以后,对于现代社会的最激进批判莫过于指出现实已经成为荒漠。在先前,本雅明已经通过考察19世纪的巴黎指认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废墟性以及在文学中流露出来的废墟感。如果本雅明的判断具有明显的价值预设,那么后来的法国人,无论是德波、拉康还是的德里亚,在否认“实在”的时候,都试图移走横贯在“现实=荒漠”这个公式中的价值杠杆,在他们的言说中,“现实”和“荒漠”不是两个词而是一个词。当然,这样做,并非说“实在”真的消失了,而是说,我们感知“实在”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感性本身虽然仍是身体与环境接触的表面,但是在这个表面上的投影却不再直接就是世界本身的投影,而是媒体所构造的世界的投影。这是由于大众传媒极度发展所产生的真实问题。
1967年,德波在其《景观社会》中第一句便说:“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全部生活都表现为庞大的景观堆积。曾经直接活着的一切都变成了纯粹的表象。”(18)熟悉马克思著作的人都会立即识别出,这是对《资本论》第一句的改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19)德波的讨论采纳了马克思的形式结构,但对象从“财富”转到“生活”,这种转向隐含着的巨大差异是:我们已经从商品世界走向景观世界。在前一个世界中,财富表现为商品;在后一个世界中,生活表现为景观。
在个人生活层面上,德波的描述无疑能够得到经验的支持。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大中城市里,繁华的街道、鳞次栉比的商场、随处可见的广告、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每日电视中展示的灯红酒绿的生活,让我们直接感觉生活在一种大都会景观之中。虽然德波否认景观是大众传播技术的产物(即仅仅是一种视觉形象),而要求在根本上将之理解为(资本)世界观的物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大众传媒在其中并非仅仅扮演了这种世界观物化工具的角色,因为它就是这种世界观所寄居的外壳,也是这种世界观自我生成、扩散并因此普遍化的世界本身。这一点正是我们的时代与马克思时代的实质性差异之一。马克思的时代,“作为商品的象征”出现,它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脱掉具体属性那张皮的抽象(从使用价值到价值,从质到量),其次是通过“对象化”、“象征化”成为一种符号(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金子这样的东西最终都可以通过一种普遍的机制脱掉自己粗糙的皮而成为财富的象征(20)。在今天,这一过程又深化了,它衍化为第三个阶段——非象征化、自我物质化。在这个阶段上,符号直接变成了“实物”,而它曾经所依托的实物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符号实物之间的交配繁衍构成了世界再生产的显著特征。鲍德里亚用拟像(similacrum)来描述这种世界的特征。各种主题公园(世界之窗、民俗村、动物园、海洋馆等等)、博览会、商品交易会等以夸张的形式直接呈现了这一点。例如迪斯尼,无论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在欧洲和亚洲,迪斯尼的每一个角落,“美国的客观性图像被绘制出来,所有个体和群体的形态学都被描画得淋漓尽致”,而它“是所有纠缠在一起的拟像秩序的完美模型”(21)。
我们可以不认同鲍德里亚的论证逻辑,但是必须承认他在描述现象方面是极为深刻的。在我看来,这是工业文明在总体实现 (并非完成)对作为实在的外部环境的控制之后必然出现的问题,而在实质上是转向对日常生活的征服——原本作为个体实现自我再生产(即日常生活)手段的工业(科学、技术、资本),现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重组日常生活,使之成为自我扩张的手段。《图门秀》中的海景岛,作为对主题公园的戏仿,便隐喻着这一逻辑,日常生活成为媒体工业得以扩张的最好资源。因此,“拟象”不是工业的自在展示,而是工业成为一种自觉主体的征兆。
工业成为真正的主体,那么,在“拟象”中,人便成为工业所制宰的一个对象。工业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呢?或许,电子游戏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启示。就如多数游戏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战胜了各种困难而站在胜利的终点上,但在这个终点上,除了那些虚拟的礼花,我们究竟还能获得什么呢?从一场战斗到另一场战斗,我们无尽地追逐着除了礼花之外的东西,但是反复重现的礼花以一种反精神分析的姿态公然地宣告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它就是游戏召唤出来的被社会压抑的那个东西。在一次次回归中,礼花清晰地表明了高技术游戏正是现代社会在原始本能与过度道德之间的直接通道,这个捷径的存在直接证明了当代精神分析有关超我与本我之间短路的断言,而这种短路的后果是自我被消解了。
如果承认精神分析的结论,作为欲望的主体,欲望的对象维持着主体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承认,由于媒体通过给我们提供满足从而维持着基本的欲望对象,它因此维持着主体的感觉。问题是,在这一机制中,那些感性对象无一例外地消失了,媒体究竟维持着怎样的基本欲望对象呢?在游戏中,一次比一次辉煌的礼花,在电影中,一次比一次更加剧烈的冲撞,那种扩大和加速的标量运动似乎透露出某些秘密,不断增加的“量”——剩余、过剩——正是我们成为主体所需要的原因。拉康和齐泽克正是在此发挥了他们的才智。他们指认:与剩余价值维持着现代资本生产逻辑一致,剩余快感维持着现代主体的生产(22)。由此,我们看到,媒体在其中的作用是,它将剩余快感转化成为直接的欲望对象,就如货币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它将剩余价值转化成直接的欲望对象(一般财富)。同样,如果说现代生产并不以直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为目标,那么,现代媒体亦不以直接满足人们的感性欲望为目标。媒体提供的仅仅是间接满足,或者更直接地说,一种替代性满足,它承担着安慰剂的功能,就如在哺乳期孩子嘴上经常看到的那些橡皮奶嘴。所以,我们便看到如此显著的对立:一方面,由于它既扩大了我们的欲望又不直接提供满足,这种对立及其心理效果必须在媒体之外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领域中展现出来,从而加剧了现代社会的精神分裂;另一方面,只要肯定媒体的娱乐功能,我们便能够接下来承认,除了安慰剂之外,媒体本身并不试图追求更多的东西。
在上述语境中,我们必须问:日常生活,还可能吗?
三、媒体批判、美学救赎、乌托邦诉求和日常生活革命
媒体革命所导致的日常生活“内爆”无疑加剧着现代性危机,这使得对媒体的揭露和批判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出来了。这一点已经在广泛的社会理论中得到回应。但在现代性批判方面,它亦同时带来一个新的理论问题:对媒体以及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先驱们曾经做过的诸种探索开始捉襟见肘。
就媒体来说,在现代性批判史中,并不是一个缺失。相反,从现代出版业繁荣开始到今天,媒体的成长自始至终伴随着恶名甚至对它的仇恨。例如,大仲马时代,作家们便喜欢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发出这样的抗议——“记者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不幸之上的人”,当然这是针对报纸的猎奇行为来说的,报纸总是通过追逐市井闲话、桃色新闻和那些“值得了解的事情”从而把那些隐蔽在日常生活海洋之中的个体打捞出水平面,以供构成这个海洋的大众来消遣。甚至,随着日常文学交易的泛滥,据说大仲马为应付对自己的需求也“雇佣了一整支由穷作家组成的军队”,这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本雅明从批判的角度一杆子捅到底:“撇开出版业的堕落史就不可能写一部信息史。”(23)正是因为这一点,对媒体革命化所导致的文化大众化,欧洲的精英知识分子始终存在着戒备心理。从圣伯夫到阿诺德这些个人,再到作为群体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今天各种批判理论的徒子徒孙们,坚信“良知”的理论家们非常明确地在自己与大众之间划出一条界线。
但是,在今天,情况不一样了,这种界线是否还能够维持?媒体以其付费娱乐功能消解了认知困难、道德重负和审美疲劳,从而使付费的娱乐成为世界的存在基础。情况似乎发展到如流行语“卡拉OK”所直接表明的那样——我“卡拉”,所以我“OK”,步随着“卡拉”,我们才抓住存在的脚后跟。但是,“卡拉”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它没有所指(大多数人使用这样的语汇时并不需要理解它指什么),或者所指的是另一个同样空洞的能指——如“休闲”(一种被现代工业和商业剥掉内涵的现代消费形式),而这种由空洞的能指相互指涉所形成的封闭性能指链恰恰就是现代媒体世界(24)。
同样,在上述语境中,20世纪产生的日常生活批判话语,从对自发(原始)日常性的崇拜(海德格尔)、美学救赎(法兰克福学派)到日常生活革命(卢卡奇、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等等,虽然它们仍然像致瘾的药品那样吸引着我们,但我们得到的只能是安慰。而另一方面,试图替代这些努力的新兴政治话语,如生活政治(吉登斯等)、话语(表达)政治(诸种后现代话语),它们亦多表现出一种“秀给你看”的伪浪漫的纯姿态,怎么着都无法成为探究的理论依靠。
我们究竟怎样继续谈论存在,或者如解放政治学要求的那样去努力实现日常生活的革命呢?只要问题存在,探索就不会停止。在新的探索中,西方学者以其自身的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有限的借鉴,这些经验包括以“媒介(传播)理论”、“大众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等等术语概括的各种新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也齐头并进,而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话语复杂地纠合在一起。
本文无法一一评价那些探索。需要简单论及的是有关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该问题成为近年文艺学以及相关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主题。我无意介入具体的争论,而只是强调: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作为人类超越日常性的基本方式在现代性之前就已发生,只是工业、资本、媒体改变了它的当代性质,反而使得日常生活本身成为一种不可能。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审美。当日常生活出现漏洞之际,我们既不能借助日常生活达及审美,也不能通过审美来改变日常生活。在流行的讨论中,人们往往忽视韦尔施(《重构美学》的作者)在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时的二元立场,这一立场与麦克卢汉有关媒体的价值立场如出一辙,而在根本上与科学技术的二元性问题同构。这见证了媒体及其引发的问题,虽然具有明显的独立外观,但实质上仍然是现代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征兆。
因此,在推动社会朝向更为公正和合理方向发展这个宏大政治主题中,媒体批判的意义和实际的操作路径不应该脱离对现代社会内在脉络的揭示。这将会使我们注意到:现代性最深刻的危机并不在于科学与技术的泛滥,而在于由于资本生活的普遍化而造成的社会结构的物化,正是这种物化把意义从任何对象中挤出来,从而把世界变成冰冷的商品或景观的堆积。
从这一角度看,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遭遇了自身的界限。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活动简化为消费,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你就在消费医疗服务,然后是上学、购物、唱卡拉OK、旅游,甚至最后去见上帝,我们都在消费,而整个人就是一个消费者。尽管这一过程亦会呈现美学特征,但是,由于人被工业塑造、意义被资本锚定、生活被媒体掏空,审美在日常中只能被贬为无意义的物的流通活动。事实上,从杜尚的“泉”到沃霍尔的“可乐”,惊世骇俗的艺术活动早已表达出对这一现实的抗议,只是这种抗议亦没有避免被收编的命运。
在今天,我们可以观察到更加广泛的例子。例如,当习惯于从数字百科全书那里获得有关自然知识和美感时,其结果便是产生叶公好龙式的虚假的欣赏口味(列维一斯特劳斯),自然反倒成了真正的奢侈品。再如,通过媒体的直播参与“奥运会”、“海湾战争”以及各种地方性和全球性事件时,媒体不是对我们不能亲临现场这种缺陷的补偿,而是对我们冷漠的掩饰:一方面,它培养我们对事件及其现场的嗜好;另一方面,它又让我们对现场本身产生深深恐惧。因此,我们似乎只能通过现场效果的无尽追求(发烧碟,极至 HI-FI的影院系统等)来证明自己的敏感性。数字化拟声、影像技术不只是一种弄假成真的仿真,而是产生比真实经验更为纯粹的真实——使真实达及化学中的那种分析纯度,在这种纯度的对照下,现实世界反倒成为一种我们不要想的噪音。人们躲在荧光屏后为一个图像流泪,却远远避开需要帮助的同胞。最终,媒体承担了哭灵人的角色,最终解除了应该去承担痛苦的个体的责任。因此,现代社会较之我们想象中的原始社会,更具有仪式的特征。正是这个原因,才产生了德波所言的“景观性”,因为真实的概念是建立在媒体定义上的,我们便始终处于这样一种悖论:我们只是用一种想象来反对另一种想象。电影《金刚》(Peter Jackson,2006)便是这样一个例子,金刚这一现代媒体技术的产物,它代表着一种比现代人更具有人性的原始性,而它最终不敌现代而倒在纽约的街头。更甚的是,当影视花絮消费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我们看到:作为被擦除的意外,代表着表演者对事件过程进行干预的那种偶然性,花絮不再是一种自我揭露和反思性事件,而成了媒体收编消费者的甜点。它见证了,媒体不再害怕虚假。
总之,媒体已经成为一个吸血鬼,它不断地从日常生活中榨出那些用以兑换货币的东西,以至于日常生活本身成为一件商品。在这一背景之中,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来说,除了各种上手性器具,生活方式和思想也都变成了可以或必须购买的商品。正是在这一状态中,我们才能够理解许多令思想者痛心疾首的现象。例如,在今天,娱乐被迫承担艺术或思想的功能,而艺术或思想只有娱乐化才能被人接受,大量不伦不类的东西,伪思想、伪娱乐则成堆地被生产出来。
当然,尽管问题并不在于审美,但审美仍然可以成为日常生活批判的有效视角。因为,文学、艺术的内在超越性所产生的乌托邦和批判力量,使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日常生活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场所,是一个需要争取的场所。围绕工作日——在现代社会,它直接界定了劳动和休闲的界线,也干预着日常和非日常的区分——的斗争早已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只要我们理解承担那种力量的并非艺术一家,我们就能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借由美学和其他路径以及各种路径之间的联盟推动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因为,“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以反对对当前现实事态的消极默认。正是符号思维克服了人的自然惰性,并赋予人以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25)。
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是从神的手中挣脱出来的一个场所,正如现代世界本身是从神的世界中挣脱出来的空间一样,但是,现代世界走向其顶点的时候,我们发现,日常生活仍然没有掌握在人的手中。更为重要的是,在传统氛围中,虽然上帝以及血缘等神圣的魅力锁定了我们,但人与人之间仍然真实地维持了日常的联系。在现代氛围中,我们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托付给媒体,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则越来越成为人所能想象的最远距离。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媒体革命所致的日常生活内爆实质上是我们生活体验的内爆:物质生活本身的革命化,当这种革命化达到自己的临界点时,由于缺乏与这种革命化过程相一致的精神生活的革命,在一种极度多样的选择机会面前,我们丧失了选择的能力。这一状态恰恰与乌托邦被逐直接相关。
然而,正如20世纪日常生活批判话语的兴起所见证的那样,乌托邦降临的地方也正是它被驱逐的地方。马克思,以及其后的尼采、海德格尔、萨特、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许多当代仍然活跃的批判性思想家,他们在打破自然性这个问题上的惊人一致性,不都是由乌托邦想象所维持的吗?因此,我们必须对现代性本身之借助技术力量塑造自然性的运动及其“终结”意识形态有着高度的警觉。乌托邦正矗立于这种警觉之中。
在今天,我们不妨回望一眼那种经验。富丽堂皇的地铁车站、宫殿一般的百货商店、令人目眩的娱乐场所等等,任何一个并不在日常生活之外的场所,都会使你忘却时间的存在,忘却窗户外面的世界在变冷、变黑,它们自成永恒的瞬间。现代性似乎真正实现了那种让人流连忘返的童话世界(26)。然而,一旦电源中断,人们便一下子陷入黑暗、恐惧和无助中。日常生活刹那间中断了。此时,我们才明白,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是建立在巨大的工业之上的,而那种工业本身与生命一样存在着巨大的脆弱性。合理化自身始终为中断风险所纠缠。经历过电梯停电、交通事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类似灾难事件的人们都会明白这种风险的意义,从而对日常生活具有独特的理解。我们不必真正等到风险成为一种确定的危险,才无奈地背过脸去。在此意义上,无论多么虚幻,我们需要一种与当下消极势态相反的乌托邦。
注释:
①日常性作为个体的存在状态,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平台,它支撑并接受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建构。在这个世界中,个体以“婆婆妈妈”的活动维持着被称为“自我”的东西。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个人才是他自己世界的主人,从而是他自己的主人。只不过,在相当长时间内,它被视为一个自明的领域,亦因此是无须论题化——即等待着被阐明——的领域。
②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③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Ⅱ, London:Verso,2002,p.226.
④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 Blackwell,1991.
⑤(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第89-101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页。
⑦马歇尔·麦克卢汉:《机器新娘》,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⑧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Harper Torchbooks,1971,p.72.
⑨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⑩克利福德·吉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1)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第20页。
(12)本雅明:《驼背小人》,徐小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年版,第24-25页。
(13)参见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载《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14)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第240-242页。
(15)“脱域”作为吉登斯的一个关键词,贯穿于其论述。较为详细的讨论参见《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16)详细事件报道,参见《扬子晚报》2006年3月2日。
(17)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年版,第80页。
(18)Guy Debord,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New York :Zone Books,1994,p.12.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21)鲍德里亚:《拟象的进程》,载吴琼编《视觉文化的奇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22)齐泽克:《快感大转移》第二章,胡大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3)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5页。
(24)布迪厄把电视中的信息循环称为“镜子游戏”,他指出:“这种镜子游戏照来照去,最终营造出一种可怕的封闭现象,一种精神上的幽禁。”(《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25)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26)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样的空间缺乏运动感。相反,在这样的空间中,“运动速度和更快的运动手段在稳步增长,掌握了最为重要的权力工具和统治工具”(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5页)。因此,我们同样看到,不断推出的新商品,定期更换的广告牌,季节性改变的商品展示柜,隔一段时间便会翻新的百货商品购物环境等等,营造着象征时间流逝的新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