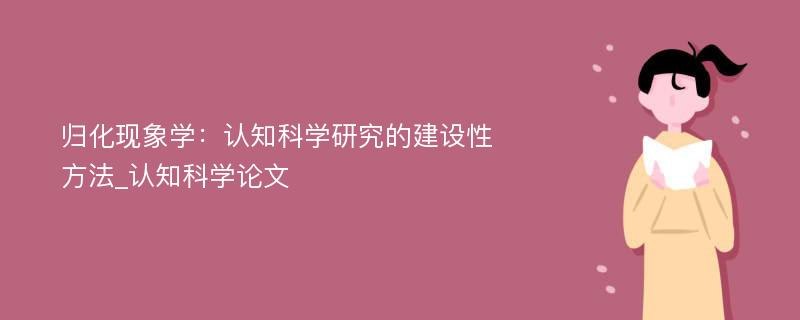
自然化现象学———种现象学介入认知科学研究的建设性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建设性论文,科学研究论文,认知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3)02-0020-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象学开始以一种建设性态势介入认知科学研究。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以休伯特·德雷福斯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利用现象学思想不断质疑表征—计算主义认知科学研究纲领,这间接推动了认知科学哲学家对一种建设性现象学的探索;二是意识、感觉质或现象心灵成为心灵哲学中一个令人倍感困扰的“难问题”,现象学对此问题的独特思考引起了心灵哲学家的关注;三是当代认知科学研究中涌现出的涉身认知、情境认知与生成认知等不同称谓的新研究范式,更加能够在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等人的现象学思想中找到共鸣[1];四是诸如神经科学等认知科学研究领域中产生的新实验科学范式尝试运用了现象学方法,即在运用大脑活动成像技术等客观方法之外,还需要结合被试对象自身体验的相关报告。自然化现象学(Naturalized Phenomenology)就是在上述背景之下适时产生的反映现象学积极介入认知科学研究的一种理论路径。
一 内容
现象学由胡塞尔奠基,同时也包含了舍勒、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以及舒茨等人作出的不同解释与发展。意图积极介入认知科学研究的自然化现象学实质也是这场现象学运动的构成部分,也是对现象学的一种解释与发展。认同自然化现象学主张的加拉格尔与扎哈维等认为,现象学两个方面的理论内核对于现象学积极介入认知科学至为关键:一是消除任何理论预设而回归主观体验本身的这一现象学基本主张;二是现象学对主观体验的描述与分析方法可以视为一种主体间性的客观方法。对现象学内容与方法两个方面的这种解释可以称为自然化现象学的理论基点。
“回归事实本身”是现象学运动的起点。在扎哈维、加拉格尔等人看来,现象学的固有内核之一就是悬隔二元论、还原主义、消除主义等各种理论预设,从而回归真正实在的主体体验本身。以视知觉研究来说,现象学要求对内在心灵、大脑活动或者外部刺激主导等传统视知觉理论预设加以悬隔,从而回归主观体验本身来揭示视知觉现象。同时,意识活动的意向性就是主观体验的基本结构,即体验可以描述为所有意识(知觉、记忆、想象、判断等)都是关于某物的一种原初关系。这样,诸如知觉、记忆和想象等意识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处于各种情境之中的体验活动,就是处于各种物理、社会环境甚至虚拟文化对象之中的体验活动。正是基于不同的情境,视知觉等意识活动也就相应展现了一种丰富性。加拉格尔如此描述:“知觉意向性就是异常丰富的。就对街上汽车的视知觉而言,知觉不仅仅是接收信息,相反,知觉涉及一种理解,这种理解经常随着环境而改变。……现象学家将会主张,知觉体验嵌入于实用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场景中,并且大多数语义活动(知觉内容的形成)源自于我所遭遇的对象、安排和事件。在某一特殊场合,我可以将对象视为一种我用来达到某地的实践工具。在另一个场合,我可以将同一对象视为我必须清洁、必须出售或者出现某种故障的对象。我对汽车的视知觉方式将依赖某种处境背景,这可以通过现象学加以探究。将我的汽车视为驾驶的对象,就是将汽车视为我能爬进去的对象,就是将汽车视为能够实现运动功能定位的对象。我的知觉体验最终是由身体能力和拥有的技巧诱发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说知觉具有表征或概念内容。但是,这种谈论方式没有能充分说明知觉体验的处境性本质。不是说我将这部汽车表征为可以驾驶的,更好的说法是,假定汽车设计、我的身体形状与行动能力以及环境状况的条件下,汽车是可以驾驶的,并且我将知觉到汽车是可以驾驶的。”[2]7-8
现象学并不否认大脑活动与外部环境产生知觉活动的因果机制,不过,现象学并不试图提出一种对意识活动的自然主义解释,现象学所根本关注的是能够理解和正确描述我们精神/涉身生活的体验结构。在加拉格尔与扎哈维看来,正是现象学所揭示的主观体验可以成为认知科学等自然主义解释的基础。他们说:“我们现在已经逐渐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认识我们想要表述什么,那么我们就不能深入地了解对于意识和大脑关系的科学解释。换句话说,任何对于将意识还原为神经元结构可能性的评估,任何对意识的自然化是否可能的评估,都将要求一种对意识体验层面的详细分析和描述。”[2]9
二 方法
尽管不少认知科学家与哲学家意识到现象学与心理学等实证研究是相关的,并且现象学揭示的体验结构有助于认知科学研究,但是,现象学与认知科学使用方法的明显不同始终是实现二者结合的最大障碍。一般认为,现象学采用了第一人称路径的研究方法,现象学通过主体体验来理解知觉,对于知觉活动的理解根本不关涉大脑活动。而认知科学等则采取了第三人称的路径,即研究者作为外部观察者而非体验主体,立足大脑状态及其功能机制等客观层面来理解知觉。
可见,两种传统的对立更多源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路径的方法论区分,正是这种区分造成了“意识难问题”及其解释的鸿沟。不过,如果人们坚持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路径的严格区分,坚持不能用第三人称术语来解释第一人称的事情,坚持科学的客观性要求对观察对象的第三人称视角,那么,这就将导致根本不存在任何关于意识现象的科学研究。这样,如果我们要对意识活动进行科学研究,这就需要对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路径进行再认识,或者说对现象学方法加以再认识。
实现现象学对认知科学的建设性介入,要求对第一人称路径与第三人称路径的重新认识。第一人称视角的现象学分析仅仅是一种对于主观体验描述结果的“客观”编写,不应当将其理解为一个给定主体自身完全封闭和私人的“主观”体验。同样,第三人称路径的科学解释也并不是完全“客观的”,不是可以独立于第一人称视角的,相信存在纯粹第三人称视角等于陷入一种客观主义的幻觉。
在加拉格尔和扎哈维看来,现象学方法并不是第一人称的“主观”方法,它也是一种“客观性”的方法,或者说,现象学能够使主观体验以“客观的”形式呈现出来。现象学对于主观体验结构的揭示由四个基本方面构成:一是现象学方法要求对各种理论立场的自然主义态度加以悬隔;二是要求对体验对象和体验自身共联的意向性结构加以现象学还原;三是要求对意向性结构加以共时与历时的本质直观;四是要求对意向性结构本质进行一种主体间的确证(intersubjective corroboration),由此实现现象学对体验描述的“客观性”呈现[2]28。这样一来,现象学的第一人称视角既是“主观的”,因为任何一种获知方式都是主观性的,同时,现象学的第一人称视角也是“客观的”,因为,现象学分析主张自我与他人具有相同的获知对象方式。所谓的第三人称视角来自于至少两个第一人称视角的相遇,这最终导致的是一种对于对象的主体间性获知。
总之,现象学可以提供一种对于意识的可控制研究,现象学方法就像科学方法一样,其目的也是为了避免偏见性和主观性的解释。现象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对体验的主观性解释,它是一种对主观体验的解释;同时,现象学方法是一种对主观体验的客观解释,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否定主观体验,或者说我们能够通过将主观体验转化为第三人称方法考察的对象来理解主观体验。这样,对于现象学方法的再认识,就为现象学积极介入认知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 本质
自然化现象学就是一种立足现象学的任务与方法、实现现象学与实证科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在加拉格尔和扎哈维看来,自然化不是指立足自然或者说只能通过客观的自然科学来进行关于心灵的研究,如此理解的自然化现象学只是一种非技术的使用。现象学的非技术使用就是将现象学体验等同于神经生物学过程,扎哈维也将其称为一种激进的现象学自然化。自然化现象学关注的是现象学的技术性使用,或者说一种温和的现象学自然化,即对体验这一自然构成部分进行现象学与科学的研究。加拉格尔指出,技术性的现象学自然化意味着,“一种自然化的现象学应当承认,它所研究的现象就是自然的构成部分,并且由此是对实证研究开放的。”[2]30温和的现象学自然化主张在现象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互动,同时维护各自的相对独立性。扎哈维这样说明两者的关系,“正如现象学也许在发展新的实验范例时提供帮助一样,现象学能够对经验性科学作出的基本理论假定发问并进行说明。经验性科学可以给现象学提供它不能简单忽略而必须能够调和的具体的研究结果,以及也许会促使现象学提炼或修改它自己的分析的证据”。[3]
将基于体验的现象学与实证科学研究相结合的自然化现象学,区别于其他一些对认知与心灵的现象学研究。
自然化现象学不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詹姆士在心理学研究所指的内省方法。在当代认知科学研究中,一些人将运用于实验科学的内省方法等同于现象学的方法。在加拉格尔和扎哈维看来,内省的方法不同于现象学方法。第一,内省的方法并不是一种客观的方法。例如,若两个实验个体的内省资料出现矛盾,那么我们将没有办法解决这种矛盾,或者说不会产生认识上的主体间共识。第二,内省的方法是一种基于笛卡尔主义的方法。内省不是揭示体验的根本方法,其实质是对原本体验的一种笛卡尔意义的“我思”或者自我反思。现象学传统关注的对自身体验的觉知,不是反思意义的觉知,而是一种在我们运用精确内省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觉知自我的体验。例如,我们在看见灯光的同时,我们就在觉知我们看见灯光这件事情。这种觉知意识不是基于对我们体验的反思性或者内省性的注意,相反,觉知意识就是我们体验的本质构成,并且觉知意识明确将我们的体验限定为意识的体验[2]15。
自然化现象学也不同于丹尼特提出的异质现象学(heterophenomenology)。异质现象学主张,现象学家通过与主体交谈并且记录其言语和其他行为表现,然后给这些发现提供一个意向性解释,如果获得的资料模糊,现象学家还可以进一步通过主体得到澄清,通过这个过程,现象学家最终能够完整地得到主体意识体验的报告。不过,异质现象学在人们是否真正具有主观体验的问题上却持有中立性的立场。丹尼特指出,人们相信他们具有体验,并且这些事实——人们相信和表达事情的事实——是任何对心灵作科学研究必须解释的现象。但是,从人们相信他们具有体验的事实,我们不能得出结论,即他们事实上真的具有体验[4]。在丹尼特看来,由于异质现象学在人们是否具有体验的问题上是中立的,因此,我们就不需预先判断主体到底是一个撒谎者、一个僵尸、一台计算机、一个身着服饰的学舌者抑或一个真的有意识的存在,或者说,就异质现象学而言,僵尸与有意识的人之间就不存在区别[4]95。在加拉格尔等人看来,异质现象学的方法本质上不关涉主体体验,异质现象学关注的是从第三人称视角来研究被试主体的言语和行为的最初表现,或者说,这是一种第三人称版本的现象学方法(a third-person version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在加拉格尔等人看来,异质现象学自身也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意识或心灵研究中,科学不可能摆脱第一人称视角或者完全实现中立化。
四 途径
自然化现象学的理念能否有效,关键在于能否提出和设计一些体现这一理念的有效的具体途径。加拉格尔等人尝试将下面三种方式看做自然化现象学的具体实施途径。
一是形式化的途径。形式化途径就是将现象学分析的结果翻译成科学能够清晰理解的数学语言。加拉格尔等人认为,一种充分复杂的数学能够使现象学和自然科学资料良好地转化为一种共同语言,诸如动力系统数学就能够应用于心灵,从而提供一种整合现象学第一人称资料和实验科学第三人称资料的形式化解释框架[2]32。
二是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途径。瓦雷拉最早提出了神经现象学进路,这种做法试图将三个因素整合起来:对体验的现象学分析、动态系统理论以及对生物系统的实证实验[5]。如果说现象学的形式化着眼于科学模型,那么神经现象学则力图使现象学可以直接应用于科学实验。加拉格尔这样描述一些神经现象学研究,即实验主体在实验中不依赖任何强加的理论范畴来描述自身的体验,这些现象学报告中描述的不同主体性参数,联结着先于刺激的各种动态神经符号,并且这些动态神经符号随着对刺激的行为和神经反应的不同而不同。这样,在神经现象学做法中,现象学体验、动态系统理论以及生物学实验就可以被整合起来说明认知活动。
三是预装现象学(front-loaded phenomenology)途径。这种路径的基本思想是,将源于胡塞尔、梅洛-庞蒂或者神经现象学的现象学洞察用于指导(即所谓预装)实验设计。不过,预装现象学的方法并不是简单地接受胡塞尔、梅洛-庞蒂或者神经现象学等给出的结论,这种途径还包括在实验设计中对上述结论的检验活动。总之,这种途径整合了先前预装的理论洞察和为了特定实验而阐述或者扩展上述洞察之间的一种动态运动。
五 效应
自然化现象学具有双重的效应:一是现象学的介入推动了认知科学与心灵哲学的发展,二是这种介入反过来也推动着现象学自身的发展。
自然化现象学区别于内省与异质现象学,因为它能够为认知与心灵研究提供富有解释力的哲学方法论工具,从而避免采取还原主义等方法来建构对于丰富科学经验材料的理解。自然化现象学还能够提供用于认知与心灵研究的理论范畴。例如,加拉格尔在《身体如何型塑心灵》一书中专门讨论了现象学提供的用于解释涉身认知的身体意象(body image)与身体图式(body schema)两个重要范畴。他指出,如果要完整地解释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生,就需要将属于一个与身体相关的知觉、态度和信念系统的身体意象与属于在没有觉知控制下发生作用的感官—运动能力系统的身体图式整合起来,由此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涉身性(holistic embodiment)思想就能够成为涉身认知科学研究的建设性理论框架[6]。
自然化现象学还能够推动我们对于认知与心灵活动的深刻理解。例如,现象学提供了一种清晰的高级意识理论并且能够推动对发展心理学、动物行为学、精神病学等经验科学的解释;现象学详细分析了体验的内在时间性本质,这是对我们大脑—身体—环境系统动态本性的现象学补充;与各种表征主义的知觉模型不同,现象学维护了一种强调涉身、生成和处境特征的非笛卡尔主义知觉观;现象学提供了一种强调心灵与世界共同突现并且取代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非此即彼立场的意向性解释;现象学提供了一种涉身和处境的认知观,通过鲜活身体与客观身体的区别表明了生物学研究等对于理解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性;结合发展心理学与神经系统科学研究,现象学提供了一种关于主体间性和社会认知的心灵理论,等等。
自然化现象学具有双重效应,也就是说,现象学还能够在认知科学的发展中获益。例如,加拉格尔说:“时间意识、身体觉知、主体间性、意向性等现象学研究,不仅能够直接受益于精神病理学或神经病理学、婴儿社会互动、知觉、记忆和情感等经验研究提供的洞见,而且能够间接地受益于这些经验科学中提出问题的方式。”[2]220
六 小结
作为现象学积极介入认知科学与心灵哲学的一种理论路径,自然化现象学为弥合现象学与分析哲学传统的对立提供了有益的尝试。自然化现象学对于回归主观体验和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现象学思想的阐释,不失为可能打开现象学积极介入认知科学与心灵哲学的一种有效途径。此外,自然化现象学所尝试的一些具体路径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能丰富认知科学与现象学的研究。
但是,加拉格尔等人倡导的自然化现象学做法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第一,自然化现象学如何在现象学运动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基础问题。或者说,自然化现象学如何与胡塞尔的反自然主义思想衔接起来,这是一个需要阐述的根本问题。第二,就异质现象学与自然化现象学的关系而言,自然化现象学认为异质现象学不可能在体验问题上保持中立性,因此,自然化现象学区别于异质现象学。但在我们看来,自然化现象学与异质现象学的区别并非像加拉格尔等人所描绘得那样明显。因为,承认中立性与否可能未必影响自然化现象学与异质现象学的研究结果。第三,自然化现象学主张,现象学所关注的现象应当得到科学知识的说明,相反,科学知识的说明同样应当得到现象学的印证。我们对体验的最佳解释应当涉及现象学与科学的整合。尽管加拉格尔等人概括了诸如形式化、神经现象学等一些实现这一整合的途径,但是,正如加拉格尔和扎哈维所分析的,如何切实地实现这一整合,这仍然并不十分清楚[2]30。第四,自然化现象学的做法在更大层面上涉及了对于笛卡尔主义形而上学和计算主义认知观的批判,因此,自然化现象学的研究更需要得到哲学和科学两个层面上的有利支持,否则,它就很难应对来自“正统”现象学家和自然主义认知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双重挑战。
[收稿日期]2011-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