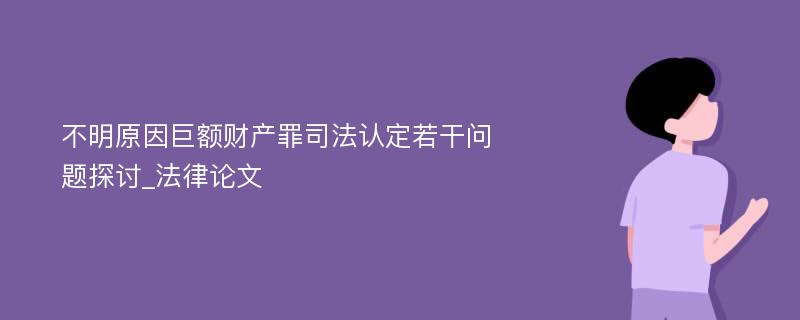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认定若干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巨额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司法论文,财产来源论文,不明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3)03-0086-04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在我国社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变革历史过程中,适应 惩治腐败犯罪分子的需要而规定的一种新罪。198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 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11条开始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997年3月修订刑法第3 95条又予以保留该罪名。但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其开始设置以来至今却一直在司 法实践中存在颇多认定方面的争议,本篇所探讨的就是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是否继承遗产、接受遗赠或馈赠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当司法机关指控被告人拥有超出其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应 论罪处罚时,被告人往往称其巨额财产属于继承遗产、接受遗赠或馈赠。但司法机关对 被告人所提证据线索难以调查核实,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类情况:(1)去世的人是否给 予被告人巨额财产。被告人提出,巨额财产全部或一部系亲朋好友所赠,当问及赠予人 情况时,称已过世,其提出的证据线索无法调查核实。(2)在境外某个地方的人赠予巨 额财产。被告人提出巨额财产全部或一部系由某某所赠,现在境外某个地方,但提不出 具体的联系电话或地址。(3)赠予巨额财物的人在国内某个地方,已失去联系,无法查 找[1](P156-157)。
在刑法学界,解决这些情况的做法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司法机关不应采纳被告人所提供的证据线索,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与常理不符。赠予巨额财产一般应有遗嘱,或赠予文书,或经公证,或经证人证明 。而被告人所提巨额赠予没有任何赠予书证或其他证据,与常理不符。
2.与常情不符。被告人提出的赠予其巨额财产的人与其失去联系,与常情不符。赠予 巨额财产是关系极为密切的表现,或是被告人有恩于赠予人,或是与赠予人关系过密。 根据一般规律,赠予人与被赠予人应保持密切联系,而被告人所称赠予人与其没有联系 ,既违背了社会的一般人情规律,又不能圆满解释接受了巨额财产不与赠予人联系的原 因,这种举证线索不予采信,应认为举证无效,仍属于不能说明来源[2]。
3.是惩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必然选择。国家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目的,是 惩处那些拥有巨额财产,来源不合法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反腐败的有力武器,立法本意 是加重拥有巨额财产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举证责任,其所举证据的要求应是:第一,司法 机关能够予以调查、核实。第二,举出的证据线索应有核实的可能性,如赠予人虽死亡 ,但有赠予人遗嘱或有其他证据,虽不能核实,但也不能否定其真实性。当事人举出的 不能进行调查又没有可能性的线索,司法机关不应采信。
(二)对被告人提供的证据线索应视不同情形区别对待。
该观点认为,对有无继承遗产、接受遗赠或馈赠在大多数案件中也有据可查;但在少 数案件中,存在着既无原始档案可查,又无当事人或证明人的情况,这成为认定被告人 合法收入的难点。被告人最容易也最可能以曾经继承遗产、接受遗赠或馈赠为借口,编 造财产的合法来源,企图逃避法律的追究。在个案中认定被告人全部财产时,不管被告 人是否进行过辩解,对有没有继承遗产、接受遗赠或馈赠都应认真细致地调查核实,如 有这种收入要查清具体的品名及其数额,实事求是地予以认定;如没有这种收入,也要 认真制作调查笔录,以证实被告人编造财产的合法来源。
笔者基本上赞同第二种观点,但在认定被告人的巨额财产是否属于继承遗产、接受遗 赠或馈赠问题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对被告人所举证提出的遗产人、遗赠人或馈赠人去世或在境外及境内而失去联系的 ,应当尽可能寻找这些人的近亲属或其他知情者了解情况,以便查明他们生前或者与行 为人有联系时有无可能遗留下财物或者赠送给财物。
2.全面调查被告人的情况:包括行为人的为人处事,言语行动的可信度,有无经常说 谎、欺诈情形等,以及巨额财产同行为人职务工作有无联系等。
3.对于被告人提出某一部分财产来源于继承遗产、接受遗赠或馈赠,但没有直接证据 能够证实时不妨采用假设和排除法,即首先假设被告人曾经有过继承遗产、接受遗赠或 馈赠,然后对各种可能逐一调查,如果都被排除,就能推定被告人没有继承遗产、接受 遗赠或馈赠。如1992年10月群众举报某区税务专管员邵某某经济上严重反常,该区人民 检察院调查后无法认定其具体犯罪事实。邵某某自己辩解岳父生前赠送给妻子3万元现 金。在假设辩解成立的前提下,经过调查证实:邵某某的岳父和岳母分别于1988年和19 85年先后病故,生前均系一般干部,除工资收入外无其它经济来源,生有两男两女(均 已成家),小女儿系邵某某妻子。其岳父的两个儿子及大女儿除知道父亲生前有3000元 银行存款外,没有其它积蓄,都没有得到过父亲生前赠送的钱物。这些事实足以排除邵 某某妻子曾经接受过父亲赠送3万元现金的可能,从而认定3万元是邵某某不能说明合法 来源的财产。用假设和排除法必须注意:第一,应当尽一切可能;第二,对一切可能都 要逐一排除。否则认定被告人的辩解成立[2]。
二、关于巨额财产是否来源于借贷关系或保管关系的认定
借贷关系与保管关系分别依据于借贷合同与保管合同。按照民法学界的一般观点,借 贷合同是出借人将一定数量的货币或者实物借给借用人处分,借用人依约定归还相同数 量的货币或者相同种类、相同数量、质量的实物的协议。保管合同是保管人有偿地或者 无偿地为寄托人保管物品,并在约定的期限内或者应寄托人的请求,返还保管物品的协 议[3](P348,P376)。
在认定被告人全部财产的过程中,往往会碰到被告人把实际控制着的财产辩解为向他 人借入或代他人保管的问题,为了确认被告人的辩解是否真实,首先尽可能认真调查并 结合已有证据分析判断被告人有否借他人财物或代他人保管财物的可能和必要;其次应 当责令被告人和被告人提供的出借人或委托人提供证据。因为借贷关系和保管关系都属 于民法调整的范围,确定这些财产关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6条“当 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如被告人和被告人提供的出借人或委 托人能提供真实合法的证据,就确认其借贷关系或保管关系成立;否则结合调查材料推 定这些财产为被告人所有。如某市人民检察院在1990年查处某镇党委书记张某时,发现 其有8000元债券来源不明。张某辩解这8000元中,有4500元是向李某某借的,有3500元 是向陈某某借的。由于察觉人民检察院在侦查他的问题,张某事先已与李某某、陈某某 串供,因此李某某、陈某某均伪证曾分别借给张某4500元和3500元,但提供不出借钱的 任何证据和理由,由此推定张某没有借款买债券的必要和可能,进而认定这8000元是张 某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2]。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存在借贷关系或保管关系,司法机关仅仅对公职人员陈述的巨额 财产来源的证据怀疑不实,但拿不出足以推翻这一陈述的充分、确实证据,则不能认定 为“不能说明巨额财产来源合法”。例如,某县检察院接受群众举报,就县公安局科长 谢某修建一幢价值5万元的楼房事,责令其说明建房来源。谢某陈述其亲家刘某(个体户 )借给3万元,好友(个体户)王某借给2万元。刘、王二人均承认借钱给谢某。检察机关 对此陈述虽然怀疑,但拿不出推翻这一陈述的充分、确凿证据,只得撤案[4]。
三、关于被告人供述巨额财产来源于贪污贿赂等其他犯罪所得的认定
关于被告人供认其巨额财产或者支出的部分或者全部系贪污贿赂等其他犯罪所得,但 无其他证据进一步证实,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在刑法学界,有学者认为,根据《刑事 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 以刑罚。因此,对于上述情况,如果虽经多方认真查证,仍不能取得其他证据证实其所 供述的犯罪的,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就按其所供认的罪行批捕、起诉。可以把这种 情况视为财产来源不明,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单纯追缴非法财产 ,而不定罪处罚。
笔者完全赞同以上观点,之所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定罪处罚,关键在于口供 具有非同一般的不可轻信的特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被指控犯有某种罪行、可能受 到刑罚惩罚的人,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用虚伪的口供掩盖其罪行,企图逃避惩 处,就成为经常出现的现象。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受到某种强制措施的限制 ,在他们的心理上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出于恐惧,出于对“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政策的错误理解,或出于其他复杂原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往往可能承 认一些不存在的或者不是自己实施的罪行。从实践经验看,口供虚假的可能性较大,但 又可能是真实的,更经常的是有真有假,真假混杂。这就决定了对于口供绝不能轻易相 信。在只有被告人供述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其是否真实,当然也就不能轻 易相信它是真实的,并据以定罪判刑。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仅以口供作为定案的根据 ,那么,一旦翻供,定案所依据的基础就完全崩溃。这种情况当然不利于维护法律的尊 严。而防止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方法,显然在于不能仅凭口供定案[5](P160-161)。
应当明确的是,关于被告人供认其巨额财产或者支出的部分或者全部系贪污贿赂等其 他犯罪所得,但无其他证据进一步证实,该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行贿人方面的因 素。因为被告人供述其巨额财产或者支出来源于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所得的,可以通 过被贪污、挪用公款的所在单位予以核实;但在被告人供述的巨额财产来源于行贿人的 行贿时,如果行贿人完全予以否认,就会造成无其他证据再予以证实的情况,这在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案中所占比例为数不少。由于刑法第389条、第390条规定了行贿行为可构 成行贿罪,因而很难鼓励行贿人积极主动检举、揭发受贿者的受贿情况,于此情形造成 受贿者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也就在所难免。
四、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家庭成员的不合法收入及其责任的认定
在刑法学界,对于查明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家庭成员的不合法收入的情形,一般认定该 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主要观点是:司法机关通过侦查发现,国 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部分,是其家庭其他成员的不合法收 入,不能认定被责令说明的国家工作人员犯了本罪。家庭其他成员也是国家工作人员的 ,如妻子是国家工作人员,差额巨大的部分是妻子的非法所得,符合本罪特征的,应由 妻子承担相应的罪责。如果家庭其他成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则不能认定为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犯了什么法就以什么法调整。若确实查不出系非法所得,只能以无罪处理, 巨额财产仍归其他家庭成员所有,因为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其他家庭成员没有义务说明 其巨额财产的真实来源[6](P35)。
上述观点以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庭成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为标准来确定能否构成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虽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却忽略了在此情形下该国家工作人员 的有无刑事责任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分为几种情形来认定:
(一)当查明国家工作人员超过合法收入的财产或支出中有一部分属于其家庭成员的不 合法收入时,应当扣除这部分属于其家庭成员的不合法收入,纯属国家工作人员超过合 法收入的财产或支出符合差额巨大标准的,则该国家工作人员只承担这部分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的刑事责任。
(二)当查明国家工作人员超过合法收入的财产或支出全部属于其家庭成员的不合法收 入时,则该国家工作人员并不一定能完全免除承担刑事责任。其根据在于:
1.如果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庭成员也是国家工作人员,因其自己的不合法收入而构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则该国家工作人员除非全然不知情;否则,事前通谋且明知是其 家庭成员的不合法收入而帮助隐匿、转移或者共同使用的,在司法机关责令说明这些不 合法收入的来源而不能说明或拒绝说明,可与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其家庭成员一起成立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共同犯罪。
2.如果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庭成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因其自己的不合法收入而构成 盗窃、非法经营、走私等罪,则该国家工作人员除非全然不知情;否则,明知是其家庭 成员的不合法收入而帮助隐匿、转移或者共同使用的,可与其家庭成员成立连带犯罪, 即窝藏、包庇罪。
3.如果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庭成员(无论是否国家工作人员),因其自己的不合法收入 不构成任何犯罪,例如因差额巨大的数额不符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案标准,或者 尚未达到盗窃、非法经营、走私等罪的数额标准,则该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构成任何犯罪 。
五、如何处理不能认定是否“说明”的案件
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对来源不明的财产,如果拒不说明或虽“说明”但被否定,不 能再说明的,可以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如果说明后被查证属实的,以查证的结 果确定案件性质,对于这些在认定上一般没有疑问;但如果行为人说明“合法”来源后 ,经查证后无法确定是否属实,既不能证其“真”,也不能证其“伪”,对于这样的案 件应如何处理?这在刑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对这类案件应认定行为人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主要理由是:对 于犯罪案件真相的证明责任一般是由司法机关承担的,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 ,而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中,对此却是个例外,即国家立法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实际上是将证明责任转移向了被告方,立法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 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 分以非法所得论……”行为人的“说明”经查证不能证明是否属实,实质上是行为“说 而不明”,仍然属于“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范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认定 其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符合立法规定的构成要件,也符合立法设置本罪的基本精 神。
另一种观点认为,上述观点是不可取的。主要理由是:我国立法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让行为人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但这与有罪推定是有本质区别的。有罪推定的主 旨是: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就是有罪的。即行为人要承担不能证明自己无罪的法律 后果。而我国立法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有其特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并没有 让行为人完全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明责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的有罪结论,不是 行为人不能履行“说明”义务的绝对后果,而是司法机关全面调查核实不能确认财产合 法,并且根据证据分析确信其为非法的结果。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机关 对所有案件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实有罪或无罪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在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案件中,司法机关的这种证明责任并没有免除。新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不能 “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而没有用“证明”,正是为了避免实践中的有罪推定。因此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被告人尽管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但并不同于有罪推定情 况下的证明责任,案件的主要证明责任,仍应由司法机关承担。行为人“说明”了其财 产的来源,这实质上是无罪证据,司法机关对其不能查实,既不能断其“真”,亦不能 证其“伪”,在这种情况下认定行为人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但有违我国程序规 定的一般原则,也不符合刑法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精神。所以,对于行为人说明 “合法”来源后经查证无法确定是否属实的案件,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7](P518-519)。
笔者认为,该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既不能断其“真”也不能证其“伪”的真伪难 辨的平等格局实难存在,事实是:行为人的巨额财产或者来源于合法的“真”可能性大 ,或者是来源于非法的“伪”可能性大,不可能存在“真”与“伪”等量齐观的情形。 司法机关应该针对行为人有关巨额财产来源的“说明”作出或“真”或“伪”可能性大 的判断,以便有利于明确界定行为人的巨额财产的性质问题。
收稿日期:2003-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