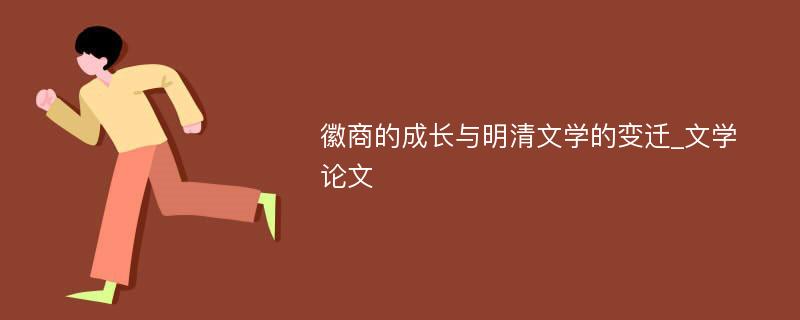
明清徽商的壮大与文学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徽商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前代文学相比,明清文学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在精神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复杂、多方面的,其中,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当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在诸多社会经济因素中,商人阶层的壮大又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商人作为文学形象在明清文学中的呈现有比较多的论述,也有的学者从“士商契合”的视角探讨明清文学的转型问题①。但对于商人阶层的壮大与明清文学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从明清文学生态系统变化角度的探讨还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将侧重以徽商为例,对此予以讨论,期望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明清文学发展的外部规律,从而更清楚地认识文学史发展的脉络。
一 商人阶层的壮大
作为社会职业的商人,早在先秦就已经出现。《尚书·酒诰》记载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的弦高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商人。司马迁作《史记》,专列《货殖列传》,为汉代及其以前的商人留下了难得的一笔记录。在他的史笔下,“既雪会稽之耻”的范蠡变名易姓做了商人;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也取得了成功;周人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成为天下“治生”之祖;猗顿靠盬盐起家,郭纵以铁冶成业,他们的财富能够与王者相比;巴蜀寡妇清靠着祖上的丹穴,“用财自卫,不见侵犯”。《汉书》亦列《货殖传》,撰写了范蠡等十三位商人的传记。此后,受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正史不再为商人列传。但是,商人作为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角色仍然活跃于各个时代。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指出,在16-19世纪,“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②。弗兰克通过大量的事例和东西方同时期的比较对西方中心论提出了质疑。而16-19世纪,“中国中心”地位的确立,显然是由中国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促成中国经济地位提升的原因当然有多种,生产力的发达,人口的增长,城市经济的活跃,都是其原因,但从商人数的增加、经商风气的蔚起,从而促进商品流通的活跃,无疑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要准确地统计出明代或清代商人在社会职业中所占的比例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第十章《其他人口结构》在考述了明代设立“商籍”后有一个推测:“1630年,中国人口约为19200万,这一年的中国城市化率大约为8%,如是,城市人口大约1536万。假定商人及其家属占城市人口的40%,则全国城市商业人口大约为610万。加上乡居的商业人口,明代商人及其家属的人口总数可能达到700万”。③限于文献的不足,这一数字还只是推测。但我们可以以徽州为例看出大致的情形。从明代中叶开始,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与其他地区相比,徽州人经商的和从事农耕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明代中叶后的各种文献记载里,我们都可以经常看到,徽州人从事农耕的只占到十分之三,而经商的则达到十分之七。例如,出生于徽州的明代文人汪道昆就说过:“新都业贾者什七八。”④这个比例当然只是指男性,即便如此,也是十分惊人的了。徽州人外出经商,并非个体式的,而是成群结队,明末徽州文士金声就这样描述道:“夫两邑(歙、休两县)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且其人亦皆终岁客居于外,而家居者亦无几焉。”⑤换言之,徽州人的经商是群体性的行为,徽商其实是一个商帮。仅仅是这个地区,商人的数量都是极为众多的。
商人阶层的壮大,与自然环境、人口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徽州经商风气的形成,就与地理环境大有关系。这个地方是山区,土地偏少而且贫瘠,随着人口的增加,生存发生困难,所以大批徽州人外出经商谋生,民国徽人吴自法撰《徽商便览》就说道:“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遇山川平衍处,人民即聚族而居之。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事业以起。”⑥关于人口增长的问题,何秉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将洪武二十六年和嘉靖二十一年各省人口加以对比,得出了“中国的人口从14世纪后期的约6500万增加到了万历二十八年的约1.5亿”的估测⑦。人口增长,土地有限,加上皇室和地主兼并土地,必然带来职业结构的调整,商人的比例越来越大。
明代中叶以后商人阶层不断壮大的事实,还有其他文献可以佐证。明清文人为商人撰写了为数不少的传记,例如大名鼎鼎的王世贞写有六十四篇,汪道昆写过七十二篇,大量商人的生活经历和行状都赖他们的笔墨得以保存。大量的商人传记说明商人的确成为了一个数量巨大、影响力甚强的阶层。余英时教授在《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一文中还从人口和科举名额的角度指出读书人“弃儒就贾”现象的发生原因。他引文徵明《三学上陆冢宰书》为据,得出以下数字:苏州地区一千五百名生员,三年之间只有五十人可以成为贡生或举人,则每一生员三年之中的成功率只有三十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读书人与其盘旋于成功率低下的科举道路上,不如“弃儒就贾”⑧。
二 商人与文学家的交往
明清时期,商人与文学家交往的事实屡见于文献记载。周晖在《二续金陵琐事》中记载的一段逸事常常为人们所征引:“凤洲公同詹东图在瓦官寺中,凤洲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东图云: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凤洲公笑而不语。”这则逸事对于商人和文人都有讽刺,却道出了两者交往非常密切或者说互相利用的事实。
周晖所记的“新安贾人”其实就是徽州商人,他们与文学家交往的密切程度最高,这是因为徽州地区向来有着“重儒”的传统。在大量的徽商传记里可以看到,很多商人都是因家计窘迫或者科举不利而走上经商的道路。因为曾经读书,即使他们经商之后,也仍然留心于经史诗赋,保持着文人的风调。如明代休宁商人汪贵,“自幼奇伟不群,读小学、四书,辄能领其要。于是通习经传,旁及子史百家,至于音律之妙,靡不究竟”⑨。又如明代歙县商人郑作“字宜述,号方山子。尝读书方山中,已,弃去为商。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识者谓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⑩。商人因为和钱打交道,所以形象往往带有铜臭气。可是这位叫郑作的明代徽商却大不一样。他号方山子,虽然四处经商,却“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难怪熟悉他的人都说:“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不仅如此,郑作在诗歌创作上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也记载了他的身世和诗歌创作成就。因此,徽商虽然是商人,却是有文化素养的商人,这正是徽商留下的历史背影。
正因为如此,从明代中叶开始,徽商——新安贾人——和当时的文学家们就有了非常密切的交往。在一般情形下,徽商“贾而好儒”,是为了得到文士们的肯定,以获得精神上心理上的满足;同时,他们广结文士名流,也能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经商过程中获得更有力的支持。如明代嘉、万间的歙县商人方勉柔,从小读书,因为家计艰难,不得不到开封经商。当生意做得很大以后,他就“谢去游闲,专精化居,所接者皆端人正士,虽贵倨如周蕃及诸戚畹,亦且折节下交,争相引重”(11)。明代休宁商人陈尤德“长嗜学古,博通群书。性孝友,然意气自豪。家世素封,善交游,海内名流恒欲得而交之,故座客常满,樽酒不空,有北海之遗风焉”(12)。明代歙县商人王廷宾“商游吴、越、齐、鲁,且性颖敏,好吟咏,士人多乐与之交,而诗名日起”。有人对他的母亲说:“业不两成,汝子耽于吟咏,恐将不利于商也。”他母亲回答说:“吾家世承商贾,吾子能以诗起家,得从士游幸矣,商之不利何足道耶!”(13)这些传记资料多少都有些夸大事实的成分,好像文士们真的对徽商“如蝇聚一膻”,但它们也充分说明了徽商与文士们密切交往的事实。
明末清初的徽商汪汝谦可以算得上商人与文人交往的典型人物。他“号松溪道人,太学生,生于明季,慕西湖之胜,自歙县丛睦迁杭州,遂家钱塘,居缸儿巷,延纳名流,文采照映,董尚书其昌以陈大邛推之。制画舫于西湖,曰不系园,曰随喜龛,其小者曰团瓢,曰观叶,曰雨丝风片。又建白苏阁,葺湖心、放鹤二亭及甘园、水仙、王庙,四方名流至此,必选伎征歌,连宵达旦,即席分韵,墨汁淋漓。或缓急相投,立为排解,故有湖山主人之目”(14)。凭着资财的富有,他在西湖建造了多个画舫,以此延揽文士,交接名流,享受湖山之胜和声歌之乐。董其昌、陈继儒、王思任、茅暎、李渔、钱谦益等明末清初的文士均曾到过他的画舫和园林,并题额赋诗。除了和文人交往之外,汪然明还与当时的名媛才女有密切来往,如王薇、林天素、杨云友等,其留存的《听雪轩集》就是专收写杨云友诗作的集子。他和柳如是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柳如是到杭州后,他不仅为之安排了住处,而且对她多方关照,后来,又刊刻了她的《湖上草》和《尺牍》。对此,陈寅恪《柳如是别传》(15)曾作详细的考证,兹不赘述。
商人与文学家的交往有种种情形。有的纯粹是附庸风雅,有的则是崇尚风雅,也有的商人本来就品第不俗,不宜一概而论。例如清代扬州的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他们是商人,但嗜好文化,研习经史,马曰璐筑街南书屋,藏书逾十万卷,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馆,马曰璐儿子马振伯献书七百七十六种。他们自己也从事诗文创作,马曰琯著有诗集《沙河逸老小稿》六卷、词集《嶰谷词》一卷,马曰璐有《南斋词》二卷。他们又筑小玲珑山馆,成为文人雅集的场所。在这里,他们曾经举行过多种文会活动,如在乾隆八年(1743)十月,马曰琯从金陵移古梅植于馆内,厉鹗、全祖望等十多位文人都有诗吟咏唱和;乾隆十二年(1747)五月十五日,马曰琯邀集文友们为“重五之会”,厉鹗撰文记载道:“岁丁卯五月十五日,马君半槎招同人展重五之会于小玲珑山馆。维时梅候未除,绿阴满庭,遍悬旧人钟馗画于壁……遂人占一画,各就画中物色,赋七言古诗一篇。”(16)类似这样的活动很多,它们在参与者的诗集文集中都有记录。《扬州画舫录》记载道:“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砚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17)除此以外,马氏兄弟还为当时的文学家们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如著名词人和诗人厉鹗利用他们丰富的藏书辑录了《宋诗纪事》一百卷,而马氏兄弟也分别参与其中;在文友们去世后,他们都为之料理后事,并为之刊刻诗文集。据全祖望记载,姚世钰去世后,“吾友马曰琯、曰璐、张四科为之料理其身后,周恤其家,又为之收拾遗文,将开雕焉,可谓行古之道也”(18)。而全祖望本人眼疾严重,马氏兄弟寄书请他到扬州,为之请医疗疾。正因为如此,全祖望去世的时候,特命弟子董秉纯将其所抄文集五十卷交给马氏藏书楼(19)。作为商人的马氏兄弟对文人们尊重有加,与文人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以自己的经济实力,为一批潦倒的文人提供了从事文学创作、文史研讨的物质条件和温馨氛围,抚慰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保持了文化的自尊。
商人和文人,有着必然的互相利用的关系。商人从和文人的交往中获得精神满足,或者提升社会地位,从而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商人的银子,又是文人们获得充足笔资的来源。但文人对于商人既有利用,在经常的交往中也逐渐对商人以及商人的社会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并给予理性的肯定。王阳明提出“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20)。在他看来,职业无贵贱之分,即使是作商人,只要善于修身养性,也能够成为圣贤之人,这一认识,客观上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同时期的哲学家何心隐认为:“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21)他把社会阶层重新作出划分,认为依次应该是:圣贤、士、商贾、农工。商贾尽管依然排在士的后面,但是已经跃居农工之前,而不是排在“四民”之末了。明代先哲李贽则给予了商人以充分的同情:“且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淘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22)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也提出“工商皆本”的观点:“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23)这些思想观念,悄然渗透到明清两代的文学创作之中,不仅使得商人生活成为重要的文学题材,许多作品对商人的描写,与以往文学的贬斥态度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贬斥乃至嘲笑,也有同情和赞美。
三 商人与文学题材
商人与文学家的交往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传统诗文中,商人题材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在明代中叶后的文集中,商人传记的数量之多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有学者统计,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有墓志铭九十篇,为商人所作的十五篇,占总数的16.6%;《弇州山人续稿》中墓志铭二百五十篇,为商人所作的四十四篇,占总数的17.6%(24);出自徽州的汪道昆有商人传记七十篇,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中商人传记同样很多。这些传记的文体大多是寿序、墓志、行状之类,大部分缺乏文学性,但它们往往表现了作者对商人的态度,记载了当时的文士和商人之间关系密切的事实,具有史料价值。
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商人传记有文学性可言,作者能够通过人物的对话、细节,写出所传商人的性格和精神,例如汪道昆的《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
处士生九年而孤,戴子之如适,既从程登仕受室,请受经为儒。戴泣下,而执处士手命曰:“自而之先,诸大父鼎立,而父从诸父,固当狱立,不幸崩析,独不得视三公……且而父资斧不收,蚕食者不啻过半,而儒固善,缓急奚赖耶?”处士退而深惟,三越日而后反命,则曰:“儒者直孳孳为名高,名亦利也;藉令承亲之志,无庸显亲扬名,利亦名也。不顺不可以为子,尚安事儒?乃今自母主计而财择之,敢不惟命!”于是收责齐鲁,什一仅存。瞿然而思:“去国余三千里,徒以锥刀而沮将,毋,即巨万何为?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贩缯则中贾耳,恶用远游?”乃去之吴淞江,以泉布起,时时奉母起居,捆载相及,月计者月至,岁计者岁输。戴孺人笑曰:“幸哉孺子。以贾胜儒,吾策得矣!脱或堪舆果验,无忧子姓不儒。”(25)
汪道昆传写的是当地一个叫吴良儒的人,上引的这段文字是写其“思想转变”的过程,他本来是想走读书业儒的道路,而且已经拜师受业,但是,养母戴氏向他分析了家庭经济窘迫的现实,要他按照先后缓急的思路进行选择。他经过了一番思考,选择了经商;在跑了一趟齐鲁之后,他分析了经商的策略,又选择经营布业,并且以“坐贾”的方式,不影响奉母行孝。这段文字其实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吴良儒本人,一个是他的养母戴氏。对于吴良儒,汪道昆使用了对话和独白的手法,表现了他由“儒”而“贾”的思想转变以及对商场策略的分析,从而写出了他作为商人的精明性格;对于戴氏,除了使用对话的手法外,他用“泣下而执处士手”和“笑曰”两个细节,将她的前忧后喜的神态以及对为贾的开明态度表现得十分生动。这只是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像这样的商人传记,为数并不少,大约是可以作为文学作品读的。
相对于文人撰写的商人传记,戏曲小说以商人及商人生活为题材的现象更为突出。正如许多研究者早已注意到的,形形色色的商贩作为文学的新主角在明代中叶以后的文学作品中粉墨登场了。长篇小说《金瓶梅》以商人西门庆作为主要人物来描写,“三言”“二拍”等短篇小说集中,商人形象更为丰富。仅以徽商为例,据我们统计,“三言”中涉及徽商的篇目有九篇,“二拍”中涉及篇目有八篇,《杜骗新书》涉及篇目有五篇,《石点头》涉及篇目有三篇。这些作品既真实地表现了商人阶层的活动和特征,也反映了文人对商人的微妙心态。在文言小说和戏曲里,描写商人的作品和笔墨也很多,对此,已有学者作过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26),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
相对于诗歌和散文而言,作为叙事文学的戏曲和小说,必须有广泛的读者对象。反之,读者的审美趣味也决定了文学体裁的变异和革新。伊恩·P·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曾经分析了读者大众对小说兴起的作用,作者从人口中受教育的比例、收入程度和书籍价格、闲暇时间等三个方面入手,指出:“尽管读者大众的队伍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但一般说来它还未扩大到商人和店主的范围之外去,比较幸运的学徒和家庭佣人是很重要的例外。虽然它的人数有了增加,但它主要还是由日益增多的富裕的人数众多的与商业和制造业有关的社会集团中得到人员补充。”(27)明代中叶后小说戏曲的兴起和繁荣,同样是由读者队伍的受教育程度、消费能力以及闲暇时间所决定的。按照这些条件,即便是在明代中叶,除了文士,也只有商人才是戏曲小说的主要的读者群。商人有购买能力,据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万历间舒载阳刊刻的《封神演义》,封面上盖有“每部定价纹银贰两”的木戳。这个价钱,按照万历时的平均米价,可购米三石有余(28),一般的农民或工匠恐怕是难以购买的,唯有商人的消费能力可以接受。商人的文化水平让他们有阅读能力,他们有的从小就准备读书应考,只是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或科举道路过于拥挤才放弃科举道路,有的在长期经商的过程中逐渐读书识字,因此不同于文盲状态的农民和工匠。他们也有闲暇时间,漫长路途上的寂寞、生意之余的时光,都需要打发,和农民、工匠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完全不一样。
当然,仅仅有这些条件还不够,决定体裁变化的还有阅读兴趣或者审美兴趣。商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他们又不同于饱读诗书的文人。虽然有少部分商人仍然对高雅的文学典籍感兴趣,但大部分商人在经商之余的阅读,更侧重于休闲娱乐式的阅读。有的文献记载就透露了商人对于小说阅读的兴趣,例如,余英时教授注意到,顾宪成的父亲是一位商人,早年就对小说尤其是《水浒传》特别有兴趣;清代道光年间的一位叫舒遵刚的徽商也说道:“人皆读四书,及长习为商贾,置不复问,有暇则观演义说部。”(29)汪道昆小的时候,喜好阅读小说野史(30),前提也是他的商人家庭里有这些书籍。关于商人喜好戏曲的文献记载更多,那是因为戏曲不仅是读的,还是演的,可以满足他们的声色娱乐需要。明代中叶后,文人蓄养家班很普遍,商人有的是银子,自然也不甘寂寞,出自徽商世家的潘之恒就特别喜爱戏曲,同时,他也记载了汪季玄和吴越石两个徽商蓄养的戏班的情况,并赋诗赞扬戏班的演员,而吴越石的家班还演出了汤显祖的《牡丹亭》。冯梦祯在《快雪堂日记》里提到他曾经观看过“吴徽州班”的演出,应该也是徽商蓄养的戏班。既然蓄养了戏班,演出就不能没有剧本,商人们自然也成为戏曲剧本的读者和需求者。商人的这种审美趣味,显然也是小说戏曲勃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商人与文学传播
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明代中叶后的文学传播发生了重要变化,那就是大量文学作品得到刊刻。
商人对于文学作品的刊刻,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富有而具备很高文化素养的商人的刊刻。他们出资刊刻文学作品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利,而是为了保存文学遗产,或者是出于尊敬文学家的动机。二是以刻书为商途,刻书成为他们获取利润的新的商业领地。他们刻书的目的就是赢利,但他们善于把握书籍市场的需要,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学传播。
以保存文学遗产和尊敬文学家为目的的文学刊刻,在徽商中有较多的事例。这是因为徽商秉承了徽州祟尚文化的传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文化素养也很高。他们的刊刻以保存文学遗产为主,同时也留心于当代文学家的创作,所刊刻的书籍质量精良。明代后期的汪廷讷是一位戏曲家,也是一个徽商,他开设了环翠堂书坊,不仅刊刻了自己创作的戏曲作品《环翠堂乐府》,还刊刻了《文坛列俎》、《元本出相西厢记》和王磐、冯惟敏、梁辰鱼、陈所闻等人的散曲集。清代,以刊刻书籍而得名的徽商更多,上文所引的马氏兄弟不仅刊刻了自己的诗词集,也刊刻了他们和其他文人酬唱的诗文作品,马曰琯刊有《韩江雅集》、《焦山纪游集》、《林屋酬唱集》,马曰璐则刊刻了《摄山游草》;他们还刊刻了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如王士祯的《感旧集》、汪士慎的《巢林集》,乃至不惜千金刊刻朱彝尊的《经义考》。著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鲍廷博也是一位徽商,他原籍徽州歙县,“少习会计,流寓浙中,因家焉。以冶坊为世业”(31)。《四库全书》开馆时,他献书三百余种,所刊刻的《知不足斋丛书》享誉士林,还刊刻了《聊斋志异》等多种文学作品。扬州程梦星是徽商世家,他曾经中进士,却以亲丧归养扬州,不复出仕,把精力用于经商、读书和著述上,既刊刻了自己的《今有堂诗集》,也刊刻了《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等前代作品;和马氏兄弟一样,他在扬州也和文士们多所唱和,他把这些唱和之作刊刻为《广陵唱和集》、《山心室唱和甲乙集》、《城南联句诗》等。这些商人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对文化、文学事业的热爱,为保存文学遗产和传播当代文学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中叶后,书坊刻书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书坊主可以说就是靠刻书发财的商人。他们注重成本和获利的核算,因此,有些书贾不惜损害质量以求得利润,明人郎瑛就记载了福建书商做假的情形:“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害。盖闽专以货利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32)但是,书坊主们的刻书适应市场的需要,注重读者的阅读兴趣,注重当代文学作品特别是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的刊刻,在书籍刊刻的形式上也有许多新的创造发明,因而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文学传播和文学创作,可以说,明清两代文学创作特别是通俗文学创作的兴盛局面是和书坊刻书的推动作用分不开的。
明万历间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说道:“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刻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恶滥,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近来吴兴、金陵骎骎蹈此病矣。”(33)根据谢氏的这段话,徽州人开设的书坊的刻书质量在当时应该是最好的。例如明代徽州歙县人汪云鹏在金陵开设玩虎轩书坊,曾经刻印过包括焦竑编定的《养正图解》、王世贞辑录的《有像列仙全传》等大量图书。戏曲小说是这个开设在南京的书坊突出的刊刻特色,它刊刻的戏曲作品有《北西厢记》三卷;《琵琶记》三卷;《重校孝义祝发记》二卷;《新镌红拂记》三卷;《会真记》一卷。关于玩虎轩本《琵琶记》,黄仕忠博士评论说:“玩虎轩本在校雠上颇能间采众长……”它作为昆本系统中较好的改定本,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它的雅致的出目取代了种德堂本、唐对溪富春堂本、唐晟刻本等粗率的命名,成为晚明《琵琶记》标准出目而通行于世。晚明各种批评本均以玩虎轩本为底本。”(34)从刊刻质量上看,玩虎轩本比起同期的富春堂、继志斋等刊本无疑也更加精致,有图三十八幅,且多为其他书坊所翻刻。又如尊生馆,也是明代中叶后有名的书坊,该坊主人为黄正位,歙县虬村人,它曾经刊刻过瞿佑《剪灯新话》和李昌祺《剪灯余话》两部文言小说集;该坊还刊刻了杂剧选集《阳春奏》,共选刊三十六种元杂剧,现存马致远《西华山陈抟高卧》、戴善夫《陶学士醉写风光好》、罗贯中《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三种。再如胡文焕,是万历间著名的书坊主,所刻书籍甚多,尤以《格致丛书》最有影响。胡氏刊刻的戏曲选本《群音类选》篇幅浩大,共约四十六卷,今存三十九卷。全书分官腔类(昆腔)、诸腔类(地方声腔)、北腔类、清腔类,为现存散曲和戏曲最丰富的选本,尤为可贵的是保存了五十九种已经散佚的戏曲作品片段,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他如汪士贤编刻的《汉魏名家集》、潘是仁编刊的《宋元名家诗集》、孙默留松阁刊刻的各家词集等(35),对保存文学遗产、传播当代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就中国出版史而言,明清两代无疑是一个繁荣时期。无论是官刻、家刻、坊刻数量较之宋元时期都突飞猛进,所刊刻的书籍种类大为丰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出版业的商业化,书籍刊刻的技术和水平得到了提高,徽州制墨名家程君房创造了套版印刷术,同样是徽州人的胡正言则创造了彩色印刷术。在徽商和徽州籍文士刊刻书籍需求的推动下,徽州又走出了以虬村黄氏为代表的一大批刻工,他们雕镌的书籍版式精美,而精美的版画插图更让人赏心悦目。凡此,都促进了文学传播,进而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
五 商人的文学创作
明代中叶以后,商人不仅与文人的交往十分密切,而且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从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构成了商人创作的现象。
商人从事文学创作的现象,仍然突出地表现在徽商群体中。徽州“重儒”的文化传统,徽商的富有程度,都使得他们较之其他商帮在文学上表现得更为出色。在徽州存世的家谱和地方志里,就有不少关于徽商创作诗文的记载,例如明代中叶歙县商人郑孔曼,在经商的同时,游历各地,他“虽游于贾,然峨冠长剑,襃然儒服,所至挟诗囊,从宾客登临啸咏,翛然若忘世虑。著骚选近体诗若干首,若《吊屈子赋》、《岳阳回雁》、《君山吹台》诸作皆有古意,称诗人矣”(36)。与郑孔曼同时的歙县商人黄长寿,别号望云,他在扬州经营盐业,“性喜吟咏,所交皆海内名公,如徐正卿、叶司徒等,相与往来赓和,积诗成帙,题曰《江湖览胜》并《壬辰集》”(37)。清代黟县商人胡际瑶“虽业商,然于诗书皆能明大义,舟车往返,必载书箧自随。每遇山水名胜之区,或吟诗或作画以寄兴,著有《浪谈斋诗稿》一册”(38)。陈建华搜集了一些有名家品题的徽商诗文集的记载:郑作,字宜述,歙县人,有《方山子集》,李梦阳作序;余存脩,歙县人,有诗集《缶音》,李梦阳作序;其子余育,李梦阳为之作传;程汝义,休宁人,王世贞为其诗集作序;吴德符,歙县人,胡应麟为其诗集作序。(39)其他如扬州马氏兄弟各有诗集和词集流传,乾隆间扬州总商江春与其弟江昉也有《新安二江先生诗集》之刊刻。由此可见,商人从事文学创作,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
对于明清时期商人的文学创作,目前尚未展开研究,这里仅以晚明时期的汪汝谦为例略作述评。
汪汝谦是留下诗文作品比较多的徽商,今存光绪间刊刻的《丛睦汪氏遗书》,收录了他的《不系园集》、《随喜龛集》、《绮咏》、《绮咏续集》、《西湖韵事》、《梦草》、《听雪轩集》、《游草》、《闽游诗纪》、《松溪集》、《梦香楼集》。其中,《西湖韵事》收录其《重修水仙王庙记》、《三贤祠记》两篇文章,《不系园集》、《随喜龛集》、《梦草》、《梦香楼集》均收录与其酬唱的文人诗歌,其余则为其本人创作的诗集。这些诗文较全面地反映了作为商人的汪汝谦与文士才女们交往的诸多情形和他个人的生活状况,从中也可窥见晚明的文化风尚。例如《不系园集》和《随喜龛集》收录的文人墨客以及名媛才女们在汪氏所造的“不系园”和“随喜龛”两条游船上诗酒唱和的作品。关于“不系园”,汪汝谦在卷首记其建造动机和过程道:
自有西湖即有画舫。武林旧事艳传至今,其规制种种已不可考识矣!往见包观察始创楼船,余家季元继作洗妆台,玲珑宏敞,差足相敌。每隔堤移岸,鳞鳞如朱甍出春树间,非不与群峰台榭相掩映,而往往别渚幽汀,多为双桥厌水,锁之不得入,若孤山法埠,当梅花撩月,莲唱迎风,令人怅望,盈盈如此衣带,何故高韵之士又驾一蜻蛉出没如飞,骄笑万斛舟,为官为估,徒豪举耳。……癸亥夏仲为云道人筑净室,偶得木兰一本,斫而为舟,四越月乃成,计长六丈二尺,广五之一。入门数武,堪贮百壶;次进方丈,足布两席;曲藏斗室,可供卧吟;侧掩壁橱,俾收醉墨。出转为廊,廊升为台,台上张幔,花辰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惊飙蹴浪,欹树平桥,则卸栏卷幔,犹然一蜻蜓艇耳。中置家童二三,擅红牙者俾佐黄头,以司茶酒,客来斯舟,可以御风,可以永夕,追远先辈之风流,近寓太平之清赏。陈眉公先生题曰不系园,佳名胜事,传异日西湖一段佳话,岂必垒石凿沼园丘壑,而私之曰我园我园也哉!
以西湖景为自家景,斫木兰为舟,以画舫为园林,家童红牙,茶酒雅会,这个“不系园”的确是个风雅之极的创意,同时也是一个激发文人墨客和名媛才女吟咏诗歌的场所,《不系园集》中就收有陈继儒、茅暎等二十九位名士文人以及才女王微的诗作,于中见出当时舟中胜会的情景,也是一部“主题诗集”。
汪汝谦除了和名士文人交往外,还和柳如是、王微、杨云友、林天素等名媛才女们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他以自己的富有为她们提供了栖身和与文士们交往的便利条件,给她们以帮助,另外一方面,他用男性的情感给她们以怜爱,甚至也发生了爱情。这些微妙的情感在他的诗作里得到了细致的表达。例如王微,他们之间似乎只是朋友的关系,唱和的作品很少;对于柳如是,他有倾慕,却未生发出男女感情,《游草》中有《余久出游柳如是校书过访舟泊津关而返赋此致怀》,陈寅恪先生据此推断柳如是崇祯十一年的踪迹,另有《无题》一首:“明妆忆昨艳湖滨,一片波光欲荡人。罗绮丛中传锦字,笙歌座上度芳辰。老奴愧我非温峤,美女疑君是洛神。欲访仙源违咫尺,几湾柳色隔香尘。”陈寅恪先生认为此诗“不仅藏有河东君姓名,颇疑此诗中尚有河东君之本事。”(40)就诗意而言,他对柳如是欣羡有加,却又道“老奴愧我非温峤”,不能够像温峤那样再来一段风流韵事了。对于杨云友,他似乎有感情,但这种感情既有才艺上的倾慕,也有男性对女性的怜惜,《听雪轩集》所收诗作均是他为杨云友所作,既有与其他文士一同到杨处观画听琴、登“随喜龛”画舫游览西湖的唱和,也有他独自看望杨云友时的情感抒发,如《雪后过云友》:“幽窗浑曙色,几榻净无尘。却喜宜人处,花飞笑语亲。”这种感情处在浓淡之间,亲而不腻;而在云友去世后所写的诗却带有深切的伤感,又表明他对这份感情的珍惜和重视。相比较而言,他对林天素的感情已完全是爱情了。《梦草》也称得上是一卷“主题诗集”,卷首有汪汝谦写的《幽窗纪梦》一篇,记他梦中遇一女郎,示其林天素之画,他醒后翻检林天素的画作,感慨万分。或许汪氏当时将此梦予以公开,陈继儒、王思任等文士各赋诗吟咏此梦,此集所收即为他们的咏梦之作。《闽游诗纪》为崇祯十四年汪汝谦福建之游所写诗作,陈寅恪先生认为汪氏此行是“访林天素之行”(41)。集中有《福州访林天素,知已移居建宁赋怀十首》,其一道:“不接风神已廿年,芳堤花下每相怜。自从南浦消魂后,何至三山复黯然。”其七曰:“凭将双履轻千里,半为名山半为君。却讶相寻无定踪,不知何处觅行云。”对林天素的忆念之情,对未遇她的失望、黯然之情均为浓挚。集中有多篇未见林天素时的忆怀之作,但在见到林天素后,林天素似乎并没有和他重燃当年的感情,最后他不得不和她分别,集中有《别林天素》四首,其四曰:“一觞一咏一呜咽,肠断春深泣杜鹃。若得重逢如此日,恐应多出再生缘。”陈寅恪先生说:“所可笑者,然明此行本专为访觅林天素,但天素终未能与之偕归西湖。”(42)但诗中表达的伤感凄切之情倒是非常浓烈的。
就汪氏现存作品看,大多是记录自己在西湖的风雅生活,或者通过和文士们的酬唱显示自己的风雅,像对林天素那份真切的情感的抒写已属难得(43)。至于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对明末社会动荡的忧虑,似乎完全不是他的创作题材,这样的诗文社会意义很有限,也恰恰显示了商人文学创作的局限性,从而和文人创作有了截然的分野。但是,他们在作品中所表达的丰富的感情,对山水风光的描写,对一定历史时期人情风物的记录,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明清时期的商人创作应该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文学史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既有文学内部因素的融合和推助,又有外部因素的影响、激发和制衡。对每一时期文学发展规律的分析和把握,内、外因素都应该予以注意,不可偏废,这样才可能全面描述文学史的发展面貌。如果我们把一个时期的文学视为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衡的生态系统的话,明清两代商人阶层的壮大,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因素,则实在改变了以往的文学生态:他们不仅是文人士大夫们频繁交往的对象,而且因彼此的需要带来了文人士大夫们思想观念乃至深层心理的变化,从而外化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之中,丰富了文学题材,也带来了文学体裁的变化。商人出于“好儒”或牟利的动机,促进了文学传播,进而繁荣了文学市场,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文学创作。还有一部分商人也加入了文学创作队伍,使作家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因此,商人阶层的壮大实在是明清文学面貌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因素,需要我们认真地审视和分析。
注释:
①近年来,关于商人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有邵毅平的《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侧重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商人题材的梳理。较早关注商人与文学发展关系的当是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其第一编第三章《元末江浙文学的社会背景》中论述了“士商关系的历史性转折”问题,第五编第一章《晚明江浙文学与人性解放思潮》中论述了“晚明江浙地区士商关系及其观念形态”问题。陈书录的《儒商及文化与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以及相关论文进一步关注到商人与文学史发展之间的关系,如《王阳明的儒商伦理及重商思想与明代中后期的雅俗文学》、《士商契合中转向俚俗与性灵》等,即就此问题展开了论述。
②[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③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
④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七《阜成篇》,黄山书社2004年版,372页。
⑤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四《与歙令君书》,光绪十七年刊本。
⑥吴自法《徽商便览·缘起》,1919铅印本。
⑦转引自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第201页。
⑧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见《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⑨休宁《汪氏统宗谱》卷三十七《传》,转引自《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41页。
⑩歙县《郑氏宗谱·明故诗人郑方山先生墓图志》,转引自《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第450页。
(11)《方氏会宗统谱》卷十九《坤斋方君传》。《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第447页。
(12)休宁《陈氏宗谱》卷三,转引自《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第449页。
(13)歙县《泽富王氏宗谱》卷四,转引自《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第457页。
(14)《丛睦汪氏遗书》卷一所刊传记,光绪刊本。
(15)见《柳如是别传》第四章《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三联书店2001年版。
(16)厉鹗《樊榭山房续集集外文·分赋钟馗画引》。《四部丛刊》本。
(17)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八,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第180页。
(18)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姚薏田圹志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页。
(19)《全谢山年谱》载:“又十日,呼纯之榻前,命尽检所著述,总为一大篓,顾纯曰:好藏之。而所抄文集五十卷,命移交维扬马氏藏书楼。”《鲒埼亭集内编》附,《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25页。
(20)王阳明《传习录拾遗》第十四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1页。
(21)《何心隐集》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54页。
(22)李贽《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8页。
(2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页。
(24)见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第335页。
(25)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四,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142-1143页。
(26)如邵毅平的《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
(27)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6页。
(28)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29)《黟县三志》卷十五《舒遵刚传》,均见余英时《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第160页。
(30)《太函副墨》所附汪道昆年谱载:“公年十二,喜涉猎书史,父封翁禁之。乃中夜篝火启箧诵读。时以文为戏,按稗官氏为传奇。”
(31)钱泳《履园丛话·耆旧类》,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0页。
(32)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65页。
(33)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
(34)黄仕忠《〈琵琶记〉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16页。
(35)参见徐学林《徽州刻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6)歙县《双桥郑氏墓地图志·明故徕松郑处士墓志铭》。
(37)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九《望云翁传》。
(38)同治《黟县三志》卷十五《艺文·人物》。
(39)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第334-335页。
(40)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356页。
(41)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370页
(42)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370页。
(43)汪汝谦《游草》为崇祯戊寅(1638)年金陵之游途中所作,其自序云:“记余少年游屡矣。吴阊凇泖间,酒炉此社,获逢名公,缙绅高流,翰墨之盛,而广陵白门托迹尤多。时观里琼花,桥边明月,泊秦淮桃叶,小姬家无不三五踏歌,十千买醉,繁华佳丽事种种在人胸臆。亡何,今秋一重过,而邗沟落叶,触目烟霜,旧游俱不可问;月夜步金陵曲中,访一二故识,筝寒雁断,哑哑只柳上鸟耳。即余弟师挚素称金石收藏家,而图书鼎彝已作王谢燕子,飞去堂上久矣!至于文酒萧条,友朋零落,可胜今昔之感!因惘然返棹,一访陈征君顽仙庐,苍颜一笑,相对欢然,使人淡然意消。于是知切感怆,亡赖不足当,有道人前耳。因出途次七言杂咏,先生为点正,聊存以志余过云。”集中多有抚今追昔之作,但并非易代后的感慨,仍无真正的沧桑之感和社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