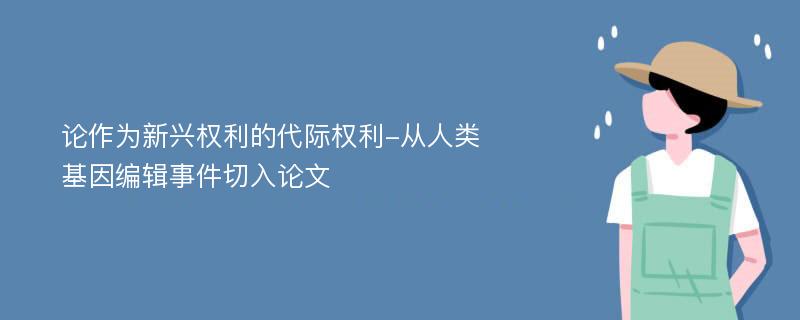
论作为新兴权利的代际权利*
——从人类基因编辑事件切入
钱继磊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摘要: “基因编辑人”已经从理论成为事实,使人类整体日益加速成为风险的命运共同体,也对传统权利法理提出挑战。代际权利并非虚妄,而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代际正义为法理基础,以对作为新兴权利的后代人权利的认可为条件,旨在为当代人权利与后代人权利之间寻求协调,以形成对人类未知风险进行控制的一种思维成果。在人类面临人工基因编辑等新科技给人类自身生物信息内在资源和环境生态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风险时,代际权利应当作为新兴权利的新维度,得到人们的认真对待。
关键词: 人类基因编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代际正义;代际权利;新兴权利
一、“基因编辑人”①:从理论到事实
①为了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因人类基因编辑技术而诞生的“基因婴儿”之权益,笔者于本文中使用“基因编辑人”这一比“基因婴儿”更为一般的概念来指涉这类自然人。
前文对于第三人侵权情形下的责任方式已做分析,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此种情形下的雇主与侵权第三人的责任方式为不真正连带责任,侵权第三人为最终责任承担人。法律对于第三人侵权时雇主责任的责任方式应该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样可避免法官在法律适用时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导致同类型案件不同判的情形发生。
在2018年前,除专业人士外,绝大多数人对于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及相关问题尚不甚了解。人文社科界学者也未有对此给予太多关注和讨论。自2018年11月26日始,这项技术因一则事件而广为世人所知。这一天受关注不仅是因为将于次日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而且是因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健康出生”这一爆炸性新闻的宣布。据称这对女性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了修改,由此使得她们出生后即获得天然抵抗艾滋病的能力。这则新闻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全球科学群体,在当今自媒体时代可以说迅速席卷了整个人类社会。这意味着,当人们还在将主要目光集中于未来的“智能人”(或人工智能)时,基因编辑后的“基因人”却突然来到现实世界,成了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这种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胚胎并孕育出了生命的“壮举”几乎受到异口同声的批评和谴责。这些批评和谴责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技术层面的,认为当前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胚胎尚不够成熟,存在脱靶及未知的可能风险等;二是伦理层面的,认为这种基因技术用于人类胚胎违背科学伦理;② 参见艾丹:《科学伦理的底线没有试探的“自由”》,《湖北日报》2018年11月28日,第007版。 三是安全层面的,认为这种行为将会对人类的基因库造成永久且不可逆转的污染和改变,威胁到人类整个基因库的安全性;③ 参见方舟子:《人类胚胎研究容不得半点轻率》,《环球时报》2018年11月28日,第015版。 四是个人权利层面的,认为目前还难以有效保护好这两个婴儿的个人隐私。④ 参见晁星:《“基因编辑”背后的伦理之门谁来守》,《北京日报》2018年11月28日,第003版。 另外,也有人对于这种技术用于人体可能面临的伦理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⑤ 参见方秀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面临的伦理问题及对策研究》,昆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22~32页、第41~49页。
如果说之前的相关研究还只是对于未来风险可能的理论准备与防范预测,那么随着首例基因编辑人的出生,人类不得不面对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对于此次事件,也有人从法教义学角度,试图从民法、行政法乃至刑法角度对基因编辑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分析和探讨,但问题是,暂且抛开现代法律自身的滞后性、刑法的谦抑性以及“罪刑法定”等不论,即便是依据现行法追究了当事人的责任,也无法解决现代法律面对涉及人类权利的高新科技所带来的未知结果和风险。
利用较长的滤波器,我们得到了具有良好的光滑性和良好的半采样延期特性的解。注意,h(n)和不需要对(近似)线性相位的进行一对Hilbert变换,但是根据应用其他原因可能是可取的。
由上可知,学界对于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限度从伦理、道德、法律等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就立法模式、隐私权利保护等方面提出了建议。然而,从法哲学角度对此进行反思性研究尚显不足。法学乃权利之学,这种权利本位其实是与权利自身的边界密切相关的。不过,权利的边界是止于自身的义务还是止于公共的善,或是止于最大的不伤害,人们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论争。若从这个的视角讲,针对上述事例,既有研究并未充分涉及这样一些问题:谁应当具有作为决定基因编辑人是否诞生于世间的权利,其未来的父母、相关专业人士或医学伦理委员会之类的组织是否应当拥有此权利;是否父母基于生育权、专业人士基于科学探索自由权、医学伦理委员会基于职业权力可以单独或共同行使决定权。这些问题背后更为深层次和根本的问题是:作为父母之当代人的生育权与作为其子女及其后代的后代人免于处于不可知风险的自由与权利之间的张力问题。这不仅意味着在当下人工智能、互联网、生物工程等新科技爆炸式发展所带来的未知风险对传统的个人权利形成的法理和法治层面的新挑战,而且也使整个人类日益加速成为风险的命运共同体。由此,在当下人类风险命运共同体时代,对作为新兴权利的代际权利理论进行梳理、反思和阐释就显得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二、代际权利是“虚妄”的吗
从既有文献看,“代际权利”的概念目前多在社会学等领域被使用,并不是一个常用且具备共识的概念,⑥ 以中国知网为例,截止2018年11月底,以“代际权利”为关键词搜索,可得到以下文献。董海军:《代际权利与话语:“80后”社会评价的变迁——基于长沙、杭州两地的调查》,《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3期;John Aron Grayzel等:《代际权利与责任语境下的青年展望——来自非洲的启示》,朱国栋、杨桂萍译,《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5期;田忠辉:《“80”后文学的代际权利与社会权力》,《文艺争鸣》2009年第12期。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并未对“代际权利”进行详尽的阐释和限定,由此,何为“代际权利”实质上是混乱而模糊的。 而“后代人的权利”概念则更多地被使用。⑦ 多数学者则使用“后代人权利”,如刘雪斌、赵融:《论后代人权利的法律保护》,《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刘卫先:《后代人权利理论批判》,《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刘卫先:《后代人权利论批判》,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李冰强:《虚幻的权利与现实的义务——对〈后代人权利论批判〉的本质解读》,《政法论丛》2013年第5期;罗飞、马永双:《代际伦理视野下的后代人权利保护问题研究》,《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年第4期;梁增然:《保护环境是后代人权理论的立论目的——读〈后代人权利论批判〉感言》,《公民与法(法学版)》2014年第4期;徐祥民:《环境保护走向何方——评〈后代人权利论〉批判》,《荆楚学刊》2014年第3期。 然而,从逻辑上讲,若“代际权利”得以证成,其前提应是“代”及“代际”命题的成立,然后才是不同代之间的权利关系问题,因为当代人享有权利应该不是理论问题,所以这其中应该又是以“后代人权利”成立为前提的。由此,是否存在不同的“代”以及不同代的不同权利是否成立,就构成了判断代际权利这一概念是否“虚妄”的两个核心要素。
(一)人类存在不同的“代”吗
张仲平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无奈之下,只好放下电话喊住曾真:“喂,对不起,你刚才是怎么叫我的?你叫我师傅?你是我徒弟呀还是孙悟空呀?”
早在1928年,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在其著作《代际问题》中就对代际关系与代际问题从社会学研究角度进行了专门研究。当然,对人类不同“代”(generations)给予提及并关注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就提及了“每个家庭由现在世代、未来世代以及他们的祖先所组成”的主张。⑧ 高景柱:《正义的历史维度——以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明确论及代际问题的则属英国的埃德蒙·柏克,他曾从宪政共同体意义上说过,国家“乃是一切科学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艺术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道德的和一切完美性的一种合伙关系。由于这样一种合伙关系的目的无法在许多代人中间达到,所有国家就变成了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在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和将会出世的人之间的一种合伙关系”。⑨ [英]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29页。 后来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等从宪政共同体角度对不同代之间的权力约束及权利保障进行了激烈的论争。⑩ 参见高景柱:《论正义与代际关系》,《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就我国而言,传统思想对于人类不同“代”际关系的关注与其说是基于生物学上的陈述,不如说是对社会伦理层面的强调。作为主流传统思想的儒学,其实解决的就是代际伦理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中,“仁”为其核心,“孝”与“爱”为其两翼。“孝”并非父对子的单向度的道德要求,而是与“慈”作为父对子的道德责任共同双向的代际契约伦理观,因而才有《颜氏家训·治家篇》的“父不慈,则子不孝”。
这样,代际正义下的代际契约论无法给后代人权利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法理基础,也就无法支撑起作为新兴权利的代际权利理论。之所以如此,在笔者看来,其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不论是约翰·罗尔斯还是弗莱切特,他们所着力解决的只是作为人自身之外的世界,如资源、生态环境等利益,这种哲学认识论依然是一种主客体二分观念。也正是如此,罗尔斯才会用正义储存原则来试图解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分配正义问题。他们都忽视了作为人自身的生物信息等也是一种资源和生态环境,这种由人自身生物信息等构成的资源生态环境随着人类的再生产得以不间断的延续。对于这种人类自身共有的内在资源与生态环境,不论是过去世代,还是当今世代,或是后代人,人类自身都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共有者,人们不能用也无需用基于仁慈和道义的“代际契约论”及正义储存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
就我国法学界而言,对于代际问题往往给予忽视,而是将其隐含于对“后代人权利”主张的阐释之中。然而,人类不同的“代”是否成立却是讨论“后代人权利”的前提性问题。因为如果人类不同的“代”本身就是无法成立的伪问题,何谈后代人权利呢?国内较早讨论后代人权利的“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及“论后代人权利的法律保护”的文献可以证明这一点。① 刘雪斌最早使用的是“未来世代权利”概念,而后来一直使用的是“后代人权利”概念,可见在他那里,两个概念是不做区分的。参见刘雪斌:《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第1期。 刘雪斌认为,“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由此“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② 同上注,刘雪斌文。 在之后的论文中,他又提出,“在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科技发展和经济进步引起的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造等问题,不仅影响同代人的利益,而且已经严重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这种情况对于后代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并对“后代人权利的内容”、“各国对后代人权利的法律保护”、“国际社会对后代人权利的法律保护”等方面进行了阐释。③ 同前注⑦,刘雪斌、赵融文。 可见,该学者实际上是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分作为一个不争事实来看待并加以认可的。
对于人类不同“代”的问题化反思则是由学者指责当代人与后代人二分的荒诞性开始的。这种观点认为,“代际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虚构了多个人类主体,即所谓过去世代的人类、现在世代的人类和将来世代的人类”。④ 徐祥民、刘卫先:《虚妄的代际公平——以对人类概念的辨析为基础驳“代际公平说”》,《法学评论》2012年第2期。 接着,该学者进一步论证了代际论者之所以会犯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其错误地把本为集合概念的人类偷换为类概念的人类。集合概念所反映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事物,即一个“个体”,类概念所反映的则是一类个体,即多个“一”。由此,“当他们说过去世代、当今世代和未来世代,并把它们放在辩说公平、签订契约的双方或多方的位置上时,实际上便把集合概念的人类改变成了类概念的人类。这个类概念是对过去世代人类、现在世代人类和将来世代人类的一般称呼,事实上,语境中,人类是唯一的集合体,它只是‘一’,没有甲乙丙等同类项”。⑤ 同上注,徐祥民、刘卫先文。
近年来,我国翻译语料库蓬勃发展,语料库翻译学作为新兴的译学研究领域,不仅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数据参照和支撑,更为翻译理论提供了新视角。然而,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针对体育领域的单语语料库或双语语料库甚少,而专业的体育文本翻译语料库的开发依然是研究空白。本研究提出一种体育文本翻译语料库建库设想,并对其可行性和未来的应用实践进行论证分析。
对于上述对“后代人权利”以及后面将讨论的代际权利看似连根拔起式的质疑与反思,有学者给予了回应,指出“判断环境法上的‘代际公平说’是否‘虚妄’,既应建立在科学的逻辑论证基础之上,又应建立在法律社会价值的判断与选择基础之上”,以集合概念、类概念二分为基础的预设路径实质上忽略了逻辑的事实要素,因而其进一步展开必然也无法达到论证结论(价值的正确)。⑥ 参见郭武、郭少青:《并非虚妄的代际公平——对环境法上“代际公平说”的再思考》,《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 然而,该论者的这种回应尽管揭示了对后代人及其权利质疑者的唯逻辑论,但也存在着不足。在笔者看来,对当代人与后代人之分的质疑论者实质上对后代人本身有误读,而进行回应的论者依然仅是在其所预设的逻辑层面上展开。在质疑论者的另一篇长文中,作者借用其他学者的表述对“后代人”进行了界定——“和现在的世代没有重叠的那些世代”,即“那些将社会在未来,但是直到现在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死亡后还没有出生的未来世代”。⑦ See Lawrence B.Solum,To Our Children's Children's Children's:The Problem of Intergenerational Ethics,35 Loyolal of Los Angeles L,171(2001).转引自前注⑦,刘卫先文。 其实这种对后代人的理解是对以前诸多学者观点的认可,如有学者就认为“未来人不在场,只是一个虚构的主体”。⑧ 魏波:《存在意义的传承见证代际公平》,《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然而,需要反思的是,是否就如质疑论者所言,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截然二分,以及在何意义上二分。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包括质疑论者在内的诸多学者认可不同代际之分,是因为其将研究问题的视角仅仅限定在了生态环境问题上。因为后代人权利理论的兴起本身就是基于环境危机以及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并得到众多学者支持,从环境法学领域逐步扩展到法哲学、政治哲学等领域。⑨ 参见前注⑦,刘卫先文。 由此,不论是从较早在《动物及未来世代权利》中提出后代人享有权利的约尔·范伯格,⑩ Joel Feinberg,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Future Generation,pp.4~5,13~14,http://site.voila.fr/bibliodroitsanimaux/pdf/FeinbergtheRightsof AnimalsandFutureGeneration.pdf,2019年1月访问。 到主张代际平等及代际信托论的爱蒂丝·布朗·魏伊丝(Edith Brown Weiss),① Edith Brown Weiss.The Planetary Trust:Conserv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ality.Ecology Law Quarterly,1984,11(4),p.495~581. 还是将环境问题、时间距离、非同一性和未来人偏好问题视为代际正义可能性论证的困难立场,② 刘雪斌:《代际正义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坚持“未来人与现代人物交涉”、③ 周谨平:《论代际道德责任的可能性基础》,《江海学刊》2008年第3期。 “‘在场’的当代人与‘不在场’的后代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其实质是当代人对后代人所承担的单方面的义务”等观点,④ 邬晓晔:《代际伦理:可持续发展伦理的新维度》,《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年第1期。 大多都未摆脱在环境生态的视角上加以观察的视域。
柳红关于那个女人的提问,苏长河就是不说话,他一个字都不说;但前几天他终于开了口,也只是感叹了一句,说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一条没有送出去的红丝巾。这条丝巾是他打算在女人的生日时送给她的,但他永远等不到那一天了;因为还没有到生日那一天,女人就跟人跑了。柳红吵着要看,苏长河就去房里找了出来。还是店里的包装。柳红拆开来一看,粉红色的丝巾,她喜欢。苏长河见她喜欢,就给了她。
从更宽泛的角度看,生态环境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部因素和条件,尽管它非常必要。其实,除了作为外部条件的生态环境外,人类自身也是其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和要素,甚至是更为根本的目的性要素。尽管生态环境情况会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繁衍与发展,但作为人类生存外部条件的生态环境与人类自身的内部环境生态并非一回事。如果说人类之所以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导致人类对外部自然资源环境的认识、改造、利用能力的不断增强的结果,那么随着人工基因编辑等生物新技术的不断提高,人类已经具有了对人自身生物信息的认识、改造和利用的能力,从而使人自身的生物信息也成为一种内在的资源、环境生态,并使其被侵犯和破坏成为现实的可能。
由此,如果对于后代人的理解仅限于传统的环境生态的保护与有效利用的视角,则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似乎是在场与不在场的关系。然而,如果将当代人与后代人关系置于人自身所带的生物信息也是一种环境生态,也需要环境生态保护的视角,则两者的关系就不可能是不在场的关系,而是通过人类共同的基因世代延续并传递下去,即便是在遥远的未来世代,人类的基因编码也具有无法割裂的连续性与共同性,不论人类自身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并承认它。
上网查了字典。原来,“怹”确实与“您”相对,“他”加前鼻音读tān,北京土语,方言,是老北京人对第三人称的敬称,用在对长辈、上司或尊敬的人的称呼上。
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分为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页。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305页。 传统上对环境生态问题的关注是基于第一种生产,忽略了人类自身生产更为根本和目的性方面。即便是有个别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有的谈到了通过人工方法改变人的一些基因强加给后代人,存在难以预料的长远后果,⑥ 参见汪堂家:《代际伦理的两个维度》,《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刘卫先:《自然体与后代人权利的虚构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6期。 有的认为“即使不存在试图通过基因技术控制全人类的野心家,基因技术也确实对后代人的生存和人类进化构成严重的威胁”,⑦ 刘雪斌:《论代际正义的原则》,《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4期。 但他们并未对此进行系统讨论,更未意识到两种生产视角所导致的对后代人的不同乃至冲突的理解。
按《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 50287—99)规定,饱和砂或饱和少黏性土的N63.5值小于按公式算出的液化临界击数Ncr时,可判为液化土。
纸箱不大,比之火车站装毛德君本人的那个纸箱小了许多,约有30厘米见方。但是秦明月等均感到心头突地一跳,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觉,那就是用于封口的纸箱上胶带与寄尸案的纸箱完全一样。
(二)后代人应当有其权利吗
即便是后代人作为独立的存在得到认可,也不意味着后代人就可以成为权利的主体,因为作为权利主体需要具备一些必要条件。可以说,当今世界是个“权利世代”,① [美]路易斯·亨金:《权利的世代》,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人们习惯用“权利”去应对和解决各种问题。然而,对于何为权利,“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什么是真理?’同样使他感到为难。”,②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9页。 J·范伯格则干脆将权利这一概念视为“简单的、不可定义的、不可分析的原始概念”。③ [美]J·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现代社会哲学》,王守昌、戴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92页。 国内学者曾对权利概念的起源及其成长历史进行过详细的考察和论述,④ 参见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0页。 也有学者对权利学说进行了较为全面而详细的梳理归纳。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页。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305页。 囿于论旨及篇幅,笔者于本文中并不打算对权利本身重点讨论和阐释,而是重点就国内目前对后代人权利质疑者关于权利的误读进行剖析。这些质疑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卫先教授。他在论证后代人权利虚构性时,专门对权利的虚构性进行了揭示。刘教授认为,权利以文化为存在的环境、以个体主义为权利的主体哲学、以自由为权利的主导价值,是利益有限度转化的结果,总之既有权利主体,“无论是‘美国殖民者’、‘奴隶’、‘女人’,还是‘印第安人’、‘劳动者’和‘黑人’,都属于‘现实中的人’。自然体权利和后代人权利只不过是一种理论的虚构”。⑥ 参见汪堂家:《代际伦理的两个维度》,《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刘卫先:《自然体与后代人权利的虚构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6期。
然而,刘卫先教授对权利的这种梳理与阐释却存在着误读,最为要害的在于其仅仅是一种历时性视角下对权利过去的回顾,这导致其忽略了权利在共时性视角下对现实乃至未来问题及风险的智慧性应对意义。首先,他指出,权利以文化为其存在的环境,“文化是人所创造的,文化的主体只能是人”。⑦ 同上注,刘卫先文。 然而,权利还是人类在应对和解决各种困难和风险而形成的智慧性结晶,其自身也会随着实践问题及风险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权利不仅仅面向过去和现在,还应当关照未来;它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人类面临的问题及风险而变动,不仅是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而且是可以被普遍适用的实践智慧。其次,他还指出,权利以个体主义为其主体哲学,权利主体的个体主义蕴涵着“权利主体的主动性和权利功能的向内性”。⑧ 同前注⑥,刘卫先文。 然而,这种权利哲学只能是一种古典自然法传统意义上的,是一种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即第一代权利意义上的理解,而后来的第二代、第三代权利理论所倡导的社会权、生存与发展权、环境权等都对这种原子式个人主义进行了修正,⑨ 对于人权划代理论,学者有不同的分法。参见齐延平:《和谐人权:中国精神与人权文化的互济》,《法学家》2007年第2期;徐祥民:《环境权论——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徐显明:《和谐权:第四代人权》,《人权》2006年第2期;邱本:《论人权的代际划分》,《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由此个体主义在哈耶克的方法论意义上更具有意义。然后,对于他所主张的权利以自由为主导价值,同样更多地是第一代权利理论意义上的,而并不适用于所有权利。因为除了自由外,还有安全、平等、正义、效率等价值,而其间的价值位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特定社会问题及风险所需而表现不一,并且视其在具体部门法中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而不同。最后,在其论证“利益转化为权利的限度”中,将利益转为权利限定为以下条件,即利益的客观存在、对利益进行权利保护必须体现主体的独立人格需求等。⑩ 参见前注⑥,刘卫先文。 这样,该论者的利益范围仅仅限于既存的、确定的可见利益,而将避免不可知的未来风险的安全等利益排斥在外。同时,对于利益转化为权利的保护主体的独立人格需求也仅适用于现实中的完全权利行为能力主体,而对尚不具备完全权利行为能力却处于未来可能风险的不安全中的主体却被排斥在外。
总而言之,正是该论者的这种历时性视角,将权利仅仅固定于过去既有的认识,从而使权利的主体仅被限定于现实的具有完全权利行为能力的独立的个体,这才导致其所主张和阐释的权利理论的不足。权利理论从来都是处于自我发展变化中的,都是其所处的特定时空下人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的有效应对的智慧。在当下科技新时代,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等使得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风险、新问题、新挑战,权利理论也应当自我发展,使其不仅能够为既定的现实问题进行有效应对和提供救济,还应当能够有效防范和避免人类所面临的各种未知风险。由此,后代人权利应当是新科技时代下权利理论的新发展,是一种新兴权利,代际权利则是对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权利的张力与有效安排进行的新思考。
三、代际权利的法理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代际正义
当然,即使上述后代人权利暂且得以确认,也只是概念层面上的,作为新兴权利的代际权利以及作为其重要前提支撑的后代人权利依然缺乏背后的深层次法理基础。由此,笔者将在法理层面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与阐释。
(一)后代人权利的既有理论基础反思
从既有研究看,学者将后代人权利的理论建立在代际正义下的代际契约论、代际平等下的代际信托论以及跨代共同体理论等基础之上。
从生物学上意义讲,“代”是一种自然界物种划分、物种进化与更替的事实性存在。任何有生命的物种都是通过不同“代”而实现生命的延续的。可见,“代”是一种生物事实的存在。代际关系则意味着上下相邻两代之间的关联,如生物学说的遗传与变异等。换言之,生物学意义上的“代”意指物种的传宗接代,新一代的诞生与发展伴随着上一代的老化与衰亡。就作为高级动物的人而言,其本身就是生命自然的组成部分,其自身的延续也离不开这种代际传递,而这种代际关系发生在家庭中并成为家庭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的前提与基础,由此,对于代际关系较早给予系统关注的是社会学家。
在环境法领域,代际契约论以克里斯汀·西沙德—弗莱切特(K.S.Shrader-Frechette)为代表。他认为,在我们和后代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可称为代际接力式的相互性——跨越时间的链式相互性。退一步讲,即使不通过相互性,只通过人的理性、正义等要素也可达成社会契约,并且,“某些形式的契约之所以能够形成,不是因为达成了预先安排好互惠利益的协议,而只是因为契约的一方主动选择了接受义务”。① 参见[美]维西林、冈恩:《工程、伦理与环境》,吴晓东、翁端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第206~207页。 这种代际契约理论是以西方传统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尤其受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影响,甚至直接借用了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假设和“无知之幕”理论。② 韩立新:《环境价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罗尔斯认为,“将正义延伸到包括我们对未来各代人义务(包括正义储存的问题)”,③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页。 是其正义理论遇到的难题之一。不过他认为,由于无知之幕是彻底的,“在假设所有其他各代都要以相同的比率来储存的基础上,他们愿意在每个发展阶段储存多少。……[他们]必须选择一个能分派给每一个发展水平以一种合适的积累率的正义的储存原则”。④ 同上注,罗尔斯书,第278页。 然而,这种对各代人利益的考虑与其所假设无知之幕的原初状态的两个条件存在矛盾:一个是原初状态当事方是理性的,其动机在于“努力为自己寻求一种尽可能高的绝对得分”,⑤ 同上注,罗尔斯书,第278页。 而此种情况下契约的达成实质上是一种作为互利的正义;另一个是原初状态当事方身份,罗尔斯要求人们从现时的角度来解释和对待不同时代的人,实质上是一种作为公平的正义。这样,代际契约所要实现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与代内契约所秉持的作为互利的正义同时出现在无知之幕的原初状态下当事方那里。作为互利的正义建立在理性自利或互利互惠基础之上,作为公平的正义则要求当代人为后代人做出让步和牺牲,承担义务和责任。可见,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而“罗尔斯在探讨其一般正义论和代际正义理论时,往往把这二者混为一谈”。⑥ 参见杨通进:《罗尔斯代际正义理论与其一般正义论的矛盾与冲突》,《哲学动态》2006年第8期。 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质疑‘后代人权利’的代际契约说基础”,认为社会契约论中“契约的达成和实现的四个核心要素,即‘缔约方力量平等、缔约方参与和保持契约的原因一致、契约的维持受到社会控制功能的制约、缔约双方具有互惠性’”,在代际契约的情况下,“都是无法实现的”。⑦ 刘卫先:《质疑“后代人权利”的代际契约说基础》,《中州学刊》2011年第1期。
如果说代际契约所依据的代际正义是作为公平的正义,那么这种能够使得第三方(即后代人)受益的正义原则,因为原初状态的正义环境要求大家相互间是冷漠的,所以不可能是基于“对于他们的直系后裔义务”。⑧ 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128. 由此,有学者认为,即使客观上承认在原初状态下的人们选择了这样一个能够使第三方受益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那也仅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人们也可以反对建立这样的一个义务。这种缺乏严格服从义务的选择之结果,也就“不可能在现在世代和作为第三方的未来世代建立任何具有约束的正义关系”。⑨ 刘雪斌:《论一种作为公平的正义》,《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
可见,“代”(或世代)不仅是个家庭意义上的,还是社会意义和时间顺序意义上的概念。⑧ See Joerg Chet Tremmel,A Theory of Integenerational Justice,Earthscan,2009,pp.19~21. 人作为主体,并非是唯一样态,而是作为类主体、群体主体以及个体主体的同时存在。⑨ 参见杨盛军:《环境代际非正义之主体原因及其对策探析》,《济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作为未来世代的后代人与当今世代不仅有可能存在重叠,而且必然存在重叠关系。⑩ 参见高景柱:《论正义与代际关系》,《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由此,对后代人的理解不仅是未来的、遥远的、不在场的后代,而还应该关注与我们重叠、交叉、共同生活的眼前的后代人。
1128 放射性 125I 粒子植入治疗胸腺肿瘤胸膜复发的短期临床疗效 朱衍菲,王常禄,朱绫琳,吉永烁,朱君秋,赵 洪,张 宇
代际平等下的代际信托论以爱蒂丝·布朗·魏伊丝为代表。她认为,人类不同世代之间是一种针对地球环境资源的信托关系,每代人“既是受托人又是受益人”,作为受托人,他“不仅是为了相邻近各代的利益,而且为了所有未来各代的利益”。⑩ Edith Brown Weiss,The Planetary Trust:Conserv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ality.Ecology Law Quarterly,1984,11(4),p.505~507. 可以说,这种代际平等理论旨在解决全球环境生态危机,不愧为一种伟大设想。不过,有论者指出,这种理论构想在逻辑上存在着循环论证之悖论和谬误,且实为虚构的结果。该论者所指出的这种理论的的困惑在于:环境问题是世代的公平问题还是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地球环境是否为人类的财产,“地球权利”的主体到底应该是谁,代际信托何以可能,后代人的权利是否比当代人的义务更有利于保护“后代人的利益”,等等。① 参见前注⑦,刘卫先文。 对这些困惑是否虚妄,限于篇幅及论旨,笔者于本文中不再详尽剖析,不过可以指出的是,其中前三个困惑之所以会出现,其背后依然是现代哲学上的主客体二分观念。这种主客体二分观念将人自身视为认识、利用、改造人之外一切的主体,人之外的一切则是作为人之主体被认识、被利用、被改造的对象而存在。主客体之间是截然的认识与被认识、利用与被利用、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由此,该论者才会提出,到底是地球环境是人类的财产还是人类自身属于地球的疑问。对于代际信托何以可能的问题,该论者指出,作为代际信托的委托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委托人即后代人对委托事务享有权利、代际信托理论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成后代人享有环境权,这样就出现了循环论证的逻辑悖论和谬误。② 参见前注⑦,刘卫先文。 这或许正是揭示了代际平等下的代际信托论的软肋之处。对于后代人的权利是否比当代人的义务更有利于保护“后代人的利益”问题的困惑,与其说是证成了代际信托论的虚妄,不如说是给人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尽管对于谁能够代表后代人行使这种权利,后代人权利不具备具体内容是什么等问题的解答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但这并非意味着后代人权利不存在,更不意味着讨论和阐释后代人权利没有重要价值,只是表明后代人权利依然是值得人们深入讨论的重要论题。
跨代共同体理论的主张者往往将其理论渊源追溯至英国的柏克以及其代表人物是乔治·赖特等。柏克认为,国家“乃是一切科学的合伙关系,一切艺术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道德的和一切完美性的一种合伙关系。由于这样一种合伙关系的目的无法在许多代人中间达到,所以国家就变成了不仅仅是活着的人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在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和将要出世的人们之间的合伙关系”。③ [英]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29页。 赖特从柏克的这段表述中诠释出支持后代人权利的跨代共同体论。显然,柏克的这种跨代共同体论是以那个时代所思考的宪政共同体意义上而言的。后来托马斯·潘恩对其将国家与社会完全等同起来以及萨拜因对其“对社会的崇拜代替了对个人的崇拜”,④ 刘玉安:《西方政治思想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页。 就可证明这一点。此后跨代共同体理论更多受到社会学界的关注,如齐格蒙特·鲍曼的对共同体的讨论,⑤ 欧阳景根:《〈共同体〉序曲·译注》,载[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论,⑥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以及桑德尔、费迪南·滕尼斯等人的理论。这些都是基于当代人间共同体的本能、习惯或者思想的共同记忆等产生的某种共同关系的心理同感。这一点也可从阿夫纳·德-沙利特(Avner Dr-Shalit)对共同体的三个特征的阐述中得到论证,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文化交流与道德相似性”。⑦ Avner De-Shalit,Why Posterity Matter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22. 然而,仅凭处于人心理上同感以及长辈与晚辈之间感情上的仁爱是不够的,其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几代后淡化而消失。由此,有学者认为,人类共同体即便存在,“也只能是所有当代人的集合体,对于永远未出生的‘场外’后代人而言”,“不可能成为人们所说的人类共同体的现在的成员,因为尚未出生的后代人不能与当代人形成相互交流和联系”。⑧ 同前注⑦,刘卫先文。 戈尔丁(Golding)也发现,跨代共同体理论存在两个困境,即当代人无法与后代人共享生活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缺乏道德上的相互作用。⑨ Avner De-Shalit,Why Posterity Matter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19. 由此,与代际契约论类似,通过跨代共同体论证成当代人对后代人的义务是不充分的。对此,有论者认为,即便是在主张当代人与后代人确实可以构成跨代共同体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沙利特(Avner Dr-Shalit)那里,也只是推出“‘当代人负有义务’,而不是后代人的权利”。⑩ 刘卫先:《对跨代共同体学说的几点质疑——以否定“后代人权利”为视角》,《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9期。
综上所述,不论是在社会学领域,还是在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等领域,不论对跨代共同体论持赞成还是反对态度,其共同预设依然是将后代人界定为与当代人没有交际的永远未出场的“未来”人,没有看到人类自身再生产中由人自身生物信息而勾连在一起的不间断的延续性和共有性。随着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日益成熟,对人自身生物信息的认识、改造等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使得人自身的生物信息成了区别于传统的人之外在的资源、环境、生态的一种人的内在资源和生态环境。
(二)作为代际权利法理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代际正义
由此,从理论上讲,作为准现实人之具体个人的后代人享有最低限度的权利并非毫无正当性理据。如果说因为“后代人权利”理论因古典自然法之自然权利建立在基础不牢固的“流沙”之上就完全排斥,那么当代人权利理论也面临同样困境。即便是早期对古典自然法基于批判和排斥的分析法学派成员,也日益意识到完全拒斥权利的不可能性和不可欲性,并提出了作为“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⑨ 哈特认为:“这些以有关人类、他们的自然环境和目的的基本事实为基础的、普遍认可的行为原则,可以被认为是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89页。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为代际权利理论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如前所述,既有的对后代人及其权利问题的讨论者显然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仅仅出于对传统的人之外部的世界视角且将其作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和前提来展开的。在笔者看来,即便是承认范伯格的设想,即由一个权利的当代人与未来世代的正义共同体作为理论基础,② 乔尔·范伯格认为,我们为了我们的子女、我们的下一代的保护环境,是一种爱的行为;而我们为了我们遥远的后代保护环境,则主要是一个诉诸未来世代权利的正义事件。See Joel Feinberg,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Unborn Generations,in E Partridge(ed)Responsibility to Future Generations,New York,Prometheus Books,p.139. 然而面对人类编辑技术等新科技浪潮,后代人权利以及建立在其上的代际权利应当有一种新的法理基础。在笔者看来,这个法理基础应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代际正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本来是个政治术语,由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旨在就解决全球性难题而提出中国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③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1版。 不过,人类共同体理念也已成为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目前学界主要关注以下方面: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渊源和发展历程;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特征;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观基础和伦理意义;从国际关系视角加以分析研究。④ 参见高景柱:《论代际正义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1期。 可见,上述研究主要着眼于当代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忽略了人类中的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多从国与国之间关系视角展开而非人与人视角;多从作为人类生存的外部条件的资源与环境生态保护出发,忽略作为人自身内部生态环境的人的生物信息保护问题。不过,笔者认为,面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可以通过诠释其新内涵而为代际权利提供法理基础。
PDA固体培养基:北京博奥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蛋白胨、酵母提取物:英国OXOID公司;葡萄糖:天津福星化学试剂厂;琼脂粉:上海国药集团;DNA Marker:Fermentas公司;PCR清洁试剂盒(AXYGEN):购于北京科博汇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PCR Mix:购于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rTaq、dNTP、pMD18-T vector:购于大连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TaKaRa);PCR引物的合成和测序:由武汉天一辉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如果说过去的共同体要么是“基于血缘、地域、情感或伦理”,要么是“基于共同利益抑或私人利益形成的一个联合体”,⑤ 同上注,高景柱文。 那么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日益成熟的现状下,整个人类由于共同的生物信息而成为一个联合体。这种因人类共有基因等生物信息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不以社会学意义上的道德、风俗、伦理等方面的共同记忆和心理同感为要件,也无须基于作为人类生存之必备条件的外部资源和环境生态而构建,而是基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即人类共有的生物信息。如果说人们之前还可以对其视而不见,那么随着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人类自身生物信息所面临的未知风险就使人们不得不对自身内部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进行问题化思考。这使得人类成为一种基于基因等生物信息安全的命运共同体。
由此,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等新科技下,应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有如下理解。一是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再是外在的、心理上的、文化上的认同,而是成为了一种无法否认的事实存在,不再以国别、民族、地域为区分,而是基于每个人固有且人类共有的生物信息资源和环境。二是这种将人类命运勾连起来形成的共同体不仅是由于作为人类生存之必需的外部资源、环境生态等,而且源于人类自身所共同固有的基因等生物信息。这种人类共有的这种生物信息将过去世代、当今世代以及未来世代的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三是此种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应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人自身外部世界的资源及利益分配与储存问题,而是更强调如何应对、预防和避免人类自身生物信息这种内在资源、环境生态面临的风险乃至危机问题。四是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的与其说是利益,不如说是面对未知风险的安全。五是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人类基因编辑技术使得当代人与所谓不在场的后代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人类基因编辑事件的发生使得当代人的行为带给后代人的未知风险成为必然。
自十六世纪开始,法律已经成为社会控制的最主要手段和方式,⑥ 参见[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13页。 法律对社会控制则是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来实现的。就人类基因编辑而言,这种技术带给当代人的可能是利益和权利的实现,对于后代人而言更多则是未知风险的安全利益问题。在此基础上,从法理角度,如何有效应对和控制这种未知风险,也需要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来实现。换言之,就人类基因编辑行为而言,如何在当代人生育权所体现的利益与后代人避免未知风险权利(或生物信息安全权)的安全利益之间进行协调,也需要一种权利义务分配的法理思维。这就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代际正义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于本文中并不是在罗尔斯所提出的代际正义意义上来使用代际正义概念的。罗尔斯所指的代际正义只是基于对人类外在的资源和环境生态等人生存必需条件意义上的,笔者于本文中说的这种代际正义则是基于由人类基因等共有的生物信息连接起来,将当代人与后代人紧密勾连起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代际正义。这种代际正义不是为了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如何分配人自身之外的资源环境,而旨在如何在当代人利益与权利的实现与后代人应当有避免未知风险之权利之间的协调与分配。如果说罗尔斯的代际正义中,当代人对后代人负有的正义储存原则所依据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与当代人间分配正义所秉持的作为交换的正义之间存在着混乱和矛盾的话,那么这种基于人类共有的生物信息而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代际正义则可以避免这一点。因为基于当代人与后代人共有共享人类基因等生物信息构成了人类得以生存和延续下去的最基础和最根本的要素,当代人和后代人共同负有维护人类自身生物信息的内在生态环境之安全的义务。后代人还未成为现实,不可能存在对人之生物信息进行破坏或构成风险的可能,因此,这种义务就应当由当代人承担和履行。也正是由于人自身的生物信息为整个人类所共有且构成人类得以延续的最根本的内在要素,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这种共同义务就无需再由代际契约论、跨代共同体理论提供法理基础。当代人对后代人的这种维护人自身生物信息安全的义务其实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维护整个人类自身的内在安全。
由此,如果说基于维护人自身生物信息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旨在解决“类概念”下的整个人类的自身的内在生态环境风险,那么其下的代际正义则旨在解决如何为了更好有效地实现前一目标在“集合概念”意义上的当代人与后代人权利与义务的权衡。⑦ 对于通过人类这一概念的“类概念”与“集合概念”二分来质疑人类“当代人”与“后代人”分割观的讨论,参见前注⑦,刘卫先文;前注④,徐祥民、刘卫先文。 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代际正义理论不但可以有效解决“类概念”与“集合概念”意义上人类这一概念的逻辑矛盾,而且可以为代际权利提供更坚实且有解释力的法理基础。
四、作为新兴权利的代际权利
如果人们承认代际权利,那么进一步需要明确的便是,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权利,这种权利与以往的权利理论存在着什么关系。笔者认为,代际权利是建立在传统权利理论基础之上的新兴权利,它不仅为人们如何解决新科技下人类面临的新风险挑战提供一种更有效的理论解释,而且还可能是人们认识和分析当下问题的方法论,能为对人类的新风险的有效控制提供可能路径和思路。
(一)作为新兴权利的后代人的权利
如前所述,代际权利的成立需要以后代人权利存在为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讲,之所以将代际权利视为新兴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代人权利的新兴性。由此,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后代人应该享有权利,然后才能讨论后代人享有的是一种新兴权利。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那样,权利意指资格、主张、自由、利益、选择等观点,⑧ 参见前注⑤,张文显书,第300~305页。 但权利并非仅仅是对当代的现实人而言的,而是还需要对虽未来到世间但应该成为现实人的人的关注。详言之,权利所蕴含的资格主要是指现实中的人的资格,但不应当剥夺后代人的资格;权利所蕴含的主张主要是指当代人的主张,但不应剥夺后代人的发表其主张的机会和可能性;权利所蕴含的自由主要是指当代人的自由,但不应当剥夺后代人的潜在自由;权利所蕴含利益主要当代人的既定的利益,但不应当剥夺后代人不应承担未知风险之安全利益;权利所蕴含的选择主要是指当代人的选择,但不应当剥夺后代人选择的机会和可能性。如果仅将权利理论限定在上述的当代人,则这种权利是不正义的,也与实定法不符。
之所以有学者将权利主体限定在具有权利行为能力的现实的当代人,是因为混淆了权利的享有和权利的行使之间的区别。其实,在当前的部门法中,类似法律也体现了权利享有主体并非仅限于完全权利行为能力范围内。譬如,我国《民法总则》第16条就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这种立法也是对域外立法普遍经验的借鉴,旨在规定非现实人权利的享有,避免使之失去可能的利益和权利的机会。其实,在我国目前已在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诸方面将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权利主体,而且对于其在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方面是否应成为权利主体,学界也已有很多讨论。尽管这种规定是基于对胎儿作为准现实人的权利保护之必要且仅限于作为纯受益人范围,但胎儿同样无法参与现实人的意思自决。另外,对于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的法律主体而言,即便是现实人,也因其无法凭自我理性之意志决定行使相应权利而需要监护、代理等制度来辅助解决这些问题。
如前所述,既有的作为后代人权利理论基础的几种观点都存在着诸多问题且受到多方面质疑与挑战,显然已经无法为新科技时代所带来的新问题提供充要的法理依据。伴随着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等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不但在改造作为人类生存必要条件和基础的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而且也从技术上掌握了认识、利用和改造人自身的生物信息等方面的能力。由此,有学者断言:“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类的力量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以至于他的决定和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影响到无法预测的未来。”① 周光辉、赵闯:《跨越时间之维的正义追求——代际正义的可能性研究》,《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3期。 然而这种影响给人类带来的不仅仅是美好的东西,还可能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由此,人们应当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和理论准备,以尽可能地防范和避免这种未知风险。
一种权利之所以可称为新兴权利,是相对于传统的既有权利而言的。对其“新”的标准“既可以从以时间和空间为核心的形式标准来判定,也可以从权利的主体、客体、内容和情景为核心的实质标准来判定”,其“产生在根本上乃是因应社会的发展而在法律制度需求上的‘自然’反应”。⑩ 姚建宗:《新兴权利论纲》,《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 就后代人权利而言,其“新”之处至少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后代人权利的主体是与当代人相对的后代人。如前所述,既有权利理论主要关注和解决的是现实当代人之间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关系的,其权利主体是当代人或由当代人组成的组织等。其预设是所有参与法律关系的当事方都是具有完全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理性人。由此,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等才成为了作为现代法律基础的民事法的基本原则,刑法中犯罪的构成才会强调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等;当然,法律对于限制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自然人的行为和权利也加以考虑,但其仅是例外性规定。后代人权利主体不可能是具有意思表示能力的客观存在的客体,而是将传统法中的非完全行为能力主体作为常态。由此,这就注定了后代人权利具有权利主体方面的新兴性。
其二,后代人权利的客体是防范和避免可能给其带来的未知风险。传统法理中,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客体通常意指“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作用的客观对象”,往往要求其具有“客观性”、“有用性”、“可控性”等特征,主要包括物、人身、人格、智力成果、行为、信息等。① 参见张文显:《法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57~159页。 可见这种对权利客体的界定是建立在具有意思表示的现实当代人设定之上的。对于后代人权利,其客体不是因其自身的意志行为所指向、影响或作用的对象,而是指当代人的行为给后代人所造成的影响的对象,即给后代人带来的未知风险。由此,后代人权利客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物、人身、人格、智力成果、行为、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信息,而是自身生物信息的安全或风险防范。这对既有权利客体理论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也具有新兴性。或许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张文显教授在其最新修订的《法理学》一书中颇有开放地将权利的“其他客体”列入其中,② 同上注,张文显书,第159页。 这为适应后代人权利客体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可能。
美国的Ingo Bayer,Richards Bay通过在电解槽的侧部碳化硅板和槽壳之间安装热管,在管内通入空气或液态介质来强制冷却电解槽,利用热管带出的热量来加热氧化铝[5]。其电解槽热管安装结构示意图见图5。
这一下震惊了李老师,李老师就是有学生来告状,然后就发现了这些罪证。看见这些东西,李老师的脸也红了,整个办公室的老师们得知情况后都傻了,李老师意识到情况很严重。但怎么样也想不到原因是周小羽讲的这样,因为她当时也没容许周小羽再分辩。她当时就在心里想,哪个老师看见会不生气啊!在她看来,这些画充满着黄色和暴力,有些是男女一起的,有些是打架的,有一张李老师记得很清楚,那就是一个人被绑在板凳上,旁边一个人在拼命地用灌木刺打着。那画面让她想起电视上那些私设刑罚的场景。这么一个小孩子,哪里学来的这些东西,所以,她是一定要上门家访的。这个孩子这样下去就不行了!
其三,后代人权利所保障的是一种特殊的利益。在传统权利理论中,权利所保护的通常是权利主体的利益,然而这种利益往往被界定为客观、可控的有利的东西,是一种正面、积极的界定,适合于当代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后代人权利所保障的利益则是一种对后代人免于处于风险和危险的安全利益,虽然这种风险可能是未知的,但是风险一旦成为现实,其带来的危害是无法估量和不可逆转的。如果说传统权利所保障的利益是一种既有利益的可得或不减损,那么后代人权利所保障的利益则是一种未来风险可能性的避免,由此可以视为一种负面清单式的消极性规定。这种权利所保障的利益与彩票购买人类似,只不过彩票购买者是通过对价获得中奖的机会,而后代人权利所保护的利益是因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代际正义使得后代人免于处于未来风险的可能性,即前者是机会的获得,后者是机会的避免。
其四,后代人权利实现的方式是享有。以当代人为权利主体的传统权利的实现方式可能是享有,也可能是行使。享有但并不要求权利人具有完全权利或行为能力和明确的意思表示,以获得利益而不需要承担义务为限,可以视为一种消极的权利。通过行使方式实现的权利则需要通过明确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来达致。这种权利需要以权利主体具有相应行为能力为要件,是典型的当代人权利的思维和实现模式。后代人权利只以享有为唯一实现方式,并不要求后代人在场,更不需要作出意思表示,也不需要后代人对当代人承担同等的对价或义务,而是以纯粹利益(即免予处于未知风险的这种特殊利益的获得为目的),这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柏林所说的“免于……的自由”。③ [美]以赛亚·伯林:《自由四论》,陈晓林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6年版,第243页。
(二)作为一种未知风险控制方式的代际权利
如果说后代人权利是一种新兴权利,那么代际权利则是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新兴权利思维方式和权利样态。这种代际权利以当代人权利和后代人权利共同认可为前提,旨在如何寻求当代人权利与后代人权利之间的协调和均衡,以更好地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代际正义。
从权利发展史看,代际权利可以被看作是建立在过去类型化、进化式权利理论之上的修正和提升,也可视为我国权利本位理论的新发展。对于权利的发展历程,有学者从人类人权发展历程维度出发,认为西方人权史经历了“自由权本位的人权、生存权本位的人权和发展权本位的人权三个历史阶段”;④ 同前注⑨,齐延平文。 也有学者将人权史划分为“初创期、发展期和升华期”,其“核心性人权分别是自由权、生存权和环境权”;⑤ 同前注⑨,徐祥民文。 还有学者提出了作为第四代人权的和谐权。⑥ 参见前注⑨,徐显明文。 限于本文主旨,笔者不拟对这些权利理论本身进行过多阐释。不过,从中可看出,这些都是类型化、单向度的权利理论,即关注和强调权利自身的正当性及其彰显,甚至将不同权利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进化式的替代关系,却对权利自身的合理边界不甚关注,也未对不同权利之间的关系进行重点阐释。过去几十年来,权利本位理论在我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也对中国法理、法治和法学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和支撑作用。不过,此理论同样过多关注权利本身的证成和实践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等,不同权利之间的关系及权利的合理限度等方面同样不是其重点关注的对象。笔者于本文中论述的代际权利理论不同于上述既有权利理论,而是着重强调当代人与后代人权利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呼吁权利自身得到更为合理的安排和规制。
可见,这种代际权利看似是建立在前述“后代人权利”理论之上,实际上是与之存在显著差异的权利理论。其核心不在于寻求、彰显某种具体的类型式权能,而更多地是在揭示隐藏于权利背后的当代人与后代人权利之间的张力。这种权利张力关系不仅仅限于生态环境领域(甚至可以说,与生态环境维度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而是一种作为准现实人的后代人所应享有的最低限度的权利,以及后代人与其上一代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如果说“后代人权利”理论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之追求的类权利,那么笔者于本文中论述的代际权利则旨在强调构建人类安全命运共同体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构是建立在对不同代际权利的合理安排和尊重基础之上的。这种新兴权利与旧有传统权利之间的冲突和协调不仅贯穿于法律权利实践的始终,而且“彰显着权利发展的真实样态”。⑦ 姚建宗:《新兴权利论纲》,《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
截至调研日期,除淮安尾水导流工程外,其他各地如徐州、新沂、睢宁、宿迁、江都段尾水导流工程实际导流量均低于工程设计导流量,具体排放情况如表1所示。
对于笔者于本文中提出的作为新兴权利的后代人权利及代际权利论,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因为依据法律思维,权利与义务作为双向调整机制,共同构成法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特有方式,由此,一般认为权利义务具有结构上相关、数量上等值、功能上互补和价值上主次等关系,⑧ 参见张文显:《法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34~138页。 因而在当代人与后代人、权利和义务之间应当有不同组合,即当代人权利与当代人义务、当代人权利与当代人权利、当代人义务与当代人义务、后代人权利与后代人权利、后代人义务与后代人义务、后代人权利与后代人义务、当代人权利与后代人权利、当代人权利与后代人义务、当代人义务与后代人权利及当代人义务与后代人义务等十对关系。这样,当代人权利与后代人权利仅是其中一个组合而已。其实笔者对其他几种组合并非视而不见。值得探讨当代人权利与当代人义务、当代人权利与当代人权利、当代人义务与当代人义务这三对组合,系纯当代人之间的代内权利义务关系,并非本文论旨,显然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后代人权利与后代人权利、后代人义务与后代人义务、后代人权利与后代人义务这三对组合属于纯后代人之间的代内权利义务关系,由于其权利义务关系主体都不在场且也属于其代内关系,显然也没有讨论的必要。剩下的四对组合即当代人权利与后代人义务、当代人权利与后代人权利、当代人义务与后代人权利、当代人义务与后代人义务值得探讨。也就是说,除了笔者于本文中讨论的作为代际权利的当代人权利与后代人权利这对组合外,另外三对最具挑战性和讨论的必要,因为其中揭示了这样问题:后代人是否对当代人负有义务;通过当代人与后代人间的义务分配是否可以达到当代人与后代人间的权利分配。对于第一个问题,如果承认后代人对当代人也应负有义务,那么是什么义务,其限度在哪里呢?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则意味着当代人对后代人只能牺牲和承担义务,这对当代人也不公平。对于第二个问题,其如果成立,则意味着代际权利可能被完全虚化和颠覆。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后代人的义务只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只为当代人权利的享有和行使提供正义法理基础,后代人的权利则可以为当代人权利的享有和行使进行适当限制提供正义法理基础,两者并非水火不容。对于第二个问题,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是义务关系的协调还是权利关系的协调,从逻辑上看,两者似乎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然而,权利思维是一种尊重主体的目的思维,是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法理思维,而义务思维只能是为了实现维续和扩大权利提供保障的手段思维。由此,通过协调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权利关系的代际权利思维才是符合现代社会人作为主体的思维,这种代际权利旨在为对人工基因编辑等新科技带来的未知风险的有效控制提供一种视角和可能。在笔者看来,代际权利作为人类未知风险的控制方式,至少可以给人们提供以下启示和要求。
其一,当代人和后代人不但负有维护人类生活之外部资源、环境生态的义务,而且负有维护人类共有的生物信息等内在资源、环境生态,使之免于承受未知风险的共同责任。面对人类基因编辑等新科技,人类已不可否认地成为另一种意义上命运共同体。如何维护人类自身生物信息等安全利益已对人们构成现实性的问题和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成为需要人们思考和解决的现实难题。
其二,当代人权利的享有和行使应当审慎和保守,以不使后代人被置于未知巨大风险之中为限。尽管当代人权利的享有和行使具有正当性依据,但也不应毫无限度和节制。如果说约翰·密尔将当代人之间的自由的限度确定为应遵循“不伤害(或不干涉)原则”,⑨ 对于权利的自由限度,约翰·密尔认为:“……这种自由,只要我们所作所为并无害于我们的同胞,就不应遭到他们的妨碍,即使他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愚蠢、背谬、或错误的。第三,着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联合,只要参加联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此即“不伤害”或“不干涉”原则。[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化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13页。 那么当代人权利享有和行使的限度还应止于给后代人带来未知巨大风险的可能性。这不仅是对后代人权利(如生物信息完整权)的尊重,对后代人的人格尊严的承认,⑩ 参见前注④,高景柱文。 而且是为了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利益。
其三,后代人权利的享有也同样有其正义的限度。就人类基因编辑等新科技而言,对后代人权利的尊重以不对其构成未知巨大风险为限,而不应使当代人权利的行使和享有受到过多限制。如果说罗尔斯针对如何解决当代人与后代人间的资源、环境生态等人类生活必需的外部条件提出了正义储存原则,那么针对人类基因编辑等技术对人自身生物信息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应当采用并遵循一种类似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中国智慧。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Right as an Emerging Righ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Gene Editing Incident
Qian Jilei
Abstract: The"Gene-edited human"is a reality developed from a theory,thus turning the whole human beings into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concerning risks in an increasingly accelerated speed,and also imposing challenges upon the traditional legal theory on rights.The intergenerational right is not vacuous but a thinking achievement by tak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under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of mankind as its legal basis and premising on the recognition of future generations'right as an emerging right,with an aim to seek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current generation's rights and future generations'right for realizing the control over the unknown risks of mankind.When human beings face unprecedented risk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gene editing to the internal resources of human bi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 intergenerational right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as an emerging right in the new dimension.
Keywords: Human Gene Editing;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Intergenerational Right;Emerging Right
中图分类号: DF0-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512(2019)05-0081-15
作者简介: 钱继磊,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优势学科项目“新时代中国法理学范畴及其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9BYSJ0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陈历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