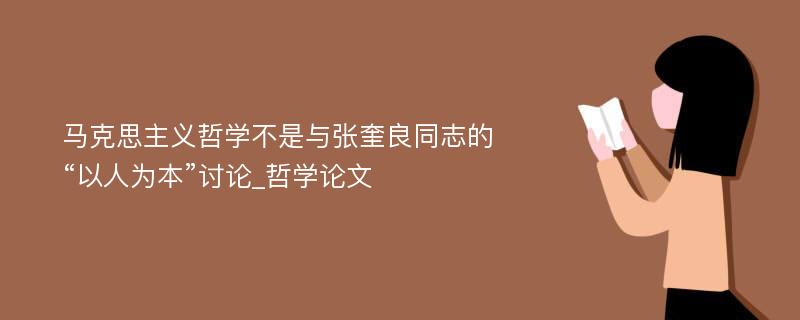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以人为本”——与张奎良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以人为本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同志论文,张奎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早期的哲学革命”
张奎良同志在《试论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哲学发展轨迹》(《哲学研究》1994年第2期,以下简称“张文”)中说:“马克思早期的哲学革命,中期《资本论》所达到的新的制高点,晚期唯物史观的新升华,都是以深化对人的正确理解为契机实现的”,这是“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哲学发展轨迹”。果真如此,“马克思早期的哲学革命”就是假的。因为即使不顾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的人道主义史,在他以前的费尔巴哈就高举人本主义的大旗,总不能否定。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神圣家族》也打着“真正人道主义”的旗号,已不可能是第一个“以人为本的哲学”,怎么会有“哲学革命”呢?
哲学上所说的“本”,当然是“本原”的意思,而不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实际对象”,因为“哲学”不是“语义学”或其他学科。而在哲学上划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标准,只能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本原,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意思。“张文”说:“先后出现了神本、物本、心本、人本等哲学派别”,就是如此。“神本”是以神为世界的本原,而不是因为研究神;“物本”是以物质为世界的本原,而不是因为研究物质;“心本”是以思维为世界的本原,而不是因为研究思维。否则,研究神和思维的人就注定是唯心主义者,而研究物质的人,就注定是唯物主义者了。
“人体”是与“神本”相对立的学派。它以人的肉体为本原,就归入“物本”;它以人的思维为本原,就归入“心本”;它以人的“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为本原,不过是“心本”和“物本”的二元论哲学。“张文”说:费尔巴哈“既强调外部的自然存在,又重视人的内在的意识和情感,认为世界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是‘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他的人本主义就是在人的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相统一的基础上对世界的一种理解”。但是这种二元论归根到底还是唯心主义,因为他说:“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下卷,第27页)。因此费尔巴哈的人本哲学也是不彻底的,他反对神学,决不想废除宗教,只想使宗教完善化。
马克思哲学以什么为“本”,当然也不能例外。他成为“费尔巴哈派”时,虽有自己的独创见解,但也是以人为本。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不过马克思不以“费尔巴哈派”为满足。他为了使人了解他的“哲学发展轨迹”,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明:“当1845年春他(指恩格斯—一引者)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结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巨著,正是针对着费尔巴哈的人本哲学,第一次详细制定了他们发现的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史上的真正大革命,不仅使从前只在自然观方面的唯物主义发展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领域,而且克服了从前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不彻底性,使之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
唯物史观不仅推翻了各种“以神为本”的哲学,而且推翻了各种“以人为本的哲学”,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领域中也确立了以物为本的哲学。因此这个“物”不只是自然物,而且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即生产关系。人本哲学从“人的本质”出发,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团体”,马克思则明确宣布:“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2页),所以正好与人本哲学相对立。唯物史观也不能叫做“唯人史观”。
只有发现了从前哲学所不知道的客观物质的社会关系,并用它来说明主观精神的社会关系,才能代替从前各种“以神为本”和“以人为本”的哲学,树立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为本的哲学”只是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以前的一种“哲学信仰”,只要不清算这种哲学信仰,唯物主义就不能在人类社会中树立起来,因而也就不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把马克思“哲学发展轨迹”归结为“以人为本”,只反映了他在制定唯物史观以前的哲学信仰,却否定了他在1845年清算了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和在制定唯物史观以后发展起来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马克思中期的哲学
“张文”说:“马克思中期的哲学思想和早期是一脉相承的,是他早期所得出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结论的继续贯彻和展开”。这就不仅抹煞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而且忽视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结论正是为了与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看作“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的思想相对立。因为他“(1)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一孤立的—一人类个体;(2)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而马克思这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正是“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因此不属于早期,而是中期开始的标志。
“张文”说:“马克思早就认识到:‘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所以马克思一登上哲学舞台就庄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颠倒了马克思的“哲学发展轨迹”。因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马克思写于1857年8月底—一9月中,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则写于1843年底—一1844年1月,何者为“早”,一清二楚。后来的观点怎么能成为早先观点的原因呢?
“张文”说:“只不过研究的取向改变了……从内在本质的揭示转向外在本质的探讨”,“无论是内在的抽象人或外在的具体人都是人的本质的局部,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独立地体现人的本质”,企图以此统一早期和中期的对立。但这只是人本哲学的机械统一,只把人看作外在肉体和内在灵魂的局部相加。唯物史观却相反,无论“内在本质”或“外在本质”都是全体,只有“内在本质”不能独立地体现人的本质,因为内在本质不过是外在本质在头脑中的反映,两者在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外在本质”也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们之间的物质社会关系。它如不能独立地体现人的本质,怎么会有“现实性”呢?对“抽象人”和“具体人”也有不同理解。人本哲学认为“灵魂和肉体的统一”,就是“具体人”,或“现实人”。唯物史观则认为,这种“现实人”只有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才能存在,因而脱离社会关系的“现实人”实际上并不存在,所以仍然只是“抽象人”。
因此人本哲学与唯物史观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前者从“人本身”出发,后者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社会关系也有不同理解。前者除了爱与友情以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其他关系,后者则把生产关系看作其他一切关系的物质基础。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友情,它们归根到底也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物。所以“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一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6页)。
马克思说:“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同上书,第88页)。可见这里注明“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正是为了指出不要因见到“统一”就忘记了不同时代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本质差别”。“张文”这个引证,不仅不能证明“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反而证明人的根本在于生产。当然生产也是人的生产,但是没有生产,人就不能生活,因而也就不会产生人,产生了也不能存在。
“张文”说:“人作为主体不能不把自身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和标准,视自己类的需求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但是人不能不受社会关系的干扰。而在私有制下,正如恩格斯所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一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人在这里不仅不把“自身”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和标准,反而“自身”也采用财富作为衡量的尺度和标准;不仅不“视自己类的需求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反而还要互相残杀,甚至以毁灭自己这个类相威胁。人本哲学只能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人的本性,要想改变就只有消灭“人本身”。唯物史观则相反,既然人的这种本性是由一定社会关系决定的,当然不能完全要个人来负责,而且只有改变社会关系才能改变人的这种本性。
《资本论》的“核心”不是“人本身”,而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它的目的也不是“揭示人的本质”,而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正如该书第一版序言所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在这里正如“张文”所说:“现实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张文”说:“马克思一向认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真正开创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因为只有这时生存斗争才停止了,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实际上这只是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以后的观点。因为在人本哲学指导下,直至1844年,马克思还不把共产主义当作“社会形式”和“人类发展的目标”。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9页)。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上,“生存斗争才停止了,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
“张文”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指出,共产主义只有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即以人自身作为目的的人类能力充分发展时才会开始”。这也是误解。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讨论的是“自由”问题,而不是“共产主义”问题。他说:“事实上,自由的领域,是在必要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依照事物的性质,那就是在狭义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未开化人为要满足他的需要,为要维持并再生产他的生命,必须与自然相斗争;同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并且,在一切社会形态内,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内,他都必须这样做”(《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73页)。共产主义当然也不能例外。只是随着人们生产力的发展,人才在自然界中逐步取得更多的自由,但是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社会中。而在私有制下,生产力的发展,只为少数有产者带来“自由”,大多数劳动者反而越来越成为自己产品的奴隶。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成了自己社会的主人,因而可能合理安排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不再让它盲目地统治自己,可以用最小的力量支出,并在最适合人自身的条件下,取得最大的成果。“但这个领域,总归是一个必然的领域”;只有“在这个领域的彼岸,把本身当作目的的人力发展,真正的自由领域,方才开始。并且这个自由领域,也只有在那个当作基础的必然领域上,方才可以繁荣起来。劳动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同上书,第1074页)。否则也只能是空想。
“张文”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又提出分工和三大差别的消失,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等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但这不是一般共产主义的条件,而是共产主义自身怎样由低级阶段的按劳分配发展为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的条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在逐步消灭“分工和三大差别”,但是资产者想都不会想到要使“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而无产者又无物质手段可以使他们达到这一步。所以共产主义就只是空想。只有首先消灭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按劳分配,才能使剥削者也和劳动者一样参加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在劳动中养成劳动习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消灭“分工和三大差别”,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张文”说:“所有这些条件都是对人的要求,是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具备的素质”。但是却忘记了这首先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三大差别”就不可能消灭;没有生产关系的变革,人就不可能具备进入共产主义的素质。在这里,归根到底,仍然是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的素质,而不是相反。否则“人自身”的一切,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三、马克思晚年的哲学
“张文”说:“马克思晚年哲学思想的最大特色是从《资本论》转向人类学的研究”。既然早已进入“人本阶段”,为什么还要“转向”人类学呢?难道“人本哲学”与“人类学”之间也有方向的不同呢?
况且,“张文”说:“从内容上看,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包括关于东方前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性质、前途,东西方社会历史演进的关系,原始社会结构、氏族,家庭和婚姻形式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等问题的摘记和评述。此外,马克思对古代法制、国家及宗教等问题也表现了浓厚的兴趣”。难道这不是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以后和《资本论》所要研究的问题吗?
《资本论》不用说了,仅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例子足以证实。它不仅证明“第一种所有形制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而且说明“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自然宗教”是对自然界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现实基础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同样,法随后也被归结为法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一70页),等等。难道马克思在第一次制定唯物史观时就“转向人类学的研究”了吗?果真如此,还有什么“转向”的必要呢?因为他在此以前正好信仰费尔巴哈的“人类学”。
但是,唯物史观要从“物质生产”出发,说明各种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为什么不能对原始社会的历史也发生“浓厚的兴趣”呢?难道在1853年马克思又一次“转向人类学的研究”吗?而人类学只关心“人本身”,又为什么要对古代社会“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呢?
实际上,自从发现唯物史观以后,正如恩格斯在1890年给布洛赫的信中所说:“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只是在撰写《资本论》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研究古代史的新成果,不仅证明他在《资本论》中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来证明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而且还可以用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事实加以证明,所以在晚年那样的条件下还作了这些古代史“摘要”。因此所谓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的研究”,不是事实,只是想用改变名称的办法,把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以后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全部体系都重新纳入早期人道主义的轨道。
因此,“张文”说:“凝聚在这些内容中的最大的思想成果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新升华,而这是与当时的世界革命形势密切相关的”,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因为马克思没有回到早期的人类学上去,怎么会有“人学理论的新升华”呢?而所谓“当时的世界革命形势”,不过是“俄国革命胜利后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提到马克思面前”,所以他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张文”说:“俄国之所以要跨越卡夫丁峡谷,首先是考虑怎样‘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却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可见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避免资本主义,而是把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孤立的俄国革命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当然也就不能避免资本主义灾难。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当时俄国革命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但是有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条件,就可能避免这种灾难。因为彼此可以“互相补充”。而把唯物史观这种具体分析和运用,说成“马克思提出了俄国等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其“深刻基础就是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充分关心”,这就抹煞了其中存在着的世界观上的对立。因为自从发现唯物史观以后,马克思就不再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和命运”。因为在私有制下,人都属于不同的阶级,没有超阶级的人。所以只有不同阶级的“人的价值和命运”,而无超阶级的“人的价值和命运”。而“人的价值”如果以是否受苦受难为尺度,那么劳动者就是最无价值的人,而剥削者就是最有价值的人,因为在私有制下,劳动者受尽了苦难,而剥削者则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从创造历史的角度来看,只有劳动人民才是最有价值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剥削者则不过是他们身上的寄生虫。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正好说明不同阶级的人,不可能有共同的“人的价值”观。而撇开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只看“人本身”,人是无价之宝。因为其他一切物体都没有人这样的天赋,人还能把自身作为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正如劳动没有价值才能成为价值的尺度一样,“人本身”也只有无价值才能作为一切价值的尺度。人如果有了价值,就有大小的不同,价值不同的人,怎么能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呢?
“张文”说:“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社会中,社会进步与人的价值成反比,这是历史的基本规律”。如果这是马克思信仰人道主义时的观点,那么决不是他发现唯物史观以后的思想。因为只有人道主义才认为,劳动者受苦受难毫无价值地度过了一生,而剥削者吃喝玩乐才是最有价值地“潇洒走一回”。而唯物史观则正好相反。既然人类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那么即使在私有制下,也正是他们的受苦受难和不得不造反才推动了“社会进步”;要说“人的价值”,也正是他们默默的无私奉献才作了充分的体现。
“张文”说:“现在,马克思正面对这个难题:英国的侵略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对亚洲社会的冲击,一方面具有社会进步的意义,但同时也给印度和东方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牺牲”。马克思对此作了唯物史观的回答。正如张文所引那样:“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只要把“人民群众”和剥削者区别开来,事情就很清楚:因为资本主义促进印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归“人民所有”,而归资产者所有,当然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和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只能“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牺牲”。
“张文”说:“为社会进步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这就是私有制社会中广大人民群众必遭的厄运。所以,在私有制社会中,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决不能是人的价值,而只能是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把“广大人民群众”与“人”等同起来,忘记了在私有制下“人”还包括少数剥削者。而把“生产力的发展”当作“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又忘记了“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的问题,因而也就不会想到“生产力的发展”在私有制下只归少数剥削者所有,而不归“广大人民群众”所有。这正是人道主义认为“在私有制社会中,社会进步与人的价值成反比”的原因。因为对少数剥削者来说,正好与这条“历史的基本规律”相反,他们正是随着这种“社会进步”而身价百倍、千倍,乃至亿万倍。
“张文”说:“在马克思看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结果将是:一方面吸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将它神奇地发展了的社会生产力承袭过来;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痛苦、灾难和牺牲,实现了人的价值追求。这样,人的价值和社会进步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和协调起来,它与生产力尺度一起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历史尺度”。但是,由于忘记了这要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俄国革命为前提,而又用人本哲学取代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就使“跨越卡夫丁峡谷”变成了空想。因为一方面,不知道“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是什么,就可能“吸取”否定的成果。何况“神奇地发展了的生产力”还在资产者手里,你没有理由将它“承袭过来”,因为他们也是“人”,就有财产、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权,而且“共产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为了高扬人的价值”,不能使他们感到“痛苦、灾难和牺牲”;另一方面,俄国在公社以外的剥削者还占有生产资料,他们不可能想到“资本主义的痛苦、灾难和牺牲”而加以“避免”,而“广大人民群众”即使想到了,又没有“避免”的物质手段。这就是所谓“至此,对于长期来困扰人们的一个历史难题,即社会发展何以伴之以人的价值贬损的问题,马克思给出了最终的解”,也是所谓“循踪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脉胳,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价值的揭示过程确实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新视角”,“所以历史奥秘的真实的解不是存在于人之外,而只能是存在于人本身,人就是解开历史奥秘的钥匙”。
但是,“张文”说:“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人的本质存在于人的社会关系中,那么,为了揭示人的本质首先就要对社会关系进行解剖”。只要在这个前提下,遵循形式逻辑的推论,“张文”就会把自己所想的“轨迹”都否定掉。因为“人本身”如果是“解开历史奥秘的钥匙”,那么为什么不是“首先”解剖“人本身”,而是“首先就要对社会关系进行解剖”呢?
责任编辑注:《试论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哲学发展轨迹》一文见本专题1994年第3期5页。
标签: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人类学论文; 社会论文; 张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