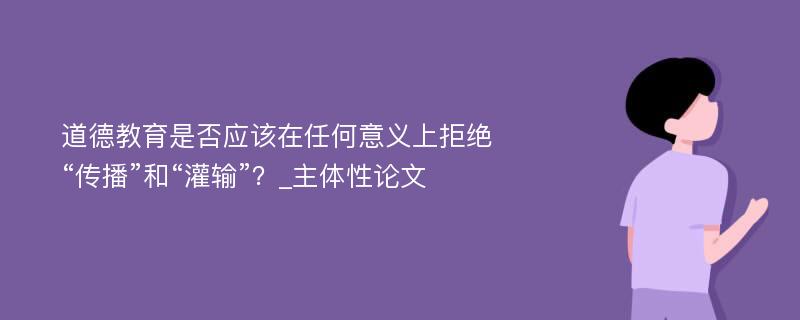
德育要拒斥任何意义上的“传递”、“灌输”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育论文,意义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有一种德育立论,主张应从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三个层次上全面“否弃”、“拒斥”灌输。在教育目的上,拒斥教育者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规范通过说服、规劝等方式转化为学生的思想意识和品德。在教育内容上,反对把某些具体的信念、教条和价值观念当成“真理”来传授,因为这种内容的传授排斥了与之相悖的信念、教条或价值思想,还因为传授的这种特定社会思想和道德规则都不能证明其在道德上的合理性。在方法上,反对传递,因为传递(灌输) 是为了达到一个固定目的而采用强制的非理性的甚至“权力主义”的手段和措施,而不管受教育者是否愿意或是否有能力接受。持这种立论者将“说服”、“规劝”、“教授”、“传递”都等同于“灌输”。而且又将“灌输”的语义释为浇灌、输送,或释为“注入”、“插入”、“用脚跟踩进”、“强制”,甚至说成是“迷惑”、“欺骗”、“洗脑子”、“吓唬人”等。这种德育论者,实际是拒斥德育“传递论”、“转化论”或“内化论”。它在德育任务和内容上反对“将一元化的东西定为一尊”,在过程和方法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教”,因为“教就是在学习者头脑中种植信仰”。这种德育理论的立论出发点,认为“传递论”是与“道德真义相背离的”,因为它是“对人的自由、尊严、个体主体性以及理智能力的蔑视甚至践踏”。认为“将一元化的东西定为一尊”否认了多元化文化中多元的信念、价值理念的存在,并培养学生对其他信念、价值理念视为危险、威胁并准备去战胜它。认为这实际是对学生的一种蒙昧、愚弄,是对学生主体的一种阉割。认为“教”实际是按着马头,强迫马饮水,就是对学生主体蔑视、压抑。因此认为“传授论”不管是从德育目的、内容上看,还是从过程、方法上看,都“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育方法”。结论是“传授论”的德育是非道德的。
如何看待“传递论”这是应该说清楚的。
我曾在一篇文章(注:孙喜亭《马克思主义与德育灌输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中说到:一切科学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都是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深入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切科学大都经过描绘、材料的积累、科学的抽象等认识过程而形成的。任何科学的发展,都可以有其历史的根据,任何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又都是由少数有教养的人经过复杂的思维加工过程,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的结果。而科学一旦产生,后人若再认识某一特定对象,就无须再走人类认识该事物的历史道路。人们只要通过传递、学习的途径,就可以掌握它。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这样,掌握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是这样。这个文化传递过程,其实,也可以称为“灌输”,即所谓的“输入”、“社会意识内化于主体”。灌输就是对人晓之以理,就是传播与传授。总之,“传递”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科学不会自发产生。崇尚“自发论”就等于否定教育,取消德育。
大家知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批评过机械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被动的产物的观点,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指出机械唯物论只是没有从实践的意义上去理解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制约,并未否认它的唯物主义基本思想。一个人生下来,总是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因此,他不能不受环境的决定,不能超越所处时代对他的制约。仅从一个人的社会意识和德性德行来说,至少有四个方面制约着个体的发展:
1)社会文化对人的制约性。不只是物质文化对人的制约,更主要的是精神文化对人的制约。人生于其文化之中,不能不受它的浸染,即我国古籍中所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一个社会占主体地位的社会道德,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主体的价值取向等,都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教、传导,通过文学、艺术等,影响一个人社会思想、道德准则的形成。
3)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教育活动,将一定的社会意识、社会道德传递给受教育的青少年一代。这种有目的性的教育活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所以,受什么教育并非由个体自由的、自主的、独立的去抉择。
4)社会法律规范。任何社会都有各种法制,个体生活其中,不能不受它的制约。尽管它是外力的他律,但它是任何社会人们生活、生存的基本的保障。人们必须遵守它,卫护它。这些维系一个社会生存、生活的行为准则,包括道德规范、法律制度、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等,都要通过所谓的“无意识”的习染和自觉的、有意识的传导、传播、传递,以实现对人的影响。否认传递,就否认教育。
是否在所谓多元开放的社会里,就不能将一元化的东西传递给学生呢?如果传递就是“迷惑”“欺骗”学生,就是给学生“洗脑子”,就是传授教义,就是“封闭人们的思想”,就是“将一元化的东西定于一尊”了呢?理论的彻底,在于能普遍地说明实际。试看一个孩子来到人间,他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方式,要不要教给他呢?待人接物的文明礼貌要不要教给他呢?公共秩序、交通规则要不要让他知晓、遵守呢?人类共同的道德理念,如正义、良心、善恶、节操等要不要树立呢?爱父母、尊师敬友、善待邻里、爱国、爱民的品德要不要培养呢?勿偷盗、勤劳、善良、正直、忠厚、诚实、俭朴等共认的美德要不要传给他呢?难道向学生传递这些一元化的人类共认的美德,并将这些美德定于一尊,就是对学生蒙蔽,对学生主体的宰割吗?难道非要让学生学会奸诈、虚伪、邪恶、偷盗、骄横、狡黠等,才是多元文化的建构,才是人主体的复归!
在从目的、内容和方法三个层面“彻底否弃与拒斥”灌输的主张中,最集中的是拒斥“传递”,拒斥“教”。大家知道,“教”涵义是“教化”、“教训”、“教诲”、“教授”、“教导”、“教正”、“教育”,反之还有“教唆”、“教猱升木”等。“教”无论褒义和贬义,其中都表现出教育者的意志性、目的性、组织性,或一定的强制性,都是教育者要给受教育者以影响。“教”在《说文解字》中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也”。所谓“施教”就是教育者要按照一定的目的,选择一定的内容,通过一定的方法手段,影响受教育者的发展方向。所以,若从目的的预设性、内容的特定性、方法的抉选性上看,都是对学生发展的限定,都可以称为“灌输”。“灌输”是否与道德的真义相背离,是否是对人的自由、尊严、个体主体性和理智能力的蔑视甚至践踏呢?
我曾在一本书中说过:“教育问题,不是单指人的发展的客观事实。而主要是依据一定的价值而作出的不同选择的有目的的行为。教育的实质是对人的素质发展的一种价值限定。也可以说,教育是为了维持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需求而被设计、被创造的文化的一种形式。”(注:孙喜亭:《教育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大家知道,一个人生下来,就带来了人的物种的基因,这种基因使人成为人,并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无限的可能性。物种的基因仅是发展的可能性,但非发展的现实性,是发展的发散性,但无定向。物种的潜能始终处在一种待发状态。潜能能否起动、发展,以及发展的方向、性质和达到的水平,这完全要取决于后天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后天所受到的教育的程度和教育的性质。这一立论可以从全部教育史中得到证明。既然,教育是对人的素质发展的价值限定,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是促使人的某些素质得到良好的发展;从消极方面来说,它又是使大部分可能得到发展的素质,实际上被荒芜。发展与荒芜是正反两个侧面。一切教育莫不如此。
道德作为维系人们之间的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任何社会,它都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的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具有善与恶、荣誉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的概念,并以此调节人们的行为。社会不同,社会的主体道德不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作为主流,并不把非主流道德当作“丰富和扩大”自己道德的内涵,通常都是要加以排斥。排斥其他道德渗透的德育,并非就是不道德的德育。所谓道德与不道德,并非由某一道德学说者的标榜而定,应该说判断标准是客观的。这就是看某一种道德是否是维护与推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奴隶社会的剥夺奴隶人身自由的道德,是不道德的,当然会引起我们现代人高度的愤慨。然而就奴隶制度与原始自由、平等的原始社会来比较,无疑是社会进步。就是对奴隶自身来说,它也较之原始部落间的残杀,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我们观察问题应有历史观,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要虚玄的抽象而使人难以捉摸。
当前,教育改革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是主体性教育问题。这一问题有人认为是教育哲学问题,更有人认为是时代的教育哲学。这一问题的提出应该说是十分有益的。它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沉淀下来的问题的角度审视,还是从面临的时代精神的客观要求的角度思考,主体性的教育问题,应是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道德人格”作为人的一种理想和追求,人们对现实的超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然而,一个正确议题,总应有一个适度的范围。实在说,在当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条件下,人的主体、独立、自由是很有限的。所谓的人的主体性,常常是将主体性异化为他体性,人的主体道德人格,常常是被异化为他体的道德人格。在这种“物役性”主宰下,在正像马克思说的“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的情况下,是不能去泛泛地谈什么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道德人格的。所以,谈“主体性”、“主体性道德人格”必须限定它的内涵。进而说,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道德人格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不是天赋固有的,天赋只给了人的主体性呈现的生理的物质基础;也不是人在自然状态下自发生成的,尽管自发性的求索给人的主体性以多方面的影响。人的主体性的形成正是靠学习、靠教育。常言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人的主体性形成,仍是靠“教”来实现。“教”包括道德目标的设计,道德内容的选择,教育方法的安排。
教育是教与学的双边共同活动,“授与受”、“讲与听”、“问与答”、“导与从”等,是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性的呈现与主体性丧失表现为多侧面:从教师的教、授、导来说是教师主体性的充分呈现,而学生的学、受、从则是主体性的丧失;从学生是认识的主体来说,他由要知到知,由要会到会,由理解到掌握等,则又是学生主体性的呈现,同时又在扩展丰富着自己的主体性。在教育进程中,学生表现为:外表面的主体性的丧失与内在面的主体性的扩展丰富性的统一,表现为前段性的主体性丧失与后段性的主体性呈现的统一。比如小学生识字,字的读法、写法、要教师教,学生必须按规范的标准去学,不能有自由,学生是被动的,这是主体性的丧失;一旦掌握文字工具,他可以利用文字工具充分表达他的主体的能动与自由,而又呈现他的主体性。这在德育过程中也是一样的。所以,主体性丧失与获得是辩证的,也是相对的。绝对的主体性是不存在的。
总之,德育是将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传递给受教育者的活动的命题,应该说是正确的。这无论是从目的的角度,还是从内容、方法的角度看,都是正确的。德育是内化过程,是输入过程,是传递过程。过去,学校德育确实存在德育目标上的空泛虚幻与内容上曾有过狭隘功利和急功近利的倾向;在教育方法和手段上曾有过“权力主义”和简单机械主义倾向;在德育过程中也存在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忽视学生的道德生活的需求,忽视德性德行的主体建构等问题。这是应该再认识的。但矫枉不能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