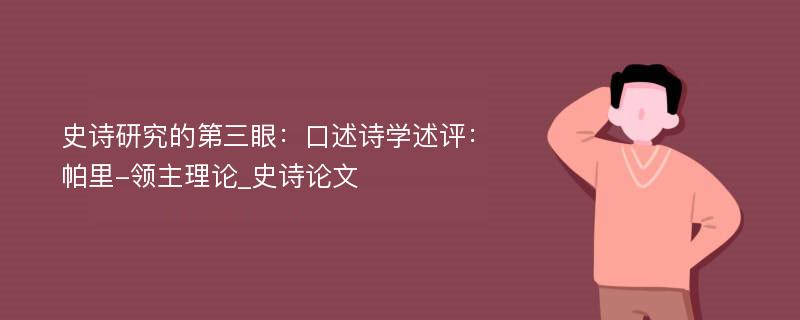
史诗研究的第三只眼——《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的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史诗论文,口头论文,只眼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03)-02-0079-04
《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这本书,是一本很不错的关于口头诗学理论方面的书,它对我国诗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有其一定的指导意义。其一,这种口头诗学理论,实实在在地烛照出我国史诗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其二,它关于史诗这样一种民间创作的记述与采风,即“田野作业”,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法,同时对我国民俗文化学的学科建设和史诗《格萨尔》的整理与研究也颇有启发;其三,是译者的一些处理,尤其是对于一些特别的表达方式、书名、篇名等的处理上,非常用心,很为读者着想。
一、关于帕里-洛德及其理论
“谁是荷马?他是怎样创作出我们称之为荷马史诗的?”
千百年来,这个著名的“荷马问题”一直困扰着荷马史诗的研究者们。谁也找不到关于史诗的创作者的确切记载,学者们只好根据零星的线索,作各式各样的推测,由此形成两派:“荷马多人说”和“荷马一人说”,彼此对立,互相攻讦,谁都以为自己掌握了有力证据,最终却发现谁也驳不倒对方。不过,这场论辩最重要的成果,却是在将荷马视为口头歌手(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论荷马最初起源》,1767年),并逐渐考证出在荷马文本的背后,有一种口头的传统。
……一切都倾向并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诗作不是为阅读、而是为了聆听而作的。(高特弗雷德·赫尔曼Gottfriel Hermann,1840,47)
十九世纪,德国古典派语文学家约翰·恩斯特·艾林特(Johann Ernst Ellendt)、亨利希·顿泽(Heinrich Duntzer)、库尔特·伟特(Kurt Witte)等对荷马史诗句法的语文学,即对修辞和步格的研究,使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从中发现了他的探索依据;而大约在同时期的瓦西里·拉德洛夫(Vasilii V.Radlov)、弗里德里希·克劳斯(Friedrich Krauss)、葛哈德.格斯曼(Gerhard Gesemann)和其他一些人类学家关于突厥和南斯拉夫的民族志报告,更使他对活形态的口头史诗演唱传统有了一定的了解。
借鉴上述学术成果,帕里从荷马史诗中的“特性形容词”的程式入手,分析发现,史诗的演唱风格高度程式化,而这种程式又来自悠久的传统。这意味着史诗是程式的,就必定是传统的。随后他又发现,这种传统的史诗演唱,只能是口头的。不过,这种对荷马史诗文本的语文学分析,听来虽则凿凿可据,毕竟还是一种缺乏印证的学术推想。
正是葛哈德·格斯曼等的报告和研究,使帕里得知在南斯拉夫地区,当时还存在有口传史诗的演唱传统,遂决定去那里进行田野作业,他的学生和助手艾伯特·洛德(Albert Lord)参与其中。在1933-1935年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前南斯拉夫省份的6个地区,用笔和特别制做的声学录音装置,记录下数百首guslari(歌手)演唱的史诗。之后,通过对这些史诗的对照和类比研究,他们确证了自己关于荷马史诗的推断,并印证了关于口头史诗创作规律的总结,从而建构起自己的帕里-洛德理论。
帕里-洛德理论,又叫口头程式理论,是一种针对民间口传文学作品,特别是史诗类大型叙事样式的方法论,它包括有三个概念,程式(formula)、主题或典型场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以及故事型式或故事类型(story-pattern or story-type)。通过对南斯拉夫guslari(歌手)的演唱进行考察,帕里-洛德发现,史诗歌手的每次演唱都是与以往不同的重新创作,他们利用从传统程式中抽取出的某个择选,来填充整个主题空间中每个转折当口的空位。这些程式既存在于史诗的颇具传统特征的循环性片语和典型场景上,也见诸诗中大量的叙事范式中。
由同一位歌手重复演唱,或由不同歌手采演唱同一部史诗的实地检测实验,使帕里和洛德进一步确证了这种术语化了的口头程式方法适用于史诗创作的有效性。这一理论形成后,他们又立刻将之运用到荷马史诗中去,从而第一次令人信服地推演并论证出荷马史诗的口头本质。随即,通过对guslari(歌手)演唱的史诗和荷马史诗的类比研究,帕里和洛德认识到:古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诗歌语言都以相同的方式被特殊化了:它们都由“大词”(large words)构成,这种大词易于变通使用,属于一种修辞单元和叙事单元,用以帮助歌手在口头表演中进行创编。歌手只要熟练掌握这些大词——程式,就可轻松表演上百、上千行的诗歌,由此解开民间歌手创编史诗的奥秘。
就这样,帕里-洛德通过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演唱进行直接观察,发掘出口头文学活动的基本特征。
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的基本内容
《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History and Methodology)是约翰·曼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出版于1988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一本关于口头创作理论的专著。根据其英文全名,我们知道这是一部对口头创作理论的历史及方法论进行评述的书籍。
根据译者朝戈金博士的介绍,弗里早年毕业于马萨诸塞大学,通晓法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意大利语、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等,是帕里-洛德理论学派自洛德之后的主帅。1986年,弗里在密苏里大学创建“口头传统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创办刊物《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由于他的才能和努力,现在这个中心和这份刊物已成为美国、乃至国际口头伎研究的旗舰,《口头传统》则成为该领域最主要的论坛。
弗里教授是一位非常勤奋的人,著述甚丰,代表作有:《传统口头史诗:〈奥德赛〉〈贝奥武甫〉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归来歌〉》(Traditional Oral Epic:The Odyssey,Beowulf and the Serbo-Croarian Return Song,1990)、《永恒的艺术:传统口头史诗的结构与意义》(Immanent Art:from Structure to Meaning in Traditional Oral Epic,1991)、《表演中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 in Performance,1995)、《荷马与口头传统》(Homer and Oral Tradition:Reading between the Signs)等等。他还主编了近10部论述“口头程式理论”的书籍,是《洛德口头传统研究丛书》、《表演和文本的表达》这两套在学界颇有影响的丛书的主编。此外,还有200多篇学术论文。
正如作者在“首版前言”所说,这是一本关于口头程式理论的简明历史。它是一本这样的著作——在口头传统的诸多形式及其对文人和文学作品的世界发生怎样影响的研究中,追溯此种独特方法的演进及其发展方向。尤其是,这一著作专门评介了由米尔曼·帕里和艾伯特·洛德所开创的学术领域——因此也以‘帕里-洛德理论’行世——由这两位拓荒者与其他学者共同耕耘的这方华野,至今已成为进入百余种评议传统中的学说。
基于此,作者在全书五章中,以平静和公正的口吻,“pravo”(笔直向前地)叙述了口头理论是怎么形成的。在第一章中,作者讨论了帕里-洛德理论的语文学、人类学和“荷马问题”的来源,对形成帕里创见的一般背景和发生真正影响的学术源头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区分,读者从中也可以看到,帕里是如何吸收前人成果来成就自己的事业的,从而领悟到做学问的技术和艺术。
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是记述帕里、洛德的学术成就,“行文中以帕里论析荷马的文章为起始,以他们一同在南斯拉夫的田野作业继之,再以洛德的延伸到其他领域的比较研究作结”,也就是以极其敛省的笔墨,概略地介绍了帕里-洛德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
第四章“学科的形成”,概述了帕里-洛德理论形成后,逐渐为学界接受并运用到“从古希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到细分为更小层次的其他传统之中,以至辐射到了多达百种以上的各自独立的语言传统之中”,以及由于这种“伸张”而终于建构出一门新的学科的现实。这里,弗里集中讨论了古希腊和古代英国在该领域的学术成果,对这两个发展进程分阶段论述,并将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详加展示;之后,对择选出来的若干其他传统加以综观。
第五章“近期和将来发展的走向”则是弗里关于口头理论在过去20年里最具有前途的发展方向的思考,以及对该理论所面临的挑战的种种观察。尽管由于该书所属“印第安纳民俗学丛书”不允许有冗长详尽的参考书目,但作者在附录中仍然列出了1800多个条目,并在每章的注脚中另加了一些参考书目,由此可见作者的博识广览及治学之严谨。
三、对于我国史诗传统的学术建构
在“首版前言”中,弗里指出:该书旨在成为一部导论性历史,因此最好从头至尾进行通读。此后,带着一些平行研究的知识去考察其它传统,便能进一步深化个人相关领域的工作。
可以说,这种荐举仍然是“pravo”(笔直向前地)的,尽管他是在推荐自己的书。但通读全书,确实令人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不能理解民间文学作品中的诸多重复,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的套话,那些千篇一律的开头结尾,或者故事模式和诗歌韵律;我们也不能理解那些民间歌手何以能演唱成千上万的诗行,特别是在像藏族文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为什么在当今时代仍会有140多位歌手,在既没有师承,也基本上是在一种不识字的情境下,竟能唱出十几部、几十部长达数百万诗行的《格萨尔》?
而当我们读过《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后,这些疑问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释。我们了解到,不管是韵文还是散文的口头创作,都既是传统的,又是程式的,但是,那些预制的、易于变通的结构或者程式,在各个传统的形成中,是必定会产生出差异的。那么,藏族史诗与蒙古族史诗间的差异在哪里呢?南方史诗与北方史诗的各自传统和差异又如何呢?“将那种共通的策略放在各自传统的背景上,联系着它们各自语言的特殊性来考辨”(作者中译本前言,6),这也就意味着,口头理论的研究,首先是一种语言学的研究,任何研究者要做一种口头创作的探讨,第一要素必须通达这种语言及其文字。
迄今为止,口头理论几乎烛照着全世界的口头传统,并贯通着从古到今的口头传统的历史。但对于其未来的最紧迫的任务,又是什么?弗里先生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在他为中译本而作的“前言”中进行了令人鼓舞的前瞻性建构:
在我看来,最首要的问题,是急需加强对活形态口头传统进行调查的田野作业。这或许是因为主要的理论进展皆出现在那些缺乏丰富的活形态口头传统的国家里,而能够进行实地调查的田野活动——唯有此类调查才能提供所需的材料——的地方,又在描述和分析材料上跟不上步伐。这恰恰是中国同行们可以施展本领的领域。在东方的这一国度中,活形态的口头传统是极为丰富宏赡的宝藏,世代传承在其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口传研究当能取得领先地位。中国同行们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有利的位置,他们可以做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所无法做到的事情:去体验口头传统,去记录口头传统,去研究口头传统。这些传统在范围上具有难以比量的多样性,因而更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如果在未来的岁月中,口头理论能够在多民族的中国,在她已为世人所知的众多传统中得到广泛检验,那么国际学界也将获益匪浅。
而这种建构,既是对我国口头诗学历史与现状的精辟概括,也是对我国学界的一种客观公允的鞭策。
四、关于译述及其他
所幸的是,弗里先生对中国口头传统的期待,很快就在中国有了回应。第一位成功的实践者,就是本书的译者朝戈金先生。朝先生2000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他的博士论文《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就是口头理论在蒙古史诗研究中成功应用的范例。不过,本文并不准备对此书更多置评,我们且将目光凝聚在他的这部译著上。
读这部译著,最令人赏心悦目的,就是译者在一些细节上的匠心。我们不必说对于正文的翻译,译者是如何尊重原来的文本;也不必说这种尊重,需要译者多么呕心沥血;而单就译者对引文、对注释,特别是对一些术语的处理,就每每能令读书的人大感方便和获益。我们在过去读一本译著,读到末了,常常还不知道它的原名是什么,原作者是谁,而在《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这部译著中,我们处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英文原文对照,这一方面大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另一方面便利于我们进一步检索或查阅。又如原书的注释,都分章排在后面。对于我国读者不一定熟悉的概念术语,译者不仅一律加注原文,还请原作者弗里先生补充说明,并加上了数十条的“译注”;最后的参考书目都没有汉译,也没有去掉,“是因为考虑到绝大多数的著作都没有汉译本,仅将书名译出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可以直接利用外文资料,保留书名,就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这些在在都体现出译者时时想读者之所想,也体现出一位学者治学的科学态度和精神。
我想,借用《亚洲民俗学研究》的评述,“这部书从哪一个方面说,也是学术研究的典范”,来评述书中的理论,评述著者,评述译者,都是极为精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