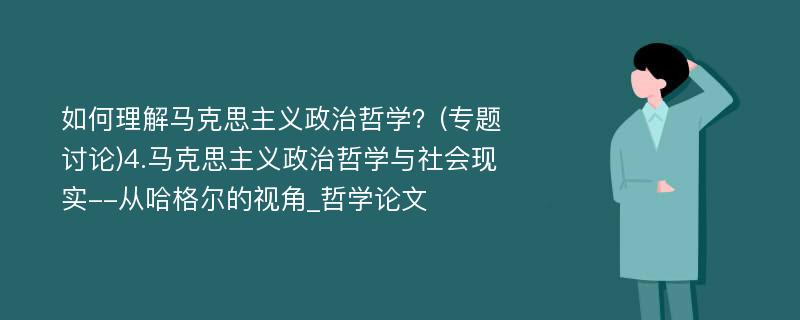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专题讨论)——4.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社会现实——从黑格尔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黑格尔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5—0001—08
政治哲学的近代形式,在黑格尔哲学中已经得到了最终的完成。这种完成,一方面意味着整个近代政治—国家的理论在黑格尔哲学中获得思辨的总结;另一方面,又特别地意味着在所谓政治事物中“社会现实”的那一度被积极地揭示出来。关于前者,正如马克思所说,“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al pari〕上的德国历史”;“德国人在政治上思考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是这些国家理论上的良心”[1](P7、9)。关于后者,伽达默尔在《20世纪的哲学基础》中写到:“黑格尔哲学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进行清晰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2](P111)
就此而言,特别是就“社会现实”的首次开启而言,黑格尔哲学乃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批判地继承这一财富的过程中产生的。这里可以举出的一个突出反例是:费尔巴哈完全错失了这笔遗产。恩格斯曾引用施达克的话说,政治对费尔巴哈来说是“一个不可通过的区域”;在这样一个区域中,与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表现出来的乃是“惊人的贫乏”[3](P236、237)。为什么事情竟是这样呢?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一般所谓人间事物的“社会现实”已被揭示出来并且被把握住了——虽说这种揭示和把握乃是思辨形而上学的;而在费尔巴哈那里,由于其社会概念仅只依循于抽象的哲学直观,所以真正的“社会现实”还根本没有进入到他的视野中,更遑论被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了。因此,即使在今天,只要我们还想对政治事物的主题作出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甚至仅仅只是为了能够就此正确地提出问题,就决不能够匆匆地越过黑格尔,越过在黑格尔那里已然绽出的“社会现实”的那一度。
在黑格尔哲学中,对社会现实的积极把握是与对主观意识(或主观思想)的尖锐批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主观意识的观点突出地表现为“反思哲学”,即立足于“外部反思”的抽象思想。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外部反思不会停留于并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上,但却知道如何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外部反思任意地把给定的事物纳入到一般原则之下,所以,说到底它只是抽象的和无内容的形式主义,只是诡辩论的现代样式。不消说,这种外部反思正是远离并且遮蔽社会现实的必由之路;同样不消说,这种外部反思在今天比在黑格尔的时代甚至更为普遍。就此而言,黑格尔对主观意识所作批判的积极意义首先就在于:要求使思想完全进入到事物的客观内容之中,并从而使“社会现实”能够真正绽露出来并且被深刻地把握住。因此,举例来说,在黑格尔那里,与其说道德出自我们具有对它进行反思的内在自由的情境,毋宁说,道德即在于按照某个国家的习惯生活。在这个看起来颇有点粗鲁的简单公设中,实际上已含蓄地包含着客观精神的概念。对于黑格尔来说,社会的现实正是在客观精神对主观精神的超越中显现出来的,就像客观精神在为绝对精神所超越时获得其真正的哲学证明一样。
因此,一方面,黑格尔猛烈抨击对政治—国家的主观思想和主观态度:针对道德、宗教或知性的意识试图在内心生活中寻求慰藉,以逃避政治现实的“喧嚣和狂躁”。黑格尔一力为政治生活的合理性辩护,针对厌恶政治的浪漫主义者,以及无视现实的国家而热衷于理想国家的空想家和改革家,黑格尔力图证明现实的国家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与上述对主观思想的批判相联系,黑格尔在政治事物的领域中积极地开启出从属于客观精神领域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如果说家庭是具有实体性的统一,它构成了一个以家庭成员的彼此信任为基础的整体,那么,市民社会则是独立成员的结合体,因而代表着区分或差别的环节[4](P241、242)。至于有别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国家,作为真正客观的和普遍的东西,既是个体之实在性的基础——个人只有在国家中并通过国家才获得其真正的实在,又是人间事物中一切冲突和对立的统一与和解——“特殊与普遍在国家中的统一是一切事物的基础”[5](P879)。
今天,我们已不难看出,当黑格尔在其法哲学中依循客观精神的方向揭示出社会现实的同时,又使这个社会现实本身被遮蔽起来了。一方面,社会现实被揭示为这样一个广大的人间事物的有机整体,“法、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进去了”[3](P236);但另一方面,体现在个人关系、家庭、 社会和国家中的所有冲突,都被归结为主观自由和客观自由的对立,并且在“地上的神”即国家中被扬弃、调和、解除了。这样一来,不仅真正的社会冲突本身被当作无关紧要的环节加以扬弃而丧失了其本身的实在性,而且冲突在国家中的调和以及理性在国家中的实现变成了纯粹辩护性的——黑格尔的“无批判的唯心主义”导致了“同样无批判的实证主义”。
正是从这里开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清算。虽说这一清算的立脚点直接出自费尔巴哈,但其结果却是批判地拯救了在黑格尔哲学中开辟出来的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洛维特的下述说法是正确的:“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并不否定黑格尔的原则,而是仅仅否定由他自己所断言的理性与现实以及普遍本质与个别实存的统一的具体落实。”[6](P195) 就这一否定而言,对立突出地表现为:“马克思和基尔克果的攻击恰恰把黑格尔统一起来的东西给分开了;两个人都颠倒了他的理性与现实的和解。马克思以政治哲学为批判对象,而基尔克果的攻击则针对哲学的基督教。”[6](P183)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引人注目的主题集中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在这方面,马克思首先是借助于费尔巴哈指证说,黑格尔在他的中介过程或“推移”(思辨推理)中实际地制造了主体和谓语的颠倒。黑格尔把主体设定为“理念内部自身”,而政治情绪和政治制度等等则成了谓语。这样一来,《法哲学原理》由家庭和市民社会向政治国家的“推移”,就不是由家庭和国家的特殊本质引申出来,而是从所谓“理想性中的必然性”或“自由的普遍的相互关系”中引申出来。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处处把理念当成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谓语,但“事实上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7](P250、251、253、255)。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在他的激烈批判中同时指证了黑格尔法哲学“较深刻的地方”,亦即“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出发,并把这种对立加以强调”;不仅如此,黑格尔还“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作一种矛盾”。而黑格尔的错误则在于:矛盾的克服或解决仅只是表面上的,亦即只是通过所谓中介作用或推论,在理论上制造一种妥协的、自相矛盾的“居间者”。因此,黑格尔法哲学的全部非批判性就集中在这样一点上,它把“现象的矛盾”直接归入“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7](P312、358)。与此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就像立法权的矛盾乃是“政治国家的矛盾”一样,政治国家的秘密植根于“市民社会的自身矛盾”;因此,被黑格尔了解为“现象的矛盾”,实际上倒恰好是“本质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等级或阶级所具有的意义——等级或阶级的差别、分裂和对立[7](P346)。 如果说这种“本质的矛盾”不能通过推论的“居间者”来迁就,那么等级或阶级就意味着“真正的极端”。而真正的极端“之所以不能被中介所调和”,就“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7](P355)。
由此可见,当黑格尔把近代社会的分裂和对立最终归入理念自身的同一,从而依循一般权力体系将国家构成为扬弃了一切对立的“宁静的整体”时,马克思则把政治国家的本质性导回到市民社会,亦即导回到市民社会本身所固有的分裂和对立中。而这就意味着在黑格尔之后“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政治国家的本质不在作为客观精神的国家理念中,而在市民社会本身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中;正像所谓普遍的权力或法(right)的本质并不居住于“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中, 而是植根于“社会权力”(social power)的冲突中一样。真正说来,这种社会权力的冲突是“理性前的”,正是它构成了理性的国家或理性的法等等的现实基础,而不是相反,仿佛作为国家或法的理性倒是社会权力的根据,本质或真理似的。总而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依靠对“社会现实”的这一重新发现——它继承并且超越了黑格尔的遗产——才真正成为可能的,而当今政治哲学的任何有意义的新成果都既不可能无视也不可能绕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伟大发现。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自我理解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只要我们仍然局限于主观意识的外部反思中,那么,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就不可能被引领着来同我们照面;而只要这样的社会现实尚未被我们清晰地认识和把握,那么,当今时代的政治事物对于我们来说就仍将是“一个不可通过的区域”。
标签:哲学论文; 政治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哲学家论文; 法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