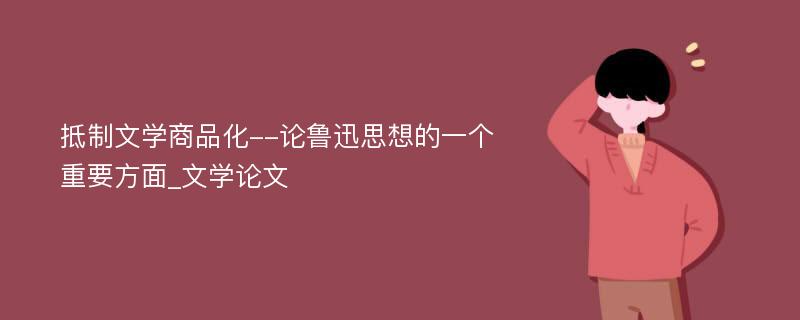
反抗文学商业化——论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一个重要论文,侧面论文,思想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反抗文学商业化的思想构成 据鲁迅《“京派”与“海派”》一文,我们知道到上海之后的鲁迅是“近商者”,繁荣的商业氛围保证了他生活富足和身份自由,“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只不过鲁迅把环境存在与思想独立分开,他拿稿酬版税,写自己所欲写,反抗文学的商业化,进行思想文化启蒙。 商业性旨在营利,而非商业性则不以营利为目的,例如慈善活动、宣传展览。而所谓商业化,则不限于目的,更注重手段与影响,它可能包含着低质量、欺骗性、浮躁性、乏意义、平面化、狭隘性等等负面特征。鲁迅对文坛商业化的概括形象逼真,它具有“三气”:洋场气、商人气、流氓气。“所谓洋场气,是不足惧的,其中空虚无物(因为不过是‘气’)”①。至于“商人气”,鲁迅更是经常提及:“上海到处都是商人气(北新也大为商业化了),住得真不舒服”(《书信·290820·致李霁野》);“一切伎俩,都已用出,不过是政客和商人的杂种法术,将‘口号’‘标语’之类,贴上了杂志而已”(《280530·致章廷谦》);“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340920·致徐懋庸》)。 鲁迅还对“流氓气”大加贬斥:“这里的有些书店老板而兼作家者,敛钱方法直同流氓,……大约开书店,别处也如上海一样,往往有流氓性者也”(《290708·致李霁野》);“上海秽区,千奇百怪,译者作者,往往为书贾所诳,除非你也是流氓”(《300903·致李秉中》);“上海的文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340920·致徐懋庸》)。前一句既指明“商”(书店老板)、“文”(作家)二位一体的流氓身份,又直斥了流氓敛钱目的与敛钱方法的卑劣,更指出流氓性的普遍存在,肆虐于中国而不为上海所独有。中间一句公开宣布书贾流氓之欺骗性和“秽区”气,损害作者译者利益。末句公然指出上海文场的凶险。 再者,鲁迅对圈子意识严重的上海刊物极为厌恶(《351118·致王治秋》),对一出锋头就排斥同志私心太重的新刊物(如《作家》之类),则痛斥其病态(《360523·致曹靖华》)。除却抨击圈子(专卖)意识之外,鲁迅同样不放过“投机”意识或赶时髦意识。“革命”办起了革命咖啡店,文学书店更是招牌多多,他直斥书店“投机的居多”,招牌轮流转,去年的“无产阶级”招牌已过时,今年流行“女作家”招牌,连广告也像香烟广告般空洞花哨、不重文化,以致书店旋生旋灭,趋时则易过时(《290708·致李霁野》)。鲁迅在其他场合将此等意识称之为“滑头”意识,它既欺蒙又卑劣,重名声不重内容,鲁迅1921年8月26日致宫竹心、1929年6月24日致李霁野的信都有涉于此。 三种“气”,两种“意识”,在文学者鲁迅看来是空洞无物、缺乏审美价值,在启蒙者鲁迅看来则是隐藏压制、瞒骗与势利,它们集中反映了文学在出版、销售、创作、评论等方面的商业化倾向,概括起来,不外乎“策略”商业化和“思想”商业化。② 所谓“策略”,着重产品、手段和利益,前述的“政客和商人的杂种法术”、“敛钱方法直同流氓”、投机意识等都是文学商业化的策略。 策略之一是以财、色为书籍销售手段。在《书籍和财色》中,鲁迅指出商家卖书打折,送物,送钱等手段,如果说这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以财为销售策略,“所给的希望却更其大,更其多”,因此欺骗也更大更多。那么,“书中自有颜如玉”,却是以色(女作家、女店员)为销售策略,使得读者欣赏或沉迷,在“秀色可餐”的欲望中顺便购买书籍,以求有玉有书。但其最终结果不是做事,而是“做戏”,令人反感。 策略之二是以名人作金字招牌。例如《革命咖啡店》一方面指出文学广告的胡编乱造,名不副实;另一方面指出文化商人以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等名人为招牌,消费名人的策略;再一方面,名人们在革命咖啡店既喝咖啡又给人教益,读者边喝咖啡边接受教益,而且谈的是无产阶级文学,使得革命咖啡店变成了革命大戏院,在那里上演着“种种好玩的把戏”。而《“商定”文豪》则可说糅合了投机意识、圈子意识和名人招牌,讽刺了“文艺广告的夸大”,揭穿了商家“根子是在卖钱”的真相,以及文豪与商家互相借助,最终文豪作品虽无价值虽然贱卖,但是却借此“爬了上去”的目的。 策略之三是自卖自夸。如《文摊秘诀十条》和《文人无文》,或者“改首古文,算是自作”,或者编文学小报或期刊,暗捧自己,或者编《世界文学家辞典》一部,将自己和老婆儿子,悉数详细编入。 策略之四则为捐作文学家。这种文学捐班除了因为岳丈、老婆富裕阔绰,主要是因为自己有钱,捐作文学家,可谓“金中自有文学家”,如文坛“暴发户意在用墨水洗去铜臭”,显示出“暴发户的做作的颓唐”,“沾沾自喜”,以此为“爬上去”的手段。③从此可见,捐文学家不会折本,而且“名利双收”。 还有一种策略就是粗制滥造,改头换面,误导读者。例如《书的还魂和赶造》,鲁迅指出商家赶造的文学书籍或者是粗制滥造、内容空洞、克日速成的文化快餐,如“剪贴,瞎抄,贩卖,假冒”(《大小骗》),如“前周作稿,次周登报,上月剪贴,下月出书”(《“商定”文豪》),如《“寻开心”》提及的乱写现象;或者是零碎不堪、过时守旧的文化冷饭;或者以“大”或“多”或“廉”或“精”误导读者,使得读者耗费大量金钱却得到一大堆废物。 究其原因,这些策略的出现是出版者“明白读者们的心想”“又很明白购买者们的经济状况”④,摸准了读者的心理和钱包,才施展其浑身解数来谋求畅销,赢得眼球效应,“根子是在卖钱”。故此,鲁迅才在《上海文艺之一瞥》入木三分地指出“现在上海虽然还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谓文艺杂志,其实却等于空虚。以营业为目的的书店所出的东西,因为怕遭殃,就竭力选些不关痛痒的文章”⑤。 如果说“策略”的商业化体现了启蒙者鲁迅对欺骗、胆小、自私、势利、虚伪思想的批判,那么“思想”的商业化则体现了文学者鲁迅对文学的独立地位、作者的严肃态度、创作的认真精神的张扬。何谓“思想”的商业化?它是指在创作、评论等过程中,作者的思想、见识、人格等被恶劣的商业化所污染所损害。 首先是“广告式批评”。每一个文学团体,都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只是他们圈子意识太强,刚愎自用,故步自封,使得“每一个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都被‘打发’或默杀了”(《我们要批评家》)。如此一来,便造成了三种不堪设想的后果:或是使得读者受迷惑被误导,结果却更加困惑,吸纳了一大堆废物;或是这些自以为进步,自命清高的文学团体,却如《随感录·四十八》所言“本领要新,思想要旧”,互相扭打,自相残杀,窝里斗而又各顾各,自私自利;或是随时提防替别人做了广告,如《“某”字的第四义》讽刺此种心态为“暴露了一个人的思想之龌龊”,更有甚者如《序的解放》所言“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甚而至于作者不仅化名为另一个人,也化名为一个社,自卖自夸。对此,鲁迅极为反感:“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了’。”⑥ 其次,思想的商业化还体现为写作赶时髦。一窝蜂地来写无产阶级文学,写女性文学,鲁迅严正地指出这些赶时髦的文学创作缺乏经典作品和严肃作家。在另一场合,鲁迅通过对幽默小品潮流分析总结了赶时髦写作的三个阶段:起初是取得轰动效应,名利双收:“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小品文的生机》),紧接下来是作者队伍混乱,作品低劣,乱七八糟:“幽默那有这许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讽刺,讽刺就是谩骂。”(《一思而行》)结果却是对时髦思潮的反动和大骂,幽默时髦“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⑦。“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势,势必有想反此以名世之人,于是轰然一声,天下无不骂幽默和小品。”⑧对此,鲁迅不禁大为感慨:“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⑨ 再次,造谣卖钱则是思想商业化的第三种表现。因为谣言“易于号召读者”(《归厚》),“可以增加一点销场”(《论“人言可畏”》),而为达到此目的需要几方面配合。笔法有趣,善于幻想和描写,此其一。鲁迅惊讶“我到上海后,所惊异的事物之一是新闻记事的章回小说化。无论怎样的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⑩。选准焦点(卖点),此其二。一者以材料为卖点,“消息那里有这么多呢,于是造谣言。……使消息和秘闻之类成为他们的全部大学问。这功绩的褒奖是稿费之外,还有消息奖”(《祝〈涛声〉》),捕捉到读者的猎奇心理,从而扩大报刊销售量。二者卖身份,“传媒强调的是认同身份,……故而其主流和卖点常常是‘女性的’而非‘男性的’”(11),对女性身份关注有加,如秦理斋夫人(《论秦理斋夫人事》),如阮玲玉(《论“人言可畏”》),如女性乳房(《忧“天乳”》)。无论是女名人抑或是女平民,无论是生理(乳房)抑或是生命(自杀),都受万众瞩目,此即为传媒报刊的“重女轻男”现象。此外,“名人”身份更被大卖。之所以鲁迅屡被造谣,是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对提高文学或传媒报刊的销售量有极大帮助。鲁迅在《〈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中就批判了高长虹对他的造谣中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利用他的知名度,争夺或取代《莽原》,以拓展地盘与提升名气。(12) 以上种种,都具有商业化的形态与实质,充满了“商人见识”,唯利是图,“根子是在卖钱”。只不过有的“专卖”,有的“广卖”;有的狡猾,有的凶猛;有的空洞,有的污秽;有的身份单一,有的身份多变,诸如此类。基于启蒙立场,鲁迅甚至对同人刊物《语丝》,也因其滥登广告而大失所望,可见他对文学商业化的极度抵触与深度蔑视。 二 反抗文学商业化的应对策略与心理动因 上述商业化的弊端凸显了鲁迅启蒙的紧张,以及启蒙空间遭到的挤压。为了打造更广的启蒙空间,鲁迅又是如何“反抗商业化”的呢? 为了反抗商业化刊物、出版的个性缺乏,鲁迅以办好有个性的文学刊物来置换坏刊物,宣扬启蒙。许广平在《札记》中回忆鲁迅的办刊思想:主张刊物应该独具个性,强调需要添加新生力量,如此便为刊物奠定了独特性,增强了生命力。例如《语丝》敢说话的风格,《莽原》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基调。此外,鲁迅提出未名社的立足点在于多量出版与出版的书可靠(《261205·致韦素园》);在1934年4月12日致姚克的信中,提到他希望出一种刊物,专门介绍“并不高超而实则有益”的东西。而为了能够保持刊物的个性和启蒙的生命力,鲁迅极为注重以刊物为园地培养新人,并以此反抗商业化的圈子意识和名人招牌。 鲁迅对新人的关注可谓有口皆碑。郁达夫回忆“鲁迅的对于后进的提拔,可说是无微不至。《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13)。李霁野也认为鲁迅“是一向注意培养青年人的,总随时注意发现新人”(14)。鲁迅一旦发现了新人才,会常常无私地助其写作,助其资财。鲁迅培养文学新人,不只是为了新人自身,也是为了文学刊物文学启蒙的生长与壮大。1931年10月27日,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评价道,“未名社开创不易,现在送给别人,实在可惜。那第一大错,是在京的几位,向来不肯收纳新分子进去,所以自己放手,就无接办之人了。”接纳新人,让其进入刊物、社团,不仅锻炼了其能力,有利于结成联合战线,还为刊物注入了生命力。 为了反抗商业化的浮夸虚假、粗制滥造、空洞无物,鲁迅主张认真、真诚与真实。“洋场气,……敌不过认真。”(《290624·致李霁野》)据内山完造回忆,鲁迅批评中国人的不认真,认为“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15)。鲁迅办刊物,一丝不苟,李霁野回忆经过自己校过两次的印稿,鲁迅往往能发现其中的错误,所以他总想在鲁迅所校对的印稿中寻找疏忽之处,“但成功的时候却绝少”(16)。他就是以实际的范例教导人们工作要严肃认真,不可喧嚣取巧,只有如此,才能把刊物办好(17),才能于文学商业化的歪风邪气中屹立不倒。 鲁迅除了提倡以认真的精神对待文学与出版之外,还倡导真诚。鲁迅自拟的文学广告就极为真诚朴实。《〈唐宋传奇集〉广告》(18)毫无废话,毫无噱头,质朴实在,展示了校录者、内容、编者的认真,此书的作用,使人一目了然。即使有时直接说到印数和价格,鲁迅也能做到有一说一,以诚待人,例如《〈阿庚画:死魂灵一百图〉广告》。(19)在另一个文学广告中,则直言“无能”和“缺钱”。(20) 落实到写作上,针对虚假浮躁、造谣惑众、时髦空洞的文学商业化现象,鲁迅大声疾呼“真实”的重要性。鲁迅要求作者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作文秘诀》),要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要“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21)此外,鲁迅强调所有的文学报刊与限制都束缚不了他的创作,“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华盖集·题记》) 再者,针对商业化贻害读者,鲁迅重视启蒙传播的作用,提倡文学出版应该有利读者。他希望“读者也因此得到有统系的知识,不是比随便的装饰和赏玩好得多么?”(22)黄源在《鲁迅先生与译文》中也谈到鲁迅的读者意识:少数读者购得《译文》后不作为时髦装饰品,但能从头至尾读一遍,《译文》只是供给少数真正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简言之,鲁迅对将文学书刊作为时髦装饰品的有闲型、消费型读者甚为反感,他期待的理想读者贵精不贵多,崇实不崇虚,重有益不重娱乐。因此,鲁迅要求刊物对读者诚实,不欺骗读者,不使读者上当,1929年4月20日和7月8日致李霁野的信中就涉及于此。他甚至宁愿亏损也要印制装订较好的书刊给读者,这让许广平深受感动,“这种替读者想的一种无我心情,我是时常体会到的”(23)。 为了反抗无论是鸳鸯蝴蝶派还是走狗文艺的商业化帮闲化,及其唯利是图与胆小怕事,鲁迅力主文学报刊必须打造“发言之地”。《〈越铎〉出世辞》中“纾自由之言论,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24)可谓是鲁迅报刊启蒙思想的高度概括。《语丝》的发刊词,虽然是周作人写的,但多少代表了作为杂志同人的鲁迅的意思:“生活的枯燥”和“思想界的沉闷”是《语丝》产生的现实基础;“自由发表”是言论自由的外在表现,“自由思想”是言论自由的内在根源,或者说思想自由与表达思想的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根本属性;而“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是言论自由的目标或内在精神。难怪鲁迅在1927年8月17日给章廷谦的信中高度评价《语丝》,认为《语丝》所说的话,有好些是其他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到了《莽原》时期,《莽原》周刊出版预告表示要“率性而言,平心而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华盖集〉题记》则表达他“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的思想。而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的这种思想则更强烈也更坚定: 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起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25) 可以看出,《莽原》说话的语气明显比《越铎》《语丝》两者的创刊词重一些强硬一些,《莽原》要造出新的批评者,打造舆论空间(“发言之地”)。到了1930年代自由的空气都快灭绝时,鲁迅仍然想方设法争取发言之地,办报,用多种笔名投稿,文章结集出版时将文章还原,展现其韧性战斗的风格。 鲁迅要求文学刊物打造“发言之地”,其根源是言论的不自由,这与严峻黑暗的社会环境有关,也源于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刊物中“凡有进步性的,也均被删削摧残,大抵办不[下]去”(26)。只不过,鲁迅以刊物打造发言之地,以文学叩开言路之门,反抗权力却意外地获得了话语权与影响力,扩大了读者群,提高了销售量,反抗商业化却获得了商业化的效果。因为说到底,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其实是对话语权力的享有与争夺,话语权力借助报刊的广泛发行获得了强烈的扩张性、渗透性、不可知性与颠覆性。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鲁迅反抗商业化的呢? 首要原因在于他办报、写作是为了思想文化启蒙,是“为人生”的。他要用文学报刊创造精神的、文化的、民族的新生,终其一生,鲁迅除了写作和翻译,他至少参编、主编过20多种报刊。从留学东京到定居上海,报业活动几乎贯穿鲁迅一生,正是社会风气、启蒙责任使得鲁迅极为关注文学报刊的创办和编辑,注重文学的独立与传播。(27)鲁迅基本上只担任著作人与编辑人的角色,没有介入出版、发行、销售等商业味浓厚的环节也为他反抗商业化提供了心理根源。他只要关注读者“需要什么”,不关注读者“想要什么”,只关注文学书刊的精英立场启蒙责任,不注重书刊的商业利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持续发展。 再次鲁迅从北京来到商业气息浓厚的上海,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他的生活从北京时期的“优越”、余裕变成了上海时期的紧张、迫切、快节奏。他发现各种商业化的文学刊物媚俗有害,丑态百出。加之定居上海时鲁迅的启蒙思想、精英立场已经根深蒂固,他反抗文学商业化是势在必行的。 另外,中国传统重农轻商的集体无意识对鲁迅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中国“商品经济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特别是中国历朝奉行不渝的‘重农抑商’政策,更加强了商品经济的依附性”,“在中国农耕经济内部滋长的商品经济,同样具有较活跃的‘革命’性质,对自然经济有着潜在的腐蚀瓦解作用,但是这种腐蚀瓦解作用成长到一定程度,往往因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而被化解或吸收,中国封建社会里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的互相转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28)鲁迅的小说没有出现一个正面的商人形象,以上文章也涉及文人混阔了便进衙门去当官,透露了商人与政客的合谋。这种“轻商”心态便是鲁迅反抗商业化的精神资源。更何况上海“直到1923年它还是一个有城墙的古城,二十年代真正的工业也只是扬子浦一处的纺织业……直到后来上海以神话般的速度繁荣起来之后,以法租界毗邻的地区还保留着老上海的面貌,是典型的江南古城风格,是一种‘时代的残留’”(29)。况且,鲁迅自小生长在小镇,一直工作在商业气息不浓的城市,到46岁思想几乎定型时才移居商业味重的上海,习惯了农民式的生活方式,也习惯了农民式的精耕细作,而不习惯上海商业化浮躁空洞的写作方式和短平快的运作方式。 三 反抗商业化的文学史意义 宏观而言,鲁迅只是反抗文学商业化的一位著名代表,事实上,反抗商业化俨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大思潮,非常值得深入探讨。 先看“五四”时期,早在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就针对鸳鸯蝴蝶派之类商业化味道较浓的文学大声疾呼:“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30)。1922年,文学研究会的中坚茅盾公开批判文学要有“资产”,有“美妻”的所谓“艺术观”,“在他们看来,小说是一件商品,只要有地方销,是可赶制出来的:只要能迎合社会心理,无论怎样迁就都可以的。这两个观念,是摧残文艺萌芽的浓霜”(31)。创造社的代表人物成仿吾也高声呐喊:“文学决不是游戏……我们要追求文学的全!我们要实现文学的美!”(32)语丝社也大力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33)换言之,这种专断与卑劣无论来自政治还是商业都要反抗。另外,早期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同样反对文学商业化,楚女极力强调:“我们底艺术制作……不可因为是要供他人娱乐,或社会的嗜好,或因得金钱而表现。”(34) 接下来的1930年代,反抗文学商业化势头依然不减。左翼作家一边破喉裂嗓鼓吹革命文学,一边不遗余力地反抗商业化:蒋光慈在《关于革命文学》中反对“颓废的,市侩的享乐主义的作品”(35);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呼吁“组织一个反拜金主义的文艺家的大同盟”。此外,自由主义作家指出鉴于思想市场的混乱与“不正当”,指出“在这类买卖上不能应用商业自由的原则”,反对“投机事业”,并且标举“健康与尊严”的原则。(36) 1940年代,反抗法西斯反抗反动派的政治浪潮汹涌澎湃,但并不意味着反抗商业化思潮的销声匿迹。杨华(叶以群)大力主张“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里,要求文学作品不带商品的性质,是不可能的”,但鲁迅、茅盾、徐志摩、丁玲、巴金、曹禺、艾芜等等作家,“都绝无例外地是不投好读者底趣味,不迎合商业底心理,而完全以真实的作品获得广大读者底爱护”,这就证明业有成就或能有成就的作者,“只要他们自信心不灭,毅力不衰,则文学底商业化的现象是决不至于逼致他们‘搁笔’的”。(37)而沈从文则思考深入:一、商业化对文学的伤害。或者误导读者,或者趣味变得低下,或者粗制滥造,造成了作品的平庸无奇,作品看去都“差不多”,记着“时代”,忘了“艺术”。(38)二、商业化与政治(革命文学)的关系思考。他指出1927年后,新文学运动与上海商业结缘,“作品成为大老板商品之一种”,1930年后,又与国内政治不可分,“成为在朝在野政策工具之一部”,致使“作者的创造力一面既得迎合商人,一面又得附会政策,目的既集中在商业作用与政治效果两件事情上,它的堕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39)三、反抗商业化与拒绝读者。他强调“好作者固然稀少,好读者也极难得”,主张“作家有意放弃多数,离开多数”,“对于在商业习惯与流行风气下所能获得的多数读者,有心疏忽或不大关心,都势不可免。”(40)为此,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近乎挑衅:“你们(读者)欢喜什么,了解什么,切盼什么,我一时尚注意不到”,“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41) 不厌其烦地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的反抗商业化思潮,是把鲁迅放置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去考察,准确理解鲁迅的反抗商业化思想具有怎样的文学史意义。 首先从外部考察,以鲁迅为首的现代作家的反抗商业化思想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反经济”维度。这种反经济维度其实有着内部的考量,旨在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和审美价值,尤其是前述的新月派作家和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就鲁迅而言,除了对鸳鸯蝴蝶派之类的商业化文学大加鞭挞外,即使对革命文学,他也反对以文艺来作政治或商业的双重宣传,“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42)出于同样理由,鲁迅也抨击虽然正在盛行,遍满报刊,但却是走到了危机的小品文,他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43)。如果说沈从文为了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和审美价值,反抗文学商业化和政治化,注重生命与美,那么鲁迅的相似反抗则注重精神与力,或者说两者都有力,但是沈从文倾向的是疏离性的力量,而鲁迅倾向的是反抗性的力量,鲁迅把文学(甚至自身)作为反抗性的精神资源,突兀、犀利,横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存在。“文学由一种遵循着自身逻辑的秩序所支配,作为相对独立的‘场’,它与经济、政治、法律,总之,与‘权力机构’,并非处于一种从属的关系,而是平行、对等的,通过拒绝对于上述领域有效的法则体现出一种离心倾向。……在文学场中,经济资本受到蔑视,相反,‘文化资本’却占有压倒优势,它构成一种特殊的象征性价值,决定着文学生产者和文学产品在整个场中的地位。”(44) 以上所提到的作家的反抗商业化思想,鲁迅基本上都有涉及,但是有一种思想是鲁迅独有的,那就是鲁迅从反抗文学商业化中发现的新的奴役关系。他发现奴役关系不仅存在于政权奴役这一显在的层面,还散布在文学出版、传媒、商业等隐在的领域,“商业化”中的商人气、流氓气、圈子意识、滑头意识等都深藏着奴役关系,此之为奴役关系的普泛性、弥散性。而这些奴役关系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权力(权力思维)、强弱对比与利益心态的存在,只要权力在手,只要己比人强,只要有机可乘,或直接或间接,都将走向奴役。来自“下面”的权力与来自“上面”的权力互相影响,有权者奴役无权者,被奴役者奴役更弱者,从政客、老板、作者到读者,现实的奴役演变为瞒与骗的精神奴役,社会结构如此,就难以走出奴役与被奴役的怪圈,而这正是鲁迅所悲哀的,对文学“商业化”中奴役关系的发现加深了他的悲哀。(45) 这种商业领域的反奴役思想体现为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是鲁迅敏锐地发现被渲染的商业化中存在着奴役关系和权力意识。他抨击文学或新闻报刊通过生花妙笔,大肆渲染,获得眼球效应,借以谋利的造谣诽谤诬陷,实质上包含着极深的权力意识,对人们造成了深深的伤害。《论“人言可畏”》,鲁迅以启蒙者的眼光发现其中的谣言诽谤内含三个层面的权力。第一层面是政权,“这种案件,是不会有名公巨卿在内的”,而且阮玲玉“没有机关报”(政权的象征),否则也轮不到新闻记者多嘴多舌了。换言之,权力与知识携手共进,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与商业利润,知识因而具有意识形态与商业手段的双重性质。第二层面是男权,文学或新闻记者对男人是一笔带过,对阮玲玉却极尽渲染污蔑之能事,虽有商业考虑,但暗含着男权意识却是毋庸置疑的。第三层面,就报刊本身而言,存在着话语权。知识浸透了权力的汁液,一旦与文学、传媒界联合,便获得了广泛性、渗透性的话语权力,即使遭到政权压抑,它依然可以用舆论权力、语言权力织就一张张网,对弱者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与名誉伤害。可以说,鲁迅从中有意无意发掘出新的奴役关系——语言奴役,在此是文学、传媒语言(而非政治语言)的奴役,是播撒性极强的语言奴役,在语言中隐藏的奴役关系令人寒心。(46)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论秦理斋夫人事》等文亦有相关思想,此不赘言。 第二方面则是鲁迅在被统治阶级特许的商业化现象中发现奴役关系的存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就是明证,鲁迅指出被官僚特许的文学商业化现象并不单纯属于商业行径,而是政治与商业的合谋,无论是禁止(禁期刊,禁书籍),还是替换(赶开书店原先的老板和店员,换上同伙),无论是自作(做些文章,印行杂志,让胡说八道的官办刊物与帮闲凑趣的“文学”杂志充斥市场,造成一种天下太平的假象),还是强作(强迫早经有名,而并不分明左倾的作者来做文章,帮助他们的刊物的流布),无论是作者“称赞春天”,还是读者“无书可读”,都潜伏着奴役关系和权力阴影。鲁迅也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指出,“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无论鲁迅如何反抗文学商业化,他却不得不面对“反抗商业化”的悖论。对此,鲁迅曾指出作品的商业性,“是卖钱的……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看书琐记(三)》]商业化的社会环境、作品作为商品的属性和商业化的过程等外在因素姑且不论,单就鲁迅自身而言:后期鲁迅放弃教席,在上海“卖文为生”,版税、稿酬和编辑费便成为他主要的经济来源,此其一。另外,鲁迅也深知自己的名气与文章可以卖得高价,他在《伪自由书·后记》提到给《自由谈》写稿“十洋一千字”“靠卖文为活”。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鲁迅注重“文”的商业性,而非“卖”与“文”的商业化,就算“卖”他也只是私下卖名气实际上靠文章,因为当时他都用笔名,读者不知其真实身份。简言之,他与上述的商业化弊病相去甚远,他旨在以写作进行思想文化启蒙。 甚至可以说鲁迅的悖论在于他一方面反抗文学商业化,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创作却也被商业化现象所帮助所启发。因为“商业文化以其特有的嚣闹、驳杂与混沌,消解和冲淡着专制政权的文化围剿与舆论钳制,拓展也活跃着黑暗时代的言论空间,这在客观上有利于鲁迅所进行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特别是有利于鲁迅将一些忧愤深广的作品顺利地输送到读者面前”;此外,商业文化热衷于标新立异,逐奇求怪,“这平添了鲁迅的精神困扰,但也给他带来了全方面的心理刺激和文学灵感,使他能够站在思想和文化的前沿阵地,不间断地同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和新现象,展开碰撞和对话,从而爆发出旺盛而持久的精神创造力。”(47)正因如此,鲁迅指出“左翼文艺有革命的读者大众支持,‘将来’正属于这一面”(《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此乃商业对创作及发表的帮助。也因为如此,鲁迅在《二心集·序言》声明:“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即在一定程度上,报刊对作品的风格要求对鲁迅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与启发,激发了鲁迅的创造力,例如报刊对短评、杂感的篇幅短小、内容充实的要求造就了鲁迅杂文的短小精悍、思想浓缩与文字洗练,《花边文学》就是证明。 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与商业化文学的对抗,不仅显示了鲁迅的意义,同时也体现了商业化文学的价值,“在任何时代,文学都是社会权力分布的象征性系统。只有把文学场的内部逻辑同外在于它的社会逻辑结合起来,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可能获得全面而合乎实际的认识。”(48)鲁迅与商业化文学同处于商业化的社会环境之中,后者与经济权力甚至政治权力合谋,这是它的社会逻辑,同时它作为文学逻辑,具有非法、非道德、反权威的特征,不断地向以鲁迅为代表的正统的文学规范发起挑战和冲击,“文学发展和更新的历史应当看作一部‘支配的、正统的话语方式与非正统、不合法的话语方式的斗争史’”(49)。 鲁迅的反抗文学商业化思想最终是寂寞的。就历史而言,像鲁迅这样长期而深入地反抗商业化的作家几为凤毛麟角,鲁迅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也是最孤独的作家。就领域而言,鲁迅对旧文学、新文学、右翼文学、左翼革命、自由主义文学的商业化都持反抗态度,简直是左中右开弓。就本质而言,鲁迅的反抗商业化思想其实是反传播的。他的反抗精神与“战斗主义”本质上是反传播的,或者说反大众传播的,鲁迅反抗商业化的文学传播思想注重“思想的传播”,或日“思想革命”,他主编的刊物如《语丝》任意而谈,无所顾忌,但他主编、参编的刊物大多短寿;一般书报出版业“根子是在卖钱”,鲁迅却要“振勇毅之精神”,打造发言之地;从文学翻译传播来看,从1909年翻译《域外小说集》直到1934年的《译文》杂志,他都只重视少数读者,不顾销路。这还只是文学文本选择、读者意识的反传播,在文学翻译语言上也如此,《域外小说集》的古奥,翻译俄文理论著作语言的艰涩便是证明。更有甚者鲁迅有时是“拒绝传播”的,如他认为中国是“铁屋子”,以文学和思想改革中国“希望之必无”,实质上就是反传播的;又如他多次声明《野草》只属于自己,不希望青年读之。总之,主观上,启蒙者鲁迅重视思想传播,要造就“精神界的战士”,至于客观上的读者影响、传播效果则无暇无力顾及,即使单枪匹马、读者甚少也不改初衷。所以,在“思想”与“传播”之间,鲁迅可谓处境尴尬,难免“寂寞”。其实,鲁迅对此有着自知之明,他曾在《通讯》中说自己“思想革命”(包括反抗商业化思想)的前途黯淡,“迂远”、“渺茫”、“可悲”、“可叹”,后来更在《答有恒先生》中悲叹救救孩子之类“空空洞洞”,充满了启蒙无效体验,他只是习惯反抗绝望罢了。 ①(22)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93页。 ②(17)(45)黎保荣:《鲁迅的反商业化思想》,《名作欣赏》2007年第18期。此文只三千字,内容殊异。 ③④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239页。 ⑤(21)(42)(43)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15、84~85、592~593页。 ⑥⑦⑧⑨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2~493、487、499、499页。 ⑩(24)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42页。 (11)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05~106页。 (12)(46)黎保荣:《鲁迅对报刊谣言及其启蒙涵蕴的深层分析》,《名作欣赏》2010年第6期。 (13)(14)(16)《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鲁迅博物馆等选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251、253页。 (15)《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鲁迅博物馆等选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3页。 (18)(20)《鲁迅佚文全集》上,刘运峰编,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372页。 (19)《鲁迅佚文全集》下,刘运峰编,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页 (23)《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鲁迅博物馆等选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2页。 (25)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26)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 (27)黎保荣:《论鲁迅与报刊关系及其启发意义》,《晋阳学刊》2009年第6期。 (28)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46页。 (29)李书磊:《都市的迁徙》,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8页。 (30)(32)(33)(34)《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北京大学等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217~218、234、401页。 (31)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 (35)《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北京大学等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36)《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北京大学等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37)《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北京大学等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300页。 (38)(39)(40)(41)沈从文:《抽象的抒情》,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7、1、22~26、351~358页。 (44)(48)(49)《二十世纪欧美文论名著博览》,章国锋、王逢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9、89页。 (47)古耜:《商业文化大潮中的鲁迅》,《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3期。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广告策略论文; 商业广告论文; 商业论文; 读书论文; 莽原论文; 名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