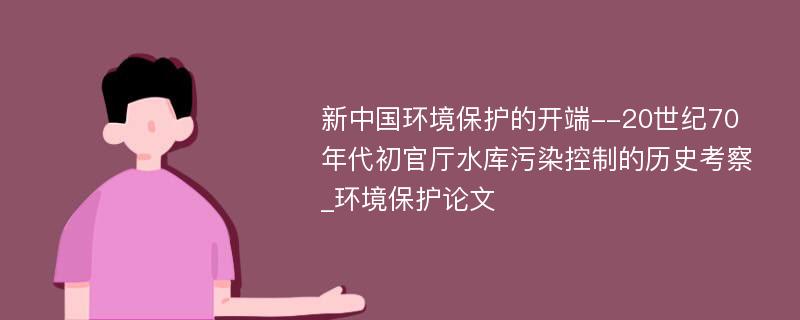
新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1970年代初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厅论文,年代初论文,新中国论文,水库论文,污染治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学术界大都认为,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起步的标志性事件,并将注意力多集中于会议及其之后的环保政策与举措。代表性研究参见王瑞芳《从“三废”利用到污染治理:新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安徽史学》2012年第1期),翟亚柳《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初创——兼述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及其历史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8期),张连辉、赵凌云《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观与人地关系的历史互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等。然而,始于1972年的党和政府对官厅水库污染的治理,却是在此次会议之前不多见的全方位环境治理,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1972—1976年间,党和政府自上而下调动相关省市、部委、科研单位对官厅水库污染进行了成功治理。它是新中国最早的水域污染治理,更是在国家层面上开展的的第一次实质性环境治理综合行动(参见曲格平、彭近新主编《环境觉醒:人类环境会议和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第474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编委会编《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第5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逐步探索中开启了新中国环境保护的实际进程。 一、对官厅水库污染的认识: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有污染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到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已面临废水、废气、废渣(简称“三废”)污染的严重问题。北京市1972年的全市工业污染源调查表明,“三废”排放量大,没有采取污染防治措施[1](P122)。特别是有害废水的数量日益增多,由于未做处理而任意排放,污染了江河、湖泊、海域和地下水源,破坏了水产资源,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人体健康[2](P313)。官厅水库污染就是极其典型的一例。 官厅水库是北京市主要供水水源地之一,上游由山西雁北地区的桑干河、河北张家口地区怀来的洋河和北京延庆的妫水河组成。1971年冬末,官厅水库开始发现漂有大量泡沫,水色浑黄有异味[3]。1972年3月,北京市场出售的在官厅水库打捞的鲜鱼有异味,食用之后人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洋河河源的良田屯社员反映,两年间患病者增多,普遍出现中毒症状,良田屯小学426名学生近一年来因病缺席率达50%,上课时打盹的半数以上,记忆力也都有不同程度减退[4]。妫水河边的社员也反映,库水有药味,食用后除有相似中毒症状外,由于饮水含氟高患关节炎掉牙的多[4]。 卫生部门就此问题向国务院作了专项报告,由曲格平将报告上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5]。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要求立即查清事件原因。很快,国家计委和建委组成调查组,并于4月开始调查。 当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即使在科学领域,“环境污染”、“环境保护”还都是新鲜概念,因而“在极左路线指导下,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存在污染” [5]。“谁要说有污染,有公害,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2](P2)还有一些人从环境污染会危害人体健康的角度出发,认为环境问题属于卫生领域,轻视环境污染对经济社会危害的严重性[6](P10)。有的上纲上线,提到政治斗争高度,判断污染原因是阶级敌人投毒。“那时人们的思想都特别‘左’,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特别紧,这水是流到北京去的,流到中南海的,一定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有人往水库投毒,想毒害首都人民,毒害党中央毛主席。”[7](P168) 在此历史背景下,由北京市“三废”管理办公室、官厅水库管理处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组成的“官厅水库污染情况调查组”对官厅水库污染展开调查。据当时被抽调参与调研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王景华研究员回忆:“上游建了造纸厂、钢铁厂、炭黑厂,小工厂很多,大量的污水进入河流,汇入水库,引起死鱼。”[8]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严肃性、准确性,调查组之后又在官厅水库区布置了采样点,对水质、渔业养殖、水生生物、水库的底泥等都进行采样分析。最终,根据大量调查事实和分析数据,确定“官厅水库的死鱼事件是由于上游工厂排放污水引起来的”[8]。化验表明,水库水质有恶化趋势。 调查组发现,沙城农药厂废水是危及官厅水库最直接的污染源[4];污染源主要是张家口、大同、宣化等地区的污水;“沿入库河流两岸建了各种工厂约500多家,根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排放污水约6786.8万吨,直接或间接地排入河道、进入水库,造成污染”[3];洋河河畔的沙城农药厂、沙城磷肥厂排出的废水污染严重,直接威胁了沿源7.5公里范围内六个生产大队的农业生产和社员身体健康;良田屯大队因距沙城农药厂最近,24口井水都有强烈地漂白粉味,含氯量在300~1000毫克/升(当时北京市自来水一般不超过100毫克/升)[9]。 显然,专家对当时国内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环境污染”的舆论、可能要因此承担的政治风险是十分清楚的。而“这样的报告上报,存在很大风险。但我们相信亲眼看到的,和向群众了解到的情况是真实的,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8]在调查结果、科学检验与政治压力面前,调查组专家选择了实事求是。 1972年4月29日,官厅水库污染情况调查组完成《关于官厅水库目前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认定了官厅水库属污染性质,而非投毒,主要是上游各河道的工业废水排放而致。报告强调,污染的程度严重,治理紧迫,“经化验,证明水质已受污染,并有急剧增加的趋势,水库盛产的小白鱼、胖头鱼,体内滴滴涕含量每公斤达两毫克(日本规定不得超过0.11毫克)”[4]。报告预估,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任其发展,按照现有废水排放量,“再过半年水库DDT的浓度可能由现在最大的0.42微克/升到0.95微克/升,其他毒物也必然相应增加,后果严重”[4]。报告郑重指出:“官厅水库受污染,势必直接影响北京市的地面和地下水的水质。保护官厅水库的水质,是关系到首都用水安全的一件大事,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4]6月,调查组正式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建议成立官厅水库水源保护小组,采取各种紧急治理措施。 四天之后,周恩来作出批示,要求成立领导小组,开展污染治理,尽快改变被污染的现状[2](P473-474)。紧接着 ,国务院以国发(1972)46号文批转《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批示指出,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对于防止污染必须更加重视,特别是对于关系到人民身体健康的水源和城市空气污染问题,各地应尽快组织力量,进行检查,作出规划,认真治理[10](P196)。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批示,显示了国家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在周恩来领导下,国务院首次向全国发出中国存在环境污染的警示,并提出对区域性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进行治理的要求。 二、官厅水库污染治理:调研治理并举,成效逐年显现 在周恩来指导下,横跨流域、统一领导的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很快成立,一边调研,一边治理,启动了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的历史进程。 (一)领导小组成立:横跨流域,跨省市协同管理 官厅水库水质污染直接关系到首都用水安全。在周恩来指导下,1972年6月23日,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迅速成立,主任万里,主要成员有: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以及中国科学院的领导[3]。领导小组和所属办公室是一个跨省、市的联合组织形式,主要任务是协调官厅水库上游,山西、河北和北京的工厂污染源治理;基本任务是组织统一规划、分头治理、联合检查、相互促进。同时,调集水文、气象、地质、水利工程等科技力量,展开对官厅水库全流域性的勘查工作,为治理收集系统完备的资料。 7月,领导小组在对13个市、县86个工厂作了详细、大量的实地调查后写出《关于桑干河水系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并上报国务院。该报告为整个流域污染源的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8月17日,国务院批转《关于官厅水库水源保护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9月5日,国务院批转《关于桑干河水系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并作出批示,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区必须严肃对待此事,积极行动起来,根治桑干河污染,一抓到底,不要半途而废[11](P549)。高密度、快节奏会议的召开和一系列报告及批示措施的出台,充分显示出党和国家对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的高效执行力。 (二)分批逐步推进:综合利用,边发现问题边治理 在有关专家指导下,领导小组采取综合利用、化害为利、改革工艺、减少污染、污水净化处理等积极治理措施,将不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和印发《工作简报》作为两个有力抓手,及时推广先进经验,并对落后单位展开批评和监督等,于1972—1976年间基本完成了对官厅水库的治理工作。 从1972年开始,国家和有关部委投入专款近3000万元展开治污攻关行动,分三批对官厅水库上游39个重点污染企业的77个项目进行治理,按其规模、性质分别确定相应治理方案[12]。同时,还在水库及其上游地区建成五个监测站。在专家和水库沿线企业及有关单位与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各污染项目治理取得了很大进展,并在系统总结中为水源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数据、分析和指导。 当然,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国家层面的治理行动,官厅水库的治理过程其实殊为复杂,并不如现今一样提前就有周密的污染治理方案,而是经历了一个边发现问题边进行治理的过程。例如,制定治理方案过程中,出现了信心不足和依赖思想,张家口有些人就认为 “设备缺,条件差,污水量大”。基于这种情况,在治理过程中,中共张家口地、市委主要领导主持会议并成立领导小组,检查并解决出现的问题;张家口计委等部门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13]。同时,这个过程中还存在着物资配备供给不及时、基层单位负责人认识不到位等混乱情况[14]。1975年5月《官厅水源保护工作简报》中亦指出,“还有一些同志和单位,对环境和水源保护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环保长期性认识不足,因此,班子不健全,遇事没人管的现象还程度不同的存在着,致使工程进度一拖再拖,长期收不了尾”[14]。应指出,当时在中国尚未形成任何成熟规范的环境保护程序,作为国家层面的首次治理行动,是蹒跚起步、懵懂摸索,出现一些问题不可避免,也可理解,无可厚非。 (三)治理成效:逐年好转,取得良好效果 官厅水库污染治理工程在1976年末基本落下了帷幕。领导小组在各方协调下,克服了种种困难,从1973年治理伊始就有了明显成效。 1973年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关于官厅水库水源保护工作的报告》指出,沙城农药厂滴滴涕车间停产以来,附近良田屯大队的社员健康状况有了明显好转[2](P448)。1974年上半年据河道和库区居民反映,除氯化物略有增加,水质略偏碱性外,水体色、嗅、味略有增加,滴滴涕、六六六等有机氯药的污染得到了控制,死鱼现象未再发现,其他多种污染物质的浓度都有所降低,库水水质得到明显好转[3]。1975年测定时,官厅水库水质显著好转,库水异味消失,水色变清,死鱼现象已经没有了。1976年以后,水库水质基本接近饮用水标准[15](P462)。 从官厅水库各河道综合污染指数(K值)的变化上看,1973年至1976年间大都呈现下降趋势。由于治理的迟滞反应,虽然1974年除妫水河之外的三个河道K值并未有减少,但从1974年起都展现稳定的下降态势,显示了治理的良好效果[16]。这项新中国历史上国家层面开展的第一项水污染治理行动取得成功,为今后环境问题的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官厅水库治理:新中国成功治理污染的历史样本 官厅水库的有效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在环境执政能力方面的一次成功实践,开启中国民众“环境保护”之启蒙,为中国治理环境污染树立了样板,奠定了中国环境保护尤其是水污染治理的模式。正如在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官厅水库污染治理中,“北京、河北、山西等省市领导同志亲自抓,统一规划,依靠群众,全面治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情况已经显著好转”[2](P315)。此次治理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第一,官厅水库污染治理开创了流域管理模式和环境保护的“三同时”制度。 在污染治理方面,“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奠定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流域管理模式;在污染防治方面,治理过程中提出的“三同时”成为中国环境保护方面的一项重要基本制度。 由于水源流域先后跨越不同省市、有不可分割的特性,对流域的管理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行政区划。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这个跨流域的水源保护机构,作为在地方政府间横向协调基础上的管理体制,证明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一是可以从流域管理的大局出发,全面协调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截至1975年,多次组织有关省、地、市“环办”、工业主管局和国务院有关部审查治理方案、检查工程进度、帮助解决技术和设备材料等困难问题,起了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作用。二是在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之后,又相继成立了关于保护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水域的环保领导小组。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作为首个国内跨流域环保机构,它的建立奠定了区域治理与流域治理相结合的环保基本格局。 在环境保护法制的建章立制方面,官厅水库治理中初步制定了涉及流域管理的制度和措施。如在1975年编制了《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管理暂行办法(讨论稿)》,并于1984年正式颁布《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管理办法》。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水库流域性地方性法规,为其后制定全国性的有关各领域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供了地方立法基础和立法经验。 从环境制度而言,官厅水库治理促成了“三同时”制度的出台。1972年4月29日,官厅水库污染情况调查组完成的《关于官厅水库目前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建议措施中就明确指出,“加强对库区周围及上游城市新建扩建厂矿的管理,必须在基建及设计中考虑工业废水的回收与处理,否则不得兴建”[4]。1972年6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建委《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中提出,“工厂建设和‘三废’利用要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10](P20)。作为新中国最早的环境管理制度,“三同时”制度自此肇始,并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环境管理手段,影响至今。 第二,官厅水库污染治理为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实践和思想认识基础。 1973年8月5—20日,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的实践,被作为做法和经验进行推广,促进了全社会对环境污染的认识和了解,以及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在会议准备材料和大会的主旨发言中都引用了沙城农药厂成功治理、对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的例子。同时,官厅水库污染得以有效治理所依赖的科学精神,也深刻影响着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对工业“三废”污染的讨论。会上,各路专家畅所欲言、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的环境污染的事实和风险,分别介绍了部分水域污染严重、局部地区大气受到污染、部分厂矿劳动环境不好不少职业患职业病等真实情况,批评了“社会主义无公害论”、“治公害误生产论”等错误认识,为客观认识现状,破除思想束缚,树立正确观念,促进思想开放,加紧污染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官厅水库污染治理体现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促进了环境科学学科的创立。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官厅水库污染治理是在极不正常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艰苦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极“左”的社会环境下,官厅水库污染治理能够排除国内种种不利因素的困扰,科学家能够秉承科学精神、实事求是讲出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并大力促成环境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体现了在那个年代殊为不易的科学精神的回归。 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研究促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出现在中国科研领域,这对于国家科学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在治理过程中创新采用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和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成为中国建构系统的环境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起点[17]。官厅水库治理因为在国内科学方面的首创,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四、余论 毋庸讳言,官厅水库污染治理作为新中国成立第一次成功的污染治理事件,不免烙刻政治挂帅的时代痕迹,也存在一些起步之初的难题,诸如管理体制、制度建设不健全,导致工作的成败完全因人而异。具体表现是,万里任组长时,深入调查,周密计划,敢抓敢管,措施落实[2](P4), 取得了很好的治理效果。而万里调走后接任的多位领导小组组长,在流域管理上没有做到一抓到底,部委之间、各省市之间,上下游之间,各种矛盾逐渐显现[7](P171)。目前,水库还是由于污染之甚退出北京城市生活饮用水体系。这种波折不仅存在于官厅水库污染治理一例,而是普遍见于环保事件中,可见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制度建设仍是制约中国环境保护成效的重要因素。 在回应民众诉求方面,未及时做好赔偿、解释等相关工作,酿成群体性事件。例如,1974年7月1日晚19—21时,良田屯生产大队千余农民包围、冲击了沙城农药厂,导致“工厂停产十二天,损失近五十万元产值”[18]。这次事件的缘起,是由于1972年沙城农药厂对良田屯的污染赔偿一直未落实。“农药厂经过停产治理后,滴滴涕、氯化苯、三氯乙醛在污水中的含量已达到或接近国家排放标准。由于非正常排碱,产生了危害,农民认为该厂在治理污水上弄虚作假,欺骗领导,是为不赔偿农业损失制造借口,如果再沉默下去,就要永远受农药厂危害。”[18]时至今日,政府因未能较好回应相关诉求、保护相关利益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仍接连不断。面对日益提高的公众环保意识,如何更好地满足公众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实现生态文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1972年官厅水库污染距今已有四十余年,但至今仍在展示着污染与治理的双重变奏,这更凸显了研究本案例深邃的历史意义和严肃的现实关怀。中共十八大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9](P39)。而要实现这一宏伟愿景,迫切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探索更加有效的体制机制,全力助“美丽中国梦”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