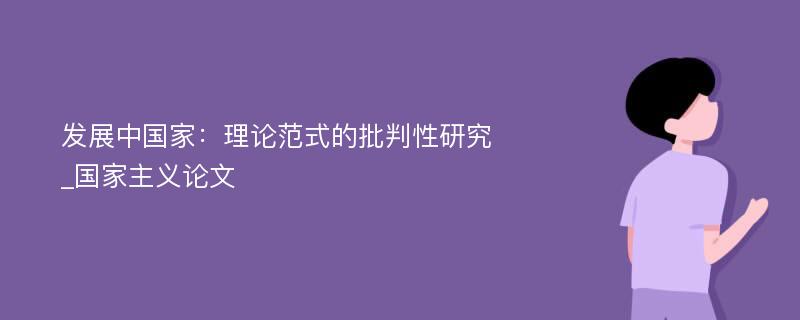
发展型国家:一种理论范式的批评性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出版《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在书中,约翰逊提出“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作为对东亚经济奇迹的一种解释。在约翰逊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对东北亚国家进行了研究,由此形成一种发展型国家理论范式。该理论范式批判了战后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抓住了东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些本质特征,具有较大的解释力。但该理论范式也存在诸多局限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发展型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该理论范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造成了发展理论的转折,超越发展型国家成为热门议题。本文结合发展型国家的发展历程,考察了发展型国家理论范式的主要内容,它所具有的解释力及其限度,并对超越发展型国家的几种路径进行了评论。我们相信,这样的工作,对于认真反思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具有深远影响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思想资源意义。
一、发展型国家理论范式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二战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独立民族国家,形成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走向,为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素材和展现自己理论成果的机会,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现代化理论,是人类以“现代性”为价值目标、以西方发达社会及其走过的路程为参照而对非西方欠发达社会的展望和规划。这幅在进步主义信念支撑之下描绘的现代社会“蓝图”,充满了乐观情调。而且,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联合国主持下,现代化理论在第三世界得以流行和实践。但现代化理论的乐观预言并没有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在这些国家,尽管国民生产总值有了一定幅度的增长,很多问题却更加恶化了: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债台高筑,经济进一步受制于西方,成为西方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经济的波动导致政治局势的混乱,等等。这些情况说明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对欠发达国家是不适用的,它导致欠发达国家对西方的进一步依附。在60年代,现代化理论受到来自学术界的连续的批评而没落,以悲观主义为色彩的依附理论取而代之,并成为解释第三世界(尤其是拉美国家)发展的主要理论。与现代化理论将一些国家的不发达归因于内部的文化和制度因素不同,依附理论将不发达归因于外部资本主义的剥削。因而,解救之道在于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必要的“决裂”或“脱钩”。依附理论观察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西方现代化的剥削特征,但它“将独立于美国(或)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之外的好处看得太多了”①。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暴露了依附理论的缺陷,世界体系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扬弃了依附论。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伴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自由主义实现了当代复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俨然成为了主流思想,该理论“把东亚有活力的发展归因于‘市场的魔力’——放任主义和一个开放的经济。如果存在某种国家干预的话,它是为市场服务的,它旨在使市场‘获得基本的权利’”②。
作为对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回应,一些发展理论家通过对东北亚国家的经验考察指出,新自由主义无法正确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东亚国家所采取的发展模式亦非新自由主义模式。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查默斯·约翰逊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约翰逊认为,日本信奉的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国家主义”或“新重商主义”的德国历史学派一脉相承③。约翰逊就是试图从这种“经济国家主义”视角阐明日本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独特制度结构。在对日本通产省历史和结构的考察中,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在约翰逊的基础上,许多发展理论家开展了对东北亚国家的研究,由此形成一种发展型国家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主要包括如下特点:
第一,强调从国情出发,超越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和自由主义自由经济意识形态。约翰逊指出,引入“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概念,主要目的是“超越美国和苏联经济的对立”④。在他看来,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是顺应形势的产物。
第二,发展主义把发展明确作为优先目标,实行策略性产业政策。“由发展、生产力和竞争力定义的经济发展,构成了国家优先考虑的目标。通过对任何平等和社会福利不做出承诺,避免了目标的冲突。”⑤这是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点。此外,高度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是发展型国家的重要特征。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提出了东亚工业化的管制市场理论⑥。爱丽斯·阿姆斯顿(Alice Hoffenberg Amsden)把韩国定义为引导型市场经济⑦。在这些学者看来,政府在驯服国内外市场力量并使之服从国家经济利益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理性地、有意识地培养出某些具有竞争力的行业,并通过这些行业带动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干预产业政策,其“主要方面是提供这样一种景象,以使经济免受因不确定性和碎片性而导致均衡的破坏,避免经济行为者共同利用经济外部性,为此目的,需要建立必要的制度,并且调解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冲突”⑧。迈克尔·罗瑞奥克斯(Michael Loriaux)从一种更抽象的道德角度理解发展型国家,把它看作是一种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国家利益的道德雄心⑨。
第三,紧密的公私合作。约翰逊指出,在日本,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建立和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企业家不承受单独追求企业短期经济效益的压力,因而有足够的余地考虑国家长远利益⑩。在对这种公私合作关系作出详尽考察后,他更是断言: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济成就都依赖于官僚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11)。康普斯(Campos)和洛特(Root)也认为亚洲奇迹的关键是铸造了一个“共享发展”的契约。这个契约把商业、劳动力、消费者和政府联合在一个合作计划中,从而确保了发展策略的成功(12)。韦德认为,正是一种阶级合作主义为东亚国家指导市场提供了基础(13)。
第四,相对自主、有效的官僚和官僚机构。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指出了通产省对于日本发展的作用。金弘基(Kim Hyung-Ki)等编辑的《日本文官制度和经济发展》一书则对日本官僚在政策上的角色转变,进行了比较综合的评价(14)。国家主义在发展型国家体现为:可以抵御近视的利益和各种社会集团的寻租行为,以及克服集体行动的问题,把自身与特殊利益相隔绝,使其可以发展和实施一种国家发展计划(15)。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精干的官僚队伍;二是官僚机构的相对自主性,统治权和治理权相分离(16);三是官僚理性,这是保持发展型国家能力的重要因素,它使得发展型国家可以避免掠夺性行为和资源浪费(17)。此外,这种官僚理性还受到来自经济优先目标的制约。
第五,革命国家主义是发展型国家获得和巩固合法性的基础。约翰逊在《农民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权力》一书中就已阐明现代东亚国家主义的本质,它包括战争在建立社会动员制度(中国共产党和日本通产省)的重要性,以及意识形态在革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18)。这种独特的国家主义赋予东亚发展型国家以合法性。他说,日本是“一个为战争而动员、但在和平时期从不复员的经济”(19)。而对韩国来说,正是日本殖民主义把日本发展模式移殖到了韩国(20)。同时,这种革命国家主义也巩固了发展型国家的合法性。一方面,它影响着发展型国家官僚的思维方式。这些官僚的战争逻辑决定了这些国家的“赶超”逻辑,从而把经济发展作为优先目标。另一方面,革命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东亚根深蒂固,以革命国家主义思维方式推行的发展型战略易于在人民群众中获得认同。而这种以经济为优先目标的发展战略在东亚所取得的成就,使经济国家主义成为革命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形态。正如约翰逊所指出,“发展型国家的权威资源并不是韦伯‘神圣三位一体’(传统权威、理性—法律权威和魅力权威)中的一个,而是一种革命权威:一个人对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转型的忠诚而产生的权威。合法性从国家的生成中出现,而不是来自它进入权力的方式”(21)。可见,发展型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这种具有革命色彩的经济国家主义之上,只有成功的经济绩效才能获得和巩固合法性。
二、发展型国家范式的解释力及其限度
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发展型国家”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发展型国家范式基于东亚国家的现实发展,批判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它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批判,暗示了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发展型国家理论对现代化理论作出了回应。现代化理论传统认为,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化与经济发展相对立,要在第三世界建立企业家文化、发展市场经济是困难的。发展型国家理论通过对东亚奇迹的研究表明,现代化并不一定只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具有新教伦理精神的国家)才能发生,它在资本主义不发达且缺乏新教伦理精神的国家里亦有可能出现。发展型国家理论对依附理论也作出了回应。依附理论只看到国内外权力资源的局限性,看不到边缘国家的创造性和对危机的适应性,把世界看作是一种可随时间进行自我复制的等级秩序。发展型国家理论研究则表明,依附性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国际结构,而是一系列不断变化的约束,在这种约束下个体民族国家有其驾驭的空间(22)。当然,发展型国家理论更对新自由主义反革命作出了回应:发展并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消极结果,官僚政治权力可以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积极有效的贡献(23)。自由市场并非某种普遍有效的科学原则,它实质上是一种“市场意识形态”(24)。
发展型国家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批判,暗示了多种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发展型国家理论家指出,并不是所有采取相似历史道路的国家都朝向相似的目的论目标(25)。在发展进程中,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是多元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道路在现实中呈现出多元性(26)。约翰逊在《日本:谁统治?发展型国家的兴起》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不是单一的(将来也不会是),它也不是由单一的、高度概括性的理论就能轻易解释的。……寻求描述历史和社会变量与政治经济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政治经济’,才是理解复杂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关键。”(27)可以看到,发展型国家理论的解释看起来比新自由主义的、以市场为中心的研究更接近现实(28)。
其次,以发展为优先目标和独特的产业政策,确实是东亚发展型国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也是其经济奇迹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很多理论试图作出解释,但是它们大多不能抓住东亚发展的关键要素。比如一些学者把东亚经济奇迹归结为东亚的文化特征。以韦伯主义为基础的讨论把社会组织的传统模式(特别是儒家文化)看作是解释发展的主要因素。但儒家文化思想并不能解释发展进程中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而且东亚儒家文化思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29)。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偶然因素促进了东亚经济发展,比如冷战促使美国对东亚进行援助,并与日本结盟,这为日本提供了三个方面的便利:低廉的防卫费用、现成的国外市场和价格相对低廉的技术转让(30)。约翰逊把这种解释称为“搭上便车”的分析类型,他批评道:“在这中间,政府做了什么,如何做法,就不单是‘搭上便车’的问题,而是公私部门之间极其复杂的交流和调整,也就是当今所谓的‘产业政策’问题。”(31)与其他因素相比,“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更符合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主要特征,更能解释东亚奇迹的产生。
再次,紧密的公私合作概念较好地表征了东亚社会的独特之处。战后,一种理想类型的西方公民社会概念被广泛运用来解释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社会特性。基于这种概念,日本等东亚社会被定性为缺乏公民社会精神的社会,它们不能培育现代社会的精神,不能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开来,这被看作是该地区军国主义(如日本)和权威主义的根源(32)。而这种缺乏公民社会精神的社会难以支持现代经济发展。毫无疑问,西方公民社会概念无法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相比之下,发展型国家理论的紧密公私合作概念,阐述了东亚社会独特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东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独特关系,它更加符合东亚的现实情况,因而更具说服力。不仅如此,发展型国家理论的紧密公私合作概念也适用于解释东亚公民社会兴起的独特方式。如果说公民社会在西方是基于经济自发秩序逻辑自下而上形成的话,那么在东亚,公民社会是在国家和社会力量相互纠缠、相互合作中形成和发展的。离开东亚紧密公私合作的社会特性,就无法理解东亚公民社会产生的独特方式。
最后,发展型国家理论对官僚制度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样的问题,即权威主义国家如何能够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兼容,以及权威主义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国家官僚如何不具有掠夺性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政策倡导是大规模的自由化——通常概括为“理顺价格”,而在政治上的政策倡导是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去政治化(33)。由此,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对市场进行强有力干预的权威主义国家不能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兼容,东亚经济奇迹必然是自由市场的结果。但东亚国家确实是对市场进行强有力干预的权威主义国家。所以,新自由主义观点并不能解释这个问题。而发展型国家理论对其官僚特性的描述,恰恰解释了这个问题。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官僚具有相对自主性,但他们与市场的关系却是独特的。韦德的“管制市场理论”和阿姆斯顿的“引导型市场理论”阐述了这种独特关系:国家官僚并不是对市场的替代,而是对市场不足的补充,并为市场运转建立必要的制度,协调市场行为者之间的冲突。而发展型国家为什么没有体现出“苏丹主义”式的掠夺性(34)?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回答是:发展型国家的官僚是韦伯式的,是与社会影响绝缘的,是价值中立的,是具有官僚理性的。而这种官僚理性来自统治权和治理权的分离,以及行为规范和职业规范的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展型国家为什么不是掠夺性的问题。
必须指出,发展型国家理论范式在具有较大解释力的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这些缺陷与不足,随着全球化的普遍深入,以及发展型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变化而日益显现出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一个转折点,发展型国家理论范式受到了广泛质疑。
首先,国家主义的局限。不断加速的经济全球化向这种国家主义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家正在不断空心化和去民族化;另一方面,脱域资本(disembedded capital)日益在全球流动,外部直接投资的兴趣不断增长(35)。面对快速转变的信息工业和“后福特主义”工业结构的非集中化,发展型国家的企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如塞宁·拉纳(Sean O.Riain)所指出,灵活的地区经济、分散的跨国技术和金融网络的出现,破坏了发展型国家的原有范式(36)。
发展型国家理论把国家描述为一个内部连贯、统一的行为者,它不能揭示国家结构内部运转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发展型国家理论把国家等同于官僚,也陷入了还原主义的窠臼(37)。这种国家主义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主权国家层面,二是主权国家之间关系层面。在主权国家层面,发展型国家理论是韦伯主义的,只强调合法性、理性和工具性,只强调经济官僚在发展中的作用,它把官僚看作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国家利益代表,把国家看作是纯粹理性的工具。这种韦伯主义立场使得发展型国家理论家无视政治冲突在国家发展中的影响(38)。国家官僚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类型”,而且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官僚既要考虑国内各阶级利益的需要,也要考虑跨国资本的利益,其自主性正受到严峻挑战。在全球化时代,仅仅依靠官僚也无法作出应对众多变动因素的“计划理性”选择。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发展型国家无法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结果。
在主权国家之间关系层面,发展型国家范式把主权国家看作是唯一的研究尺度,忽视了国际背景。它局限于本国视野进行的理论概括不能反映国家的真实情况,把尺度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政策也将失去其有效性。葛力·格里夫(Gary Gereffi)通过对东亚经济跨国“商品链”的研究指出,一个国家在不同链条中的位置不能完全由自由市场力量和蓄意的国家政策来解释。产业升级不仅源于市场和国家,它更是一种复杂混合背景的结果。国家不是一个孤岛,它存在于一个竞争的国际体系当中,国际体系对国家力量、自主性、嵌入性和凝聚力有着非凡的影响(39)。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影响力日益壮大,国家作为完全自主独立的权力维度已不再可能。
其次,经济主义的局限。现代化理论、新自由主义和依附理论都是要解决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因而把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40)。发展型国家理论是在扬弃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它扬弃的只是这些理论主张的发展手段,它并没有扬弃其经济发展目标,反而把经济发展目标更加凸显了。
发展型国家理论把发展作为优先目标,陷入经济还原主义的泥淖。约翰逊说:“度过萧条要求发展经济,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要求发展经济,战后重建更要求发展经济,而摆脱美国的援助也要求发展经济。”(41)所以,在发展型国家理论家看来,国家机器整体中的各个部分是同质的,都可以还原为经济发展。而事实上,国家是充满矛盾的。经济还原主义不能解释国家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它最多只是一种政治经济的弱理论和狭窄建构理论(42)。
以发展为优先目标的发展主义也受到新环境的挑战。一方面,排斥劳动力、以发展为优先目标的福利模式,受到新阶级结构的挑战。哈根·库(Hagen Koo)指出,在韩国,劳动力关系管理作为一种国家计划与发展本身具有同等重要地位(43)。但随着发展型国家的发展,这种旧的阶级结构逐渐被打破。精英阶层和大众集团之间,由最初相互对立、排斥、冲突逐渐走向相互沟通、协调、融合(44)。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和国内经济局势的变化,尤其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使得发展型国家的贫困化、贫富分化以及失业率增加等问题日益严重(45),重新审视发展主义取向,重新审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的强烈要求。韩国学者金渊明指出,近10年来韩国和台湾的再分配型福利制度表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发展主义的福利政策正在不断被超越(46)。
最后,权威合作主义的局限。发展型国家理论认为权威合作主义是东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种解释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东亚社会的特征,但这种权威合作主义本身不能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选择一种策略性工业政策,以及为什么这种政策在实践中是有效的。韦德指出,不能从潜在的合作主义政治安排中推论出国家力量的程度或具体政策的选择。而且,根据理论逻辑,合作主义安排有助于达到诸如宏观经济稳定、收入再分配以及福利国家的建立等目标(47)。但发展型国家权威合作主义与这些目标几乎是不相关的,甚至是相排斥的。
经济全球化使发展型国家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有力地挑战了它的权威合作主义倾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东亚,对政治和官僚的逐渐不信任,国家缺乏能力,以及私人部门对社会需要作出的反应,导致了第三部门的复兴(48)。全球化浪潮不断增强着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在这些来自底层的和外部的力量的作用下,东亚非政府组织数量迅速增长。同时,中产阶级也逐渐壮大,成为政治经济中的主要力量。在这一进程中,以强国家—弱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权威合作主义格局被打破。而私人经济领域的自主性得到增强,使发展型国家的权力和自主性同样受到削弱。“当市场更少地从国家那里获取资本,而更多地从国际流通和资本市场获取资本的时候,将会使得市场有更少的理由追随(尤其是服从)国家了。金融的全球化把控制杠杆转向市场,国家的权力减少了。”(49)更进一步说,发展型国家为了提升国内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而扶植了大量经济团体和财阀,而这些社团财阀的强大反过来削弱了发展型国家的自主性。智亚·奥尼斯(Ziya Onis)指出了这种辩证法:“在发展型国家内部,‘官僚自主性’和‘公私合作’条件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紧张关系。例如,韩国的例子证明了发展型国家播下了它自己毁灭的种子……在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化进程中,财阀的相对权力和自主性已然剧增,这反过来日益限制着国家控制这些集团行为并引导它们朝向策略目标的能力。”(50)为了能够成功协调这些利益,发展型国家需要更完善的机制,甚至需要重估其存在的理由和目的(51)。
三、超越发展型国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触发了批判和反思发展型国家的浪潮。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指责该地区的政治权贵和企业巨头”(52),它们认为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亚洲国家的金融部门没有实现足够的自由化,没有按西方的标准改造国内银行,使之成为有很高透明度并以市场为导向来配置资源的机构,没有建立适当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没有执行谨慎的政策来控制过度借贷”(53)。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亚洲价值观”有其固有的劣根性,正是因为东亚的这种“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54)。阿马蒂亚·森认为政治自由、透明性自由和防护性自由的缺失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55)。
作为一种回应,发展型国家理论者认为,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推行的自由化政策。韦德和弗兰克·维尼罗索(Frank Veneroso)认为,资本开放是危机的根源,全球金融流动破坏了东亚发展型国家中连接国家、金融机构、公司之间的健康合作关系。乔莫(Jomo K.S.)认为亚洲地区的宏观经济管理并未严重扭曲,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力量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裙带关系和寻租等因素在危机过程中的作用要比公众想象的更为复杂。曼纽尔·蒙特斯(Manual Montes)和沃尔顿·贝洛(Walden Bello)认为危机是国内金融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双重自由化”的结果(56)。
围绕亚洲金融危机究竟否证了发展型国家还是否证了新自由主义的争论还在进行。但发展型国家的诸多局限性在危机面前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它在全球资本流动中过于刚性,无法灵活应对新的变化,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同样地,在危机中受害严重的一些亚洲国家,往往是采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金融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建议的国家。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说,在没有良好监管和规则的前提下,追求快速的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57)。因此,亚洲金融危机,既有缺少良好监管和规则的过度自由化问题,也有刚性的汇率制度等自由不够的问题。危机的根源不是非此即彼的。
从超越发展型国家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的抽象对立出发,斯蒂格利茨等人倡导从“华盛顿共识”走向一种“后华盛顿共识”。首先,后华盛顿共识重新审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承认市场有其作用的同时,承认政府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不单纯是保障契约实施和保护产权这些最基本的职责。其次,扩大发展目标:提高生活标准,包括改善卫生和教育,而不仅是增加可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寻求可持续发展,包括保护自然资源和维护有益健康的环境;寻求公正的发展,这种发展能确保社会中的所有集团、而不仅仅是上层集团享受发展成果。再次,超越项目和政策,关注制度包括公共机构及其治理。最后,鉴于在华盛顿共识框架内不能制定出成功的发展战略,因而需要以重要的和实质性的方式吸纳发展中国家参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讨论。另外,认识到“一刀切”的政策注定要失败。问题依然是,政策被移植到其他国家时,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运转良好(58)。
就发展型国家而言,它将如何被超越?如前所述,在发展型国家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应该避免非此即彼的观点。事实上,我们从东亚国家的发展看到,有活力的市场竞争、积极的国家管理、积极的出口促进、蓄意的进口替代、吸收和管理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努力之间是共存的(59)。克拉克(Cal Clark)和斯蒂芬·陈(Steven Chan)通过对一系列亚太国家的比较研究后指出,新古典主义和发展型国家理论都不能完全说明这些不同国家的成就。积极的国家干预既与好的经济表现有关,也与坏的经济表现有关。同时,自由放任经济有时候也会做得相当好(例如香港),可见一种强国家干预也不是良好表现的必要条件(60)。
就此而言,超越发展型国家并不意味着将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而是指出了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关系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对这些问题的重新思考中,新自由主义、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一些并不直接回应亚洲金融危机的理论,如杰索普(Bob Jessop)的李斯特工作福利民族国家理论、发展型制度理论、菲利普·瑟那(Philip G.Cerny)的竞争性国家概念、治理与善治理论以及网络理论等,也都值得认真借鉴。
首先,超越国家主义:重构国家角色。
著名国家理论家杰索普提出以“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Listian workfare national state)概念取代发展型国家范式。在他看来,发展型国家范式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忽视了经济发展在更大范围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策略中的作用;它以国家机器固有的特性解释国家的能力,片面夸大了国家的自主性。而“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涵盖了经济、社会、尺度和治理四个方面。在经济政策层面上,它将一个相对封闭的民族经济通过出口引导的工业化来确保经济增长;在社会福利方面,它是一种工作福利制度,表现为限制工资成本、投资人力资本、提高作为确保劳动力再生产手段的个人储蓄等等;在决策尺度上,它是民族国家的,其经济和社会政策在民族经济、民族国家以及一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基础上进行;在治理主体上,它是国家主义的,一个强大的民族安全国家以及它在不同层次上的制度是确保经济增长、社会凝聚力的主要手段,也是指导和补充市场力量的主要手段(61)。这比发展型国家范式更加全面地涵盖了东亚国家的各个方面,超越了局限于经济主义或国家主义立场解释东亚国家的缺陷。
在杰索普看来,在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尺度的政策制定方法必然陷入困境,必须超越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尺度的政策制定方式。在全球化进程中,一个普遍趋势是国家的去民族国家化,体现于民族国家机器的“空心化”,国家能力在亚国家、国家、超国家等层面上被加以重组,国家权力向上、向下和向侧面转移。为了应对这种新的变化,必须让政策规制国际化,国家活动扩展至各种超经济领域和超国家领域,主要的政策参与者也扩展至国外代理人和机构,使之成为政策理念、政策设计和政策执行的一种重要源泉(62)。
菲利普·瑟那则认为,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来自不同国家和跨国行为者的多样性压力,使得一个国家难以成为发展型或策略性国家;不断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和政治进程消蚀了发展型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和政策能力。由此,必须以“竞争性国家”替代发展型国家,它以国内经济取得国际竞争力为目标而追求自由化。在某种程度上,发展型国家应该让位于一种新自由主义传统国家(63)。尽管瑟那的分析本质上是一种新自由主义观点,但是他正确地指出了发展型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必须进行一种角色转换。
其次,超越发展主义:重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
杰索普的“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概念,因为指出了不能仅仅从国家的经济方面来解释国家,因而也是对发展型国家发展主义的批判。穆成因(Chung-in Moon)和拉瑟米·普拉萨德(Rashemi Prasad)也指出,发展型国家范式对东亚政治经济景象的描绘是不完整的,它不仅需要聚焦成功的产业政策,也需要覆盖其他政策领域,比如福利、环境和分配政策,必须把国家、网络和政治放在更大的制度背景当中去分析(64)。佩普尔(T.J.Pempel)则进一步提出以“发展型制度”范式替代“发展型国家”范式,认为应从更广泛的制度层面上考察国家(65)。可以看到,仅仅从经济主义或国家主义方面理解国家的做法是片面的。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目标的发展主义,也产生了严重后果。
发展型国家的首要特征是它的发展主义,它的所有政策都围绕着经济发展而制定,包括社会福利政策。伊恩·霍利戴把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福利政策特点称之为“促进生产的福利资本主义”(66)。在这种福利资本主义中,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高于一切,社会政策必须服从于它。斯蒂芬·哈格特(Stephan Haggard)也指出亚洲发展型国家福利计划的特点是,在限制社会保险的同时,开发人力资本(67)。这种独特的社会政策曾经发挥过显著的历史作用,但这种排斥劳动力的工作福利模式或“促进生产的福利”模式日益显现出了它的局限性:“它无力承认并且充分认识社会的复杂性,也没有考虑到这种复杂性与其他关键性发展层面——诸如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层面——的相互作用。”(68)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及更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因此,“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69)对这些诘问的回答,推动着发展型国家对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重新审视。
再次,从统治到治理: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
发展型国家理论之所以具有国家主义、发展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倾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把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分离物化和中立化了(70)。因此,必须超越国家和市场的传统二分法,才能更好地解释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国家政策之间的相互渗透。在这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形成的网络理论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置于理解东亚经济运转和表现的中心地位(71)。彼得·伊文斯(P.B.Evans)通过引入“镶嵌的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概念,克服了国家与社会二分法的困境,说明了发展型国家行为为什么是“良性的”、“发展型的”,而不是“掠夺性的”(72)。丹尼尔·奥基莫托(Daniel Okimoto)等学者运用政策网络理论,认为在发展型国家中,不是官僚的计划理性,而是中介组织构成的多元关系网络塑造着产业政策(73)。李(Lee,Chung H)和那雅(Seiji Naya)提出了“准内组织”(quasi-internal organization)概念,认为东亚的国家和私人部门不仅通过组织间的网络发生联系,且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呈现出一种内组织结构。这从根本上抛弃了国家与社会的传统二分法(74)。
另一方面,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中,民间非营利、非政府组织都以惊人速度蓬勃发展,形成了一个遍及全球的第三领域。第三部门研究的权威学者赛拉蒙教授称之为一场全球性的“结社革命”,他指出,“如果说代议制政府是18世纪的伟大社会发明,而官僚政治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那么,可以说那个有组织的私人自愿性活动也即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代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75)。这些非政府组织不仅深刻改变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民主化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治理理论的形成,“治理”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分析概念。治理的内涵与实质主要是:第一,治理意味着政府组织已经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承担者从政府扩展到政府以外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第二,治理中的权力运行方向从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统治,转向上下互动、彼此合作、相互协商的多元关系;第三,形成了从事公共事务的多中心的社会网络组织治理体系;第四,政府治理策略和工具发生转变。“治理”的兴起反映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深刻的结构性变迁,涉及到政府权力、市场边界和社会自治的多重关系调整。
如果说发展型国家理论曾经解释了东亚公民社会兴起的独特方式,那么,“治理”的兴起吁求发展型国家必须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推动并激发社会,将自我组织和公民直接参与当作目标。而走向“治理”并不是削弱了国家能力,它恰恰扩大了国家能力(76)。奥尼斯指出,“国家通过社会中的商议和合作进程来渗透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和实施政策的能力”,是国家的一种“基础权力”(77)。因此,发展型国家的分权和民主化进程,并不意味着它变成一种没有能力的国家,而只意味着一种权力的转型,它原来的权威主义权力被削弱,但它的“基础权力”却得到了增强。这样,发展型国家并没有被捣毁,而是实现了从“追赶”到“持续升级”的一种调整(78)。
最后,建设服务型政府:重构合法性基础
如前所述,发展型国家合法性的建立和巩固,一方面来自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规范——革命国家主义,另一方面来自于经济政策所产生的经验有效性。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革命国家主义在发展型国家的合法性中是否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值得质疑的问题。而发展型国家固有政策的有效性也日益受到质疑,最主要的失败经验当然就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无疑,发展型国家必须重新寻求合法性来源。
面对全球化、阶级结构变化、公民社会兴起所带来的挑战,发展型国家可以通过实现上述三个转变来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首先,面对全球化给发展型国家带来的空心化和去民族化进程,发展型国家通过超越民族国家的尺度,把它的政策范式建立在更广泛尺度上,来重新寻求其政策的合理性。其次,面对阶级结构变化和贫富差距扩大,发展型国家通过重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把合法性基础建立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之上。法伊穆勒·夸迪亚(Fahimul Quadir)和迦彦特·黎力(Jayant Lele)指出:“如果目前趋势得到持续,如果志愿性社团相对于国家和市场能够持续保持其自主性的话,东亚有可能见证一种新社会政治秩序的发展,在那里,不再那样强调资本问题,而是更加强调消除贫困、歧视和剥削问题。”(79)这意味着发展型国家的发展目标从原来以经济为中心的增长模式转化为以人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模式。最后,通过权威主义管理模式的转变,走向一种多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把合法性建立在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
进一步说,如新公共服务理论倡导者罗伯特·B·丹哈特和珍妮特·V·丹哈特所指出,在治理体系中要将公民置于中心位置。在丹哈特夫妇看来,长期以来“政府独自掌舵”的局面必须被改变。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因而政府在为“国家”这条船掌舵的时候,必须听从人民的意见。“公务员的首要作用乃是帮助公民明确阐述并实现他们的公共利益,而不是试图去控制或驾驭社会。”(80)
由此,发展型国家为重构合法性基础而发生的转变,将使其国家职能发生深刻转变,即逐渐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这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型国家的角色必须从“统治”转变为“治理”,从“经济优先”转变为政府以提供公共物品为主要职能;不仅关注“市场”和“生产率”,而且必须关注公民利益和人的发展,不再把公共利益看作是发展的一种副产品,而是把它本身作为一种目标;它不再只是像企业家一样追求经济利益,而必须与各种非政府组织和部门形成伙伴关系,为公民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并最终形成一种善治局面。
综上所述,发展型国家理论范式既是对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的扬弃和超越,又是对东亚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政治经济发展经验的反映,从而具有较大的解释力。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包括东亚国家在内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型国家范式的固有局限性日益暴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既向发展型国家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为超越发展型国家范式提供了契机。关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讨论的热潮,引导人们通过重构国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来超越国家主义,推进政策规制的国际化;通过重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来超越发展主义,把改善人们的福利置于更优先地位;通过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超越传统的二分法,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通过上述三种转变,发展型国家可以获得和增强新的合法性来源,而这三种转变推动着发展型国家向“服务型政府”角色的转型。
注释: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
②Gary Gereffi and Stephanie Fonda.Regional Paths of Development,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2,(18).p.424.
③[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8页。
④Chalmers Johnson.The Developmental State:Odyssey of a Concept,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ited,The Developmental State: 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32.
⑤Ziya Onis,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Comparative Politics,1991,24(1),p.111.
⑥[美]罗伯特·韦德:《驾驭市场》,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8-24页。
⑦Ziya Onis,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Comparative Politics,1991,24(1),p.112.
⑧Sean O Riain.Putting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Their Time and Place,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2000,2(3):p.151.
⑨Michael Loriaux.The French Developmental State as Myth and Ambition,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ited.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p.235-275.
⑩[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戴汉笠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23-325页。
(11)[美]查默斯·约翰逊:《政治制度和经济运行:日本、南朝鲜和台湾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载弗里德里克.C.戴约等:《东亚模式的启示——亚洲四小龙政治经济发展研究》,王浦劬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39-174页。
(12)Sherry Gray.The Developmental State as (Non)Replicable Model,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1997,41(2).p.298.
(13)[美]罗伯特·韦德:《驾驭市场——经济理论和东亚工业化中政府的作用》,吕行建、沈泽芬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22-23页。
(14)David Donald.Review,The Economic Journal,1998,108(448),p.900.
(15)Steven Chan,Cal Clark and Danny Lam.Looking 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in Steve Chan,Cal Clark,Danny Lam.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Macmillan,1998.p.2.
(16)[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第326-332页。
(17)Vivek Chibber,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ume 107,Number 4(January 2002).pp 951-955.
(18)参见Chalmer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Chalmer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Revisited:The Biography of a Book,China Quarterly,1977,(72),pp.766-785.
(19)Chalmers Johnson.Japan,Who Governs The Ris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New York:WW Norton press.1995.p.10.
(20)Atul Kohli.Where Do High-Growth Political Economics Come From The Japanese Lineage of Korea's' Developmental State',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ited.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p.93-136.
(21)Chalmers Johnson.The Developmental State:Odyssey of a Concept.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ited.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53.
(22)T.J.Pempel.The Developmental Regime in a Changing World Economy,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ited.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143.
(23)Ibid,p.140-141.
(24)Jeffrey Henderson and Richard P.Applebaum.Situating the state in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Process,in Applebaum and Henderson(ed).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Newbury Park:Sage Publications.1992.p.19.
(25)T.J.Pempel.The Developmental Regime in a Changing World Economy,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ited.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p.141-142.
(26)Ziya Onis,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Comparative Politics,1991,24(1),p.125.
(27)David Donald.Review,The Economic Journal,1998,108(448),p.901.
(28)Bob Jessop.A Regulationist and State-theoretical Analysis,in Richard Boyd and Tak-Wing Ngo (ed.).Asian States: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5.p.23.
(29)Sherry Gray.The Developmental State as (Non)Replicable Model.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1997,41(2),p.297.
(30)[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5-17页。
(31)[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第18页。
(32)Muthiah Alagappa.Introduction.,in Muthiah Alagappa(ed.).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sia,Expanding and Contracting Democratic Space.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1.
(33)Ha-Joon Chang.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in.Meredith Woo-Cumings (ed.).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p.184-185.
(34)Adrian leftwich.Bringing Politics Back in:Towards a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5,31(3),p.407.
(35)Bob Jessop.A Regulationist and State-theoretical Analysis,in Richard Boyd and Tak-Wing Ngo (ed.).Asian States: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5.p.29-30.
(36)Sean O.Riain.The Flexible Developmental State:Globalizat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and the' Celtic Tiger',Politics & Society,2000,28 (2),P.157.
(37)Steven Chan,Cal Clark and Danny Lam.Looking 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in Steve Chan,Cal Clark,Danny Lam.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Macmillan Press,1998.p.11.
(38)Richard Boyd and Tak-Wing Ngo.Emancipat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sia from the Growth Paradigm,in Richard Boyd and Tak-Wing Ngo (ed.).Asian States: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5.pp.1-3.
(39)Gary Gereffi.More than the Market,More than the State: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East Asia,in Steve Chan,Cal Clark,and Danny Lam edited.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p.38-59.
(40)许宝强;《前言:发展、知识、权力》,载许宝强、汪晖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41)[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19页。
(42)Richard Boyd and Tak-Wing Ngo.Emancipat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sia from the Growth Paradigm,in Richard Boyd and Tak-Wing Ngo (ed.).Asian States: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5.p.9.
(43)Hagen Koo.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Korean state,in Richard Boyd and Tak-Wing Ngo (ed.).Asian States: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5.pp.129-144.
(44)李文:《东亚社会变革》,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14页。
(45)世界银行:《东亚的复苏与超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4-157。
(46)[韩]金渊明:《超越“生产主义福利体制”:韩国的经验》,载《当代社会政策研究(Ⅱ)/第二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文集》,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2007年,第76-98页。
(47)Ziya Onis.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Comparative Politics,October 1991.P.119-120.
(48)Muthiah Alagappa.Introduction,in Muthiah Alagappa (ed.).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sia,Expanding and Contracting Democratic Space.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2.
(49)Eul-Soo Pang.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997-98 and the End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al State,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2000,22(3):pp.583.
(50)Ziya Onis,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Comparative Politics,1991,24(1):pp.121.
(51)Bun Mee Kim.Contradictions and Limits of a Developmental State:With Illustrations from the South Korean Case,Social Problems,1993,40(2):pp.242-243.
(52)[美]彼得W.普雷斯顿:《解读亚洲金融危机:历史、文化和机构实况(上)》,《南洋资料译丛》2000年第3期。
(53)[美]保罗·赫斯特、格雷汉姆·汤普森:《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几种解释和亚洲模式的未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5期。
(54)[美]保罗·克鲁格曼:《拯救亚洲:应当改弦易辙了》,《国际金融研究》1998年第9期。
(55)[英]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9-181页。
(56)沈红芳:《危机的理论与理论的危机》,《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5期。
(57)Jason Furman,Joseph E.Stiglitz,Barry P.Bosworth,et al.Economic Crises:Evidence and Insights from East Asia.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8,1(2),pp.1-135.
(58)[美]斯蒂格利茨:《后华盛顿共识》,《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9年第1-2期;《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载黄平、崔之元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86-102页。
(59)Steven Chan,Cal Clark and Danny Lam.Looking 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in Steve Chan,Cal Clark,and Danny Lam edited: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Macmillan,1998.p.3.
(60)Cal Clark and Steven Chan.Market,State,and Society in Asian Development,in Steve Chan,Cal Clark,Danny Lam edited: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Macmillan,1998.pp.25-37.
(61)Bob Jessop.A Regulationist and State-theoretical Analysis,in Richard Boyd and Tak-Wing Ngo (ed.).Asian States: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5.pp.19-29.
(62)Bob Jessop.The state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knowledge-driven economy,in John R.Bryson,Peter W.Daniels,Nick Henry et al Edited.Knowledge,Space,Econom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p.75-76.
(63)See Philip G.Cerny.Structuring the Political Arena:Public goods,states and governance in a globalising world,in R.Palan (ed).Global Political Economy:Contemporary Theories.London:Routledge,2000.pp.21-35; Philip G.Cerny.Paradoxes of the Competition State: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Globalisation,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1997,32 (2),pp.251-274.
(64)Chung-in Moon and Rashemi Prasad.Networks,Politics,and Institutions,in Steve Chan,Cal Clark,Danny Lam edited: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Macmillan,1998.pp.9-24.
(65)T.J.Pempel.The Developmental Regime in a Changing World Economy,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ited: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p.137-181.
(66)[美]伊恩·霍利戴:《东亚社会政策的特点;促进生产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2期。
(67)Stephan Haggar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welfare state,in Richard Boyd and Tak-Wing Ngo Edited:Asian States: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5.pp.145-171.
(68)[美]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发展型社会政策》,罗敏、范酉庆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页。
(69)许宝强:《前言:发展、知识、权力》,载许宝强、汪晖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70)Bob Jessop.A Regulationist and State-theoretical Analysis,in Richard Boyd and Tak-Wing Ngo (ed.),Asian States: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5.pp 23-25.
(71)Chung-in Moon and Rashemi Prasad.Networks,Politics,and Institutions,in Steve Chan,Cal Clark,Danny Lam edited: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Macmillan,1998.pp.15-17.
(72)See P.B.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73)See Daniel Okimoto.Between MITI and the Market: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Yeom,Jaeho.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in a Network Setting:MITI and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74)See Chung H.Lee.The government,Financial System and Large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 Korea,World Development,1992,(20):187-197; Lee,Chung H and Seiji Naya.Trade i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With Comparative Reference to Southeast Asian Experience,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88,(38):123-152.
(75)[美]莱斯特·萨拉蒙、赫尔穆特·安海尔:《公民社会部门》,载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7页。
(76)Bob Jessop.The state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knowledge-driven economy,in John R.Bryson,Peter W.Daniels,Nick Henry et al Edited.Knowledge,Space,Econom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75.
(77)Ziya Onis,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Comparative Politics,1991,24(1),p.123.
(78)Linda Weiss.Developmental States in Transition:Adapting,Dismantling,Innovating,not 'Normalizing'.The Pacific Review,2000,13(1),pp.21-55.
(79)Fahimul Quadir,Jayant Lele.Introduction:Globalization,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the 1990s,in Fahimul Quadir,Jayant Lele (ed).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in Asia:Volumel.Palgrave Macmillans.200.p.10.
(80)[美]罗伯特·B·丹哈特、珍妮特·V·丹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10期。
标签:国家主义论文; 依附理论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官僚资本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