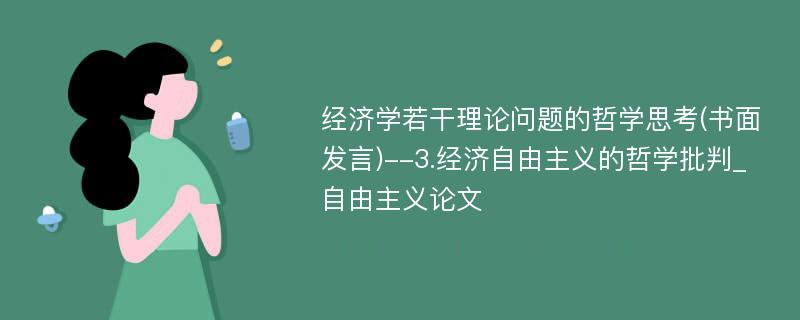
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的哲学反思(笔谈)——3.经济自由主义的哲学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笔谈论文,自由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发端于亚当·斯密。但如果认为源于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只是“自由放任”之意,则有不得要领之嫌。按传统的说法,斯密的市场经济原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石,而他对自私的批评,对公正和道德的强调,乃至对政府职能的肯定,则历来被归属于非主流经济学的思想。斯密实乃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共同的鼻祖。从这个角度看,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分野,不过是对斯密思想解释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斯密追求的是一种“利益的自然和谐”。在这个目标之下,似乎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别并不重要,“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也只是无关宏旨的技术性的细枝末节而已。
传统社会秩序的缓慢解体始于13世纪,17世纪加速了这一进程。摒弃了建立在神性之上的社会秩序,似乎传统社会作为整体的形象也逐渐变得支离破碎了。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现代性的“大问题”就是如何思考一个世俗社会,即思考这种社会是不依赖任何外部的命令而建立和运行的。肇始于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便是回应这个“大问题”的一种学说。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怎么能够通过供求关系而统治全世界呢?用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种关系就像古典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遨游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把幸福和灾难分配给人们,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1]87。
当经济自由主义的伟大旗手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其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时,处于“伟大转折”之中的英国社会的一个最为普遍的观念,是每个个人的每一笔收入都将导致另一个个体相应的损失,国家之间的关系亦如此,均符合“零和游戏”原则(即人们只能赢得别人输掉的)。但斯密用市场观念取代了契约观念,不再从政治上而是从经济上理解社会。他以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明确指出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自发协调的秩序,能够将个人天然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追逐私利的欲望引导成为增进社会利益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自由。在他的经济自由主义视阈内,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同于军事关系,可以成为一种多赢的博弈。不仅如此,经济自由主义的交换理论还可以一举两得地解决社会体制与社会调节问题,即通过需求与利益自身的作用,影响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自由主义是对以“社会契约”为核心的近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它从更深层次上反映了市民社会的要求,而这个市民社会本身也要求实行自我调节。
个人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渊源。虽然不能说个人主义在经济上的直接表现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但经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却是不可否认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是:以每个人的私利为基础的资本市场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资本永远是一种不受限制的和不可控制的社会新陈代谢方式,这种方式必然要阻挡其自我扩张的一切东西,即一切有碍于资本拓殖的外部障碍都将为“看不见的手”所克服或消解,社会必然会走向利益自然和谐。曾经令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最头痛的问题之一,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直接意志”,它直接涉及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他们的解释中,合理性之所以导向神秘性,原因在于他们的解释完全基于一种纯粹的资本立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康德的“大自然的隐蔽计划”以及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都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勇敢尝试,他们都采用了某种超越个人的主体性形式,因而仍然处于一种个人主义的解释框架之中。斯密视“看不见的手”为个体资本家的引导力量,也就等于说,他所理想化的作为社会协调机制的资本再生产体系,实际上是不可控制的。他还假定这种神秘的“看不见的手”,无论对特殊的资本家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慷慨仁慈的,并将经由私有财产的运动而达至人类的整体福利。
熊彼特在《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书中列举的10个人中,除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独树一帜之外,其他虽有英美学派(马歇尔、陶西格、费雪、米契尔、凯恩斯)、奥地利学派(门格尔、庞巴维克)、洛桑学派(瓦尔拉、帕雷托)之分,但从他们的基本理念来看,都是建立在以主观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石而应用边际分析方法的经济学理论。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主流经济学理论始终未偏离个人主义的解释框架。马克思则深入批判了这种个人主义的解释框架所赖以成立的利益观念,这主要集中在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以商品为出发点的资本批判中。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经济自由主义所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实质上是资本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宏观目标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试图调剂一种类似完美的化学配方以确保资本免于其痼疾之忧。斯密及其追寻者始终局限于试图按照控制个人的意图和动机来理解资本的运行,因为在资本原则主导下的生产和控制的彻底分离,除了通过这种虚假主体的中介来维护资本制度的客观规则并将其作为“自然的”和“完美的”东西认同之外,别无他途。这无异于在找不到答案的地方寻找答案。
有学者指出,欧洲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就是把个人自由实现在作为抽象的交换价值之动产的自由中[2]113。随之而来的一个错觉是,人们也容易将资本原则下的经济自由混同于人的自由,就像一些人在房地产开发商的广告宣传中也幻想着能“诗意地安居”一样。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是私有财产的运动,所谓经济自由不过是私有财产运动的自由,亦即资本的自由。经济自由主义信誓旦旦地宣称并且为之保证的人的自由,事实上不可能超出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范围,它是以工人不自由的雇佣劳动为前提和内容的,而非真正的人之为人的自由。在资本原则下,工人只有服从资本和市场强制的自由,即出卖劳动力的自由,甚至资本家也只有作为资本之人格化并符合资本的拓殖本性时才是“自由”的。换言之,工人和资本家只有作为资本要素的自由,而无力寻求真正的人的自由。当然,历史地看,相对于“人的依赖性”社会,资本原则下的自由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它毕竟未能摆脱“物的依赖性”,工人也毕竟没有摆脱资本、劳动、市场和国家的强制。马克思说:“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3]167。
在理论上,经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利益自然和谐得以建立的体制基础,是崇尚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这正是资本制度的神秘化之所在。恰是在这种神秘化中,资本的捍卫者确立了资本的神圣化地位。经济自由主义者强调维护作为人类最高价值准则的自由,实际上它和专制主义一样包含着极权主义的特征,不同之处仅在于,经济自由主义所代表的是市场极权主义,要求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市场的支配。
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最大的欺骗性,就是通过政治的、文化的手段,把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历史生存状态曲解为一种自然生存状态,并悄无声息地抹去了批判反思这种历史生存状况的可能性。显然,经济自由主义所承诺的利益自然和谐,终究只能是一种乌托邦。正如法国著名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经济自由主义“有一份真理,有一份坏心,有一份幻想”[4]29。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经济自由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亚当·斯密论文; 政治论文; 看不见的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