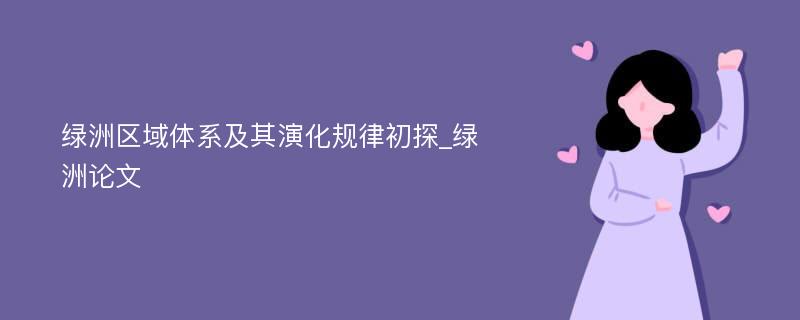
绿洲地域系统及其演变规律的初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绿洲论文,地域论文,规律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绿洲是干旱区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也是干旱区最主要的人文—自然景观。在现代气候环境下,世界干旱区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0%;我国干旱区面积约为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4/1。近年来,绿洲科学的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科学家的关注,但目前对绿洲系统的理论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人们对绿洲的认识也很不统一。然而,作为一种独特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绿洲系统仍然在其结构、运行机制和空间演化上有其一般规律,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
1 绿洲及其特点
1.1 绿洲
绿洲(oasis)一词见诸文献已有悠久历史,然而绿洲一词最早由文学家、历史学家使用,加上这个词本身所具有的浪漫文学色彩,在早期,绿洲一词被更多地用在文学作品中,并在人们心目中各行其是地给予了各种各样的定义。这对于绿洲一词的科学定义十分不利,是导致绿洲定义长期模糊不清,定义太多的重要原因。即使是人们开始以科学的眼光看待绿洲,试图赋之以科学的定义的时候,也还是从绿洲表象的认识开始的,初期人们较多注意的是绿洲的分布、地表的绿色植被及灌溉农业等[1~6]。然而随着对绿洲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表象的描述似乎难以说明绿洲作为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长期与荒漠共存的本质特征,因此从系统论、哲学思想的观点认识和定义绿洲成为一种新的潮流。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参与这一讨论的主要是地理学家和区域经济学家,他们对经洲的定义已不简单是对表象的描述,他们更注重的是绿洲概念的内涵[7~14]。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对绿洲的概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认为:“绿洲是干旱环境下一定时段内,生物过程频繁、生产量高于周围环境的镶嵌系统”[15];“绿洲是在干旱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在荒漠背景基质上以天然径流为依托的,具有较高第一性生产力的,以中生或旱生植物为主要植被类型的中、小尺度景观[16]”。在这些定义中,特别注意到了绿洲第一性生产力明显高于周围荒漠的特点,实际上这正是绿洲有别于荒漠的本质特点。考虑到绿洲产生和存在的环境特点,我们给出的绿洲定义为:绿洲是存在于干旱区、以植被为主体的、具有明显高于其环境的第一性生产力的、依赖外源性水源存在的生态系统。本文在这里对以下三点予以强调:
(1)绿洲是存在于干旱区的特殊生态系统。据《中国自然地理(总论)》,干燥度k≥3.5的地区即为干旱区。干旱区以外位于其它类型地理区中与周围环境形成对比的密集植被生长区不能被定义为绿洲。(2)绿洲的主体景观是繁茂的植被,它们形成了与周围环境成鲜明对比的隐域性植被群落,因而,绿洲具有明显高于其环境的第一性生产力。(3)水是绿洲形成和维持的根本要素,绿洲的植被依赖于来自山区的地表和地下水生长,以此界定干旱区绿洲与非绿洲的界限。
现代绿洲是干旱区人类生存最重要的基地,密集的人类活动是现代绿洲的特征。因此从地理学的观点出发,绿洲是干旱区特殊的地理景观,同时也是干旱区最重要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我国干旱区平原地区一般年降水量均小于200mm,而潜在蒸发量则高达2000~4500mm,因此,平原区的降水既不具备重要的生态意义,也形不成有意义的径流,绿洲地区所用水量几乎全部来自山区。每片绿洲均有属于自己的山区集水盆地。山区集水盆地的大小及集水量决定了山前绿洲规模的大小,山区水源的构成(降水、冰雪融水比例)决定了山前绿洲水源供应的质量(季节供水保证率)。因此,在研究绿洲时必须同时注意到其山区集水盆地的特性,以利于对山前绿洲的发展趋势与潜力做出正确的评价。
1.2 绿洲的特征
绿洲作为干旱区最重要的生态系统和人类活动的基地,在自然和人为双重影响下,体现出一些有别于其它系统的特征。(1)绿洲相对孤立,自然与人文环境封闭,不利于对外交流与联系。绿洲散布于广大荒漠地区,空间上相互分割,极易形成低水平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体系,这种惰性无论对生产的发展还是思想的开放都十分不利。据统计,作为交通中心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到其它15个城市(1995年)的平均距离为666km,16个城市间平均距离为1100km,最偏远的和田市到其它15个城市间的平均距离为1942km[17]。绿洲的分散与孤立造成了生产力布局的分散,使有限的生产力难以发挥集聚效益。(2)绿洲依赖地表径流存在,依靠开发水资源而扩大,且有圈层结构特征。绿洲可分成内核和外圈两部分,内核是受地表径流天然滋养的部分,一般位于现代绿洲中上部,那里土地肥沃,地表水源充足,地下水位适中,生物活动频繁,是原有“天然绿洲”之所在,绿洲的外圈是人类为扩大其生存空间,利用水利工程对“天然绿洲”外延的结果,即所谓“人工绿洲”。在地表径流保持稳定的情况下,绿洲内核的生态必定处于稳定的状态,人类在其上的农耕或其它活动,只能改变绿洲内核的地表景观,无法改变其本质属性。然而绿洲外缘的所谓“人工绿洲”全部依赖人类修筑的水利工程供水而存在,它们是人类对绿洲外围环境改造的结果,“人工绿洲”始终存在返回其原始生态的倾向。(3)各绿洲具有相似的自然条件和资源,导致了绿洲经济结构的一定水平的趋同性。由于绿洲均位于山前地带,依赖山区径流而存在,在一定地理区域内,各绿洲自然条件相似,除矿藏资源分布的差异外,农业自然资源十分相似,从而导致各绿洲产业结构趋同,低水平重复,产品档次低,经济效益差;这种经济结构的趋同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区间贸易水平,不利于经济发展。但反过来讲,资源和产业结构的类同又容易形成规模化经营,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因此,绿洲资源开发中要兴利除弊,强化产业指导。(4)现代绿洲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人类活动决定着绿洲的演化方向。现代绿洲是一种高熵系统,呈现着很强的动态特征,使其呈现出向荒漠化和向系统优化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变化的不稳定性。在较短的地质历史时期,自然变化不很强烈的情况下,人类活动对绿洲的演化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是造成绿洲地区普遍存在的沙漠化、盐渍化、草场退化等环境问题的主因,但也是人类通过充分利用绿洲自然资源,大幅度地提高了绿洲的产出水平。
2 绿洲地域系统的结构
自人类活动叠加于绿洲之上时,绿洲就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生态系统,而成为自然和人文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随着绿洲人口的聚集,人类活动施加于绿洲的影响不断增强。现代绿洲中最活跃、最重要的作用因素是人类活动。现代绿洲系统大致包括以下四个亚系统,即:自然资源亚系统,人力资源亚系统,经济-社会亚系统和环境容量亚系统。
2.1 自然资源亚系统
自然资源是绿洲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包括气候、地质、地貌、水文、土壤、生物(微生物)等绿洲自然要素。概括地讲,干旱地区光照充足,热量丰富;降水少而蒸发强烈,干燥度≥2.0;地质构造较为活跃,矿藏丰富;区内常见的地貌组合为高山盆地相间;地表河流流程较短,多为季节性河流,河流径流年内变率较大;山前地带常有富含地下水的构造;生物生长稀疏,活动较弱,土壤发育不良,土层薄,肥力差。然而在绿洲地区水源相对充足,生物活动明显增强,土壤发育较好,土地肥沃,与其它区域性资源组合,使得绿洲区具备了优良的光、热、水、土资源,为绿洲农业开发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基础。
2.2 人力资源亚系统
人类活动是现代绿洲演化的主导因素。人力资源包括人口、科技和教育、民族与宗教信仰等体现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的要素。由于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不同,人力资源亚系统并无统一特征。以我国的新疆为例,干旱区总体表现为:人口总数较少,人口密度远低于全国平均值,而绿洲地区人口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数。以1992年资料为例,新疆总人口为1067.98×10[8],仅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9.3‰;全新疆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10人,远低于全国119人/km[2]的水平,但绿洲地区人口密度却已达200人/km[2],相当于江苏、浙江等高密度人口地区的水平。由于地处偏远,信息闭塞,科技与教育水平长期落后于内地省市,加之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及历史负担的影响下,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绿洲散布的干旱地区,往往也是少数民族集聚区,民族构成复杂,生活习惯不同,语言文化各异,加上宗教信仰上的差别,使得人口的素质教育及科学技术知识的推广比较困难。
2.3 社会-经济子系统
包括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的生产活动及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绿洲地区农业自然资源丰富,且便于利用,因此绿洲发达的农业是其基本产业;尽管近代绿洲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由于区位及集聚效应较差等方面的原因,绿洲地区轻工业、加工工业等产业仍处于落后的状态,现代干旱区工业是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的原料输出型工业,是低效益的工业。只是在国家投资建立矿藏资源后续加工工业的条件下,绿洲工业才得以不断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这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绿洲地区的社会—经济系统总体上说来是一种主要靠外来投资(计划经济下主要是中央政府)扶持的脆弱系统。
2.4 环境容量子系统
绿洲处在干旱区大背景下,自然环境十分严酷,现代绿洲早已扩大到绿洲内核区以外,使绿洲外缘处于沙漠化、盐渍化、土地退化的威胁下,绿洲外缘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已成为维护绿洲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内容。绿洲生态环境“内部优化,边缘恶化”似乎已成为人们对绿洲环境问题的一般认识[15];绿洲系统是一种有限系统,资源承载能力及环境容量有限。目前人类对绿洲的开发实际上是运用人力对绿洲地区最稀缺的环境要素—水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的结果,绿洲农业消耗水量的增加实际上是以剥夺维护绿洲周边生态用水取得的。在水资源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绿洲的开发与周边环境的维护,通过水资源这一要素直接发生了联系。因此,绿洲环境容量具有了与其它类型生态系统环境容量所不同的含义,它不仅表示环境对污染物的容纳能力,同时也表示对人类生产开发活动强度的容纳能力。
3 绿洲地域系统的运行机制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运行机制是指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以及系统内在的运行方式。绿洲系统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经济-社会和环境容量四个子系统,代表了绿洲系统中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两大亚系统的主要特征。根据其本质属性,二者合一便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在区域可持续发展受到空前重视的今天,绿洲地区的生态经济被作为一种能够协调自然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概念也受到广泛的注意。所谓绿洲生态经济,是在充分认识和考虑到绿洲地区特殊生态与环境特点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来促进绿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因此,绿洲地域系统应该是自然与人文两大亚系统相互共存、相互融合的动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自然因素在干旱环境大背景的驱动下,始终存在返回其自然循环状态的趋势;而人文因素则在人类不断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的目标吸引下,不断改造绿洲,使之朝更符合人类需求的方向发展。
实现绿洲生态与经济协调、融合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是水。水资源是绿洲生命之源,它既是建造绿洲的主要动力,也是维护绿洲的最重要因子。水在绿洲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在于:(1)水是绿洲内物质、能量和信息最主要的携带者,水带来了建造绿洲的土壤,同时也是绿洲植物及经济作物养分的携带者;绿洲地区的水能是绿洲能源的重要成分;绿洲地区许多环境变化和其它信息是由水量、水质的变化反映出来的。(2)水是绿洲生态(自然)和经济社会(人文)系统共同依赖的要素,水资源在绿洲间和绿洲内的时空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绿洲地区基础产业的结构与布局,影响着绿洲区域中心的空间结构、职能和规模;水资源的数量还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绿洲经济发展的总量。
影响绿洲地域系统演变的自然因素往往作用范围广,时间尺度上以地质时间为参照,对绿洲的演化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文因素的作用范围虽较为局限,时间上也只是发生在人类历史时期,但其作用明显而强烈,可以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改变绿洲的演化方向。
人类活动对绿洲地域系统运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农业生产来实现的。绿洲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与经济系统的交织偶合环节就是绿洲农业。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人类借助生物的自然再生产,实现经济的再生产,从而达到人类的经济目的[19]。在现代经济与技术发展的条件下,人类对绿洲的主观改造不断取得成功,以至忘记了干旱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对绿洲的种种限制,从而在绿洲内部及其边缘地区产生了沙漠化、盐渍化、草场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使我国干旱区存在着绿洲和荒漠同步扩大的趋势。可以认为人类目前还没有找到维持干旱区绿洲地域系统良性运行的科学机制。因此,正确认识和遵从绿洲地域系统的发展和演化规律就显得十分重要。
4 绿洲地域系统的空间演化规律
在天然绿洲状态下,绿洲的演化以自然过程为主,绿洲随河流摆动而变化,早期少量的人类活动没有对天然绿洲形成太大的干扰。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样,绿洲地区人类最早从事的是狩猎及采集生产,这就要求早期人类选择自然条件优越、水草丰美、野生动物较多的绿洲地区,因此新疆最早的石器时代的遗址多发现于低山地区有河流的山间盆地中。例如新疆现已发现的17个石器时代遗址,除8个在吐鲁番盆地外,其余9个全部位于低山区河流谷地与盆地中[20]。汉代以后,随着人类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及人口增加,狭小的河谷和山间盆地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人类活动下移到山前平原地区,出现了以农业为主的农耕时期。这一时期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在水资源利用上,尚无力控制大河水,而以利用流量较小、且相对稳定的泉水为主,或利用大河在下游没入沙漠前在河流三角洲上流动分散、缓慢的水流,因此这一时期的人类生活遗址主要分布在各大冲洪积扇泉水溢出带及一些河流的下游地带,它们比现代人类生活区更深入进盆地(塔里木和准噶尔盆地)内,后来多为沙漠掩埋。唐代以后,人口增加迅速,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人类活动区域沿河流向具有更广阔绿洲土地和更稳定水源的上游地带转移;到了近代,人口激增,生产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急剧扩大,人类活动范围呈现出向四周放射扩大的趋势,最终形成现代绿洲分布态势。为一进步证明这一规律,选天山北麓吉木萨尔地区和昆仑山北麓克里雅河流的实例进行说明。
吉木萨尔地区是秦汉时代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人类活动集中于大龙口与小西沟一带。小西沟遗址分布在现今天山北麓的森林线附近的山地丘陵地带,是吉木萨尔地区人类生活范围最靠山区的遗址,当时的人类生产方式为狩猎、采集与部分农业并存。唐朝时期,人类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今山前平原地带和今沙漠前沿一带,唐北庭故城遗址位于吉木萨尔县以北12km的后堡子乡破城子,南距南山35km左右,北距沙漠20余km,唐代有名的草原丝绸之路(唐朝路)就是在今沙漠前沿经过,沿路有许多护路遗址散布于古道旁。宋元时代,人类的活动区域与唐时基本相同,仍集中在后堡子的破城子附近。到清朝时代,人类的活动区域普遍向河流上游方向迁移了10km以上。清代本地区的行政中心孚远城、保惠城、垲安城均建筑在今吉木萨尔县城(北距北庭古城12km)周围,其它清代建筑,如育昌堡、时和堡、惠来堡等也分布在这一线上。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剧增,清朝后期人类的活动范围已不局限于孚远城一线,而是广泛分布于全县可供利用的土地之上。民国以来,人类的生活的足迹遍布全县各地,人口的更加庞大,在水资源允许的范围内,能够开垦和利用的土地均已被人类占用。
昆仑山北麓克里雅河流域是著名的古代人类活动区,也是典型的自原始的细石器时代开始,到近代的人类文化遗址都俱全的古人类文明区。距今约1万年前的细石器时代,人类主要生活在克里雅河上游山区地带,人类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狩猎和采集。秦汉时代,在克里雅河下游形成了比著名的于阗国和更为强大的扜弥国,使和田—克里雅河下游形成了以扜弥国为中心的于阗王国。唐代,在克里雅河流域形成了以喀拉墩为中心的城池区,这里的遗址基本上位于现克里雅河末端已废弃的古河道中,主要城池有喀拉墩、玛坚勒克等,遗址已南移了50km以上,说明人类活动已经沿河上溯;清代时期,人类的居住区中心上溯至克里雅河中游的现在县城一带,较唐时的喀拉墩遗址沿河又上溯了200余km。显然克里雅河流域的人类活动中心同样经历了从低山山到平原下部,而后上移至山前的过程。
不难看出,吉木萨尔地区和克里雅河流域绿洲人类活动的中心区随时代的变迁,先后经历了从低山地带到盆地内部,然后由盆地内部到山前平原的移动,最终由中心向外辐射,形成了现代绿洲格局的过程。吉木萨尔地区和克里雅河流域绿洲地域系统空间演化的这种相似性,反映了干旱区绿洲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空间演化的一般规律,这对于正确认识干旱区人地关系系统的形成与演化,解释干旱区环境变化的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