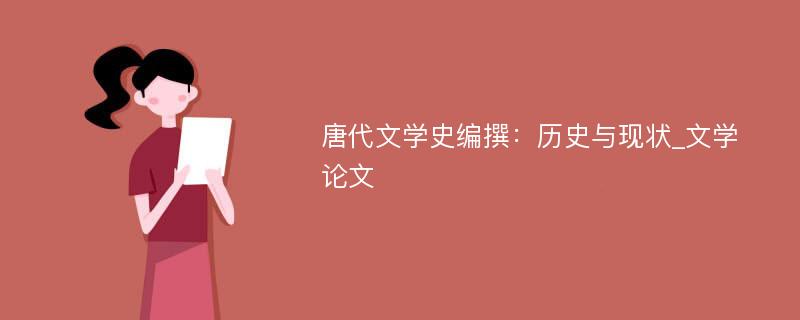
唐代文学史的编撰:历史与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唐代论文,现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3-0089-08
一
“唐代文学史”是断代文学史的一种,所以回溯唐代文学史编撰工作的历史、论析其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还需从为断代文学史正名说起。
这里所说的断代文学史,是指与通史性质一致的综合性文学史,即它们所述所论不限于某一种文体而涉及各种文学体裁、各类作家,它们与通史的区别,最显眼而又根本的,是在于叙述的时间范围上一个“通”一个“断”而已。像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的《汉文学史纲》,就是两部产生年代较早的著名断代文学史。(注:刘书是其在北京大学的讲义,1920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鲁书是其1926年在厦门大学任《中国文学史》课的油印讲义,未编完,至西汉司马相如而止。先生逝世后才出版。)断代文学史毕竟是从文学通史的整体上割截下来的,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反过来,将断代文学史相连缀,也就可以成为一部文学通史。鲁迅在厦门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课程没有完成,已写出的部分讲义就成了断代文学史;新时期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撰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原曾取名为《中国大文学史》),实际上也就是十部断代文学史的汇集。
我们现在所见的断代文学史多是以朝代,如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来划分的。(注:先秦不是一个朝代,大抵从中国文学之起源叙起而止于秦统一者,均可称为先秦。)文学的发展演变,犹如一条滔滔长河,照理是不应切割的,而且文学的演化并不与朝代的变迁同步,那么,通常所见的按王朝更替把它分为几段,成为断代文学史,这是合理的吗?可取的吗?这就关乎断代文学史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问题了。
对这个问题,钱钟书先生曾有所论述,他的观点见于《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原载《国风》半月刊第三卷第八期,1933年10月16日。本文所引,见《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该文针对当时有人“力非文学史之区划时期”,说道:“夫文学史之时期,自不能界域分明,有同匡格;然而作者之宗风习尚,相革相承,潜移默变,固可标举其大者著者而区别之。”这是一种很通达的观点,要旨在于:文学史之分期当然不是绝对的死板的,但就“作者之宗风习尚”的沿革演变来看,分期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分期虽不必“界域分明,有同匡格”,但从文学风尚的递嬗试为分期,还是可行的,分期自需建筑在研究的基础上,其本身也就是一种研究的成果。那么,对于大体依王朝更迭为文学史的做法又该如何看呢?钱先生继续写道:
且断代为文学史,亦自有说。吾国易代之际,均事兵战,丧乱弘多,朝野颠覆,茫茫浩劫,玉石昆冈,惘惘生存,丘山华屋。当此之时,人奋于武,未暇修文,词章亦以少少衰息矣。天下既定于一,民得休息,久乱得治,久分得合,相与燕忻其私,而在上者又往往欲润色鸿业,增饰承平,此时之民族心理,别成一段落,所谓兴朝气象,与叔季性情,迥乎不同,而遗老逸民,富于故国之思者,身世飘零之感,宇宙摇落之悲,百端交集,发为诗文,哀愤之思,惨苦风霜,憔悴之音,托于环玦;苞稂黍离之什,旨乱而词隐,别拓一新境地。赵翼《题梅村集》所云:“国家不幸诗人幸,说到沧桑语便工”,文学之于鼎革有关,断然可识矣。夫断代分期,皆为著书之便;而星霜改换,乃天时运行之故。不关人事,无裨文风,与其分为上古、中古或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何如汉魏唐宋,断从朝代乎?
这就是说,文学风貌与社会变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朝代更迭这样的大事,自不能不给文学以多方面的影响。文学史之由唐至宋,既有文学内部的沿革演变,又与朝代的兴替(关键是与这种兴替紧密相关的社会生活和人民心理的深刻变迁)分不开。所以,文学史如不分期则已,如若要分,那以与其按自然时序百年一个世纪或数世纪为一大段来分,还不如按朝代的替革来分为好。这样就把文学史的断代与中国历史的习惯分期对应起来了,文学史本来就是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这种做法与文学史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位置,也是相称的。所以,依王朝的更替来划分文学史段落,不仅用于断代文学史,即在文学通史的编撰中,也一直沿用下来,目前似乎尚无公认的更好办法可以取代它。
断代文学史既是文学通史的一截,那么在文学通史之外又出来个断代文学史,必要性何在呢?或者说,断代文学史有哪些文学通史所不具备的特点呢?
关键就在于断代文学史具有比文学通史更强的专业性,是一种更专门的文学史。它所叙述的时间短了,但内容则向深细方面拓展,深入到文学通史受体制限制所不能涉及的许多方面。文学通史无论是作为大学教科书还是作为一般的知识性读物,它的篇幅总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篇幅中要包容各个朝代,每个朝代能够分配到的分额都不会多,至少不可能比一部单独的断代文学史多。篇幅的限制决定了编写的方针,能够进入文学通史的自然只能是更为重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因为通史的参照系是上下数千年许多朝代的文学成就,而断代文学史则是在一代之中作比较和选择,作家作品的入史标准自然就比通史要宽。从某种意义上说,断代文学史与文学通史的关系就是断代史与通史的关系,亦如区域文学史之于文学通史,就像地方志之于国史的关系一样。断代文学史是缩短了的文学通史,地方志则是缩小了的国史。方志可以而且应该更详尽更细致地把一个地区的山川、物产、历史沿革、民情风俗和历代人物写入书中,正如断代文学史可以写入更多的作家作品和文学事件而这些内容在国史和文学通史中却不一定都有位置。
不妨略举实例说明之。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是一部内容很丰富充实的通史,它的魏晋南北朝(含隋)部分占四章,分量已然不轻。从内容看,它以一章篇幅述当时文学思潮,涉及文学理论的建设和神怪小说的兴起等,又以一章述魏晋诗人,一章述宋齐梁陈及隋的诗风,一章专述南北朝民歌,可以看出它一方面汲取了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优长,一方面又因文学观念的演进而有所发展。但刘师培书作为一部总篇幅不长的断代文学史,却仍有许多刘大杰通史所无法涵盖的内容,尤其是对于魏晋至陈文学家有关史料巨细不遗的勾稽和对文笔说、声律论的专门讨论,更是断代史之特长,而为通史所难以效法。若再与后起的《魏晋文学史》(徐公持编著,1999年)、《南北朝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1991年)相比,二者的区别就更大了。两部断代史合共83万字,是刘大杰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部分的九倍多,篇幅差距如此,其叙论的详略粗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史专业性之强弱,自然不会很小,而之所以有如此区别,即源于二者史体的不同。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是这样,其他各段文学史断AI写作法与通史写法的区别,大致也是这样。
由于史体不同、所述历史时间长短不同,断代文学史在内容上要比文学通史专精。由此亦可推知,断代文学史若再作分体的处理,由于进一步根据文体对所述论的范围作了限制,其内容就必然要比断代文学史更为专精。从文学通史到文学断代史到各类文体的断代文学史,时限愈严、范围愈窄而所述论则愈专愈精愈深,这是文学史学科发展进程中的明显趋势。
二
现在我们来看看唐代文学史的发展演变情况。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最早的稍具文学史意味的唐代文学论著,是朱炳熙编写的《唐代文学概论》。(注:朱炳熙《唐代文学概论》,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9年版。)此书除极简单粗略地谈到唐代文学发达的原因,唐代文学的特点、派别和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外,主要是分体介绍唐文学,文、诗、词、小说及其他艺术。全书10万字左右,不但所述粗疏,所论尤为随意,科学性非常薄弱。然而,此书不可忽视的地方在于,它已经提出了此后直至今日新写的唐代文学史仍然不可不考虑的几大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该书作者表现出他的敏感,虽则他的解答不能令我们满意。
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朴安、胡怀琛兄弟合编的《唐代文学》,内容简略粗浅。直到40年代出版的几种唐代文学史,如陈子展在1944年后出版的《唐代文学史》,(注:陈子展又有《宋代文学史》一书,后曾与《唐代文学史》合印为1册,称《唐宋文学史》。)依然如此。不过,此书虽然短小,却已具断代文学史的雏形。它以概论性的“说到唐代文学”开篇,以下讲唐诗,即以初、盛、中、晚分为四章,显然是以时序为线索来叙述。同时辅之以文体的分述,再列出古文运动、唐人小说、唐五代词人等章。从体例上看,已可说是后来唐代文学史的具体而微。
进入5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有渐成显学之趋势,可是,唐代文学史的专著仍然十分罕见,就我们所见到的这一时期的正式出版物,似乎惟有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注: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一种。此书所述的时限从杨隋到五代,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阶段。其体例已完全是“史”的规模,除开篇的一章概论外,其余四章为隋及初唐文学、盛唐文学、中唐文学、晚唐五代文学,在每一段中包含各类作家(诗人当然是主体),不再因某些文体而另辟新章,而只在各章中设节。作者处理时代与文体两者关系的原则显然是先时代而后文体的,这就使本书成为规范的断代文学史。
本书字数不多,仅18万,但内容相当充实,虽非面面俱到,但凡有所述论均颇详明,尤重艺术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观点往往不同时俗,而敢于独树己见。如对王维的田园诗,当时一般观点是评价不高,此书却说:“尽管王维不是一个真正的农民,没有理解农民在官僚地主压迫下的痛苦生活,但无论如何他已经认识到在那种社会里,只有农民和自然生活才是真正美的。”“评价他的一些诗,不应该从它有无揭露了社会矛盾或作者有无斗争性去理解,应该从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形象带给读者的美的感受和体现在这些诗中的内容对于过滤读者脑海中的庸俗思想的作用来理解。”作者很正确地抓住了文学审美功能和对人的潜移默化作用来衡量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最后甚至喊出这样的话:“让庸俗社会者去否定这些诗篇吧,这些诗篇也决不因他们的否定而丧失其应有的价值。”(注: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由此可以察知本书作者对其时甚为风靡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极为反感。
60、70年代的中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被紧缚于政治,断代文学史的写作也颇萧条,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情况才有所变化。随着“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再一次成为学术热点,唐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编著,在这次热潮中,成绩更是突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中,一下子涌现出好几部分量远超前人的唐代文学史。兹略按出版先后排列:
《天宝文学编年史》,熊笃编著,重庆出版社1987年。
《隋唐五代文学史》,罗宗强、郝世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上卷,1993年3月;中卷,1994年;下卷,待出。
《唐代文学流变史》,李从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0月。
《唐代文学史》,上卷,乔象钟、陈铁民主编,下卷,吴庚舜、董乃斌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傅璇琮主编,辽海出版社1998年。
这些著作一个显眼的共同特点是篇幅都比以往同类著作大大加长。其中《天宝文学编年史》仅述天宝一朝15年的文学,字数已为15万。《隋唐五代文学史》仅上、中二卷,述至中唐,已近70万字。《唐代文学流变史》50万字。《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字数过100万。最长的是四卷本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达到250万字。这些新出之书之所以篇幅扩大,主要是在资料的引用数量和剖析的详细上有很大进展所致,这就使唐代文学史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有了明显的提高。专业性和学术性的提高,是这些著作的共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们与30、40年代带有普及性的唐代文学史著作区别了开来。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关于唐代文学发展演变之时代文化背景。
在普及性读物中,这一内容也必须涉及,但往往是概括言之一带而过,而在专业性的文学史著作中,就需要详细、周到和具体,要更多地利用史学研究的成果,甚至在某些方面补充、发展史学的工作。如乔象钟、陈铁民、吴庚舜、董乃斌等集体编著的两卷本《唐代文学史》,除在“唐代文学总论”一章论述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时谈到经济发达、政治开明、文化多元、思想自由和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等情况以外,在初、盛、中、晚各大段落乃至一些有特殊意义的时期(如大历、贞元至大中、咸通至天祐、五代十国等),也都紧扣文学发展状况安排了专论背景的文字。在这些叙述中,注意了史学成果的利用,如对中晚唐政治和社会重重矛盾的分析,对这一阶段虽战乱频繁而生产和经济状况在某些地方仍有所上升的揭示。而有的问题史学界尚有争议,如牛李党争的实质与是非等,唐代文学史则通过对一系列作家与党争关系的剖析发表了看法,推动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二、关于文学思潮和流派。
普及性读物较少或者并不涉及这个方面,但却是专业文学史用力的一大重点。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它在初唐即设“文学思想的发展”一章,至盛、中唐则列有士人精神面貌(士风)、文学观念变化、文体文风改革的理论等章节。这说明了它对文学思潮变化的重视。其叙盛唐诗歌,有意打破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之类传统提法,把研究诗歌的题材视角改变为风格、意象和审美效应视角,从而做出了崭新的概括。如它把王维、孟浩然及其周围或风格相近的诗人(如常建、储光羲、綦毋潜、卢象、丘为、阎防等)称为“一个以人与自然为题,追求静逸明秀之美的诗人群落”,把王昌龄、李颀、王之涣,崔颢、高适、岑参等人统称为“寄热望于人间世的诗人”,然后又按“追求雄健旷放的清刚之美”、“追求慷慨苍凉的豪壮美”、“追求奇峭俊逸的壮丽美”将他们分为三种类型,实际上也就是三个流派。该书对文学思潮的来龙去脉,渊源流变,对不同风格流派的构成及其特色,都花费了很多笔墨,成为它的一大特色。
三、关于作家创作道路和作品艺术鉴赏。
无论是在普及性的还是专业性强的断代文学史中,这都是构成著作的主体部分。但在前者,叙作家生平,往往限于摘抄史传所载的宦历游踪;叙其创作成就,则常常是引出几首著名作品以示例而已。而在后者,这两方面的内容都大大扩充和深化,由原先的简叙生平发展为系统评述创作道路,即结合作家的生活遭际论析其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的演变,以及创作重心的转移和个人风格从形成到定型的过程等等。断代文学史中某些大作家的章节,往往篇幅颇长,叙述全面而深细,或对这位作家进行分期剖析,或对其作品进行分类批评,不啻这位作家的文学专传。与此相关,对于他们代表作品的引用数量和艺术分析,也大大增多加深。
试看社科院文学所《唐代文学史》的杜甫章,在这部断代文学史中,杜甫与李白、白居易三位每人占了两章,算是第一等大作家。杜甫两章四节共4.2万字(李白的字数相当)。第一节述其生平和创作道路。第二节为杜甫诗文的思想内容,径引诗句加上未引句子而概括介绍诗文内容的,共有46处,用“居中引”的办法列出杜诗杜文较长段落进行分析评论的,有16处。第三节论杜诗艺术,引述杜诗31处,具体地论析了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内涵和原因、杜诗风格的多样性、杜诗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和其他人物形象、杜诗对“赋”法的运用、杜诗的议论特色及其抒情性,还有杜诗在形式和语言锤炼上的成就,等等,可以说非常全面而细致。最后一节论杜甫的影响和历代的杜甫研究,则涉及中晚唐和宋以来大量古人对杜诗整理研究的成果,几乎是一篇杜诗学简史。像这样的写法,是只有专业性更强的断代文学史才允许和能够做到,而为一般通史和普及性读物所不能或不需的。这也就成了断代文学史独立存在的重要依据。
四、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史规律的阐释和探讨。
近年新出的几种唐代文学史在这方面都树立了较高鹄的,用力较勤,探索较深,这也是它们专业性较强的一种表现。
例如,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有“盛唐诗人的精神风貌”一章,鲜明描绘了盛唐士人的强烈入世精神和基于自信、自负、人格独立而产生的豪纵傲世姿态,并论证了这种精神、姿态与儒、道、禅思想及游侠风气的关系,特别是精辟地论述了士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以及他们精神世界内部的深刻矛盾。其文云:当时士子不欲入世则罢,倘欲入世且有所作为,则唯有求仕为宦一途,而只要走上此途,无论是否真能进入官场朝廷,就都将某种程度地改变或压抑自己的人格。“他们之中,有的因此而完全异化为皇权的工具,有的媚附权要,多数是辗转奔突于难以自解的精神苦闷之中,或是发扬蹈厉、挥斥幽愤,或是随缘任运,寄情自然。……当他们通过诗的渠道把自己的追求、奋争与矛盾、烦恼宣泄出来的时候,盛唐文学的主体色彩,也就这样形成了。”(注:见该书第163页。)这里的论析呼应了前文对盛唐文学特色的描绘,把唐代社会体制、士人生活道路和复杂心态与盛唐文学精神联系起来,实际上就从人与文学的关系这个角度切入了文学与文学史发展的规律。这一论述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特征的认识都有所启发。类似的论述在罗、郝二氏主编的文学史中还有多处。
李从军《唐代文学流变史》更以恩格斯《反杜林论》关于思维的任务是揭示历史过程内在规律性的论述为指导,将全书根本宗旨归结于探索规律,明确宣布:其书“旨在反映唐代文学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关系;唐代文学不同时期的作家、流派、作品的文学倾向和文学思潮;各个时代文学的风貌特征及演变状态;文学对社会生活及社会现象的反映和作用;文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之间的联系;文学创作者与现实生活、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唐代文学总体演变和发展趋势,并力求从中探讨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注:见该书《前言》。)由于作者持此目标,故对唐代文学从分期到特征的概括、到具体作家的述评,均紧扣揭示规律性这一主题。
对规律性的探讨,带有科学试验从已知事实向未知领域挺进的性质,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断代文学史在这方面的收获尽管还是初步的,其观点和结论尽管尚需接受检验和不断修正,但这一努力已使这类著作的理论品位大大提高。
三
以上,对近年出版的诸种唐代文学史的主要共同点作了分析,由此也可大致窥见文学史断代研究与专书著作的性质及其学术要求。当然,这几种唐代文学史又各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上、中册),还有三个明显特点应予注意:一是有意与文论史相融合,将文学思潮、文学批评和一代文学创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历史的考察,从而增加了理论观点的厚实程度。这与主编之一的罗宗强先生对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曾作过专门系统的研究有关。二是行文有气,笔端常带感情,因而颇富个性色彩,一般集体合作的文学史不易臻此。三是注释详尽,附载了大量为进一步研究所必需的资料,凡有争议的问题则尽量将各家观点客观介绍,以为进一步深入探讨之基础。这也是这部文学史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表现。
李从军的《唐代文学流变史》无论章节编排还是文字表达,都刻意打破传统文学史模式。就其理论色彩之浓而言,可称它是一部史论体的文学史;就其各章节标题的恢诡、行文的挥洒而言,又不妨视之为杂感随想式的文学史。这两点在文学史撰写史上都颇具创新的意义。如果要说有什么不足,那就是本书的操作方式基本上还是运用先有和外在的各种中外理论于唐代文学,论述的结果是证明唐代文学的发展演变与那些理论相符,大体不出那些理论的范围,所以,此书的分析更多的属于印证和演绎。不能否认这种论证的意义,也许这是走向独立理论创造的必经之途,但更高的境界毕竟应是从唐代文学的实际出发,从唐代文学本身提炼出切合其真实状况的规律性认识。应该说,唐代文学的丰富多彩及其发展中的曲折变化,是为这种理论抽绎提供了充足条件的。如果研究者所获得的认识只适合于唐代文学,那是唐代文学的特殊规律;倘若它的涵盖面更广,对认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效,那就有可能上升为更高一层的规律性认识。对于一切有志于作理论探索的文学史研究,这是一个值得下功夫追求的目标。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同人合著的两卷本《唐代文学史》规模宏大,涉及面广,写入了一般文学通史所不载的许多人物,对唐散文家、小说家创作成就和俗文学状况的介绍也比一般通史丰富得多。这样就大大扩展了文学史的视野和容量。又有意识地从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唐代文学家生平游踪的考订、唐集的整理笺释、敦煌文献的解读以及对唐代社会、文化、民俗的系统研究中汲取最新成果,使本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学术水平。
下面谈谈两部编年体的唐代文学史。
两部编年体唐代文学史虽大小悬殊,但各有其贡献。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虽仅述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的文学,但具有开创之功。
全书以作家游踪和创作活动为主,每年按每人一条列出若干人,如天宝元年十条即叙述了王之涣、王维、崔颢、高适、李白、储光羲、杜甫、岑参、萧颖士、贾至等10位作家,以后各年有所变动增损,共记述了30位作家,而王维、王昌龄、高、岑、李、杜自是主角。叙述中颇注意彼此的关连,有意将作家交游编织成网;对作家往昔有关行事和作品,则予以回溯,并引出代表作加以品评赏析。有些安排颇见匠心,如天宝五年(746年),是诗人李颀在本书中第二次出场,史文较长,先述其在洛阳听董庭兰奏《胡笳弄》,作《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诗,遂引此诗全文论析之;接叙“李颀是盛唐诗人中善于描写音乐的能手”,又引出作年不明的《琴歌》和《听安万善吹筚篥歌》,云“三诗虽同写音乐,却春兰秋菊,各尽其妙。”下面又引出他的好友綦毋潜,简介了綦的生平、仕历,引述了李颀给他的赠诗,一直叙到綦赴周至尉之前去终南山访储光羲时的赠诗(亦引出全文)。这样就使本书对作家的描叙血肉丰满,比较生动。本书除充分利用前人和同行研究成果外,亦有作者自己的考证所得(如王维生年),尤以史述与文学性赏析结合得较好为特色。若论其不足之处,则其一、所写年限过短,尚难以看出盛唐文学的总貌,单个作家的行踪介绍也欠完整;其二、全以作家列目,而缺少其他性质(如有关政治、经济与文化艺术其他门类、中外交流等)的条目,仍留有作家年谱之拆散重编的痕迹,显得视野不够开阔。
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比熊著晚出10年,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且以多位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合力编成,所述时间下及五代宋初,达360年之久(618-978年),是一部体大思精、资料丰富、考据详实的专著,代表了当前这一领域的最新成就。
此书编者对编年体史书的特点和优势有充分的自觉。主编在《自序》中写道:“研究文学确实应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的实体的存在,还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可能互相排斥而实际又互相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这样做,就会牵涉到总的研究观念的改变。”(注:见该书第1册,第3页。)为了在研究中贯彻这种整体性原则,为了克服前此大量章节体文学史所暴露出来的共同弊病,这才想到了“逐年地作综合记录,把政治发展、经济改革、人们思想情绪的变化、作家们复杂多样的经历及其创作活动,作总体、流动的考察”这样的编年体模式。具体到唐代文学史,便是“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如生卒、历官、漫游等),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印刷等门类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资料,一年一年编排”,(注:见该书第1册,第5页。)从而使文学史成为一幅“立体交叉”的生动活泼的图景。
资料数量的丰富和胪列原始材料以考证的方法,特别是全书客观冷静、不加评骘更不作描绘渲染的著录方式,使这部文学史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由于是纲目体的编年纪事,又由于有足够的篇幅,本书所涉及的人物、作品、现象和事件在同类著作中是最多最广的,表现出一种非常宏阔的视野。
这部断代文学史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它标志着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范型新的深刻变化。中国文学史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表现了愈来愈清晰、科学的文学观念,把许多原先被传统文学观藐视和排斥的文体,如词曲、小说、戏剧和通俗文学等,请进了文学史,并给以崇高地位。然而,同时也将一些在历史上曾受到重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学作家和作品排除出了文学史,发生了削中国古代文学之足以适西方现代文学观之履的弊病。经过近年来的痛苦反思,愈来愈多的文学史家认识到加强文学观的科学性、努力使我们的文学观与国际同行沟通甚至接轨固属必要,但尊重中国文学的历史事实,把我们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建筑在本国文学史的事实之上,则尤其重要。不强用今人的文学审美取向去硬套古代作品,惟有这样,方能写出全面真实反映中国文学实际的文学史。《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所持的正是这种经过近代文论洗礼的新的大文学史观,它尊重唐人的文学观,彼时普遍观念所视为文学者,本书多予采录,并不因其不合近数十年来通用之所谓纯文学标准而简单排斥。在本书中诗歌与诗人活动自然仍是重镇,并且不以将载录范围扩大到传奇小说和通俗文学为满足,而是把当时若干虽具实用性而不失美感的文章(包括骈散二体)和善写此类文章的作家也都尽量记入,从而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唐代文学的巨大繁荣。
唐代文学史研究在近年的成就是可喜的。取得这种成就的根据和保证是唐代文学专题研究的全面丰收。文学史当然有它的独立学术价值,但归根到底,它又必须建立在各专题研究的坚实基础之上。专题研究的成果不断进入文学史,促进着文学史水平的提高;文学史又不断整合和反映着专题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就在刺激着专题研究的深入,二者就处于这样一种互动互利的关系之中。所以,走向专业、追求精深,这是文学史研究的大趋势,也必然要在文学史的撰写工作中表现出来。文学史不但因向专题研究汲取营养而日益深化,而且通过本身体制的变化而走向专精。由一般的文学通史,进至断代文学史,再到断代的文体史,研究区域呈缩小之势,而研究深度和精细程度则大大增加,这个发展趋势从近年来有关唐诗、唐词、唐斌、唐小说、唐判文、唐试策的专史和专题研究的涌现,已看得相当清楚了,而可以预见的是,这一类专史还将拥有更远大、更美好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