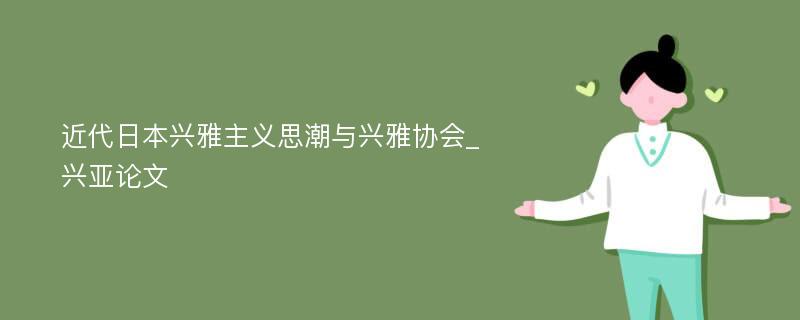
近代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与兴亚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思潮论文,近代论文,主义论文,兴亚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亚洲主义问题是一个庞大而十分复杂的课题,近年来研究者虽不乏人,然意见纷纭,见仁见智,迄今莫衷一是。争论的焦点是“早期亚洲主义”的性质问题。对于所谓“早期亚洲主义”,有论者解释,乃指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兴亚主义思潮或兴亚论。既然如此,争论的双方,理应以此为中心而展开讨论。古人云:“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撇开中心议题而侈论成篇,是难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论者提出“早期亚洲主义”是“一个多翼并存的思潮”,但对于“多翼”表现为哪些、其中何者属于主流、如何对兴亚会进行分析和评价等核心问题,或避重就轻,或一略而过,不肯多着笔墨,给人以“王顾左右而言他”之感。故笔者认为,对此问题还大有进一步商讨的必要。
一 兴亚主义思潮流派及其主次地位
论者指出:“对于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我们主要应该肯定其团结亚洲以抗西洋的‘亚洲同盟思想’。其‘中日提携’论出于当时兴亚论形成之际,独树一帜,诚属难能可贵,应在亚洲近代思潮史上占有适当历史地位。”①对“早期亚洲主义”的“中日提携”论做了很高的评价。还进一步提出:“1878年②经由曾根俊虎等人的活动,振亚社(后称兴亚社)成立,主张‘亚洲连带’的‘兴亚’论即战略亚洲主义的提出,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进入‘成立期’的标志。”因此,虽然“早期亚洲主义”是“多翼并存”的思潮,但就矛盾的主次论而言,以曾根俊虎为代表的主张“中日提携”的“兴亚论”,“乃是本期亚洲主义的主旋律”。③既然如此,在考察兴亚主义或“兴亚”论时,就不能仅着眼于兴亚会一家,更不能以曾根俊虎其人为中心。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一叶障目,只看到曾根所代表的一翼,既罔顾曾根以前兴亚论的存在,对与其并存的其他多种流派的兴亚论也视而不见了。若不是在全面考察兴亚主义思潮各种流派的前提下来讨论其矛盾的主次,是不可能真正做出正确判断的。
应该看到,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日本兴亚主义思潮,确实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各种流派纷呈,不只是兴亚会一家,更不止是曾根俊虎所代表的一派。流派与流派之间,其主张既相互影响,其成员又互有交叉,而且每一流派之中还有派别,它们或同中有异,或迥然异趣。即或是兴亚会,也不是单一的流派,而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所以,要想全面地了解当时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首先必须扩大研究的视野,不能仅限于兴亚会本身。关于兴亚主义思潮流派种种,名目繁多,难以一一列举,兹择其要者略作评述。
(一)宗教启蒙派。如真宗兴亚论,以小笠栖香顶为代表。小笠栖香顶(1831-1905),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教派僧人。他认为:“佛法兴于天竺,至中国、日本。方今印度先衰,中国次之,日本尚有可取焉。”④所以,应以日本为主,到中国开教,启蒙华人皈依日本真宗,并连印度结成三国联盟,带动亚洲佛教徒共同对抗西方的耶稣教。所作《日本刀》诗有云:“报国精神凭剑彻,勤王事业盖棺知。”⑤可知其内心世界是热衷于日本国权之伸张的。小笠顶于1873年和1876年两次来华传教。第一次在北京龙泉寺挂单时,曾为潜伏于北京的岛弘毅等三名日本军事间谍教授汉语。⑥第二次是偕谷了然等僧人一起西渡上海,开上海别院传布真宗。此举得到了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偕谷了然曾有诗记此行道:“欲化世界五大洲”,“先度支那四百州”。可见其野心之大。故有日本学者称他们是“充当了伸展国权的先锋,做了国家的别动队”。⑦这话是不错的。上海别院开张后,尽管活动甚力,然影响终究有限,根本无法与西方的在华宗教势力抗衡。
(二)文化复兴派。如国粹兴亚论,以三宅雪岭、冈仓天心等人为代表。三宅雪岭(1860-1945),以评论家而著名。他与杉浦重刚、井上圆了、志贺重昂等人创办政教社,先后出版《日本人》、《亚细亚》、《日本及日本人》等杂志,反对欧化主义,主张坚持国粹主义,认为日本是亚洲文明的真正继承者,对复兴亚洲负有责任。此派的政治主张本质是日本中心主义,维护天皇制国家,属于国家主义。正像江户时代的日本中心主义演变为“大日本帝国”构想⑧一样,建立在日本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国粹主义也必然要融入到维护“大日本帝国”构想的思想体系之中。果然,后来政教社便发动了“对外强硬运动”,鼓吹要采取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冈仓也提出要“为明治维新的理想,为宝贵的古典文化遗产,为整个亚洲复兴的和平理想而战”。⑨此派的活动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整个中日关系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
(三)自主联盟派。主要包括同等兴亚论和革命兴亚论两种。
1.同等兴亚论,以植木枝盛为代表。植木枝盛(1857-1892),是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其思想核心是人民主权论,主张“天下万人”皆平等,国家之间亦应如此,提出“国家同等论”。进入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加紧了吞并琉球的步伐。此时,民权论者的立场开始分化:或谓“民权即国权”,倒向了国权论,起而为日本政府的侵略扩张行径辩护;或仍坚持民权论立场,对日本政府的无理举措进行抨击。后者警告当局在与“邻邦交集间,不可有悖条理,失信义”,竟采取“轻侮弱小之卑劣处置”。并对“琉案”引起的中日交涉表示忧虑,指出日本不应见中国国势日弱而予以轻蔑和侮辱,因为日本无法单独确保一国的繁荣与独立,必须采取“合纵连横”之策,与中国结为兄弟互助互援,同晋贸易大国之列,才是图谋日本在亚洲拓展之路。⑩植木枝盛则发表题为《论应让琉球独立》的文章,批判西方殖民活动是用“武威腕力”进行侵夺的“野蛮行为”,并谴责日本政府仿效此类野蛮行为对琉球“强行处置”,既“残害人类自主之理”,亦形同“国家同等论之贼”。(11)与其他主张中日“提携”或“合纵”的流派相比,此派强调“国家同等”乃其一大亮点,是值得肯定的。惜乎曲高和寡,响应者寥寥无几。其后,日本国内政局逐渐稳定,包括植木在内的许多民权论者也转向热衷于仕途,此派亦趋于式微了。
2.革命兴亚论,以宫崎滔天为代表。宫崎滔天(1871-1922),是坚定的“支那革命主义”者。他以社会革命者自任,但认为革命的中心应是中国,而不是日本。因为亚洲“命运的转折点,实系于中国的兴亡盛衰。中国目前虽然衰弱,但地广人多,如果能扫除弊政,统一治理,并能善加利用,不仅可以恢复黄种人的权利,更足以号令宇内,行道于万邦”。果能如此,“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以兴起,菲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12)宫崎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支持始终如一,从不稍懈,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日本志士襄助吾国革命事业者,以此君为最努力”。(13)故孙中山对其做了高度的评价:“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勖勉极挚。”(14)但宫崎的“支那革命主义”思想形成较晚,与孙中山相知相识是在1897年。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宫崎对孙大为倾服,表示将“举全力尽先生之事”(15),从此便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众多的兴亚主义流派当中,此派是最值得肯定的,但它始终未成为思潮的主流,故在讨论“早期亚洲主义”时过多地着墨于此,完全没有必要。有论者质疑道:“评析日本亚洲主义,简说与不说宫崎滔天,是否为一个有意的‘疏漏’?”(16)应该说,提出这样的妄测,纯属误解。
(四)大陆政策派。主要包括征服兴亚论、经略兴亚论、殖民兴亚论、连带兴亚论等。
1.征服兴亚论,以江藤新平为代表。江藤新平(1834-1874),是明治初最狂热的对外扩张论者。他于1871年起草《对外策》,提出要警惕西方列强“吞并亚细亚”的动向,而中国正是“亚洲必争之地”。“倘若俄国一旦结合美、普而进攻,则必得此地”,“如此则皇国危如累卵”。建议政府先大力整饬军备,待时机成熟,“一举征服中国”,“形成占据亚洲之势……最终与美、普争霸世界”。(17)其后,他觉得中国太大,难以一口咽下,又于1873年抛出一份《支那南北两分论》,提出联合俄国瓜分中国:北部让给俄国;南部划归日本版图。“以十年为期,在中国内地敷设铁路,待经营就绪,即驱逐俄国,请圣天子(日本天皇)迁都北京,从而完成我第二次维新大业”。(18)不久,江藤以叛乱罪处死。其狱中诗云:“欲扫胡尘盛本邦,一朝蹉跌卧幽窗,可怜半夜萧萧雨,残梦犹迷鸭绿江。”(19)死到临头,还念念不忘征服中国,可谓冥顽之至!其人虽逝,然香火不断,衣钵代有传人。其著者有时任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的小川又次陆军大佐,于1887年提出了灭亡中国的《清国征讨方略》,计划将中国分割为六块,或直接纳入日本版图,或建立傀儡政权,或成立日本的保护国与监督国。换言之,即将中国永远从地图上抹掉,其狠毒较江藤新平有过之而无不及。
2.经略兴亚论,以副岛种臣为代表。副岛种臣(1828-1905),是“大陆经略论”的提出者。早在1871年任外务卿时,他便萌发了“大陆经略论”的思想,即为了对抗西力之东渐,要赶在俄国进入东亚之前,进行对大陆的经略。(20)其后撰写《大陆进出意见》,系统地论述他的“大陆经略”思想,以为明治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内称:“日本四面环海,若以海军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岛国之境,则永远难免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欲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以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今日欲将朝鲜占领,中国决不会袖手旁观,则势必依靠武力决战以获得朝鲜,此外别无他途。”并强调指出:“依靠战争使国家强盛”,“此乃国家之正理”。(21)副岛的这套歪理,在当时的日本影响很大,倾倒了许多“大陆雄飞”论者,咸奉为金科玉律,决定付诸行动。著名的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因受其影响,深信在西力东渐的情势下,亚洲各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要振兴亚洲,“必须首先防止中国之灭亡”。(22)就是说,由日本来控制中国,才能避免亚洲沦于西方列强的统治之下。从此决心要走“大陆雄飞”之路,盘算着“何时鞭起铁蹄马,踏破坚冰鸭绿江”。几年后,他终于怀着“误忧天下事,拂泪上征舟”的复杂心情西渡上海,成为一名间谍。(23)时在长崎《镇西日报》任职的浦敬一,亲自拜访副岛之后,也坚定了西渡的决心,准备“叱咤驱马举长鞭”,“亦以单骑入北燕”。(24)随后便毅然放弃报社工作,抛开结婚不久的爱妻,往投荒尾精门下,成为汉口乐善堂的一名骨干。
3.殖民兴亚论,以头山满为代表。头山满(1855-1944),本是民权运动的支持者,后转变为国权论者,于1881年成立玄洋社,以宣扬“敬戴皇室”和“爱重本国”为宗旨。(25)他与先前的“征韩”论者不同,主张先“处置中国”:“与其先向小小的朝鲜下手,不如先处置庞大的中国。”(26)因为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势,但靠日本一国的力量难以应付,“若能使支那真正觉醒,日本与支那、印度提携,其力量则足以慑服列国”。而与中国的“提携融合”最为重要。“日本与支那,数千年来,同文同种,自地理而言,自民族而言,或自人情而言,都非提携融合而不可”。“支那离开日本,则无可以凭赖立国;日本不与支那结合为一体,势亦不能自立”。那么,中日两国怎样“提携融合”呢?他的答案是:“支那治世的大目的乃国民之安居乐业。支那虽然到处皆有无限之宝库,而其国民却陷于终年贫困之中。解决此一矛盾,即日本之使命也。以日本为指导,矫正支那政治上之缺陷;以日本的资本、技术,开发支那的无限宝库。”(27)可见,他的所谓中日“提携融合”不是别的,而要将中国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头山满的信徒颇众,活动时间很长,对大陆浪人的影响尤甚。
4.连带兴亚论,以荒尾精为代表。荒尾精(1859-1898),是汉口乐善堂间谍机构的创始人。他曾多次表述其“兴亚”思想。如在《兴亚策》中提出,当此西力东渐之际,欧亚之竞争势所难免,然朝鲜贫弱,中国老朽,令人堪忧。日本应“内张纲纪,外施威信”,“必得先救此贫弱者,扶此老朽者,三国鼎峙,辅车相依,进而挽回东亚之衰运,恢弘其声势,膺惩西欧之虎狼,以杜绝其觊觎之念”。(28)既成中日韩“三国鼎峙,辅车相依”之势,却不能没有主导者。因此,他在《复命书》中向政府建议:“今日之形势,虽云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倘有能执其牛耳而起者,足以一跃而雄视宇内,亚细亚振兴治安之机亦系于此。是岂非天与我国之一大机运哉!”(29)其后,他又在《对清意见》中进一步陈述这一主张:“我国为东洋的先觉者,而中韩两国为诱掖者,由此我可常执东方之牛耳,倍增我国的元气,内则殖产兴业而强盛,外则交通贸易而兴隆,不久之后,在宇内海港到处均可见光荣的旭日旗飘扬……向来为东方区区一岛而被世界藐视的我日本,将由此而一跃为亚细亚的雄邦,令欧美列强生畏。”对此,日本学者升味准之辅评之曰:“这里说的日本为‘东洋的先觉者’,‘中韩两国为诱掖者’,把连带责任意识和盟主意识结合在一起了。”(30)此派的活动卓有成效,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大陆浪人的中坚。
(五)合纵连横派。主要包括合纵兴亚论、均衡兴亚论、同文兴亚论等。
1.合纵兴亚论,以曾根俊虎、金子弥兵卫、草间时福等为代表。曾根俊虎(1847-1910),是合纵兴亚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曾撰有《兴亚管见》一册,但未见公布于世。1874年,他曾提出,亚洲要能够与欧美抗衡,中日两国,“必先为同心协力,兴亡相辅,然后推及亚洲诸邦,共相奋勉,俾能自强独立”。(31)1877年,曾根与南部(东)次郎、金子弥兵卫等人议及亚洲局势,皆认为:“今欲振兴亚洲,唯合纵一策耳。”(32)遂成立了振亚社。1880年,他再与金子、草间时福等人联络,共议组成了兴亚会。当时,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与曾根相见时,曾问及兴亚会的宗旨何在,曾根称:“‘兴亚’二字,乃欲挽回我亚细亚衰颓萎靡大局之意,而欲挽回全亚洲衰颓之势,非亚洲各国合纵连横,心志相同,缓急相扶,苦乐相共而不可也。”(33)那么,由谁来主持亚洲各国的“合纵连横”大业呢?对此,曾根并未直接回答。但草间却在一篇文章里透露出了此中的消息:在亚洲国家中只有日本有资格担当此任,借此“维持欧亚大陆之权衡,欧洲将无法再对亚洲做蚕食之态,日本将由此稳操东亚盟主之牛耳”。(34)金子著《亚洲志论略》一书,亦指出:“我邦之人所为,不止于邦内,犹进而与全洲共有所为,以挽回亚洲数千年之颓废,而争雄于欧洲之富强。且时不可失,事之成败在时之得失。昔者英吉利富强文明,先于欧洲诸邦,虽国僻在海岛,为大洲之盟主者数百年,诸邦皆仰之如山斗,其权势威望至今不衰……今我邦之亚细亚大洲,势类此焉。欧人尝有言曰:东方应有一英国,谓我邦之将雄长于全洲也。”(35)同是兴亚会创始人的草间和金子,终于讲出了心里话,一个说要“操东亚盟主之牛耳”,一个说要做“东方的英国”。然而,《兴亚会规则》也好,其公开的宣言也好,对此却只字不提,讳莫如深。可见,与头山满的殖民兴亚论和荒尾精的连带兴亚论相比,此派具有更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2.均衡兴亚论,以小泽豁郎为代表。小泽豁郎(1858-1901)本是一名工兵少尉,因通法语,于1884年被参谋本部派往福州,侦察中法战争情况,因策动哥老会暴乱未成,被调至香港,不久病休回国。1890年,与福本诚、白井新太郎等组织东邦协会,发表《设置趣意书》。其大意谓:西洋诸国搜括殖民地,西南洋各地掠夺一空,其势渐及东洋,“而日本、支那首当其冲。当此之时,以东洋先进自任的日本帝国,不讲求详察近邻诸国之近况,则无由向外伸张实力,与泰西诸国均衡以保东洋”。并规定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对有关东南洋各地之地理、商况、兵制、国际情势及历史进行调查研究,必要时派遣要员前往实地考察,以为他日“我邦人进出东南洋”预做准备。(36)副岛种臣先任副会长,后改选时被推为会长,由近卫笃麿担任副会长。会员最多时达到1200余人,伊藤博文、头山满、曾根俊虎等皆册上有名。(37)显而易见,此派成立东邦协会的目的,是以“与泰西诸国均衡以保东洋”为名,基于日本日益膨胀的扩张野心的需要,而为日本将要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从事搜集情报的工作。
3.同文兴亚论,以近卫笃麿为代表。近卫笃麿(1863-1904),是“支那保全”论的提出者。1886年10月,乙未同志会成立。会员主要包括汉口乐善堂骨干、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学生、东洋学馆成员,共148人。“平时为对清国与其他东邦的友好团体,一旦有缓急之时,将着社会行动之先鞭”。(38)1897年春,陆羯南(1857-1907)与三宅雪岭、志贺重昂、井上雅二等共议,设立东亚会,并决定发行机关杂志,研究时事问题。1898年6月,在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中西正树、田锅安之助、白岩龙平等的推动下,以时任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为中心组织同文会。同年11月,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改称东亚同文会,由近卫担任会长。乙未同志会亦解散而参加该会。日本政府以支持“对支民间外交”的名义,将其活动费和机密费皆列入预算项目。东亚同文会确定的纲领第一条就是“保全支那”。还公布了其“兴亚”主张的《意见书》,认为中日两国“文化相通,风教相同。以情而论则有兄弟之亲,以势而论则有唇齿之形”。应该“忘愆弃嫌”,共防外侮,“同致盛强”。(39)到1900年,兴亚会(亚细亚协会)亦并入东亚同文会。由于以“保全支那”为思想核心的同文兴亚论,正符合了当时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需要,从而“成为舆论的中流砥柱,慷慨激昂之士皆知其所向,喧嚣的议论得以统一”,达到了“统一舆论,团结同志”的目的。(40)至此,兴亚主义思潮的各个流派终于并轨合流,标志着旧的“兴亚”诸论纷乱杂陈的局面告一结束和一种新的亚洲主义思潮改头换面而兴起。
通过以上对兴亚主义思潮各种流派的评述,可以从中得出几点认识:第一,尽管对作为兴亚主义思潮主流派别的各种兴亚论不能肯定,但并不是所有的兴亚论都要否定。如宫崎滔天的革命兴亚论即是。第二,在兴亚主义思潮各流派当中,无论从其发展的持续时间还是对近代中日关系的影响看,大陆政策派的各种兴亚论和合纵连横派的合纵兴亚论,应同居于主流的地位。论者认为兴亚会一家代表了“本期亚洲主义的主旋律”,是不能成立的。第三,这些居于主流地位的兴亚主义派别,其宣言内容不尽相同,或各有侧重,或策略有别,但都属于主张“大陆雄飞”的对外扩张主义思潮,是应该予以批判的。如果看到某些兴亚论者一开口就讲“提携”,讲“合纵”,便大为欣赏,赞声连连,未免太天真了。古往今来无数事实警示着人们:对于政治人物的言论,光欣赏其漂亮的词句不行,最重要的是看其实际的行动。即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也。一些兴亚论者口中高唱中日“提携”和“合纵”,心中却“抱着在政治与经济上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期待”。(41)故有学者指出:“‘兴亚论’因背后充斥着危机意识而强调日本人领导亚洲的‘使命感’”,“借由‘兴亚论’此美名,日本自己陷入一种逻辑上的骗术”;明明是“日本追求单一国家利益”,却宣称“是造福亚洲。至此证明,日本的亚洲论并未基于互惠互尊之义,有的不过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益的追求而已”。(42)可谓切中要害之论!
二 兴亚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
兴亚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东亚同文会所编《对支回顾录》说它是“民间组织”。(43)沪友会所编《东亚同文书院》更肯定它是“民间对清友好组织”。(44)还有论者进一步认为,兴亚会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最初的重镇”,其所倡导的“中日提携”论与“兴亚”论“具有较多的民间性”,亦可称“民间亚洲主义”,故代表的是“民间温和派”。(45)其实,当兴亚会成立之初,即有人对其所宣扬的“兴亚”论表示怀疑。如王韬主编的香港《循环日报》刊载《兴亚会宜杜其弊论》一文,指出:“日人创立兴亚会,其志则大,其名则美,而事势之难处,意见之各殊,则非特等于无补空言,且将类于阴谋诡计也。”(46)既然人们早就对兴亚会性质有不同的认识,显然对其轻率地做出结论是不行的。
兴亚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其长期的发展历程已经展示得十分清楚。它是1880年成立,到1900年并入东亚同盟会,存在了整整20年。其整个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一)兴亚会时期,从1880年3月9日正式成立时起(47),到1883年1月20日,历时约两年零10个月。成立之初,以长冈护美为会长,渡边洪基为副会长。不久,长冈被任命为特命全权公使,赴荷兰任职,会长一职由伊达宗城接替。其后,继任会长的还有副岛种臣和榎本武扬。1882年11月,因榎本已派赴北京担任驻华公使,仍由从欧洲回国的长冈接任会长。(二)亚细亚协会时期,从1883年1月20日正式成立时起(48),到1900年3月,历时约17年零两个月。亚细亚协会成立后,仍由长冈继续担任会长,渡边担任副会长。直到1899年,才改由榎本武扬担任会长,花房义质担任副会长。第二年,亚细亚协会并入东亚同文会,终于结束了其存在的历史。
兴亚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一)会员所缴纳的会费,有“创立员入会金”、“同盟员入会金”、“终身会员纳金”等名目;(二)捐款,有“助会金”、“寄附金”等名目;(三)日本当局奖励而颁发的“赏金”;(四)外务省以“机密费”名目拨给的补助费。
推动兴亚会成立最力者有:宫内省修史馆御用员宫岛诚一郎、以中国为中心搜集亚洲情报的海军中尉曾根俊虎、外务省权少书记官北泽正诚、驻北京公使馆馆员金子弥兵卫、派任中国厦门领事馆馆员宫崎峻儿等,都是承担外务省有关涉亚(洲)事务工作的成员,但“掌握实权的是历任会长、副会长的长冈护美、渡边洪基等”。(49)
首任会长长冈护美(1842-1906),原熊本藩藩主细川齐护之子。后列入华族,获子爵称号。时任外务省敕任御用挂,致力于与西方国家修改不平等条约事务。副会长渡边洪基(1848-1901),明治初任外务大录。曾随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等国,回国后任外务大书记官。此时以副会长协助长冈管理会务。长冈、渡边二人皆来自外务省,其行事风格平和而不张扬,对其真实用意从来深藏不露。如长冈有《呈姚先生》(50)诗云:“诸夏有山皆拱北,中原无水不朝东。古来和汉邻交好,岂伹(徒)高谈地势雄?”(51)他表面上讲的是日中友好,却又巧妙地突出日本在亚洲的中心地位,受诗者竟浑然不觉。有论者指出:“长冈的政治主张是,日本应该执亚洲之牛耳,但要‘保全中国’,即在中国承认日本领导的条件下,可以允许中国‘独立存在’。”(52)渡边作为副会长,更是一贯低调,但当1881年5月日本在朝鲜一度处于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时,他便为确定日本在朝鲜的盟主地位而积极谋划方策。为此,他提交了一份内部报告《对韩现今政略大要觉书》,建议由日本发起,于翌年1月缔结日、朝、清关税同盟,并在此基础上组成政治联合体。(53)像长冈、渡边这样的正、副会长,能否真正在平等的基础上执行“日中提携”方针,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除长冈护美之外,其他几位先后接任的兴亚会会长,也都与外务省有密切的关系。伊达宗城(1818-1892),江户末期藩主、华族。明治政府成立后,历任外国事务总督、参议、大藏卿等职。1871年,以特命全权大臣来华谈判,与李鸿章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十八条。副岛种臣,历任参议、外务省御用专务、外务卿等职。1873年,以特命全权大臣名为互换《中日友好条规》来华,实则为日本发兵入侵台湾进行外交准备。1874年,因“征韩”派失势而下野。期间曾来华进行考察,回国后提出了著名的“大陆进出意见”书。副岛认为:“支那的根据地不在北京而在满洲,朝鲜又是中国重要的屏障之地。故清政府即使失去华南,也不会放弃满洲。”因此深信仅靠外交手段无法解决朝鲜问题,断言日中之间必有—战。当1884年日本在朝鲜策动甲申政变失败后,副岛主张:立即与中国开战,请明治天皇行幸九州,以长崎为行宫,派大军西进,一支登陆烟台,攻略山东,一支入朝鲜,占领汉城而逐朝王;山东的作战目的达到后,开始与清政府谈判,多索偿金,并将所攻之处尽量占领,“采渐次蚕食之策,以经营占领地奠定国家富强之基”。(54)榎本武扬(1836-1908),曾以海军中将衔担任驻俄公使。1878年夏,榎本从彼得堡卸任归国时,绕道中国进行考察,撰成题为《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55)回国后一度任海军卿。1882年,奉派为驻华公使。1885年,曾随同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李鸿章签订《天津条约》,为日后日本出兵朝鲜埋下了伏笔。让副岛、榎本这样激进的侵华派担任兴亚会会长,指望他们会真的推行日中睦邻和提携,岂非缘木求鱼?
如若不信,请看副岛种臣对兴亚会办会宗旨是怎样解释的。副岛在《致兴亚会诸君函》中把亚洲各国合纵、提携比作“苏奏合六国”,把争雄欧洲比作“鲁仲连不帝秦”,是值得仔细玩味的。他对前者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无济于事。称:“兴亚之会何也?是大可思也。兴亚之为会也,诸君令亚国国自兴乎?将令日本政府与亚诸国相提携抱负而兴乎?是苏秦合六国之策,吾知其不可用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其“罔法可加,朝入而暮散”,乃势所必然。“拮据经营之劳,徒为也”。与前者不同,后者则表明兴亚之会不可不办。“夫国也者,一人精神之累积之点也。一人精神能为万里长城,而国皆万里长城也;一人精神能干城,则国皆干城矣;一人精神能弓矢矛戟,而国皆弓矢矛戟矣。然则一人能磨砺自己精神,则兴亚目的可达也。是鲁仲连不帝秦举动,诸君有焉”。最后,表明个人的态度:“余兴亚之精神,则虽死且弗休也。”(56)副岛在信中讲得十分清楚:提出争雄欧洲口号,是为了凝聚人心和振奋国民的士气,这才是兴亚之为会的主旨所在,也是兴亚之精神所在,而所谓“提携”、“合纵”云云,不过是廉价的宣传手段,是明知其不可用而不得不用之,是不能当真的。想不到一百多年以后,仍有论者怀着美好的愿望,一厢情愿地相信“提携”、“合纵”之策的善意,给予充分的肯定,盖炫于其漂亮口号而未深入了解真相之故耳。
兴亚会有多少会员,因入会时间有早有晚,缺少全面的统计。从保存下来的几份《会员姓名录》看,包括东京本部、神户分部、大阪分部、地方分部和海外分部,连创立员及同盟员计273人,皆非泛泛之辈。其中,有三种人特别需要注意:
第一,外务省系统的人员。粗略统计,约20余人。这些人,或在外务省任职,或派为驻外公使、总领事、领事及使领馆馆员,或被安排执行临时任务,大都是激进的侵华派。其著者如:柳原前光(1850-1894),1869年进入外务省,任外务大丞,提出“弘张国威”之策,认为征服朝鲜和中国,“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本”。(57)翌年,日本政府为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做预备谈判,派柳原前光为驻华公使。1874年9月,大久保利通奉派来华谈判日军侵台善后事宜,柳原作为驻在国公使,却与日本侵台军参军、海军少将赤松则良及驻厦门领事、陆军少佐福岛九成密议,炮制了一份《与清国决战策》,提出:一旦谈判破裂,先以海军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吸引清军主力南援,然后在军舰的掩护下运送精兵一万,“攻陷北京,穷追清帝,则十八省顿时瓦解”。(58)竹添进一郎(1868-1917),有极高的汉学素养,是著名的中国通。1875年,作为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的随员来华。曾入蜀游历和考察,撰《栈云峡两日记》一书,以此声名鹊起。是时,陆军大佐福原和胜为首任驻华武官,命竹添驻上海从事情报搜集工作。1880年,任驻天津领事。期间,为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多次与李鸿章商谈解决方案,因其每每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辩护,甚至无理取闹,终使“琉案”成为悬案。1883年,竹添调任朝鲜公使。翌年,便在汉城策划甲申政变,因失败而逃回国内。南部次郎(1835-1912),明治初任盛冈县大参事。1874年,日本发兵侵台,南部往见台湾事务总裁大隈重信,提出:一旦战事发展为“征清之役”,愿率旧藩部500人进攻中国,扰其一方,以配合大军。1880年,奉参议黑天清隆内令,来华考察政治情况,为时3年。在此期间,曾潜入蒙古,物色同党,以为他日起事之助。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后,大院君李昰应被移居保定总督衙门,南部竟乔扮清吏夜潜督署与大院君相见,并摄其小照为凭。外务卿井上馨对其才干十分赏识,派为驻烟台领事,并传内命:“领事日常事务可由书记生处理,君则专留心政局,以大要上报。”南部莅职后,日以“改造”中国为念,多有日本“兴亚”志士寄足此间,往往彻夜密谈“支那改造”之策。及中法战争全面爆发,南部大为兴奋,说:“此时清廷无暇内顾,正起事之良机也。”(59)与南部相互应,驻天津领事原敬(1856-1921),此时也正与法国领事林椿(Paul Ristelhueber)暗中勾结,密议若法军大举进攻北京,日本决不袖手旁观,将协助法国领事馆人员撤至神户。(60)这不过是人们所熟知的几个例子,由此可见一斑。这些来自外务省的会员们,在他们履行职务时必然按政府的指令行事,是不会真的去践行兴亚会“日中提携”宣言的。
第二,军队系统的人员。会员中包括不少现役和退役军人,尤为值得注意。其中,既有位居要津的高级将领,也有执勤海上或于役中国大陆的中下级军官。如伊东佑亨(1843-1914),就很典型,他自从1868年投身日本海军,以舰为家,衽席波涛,几十年如一日,却要参加兴亚会,成为海外分部的会员,颇令人费解。其实不足为怪,因为日本发展海军的首要目标是打败北洋舰队,而兴亚会会员的身份正为他日后在中国沿海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试看伊东80年代以来的主要经历:1884年,以海军大佐任扶桑舰长,出没于中国东南沿海,视察中法之役的战况和战迹;1886年,以海军少将任常备小舰队司令官,率诸舰巡航于中国各港口之间;1889年,调任海军参谋本部,担任负责舰队编制、作战计划及谍报工作的第一局局长(61)兼海军大学校长;1892年,晋海军中将,转补横须贺镇守府司令官;1894年,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参加甲午之役。(62)由此不难看出,伊东之所以参加兴亚会,绝非率性之举,而是有着长远目标的。还有些军人会员属于三栖人物,即既有军职在身,又是外交官兼间谍。如井田让(1838-1889),本是陆军少将,却于70年代初派为驻福州领事,因为福州靠近台湾和琉球,而且有船政局和福州水师,在日本准备发兵侵台和吞并琉球的情势下,此处正是观察中国军事动向的理想地方。福岛九成(1842-1914),70年代初以陆军少佐奉派调查华南及台湾形势,为日本出兵台湾做准备。福岛在华南调查时,适与日本画家安田老山相遇,便装扮成安田的弟子,随其进入台湾。于是,他以写生为掩护,绘制了十分详细的台湾地图,为日军侵台发挥了重要作用。福岛也就以此被派为驻厦门领事。兴亚会成立后,受到明治政府高层的极大重视,从而吸引了不少军职人员纷纷参加。最奇特的事情莫过于一些军职在身的亲王,也“辱临吾会,赏列员名”(63),兴亚会诸人感到无尚光荣,共推他们为名誉会员。这些亲王贵为皇室懿亲,又担任军事要职,却屈尊参加这样一个所谓“民间组织”,确乎是不寻常的。如小松彰仁亲王(1846-1903),历任军事总裁、征夷大将军、近卫都督、近卫师团长等职。甲午战争期间任大本营参谋总长,后又亲任征清大总督开赴旅顺。北白川能久亲王(1847-1895),历任旅团长、师团长,晋陆军中将。甲午战争期间任近卫师团长,于1895年5月率部入侵台湾,纵兵肆虐,遭到抗日军民的猛烈抵抗,终因伤病不治而丧命。伏见贞爱亲王(1858-1923),早年投身军旅。晋陆军少将。甲午战争期间任步兵第四旅团长,参加进攻山东半岛及台湾之役。可见,看似一般的兴亚会其实并不简单,这些亲王们正是看上了兴亚会在日本推行大陆政策过程的价值和作用。
第三,情报系统的人员。《源流》称:“注意中国情报的搜集也是日本亚洲主义的重要活动方式。兴亚会的曾根俊虎就是—个情报人员,兴亚会曾囊括40余名情报人员为会员。”(64)表明《源流》的作者是看到了兴亚会搜集情报这一重要职能的,但却只将此视为一种“活动方式”,而没有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将其与兴亚会这个团体的性质相联系,以致得出来的认识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是非常令人惋惜的。其实,应该由此想到,搜集中国情报正是兴亚会的最主要的职能。还必须指出,兴亚会吸收桂太郎作为“创立员”也正是要加强这方面的职能。桂太郎(1847-1913),曾留学德国研究军队建制问题。1874年调入陆军省参谋局,任谍报提理。在他的建议下,日本开始建立派遣驻外公使馆武官制度,规定武官的职责:“在调查驻在国情况时,与其军事制度、战术相比,更注重了解其军事地理及军队之政治态度,并按以往在参谋科学习之方法,进行实地试验。此外,还应特别注意驻在国与其他国家之外交关系,并将其利害关系和实力强弱等情况呈报国内。”(65)1878年,日本参谋本部正式成立,由山县有朋任参谋部长,桂太郎出任管西局长,主要分管对华谍报工作。桂太郎上任伊始,就坚决执行山县“对清国兵制及实况的调查,应以缓急之际能够实地应用为目的”(66)的指示,规定从1879年起,遣华日谍要定期进行内地侦查旅行,并在中国多设常驻日谍据点。他还亲自到大陆实地考察,便装微服潜入中国,从华南到华北,特别是重点对京津地区进行调查,归国后起草了对华作战方策《邻邦兵备略》。安排桂太郎这样一位军方情报头子进入兴亚会,其用意不言而喻。兴亚会除吸纳大量外务省系统和军队系统的情报人员为会员外,还建立了通讯员制度。派到中国各地的通讯员,既有会员中的情报人员(如曾根俊虎、町田实一(67)等)和大陆浪人(如石川伍一(68)等),也有兴亚会所办支那语学校的优秀生,规定他们要“送回关于所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地理、兵要地志的详细情报”。(69)
由此看来,很难将兴亚会视同于单纯的民间组织,兴亚会的成员构成和经费来源便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它所宣扬的“中日提携”是否有值得肯定之处呢?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从兴亚会成立时起,它的宣言与行动背离的问题便明显地暴露出来。是时,日本刚吞并琉球不久,受到日本国内外正义舆论的谴责。如植木枝盛批评日本政府此举“残害人类自由之理”。王韬也揭露说:“日于琉球,入其国,擒其王,并其土地”,反“必欲掩其倾覆剪灭之迹”,“为掩耳盗铃计”。(70)而声称主张亚洲国家睦邻提携的兴亚会,对此不但不置一词,反为之辩解(71),不能不引起质疑。《循环日报》即刊文指出:“今日本无端而构衅台湾,蓄谋而歼灭琉球,则其(兴亚会)所谓睦邻者,盖可知已。即繁称博引,援古引今,欲维时局,其谁信之?”(72)不仅如此,以后凡遇有舆论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时,兴亚会总是出面为之洗刷。如1884年日本在朝鲜策动甲申政变后,上海《申报》报道有“今东洋肆无忌惮,掳王宫,杀大臣,挟虏国王、王妃”之语,亚细亚协会在报告中则指出“极怪极妄处”,并加以否认说:“总是梦中漫言,毫不与事实相涉。”(73)俨然成为日本当局的代言人,事事处处站在维护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立场上,它所表白的“睦邻”、“提携”、“合纵”等漂亮言词,能有多少真实可信的价值呢?
兴亚会成立后,东亚发生的头一件大事,就是中法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日本当局高度关注这场战争,战局的发展成为当时的焦点新闻。1883年和1884年的两年间,日本各报特设“中法警报”、“中法特报”等专栏,竞相报导中法战况。日本政府也倾其外交与军方的全力搜集有关这场战争的情报,以便确定对策,从中渔利。那么,兴亚会(亚细亚协会)在此期间做了些什么呢?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兴亚会密切配合日本政府的侵华方针,发动其会员积极行动起来。于是,许多被派到中国的会员都非常活跃。在北方:驻北京的榎本武扬与法国公使宝海(Frédléric Aibert Bourée)接触频繁,商讨日法联合的问题(74);原敬因通法语而被派到天津,与法国领事林椿暗通消息。在南方:驻上海的曾根俊虎支持以小泽豁郎为首的“福州组”,计划策动叛乱,并得到了以南部次郎为首的“芝罘组”的呼应;末广重恭(1849-1896)等人也西渡上海,创设东洋学馆,作为反清基地,以期有朝一日“龙吟虎啸而唤起风云骤聚于大陆”,成就英雄大业。(75)
与此同时,兴亚会的东京本部也没有闲着。当时,协会“役员”宫岛诚一郎与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笔谈底稿,尚有多篇保存下来,可供我们了解长期不被人知的外交内幕。其中,有两篇最值得注意:
第一篇,是1883年6月17日的笔谈。斯时,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德理固(Aethur Tricou)来华莅职,于6月6日抵达上海,8日与李鸿章开始谈判。日本政府对谈判的进展极度关心,希望谈判破裂,中法交战,以坐收渔翁之利。外务省先命潜伏在已回到北京的何如璋身边的协会“新列会员”井上陈政速探消息。(76)井上第一次报告称,李鸿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因原件存留太后宫中,“无从得其底稿”;第二次报告称,有人访何如璋问越南事,何谓:“吾闻似归和议。”(77)外务省因不得要领,示意宫岛招清黎庶昌,于是有了这次笔谈。宫岛先问:“法国公使于上海与李中堂开议否?”表明与井上报告中显示日本急于获知李鸿章和德理固谈判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黎答:“如法人决意吞并安南,置中国与不问,开仗必矣。若仍循照前议,两国和同保护,则在未定之天。”表示是否开仗要看谈判结果如何。此时,宫岛竟然不顾起码的礼仪,鼓动中国对法国开战,称:“贵邦与我,本属同洲。亚洲振不振之机于是乎决。余愿贵邦开仗,惟期必死保护安南而已。其间岁月期三年,则亚洲必生不测之活泼气力,如我小国亦在振作气中。”(78)笔谈时,副岛种臣(79)和长冈护美也都到场,且有插话,表示对中国同情和支持。由此可见日本对笔谈之重视及其居心所在了。
第二篇,是1885年1月6日的笔谈。1884年8月马江之役,福建海军全军覆没。日本误判形势,预测中国败局已定,这正是在朝鲜扩张势力的大好机会,便于12月4日策动了甲申政变,然令日本没有想到的是,政变却以失败而告终。如何处理善后,成为日本当局十分头疼的事。所以,笔谈必然要涉及朝鲜善后问题。笔谈中,黎庶昌信笔写道:“此次朝鲜之事似易了结,所关要者在以后之措置耳。贵国本拟朝鲜以独立而又越海驻兵,非朝人所心服。仆之私意,以为贵国以后应不干涉朝事。”宫岛立表赞同,写道:“了善后之事,特愿阁下与我政府谋,我辈始高枕。”黎始觉有些失言,又称:“此不过两人私谈,幸勿与外见则可。”事后,黎仍不放心,致书宫岛谓:“昨日笔谈,此不过我两人至好之私言,千万藏之于心,不示人为幸。”(80)然话已出口,悔之何及!黎视宫岛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无意中泄漏了国家的外交机密。这样,日本方面便摸到了中国的底,于是派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并签订《天津条约》,为日后日本出兵朝鲜留下了口实。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兴亚会是披着“民间组织”的外衣,事实上背后是由日本外务省直接掌控和主导,并有军方参与运作的一个机构。其主要活动方式和功能是搜集情报:(一)以高唱“睦邻”、“提携”、“合纵”等动听曲调为手段,联络中、朝等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从中得到日本政府所需要的情报。(二)兴亚会下设的“事业部”,主要负责对各国情报报告的搜集,并选派支那语学校的优秀生到各国去,作为通讯员,专门从事谍报活动。(三)兴亚会所办支那语学校,除本课外,另设别课,专收陆军教导团的下士官,以便培养侵华所需的军事、情报、汉语翻译等各方面的人才。所以,兴亚会并不简单,千万不要轻看了它,过分渲染它的“民间性”实是皮相之见,是要不得的。
注释:
①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29页。
②论者谓振亚社成立于1878年,非是。振亚社应成立于1877年春。见草间时福《兴亚会创立的历史》,兴亚会编《兴亚公报》第1辑,明治13年3月24日刊行,第4页;北泽正诚《祝文》,见亚细亚协会编《亚细亚协会报》第5篇,明治16年6月16日刊行,第2页。
③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33—134页。
④[日]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转引忻平:《近代日本佛教在华传教的主要基地——净土真宗东本愿寺上海别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⑤[日]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东京:原书房1968年版,第48页。
⑥戚其章:《甲午日谍秘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卷,第69—70页。
⑧戚其章:《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⑨[日]龟井胜一郎、宫川寅雄编:《明治文学全集38·冈仓天心集》,东京:筑摩书房1968年版,第120页。
⑩[日]植手通有编:《明治草创启蒙と反乱》,东京:社会评论社1990年版,第258、268—271页。
(11)[日]伊藤照雄:《ァジァと近代日本》,东京:社会评论社1990年版,第16页。
(12)[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0—31、86页。
(1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页。
(14)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页。
(15)《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8页。
(16)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41页。
(17)[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
(18)[日]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东京:原书房1933年版,第577—578页。
(19)王振坤、张颖:《日特祸华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谋略谍报活动史实》第1卷,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页。
(20)[日]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第91页。
(21)[日]平山岩彦等:《我们的回忆录》,《九州日日新闻》,1934年9月连载。见吴绳海、冯正宝译编《宗方小太郎与中日甲午战争》(未刊稿)。
(22)[日]上坂冬子著、巩长金译:《男装女谍川岛芳子传》,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23)[日]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第221、227页。
(24)[日]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502页。
(25)[日]苇津珍彦:《大ァヅァ主义と头山满》,东京:日本教文社1965年版,第25—26页。
(26)[日]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310页。
(27)赵军:《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03页。
(28)[日]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361页。
(29)[日]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491页。
(30)[日]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译:《日本政治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8—289页。
(31)[日]曾根俊虎著、范建明译:《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70页。
(32)[日]兴亚会编:《兴亚公报》第1辑,明治13年3月24日刊行,第4页。
(33)[日]亚细亚协会编:《亚细亚协会报告》第2集,明治13年4月1日刊行,第4页。
(34)[日]草间时福:《东洋连横论》,《邮电报知新闻》,明治12年11月19日。
(35)[日]兴亚会编:《兴亚公报》第2辑,明治13年4月1日刊行,第13—14页。
(36)[日]沪友会编:《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东京:兴学社1982年版,第42页。
(37)[日]霞山会编:《东亚同文会史》(昭和编),东京:平成15年,第28页;狭间直树:《东邦协会につぃて》,《初期ァヅァ主义につての史的考察》(5),《东亚》2001年12月号,第68—69页。
(38)[日]佐佐博雄:《日清战争と通译馆》,见东ァジァ近代史学会编《日清战争と东ァジァ世界の变容》下卷,ゅまに书房1997年版,第387页。
(39)[日]霞山会编:《东亚同文会史》(昭和编),第30页。
(40)[日]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958页。
(41)[日]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8页。
(42)[日]藤井志津枝:《甲午战争前日本大陆浪人的思想与行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印:《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5年,第451页。
(43)[日]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202页。
(44)[日]沪友会编:《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第41页。
(45)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36、134、132页。
(46)[日]兴亚会编:《兴亚会报告》第12集,明治13年11月15日刊行,第8页。
(47)[日]兴亚会编:《兴亚公报》第1辑,明治13年3月24日刊行,第1页。按:“正式成立”是指兴亚会举行成立会的时间。此前曾召开过一个筹备会,时间是在1880年2月13日。据《兴亚会假规则》载,“创立委员”(发起人)为15人,共推长冈护美为会长,渡边洪基为副会长,曾根俊虎、金子弥兵卫、草间时福三人为干事,桂太郎等10人为委员。(黑木彬文、鳟泽彰夫编:《亚兴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2卷,东京:不二出版,1993年,第254页)故《第三周年历届事迹》称:“吾会之创始,实明治13年(1880年)2月也。”(亚细亚协会编:《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编,明治16年2月16日刊行,第3页)此指筹备会召开的时间也。有论者则称:“1880年11月11日,兴亚会成立。”(《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33页)将兴亚会的成立时间后移了八、九个多月,不知所据为何?
(48)[日]亚细亚协会编:《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编,明治16年2月16日刊行,第2页。按:1883年1月3日,兴亚会召开议员会,决定将会名改为“亚细亚协会”。(黑木彬文:《兴亚会·亚细亚协会の活动と思想》,《亚兴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卷,第13页)到20日举行成立三周年大会时,始正式改名。
(49)[日]黑木彬文、鳟泽彰夫编:《亚兴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卷,第3页。
(50)“姚先生”,即姚文栋(1853-1929),字子樑,上海人。曾以直隶道员随黎庶昌赴日。著有《东槎杂著》、《东北边防论》等。
(51)[日]亚细亚协会编:《亚细亚协会报告》第6编,明治16年7月16日刊行,第38页。
(52)王振坤、张颖:《日特祸华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谋略谍报活动史实》第1卷,第18—19页。
(53)[日]黑木彬文、鳟泽彰夫编:《亚兴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卷,第19页。
(54)[日]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89—90页;下卷,第106页。
(55)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0卷,北平:1932年,第2页。
(56)[日]兴亚会编:《兴亚会报告》第24集,明治15年1月30日刊行,第3—4页。
(57)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东京:1938年,第149页。
(58)[日]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第542页。
(59)[日]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109—111页。
(60)[日]伊文成等主编:《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0页。
(61)[日]有贺传:《日本陆海军の情报机构とその活动》,东京:近代文艺社1994年版,第234页。
(62)[日]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707页。
(63)[日]亚细亚协会编:《亚细亚协会报告》第2编,明治16年3月16日刊行,第1页。
(64)《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37页。
(65)[日]铃木健二著、李苑译:《神秘的使者—武官》,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66)[日]小林一美:《明治期日本参谋本部の对外谍报活动》,见滕维藻等编《东ァジァ世界史探术》,东京:汲古书社1986年版,第392页。
(67)[日]町田实一(1842-1916),曾任海军大主计,长期在中国沿海一带从事侦察活动。后派为驻香港领事,兼管广州、汕头、琼州等处领馆事务。中法战争后调任驻汉口领事,对荒尾精所办汉口乐善堂的情报活动大力进行保护。
(68)[日]石川伍一(1866-1894),1884年来华学习汉语会话,并研究中国问题。1887年投奔汉口乐善堂,开始了在中国的间谍生涯。甲午战争期间潜伏天津被获处死,成为著名的“甲午日谍第一案”。
(69)[日]黑木彬文、鳟泽彰夫编:《亚兴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卷,第11页。
(70)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
(71)《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37页。
(72)[日]兴亚会编:《兴亚会报告》第12集,明治13年11月15日刊行,第8页。
(73)[日]亚细亚协会编:《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7编,明治18年3月25日刊行,第23、25页。
(74)[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00页。
(75)[日]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318—319页。
(76)[日]井上陈政(1862-1900),本姓楢原,幼时为井上家收养,改姓井上。1888年恢复楢原姓氏。井上成为亚细亚协会的“新列会员”,是在1883年。(亚细亚协会编:《亚细亚协会第二年报》,明治18年6月25日刊行,第15页。)
(77)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24—25页。
(78)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第27页。
(79)笔谈的整理者将“副岛”误为“副鸣”,兹予改正。盖“副岛”之“岛”,日人或写作“嵨”,因未细加辨认而误识为“鸣”。
(80)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析》,第36—37页。
标签:兴亚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朝鲜经济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亚细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