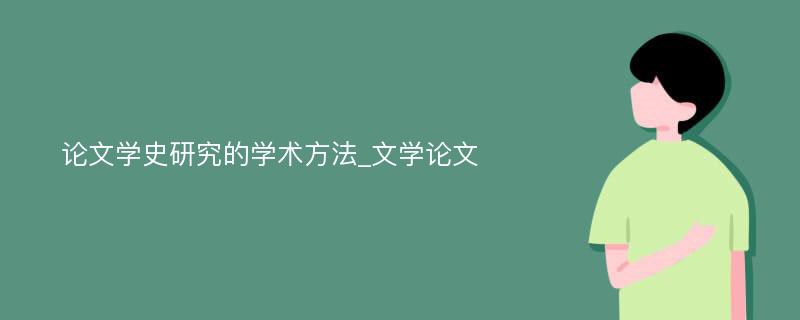
论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学术论文,方法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0)04-0001-07
世纪之交,“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此伏彼起。它既反映着学术界对以往文学史著作因受时代思潮和思想认识局限而不能完全准确客观地描述中国文学发展的真实历史的不满,也反映着学术界企图建立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复兴民族文化要求的文学史学科新体系的努力。然而,究竟如何重写文学史,学者们见仁见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有的认为应该有必要重新接纳过去被排斥被忽略的流派和作品,重新探讨文学与政治之外的其他关系,以期重新解释文学史的发展规律[1];有的认为应该建立多元的文学发展观,不要千篇一律,可以大家都来写,写出各种不同文学史[2];有的认为文学发展过程与人性的发展过程是同步的,并由此写出了新的文学史[3]。笔者也曾呼吁最根本的是要转换文学观念,认真清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以此作为建构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史体系的理论基础,改变过去那种以西方文学理论和观念硬套中国文学事实的做法,并尝试着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4]。凡此种种,都是试图从思想观念的转换或学术视点的改变入手来推动文学史的研究。毫无疑问,思想观念的转换是最根本的转换,学术视点的改变也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仅有思想观念的转换或学术视点的改变是不够的,必须辅之以正确的学术方法,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正确的方法甚至能够帮助我们克服思想观念上和学术视点上的某些局限。本文之所以提出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方法来讨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一
文学史研究应该运用怎样的学术方法?这样提出问题也许会受到责难:难道文学史研究还需要有统一的学术方法?方法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什么方法有利于解决问题就用什么方法,难道这还有疑问吗?
这样的责难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的确,学术方法只是解决学术问题的一种手段,学术研究一般可以利用一切有效的方法。然而,就具体学科门类来说,事情就绝非如此简单。为了使我们的研究符合这一学科的特点,科学地揭示这一学科的客观规律,就必须采用适合这一学科本质特点的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可的学术方法,不然,其研究就不可能揭示这一学科的规律,其结论也就没有价值。例如,自然科学普遍采用实验的方法,任何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大量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如果我们不进行严肃认真的科学实验,就想得出一个为学术界所认可的自然科学结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样,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学科,也不是任何方法都可以采用,都能够得出科学结论来的。例如历史学、考古学就是这样的学科。考古学必须以地下出土的文物为依据,没有文物依据的所谓考古学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历史学必须以历史文献和文物即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没有历史事实依据的所谓历史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因此,这些学科不能脱离实证的方法,不能离开真凭实据而仅凭想象或仅仅依据逻辑推理来做结论。
应该承认,社会科学领域对方法问题缺少应有的重视,一些本应强调实证研究的学科却充斥着太多的自由想象,甚至把它变成了对现实的一种图解,或者当做了可以按照自己意志任意打扮的“灰姑娘”。这不仅不利于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而且丧失了这些学科在人们心目中的应有的地位。
在一桩历史旧案值得重提。20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和金岳霖审读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分别写出了审查报告。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寅恪和作为哲学家的金岳霖都对冯著表示了肯定,又都对当时的不良学风和不正确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陈寅恪指出: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所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5](P1-2)
陈寅恪主张设身处地了解古人,在“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批评其学说;不赞成用今天的思想去解说古人,以为这样就会流于“穿凿傅会”。这里既有态度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所谓方法,主要两种:一种是对古代材料的细致考辨和合理运用,如冯著对伪书的考辨和利用;一种是没有材料依据的“呼卢喝雉”和随意改移,如“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之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5](P3)。
金岳霖则在《审查报告》中肯定冯著的同时批评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牵强附会”,他说:
我们可以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来写中国哲学史,我们也可以不根据任何一种主张而仅以普通哲学形式来写中国哲学史。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在工商实业那样发达的美国,竞争是生活的常态,多数人民不免以勤作为生命,以变迁为进步,以一件事体之完了为成功,而思想与汽车一样也就是后来居上。胡先生既有此成见,所以注重效果,既注重效果,则经他的眼光看来,乐天安命的人难免变成一种达观的废物。对于他所最得意的思想,让他们保存古色,他总觉得不行,一定要把他们安插到近代学说里面,他才觉得舒服。同时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哲学既离不了成见,若再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所以写出来的书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6](P6-7)
如果说陈寅恪以史学家的诚实和严谨论证了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史实与史识的关系,那么,金岳霖则以哲学家的机智和敏锐指出了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的区别。“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这一概括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哲学是人们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任何哲学都应该有对于世界的基本看法,否则就不成其为哲学,因此“哲学要成见”。然而,哲学史却不一样,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哲学,哲学史要研究这些哲学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研究这些哲学思想的相互联系及其影响,它需要依据历史的事实,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它需要“了解之同情”,而不要“成见”,因为成见会造成“牵强附会”,从而歪曲哲学的历史。
陈寅恪和金岳霖的《审查报告》不仅提出了哲学史研究的态度问题,也提出了哲学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从态度上讲,“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从方法上说,“哲学要成见”,当然可以运用演绎的方法,充分展开自己的思维逻辑;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必须运用归纳的方法,实证的方法,在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前人的思想,科学地评价其价值和得失。
当然,这种方法上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并且是就主体而言的。其实,哲学既然是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就不能排斥归纳的方法。同样,哲学史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研究者主观思想即“成见”的介入,否则将无法开展研究。所谓不要成见,不是说研究者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而是说研究者不要以自己的思想去歪曲改造古人的思想,要尽可能地以理解同情的态度去研究古人的思想。金岳霖便指出:“冯先生的态度也是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但他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成见他当然是有的,主见他当然也是有的。据个人所知道的,冯先生的思想倾向于实在主义;但他没有以实在主义的观点去批评中国固有的哲学。因其如此,他对于古人的思想虽未必赞成,而竟能如陈先生所云:‘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同情于一种学说与赞成那一种学说,根本是两回事。冯先生对于儒家对于丧礼与祭礼之理论似乎有十二分的同情,至于赞成与否就不敢说了。”[6](P7)显然,主张“哲学史不要成见”绝不是说哲学史家不要有思想,而是说哲学史研究不能像哲学研究那样自由地表达研究者自己的思想,而应该以同情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正确的方法去解说和批评前人的思想,而所谓正确的方法主要是建立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的历史实证的方法。这种方法,比较接近梁启超所说的清儒的治学方法。梁启超说:
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而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7](P56~57)
梁氏所总结的清儒的治学方法,正是朴学考据和历史实证的方法,是历史研究的正确而有效的方法。而无论是哲学史还是文学史研究,都属于是历史研究的范畴,当然也应采用这样的方法。
二
陈寅恪、金岳霖对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认识,同样适合于文学和文学史研究。金氏“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的思想,若作泛义的理解,完全可以转换为“文学要成见,而文学史不要成见”的理论表述。
文学是人类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感受生活和认识生活的一种方式。就个体而言,每个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都不会完全一样,这样便必然形成他们对于生活的“成见”。同时,生活的无比丰富性使得任何作家都不可能穷尽生活的底蕴,因此他们对生活的反映只能是他们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与认识,具有独创性与唯一性。正因为如此,同样的生活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一定是不同的面貌,作家们总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去演绎生活,表达情感。这正是“文学要成见”的最充分的理由。
也许文学创作具有某种特殊性。即使在文学研究领域,“文学要成见”也仍然是成立的。如果不作细致区分,纯粹的文学研究大体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或曰文学鉴赏)两个方面。而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文学批评,它们与文学创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文学理论应该是对文学创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然而由于文学创作的独创性与唯一性不易把握以及文学问题必须放在人类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整体世界中去理解,因而文学理论常常需要借鉴已有的思想成果特别是现成的哲学体系来构建自身的体系框架,这便使得文学理论无法摆脱现成的思想束缚,所采用的方法常常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思想的演绎。至于文学批评或文学鉴赏,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审美的,它都只是读者对文本的一种解读,都是批评者或鉴赏者主观意志和情绪对文本的一种观照,在本质上是个人化的,因此,它不仅需要成见,事实上也不可能排除成见。
文学史研究则不同。文学史关注的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文学事实,以及这些事实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还是一个流派,一种思潮,都只有弄清楚它的全部事实真相、它的来龙去脉后,才能对它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判断,也即陈寅恪所说对古人“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对作者没有“了解之同情”,就不易评论其是非得失。这里需要的首先不是“成见”,而是扎扎实实的收集材料、辨证真伪、考镜源流的考据和实证工作,然后才能从具体翔实的历史事实中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由于文学史研究就其本质而言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因此它必须采用历史学的学术方法。中国自古就强调史家要有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而作为历史学的基础的却是史料。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便指出:“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文史通义·答客问》)梁启超则进一步指出:“史实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8](P44)文学史研究也不例外,它的基础不在“成见”,而在“史料”,我们关于文学发展史的一切结论,都必须建立在真实而充分的文学史料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不是严格意义的文学史研究。梁启超认为:“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史料,因其所致力者在瞑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8](P43)而就方法而言,重史料必重实证,因为只有实证才能对史料加以辨析;重史料必须重归纳,因为只有归纳才能让纷繁的史料具有统序和条理,从而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史料的意义与价值。
应该承认,胡适也是一个非常重视实证研究的学者,从根本上说,他是反对用“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的方法来进行哲学史研究的。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说:
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部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9](P25)。
显然,胡适所强强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是实证的方法、归纳的方法,而不是推理的方法、演绎的方法,也就是说他并不赞成“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因为以一种“成见”去推理、演绎中国哲学史,它只能是这个哲学家自己的哲学,而不会是符合中国哲学发展实际的中国哲学史。同样的道理,研究中国文学史,也应该运用实证和归纳的方法,在“述学”的基础上“明变”、“求因”、“评判”,只有这样,才能客观、真实、准确地描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各种文学现象。如果先有“成见”在胸,按照“成见”去演绎推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随意寻找自己需要的例证,那么,这样的文学史其实并不是中国文学史,而是研究者自己所理解的中国文学,也即今人所说的“学者作家化”的副产品。
既然胡适与金岳霖在哲学史研究方法的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什么会受到金岳霖的批评呢?这既与胡适在学术方法的主张上存在缺陷有关,也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述史实和所作评判多与金氏意见不合有关。后一个问题牵涉面较广,这里不予评说,只重点谈谈胡适所提倡的学术方法。
在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同时,胡适还发表了《实验主义》、《杜威先生与中国》、《少年中国之精神》、《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文,系统论述了他对学术方法的主张。他提倡学术研究要用“科学方法”,而他所说的“科学方法”则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加清儒的朴学的方法。杜威的思想方法分五步:“(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出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含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10](P94)而清儒的朴学方法,“概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11](P182)相当于杜威五步法中的第三、第五两步。按胡适的说法,杜威的方法是“历史的方法”,“实验的方法”,清儒的方法是“考据的方法”,“归纳的方法”,它们的共同点是“注重事实”,“注重假设”,“注重证实”[12](P6)。因此,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学术方法应该说是比较接近历史实证的学术方法的。然而,历史实证方法首先要求有对于基本事实的尽可能全面的收集和细致考辨,而“大胆的假设”并没有预设这个前提,如果假设者没有扎实的材料功夫作为基础,而将大胆假设直接作为治学方法的第一步,则有可能会影响甚至破坏第二步“小心的求证”,因为“假设”常常是一种“成见”或者很容易被成见所左右,有了成见,就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往往只看到对假设有利的证据而忽视不利的证据,对证据的选择和运用就难免出现偏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便暴露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学术方法所存在的缺陷。
文学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一样,同样需要全面收集材料,细心考订真伪,努力探索源流,公正评判得失,尽量避免因成见的干扰而曲解历史,轩轾失当。胡适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就有不少“大胆的假设”,例如他假设“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13](P106),“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14](P16),就不完全是对中国文学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而主要是一种“成见”。因为这种假设是在他还没有充分研究中国文学史实的1916年初就形成的[13](P106)。即使他后来按照这种假设写出的《白话文学史》也只能说明中国文学的部分事实,并不能说明全部事实。陈平原先生对此有十分公正的评论,他说:“从一个文学革命倡导者转为文学史家,胡适的优点是有成见,缺点则是太有成见。倘若只是以史为鉴,胡适的文学史知识绰绰有余,也只以支撑其提倡白话文学之主张。可作为一个史家,胡适抱定‘白话正宗’说,闲置其终生信仰的‘历史的眼光’,将一部中国文学史简化为‘古文文学的末路史’和‘白话文学的发达史’,其牵强附会之处,甚至远比《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多。即便如此,胡适的文学史著仍然具有某种典范意义,因其毕竟提出了一套崭新的研究思路。”[15](P227)
三
相对于中国传统国学研究而言,胡适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确是一套新的研究思路,他很顺利地将西方引进的文学观念和思想方法与中国传统思想方法相衔接,其文学史著具有思想鲜明、条理清楚、线索明晰、统系严整的特色,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因而后来的文学史家都自觉不自觉地以胡适的文学史著为典范。然而,正如陈寅恪批评某些中国哲学史著“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一样,中国文学史著愈整饬,愈纯粹,离中国文学发展的史实也就愈远。因为不仅中国文学观念与西方文学观念颇不一致,而且中国文学观念自身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国人对人文科学的整体把握方式更造成了文学现象的纷繁复杂。这些情况,胡适及后来的文学史家们当然清楚,然而,为了改变中国人文科学长期混沌的局面,为了与西方学术接轨,为了用文学革命推动文化革命,他们仍然选择了用西方的成见来解说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思路,选择了以演绎和推理为主的学术方法。
应该承认,用胡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史存在不少问题,他的文学史著并不能客观反映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对此,学术界早有认识。例如,在胡适《白话文学史》风行的30年代末,钱基博在国立师范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就不用胡适的观点和体系,而是自己动手编写符合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中国文学史》。50年代中国大陆批判胡适,撇开政治因素不谈,学者们对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多是击中要害的。如游国恩批评胡适把文学形式看得太重[16];余冠英指出胡适的文学史研究有五方面问题;一是割截历史,二是抹煞事实,三是隐蔽精华,四是搬运糟粕,五是捏造或歪曲公例[17];王瑶更看出胡适文学史研究的内在矛盾,指出《白话文学史》从方法上“可以说是标本的用他自己的理论来解释作品”[18](P81)。
尽管人们看到了胡适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从思想到方法的毛病,然而在实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还是自觉不自觉重复着胡适的学术方法。就在批判胡适最为激烈的50年代,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分别编写出了自认为最具革命性的中国文学史,而这些文学史著作不过是把胡适的“古文文学”与“白话文学”的斗争史改换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把“文字工具”的形式区分转变为“人民性”的价值判定。而从方法上看,二者并无根本的区别,后者只不过是用一种新的“成见”取代了前者的旧的“成见”。按照胡适的成见,楚辞、汉赋都进不了中国文学史,李白、杜甫文学成就也不算高;按照新的成见,“汉代‘铺采摛文’的大赋,六朝色情唯美的宫廷文学,明代后期的才子佳人小说”都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品”,应该排除在中国优秀文学遗产之外[19](P10~11)。这些结论,并不是在详细占有原始材料,悉心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全部文学现象与文学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的,而是按照事先已有的“成见”演绎出来的。所以严格地说,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的文学史的研究,而是文学的研究,或者说是一种以史的面孔出现的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并且是有着很深成见的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
当然,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并不赞成用一种成见来演绎中国文学发展的研究方法,他们用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成果,昭示着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途径,给我们以巨大的学术方法的启迪。例如,早在30年代,朱自清就曾呼吁:
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20](P3)。
朱先生所论虽然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但其基本思想无疑适合于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中国文学史从来就密不可分,其基本学术方法当然也是相通的。朱自清按照这一思想方法撰写的《诗言志辨》也起到了这一学术方法的示范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值得学习和借鉴。
再如,陆侃如自1937年至1947年花了10年时间初步完成后来仍不断修改补充定稿的力作《中古文学系年》,也是不同于以成见来演绎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研究的成功范例,在学术方法上同样给我们以启迪。陆氏在《中古文学系年·序例》中说:
文学史的目的,在鉴古以知今。要达到这目的,我们不仅要明白文学史上的“然”,更要知道“所以然”。如以树木为喻,“然”好比表面上的青枝绿叶,“所以然”好比地底下的盘根错节。我们必须掘开泥土,方能洞悉底蕴。所以我认为文学史的工作应包含三个步骤:
第一是朴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等。这是初步的准备。
第二是史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社会经济情形,必须完全弄清楚。这是进一步的工作。
第三是美学的工作——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这是最后一步。三者具备,方能写成一部完美的文学史。
我自己很早就想研究文学史,可是经过若干年的探索之后,深深感到过去走过的路都不十分对。朴学的工作不精确,史学的工作完全没做。因此,对于“然”既仅一知半解,对于“所以然”更茫然无知。于是我立下志愿,打算对中古一段好好地探索一下。[21](P1)
这一段话既是陆先生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方法的理论归纳。1931年,陆侃如和冯沅君出版了他们合著的《中国诗史》,他在《史古文学系年·序例》中所说的“若干年的探索”,“深深感到过去走过的路都不十分对”,自然也包括这部分体文学史在内。其不对就在于“朴学的工作既不精确,史学的工作完全没做”。这里既有思想观念的问题,更有学术方法的问题。陆侃如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他更赞成文学史研究首先必须做好朴学的工作和史学的工作,然后才能做好美学的工作。所谓朴学的工作、史学的工作,从学术方法上说,就是资料考据的方法和历史实证的方法,这应该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然后才是文学的方法,美学的方法,即分析的方法,演绎的方法。
朱自清和陆侃如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方法的思想,与陈寅恪和金岳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方法的思想可谓不谋而合,说明他们都意识到学术方法与研究结论的科学性有着紧密的联系。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汗牛充栋,截至1991年,共出版各类文学史著作800余种[22],真正做好了朴学的工作和史学的工作的文学史著作,可以说凤毛麟角,而大量的是用成见演绎甚至靠稗贩转抄而成的作品。这一现象也说明了规范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方法是重要而迫切的。
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必须转换思想观念,改善学术方法,才能开创新局面,获得新发展,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共识。一些学者正循着朱自清、陆侃如的思路,运用考据的和实证的方法,扎扎实实地做着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我们之所以提倡这样的文学史研究,是因为以前的文学史研究中有太多的成见,太多的想象,太多的牵强附会,而较为缺少的正是朴学考据和历史实证的功夫。我们之所以提倡文学史研究应该采用考据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并不是想把演绎的方法和分析的方法逐出文学史研究领域。事实上,文学史研究毕竟不是一般的历史研究,而是对于文学的历史研究,因而文学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当我们做好了朴学的工作和史学的工作以后,文学的工作和美学的工作就会提上议事日程。只是由于中国文学史研究现在仍然没能摆脱西方传来的成见的束缚,比较忽视资料的收集考辨,却有着太多的想象和过于大胆的假设,所以必须在一段时间内提倡历史实证的学术方法,以便为建设真正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2000-04-08
标签:文学论文; 胡适论文; 陈寅恪论文; 金岳霖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白话文学史论文; 文化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读书论文; 哲学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