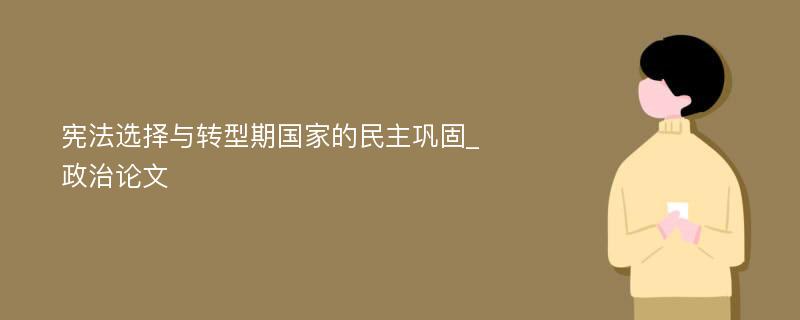
转型国家的宪制选择与民主巩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亨廷顿所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逐渐展开,南欧、拉美、非洲、东亚等地区的专制与威权政体纷纷发生转型,由此诞生了许多新生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有一些经过几十年的运转而逐渐巩固下来,例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韩国等;而另一些则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甚至发生民主崩溃而重新返回威权政体,例如泰国、伊朗、尼加拉瓜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政治经济发生根本性变动,大批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国家转向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这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世界性政治事件之一,不仅对世界政治格局变动造成极大影响,而且急剧震撼着学者们的思维头脑。许多西方的政治学家鉴于以往的历史事实,以一种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向,开始思考这些国家民主巩固的前景,反思和总结以往民主转型失败与民主巩固的教训与经验。以Juan J.Linz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总结转型国家民主巩固的经验与民主崩溃的教训,考察不同宪制形式(总统制、议会制、混合制)的选择与民主巩固的关系,并促成了一场关于宪制形式与民主巩固的学术争论。实际上,这场学术争论到今天仍在继续,关于宪制形式与民主巩固的话题并未结束。
对这样一个宏大主题的学术争论,按照学术观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以Linz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不同宪制形式(总统制、议会制、混合制)的内在制度特征使得它们在民主巩固方面表现差异,民主转型之后不同宪制形式的选择决定了民主巩固的不同结果。而另一些学者则驳斥了宪制形式与民主巩固的关联,他们认为,转型国家民主崩溃的原因并不在于总统制和议会制、混合制的制度差异,而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条件与经济条件不足以维持稳定的民主制度,跟宪政体制的选择无关。这显然是两种关于制度的内源型与外源型看法。而在这两个学术阵营的内部,又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在内源型观点阵营内部,围绕着宪制形式,以Linz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总统制不利于民主的巩固,容易导致社会与政治动荡,而议会制则有助于民主的巩固;以DonaldL.Horowitz为代表的学者则为总统制辩护,认为总统制框架与适当的制度安排相结合,同样能够实现民主的巩固,不适当地采用议会制也会导致民主崩溃,相关配套制度的选择尤其重要;以Giovanni Sartori为代表的学者则扬弃总统制与议会制的优点与不足,提出在纯粹总统制与纯粹议会制之外,采取某种混合体制来保障民主的巩固与稳定。而在外源型观点阵营内部,围绕着民主巩固的影响因素,则又有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国家规模、地理位置等侧重点的不同,最近的观点则是强调历史政治遗产的后续影响,即认为总统制与议会制民主巩固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不同的前民主政治遗产,而不是宪制形式的制度差异。毫无疑问,民主巩固这样一个宏大主题,它的影响因素绝不是单一的,而这场关于宪制形式与民主巩固的学术争论,对于我们开阔研究视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总统制、议会制与混合制
按照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划分标准,宪政体制有三种基本形式,即总统制、议会制,以及综合了这两种体制某些要素的混合制。① 每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宪政体制虽然各有特色,但其基本要素都可以归结到这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在制度安排上存在明显差异,在政治过程中也有很大不同。
议会制是英国在长期的民主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政府形式,议会主权成为许多国家民主革命的目标之一。它的基本特征是:(1)议会是唯一的合法性机构,它由选民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2)而政府的组成由议会决定,其权威完全依赖于议会的授权;(3)当议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时,政府就要辞职,或者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由新议会决定政府的去留;(4)政府的行政权实施基本服从于议会的立法权;(5)议会制的国家元首不兼任政府首脑,不直接掌握行政大权,而且也很难与首相或总理竞争行政权。
总统制于18世纪末由美国率先垂范,后被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的许多国家所效仿,它的基本特征是:(1)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同时兼任政府首脑,掌握行政大权;(2)议会与总统分别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总统的权威直接来源于选民授权,而与议会无关;(3)议会虽然对总统有弹劾之权,但很少使用或很少成功使用;(4)议会的立法权实施与总统的行政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
而混合制则以戴高乐所建立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为代表,它的基本特征是:(1)总统与总理同时存在,总统是国家元首,总理是政府首脑;(2)总统与总理都具有相应的统治权力,总统不仅是象征性角色,而且是具有实权的政治领袖;(3)总统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不依赖议会任命;总理由总统任命,但需要议会的信任与支持;(4)总统可以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但需要总理同意与支持;(5)总统拥有紧急状态权力与全民公决权力,这使其可以越过议会进行统治。②
那么,面对这些不同形式的宪政体制,新生的民主国家应该选择哪一类型呢?换言之,哪一种宪政体制更加有利于民主的巩固呢?
观点之一:议会制推动民主巩固,总统制破坏民主巩固
自1990年开始,Juan J.Linz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宪制形式与民主巩固的关系,③ 并引发了关于总统制与议会制何者更有利于民主巩固的大讨论。Linz认为总统制不利于民主的巩固,而议会制更能有效地化解民主政治的体制性危机,保持民主政治的持续存在;那些政治稳定的民主国家,绝大多数都采取了议会制的宪制形式;“这一结论尤其适用于具有深刻政治分歧和众多政党的国家”。④ 这一观点既引起了一些争议,也被许多学者所认同,成为这一场学术争论的主流观点。
Linz认为,总统制之所以不利于民主巩固,原因在于其内部的制度安排,其中最核心的有两个,即总统由单独选举产生以及总统的固定任期。所谓单独选举产生,是指总统的选举与议会的选举互不干涉,各自单独进行,总统与议会都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它们因此而具有各自独立的合法性来源,或称为双重民主合法性(dual democratic legitimacy)。所谓任期固定,是指总统的任职期限一般在宪法中都有明确规定,任职结束后由新选举产生的总统继任。一般而言,总统制下的总统任职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对总统的弹劾机制很少能够成功发挥效力,总统一般都能完成任期,这又被称作总统的任职刚性(rigidity)。许多学者认为,在实行了总统制的转型国家,正是这两个制度安排造成了政治过程中的严重后果,导致了民主政治的不稳定与社会动荡。这些严重后果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
第一,总统单独选举造成的零和博弈与社会分裂。总统由选民单独选举产生,获胜者即可掌握行政大权,而不必须考虑其余政治力量的态度,这使民主政治成为一种零和博弈与胜者通取。总统将自己视为人民意志的唯一代表,将反对者视为狭隘利益的代表,甚至对反对者施以政治压制,反对者则只能以失败者的身份游离于行政权力之外。总统的任职刚性使得这一情形更加强化,胜败二分的局面延续至整个总统任期而很难改变。总统制的胜者通取与零和博弈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与社会分裂,总统与反对党之间、总统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很可能造成激烈的政治冲突,甚至形成社会的极化分裂,威胁到民主体制本身的存在。而且,“总统制缺少一个君主或‘共和国总统’来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调节力量,这使得这一体制缺乏弹性和缺少限制权力的一种手段。”⑤ 特别是在一个面临严峻的民主巩固任务、并且存在极化多党体制的转型国家,边缘性极端主义政党的政治影响力会因此而被放大许多,极易造成社会的极化分裂。
第二,双重合法性引发的政治僵局。在总统制国家,由于总统与议会相互独立,并且具有一定的相互制约权力,两者在某些议题上一旦持有不同意见,很可能演化为两者之间的政治僵局。这种情况尤其发生于总统职位与议会分别由两个政党掌握的情形之下。面对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政治僵局,宪法提供的解决程序往往过于复杂或者流于教条主义,在实践中难以发挥效用。一旦政治僵局演化为政治争端,双方就有可能诉诸于人民合法性。但是,由于总统与议会都有独立的合法性来源,“没有民主原则来解决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关于谁是人民意志真正代表的争执。”⑥ 特别是对于刚刚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而言,民主体制尚未巩固,这一政治争端很可能要通过基于社会分裂的暴力冲突来解决。在一些地区发展失衡的发展中国家,议会与总统往往相互指责为寡头和地方贵族利益代表,机构之间的争执就有可能演化为意识形态的争论以至爆炸性的社会或政治斗争。
第三,行政权的任职刚性及对政治分裂的强化。由于总统任期固定,具有刚性,不能根据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动而改变任职人选,因而其统治过程很难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动而做出灵活调整。“体制转型与巩固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得总统制远比议会制问题多多,因为议会制可以对变化的环境做出灵活回应。”⑦ 一旦围绕着现任总统的任职产生分歧,总统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很容易产生冲突,进而造成政治与社会的分裂。当这种敌对的情绪再也难以和平方式弥合时,军队的政治性介入也是很有可能的。议会制下的政府危机在总统制下则可能演化为完全的体制危机,由此引发的社会分裂与冲突也很难抚平。
第四,任期任次限制的政治后果。总统制国家一般都要对总统的任职时间和任职次数加以明确规定,但这种任期任次的规定也限制了总统实现竞选承诺的能力,特别是就那些在短期内难以完成的社会变革计划而言。为了在有限任期内兑现竞选承诺或者实现自己的计划,总统往往会力推某些不成熟的政策,不顾反对派的异议而草率执行。这不仅可能造成国家财政资金的挥霍,而且可能造成国家的政治、社会分裂。一些雄心勃勃的总统还会以政策连续性的名义,试图修改宪法对总统任期任次的限制。
与以上总统制的弊端相比,议会制则很少出现这种情形,原因在于议会制内在的制度安排,即行政权产生于议会多数。首先,议会制更多体现为政治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议会制下的政府依赖于议会的信任和多数支持,为了建立一种稳定一致的绝对多数,议会制不可避免地具有协合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的特色。因此,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非常注重政治的协商与权力的共享。反对党或反对派怀有一种分享权力的期望和预期,因而基本不对体制本身造成危害,能够保证民主体制本身的稳定。
其次,议会制也没有总统制的双重合法性与政府任职刚性问题。政府内阁的合法性来自于议会,议会中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可以使得政府随时更替。议会制虽然表面上看,政府更迭频繁,但是这种灵活性却有助于防止政府危机演化为宪制危机。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尽管政府更迭频繁,但是执政党与执政联盟、主要阁员往往能够保持稳定性。
再次,议会制也不会出现任期任次限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议会制具有变更政府的灵活性,因此对政府首脑的任期和任次限制并不太敏感,首相/总理往往可以多次执政。政府首脑也不会过于贪恋权位,因为其本人、其政党或执政联盟都有再次进入行政权力的机会。
总体来看,以Linz为代表的总统制反对者认为:总统制缺乏一种政治联合的制度动力,而内含着走向政治分裂的制度逻辑。用Arend Lijphart的术语来讲,总统制容易导向多数民主,而缺乏一种共识民主的基础。“尽管权力分立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共识民主的形成,但是总统的大众选举与行政权的高度集中却强力促成了多数民主特征。”⑧ 对许多转型国家而言,共识民主是非常必要的。许多国家存在族群、种族、宗教之间的裂痕,以及由内战、独裁、社会经济发展不一致而造成的政治上的差异性。对这些国家而言,民主转型的成功与民主的巩固依赖于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妥协与共识达成。而议会制民主的制度安排内含着对于政治联合的激励,从而有助于减轻政治分裂的现象,有助于民主体制的生存。因此,议会制是一个优于总统制的选择。
在现实制度的设计上,议会制的支持者也非常重视具体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例如,Lijphart偏爱一种与比例代表制相结合的议会制民主。首先,他认为议会制-比例代表制相比于其它各种体制类型更加有助于增加体制的包容性,有助于政治、社会力量之间的调和与妥协。议会制具有强烈的共识民主倾向,比例代表制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其次,议会制——比例代表制也有助于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经济发展更需要一种稳定持续的温和政策,这是具有中庸倾向的比例代表制和联合政府所易于提供的。议会制很可能无法短期做出决策,甚至因为相互争吵而显得毫无效率,但由于建立在广泛争议与协商的基础上,却可以保证长期成功执行,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实际发展。
Lijphart设计了一个综合性评价体系,包含公共秩序维持能力、公民参与水平、代表性、回应性(responsiveness)、经济平等(economic equality)和宏观经济管理(macroeconomic management)几个指标,从民主质量(quality of democracy)与民主效能(effectiveness of democracy)两个角度来比较各种类型的民主制度。⑨ 通过相应的数据比较,Lijphart发现,在各项指标方面,议会制——比例代表制绝大多数都要优于其它三种体制,⑩ 特别是在代表性、保护少数派利益、投票率和失业控制等方面。因此,“与其它选项相比,议会制——比例代表制民主形式在容纳族群分歧方面显然具有优势,并且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略胜一筹。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基于统治效能考虑应该摒弃议会制——比例代表制的观点实难可信。如果忽略了这一民主模式,新生民主国家的政制设计者将使其自身及其国家深受损害。”(11)
观点之二:总统制同样可以实现民主巩固
Linz关于总统制弊端的观点一经提出,便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异议。他们反对Linz关于议会制更加有利于民主巩固而总统制则不利于民主巩固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总统制并不缺少政治联合的情形,有些学者则结合具体的配套制度来探讨总统制对于民主巩固的可行性。
José Antonio Cheibub以总统立法权力的大小、各政党政策立场的差异性程度以及各政党的议会议席分布为指标来考察总统制下联合政府与少数派政府的产生。他发现,如果宪法赋予总统的立法权力较小,总统不能有效控制立法进程,总统政党与各政党政策立场差异性较大,同时总统政党未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优势,那么总统将很可能通过提供政府职位的方式以换取其余政党的政策支持,联合政府就会形成。反之,如果各个政党之间的政策立场接近一致,那么总统将独揽政府职位,而将政策的提案付诸于其它政党,这很可能会出现少数派政府。尽管总统制国家少数派政府的出现几率远多于议会制国家,但是联合政府的出现也并不是异化状态。此外,联合政府的缺乏并不意味着各政党之间政治合作的缺乏,理解这一点必须明确政府联盟与立法联盟的区分。政治行动者的目的往往有两个,即一定的政府职位以及一定的政策法案。联合政府是以共享政府职位的形式出现的,立法联盟则是以共同的政策法案为基础的。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总统制缺乏政府联盟/联合政府,立法联盟却也是经常出现的。那种认为总统制缺乏政治联合的观点,是过于强调了职位共享,而忽视了政策联盟。而且,许多少数派政府在立法有效性(effectiveness)方面,并不弱于联合政府。数据表明,政府状态(少数派或多数派)与政府法案获得批准的比率无关。“政府状态——无论是一党政府或多党政府,无论是否持有议会多数席位——对民主生存的可能性并无影响。”(12)
正是由于这种政治联合的存在,许多总统制国家避免了社会分裂,而出现了政治缓和的情况。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巴西都曾呈现调和政治的景象,作为总统制发源地的美国其社会冲突也非常和缓。许多学者将这些案例都视为异态或例外,这实际上是将总统制国家的成功归结为其它因素,而将其失败归结为总统制本身。Donald L.Horowitz认为这是一种扭曲的见解。与此相对照,议会制同样可能出现零和博弈的情形。尼日利亚在民族独立初期采取了议会制形式,结果,北方一些种族却试图通过控制议会多数席位而剥夺其他种族的政治权力。这既是一种零和博弈,也是一种任职刚性,政府可以利用自己政党的议会多数席位而长期在职,“固定任期的总统制可能引发的统治危机,灵活任期的议会制同样可以发生。”(13)
Horowitz认为,议会制和总统制都有可能促进或阻碍民主的巩固,关键在于它们在实践中与什么样的配套制度相结合,两者的优点与劣势不应被过度放大;总统制并不必然导致民主崩溃。对于民主巩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选择总统制或者议会制的问题,而是设计良好的配套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来弥合社会的分裂与冲突。他特别强调选举制度对于总统制国家政治稳定与民主巩固的重要性,他认为所谓总统制的弊端,都是源于简单的相对多数或绝对多数直接选举制度,而非总统制本身。新生的总统制国家可以采取一种更为复杂的选举制度,以有效削弱极端政党的政治影响,防止社会的极化分裂。他引用了尼日利亚与斯里兰卡的选举制度为例:尼日利亚第二共和国采取了一种具有广泛分布性的相对多数总统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必须在19个州的2/3以上均赢取至少25%选票才能成为总统。这意味着总统必须得到大量种族群体的支持,这有助于削弱种族极端势力的影响,选择一位稳健派总统。斯里兰卡于1978年后实行了一种相对复杂的绝对多数总统选举制度。选民在选举时可以选择多个候选人,并按偏好程度将其依次排列。首先计算选民的第一偏好。在选民第一偏好中赢得绝对多数的候选人当选总统。如果在第一偏好中无人获得绝对多数,那么从中拣取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同时计算这两人在其余选票第二偏好中的得票情况,并与这两人的第一偏好得票情况合并计算,获得绝对多数者当选总统。如果仍未达到绝对多数,则按照前述方法依次累计各偏好得票情况,直到产生绝对多数。这样产生的总统将是选民不同层次偏好调和的结果,有利于各个族群之间的和解与妥协。
此外,所谓总统制的任职刚性、弱势内阁以及权力滥用,都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议会制同样可以出现这些情形。(14) 总之,总统制并不必然导致民主崩溃,所谓的总统制弊端,有些在议会制中也不可避免,有些则可以通过相应的配套制度加以避免,不应脱离选举制度和其它具体制度而对总统制与议会制做出简单评价。实际上,Linz等学者“不是在反对总统制,而是在反对相对多数选举;也不是在支持议会制,而是在支持议会联盟。”(15)
观点之三:混合制是更加可行的选择
正当许多学者陷于总统制与议会制之间的争论时,Giovanni Sartori为新生民主国家提出了第三种选择,即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为代表的混合制政府形式。(16) 他从政府绩效以及合法性的角度考察宪制形式,认为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内在制度特征都有可能造成无效统治,从而威胁到民主的巩固。对于一种政治体制而言,其合法性如何、其能否得到巩固,最终取决于其统治效能。如果不能实现有效统治,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即使所谓民主的制度,也最终将被人们所抛弃。政府绩效才是最终的合法性来源。
Sartori指出,许多学者认为议会制具有适应环境条件的灵活性,能够化解政治刚性带来的政治危机,控制政府危机不至于演化为体制危机。但是,纯粹议会制的政局混乱、更迭频繁、统治低效也有目共睹,法兰西第三、四共和国以及前法西斯统治时期的意大利就是实例。这使得体制合法性逐渐丧失,无法避免体制危机,最终导致这些国家议会制的崩溃。一些学者认为议会制也能够实现行政权的稳定;但是在纯粹议会制国家,这种政治稳定很多时候是通过政府或者各部部长的无所作为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政府避免采取任何政策,避免触犯任何集团,以此保障自己的在职与稳定。这种政权稳定没有什么意义。
若要议会制能够有效运转,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形成适合议会制的政党(Parliamentarily fit parties),即以少数几个具有内聚力的纪律型政党为主导,各政党能够遵守民主政治游戏规则,做一个对国家负责的执政党与反对派。这实际上是一种半议会制,可以避免政治动荡与政府更迭频繁。但是,如果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总统制转向议会制,却很可能转向纯粹的议会制,因为它们缺乏适合议会制的政党。拉丁美洲国家多数呈现一种极端化的多党制,政党数量众多,政党力量涣散,政党制度虚弱无力。一些国家如巴西还呈现出反政党的风习,政客们穿梭于各个政党之间,不断变换自己的政党身份,政党阵线变动不居,各种无党派的自由选民不断出现。这种虚弱的政党生态必定不利于议会制的运行,向议会制的转型必定造成更大的混乱。而且,议会制本身并不能造就强大的政党制度,这有赖于选举制度变革以及由于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政党压力而造成的政党融合与纪律性建设。
关于纯粹总统制,也具有不可避免的重大弊端。其行政权与立法权分割所造成的政府僵局很难避免,各政党出于自己利益考虑而使行政权与立法权互相扯皮,决策难以出台,政府治理难以实行。美国总统制能够基本运转只是一个例外,而且近年来也出现了政府僵持的现象。它的有效运转有赖于三个条件,即: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柔性;散漫型(非纪律型)政党;地方型政治(locality- centered politics)。这三个条件促成利益导向的政治,利益交换造成的协合式民主能够化解政治僵局。而在转型国家,这些条件都是不具备的。而且,现代选举的视频政治(video politics)特征日益突出,外在形象与演讲表态掩盖了更重要的政治能力和对国家事务的洞察力,这种视频政治更有利于政治圈外人胜出。如果一个民粹主义者或者煽动家上台执政,谁也无法确知其是否会做出违背宪法的事情来。
正因为如此,混合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它可以有效地克服纯粹议会制与纯粹总统制的不足。首先,半总统制下的总统与总理共同领导行政权力,总理需要议会的多数支持,具体政策的制定权也由总理负责。这可以克服总统一人大权独揽的弊端,避免行政权力受到民粹主义影响。其次,半总统制也可以解决总统制的多数不一致而造成政府僵局的弊端,因为它不是建立在权力分割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权力共享基础上,即总统与总理合作共事。这种权力分享将迫使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协商共识,特别是总理来自于另一个不同政党或政党联盟时。(17) 而且,这种半总统体制有助于使政党制度演化为一种两极模式,从而形成一个有力的政党制度。
关于半议会制,当然也是一种有效选择,但是转型国家往往缺乏适应的政党制度,这显然有些可遇而不可求的意味。半议会制与混合制/半总统制,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在抽象上何者为优、何者为劣的问题,关键是与某一国家的政治文化、政治传统以及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相契合。(18)
非宪制因素与民主巩固
随着宪制形式与民主巩固争论的深入,许多学者开始超越宪制形式本身来思考转型国家民主巩固的问题,这就是一系列外源型观点的出现;他们认为:民主巩固实际上与总统制、议会制、混合制这些宪制形式没有太大关系。Seymour Martin Lipset就指出:采取总统制或议会制,对于民主制度的巩固并无明显的影响。作为民主政制形式的总统制与议会制,二者都有民主巩固与民主崩溃的案例,“行政权力的宪制类型差异与民主或威权结局之间的所谓密切关系并不明显。”(19) 但是,在历史与现实中,总统制的崩溃频率又远高于议会制,总统制的生存时间也远低于议会制,例如1946-2002年之间的新生民主国家,总统制的平均寿命为24年,而议会制的平均寿命为58年。(20) 这样就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因此,为了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这些外源型观点一方面要揭示外源型因素与民主巩固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回答为什么总统制民主比议会制民主更多走向崩溃的问题。传统的外源型观点往往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国家大小、地理位置等方面探讨民主巩固的影响因素,其中有些讨论已经是由来已久;最近则有关于军事专制的历史遗产与民主巩固之间关系的探讨;而最具有认可性的观点,则是关于政治文化与民主巩固的理论。
1.传统观点: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国家大小、地理位置与民主巩固
(1)关于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论述。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的大量存在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稳定。而在现代社会科学中,人们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21) 因为一个国家越富足,其国民进行政治表达的利益驱动力就越大,同时又不至于突破理智和自我约束。而且,富裕国家的贫富差距往往更小,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公平,从而有助于缓和社会冲突,遏制极端主义势力,创造一个和平理性的民主环境。“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和更为复杂的社会及其所需要的受过教育的人口更有助于民主政权的建立。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些社会也将比那些非工业化的社会更有利于新民主政权的巩固。”(22) 这种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稳定之间关系的观点在西、北欧——英语系国家与拉美、非洲的对比中相当明显,被很多学者借用来解释总统制、议会制、经济发展与民主巩固的关系。正如Adam Przeworski等人的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民主政权转变为威权政权的可能性越小;议会制多存在于富裕国家,这些国家的民主更容易甚至是必然能够生存。(23) 而总统制国家的经济状况则很难比得上一般意义上的议会制国家。既然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到民主制的巩固,那么总统制国家的广泛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
(2)关注政治文化的学者们特别看重与民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他们认为民主政治能否稳定,民主政治能否有序运转,与采取总统制或者议会制并无密切联系,其中最根本的变量在于政治文化。他们认为,不同的文明群体和历史文化传统在价值观与行为上对民主巩固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有支持民主的文化,有反对民主的文化,也有比较中庸的文化。Seymour Martin Lipset就说:“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历史记录,就会得出我早在1960年《政治人》中提出的结论:持久的民主政治大多存在于比较富裕和倾向于新教文化的国家。”(24) 非新教文化往往难以产生稳定的民主政治。(25)
许多学者认为,天主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不适宜民主政治的生长。天主教文化崇尚精神权威,而对民主缺少热情,他们对计算选票的民主方法并不热心,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就是例证之一。魁北克多元政党体制的建立比其它新教地区晚了接近100年。而且,魁北克的这一变化也得益于天主教会自身定位、国民教育内容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在此过程中,魁北克的政治体制并未发生任何变动。而伊斯兰宗教信仰不愿意做出世俗与宗教两个领域的区分,这使得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在伊斯兰世界难以出现。当然,结论并不能绝对化,因为伊斯兰的信条与实践也会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变动。
根据一些学者的观察,二战后的新生国家之中,建立起持续性民主政治的,绝大部分是前英国殖民地,深受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前比利时、荷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地却没有这种情况,它们更多是一种崇尚君主权威的文化。据此,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是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和维持民主政治的有利因素。
(3)国家规模(地理面积与人口数量的大小)对于国家治理也有重要影响,“尽管面积和人口(还有地理位置)并不严格确定政治、经济或文化,但却是影响经济发展、对外政策和国防以及其他许多有政治意义的问题的重要因素。”(26) 一般而言,一个小国总会比一个大国更容易统治。国家的面积越大、人口越多,国家的内部差异性也就越明显,国内各个群体、族群在语言、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不一致就越可能引发政治分歧,甚至民族分离主义。特别是那些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新生民族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家建设问题,解决民族性问题,即建设统一的政治民族的问题。在这一问题解决之前采取民主制度,也就是在社会政治冲突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制度,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这样的民主制度很难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容易转向专制或威权体制。根据学者们的发现,议会制倾向存在于小国家,而总统制国家往往是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国家。(27) 如此,由于国家规模的原因,总统制国家相比于议会制国家更加难以治理,总统制也就往往比议会制更容易崩溃。
(4)另外,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总统制多出现在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而议会制多出现在欧洲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是民主不稳固的地区,而欧洲则是民主较为稳固的地区。拉美与非洲很多国家多是在二战之后才成为独立国家,在独立时又选择了民主道路,面临着国家建设与民主建设的双重任务。对这些国家而言,民族国家构建中的认同性、合法性、渗透性、参与性、分配性危机同时到来。“新兴的独立国家一般都有严重的认同性和合法性问题,它们希望推行复杂的法律,给予所有公民投票权,提供不断增长的和公平的生活水平。对它们虚弱的制度来说一下子承担这些任务实在是太多了,最后可能发生革命或接受军人的统治。新政府取消的第一个项目通常是参与,因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实行的是独裁制。”(28) 如果国家性(stateness)问题难以解决,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都将是动荡不定的,能否实现也在两可之间。(29)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巩固型民主制度都诞生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都是一些古老的民主国家,而且多数是在西部和北部欧洲。由此看来,总统制的不稳定与议会制的相对稳定跟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也有些关系了。
但是,检视这些传统观点,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国家大小、地理位置能否足够解释不同国家的民主巩固以及总统制与议会制民主的不同命运?Cheibub认为,这些因素可能对转型国家的民主巩固有关联,并会对总统制与议会制民主的不同命运产生影响,但是却并不足以解释这一差异,因为那些大致处于同等经济发展程度、同一政治文化区域、同等国家规模以及同处非洲拉美地区的国家,总统制民主崩溃的几率也要大于议会制。因此,需要寻找新的外源型解释因素。
2.新型观点:军事专制的历史遗产与民主巩固
那么,这种新的外源型解释因素要到哪儿去寻找?Cheibub认为,这就要考察不同形式民主国家的历史遗产,即前民主时代的政治制度特征(军事专制抑或文官专制)。Cheibub通过考察一系列数据发现,军事专制之后的民主要比文官专制之后的民主更容易死亡,其比率要高出70%。(30) 文官专制之后的民主大约持续89年,而军事专制之后的民主大约只持续20年。(31) 而如果不考虑前民主时代的政治遗产,总统制与议会制的生存几率和生存时间并无多少差异。因此,新生民主国家的历史遗产,即历史上采取的军事专制还是文官专制,是影响这些国家民主制度能否巩固的主导性因素。那些历史上出现过军事专制的新生民主国家容易崩溃。军方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往往难以控制,随时都可能推翻民主政府与民主体制。而且,这种军队对政治的干预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一旦出现第一次,就会产生路径依赖的效应,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很可能会持续不断地出现,呈现一种循环往复的态势。于是我们看到军事政变在拉丁美洲等地区呈螺旋状反复出现。(32) 这是许多新生民主国家难以实现民主巩固的最大原因,而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宪制形式则仅仅是一种表象。
那么,如何解释转型国家总统制与议会制民主巩固的差异呢?Cheibub认为,这是因为近现代新生民主国家中的总统制国家往往具有军事专制的历史遗产,而议会制和混合制国家则往往是拥有文官专制的历史遗产,而军事专制的历史记忆更容易造成民主的不稳定。(33)
但这也不表明军事专制与总统制就具有某种必然联系,并不是说军事独裁者倾向于采取总统制,并利用总统制的制度特征保持自己的专制权力,继而导致民主的不稳定。首先,在拉丁美洲等地区和国家,总统制的诞生要早于军事专制的出现,它们早在19世纪就已经采取了总统制的形式。(34) 而新生民主国家宪制形式的选择,虽然有各种原因,但都是在国家诞生之时、军方干政之前就已确定下来。这种早已确定的政府形式往往具有历史固存性,许多国家在军事专制之后重新回到传统的总统制形式上来,因为这种政府形式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传承的历史基因,政治行动者对这种政府形式最为熟悉,而变动政府形式的后果又难以预估。其次,历史事实证明,在剥离军方政治影响的民主化过程中,很少将民主体制类型的选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关于民主体制类型的讨论往往是军方卸去权力之后的事情。此外,军事专制在民主化之后也不必然转向总统制,在拉丁美洲之外的军事专制体制有很多都转向了议会制或者混合制。因此,军事专制与总统制的这种一般联结,乃是一种历史偶然性,“军事专制——总统制联结的存在是因为:那些在20世纪中期军事主义弥漫的国家同时也是早已采取了总统制安排的国家。如果这些国家原先采取了议会制的安排,那么议会制民主的不稳定性将远高于当下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形。”(35)
那么,反过来讲,是不是说总统制更容易造成军事专制从而使得民主难以巩固呢?Linz等人认为,总统制容易陷入政府僵局的制度特征,为军方干预政治提供了契机。但是,Cheibub通过数据整理与分析得出结论,军方干预在总统制与议会制(和混合制)国家具有大致相等的发生几率,总统制并不是为军方干预提供更多的机会。实际上,军方如果有力量作为一支独立势力干预政治,那么任何一种政府形式都不可能阻止他们,采取总统制或议会制的形式根本不重要。军方干政在总统制国家之所以频繁出现,Cheibub认为,完全是一种历史巧合。以拉丁美洲为例:拉丁美洲在二战之后之所以能够保持军事专制的广泛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军方在二战中没有经历军事失败,军方保留了治国的可信性与政治能力;另一方面,冷战的开始使得右翼军方成为抵制“共产主义威胁”的屏障,军方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具有随时干预政治的能力。与此相对照,欧洲大陆许多专制国家在二战中发生了军事失败,威权政权和军方都已经失去了政治可信性,美国只能通过支持中间——右翼的民主派政党来进行冷战,民主制度于是能够广泛建立起来。因此,尽管议会制和总统制民主同样都可能因为军方干预而死亡,但20世纪民主制的死亡仍然主要发生在总统制比较广泛的拉丁美洲地区。如果这一地区原先采取了议会制政府形式,议会制民主同样也是不稳定的。军方干预政治不是某种政府形式的结果,而很可能是社会经济结构造成的结果。转型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处于急剧变动期,经济社会的不平等趋于扩大,现有体制没有能力容纳过多的社会利益诉求,或者无法做出有效回应,社会失序,政治动荡,这为军方干政提供了历史契机。
因此,Cheibub认为,总统制比议会制更容易民主崩溃的现象仅仅是一种表象,民主崩溃的根源还在于宪制形式之外的政治历史遗产。“总统制民主的问题不在于其‘制度性缺陷’,而是它们往往存在于那些任何民主形式都不稳定的地区,因此,新生民主国家对总统制的惧斥无所实据。以严格的制度观点而论,总统制可以与议会制一样稳定。既然宪制框架难于变更,那些变更宪制的企图将是徒耗心力。当民主不稳定与制度结构无关时,改变制度结构的努力将是对资源的错误使用。因此,并不是说,被总统制所‘粘定’的国家必然要经历民主不稳定,也不是说总统制没有改进的余地,或者制度改革无关紧要。人们可以采取某些行动以促进民主生存,而又不必变革那些难于变革的制度结构。”(36)
结论
历史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政治现象的影响因素都不是单一的,民主巩固的问题同样如此。转型国家的民主巩固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不同学者和政治家都可以为此贡献自己的智慧。学术探讨的成就之一就是可以提供不同的观察视角,发现一些原本未曾发现的历史要素。
尽管民主巩固是多种因素混合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转型国家就只能静静等待历史的裁判而无能为力,政治精英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历史的发展,为民主巩固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外部因素往往是难以选择的,经济发展的程度、政治文化的状态、国家规模以及历史上的政治遗产,这些都是事先存在的要素,难以为人们所把握。其中有些因素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动,但是其历程将是缓慢的而显得时不我待。但是对于政治制度(包括宪制框架、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而言,处于民主转型之中的政治行动者却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他们完全可以构建一个能够更加适合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制度体系。关于制度的作用,很少有人会加以否认,有效的制度甚至可以推动政治文化的民主转型与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为民主巩固提供更多的有利因素。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是一个紧迫任务,其本质上就是制度的建设,这也是政治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制度的建构与变革需要审慎,它关系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整体,需要与本国的政治传统、政治文化相融合,与社会大众可以接受的程度相联结。政治制度的建构必须要事先考虑各种不利条件,以选择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克服不利局面、利于平稳转型的制度形式。尽管有时需要付出一定的创新成本,这种选择也是必需的。“宪制创新并不必然十全十美,但如果囿于既往经常失败的制度而逃避变革,必定将错失历史赋予的机遇。”(37) 这又牵扯到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即制度设计的问题。
注释:
① Scott Mainwaring等学者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政体制做了更为详尽的划分,包括presidential,parliamentary,premier- presidential,president- parliamentary,assembly- independent,directly elected prime- ministerial。本文认为,作为一种主流看法,总统制、议会制与混合制的类型划分对于一般性研究已经足够,除非进行具体的国别研究或者两个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更为细致的划分是不必要的。
② 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为代表的这种宪政体制被国外许多学者冠以不同的名称,如a bipolar executive,a divided executive,a dual executive,a parliamentary presidential republic,a quasi- parliamentary,a semi- presidential government,a premier- presidential systern。国内很多学者将这种体制称作“半总统制”。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将其一律称为混合制,即混合了总统制与议会制的某些制度要素。
③ Juan J.Linz:“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in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No.1 (1990),also in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Second Editien) (Larry Diamond & Marc F.Plattner ed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Press,1996) ;“The Virtues of Parliamentarism”,in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Second Edition);“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in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Juan J.Linz and Arturo Valenzuela ed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Press,1994).
④⑤⑥ Juan J.Linz:“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in The C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p.125,p.135,p.136.
⑦ Juan J.Lira:“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in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p.9.
⑧ Arend Lijpahart:“Presidentialism and Majoritarian Democracy:Theoretical Observation”,in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pp.98-99.
⑨ 民主质量与民主效能是衡量民主体制的两个基本指标。所谓民主质量,是指某一体制在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负责性(accountablity)、平等性(equality)和参与性(participation)等民主规范性标准方面的实现程度。所谓民主效能,则是民主体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在(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等方面所达到的程度,即治国绩效问题。这样,民主质量更加体现规范性标准,民主效能则更加注重经验性标准。
⑩ 出于数据精确性的考虑,Lijphart使用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成员国的数据,因而缺乏了拉丁美洲的数据,未能将其纳入比较范围。尽管如此,Lijphart认为,拉丁美洲的总统制——比例代表制不能被视为成功,因为总统制与比例代表制的结合极易导致立法——行政僵局;而且,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方面都没有良好表现。
(11) Arend Lijphart:“Constitutional Choices for New Democracies”,in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Second Edition.Larry Diamond & Mare F.Plattner ed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Press,1996),p.173.
(12) José Antonio Cheibub:Presidentialism,Parliamentarism,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Press,2007),p.19.
(13)(14)(15) Donald L.Horowitz:“Comparing Democratic Systems”,in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p.148,pp.148-149,p.149.
(16) Sartori的政府分类形式有些特殊,他提出了纯粹总统制、纯粹议会制、半总统制、半议会制几个概念。他认为,美国的政府体制是一种纯粹总统制,法兰西第三、四共和国是一种纯粹议会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是一种半总统制,英国和德国的体制则是一种半议会制。在纯粹议会制下,议会拥有绝对主权,但其代价是议会政治的混乱与政府的频繁更迭。半议会制虽然名义上为议会主权,但却通过政党制度化解了议会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形成了行政权的主导格局或者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平衡局面。他认为半议会制是与特殊的政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可遇而不可求的意味;新生国家应该采取一种半总统制,更加有助于民主巩固。参见Giovanni Sartori:“Neither Presidentialism nor Parliamentarism”,in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pp.106-107.
(17) 这一点可以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中得到证实。20世纪80年代Mitterand总统与Chirac总理之间以及90年代Mitterand总统与Balladur总理之间的“左右共处”与合作表明来自不同政党的总统与总理以及总统与议会之间可以相互合作。
(18) Linz并不认为混合制更有利于民主的巩固。他认为混合制的有效运转依赖于两个条件:稳定强大的政党制度,总统—总理良好的合作精神与政治能力。而这些并不是混合制所必然能够提供的。政党制度更多与选举制度相联系,而双头行政蕴含了总统与总理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他认为混合制能够有效运转的条件完全适合于采取议会制。参见Juan J.Linz:“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in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19) Seymour Martin Lipset:“The Centrality of Political Culture”,in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Second Edition),p.150.
(20) José Antonio Cheibub:Presidentialism,Parliamentarism,and Democracy,p.136.
(21)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22)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26页。
(23) 参阅Adam Przeworski,Michael Alvarez,José Cheibub,and Fernando Limongi: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 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24) Seymour Martin Lipset:“The Centrality of Political Culture”,in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Second Edition),p.152.
(25) “在第三波的早期年代,这一观点是由乔治·凯南所明确提出的。他说,民主是一种‘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西北欧发展起来的’政体,‘它形成于主要那些靠近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国家(但是也延伸到中欧),然后这一政体又被带到世界上其它地方,包括北美的人,因为北美人来自西北欧地区,要么作为最早的定居者,要么作为最早的殖民者。他们规定了文明政府的主导形式’。可见,民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基础都相对狭隘;当然,至于这种政体是否也是其狭隘的发源地之外的人民的天然统治形式,其证据还有待找出。”’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326页。实际上,有许多学者也不认同政治文化对民主巩固的影响,因为政治文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可能既包含反民主的成分,也包含支持民主的成分;而且,政治文化是不断处于变动之中的。
(26) 阿尔蒙德、小鲍威尔主编:《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2页。
(27) 参阅Scott Mainwaring and Matthew Soberg Shugart eds.: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8) 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29) 参见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39页。
(30)(31)(35)(36) José Antonio Cheibub:Presidentialism,Parliamentarism,and Democracy,p.140,p.142,p.147,p.160.
(32) Cheibub认为,拉丁美洲总统制民主与军事专制之间的螺旋交替已经接近尾声。这一方面是由于拉丁美洲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使得这一地区达到了与民主相适应的经济水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最近一轮的官僚——威权政治中,军方因其残酷与无能而名誉扫地。而且,冷战压力的消失使得军事专制所仰赖的国际支持也不存在了。军事专制在该地区再次出现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小。
(33) Cheibub提供的数据表明,大约2/3的总统制国家都曾经历军事专制体制,而议会制和混合制的这一比例仅不足1/3。
(34) 19世纪时,议会制的政府形式尚未出现,英国式的政府形式更多体现为一种特殊的君主制,新生国家政府形式的选择是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而不是总统制与议会制之间。
(37) Juan J.Linz:“Presidential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in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p.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