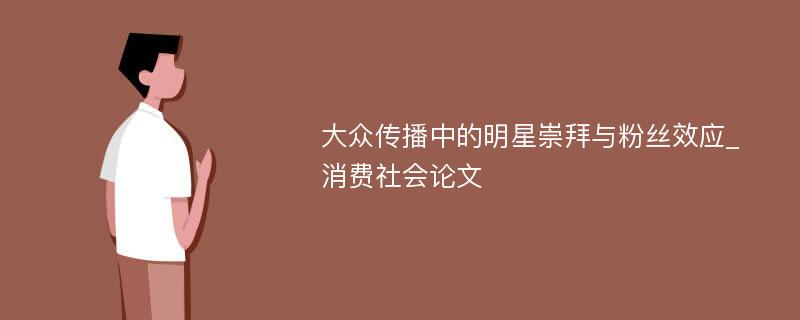
大众传播中的明星崇拜和粉丝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崇拜论文,效应论文,粉丝论文,明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1-0131-04
近年来,随着传播媒介与大众娱乐的携手,粉丝(即追星人群的一种新称呼)借助一场场选秀浪潮闯入了大众的视野,他们热烈、张扬,充满着活力与创造力。他们疯狂而执着的追星行为也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媒介景观。如今,粉丝一族利用大众媒介展开的声势浩大的追星活动已屡见不鲜,但是在这些华丽的演出背后却有着一系列的问题一直困惑着人们:明星到底有何种魅力让粉丝们如痴如醉?粉丝是如何生产和消费明星的?大众媒介、明星与粉丝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将成为本文的分析重点。
一、明星崇拜的内在机制和作用
在汉语中,明星最早是指天上明亮的星,比如,朱熹集传中就有:“明星,启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1]这儿所提到的明星,就是指金星。以后人们也用明星来指称一些有名望的、有成就的人。《汉语大词典》对明星的解释是“有名的演员、运动员等”[2](P605)。在西方,“明星”一词最早出现在1824年,用来指戏剧界有名的演员。1919年,它从英语词汇中引出用来专指电影明星[3]。关于“明星”一词的具体内涵,笔者在此采用费斯克等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中的界定:由于在银幕与其他媒介上的公开表演而出名,并被视为各种文化群体之内与之间重要象征的个体[4](P270)。
该定义点明了明星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一,大众媒介是明星出名的平台。追溯国内外明星发展史不难发现,明星之所以能够成为明星,其关键就在于大众媒介这一不可或缺的舞台。英国学者戴尔在《明星》一书中曾写道:“明星历史上有一件重大事件,通常被指卡尔·莱姆尔在《圣路易斯邮报》上采取的行动:他为了提升当时被称为‘比奥格拉夫女郎’的弗洛伊斯·劳伦斯的形象,特意安插了一段故事,说她在圣路易斯遭遇车祸,被一辆有轨电车撞死,第二天又在这家行业报纸上刊登一则启事,称上述故事纯属捏造。这件事系电影演员的大名为公众所知的第一个案例,也是精心打造明星形象的第一个范本。”[5](P13)由是观之,好莱坞大鳄正是利用明星来刺激人们的眼球,同时也成就了明星自身。明星发展初期主要以平面媒体为阵地,以后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依靠媒介生存的明星们开始不遗余力地利用广播、电视乃至今日的网络。其二,明星经常是文化群体的重要代言人。有学者指出:“当代媒体文化为认同性及其新的模式提供了资源,其中外表、风格和形象等取代了作为认同性的构成因子的行动和承诺等。”[6](P440)而约翰·费斯克也认为,明星正是“种种理想与价值的化身”[4](P270)。2009年6月25日,迈克尔·杰克逊辞世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名流都纷纷缅怀这位传奇人物。不难想见,人们缅怀的不仅是一位“流行天王”,也是他所代表的流行音乐和流行文化。
随着明星的兴起,也产生了明星崇拜现象。“崇拜”一词,在牛津词典中被解释为:1.(对上帝或神的)崇敬、崇拜;2.(对某人或某事物的)崇拜、仰慕或热爱(尤指看不见其缺点)[7](P1758)。可见,崇拜最初强调人对“神”的顶礼膜拜,对宗教的虔诚信仰;以后人们将这种对“神”的迷恋转移到了对人的身上,而且是无视其缺点地仰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崇拜心理一直存在,它是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思维能力发展的自然产物,是各个民族都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并且,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介狂欢、娱乐至死的年代,明星崇拜更加广泛与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情感和行为。笔者以为,明星崇拜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以主要归结为社会认同及行为模仿两个方面。
认同(identity)或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源自现代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它是“对某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认可,其中包括其自身统一性中所具有的所有内部变化和多样性。这一事物被视为保持相同或具有同一性”[8]。简单地说,社会认同表现为个体认识到他所属于的特定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偶像崇拜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人员认为,那些十几岁的追星族通常能把他们的情绪调节得很好,并且有较好的人缘。这说明,对名人的兴趣有助于青春期的心理调整和同龄群体的交往[9](P151)。我们知道,现代社会高度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民众走向了“原子化”,人际关系日趋淡漠,人际沟通与交往减少。当前的青少年大多为独生子女,其孤独感就更加明显。因此,他们对明星的追逐,不仅是从明星身上找到了自己渴望的某些特质,也是因为这种兴趣及相关行动能够使他们进一步发现志同道合者,形成一种新的群体或圈子并从中获得一种认同感,个体也可以通过这种认同来重新确定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
如果说认同主要体现在明星崇拜的心理层面,那么模仿则更多地出现在其行为层面。米德曾指出,个体对于其社会角色和行为的掌握是通过模仿他人的言行而获得的。也就是说,模仿是模仿者实现社会化的一种手段。个体尤其是青少年在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总会通过模仿心目中的“认同者”来和他人进行交往,之后再慢慢体会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在大众媒介疯狂造星的年代,明星不仅被幻化成个体认同的对象,同时也被转变为个体主动模仿的对象。
那么,明星崇拜对于个体产生了哪些作用呢?首先,它表现为一种投射作用,即明星成为个体情感投射的对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常常会将自我的某些梦想和欲望投射到他人身上来聊以自慰,粉丝更是经常如此。他们因为没有小燕子的率性勇敢而疯狂迷恋赵薇;没有王力宏的多才多艺而为之倾倒;没有周杰伦的特立独行而狂热膜拜。其次,它还表现为一种慰藉与补偿的作用,即个体在崇拜明星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情感上的平衡与共鸣。在生活节奏如此之快、压力如此之大的今天,无奈、不满等负面情绪经常充斥于人们的内心,于是粉丝将自我理想、信念与情感寄托在自己所崇拜的明星身上,从偶像的成功与荣耀中分享喜悦,并获得一种心灵的慰藉。
二、粉丝的特性与消费
正是在明星崇拜心理的主导下,一批又一批的粉丝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投入到追星活动中,有时甚至到了不能自拔的程度,而2005年的《超级女声》更是开启了粉丝时代的新纪元。粉丝又叫媒介迷,其主要特征是不仅对某些明星,而且对某些特定的媒介内容表现出极度的喜爱。有学者认为,粉丝是指一群因过度沉浸于媒体建构的虚拟世界而扭曲了时间概念,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主动的受众[10]。当然,对于粉丝的概念,国内外学界尚未得出一致的意见,相关研究也非常繁杂。但具体说来,粉丝通常具有以下特性:
1.参与性。著名学者詹金斯曾颇具建设性地指出,不断发展的媒介技术使普通公民也能参与到媒介内容的存档、评论、挪用、转换和再传播中来,媒介消费者通过对媒介内容的积极参与而一跃成为了媒介生产者[11](P101-113)。而约翰·费斯克也早就指出:粉丝是一批流行文化资本积极的生产者和使用者[12](P33)。进入WEB2.0时代,互联网为粉丝追星提供了最快捷、最有力的工具。以百度贴吧为例,粉丝在其中创建的有关内地、港台、日韩以及欧美明星的贴吧总数就有12385个。粉丝们长年累月驻守这些贴吧,将自己获得的明星信息、图片等第一时间上传到贴吧中与他人分享。比如,截至2010年9月12日,李宇春吧里的帖子已逾千万,而每个帖子下方的跟帖更是无可计数。这种高度的参与性成为粉丝的一大特征。
2.过度性。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曾这样描述:“粉丝是过度的读者,其对文本的投入是主动的、热烈的、狂热的、参与式的。”[13](P163)换言之,粉丝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其过度性,这也是他们与普通受众最大的不同。事实上,我们都早已听到、看到、领略到粉丝的各种过度性行为。譬如,为了收集明星的相关物品,他们不惜重金;为了一睹明星风采,他们可以在活动现场不吃不喝等上十几个小时;更有甚者,诸如“大肆整容追孙燕姿”、“服药自杀追周杰伦”、“倾家荡产追刘德华”等悲剧性事件时有发生,而这一切只能用过度和狂热来形容。这种过度性也是粉丝带给社会最大的困扰。
3.区隔性。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提出过“场域”这一概念,它指的是在社会文化领域中被划分的不同区隔,而每个区隔的领域的运作就像物理学意义上的“场”一样,是由内部和外部的不同作用力而构成的。“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14](P46)“这些斗争旨在继续或变更场域中各种力量的构型……争夺的策略取决于人们所具有的对场域的认知,而后者又依赖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15](P139)我们知道,不同的粉丝追随不同的明星,于是明星的不同会造成粉丝之间的相互区分乃至对立。再往深处说,只有具备足够的消费能力,粉丝才能够拥有更多曾被偶像拥有过的物品,或由偶像代言的产品,才能够亲身参与和偶像相关的各种节目或演唱会,并获得话语权,经济实力往往是其参与的基础。于是,就是在同一明星的众多粉丝中,这种来源于经济实力而产生的差异也会形成一种区隔。
面对所崇拜的明星,粉丝的投入不仅表现在精神和心理层面,其实更多地还表现在消费层面。换言之,粉丝对明星的认同和喜爱通常会以或高或低的消费行为来予以呈现。而在这些以金钱为基础的消费活动中,符号消费与情感消费又成了引人注目的两个方面:
1.符号消费。通常符号的实质是象征,它传达了某种意义,如玫瑰象征爱情,稻米象征丰收。同样,若将语言符号、标识符号转移到明星身上,我们可以发现,明星也是一种象征符号。以一夜走红的超女为例,走中性路线的李宇春有着爽朗阳光的外形,帅气且率真,故而在“玉米”眼中她象征着一种生命的活力;惯唱英文歌曲的张靓颖则象征着一种女性魅力和时尚的生活品质;而知性且个性的尚雯婕更是象征着一种白领女性追逐的小资文化。为了表达自己的喜爱与认同,“玉米”们经常做中性打扮,举着李宇春的海报为其呐喊助威;而张靓颖和尚雯婕的粉丝也会偶尔逃离都市的喧嚣与浮躁,静静地坐在演唱会现场聆听偶像如天籁般的歌声。总之,这些明星可能正好具备我们自身的某种特征或品质;或者这正是我们一直想要追求的理想形象。所以,粉丝之间的较量“实质上是众多的不同符号意义间的较量,或是粉丝们爱好,梦想及品位的较量”[16],而粉丝们一路追随明星的同时,也是在追随一种精神或一种价值观。
2.情感消费。阿多诺曾发出感慨:“现代文化产业就是一种商品的生产,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什么灵性的表现或风格的追求,而是创造需要,占领市场。实现最终的目标——交换原则,即把产品变成一种交换的商品。”[17](P118)粉丝的明星崇拜乃至行为模仿其深层因素还在于其情感层面,正是出于情感,他们愿意竭尽所能地去拥有与明星相关的一切产品来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我们看到,不论是“玉米”、“凉粉”,还是“格格”,他们从节目一开始就积极介入,为自己的偶像投票、拉票,制作海报、横幅,组织亲友团,吸纳新粉丝。其中,经济条件较好的粉丝还会亲临演出现场为自己的偶像摇旗呐喊。值得注意的是,粉丝的情感消费不再是原来分散凌乱的“小打小闹”,它造就了一条巨大的经济产业链。其中,粉丝的情感已经被自我和他者操纵为机械化、模式化、批量化的商品。故而,琳琅满目的电视选秀节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以广告收入、明星周边物品和线上虚拟社区三大业务为主的粉丝网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这正如美国学者哈特所言:娱乐工业和各种文化工业的焦点都是创造和操纵情感[18],而情感经济也正是粉丝经济的特质之一。换言之,粉丝对明星的情感是维系粉丝产业链的纽带,是推动粉丝经济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三、大众媒介、明星与粉丝
粉丝们不计回报地疯狂付出,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自己喜爱的明星,他们得到了什么?也许除了心理满足和精神愉悦之外,他们在物质上的收获几乎为零。有人认为,粉丝在这个消费社会中已然掌握了主动权,他们是大众文化、草根文化的开路先锋,是明星的创造者;也有人认为,粉丝头上的各种光环不过是大众媒介为其编织的一个梦而已。那么,在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在大众媒介“一统天下”的今天,明星与粉丝之间究竟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大众媒介在其中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呢?笔者将运用社会学中的功能论和冲突论来分析以上问题。
功能论强调社会的每个部分都是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而构建起来的。作为功能论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将社会看作一个由各个部门相互连结而形成的巨大网络,其中的每个部门都参与协调并维持整个体系的工作[19](P18)。换言之,在功能主义者看来,社会是由相互依存的各部分构成的整体系统,各部分都在系统中承担一定的作用或功能。而明星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也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一些功能。比如,明星的存在使粉丝找到了情感的寄托。正是有了明星,粉丝才得以将内心的缺失转移到明星的身上。尤其是在如今这样一个他人导向型社会,个体害怕被孤立和遗弃,于是,“根本性的无情和对情感的本能渴望形成了当代个人存在的内在焦虑。因为无望寻找一条超越焦虑的现实出路,个人或者用美化旧日时光的虚拟性回想,或者用一种模式化的情感反讽来淡化或释放自己的内在焦虑”[20](P74)。适因于此,对于茫茫人海中的粉丝而言,在追星的过程中,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群体,并在这个群体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当粉丝与志同道合者形成了一个围绕某明星的小群体时,他们就不再是大众中默默无闻的一员,这一群体赋予了他们新的角色与身份。在现实中,这样的一群人往往有着相似的文化品味或个人偏好,他们能够通过特殊的话语体系来确认彼此的身份。譬如,SUJU是粉丝们对SJ组合的爱称,ELF是SJ组合官方粉丝团的名称等。这种类似的“暗语”每天都在粉丝之间悄然流通,由此形成的独特语言风格、行为风格也融入了粉丝的日常生活。所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粉丝拥有了一种自行选择的亚文化,而对不同明星及其所代表的意义与精神的追随正是这些不同的亚文化的形成基础,比如“玉米”、“乙醚”和“什锦八宝饭”就代表了各自不同、相对独立的群体关系。同时,多种明星的并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多种多样的粉丝亚文化也有助于建构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让现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美好。
相对于功能论强调稳定与共识的思考方式,主张冲突论的社会学家将生活视为持续不断的斗争,而我们的社会行为也必须从竞争团体间冲突与紧张的角度来分析。由此出发,粉丝团体的另一种生存状态是“冲突”。一般而言,冲突发生在不同的粉丝阵营之间。譬如,在偶像们紧锣密鼓地进行比赛时,粉丝们也会形成各种小帮派,并且拥有各自的“盟军”及“敌手”:如“玉米”、“笔迷”、“凉粉”之间总是剑拔弩张,冲突不断;而“玉米”与“盒饭”、“笔迷”与“荔枝”之间却结成了盟友。在进入比赛的白热化阶段,我们甚至可以在网络上看到粉丝们各为其主疯狂对骂的帖子。令人玩味的是,粉丝的此类举动无疑是粉丝领域内一种“自我精神”的扩张。在强烈认同的感召下,他们甚至觉得自己与偶像已经成为一个共同的“我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在偶像遭遇挑衅时,粉丝团队会迅速分清“敌我”,并像“我们”对抗“他们”一样,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然而,当人们结束狂欢、重归现实时,阶级或阶层的概念告诉我们,在真实世界中明星多属于一个富人阶层,而粉丝们则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并且大多数属于社会的中下层,和谐的表象并不能掩盖差异化的实质,那种所谓的“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会因为语境的转换而变得不堪一击。
对于传播机构而言,大众媒介生产明星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牟利。以各种电视选秀节目为例,粉丝的热情参与上演了一场颇为绚烂的财富传奇:一路攀升的电视收视率,令人咂舌的短信投票,以及诸多让粉丝慷慨解囊的明星代言产品。毫不夸张地说,大众媒介在打造明星吸引粉丝的同时,也打造了一条文化产业的流水生产线,而明星即是大众媒介取悦、迎合受众的最佳方式,也是其获取巨额利润的重要工具。有人曾经批判道,在这样一条生产线上,大众媒介像生产芭比娃娃一样生产着明星,明星不过是其“绑架”粉丝的诱饵。但在粉丝自己看来,这也许是一次甜蜜的“绑架”。因为当他们内心挣扎不知所措时,至少还有明星的陪伴;当他们因为重重阻碍而不能实现梦想时,明星的成功便是一种安慰;而当他们抱怨命运不公时,明星的坎坷历程还可以鼓舞他们。或许,在这样一个娱乐至上、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大众媒介、明星和粉丝恰恰建构了一个相对和谐的生态圈,他们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媒介获取利润,明星赢得掌声,而粉丝则找到了内心的桃花源。
综上所述,随着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社会文化环境已悄然发生了改变,今天的明星崇拜和粉丝效应已然成为某种常态。明星崇拜的内在机制确实有助于粉丝投射情感,获得慰藉。但不容忽视的是,粉丝的参与性、过度性以及区隔性等特征在推动粉丝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粉丝容易被媒介操纵为机械化、模式化、批量化的商品。虽然明星崇拜机制有助于维持粉丝群体的内部团结以及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但粉丝与明星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其和谐共处、荣辱与共的场景实乃是一种幻象。事实上,大众媒介、明星与粉丝三者处在一个各取所需、相互依赖的文化产业链上,并且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还会变得更为密切。
收稿日期:2010-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