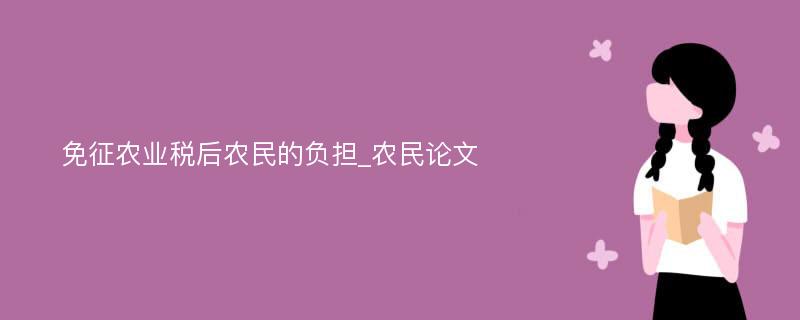
免征农业税后的农民负担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负担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工业化、城市化单纯依靠农业、农村进行原始积累时代的终结,又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时代开始。但免征农业税并不意味着农民负担的终结,相反,农民负担反弹压力巨大,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值得关注。
一、农民负担变化的总趋势
取消农业税,造就了农民负担总体下降的趋势,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的数据,2004年我国农民直接负担的税费总额(包括农业税、上交集体的各种款项、各种社会负担和以资代劳)为581.7亿元、人均64.4元,分别比2000 年的负担总额(1259.6亿元)和人均负担(141.42元)下降了53.8%和54.4%(陈凤荣,2005.7)。在这个总趋势下,农民承受的四项负担的变化各不相同。
1.国家法定的税收——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牲畜屠宰税等三项已经或正在被取消。有报道说,截止到2005年的上半年,全国已有27个省(区、市)免征农业税,剩下的河北、山东、广西、云南4省区也将再降低农业税税率2个百分点以上。今年全国减免农业税预计受益农业人口8亿多人,可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210亿元。
2.乡村两级的“三提五统”(注:国家政策规定,行政村三项提留是指公积金、公益金、公共管理费提留;乡镇政府的五项统筹是,农村教育费、计生费、民兵训练费、优抚费、乡村道路建设费统筹。) 将与取消农业税同步被取消。 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乡级的“五统筹”被规范为农业附加税,税率大约在4%左右,与农业税(2.5%—3%之间)合并,按7%的税率征收,全国每年大约征收700亿元。 村级“三提留”不是一级政府征收的,一般相当于正税的20%,变成附加税后,相当于在7%税率的基础上再增加1.4个百分点(陈锡文,2004.9)。就是说,在减免农业税之前,国家是按照全国农业总产值的8.4%来征收农业税及附加税的。 如果全部取消农业附加税,全国农民每年可以减轻总额为800—900亿元的负担。
3.农民劳均两工亦呈下降趋势,但村民自治中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有抬头的趋势。据农业部经管司的数据,2000年为16.3个,2001年为16.2个,2002年为10.5个,2003年8.3个,2004年为2.1个(陈凤荣,2005.7)。我们的实地调查表明,乡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费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形式转嫁到农民身上,人均负担在15—60元之间。
4.在自1997年以来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系列政策和监督措施的高压态势下,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得到了有效遏制,但目前“三乱”有反弹迹象。
二、农民负担的认识误区
当前社会对免征农业税后的农民负担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四个认识误区:
1.认为免征农业税后农民的负担是零负担。这种认识不断被有关媒体强化,无疑会给农民乃至整个社会过高的期望值,这是十分有害的。农业税减免以后,农民仍需或事实上还承担着较重的负担。作为舆论引导或政策导向,应该强调合理负担而不是其他。
2.认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农业、农村哺育工业和城市的终结。我认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与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将在目前至未来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同时并存。准确地说,我们将进入的是一个工农互促、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时代。
3.认为当前农村基层财务困境都是免征农业税造成的。确实,免征农业税对中央财政收入影响不大,而对乡村两级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很大。免征农业税凸显了乡村财政困难。但我们应该看到,当前农村的许多问题是体制弊端长期积累的结果,比如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合作医疗中出现的问题,就是家庭承包经营的负面后果,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农业税免征,否则会加大正在进行中的免税和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压力。
4.认为农民负担就是农户负担。许多地方,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操作上,都将有关负担或按人口或按承包土地面积分摊派给农户,减轻农民负担也只在农户负担上作文章。解决农民负担的办法中忽视了公共财政的作用,也忽视了当前我国村域中事实上已存在的农户、集体、新经济体(工商业主经济、合作经济组织等)三足鼎立的格局。当前亟需研究既减轻农户、集体和新经济体的实际负担问题, 又动员农户、集体和新经济体等多元经济的力量,合理分担乡村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
三、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
2005年暑假,浙江师大农村研究中心课题组分别到四川、青海、新疆、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区)进行典型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的调查。这些地区都先后取消了农业税,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
1.乡村两级收支不平衡,当年支出缺口巨大,这是农民负担反弹的当前压力。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并不大,每年不超过300亿元,但却对乡村两级的收入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据有关专家提供的资料估算,在改革前,通过“三提五统”和各种集资摊派罚款等,乡村两级每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0亿元。现在,农业税取消了,农业附加税征收没了根基,“三乱”得到了有效遏制。如果算上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乡村两级每年可支配收入比农村税费改革前减少了约700亿元,而乡村两级的年支出有增无减,缺口可想而知。
2.乡村债务越来越大,基层组织正常运转所需经费严重不足,这是农民负担反弹的潜在压力。我们对农民负担的潜在压力有三个基本判断:(1)化解农村债务将对农民负担形成巨大压力。有媒体曾经报道,目前全国乡村债务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我们根据在东中西部农村调查的个案分析,目前我国平均每个乡(镇)债务约300万元,村均债务东部地区约40万元(注:东部省L市L区14个乡镇负债总额1000多万元;P市S村2004年村集体全年应收公益事业费14.5万元,只收了5万元左右,加上出租固定资产收入4~5万元,全年可支配收入不足10万元,而同期全村专职人员6名,仅工资就需近10万元。2004年底,全村已拖欠乡村道路和桥梁建设、自来水管道铺设等工程应付款50万元左右(资料来源——《Z省农村调查》2004.12.21)。)、中部约60万元、西部约20万元。(2)乡级组织运转经费不足,有可能转嫁给农民。根据农调队的测算,全国乡级每年需要3700亿元才能维持正常运转,如果按支出的70%计算,乡村每年支出需要2590亿元,而当前年收入来源只有750亿元。这种状况在东部发达地区也不例外。(3)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缺口很容易转变为农民负担。我们的实地调查表明,在不进行任何建设的情况下,维持一个村的日常运转(工资、办公费、报刊费)每年约需3—5万元的开支,但目前我国至少有30%的行政村集体可支配年收入低于这个水平。
3.新乡村建设所需大量配套资金,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形式转嫁到农民身上,这是农民负担的重复压力。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借助农村制度创新和“三农”新政策的动力,我国新乡村建设事实上已由下而上广泛展开,有的地方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有的地方叫全面小康示范村建设或生态文明村建设等。我国目前的新乡村建设表现出鲜明的区域差异:在贫困地区主要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的农业综合开发(见例2);在发达地区则表现为城市工业文明辐射下的农业产业化与合作化、乡村工业化、村落集镇化或社区化、农民生活方式市民化、基层治理结构民主化的大趋势。比如:苏南的“农田向规模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浙江的“万村整治、千村示范”工程,以及由此演化发展而来的农村社区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家庭美化、环境优化等。尽管新乡村建设存在区域差异,但所需投资中部分转化为农民新负担却是相同的(见例4)。
四、农民负担的新内容、新形式
我们发现,当前我国农民负担已不再是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农业附加税等内容。农民负担的内容已由“税”再度转化为乡村组织运转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和农村公益事业维持费;农民负担的形式主要从“征收”转变为“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通过村民自治把不合理的负担合法化。
1.村级收不抵支的压力,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形式直接转化为农民负担
我们从全国百强县中选择一个中等水平的农业大县作个案研究(见例1)发现,自税费改革和减免农业税以来,在农业比重大的县份,已有70%的村连续4 年收不抵支,每年支出缺口约占村集体可支配收入的22.2%。仅此一项,每年就需向农民转嫁人均15元左右的费用。如果再加上农村公共事业运转费用需求,每年需要由农民承担的公共财政开支人均达54.53元。
例1:我们曾经分别于2003年7月和2005年8月两次到东部某省D市调查。D市是县级市,属于农业大县,全市总面积234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57.3万亩,总人口115.9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73.35万人,全市403个行政村。
D市的整体经济实力并不差,已连续4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排在百强的中等位次。2004年,D市GDP总值143.71亿元,人均12379元(1495美元)高于全国平均10561元(1275美元)的水平,财政收入9.137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26.0/41.9/32.1。全市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1265和5095元。
即使像D市这样的百强县,村集体债权债务矛盾也相当突出。2002年, 全市曾经组织过较大规模的清减债务的工作,化解债务5000万元,村均已化解债务12.4万元。但该市目前村级债务仍然较大。据了解,截止2004年底,全市村一级总资产5.3亿元,其中债权2.6亿元,固定资产1.7亿元,货币资金1.0亿元;全市村级负债1.8亿元,其中必须偿还的债务1.2亿元(欠农户借款2500万元、银行借款3500万元,欠银行及农村合作基金3000万元,欠各种工程建设等应付款6000万元),村均必须偿还的债务还有29.85万元。
取消农业税后,该市每年要减少财政收入1.1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2.01%。村集体更是入不敷出。据该市农村财务辅导站的统计,自2001—2004年以来,已有70%行政村的收不抵支。2004年,全市村级财政三项(占农业税的20%附加税中的三项提留、占农业税的10%农业税返还、转移支付)收入2500万元,零星土地、预留地、水面、房产等财产性出租收入大约1000万元(村集体基本没有二、三产业的收入来源),全市村级可支配收入合计3500万元左右,而全市村级总支出却需要4500万元,村级收支缺口合计1100万元,村均收支缺口4万元。 若按全市农业人口转嫁这笔开支,平均每人需负担15元。
事实上,该市为了弥补村级收支缺口,以及维系必须的农村公益事业(如农村小型水利、道路、植树造林等),2004年全市农村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形式收入4000万元。若按全市农业人口平均为54.53元;如果按耕地面积分摊,亩均25.43元。
2.新乡村建设在给“三农”现代化创造条件的同时增加了农民负担
政府以各种形式对新乡村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农民仍要承担相当沉重的配套费,同时,需要超负荷投资于拆迁费和新住宅建设。农民在新乡村建设中的投入也存在着区域差异。
(1)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转嫁给农民。 贫困地区农民生产生活设施改造或新建,政府通过各种形式投入了大量扶持资金,但仍需农民分担公共设施建设的配套资金。(见例2)
例2:西部某省B市共三县一区,分别是国家级贫困县和省级贫困区。作者2005年8月实地调查了解到,B市B区的M村是2003年启动建设的扶贫新村。该村6 个村民小组,487户,1646人,耕地900亩。2004年,M村农民人均纯收入2200元。
扶贫新村建设是省里的工程,其内容主要是“五改三建”,即建池(蓄水池)、建园(庭院经济)、建家(家庭工副业)、农民住房改造(刷墙做脊)、改厨(沼气利用)、改厕、改水、电、改路(村通晴雨路、户通石板路)。通过“五改”达到五通(水电路及电话和电视光纤),从而增强农民收入能力和改善农民生活。我们在座谈中了解到,目前M村的建设工程已基本完成,共投入200万元。其中:扶贫新村建设列入国家项目资助计划,投入30万元;省市区三级政府投入扶贫资金50万元;镇政府配套投入约20万元。政府投入三项合计100万元,其余上百万元经费,村民只能通过小额贷款和“一事一议”等办法筹资筹劳。
(2)自发或政府推动的中心村建设, 使中等发展地区农民分担了更多的公共设施配套建设资金。作者2005年8月在实地调查中了解到,农民自发进行中心村建设,需要承受住房拆迁和新建、公共设施配套等负担,即使有政府推动或扶持,农民负担依然很重。(见例3)
例3:东部某省L县W村处于农村腹地,有24个村民小组,30个自然村,780户,总人口3500人,耕地面积5000亩,2004年人均纯收入2800元。该村从1999年开始自发地进行中心村建设。用全村18亩机动地作为中心村村址,然后动员农户自愿到中心村址上(按照统一的规划)建新居,并要求自己拆迁和复垦土地。因为没有任何资助,平整土地、通路、通水、通电等基础建设完全依赖拆迁农民分段分户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农户住宅选址显得非常重要。因为选在耕地上或塘堰或水渠地段,进行“三通一平”的投资有很大差别,农民就用最原始的抓阄办法解决矛盾。经过几年努力,到目前为止,全村已有287户迁入中心村,中心村占地面积已达170亩(总规划248亩),37个自然村中已有7村全部拆迁并完成土地复垦(将来全部自然村拆迁可复垦土地1200亩)。作者在该村走访了第一批入住中心村的3家农户,了解到,在没有任何资助情况下,农户在中心村建设中的负担,每户用于“三通一平”和建房的投资约7—8万元,其中5万元左右是建房投资,2万元左右是本该由公共财政投资的配套建设费用。从2004年开始,该村被确定为H市L县的中心村建设示范村,此后政府扶持逐渐增多,包括:2004年县财政拨款42万元;2005年市财政拨款70万元,县财政拨款30万元(调查之日已到位20万元)。除此之外,国土部门下拨土地复垦费680万元(已全部拨到县财政局),可根据该村土地复垦进度随时资助。 我们在该市的另一个区了解到:在中心村建设中,农民拆迁补偿标准是,楼房270 元/平方米,砖瓦房按建房年代分别按180—200元/平方米的标准计算,土坯房分草、瓦房分别为100元/平方米和150元/平方米,其它临时性建筑40—80元/平方米。农民反应,这样的标准不能满足新居建设的资金投入(新居造价包含装修每平方米接近1000元),尽管这种投资形成的是农户固定私有财产,但突击性投资使农民仍觉不堪重负。
(3)发达地区的新乡村建设丰富多彩,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型,但同时造成农民新的负担。(见例4)
例4:案例1,东部某省D市S村共15个村民小组,1432户,3263人,耕地7645亩,2004年人均纯收入5000元。该村2005年上半年修水泥路4.2公里,每公里造价25 万元,总投入105万元。省政府两年前即承诺为农民办五件实事, 其中之一是村村通公路。该省规定,中部地区农村修建1公里公路,由省政府财政补贴15万元、 地县级财政分别配套1万元,加上镇政府及其他补贴,每公里资助额度约为21 万元(南部地区不补贴)。显然,发达地区政府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但每公里仍然有4万元的缺口,需要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 全村农民需要负担16.8万元。该村准备在2005年秋季(农历9月份动工)再将3公里泥土路改造为柏油路,预算每公里造价为12万元,财政资助每公里6万元,另外6万元(3 公里共计18万元)由村里自筹经费解决。该村集体年收入只能维持村干部工资和办公经费,修路的配套费事实上只能靠“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计算该村修建和改造公路配套费,农户就需分摊32.8万元,人均负担100.52元,占全年人均纯收入的20.1%。
案例2,长三角Z省J市W区城郊H村有25个村民小组,1008个农户,总人口2780人,其中农业人口2480人,耕地2000亩,2004年人均纯收入4790元。村集体年可支配收入76万元。该村从2002年开始农民小区建设,是J市农村现代化示范小区之一。小区土地规划标准为,5户宅基占地2亩(每户266.7平方米)、小区道路占地8—10米,非农建设用地由基层政府按国家征地模式办理,每亩补偿1.8万元,并由政府投资进行土地平整和通路通水通电等基础建设。目前规划的A、B两个小区,其基础建设已完成,总投资200万元, 这笔投资基本上由市区县镇财政分担。然后农户按照统一规划和住宅设计图,在小区修建住宅。每户三层带帽(歇山顶),建筑面积大约300平方米,总造价约30万元。截止作者调查日(2005.8.1),全村已有140户农民迁入小区。农民反映,拆迁补贴远不够新房建设的投入。
3.免税以后的配套改革、政策调整以及体制变化中农民需要支付较大的成本
免税以后,农民为配套改革、政策调整以及体制变化支付的成本大致包括四块:其一,随农业支持政策逐步实施和农产品价格上升而来的农资价格上涨,增加了农民负担;其二,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农民要为迟到的“国民待遇”买单;其三,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调整,尤其是合村并组、村改居等过程,农民要增加经济负担;其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经济开发、土地整理以及农业新技术推广,增加了农民投资风险,有的甚至造成对农户经济的致命打击。
在上述四大背景下,农民新增或被强化的负担有:(1)城乡社保一体化, 参保农民人均年缴费额将超过1000元。(2)过重的医药费、 计划外生育户缴纳的社会抚养费,以及正在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或者大病统筹中的农户出资。(3)农民承受过重教育费负担已成为一个顽症。从东部某县的个案看,教育费负担大约占农民人均消费支出的8%。(4)农民拖拉机、三轮车、摩托车税费也是不小的负担。比如,东部S省某县一辆三轮车办驾驶证、行车证要700多元,养路费每年700元,证件年审费100元;F省某县每部摩托车平均175.25元/年,其中养路费48元、车船使用税31元、年检20元、保险105元、年检单项不合格调试费5元。(5)个体工商户交纳工商管理费60元/月,卫生费5元/月,其他收费210元(比如屠宰检疫费等)。(6)有线电视维护费每户13元/月(未并入市网的农户不需缴纳)。
五、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建议
农业要发展,综合生产能力需提高;农村需要加快建设、加快发展;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要改善,收入能力要提高。哪一项都需要钱,没有钱是绝对不行的。但国家、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财力有限,工业反哺和城市支持的力度还较弱。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民负担增加有其必然性。因此,农民负担不是靠堵、靠监督和高压政策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们建议:
第一,转变观念,逐步将“减轻农民负担”舆论宣传和社会心理,引导和调整到“合理农民负担”的社会舆论和心态上来。我们理解,取消或免征农业税并不是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终结,合理农民负担,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按照公平负担、合理负担、合法负担的原则,重新安排农村税费制度非常必要。
第二,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办法是发展农户、集体经济、农村社区工商业主经济,使农户、集体、工商业主具备承受合理负担经济实力;同时,通过制度规范,使村域三大经济成分合理分摊公共产品生产的成本。
第三,当前,工业反哺育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目标,首先应该卸掉农民身上背负了50多年、本应由公共财政承担的沉重负担;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供给体系以及运作机制,使农民真正享受公共财政的阳光,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第四,中国新乡村建设,不仅是现代化进程中防止农业衰落和农村凋敝的必然选择,而且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载体和落脚点;不仅是统筹城乡、工农互促、协调发展的关节点,而且对于我国预防通缩、拉动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重要作用。新乡村建设应该成为全国性的重要发展战略,建议及时启动并正确引导。新乡村建设一定要综合考虑国家财政、地方政府、村社组织和农民的承受能力,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合理分担、量力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