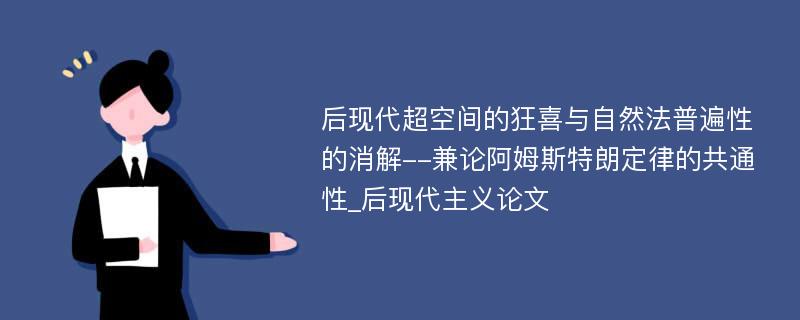
后现代超空间的迷幻与自然定律普适性的消解——评阿姆斯特朗的定律共相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律论文,迷幻论文,后现代论文,姆斯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定律问题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因而一直受到科学哲学家们的高度重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以倡导“心灵唯物论”而闻名于世的澳大利亚哲学家阿姆斯特朗(D.M.Armstrong)对传统的自然定律理论又展开了批判,提出了“定律共相论”,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但争议也很大。我认为,要对一个理论作出恰当的评价,不仅要指出该理论的长处与短处,而且要找出该理论局限性的根源何在,指明该理论前进的方向。正是从此宗旨出发,本文撇开该理论论证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另辟蹊径,从后现代文化角度去评判。本文认为,定律共相论实质上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本体论上的延伸与表现,它们都同源于对后现代超空间的迷幻,是后现代社会高度发展、而人们的思维能力尚未适应的产物,因而它们有着相似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一)
后现代主义是目前流行于欧美思想界的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它最早孕育于30年代的现代主义思潮母体中,60年代才开始崭露头角。到70、80年代,随着伽达默尔与德里达、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大师的理论之争以及罗蒂无镜哲学的阐释,它风靡欧美思想界,影响涉及建筑学、绘画、音乐、社会学、政治学与哲学等领域。随着后现代概念的广泛运用,后现代主义思想体系也层出不穷,分歧也很大,以至于有人说,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后现代思想。
后现代主义思潮尽管形态各异,但它也有共同的或基本的理论特证,即反中心性、反元话语、反二元论与反体系性。表现在哲学上就是消解认识的晰明性、价值本体的终极性与真理的永恒性。后现代主义思潮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语言表征怀疑论与价值虚无论,它怀疑、甚至否认人的认识能力、语言的指称性以及理论的价值,是后现代社会高速发展产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科学技术与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代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首先,在政治领域,如美国学者弗·詹姆逊所说的,它从垄断资本主义向晚期资本主义过渡,以其“有活力的、有原创力的、全球性的科技扩张”向被前资本主义所包围的第三世界农业及第一世界的文化领域渗透、进攻,进行着全球性的经济侵略与文化渗透,同时资本主义也呈现出政治的多极化与文化的多元化倾向;在经济领域,它由以工业生产为主的现代社会向以服务性行业为主的后工业、后现代社会过渡,享乐主义流行,黄色文化泛滥。信息的社会化与商品化,全球性的、多元的和非中心的信息网络的形成,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对传统的认识论与哲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
这种时代性巨大变化的结果是迫使人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发生根本变化。首先是机械论的世界观必须被抛弃。世界政治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以及科学对大量不确定、无序现象的研究与发现,尤其是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发现,迫使人们放弃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公式以及决定论性质的定律来说明与解释世界,放弃统一性与整体性,主张多元性与开放性,强调变革与创新,承认并容忍差异;其次是主体意识的消失。随着电脑的广泛运用,计算机网络的形成,世界各地的信息被发达的通讯设备迅速地传递、压缩、改编、储存,同时又被大规模地、高速度地再生产、再抟播,世界成为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人们在庞大的信息系统中不断地受到来自电视、广播、报纸、广告等传播媒介商品化信息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商品化信息的影响与干扰,甚至人们的潜意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与干扰,人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外在行为严格意义上的主体;再次则是传统的镜喻认识论或机械反映论必须被抛弃。正如法国解构理论家所预言的,商品物化的最后阶段是形象,商品拜物教的最后形态是将物转化为物的形象。在后现代社会,艺术成为“类象”,即成为没有原本的摹本。形象、照片、摄像、电视、电影以及商品的复制与再生产,所有一切都成为类象。(Simulacrum)人们在电视、录像与艺术作品中看到的“现实”不再是自然现实本身,而只是现实的影像,是人工现实或第二自然。语言、符号的意义由于通讯规模的庞大和反复传播也变得日益模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受到极大削弱,尤其是语言的描述功能日益萎缩,而叙事功能、演绎功能与虚构功能日益膨胀,语言体系与文本自我关涉,失去了原本的指称意义,它已不再描叙述外在的客观现实,而是描叙语言化、观念化的人工现实,这样,文本成为一种语言游戏。所以,艺术家瓦豪(A.warhol)说:“当我照镜子时,我什么都没看见。人们称我是一面镜子,镜子照镜子,能照见什么呢?”①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认识论自然被抛弃。
但是,由于后现代社会变化的速度、规模及其多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与适应力,后现代人在抛弃了旧的观念体系后,并未能及时地调整过来、建立新的观念体系以适应后现代社会,而是陷入了一种丧失空间定位能力的迷幻状态,即类似精神分裂症的迷幻状态,也就是詹姆逊(F·Jameson)所说的“后现代超空间”的迷幻状态。所谓超空间是相对于正常空间而言的,正常的空间由事物构成,具有一定的结构与秩序,人们在其中也能感受到事物发展的时间性与历史性。但是,在后现代社会,人们面对全球性的、多元的、非中心的信息网络丧失了空间定位能力,莫知所处,陷入了一种类似精神分裂症的幻觉状态,人们的时间感完全空间化,而空间感也缺乏组织性与结构性,事物仿佛是杂乱无章地堆集在没有时间的空间中,人们对外在世界丧失了现实感、深度感与时间感,语言体系也丧失了原有的意义,人们不能用它来把自己的生活经历统一起来。拉康所谓示意链的崩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正是由于这种对后现代超空间的迷幻,后现人代艺术丧失了传统的美学趣味,从而具有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性丧失、距离感消失四大特征。后现代思想家、哲学家则走上了反元话语、反中心性、反同一性的道路,他们只消解、摧毁传统理论,但不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新理论或新方法,这在罗蒂的理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显然,后现代人示意链的崩溃,或者说对后现代超空间的“迷幻”,实际上已蕴含着对自然定律普适性的消解。尽管后现代思想家大都局限于话语领域,强调能指的独立性、文本的歧义性与游戏性,否认真理符合论,很少涉及本体论领域,因为“如果真理不是一个与非人类的实在相符合的问题,那么关于一个不管我们是否认识都会约束我们的规律的观念就不能有任何意义。”②但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不可能不影响到哲学对世界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思潮本身也需要本体论的依据与证明,即使是库恩的范式理论与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理论没有这种根据,也还是显得无力。因此,如何对自然变化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与非决定论性作出本体论的说明,不仅是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物理学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后现代主义发展的内在需要,成为科学哲学们关注的首要问题。阿姆斯特朗的自然定律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二)
阿姆斯特朗在七十年代就已开始酝酿他的自然定律理论,到八十年代才形成体系,力作《自然定律是什么》(1983)的出版是其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在欧美思想界,这段时间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发展的鼎盛时期,科学哲学界也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阿姆斯物朗反对塞拉斯、司马特等人提倡的形而上学实在论,倡导自然主义实在论,主张把科学哲学的研究建立在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反对语义对应真理论,显然是受到这股思潮影响的结果。这一点在他的自然定律理论中也得到体现。
阿姆斯物朗的定律理论是建立在对传统定律理论批判基础上的。休漠是传统定律理论的开山鼻祖,现代定律理论无不受到他的影响。在休谟看来,所谓自然定律就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齐一性或规则性,因果联系是这种规则性联系的一种。到本世纪六十年代,乔治·蒙纳(George Monler)抛弃了其中因果理论,直接把普适的宇宙齐一性等同于自然定律。
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定律理论研究的深入,这种理论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阿姆斯特朗指出,首先,有些自然定律就不具有普适性,如统计定律和函数就不是普遍成立的;其次,许多现象具有普适的齐一性,但并不是自然定律,如“旬独角兽并不存在”这一现象具有普适性,但并不是自然定律;换句话说,这个理论存在着如何区分偶然的齐一性与作为定律表现形式的宇宙齐一性问题;再次,宇宙齐一性缺乏自然定律具有的必然联系的特征,对已观察的自然齐一性也没有给出应有的解释。尤其重要的是,自然定律应当说明尚未实现的可能现象即逆事实(Counterfactual),但宇宙齐一性理论无法做到这一点;最后,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这种朴素的定律理论,它也无法避免归纳怀疑。古德曼(N.Goodman)1954年提出的“grue”。悖论也是该理论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
由于朴素规则论面临着这重重困难,许多哲学家便不断对它进行批判与修正,最终形成了种种精致规则论,其中以雷姆斯和路易斯提倡的体系规则论在学术界影响最大。按照这种理论,宇宙齐一性成为自然定律的根本条件是,它应当是某个公理体系当中的命题,或由该公理体系推演出来的命题,而且,该公理体系应当是由各真值命题按照最简单方式组合而成的,否则,就不构成自然定律。但是,阿姆斯特朗指出,该理论也有问题:首先,它具有人类中心论倾向,因为它涉及到公理体系简单性的标准问题;其次,它同样面临着古德曼“grue”悖论的挑战和如何说明逆事实的问题;最后,它还面临着产生同等一致而又互不相容的两个公理体系的可能性问题,如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
在对上述诸定律理论提出批判后,阿姆斯特朗为解决上述理论所面临的困难,提出了定律共相论。他认为,传统的经验主义定律理论之所以不能对自然定律作出恰当的说明,是因为它分析事物本身,而忽视了事物的性质与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忽视了事物的共相。实际上,要想对自然定律作出恰当的说明,就必须抓住事物的共相,而不应分析事物的现象以寻找所谓的齐一性。由此,他建立了以“共相”概念为中心的定律理论。
他认为,自然定律是事物的共相之间具有的一种迫使关系(或可能关系),是一种高级事态。所谓共相,是阿姆斯物朗对事物的性质和关系的合称;所有真正的自然定律都应当是可例证定律,所有的不可例证律陈述都属于逆事实陈述,即属于条件从句陈述,这种定律的存在依赖于高级定律的存在,一旦设定高级的可例证定律并满足逆事实陈述所需要的条件,那么不可例证定律就可以从中演绎出来;函数定律就是控制低级定律的高级定律,在独立变量取代特定值后,低级定律就可以从函数定律中推演出来;所谓高级定律就是事物的高级共相(即事物的性质之间和关系之间的性质或关系)之间的关系,这些高级共相为包含在低级定律中的低级共相所例证,不可还原的概率定律也是事物的共相之间的关系,决定论性的定律是概率定律的极限(即概率为1)。
既然自然定律是事物的共相之间的关系,那么,自然定律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呢?阿姆斯特朗根据他自己独特的可能组合理论指出,自然定律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因为如果自然定律是事物的共相之间的关系,事物具有某种性质或与其它事物具有某种关系本是偶然的,那么它具有某种性质或关系导致它具有另一性质或关系也是偶然的,因为它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完全可能具有别的性质或关系。换句话说,事物在不同的可能状态中可以具有不同的性质或关系,并导致它可以具有另一不同的性质或关系。所以说,自然定律是事物共相之间的迫使(或可能)关系,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
应当承认,他的定律共相论比之前述诸种定律理论是一大进步,它解决了传统定律理论所面临的区分偶然齐一性与作为定律表现形式的宇宙齐一性问题,解决了有关函数定律、概率定律以及逆事实的说明问题,此外,由于它从事物的共相角度入手,也就避免了定律解释中的归纳怀疑问题,古德曼的“grue”悖论也随之迎刃而解,这些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是它否认自然定律的齐一性与必然性,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自然定律的普适性。这是对传统的经验主义定律理论的一大挑战,也是对人们关于自然、关于宇宙的直觉的一大挑战,因而引起学术界的论战。
(三)
从直觉上讲,我们感觉到经验论者关于定律的规则论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自然界尽管千变万化,但其变化总还是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与内在关联性,自然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整体。但是,在阿姆斯特朗那里,自然定律并不是事物共相之间逻辑的必然关系,而是共相之间非逻辑的必然关系即迫使关系,它提供给我们的自然图景富于变化性,可以说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让人感到变化莫测,缺乏规律性、有机性与整体性,这一点显然不如传统理论。
从阿姆斯特朗定律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来讲,它是建立在自然主义实在论和他本人的可能组合论基础上。按照他的实在论与可能理论,现实世界的确只有一个(即时空世界),但现实世界诸要素的不同组合会形成难以计数的可能世界,在不同的可能世界,相同的要素完全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甚至是不相容的性质,要素之间具有的关系也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事物具有某种性质是偶然的,它由这种性质导致具有另一种性质当然也是偶然的,不具有逻辑的必然性。显然,他的定律理论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从理论的出发点来讲,它是从事物的共相入手,也比经验主义理论从诸种事物的现象入手合理得多。因为诸种事物的现象之间有同有异,我们用宇宙齐一性只能说明其“同”的一面,不能说明“异”的一面。况且,宇宙齐一性吸只是对诸种事物“同”的一面所作出的高度概括,并未对“同”和“异”这两面作出合理的解释。相反,如果用事物的共相之间在某种条件下所具有的非逻辑的必然性就为这两方面作出了解释,并且为事物变化的多样性、随机性提供了内在根据,比经验主义的定律理论在多变的自然界寻找僵硬的宇宙齐一性要令人信服得多。但是,他的理论提供给我们的世界图景的确只具有非逻辑的必然性或随机性,体现不出任何历史性,有机性与整体性。尤其是按照他的理论推论,可以得出结论,在自然界的千变万化中,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换句话说,“什么都可能”,这显然不符合人们的常识与直觉。
如此说来,他的理论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我认为,问题出在他的共相理论本身。他的定律理论、可能理论都是建立在他的共相理论基础上的。按照他的共相理论,作为单元共相的性质与作为抽象个体的事物之间是一种属性关系,个体事物=抽象个体(即无性质的事物)+性质,这样,性质与事物之间只具有外在的偶然关系。虽然他曾认真地比较过在性质与事物关系问题上的“属性论”与“层次论”,所谓层次论就是认为事物本身只由一层层性质构成,别无他物,他得出的结论是两种理论各有优缺点,所起作用大致相等。但他基本上还是倾向于属性论,这就导致了他的“什么都可能”的可能世界理论及定律偶然理论,这一点是他始料未及的。从他的定律理论本身来讲,如前所述,他从事物的共相入手分析是要比从事物的现象本身分析有进步,但是,他所侧重的是作为个体的同一事物的共相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不同事物的共相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这就使他的世界图景缺整体性、有机性与内在关联性,自然变化的历史性与多样性完全体现在世界变化的各种逻辑的可能性之中,世界的历史性、时间性与深度性完全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的此在性、空间性与平面性。如果换个角度,既从同一事物的共相之间分析,又注意不同事物的共相之间的内在关联,事物与性质不是处于外在的属性关系中,而是处于某种内在的关联之中,那么情形就完全不一样,该理论所具有的缺陷就有可能避免。在这方面,中国上古时期流传的阴阳理论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典范。在它那里,阴与阳既可以指事物的性质,也可以指事物本身,同一事物及不同事物之间都用阴阳理论来说明,它所提供的世界图景既具有偶然性,随机性,又具有必然性与有机性,整个世界既具有三维的空间性,也具有一维的时间性,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整体性。当然,该理论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在此不赘言。
实际上,阿姆斯特朗本人对这种“什么都可能”的本体论也持怀疑态度。在其力作《自然定律是什么》中,他明确指出:“尽管我不相信可能世界的真正实在性,甚至不相信事情或许是如此意义上的真正实在性,但是除非动用可能世界理论,否则无法解决这个问题。”③由此可见,他是出于理论说明与解释的需要而运用这种可能世界理论。值得深思的是,他既然不相信这种可能世界理论,为什么又要构造与运用这种理论呢?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我认为,其症结就在于前文所分析的后现代超空间的迷幻。后现代社会变化的速度与发展的规模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与适应力,哲学家们面对后现代社会的巨大变化难以从理论上进行合理的说明,因此只得在理论上主张“怎么都行”,对理论的解释也主张多元化、开放性,否认普遍真理,否认认识的客观性与解释的唯一性,否认人们的认识能力,反映到本体论领域自然是“什么都可能”,否认自然定律的普适性与齐一性,否认自然定律的必然性(逻辑上的),只承认自然定律的偶然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阿姆斯特朗的定律理论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本体论领域的再现,是后现代哲学的逻辑延伸。所以,阿姆斯特朗尽管出于本能的直觉不相信这种可能世界理论,但出于理论解释与理解的需要,又不得不构造这种理论,并运用达种理论去解决问题。这种悖论或许就是哲学理论及其他理论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总之,阿姆斯特朗的自然定律理论合理之处在于为自然界、尤其为后现代社会变化的多样性与各种可能性提供了说明,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后现代哲学否认元叙事的合法性也提供了本体论的依据,但它未能说明自然界及后现代社会变化的有机性、整体性及历史性,其根源在于对后现代超空间的迷幻,这是它的不足之处,也是该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前进的方向。同理,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及前进的方向。
注释:
①《当代法国哲学》,1987年英文版第117页,A·菲利普与克里夫特编。
②R·罗蒂:《后哲学文化》,1992年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51页。
③D·M·阿姆斯特朗:《自然定律是什么》,1983年英文版,第1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