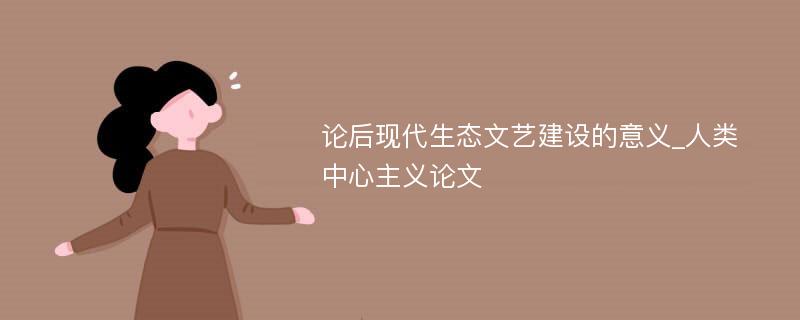
论生态文艺学的后现代建设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后现代论文,生态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2)01-0126-05
当今之世,所向披靡的现代文明已经危及人类和地球的持续存在,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显示出存在根基崩溃的前兆。超越现代性是人类不可避免的选择,而纯然批判性、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必须渐渐让位于建设性的、创造性的后现代主义,生态世界观、生态文明无疑是超越现代性的最佳选择。生态文艺学的兴起与繁荣具有重要的后现代建设意义,它促使文学重新履行对大自然的守护功能,并能够深入地阐释文艺审美本质,具有促使文艺学范式转换的意义。
一、文学对大自然的守护意义
现代自然科学的机械论自然观主宰着现代人的头脑,而尼采曾说:“一个本质上机械的世界是一个本质上无意义的世界!”[1]256这种机械论世界观所阐释出来的无意义世界是一个不适宜于人的心灵的世界,会导致大自然乃至整个世界的溃败。生态世界观的核心要义则是强调世界万事万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从整体性角度观照世界。生态自然观让我们看到,人决不能把自己从普遍联系的自然生命之流中孤立出来,也不能以一种机械论式的态度对待大自然,把大自然看作只给人类提供满足需要的资源库,而应从更高的整体生命立场上看待大自然,把人类重新放入自然生命的整体背景中。生态自然观深深地意识到人只有首先放弃对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征服者形象,尽力去保护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自然的生命之流才会重新接纳人,人也才会有归根复命之可能。
生态文艺学就是奠基于这种生态自然观,它促使文学实现对大自然的守护功能。也就是说,文艺通过对人的精神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充分地意识到自己与自然生态之间的亲密关系,从而摆脱对大自然的暴力的征服与奸狡的利用态度,以一种生态意识对待世间万物,守护自然生态,融入气韵生动的大化生命中,与万物一同摇曳于宇宙大生命枝头,生机勃勃,仪态万千。
文艺的生态守护功能首先表现于对人的精神的疏导之中。虽然文艺从根源上看来自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生态感应,但是,随着人类文明渐渐地远离自然生态,渐渐地把目光局限于人类自身,尤其是现代文明对人类中心主义极度张扬,使得人类丧失了更为宏阔的生态眼光。因此,文艺的生态功能对人而言,首先是让人突破个体化原理对人的拘囚,让人能越过欲望、知性对自我的局限,领会到人与人的生命相通性,他人与自我的普遍联系性。在荣格看来,艺术的终极目的是对集体无意识的传达,“艺术家并不顺应个人的冲动,他顺应集体生活之流。这集体生活之流不是直接起自意识,而是起自现代精神的集体无意识”[2]154。这种集体无意识在文艺中就凝聚为某种特定的原型,“一旦原型的情境发生,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2]121其实所谓整个族类力量对人的超度,无非是说人通过文学感受到了所有人的生命终极相通性,并被那种大生命的雄浑力量慑服而跃入终极的自由境界。
更为关键的是,文艺试图把人带出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让人能充分感受到自然万物的本性。马尔库塞曾说:“艺术通过让物化的世界讲话、唱歌或起舞,来同物化作斗争。”[3]“物化”主要是指人对自然万物的机械论态度,即忽视万物的本然生命,仅把它们纳入到人的征服与利用的范围中;艺术就是要把万物从人的这种宰制中解放出来,恢复盎然生机。什克洛夫斯基认为:“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4]人把石头仅当作一种可资利用的东西带到身边加以利用时,人恰恰是远离了石头;而当人在艺术中尊重石头的本性,使石头更其成为石头时,石头才向人显示出其本真一面,人才能从这种本真之中获得人性的丰富可能。在艺术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亦如此。因此,海德格尔说:“诗并不飞翔凌越大地之上以逃避大地的羁绊,盘旋其上。正是诗,首次将人带回大地,使人属于这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5]文艺把人带回大地,也就是把人曾经狂妄自大的灵魂重新变得谦卑,让它重新以万物之一员的身份进入宇宙生命之根中,以敬畏、欣赏、平等的眼光对待自然万物。
文艺对自然生态的守护功能在中国表现得更为充分。中国文艺家们特别能突破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善于以物观物,竭力护持自然生态的本真之美。《庄子·至乐》中的鲁侯养鸟的寓言,就颇能说明问题。鲁侯以人养养鸟,就是把人的标准强加于自然,结果是自然的溃败;而以鸟养养鸟,就是以自然的方式对自然,自然才能生机盎然,人也才能亲领天机。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就曾对人以自己病态之美的标准强加于自然生命愤愤不平,主张人应该纵情自然,欣赏自然生态的本真之美。这是真正对自然生态的守护,也是对人类种种畸趣的抗争。
其实,当我们对自然生态“屈物之性以适吾性”时,最终人性也受到伤害,也被扭曲。而当我们能顺物性,让自然万物“各适其天”时,人性也将自由展开。正如有的论者所言:“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是与我们相分离的,是由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的,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孤立的人,我们待人接物的动机也将是操纵与计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获得一种对整个世界的直觉的和想象的感觉,认为它有着一种也包含于我们之中的秩序,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6]95但是,现时代里,人类与自然宇宙的联系被无情地割断了。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对现代文明对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大肆摧毁极为担忧,他曾写道:“一旦树叶凋落,/甚至连上帝也不能使它返回树身。//一旦人类生活与活生生的宇宙联系被击破/人最后变得以自我为中心,/不管什么人,不管是上帝还是基督/都无法挽回这种联系。//只有死亡通过分解的漫长过程,/能够溶化分裂的生活。/经过树根旁边的黑暗的冥河,/再次溶进生命之树的流动的汁液。”[7]劳伦斯的诗歌恐怕不是危言耸听,彻底的人类中心主义只能把人类的生活带向败坏,最后只有死亡的轮回才能赋予生命又一次机会。生态文艺学非常重要的后现代建设意义之一,就是促使文学与现代生态学、量子力学、相对论乃至基因技术等自然科学一道为自然的复魅而努力,充分发挥对自然生态的守护功能。
二、文艺审美本质的揭示意义
生态文艺学的后现代建设意义还表现于对文艺审美本质的揭示中。鲁枢元曾指出:“艺术的价值也是精神的价值,真正的艺术精神等于生态精神。”[8]388曾永成也说:“对文艺活动进行生态学审视之所以可能,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文艺活动作为一种审美活动本来就是一种生态性的存在。”[9]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只有从生态文艺学角度才能真正揭示出文艺审美的本质属性。
在此问题上,张世英对人的精神发展阶段的看法具有启示意义。在他看来,人的精神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划分为原始的天人合一、主客二分和高级的天人合一这样三个阶段。原始的天人合一基本上是无主客、无自我意识的阶段,例如原始人、婴幼儿就基本上是处于此一阶段。主客二分则包括意识、认识、实践三个小阶段,人类的大部分活动,如自然科学实践、经济政治实践、道德实践都是此阶段的活动,人把浑然世界划分为主客不同的两部分,或改造客体,或改造主体,世界于是处于永无休止的对立之中。而更高级的天人合一,则是原始的天人合一在更高阶段上的回复,它泯除了主客之分,超越了本能欲望,超越了知识,超越了功利,超越了道德意识,达到对天地万物一体之体验[10]。
在原始的天人合一阶段,人与自然万物虽然融为一体,但是由于人的理性并未足够觉醒,人的力量弱小,人性的丰富性尚处于浑然之中,所有与自然宇宙相融的生趣往往是短暂的,非自觉的,随时有可能被大自然所中断。而在主客两分阶段,虽然人获得了足够的主体性,理性觉醒,获得了力量,但由于这种主客两分的思维惯性使然,人往往或受制于客体,或无法按照自然万物的本性来对待它们,结果是大肆扭曲万物,以满足人的主体所需,最终只能导致万物生命的溃败,而人自身也被从万物的生命之流中逐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这种主客两分的精神是不自由、有限的,它把人性引向歧途。因此,人向更高的精神阶段的超越迫不及待。更高级的天人合一阶段中,其实质也就是生态世界观阶段中,人认识到了人是有限的,人性是有缺陷的,意识到万物万事的普遍联系特点,人应充分地体验宇宙大化流行,融入大化生命之中,克服自我的孤立,获得对永恒的体验,从而领悟生命之意义。
在原始的天人合一阶段,人由于缺乏足够的自我意识,与自然万物又处于一种浑然不分的境地,文艺审美往往只是不经意的自然流露,而其必要性并未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主客二分的精神阶段,人虽说由于理性的觉醒而力量大增,但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又让他身受羁绊,无法获得自由。更为根本的是,他被自身的思维方式逐出了自然宇宙的生命之流,陷于孤立之中,生命浑然之感被割裂,意义沦丧,因此他就企盼着对主客二分的世界的超越,而文艺审美恰恰是在这种超越之中产生的。文艺审美对人而言,首先是出于一种生态需要,即人从脱离了原始的天人合一阶段,就一直有种自我孤立、自我隔绝的倾向,而这种孤立与隔绝又使他与生命本真体验失之交臂,因此他就急于超越这种孤立与隔绝,融入万物一体之中。其次,文艺审美最终超越了主客二分的世界观,通向一种生态境界。张世英曾说:“要进入澄明之境,就要有这种万物一体——万有相通的体会。没有这种领会,也就达不到澄明之境,这种领会乃是澄明之境的根本要素。”[11]133这种万物一体、主客不分的境界就是一种普遍联系、大化流行的生态境界。
在文艺起源诸说中,模仿说和表现说是最为深入人心的。模仿说强调文艺对外在事物的模仿,而表现说强调对内在情感的抒发。其实,若能从文艺审美的生态本性看,无论是模仿说,还是表现说,无非是追求人与万事万物最终的一体感而已。人模仿外界事物是源于人与外在事物之间的深层感应与联系,是人性在突破个我的孤立寻求他者的呼应,而人抒发自己的感情也无非是为了唤醒他人的同感,从而达成生命之间深层的联系。黑格尔曾说:“艺术对于人的目的在于让他在外物界寻回自我。”[12]如果把此自我理解为狭隘的属人的小自我,这种说法就是不够确切的。那样人通过外物界只能与人自身打交道,只能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循环,艺术就无法对人性构成一种丰富,这是较为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看法。如果我们把这个自我理解为一种更为广大的生态自我,那就合理了。
文艺审美的深层指向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世界观。从尼采对悲剧的研究结论也可看出他对生态世界观的深深领悟。尼采说:“谁只要感觉到自我变化的冲动,渴望,谁就是戏剧家。”[1]31为何人会有自我变化的冲动?为何人会渴望从别的肉体和灵魂向外说话?归根到底,不过是说人自从与宇宙大化生命分离以来,由于个体化原理进入到孤立的存在之中,饱受生命意义飘零之苦,于是就渴望通过戏剧这种艺术形式超越个我的孤立,追求普遍联系的大化生命,追求生命的深层意义。
三、文艺学的范式转换意义
生态文艺学的后现代建设意义还表现于对文艺学的范式转换意义中。在我国,从1949年到20世纪90年代,特色鲜明的文艺学基本上是在反映论和主体论两个范式中展开的。反映论文艺学以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为代表,主要盛行于建国后到80年代初。而主体论文艺学以刘再复的《文学的反思》和九歌的《主体论文艺学》为代表,从80年代中期以后到90年代较为突出。至于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等则往往是取两者的中道,或加以混合,而其他数不胜数的文艺学编著也大都是在这两种范式中言说,甚或没有自己鲜明立场,纯就文学理论中较为“客观的”一些问题略加阐释。
反映论文艺学旗帜鲜明地把马列主义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理论基础,从意识反映存在这个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出发,把文学视作客观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是古典的模仿论的现代回响。“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13]别林斯基的这句话成了反映论文艺学立论的根基之一,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成了对文学最基本的认识。反映论文艺学强调强调客观现实对文学的决定作用,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具有一种机械决定论倾向,很容易扼杀作家的创作活力,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定位,显然与文学的本性相去甚远,有失偏颇。
在主体论文艺学倡导者看来,“以认识论为理论基础的反映论文艺学,把文学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反映性的认识关系,片面地突出了文学主客体关系中的一种非本质性的关系;在文学主客体之间的这种反映性的认识关系中,则无条件地强调作为客体的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颠倒了文学主体与客体的地位和作用,未能把握文学活动的动因和动力”[14]。主体论文艺学要把人的主体性在文学中凸显出来,强调完整的文学创造过程由作为创造主体的文学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共同承担,还特别强调这三种主体的内在精神世界,认为这既是文学创造的内在源泉,也是文学必须表现的中心。刘再复因此要求文学家要向内(灵魂/性格/精神)、向深(深层精神主体)、向我(个性)拓展“人学”。“文学并不以社会生活为表现对象,而是以创作主体对人生的切身体验为创作对象。”[14]与反映论文艺学相比,主体论文艺学把文学的重心从客体转到了主体上了。在文学属性上,它明显地开始重视审美属性;在文学功能观方面,它强调文学对主体精神的发展功能。主体论文艺学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的确具有解放性力量,它对创作主体的高扬是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对反映论文艺学具有补偏救弊的功用。
从表面上看,反映论文艺学强调的是文学与客观的社会现实的关系,而主体论文艺学强调的是文学与主体的切身体验的关系,两者具有很大的歧异性,但细加审视,可以发觉两者在许多方面具有共同性。这两种文艺学都是在一种现代性语境中展开的。现代性是以主客二分的二元论为根基的,心与物、人与自然、中心与边缘等二分法由此而成。无论是反映论文艺学,还是主体论文艺学,都是以主客二分为根基的,虽说两者所强调的是不同方面。此外,主客二分后,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就成了现代性的又一个根本特征。主体论文艺学对人的主体性的追寻是它的显著特征,就不必去说。而反映论文艺学从表面上看是人的主体性的遮蔽,让人误以为它与现代性了不相关。其实,这是一种误识。反映论文艺学对客体的强调最终还是落实在人的主体性上的,这从其把文学视为人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即可知。只不过反映论文艺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意义上的主体性,而主体论文艺学更强调倾向个人本位意义上的主体性而已。由此,我们又可发觉两者都具有鲜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特色。在反映论文艺学的视野中,大自然根本不具有自足的价值,即使是古人写的山水诗,它也要从其中找出社会意义也即属人的意义才肯罢休,无论是考察文学的性质还是文学的起源等问题,它都是在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中进行的。而主体论文艺学明确地承认,“人应该是目的性因素,而不是工具性因素”[15],“文学是人学”等。
那么反映论文艺学与主体论文艺学这种相通的立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必再复述主客两分、人类中心主义等倾向带来的现代性危机问题,我们要追问的是它们作为现代性语境中出现的文艺学范式的局限问题。
这两种文艺学范式最关键的局限在于它们建立在主客两分的世界图式、思维方式上,而文学的奥秘恰恰是对主客两分的世界图式、思维方式的超越。张世英曾说:“审美意识是一种人与物融为一体的境界,或者说是一种万物一体的主客不分的境界(严格说,是一种超主客的境界)……万物一体不仅是指人与人一体,而且指审美意识中人与物融为一体。”[11]252的确,他对文艺审美的本性的把握是很准确的,主客两分的世界图式是容纳不了文学的,这种思维方式也是无法真正深入到文学核心奥秘之处的。反映论文艺学把文学视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仅把握了文学的极为肤浅的属性之一,以此定论文学就必然是盲人摸象式的荒唐。而主体论文艺学把文学定位为主体的切身体验之表达,同样忽视了超越主客之外的审美本性问题。此外,这两种文艺学范式张扬人类中心主义,不约而同地倡导“文学是人学”之说,忽视了文学与更为广阔的宇宙自然之深层关联,正如有的论者说:“将文学定义为与自然失去了原始联系的人学既削弱了文学的丰富性,又看低了文学的价值。”[16]正是有了这些根本的局限,这两种文艺学范式必须被超越,一种新的能直逼文学本质属性也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文艺学范式必须凸显,那就是生态论文艺学,或直接称为生态文艺学。
如果说反映论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奠基于现代性的机械论世界观,两者又各有不同的侧重点的话,那么可以说生态论文艺学是奠基于后现代的生态世界观。生态文艺学的根本就是超越主客两分的世界图式、思维方式,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把文学纳入天、地、人、神的浑然存在系统来考察,承认文学不仅是人学,还是与自然宇宙息息相关的。刘锋杰曾说:“生态文艺学是一门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文艺与自然生态之间关系的学科。”[17]这个论断指出了生态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和对象,即研究方法是生态学视角,对象是文艺和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应该说,生态文艺学的研究出发点是文艺和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但若把其对象完全限定于此,就是没有注意到生态文艺学相对于反映论和主体论文艺学的范式转换意义了。
四、结语
超越现代性,最关键的无疑是超越现代性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方式,重新确认生命内在的生态联系,体认存在的内在同一性。生态文艺学就是在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向度上超越现代性的。鲁枢元曾说:“生态文艺批评把艺术想象当作乌托邦的精灵,志在‘重建宏大叙事,再造深度模式’,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艺批评。”[8]388的确,在解构性的后现代浪潮中,我们曾经迷失得太远,对一切宏大叙事、深度模式都避之唯恐不及,结果我们往往就被极其短视、平面的消费文化所掳获,完全丧失精神的尊严。而生态文艺学对生态意识的张扬,显然是一种有所为的建构,它对人类文明持一种有为的态度,希望人与自然、人与人重新修好,而不再像现代性所鼓吹的那样对自然竭尽榨取之能事,对异族或异阶层或异性的人无所不用其极。
当然,生态文艺学的出现也为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换找到了一条最好的通道。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曾经较为关注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也极富一种生态意识。但是进入现代语境后,文学与自然这一维度在文学研究中渐渐被忽视了,文学渐渐地变成了一种“人学”,文学研究往往也是对作为“人学”的文学的研究。在生态文艺学出现后,情形迥然不同。由于生态文艺学对生态世界观的再次彰显,使得它能从根本上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到位的后现代转换,从而有可能彻底激发出中国古代文论真正的生命力。
不过,生态文艺学的出现最为深远的意义也许还是表现于对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现代性罅隙的弥合中。现代文明独尊客观、冷静的自然科学,唯物、实证、分析倾向浓郁,从而与人文精神的距离日渐拉大,直至两者形成敌对态势。这种分裂无疑是人性的分裂,是文明的不幸。但是生态学精神慢慢地走向整体性,与人文精神开始不谋而合了。这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人类未来文明的生态转向就是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融合,而生态文艺学的推波助澜意义将日渐明显。
收稿日期:2011-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