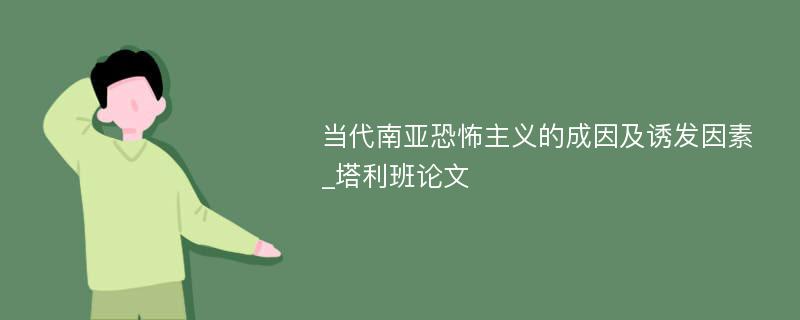
当代南亚恐怖主义的起源与诱发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亚论文,恐怖主义论文,起源论文,当代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508(2013)01-0007-08
南亚的恐怖主义问题极为严重,被公认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重灾区和全球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前沿地区。事实表明,南亚地区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要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南亚的恐怖主义袭击频发度冠全球之首。其中,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均为恐怖主义威胁尤为严重的南亚地区国家。①恐怖主义在南亚地区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有若干重要的历史诱因影响了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其中既有地区内部的因素,也有跨地区和国际范围的因素。今天该地区存在的严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挑战,均可从这些因素中找到渊源。但需要首先说明,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至今仍缺乏普遍接受的标准和确切定义,多从性质、特征、活动方式及实施手段等方面对其加以辨别。本文承认这一认知局限,因此不涉及对恐怖主义概念的辨析和论证,仅通过现象探讨当代南亚恐怖主义的起源与主要诱发因素。
一、伊斯兰化与“伊斯兰革命”
从较近的历史渊源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化与发生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其后阶段以伊斯兰“圣战”为招牌的国际恐怖主义提供了滋生土壤,并成为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挑战和暴力武装活动日益严峻的助推器。
1978年12月2日,以政变上台的巴军事领导人齐亚·哈克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在巴基斯坦实行伊斯兰教法,强调必须“纯洁和净化巴基斯坦”,使它成为一个强硬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坚固堡垒。②哈克试图使国家的法律、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与伊斯兰教的教法、价值观和传统相符,要求巴基斯坦人按传统伊斯兰教主张的方式生活。哈克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以清除非伊斯兰教的社会习俗。③重大举措包括建立伊斯兰议会(苏拉)和伊斯兰法院并赋予其极大的职权。伊斯兰议会的大多数成员为宗教学者和神职人员(毛拉),它取代了国民议会而成为国家的实际最高立法和咨询机构以及总统的顾问班子。伊斯兰法院由乌尔玛(拥有权威地位的宗教学者)组成,依据《古兰经》和《逊奈》(圣训)的教义对法律案例进行判决,负责监督国家的立法和司法事宜,确保符合伊斯兰思想和教规,甚至有权裁决政府的执法是否合乎伊斯兰教规。向各级法院的上诉必须递交伊斯兰法庭听证,任何亵渎先知的行为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④在经济领域,巴政府在1980年6月颁布了“扎卡特”法令(Zakat)和“乌萨尔”(Ushr)法令(也称“天课税法令”),宣布对国家的经济制度实行伊斯兰化。这些法令针对所有穆斯林个人和伊斯兰教组织、协会和机构,但什叶派等少数派穆斯林因激烈抗议而被排除在外。⑤
在社会文化领域,新闻媒体成为伊斯兰化过程中首当其冲的目标。政府要求电视和广播一律用阿拉伯语播报新闻,女性主持人出现时必须遮面,祷告钟声定时在广播和电视上反复播放,提醒祈祷的时间。作为伊斯兰化在教育方面的体现,政府要求国民必须学习伊斯兰教义和阿拉伯语,大学本科以上无论何种专业必修巴基斯坦研究和伊斯兰研究。巴基斯坦研究和伊斯兰教研究成为必修课。此外,政府提高了宗教导师在军队中的地位,以便吸引来自大学或宗教机构的高素质人才到军队担任教职。随着政府公开出面极力推崇伊斯兰学术,清真寺的数量有增无减。法令禁止人们斋月在公开场合饮食,一旦违反条规将被判以3个月的监禁和500卢比的罚金。哈克政府还在巴基斯坦首次引入“哈杜德”(Hadood)法令,规定依据《古兰经》和《逊奈》对饮酒、偷盗、通奸和鸡奸等行为加以惩罚。
齐亚·哈克的国家伊斯兰化政策广受争议,也导致教派暴力在巴国内频繁爆发,保守派宗教领导人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他们利用各种方式在大众中广泛散播针对非穆斯林国家和非穆斯林人口的不宽容教派思想。巴国内的哈拉菲派、什叶派穆斯林等少数教派在其执政期间受到歧视和非人道迫害。与此同时,由于强调不宽容,巴基斯坦与许多非穆斯林国家的矛盾愈演愈烈。后来的事实证明,哈克在执政期间重新阐释和推动伊斯兰教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导致原教旨主义在巴基斯坦迅速升腾的重要因素,为后来教派极端主义和武装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伊斯兰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后巴国内滋生蔓延的教派主义暴力和恐怖主义的重要背景线索。
与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化相比,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是影响当代南亚恐怖主义的重要外部激励因素。1979年2月,由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的统治。这场带有强烈宗教和政治色彩的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了整个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格局。霍梅尼宣称,西方并非是进步的象征,西方文化是一种瘟疫或麻醉品,必须加以根除,只有伊斯兰教才是第三世界摆脱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压迫的真正解放者。在社会政治领域,霍梅尼提出“法理学家监护”(velayat-e faqih)的观念,强调无论政府还是穆斯林个人都需要接受伊斯兰教法理学家的“监护”,由后者治理和监督国家;这种“监护”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祈祷和斋戒,它能确保伊斯兰教不背离传统教法,并消除贫穷、不公正和外国“异教徒”对穆斯林土地的掠夺。⑥
伊斯兰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强大的冲击波。一方面,它将矛头直接指向西方及其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盟友,致力消除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穆斯林国家的渗透,宣扬伊斯兰教文化的复兴。但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通过鼓吹在穆斯林世界反美(反西方)、反资本主义、反世俗主义、反社会不公的政治纲领并付诸实践,在扩大伊斯兰教的国际影响的同时,也促成了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影响了阿富汗、南亚及其他地区的伊斯兰“圣战”。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当两伊战争约束后,“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的辐射范围超出传统的什叶派地区,迅速输往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逊尼派穆斯林居主体地位的地区,推动了这些地区的伊斯兰“圣战”运动。⑦在20世纪80年代,中东国家发生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美国虽然支持同期阿富汗境内抗击苏联的伊斯兰“圣战”,但日益关切恐怖主义在中东地区的迅速崛起。
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局势此时也在与伊斯兰革命悄然发生联动。有学者注意到,巴基斯坦的宗教少数派什叶派不仅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也从这次革命中得到启示,希望在巴国内也能发生伊朗式革命。并且在伊斯兰复兴的背景下,当时阿富汗境内的“圣战”是伊朗革命的继续与发展。如果说伊朗革命对巴基斯坦的什叶派产生了示范效果,那么阿富汗的“圣战”尤其是塔利班政权的建立,也对巴基斯坦的逊尼派起了示范作用。在阿富汗抗苏战争期间,巴国内伊斯兰武装组织的数量急剧上升,并向自己认定的目标发动“圣战”。⑧
二、阿富汗抗苏战争与伊斯兰“圣战”跨国化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并扶持亲苏阿富汗势力执政,阿境内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开展了反抗苏联军事占领的武装斗争。在抵抗苏联入侵期间,这些“圣战”组织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其中美国、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作用最为显著。美国和沙特出于复杂的利益考虑,不断向“圣战”组织提供大量援助,支持其抗击苏联,巴基斯坦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中介作用。
在阿富汗抗苏战争期间,美国向阿境内的“圣战者”(穆贾赫丁)武装组织提供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被视为美国中情局历时最长、最昂贵和最隐秘的行动之一。这项称为“旋风行动”的计划是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来具体实施的。在此期间,约有至少30亿美元的美国武器装备源源不断运入阿富汗,用于训练和装备伊斯兰抵抗组织。里根政府时期,出于在全球范围围堵苏联扩张的需要,开始将支持阿富汗“圣战者”作为美国的正式外交政策。里根公开称赞“圣战者”是“自由战士”。⑨里根政府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上依赖的主要智囊是美国传统基金会,支持“圣战者”的政策也是该智库影响的产物。传统基金会学者约翰斯(Michael Johns)认为,美国对“圣战者”的支持不仅能迫使苏联在阿富汗转入守势,而且能消除外界对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军事扩张不可阻挡的担心。⑩对美国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圣战者”中不少形成其后塔利班的基本力量。
受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斯兰革命和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崛起的影响,南亚地区的暴力武装活动和恐怖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呈现跨国化特点。在抗苏战争期间,有不少阿拉伯国家的“圣战”自愿者纷纷前往阿富汗参加战斗,并得到沙特等保守派伊斯兰国家的支持。(11)这些“圣战”自愿者称自己为“阿拉伯-阿富汗人”。阿境内的伊斯兰“圣战者”除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外,也来自索马里、苏丹、车臣、波黑、孟加拉国和东南亚等其他穆斯林国家和地区。在此期间,大量多国籍“圣战者”穿越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进入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的巴西北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该地区出现了许多跨国武装人员的训练营地。伴随这一趋势,枪支文化和毒品走私开始在整个“金星月”地区泛滥,传播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宗教学校大量涌现。苏联1989年从阿富汗撤军后,阿富汗国内爆发激烈内战,绝大多数国际化“圣战者”并未解除武装,他们中许多人训练有素、久历战阵,继续在阿富汗及南亚其他地区开展暴力武装活动,并介入在北非、印控克什米尔、俄罗斯车臣、中国新疆、波斯尼亚和菲律宾等地的武装暴力叛乱和分离主义活动。在后来时期,这股跨国恐怖武装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并日益将攻击矛头指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以色列,成为美国与这些武装组织矛盾不断激化的最主要原因。
巴基斯坦因受美国驱使和自身的战略考虑而实际卷入了阿境内抗击苏联的伊斯兰“圣战”。一方面,巴基斯坦的角色在这一时期是美国在南亚制衡苏联的“前线国家”;另一方面,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介入和支持阿境内的“圣战”对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能有效增强它在阿富汗的政治影响,使其成为抵消来自印度的军事压力的“战略纵深”。巴向阿富汗境内“圣战”武装组织提供各种支持和援助,巴领土也成为中东与南亚间的通道地带。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及巴基斯坦不再是美国优先考虑的战略重点。但巴基斯坦支持阿国内“圣战”武装组织以影响其国内政局的政策并未改变。此外,巴阿边界两侧居住着跨境民族普什图人,持续战乱使大量阿富汗难民流入巴境,因此阿富汗尤其是巴阿边境地区的局势也直接影响巴国内安全与稳定。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巴在美国“反恐战争”打响前一直支持塔利班的原因。巴总统扎尔达里和巴前领导人穆沙拉夫均承认,恐怖主义组织是(巴基斯坦)过去多届政府“故意创造和培植的,它被当作一种实现某些短期战术目标的政策工具”。(12)
三、“基地”、塔利班与南亚本土伊斯兰武装组织的崛起
(一)“基地”组织
“基地”组织现身于1988年,由原籍沙特阿拉伯的“恐怖大亨”奥萨马·本·拉登组建,成员身份具有广泛国际色彩。在阿富汗抗苏战争时期,“基地”组织赞助、招募、输送、培训并武装了成千上万的“圣战者”,使之成为一支抵抗苏联入侵的有生力量。“基地”组织公开宣称的长远目标,是推翻“非伊斯兰”政权并从穆斯林国家驱逐西方势力和非穆斯林,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泛伊斯兰教哈里发国家。“基地”组织并提出要在地球上建立真主的统治、为真主的事业杀身成仁(献身为烈士)、纯洁伊斯兰教阵列、清除腐败堕落成分等。但在发展过程中,“基地”组织逐渐蜕变为一个声名狼藉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1998年2月,“基地”组织以“世界反犹太人和十字军圣战伊斯兰阵线”的名义发布宣言,呼吁在任何地方杀死美国公民(平民或军人)及其盟友是所有穆斯林的义务。2001年6月,以扎瓦希里为首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与“基地”组织合二为一。
“基地”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手段包括暗杀、爆炸、劫机、绑架、自杀袭击等。一些报告和拉登的公开言论甚至表明,“基地”组织欲获取并使用生化武器和核武器。“基地”组织将美国等西方国家、犹太人以及被视为“腐败堕落”或“不虔诚”的穆斯林国家列为攻击对象,袭击目标包括象征意义重大的公共建筑和外交与军事设施等。在“9·11”事件前后,由“基地”组织直接策划、参与的重要恐怖袭击包括:1993年对纽约世贸中心的爆炸袭击;1995-1996年期间针对沙特境内美国目标的一系列袭击事件;1998年8月对美国驻内罗毕(肯尼亚)和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两处使馆的爆炸袭击;2000年10月12日在也门亚丁湾对美国军舰“科尔号”的袭击;2001年9月11日在纽约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发生的被劫持客机撞击事件;2002年10月12日对印尼巴厘岛某夜总会的爆炸袭击;2003年5月,“基地”组织涉嫌实施并指挥同情它的其他组织对位于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西方国家目标实施的自杀袭击。(13)其中尤以“9·11”恐怖袭击,导致造成3000余人丧生的严重后果,也直接引发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动的“反恐战争”。
“基地”组织通过其跨国网络,资助、培训和支持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圣战”武装人员,包括巴基斯坦“虔诚军”、“真主军”及伊斯兰神学者协会;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黎巴嫩真主党;也门亚丁伊斯兰军;印尼伊斯兰祈祷团;菲律宾伊斯兰解放阵线、阿布沙耶夫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即东突)等。连接“基地”组织与这些组织的精神纽带,是共同持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念。1996年,拉登受苏丹政府驱逐,潜回阿富汗,成为刚掌权的塔利班政权的座上宾,并在阿境内直接策划了“9·11”事件等一系列重大恐怖袭击。“基地”组织拥有自身的资金来源。拉登家族是沙特的建筑业巨子,资产高达数亿美元,他用继承的大笔资产资助“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基地”组织也染指包括产毒贩毒在内的非法行业,并接受支持者的大批捐款。“反恐战争”开始后,“基地”组织的资金来源因美国的制裁而受到很大程度的阻断。
(二)塔利班
塔利班是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普什图人为主体的反政府武装组织,是2001年以来美国在阿富汗及南亚的“反恐战争”的主要打击对象之一。“塔利班”(Taliban)一词在普什图语中的含义是宗教学生或神学生。塔利班的前身是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抗苏战争中“圣战”游击队与在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学生的结合体。苏联1989年底撤出阿富汗后,阿国内出现政治权力真空,各派“圣战”组织和地方军阀拥兵自重,爆发内战。塔利班在内战中脱颖而出,成为阿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和武装势力。塔利班最高首领穆罕默德·奥马尔是一位神职人士(毛拉)和军事指挥员,在初期阶段因主张使阿富汗摆脱内战、腐败和犯罪而得到众多民众的支持。与此同时,来自巴基斯坦、沙特等外部势力的援助(资金、装备与训练)也对塔利班的迅速发展壮大发挥了重大作用。1996年,塔利班攻陷首都喀布尔,掌握了阿富汗的国家政权。
塔利班入主喀布尔后,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在阿国内实施原教旨主义统治。伊斯兰教法被重新解释,以便禁止和限制许多原来被视为合法的社会活动,包括不许妇女外出就业、接受教育和参加体育运动,妇女外出必须穿密不透风的“巴尔克”(罩袍);禁止电影、电视、音像、音乐、舞蹈及在家中悬挂画像;规定男性须将胡须保持在超过下巴以下一握拳的长度,不许蓄留长发,并必须以头巾包头;强行禁止一切非伊斯兰教的活动,否则将遭受最严厉惩罚。为实施这一苛令,塔利班专门设立“促进美德与镇压劣行部”并招募大量宗教警察。在许多城镇时常出现宗教警察围殴违规者的场面。(14)一份塔利班时期的违禁物品清单上包括:猪肉及猪油制品、头发制品、卫星天线、摄像机、录音机、台球、象棋、面具、酒类、磁带、计算机、录像机、电视、性宣传品、龙虾、指甲油、鞭炮、雕像、缝纫手册、图片、圣诞卡等。(15)塔利班对文化的破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家博物馆内的大量艺术品遭到毁坏。2001年3月,塔利班政权命令摧毁位于巴米扬的两座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佛像。巴米扬大佛是世界著名文化瑰宝和宗教宽容的象征,这一破坏行为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许多国家的谴责。
在被美国的“反恐战争”推翻之前,塔利班政权实际控制了阿国内约90%的领土。但塔利班从掌权开始便受到国际社会的抵制,在外交上极为孤立,一直未获联合国的承认,仅与沙特、巴基斯坦和阿联酋三国存在外交关系。安理会曾通过一系列决议敦促塔利班政权结束苛待妇女等原教旨主义政策,并因塔利班及“基地”组织支持恐怖主义而在1999年10月宣布对其实施制裁。国际制裁令后经多次更新,直到2011年6月安理会最后通过1988号和1989号决议。塔利班军事实力的基础建设则受益于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对阿境内“圣战”武装提供的大量武器援助(如前所述,多通过巴基斯坦渠道)。“9·11”事件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与塔利班打交道时多用外交手段,克林顿政府尽管不承认塔利班是阿合法政府,但双方曾进行直接对话。1997年8月,美国务院因塔利班支持和参与恐怖主义行为下令关闭美驻阿使馆。
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国内的主要对手是“北方联盟”。“北方联盟”的领导人为前阿富汗政府国防部长阿赫迈德·马苏德(Ahmad Shah Masood),其队伍包括由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哈拉扎人、普什图人组成的反塔利班各派武装。在美国反恐战争爆发前夕, “北方联盟”已控制阿境内约10%的地域和30%的人口,并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但马苏德在2001年9月遭到塔利班杀手的谋杀,他被害距“9·11”事件的发生仅有数天。美国在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后,“北方联盟”为推翻塔利班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塔利班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则较为复杂。在2001年底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之前,塔利班一直得到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如前所述,巴惯于将阿富汗视为自身抗衡印度的战略纵深,因此塔利班在阿取得政权能为巴带来可观的战略利益。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支持包括经费、后勤和军事装备。但就巴方武装人员是否直接参与塔利班作战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据持异议的巴基斯坦分析家拉希德(Ahmed Rashid)的说法,在1994-1999年间,约有8万-10万名巴基斯坦人在阿富汗境内接受军事训练并站在塔利班一边与“北方联盟”等反塔武装作战。(16)但这一数据似有夸大。美国务院1998年的一份文件却指称,阿富汗塔利班士兵中有20%-40%是巴基斯坦人。(17)此外,跨地区暴力武装活动催生并助长了巴阿边界地区的极端主义,致使巴基斯坦政府的制约能力进一步受限。例如在巴阿边境地区,巴籍武装分子与塔利班和“阿拉伯-阿富汗人”的活动相互混杂,相互间的联系日渐增多并难以辨别,并共同将袭击本土、本地区之外的目标纳入行动方案,由此该地区逐渐取代阿富汗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策源地。
“9·11”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穆沙拉夫政府改变了政策,决然断绝与塔利班的关系,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主要盟友,并集结10余万重兵布防巴阿边界承担反恐任务。但尽管如此,仍有不少美国人认为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活动符合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继续得到伊斯兰堡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其性质是一场代理战争。(18)但巴政府始终否认有关继续支持塔利班的任何指控。
(三)伊斯兰本土武装组织
上世纪80-90年代是南亚地区暴力武装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期。除“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之外,还有不少其他伊斯兰武装组织在印度、巴基斯坦及孟加拉国境内逐渐形成并开展活动。以针对印度的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为例,主要包括“虔诚军”、“真主军”、“圣战者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圣战者同盟”等极端主义武装组织。
“虔诚军”(LeT)成立于1993年,以巴基斯坦领土为基地,活动范围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尤其是印控克什米尔地区。2001年底印度议会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将其列入“外国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巴穆沙拉夫政府冻结了其财产。尽管遭到禁止,该组织仍改头换面在克什米尔及巴国内继续进行恐怖活动,被指控策划并参与了近年来某些针对印度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包括2006年7月的孟买火车站连环爆炸和2008年11月的孟买袭击。该组织与“基地”组织在理念上相互认同,但是否在具体活动上协调或联系尚无法肯定。(19)与之相近,“真主军”(JeM)也以巴领土为活动根基和以印控克什米尔为主要活动区域,矛头针对印度。该组织2000年成立,以将克什米尔从印度分离和并入巴基斯坦为主要政治目标,并且公开敌视美国,并向巴基斯坦政权及巴境内其他少数教派发动袭击。它策划并参与的重大恐怖活动包括2001年12月对印度议会大厦的袭击,并别指控实施对时任总统穆沙拉夫的两次未遂暗杀。此外,“圣战者组织”(HuM)、“伊斯兰圣战组织”(HuJI)和“圣战者同盟”(JuM)分别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皆以巴基斯坦领土为活动基地,起始宗旨是反抗苏联入侵阿富汗,但90年代将活动中心转移到印控克什米尔,并将恐怖袭击的矛头指向印度。(20)但除主要针对印度的暴力武装组织外,还有数量繁多的恐怖武装组织在巴基斯坦境内活动,要确定它们的数量和类别并不容易。
从美国“反恐战争”开始后的情况看,一些出现相对较晚、以恐怖主义为工具的暴力武装组织与“基地”、阿富汗塔利班及先前的伊斯兰“圣战”武装也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其中,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TP)的兴起是一重要发展。“巴塔”实际囊括了活动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现开伯尔-普什图省)和部落地区的各武装派别,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常规兵力总数约3.5万人。与阿富汗塔利班不同,统一旗号的“巴塔”兴起于2002年,与“阿塔”并无组织联系,是因反抗巴政府军开入部落地区清剿武装分子的产物。但“巴塔”在政治上认同并支持“阿塔”领袖奥马尔,并且巴部落地区成为“阿塔”武装分子躲避美国军事打击的庇护地。“巴塔”的代表性武装派别领导人包括南瓦济里斯坦的巴伊图拉·马哈苏德(Baitullah Mehsud,2008年8月被美国无人机击毙,后由其外甥哈基姆拉·马哈苏德接任)、巴焦尔的法齐尔·穆罕默德毛拉(Maulana Faqir Muhammad)和“法典运动”(TNSM)领袖卡兹·法兹努拉毛拉(Maulana Qazi Fazlullah)。“巴塔”为控制部落地区局势,曾杀害了200多名部落酋长,取而代之成为部落地区的实际控制者。
除“巴塔”外,与“基地”和塔利班关系复杂的武装组织还包括俾路支斯坦解放军(BLA,在俾路支省活动):巴政府在2006年将它定为恐怖组织;“旁遮普塔利班”:曾在2008-2009年间在巴基斯坦旁遮普境内发动多起恐怖袭击;“哈卡尼网络”:美国指控其以巴领土为根据地、在阿富汗境内对美国、北约和阿政府目标频繁实施袭击(现已被美政府正式列入“外国恐怖主义组织”(21))。此外,还有若干近年来声称对印度境内的部分恐怖袭击负责的印度本土伊斯兰激进武装团体。
四、克什米尔因素
探讨南亚恐怖主义的起源和动因,难以回避克什米尔因素。克什米尔内部的民族与宗教纷争也是导致该地区长期不稳的主要原因。在印控克什米尔(尤其是克什米尔河谷地区),穆斯林人口占据绝大多数,加之历史原因,一直存在严重的分离主义倾向,其中既有部分政治派别主张建立独立的克什米尔国家,也有一些政治势力赞同归属巴基斯坦。由于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一直存在对克什米尔的主权争议,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该地区内部的穆斯林反抗斗争和分离主义倾向,也使克什米尔问题成为印巴两国之间的争端和冲突焦点。
在克什米尔地区,当地穆斯林民众在政治和经济上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遭到驻防印度军人的压制、苛待和迫害,人权问题突出。尽管印度官方从未正式公布在查谟-克什米尔邦(即印控克什米尔)的驻军人数,但分析家认为接近60万人,这些军队被指控参与甚至制造了人道主义危机。(22)2010年10月,驻克什米尔印军最高长官V.K.辛格在一次采访中称,1994年以来共接到988次针对军人的指控,但在经过调查的965件案例中,有940件属不实之词,即超过95%的人权问题指控被证明是错误的,显然是“别有用心地诬蔑武装部队”。(23)
印度中央政府赋予驻防军队在紧急状态下采取武力行动的特殊权利,并允许军队有权压制民众的民权自由,从而致使许多民众同情甚至支持民间的武装叛乱活动。另一方面,武装叛乱分子有时也漠视基本人权,对对立教派民众肆意袭击甚至不惜大开杀戒,制造类似种族清洗的严重事端。由于地方政府无力有效保护普通民众免遭己方军队和反叛份子的双重伤害,极大地削弱了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并使克什米尔内部的安全局势趋于恶化。
当地穆斯林的政治权利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在1987年的地方选举中,受中央政府支持的候选人被发现通过舞弊行为当选,从而引发克什米尔民众的反政府情绪上升,进而导致在部分地区发生了反政府武装叛乱。尽管印度自诩为一个世俗化民主国家,但穆斯林群众与占主体的印度教徒相比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边缘化。此外,历年来的印度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也显示,印控克什米尔的大多数社会发展指标落后于印度其他邦,包括识字率和失业人口比例。这一因素也是导致当地人民不满和反对政府的重要原因。
在上述背景下,内部和外部矛盾的共同作用使克什米尔成为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和暴力武装活动的摇篮。在克什米尔活动的不少武装分子都曾在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境内“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赞助的宗教学校接受训练,其中一些人并在塔利班治下阿富汗的武装营地接受军事培训。其中某些组织的领导人也与“基地”组织保持联系。例如,巴基斯坦“伊斯兰圣战者组织”领导人哈利尔(Fazlur Rehman Khalil)曾在“基地”组织的圣战宣言上签字,号召穆斯林攻击一切美国人及其盟友。“真主军”的创建人马苏德·阿扎尔毛拉也曾多次前往阿富汗与拉登见面。“真主军”也涉嫌从“基地”组织接收经费。
结语
以上考察表明,南亚的恐怖主义问题由来已久,影响因素众多,涉及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其中既有国别背景和地区背景,也深受国际环境的影响,相互形成联动态势,并且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互为交织,盘根错节。产生一系列连带性社会政治效应,长期影响地区稳定和安全。“9·11”事件以来,美国在该地区主导的“反恐战争”迄今并未取得根本性胜利。显而易见,引发当代南亚恐怖主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清除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土壤是一项异常艰巨而复杂的社会工程,仅靠军事或强制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威胁,更重要的是实施积极的政治、经济、社会措施,消解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动因和铲除它们的滋生土壤,创造条件让其参与者和信奉者重新回归社会主流。因此,对地区国家而言,打击恐怖主义与发展落后地区经济、消除贫困和愚昧、加强良治和社会公正、消除腐败、实现民族平等、推动跨文明对话、倡导文化宽容等深层次改革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这也注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南亚的恐怖主义仍是国际社会必须关注的重大挑战,反恐斗争依然任重道远。
注释:
①总体上讲,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种类复杂,渊源复杂,既包括具有鲜明国际背景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巴基斯坦境内和印控克什米尔的暴力武装叛乱活动,也包括印度境内的纳萨尔武装活动、印度东北部武装分离主义以及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本文重点考察以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控克什米尔为活动范围的伊斯兰恐怖主义。
②Husain Haqqani,Paksitan between Mosque and Military,Lahore:Vanguard Books,2005,p.133.
③“Islamization Under General Zia-ul-Haq”,June 1,2003,http://storyofpakistan.com/islamization-under-general-zia-ul-haq/.
④Anita M.Weiss ed.,Islamic Reassertion in Pakistan,Lahore:Vanguard,1987,pp.13-14.
⑤Owen Bennett Jones,Pakistan:Eye of the Storm,Lahore:Vanguard,2002,pp.21-22.
⑥“Iranian Revolution”,http://en.wikipedia.org/wiki/Iranian_Revolution.
⑦Elie Rekhess,“The Terrorist Connection:Iran,the Islamic Jihad and Hamas”,Justice,Vol.5,May 1995.
⑧张玉兰:“伊斯兰极端势力:困扰巴基斯坦的梦魇”,http://iaps.cass.cn/news/112714.htm.
⑨Jim Kelly,“Osama bin Laden,America's bogyman,was recruited by the CIA in 1979”,May 5,2011,http://www.patriotfreedom.org/news_20110505_3836/osama-bin-laden-americas-bogyman-wasrecruited-by-the-cia-in-1979/.
⑩Michael Johns,“The Lessons of Afghanistan:Bipartisan Support for Freedom Fighters Pays off”,Policy Review,The Heritage Foundation,Spring 1987.
(11)John Moore,“The Evolution of Islamic Terrorism:An Overview”,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target/etc/modern.html.
(12)“Zardari says Pak created and nurtured militants”,CNN News; “Musharraf admits Kashmir militants trained in Pakistan”,BBC News,Oct.5,2010,http://www.bbc.co.uk/news/world-south-asia-11474618.
(13)“Al-Qaeda:General Overview”,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para/al-qaida.htm.
(14)Jayshree Bajoria,“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CFR Backgrounder,Oct.6,2011,http://www.cfr.org/afghanistan/taliban-afghanistan/p10551.
(15)Amy Waldman,“No TV,No Chess,No Kites:Taliban's Code,from A to Z”,The New York Times,Nov.22,2001.
(16)William Maley,The Afghanistan Wars,Palgrave Macmillan,2009,p.288.
(17)“Documents Detail Years of Pakistani Support for Taliban Extremists”,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2007,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227/index.htm#17.
(18)“Bhutto Conspiracy Theories Fill the Air”,Time,Dec.28,2007; Ahmed M.Quraishi,“Strategic Depth Reviewed”,Newsline,March 2002.
(19)Jayshree Bajoria,“Profile:Lashkar-e-Taiba”,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Dec.2,2008,http://www.cfr.org/publications/17882/.
(20)Carin Zissis,“Terror Groups in India”,Nov.27,2008,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2773/terror_groups_in_india.html.
(21)Robert Chesney,“The Haqqani Network to Be Designated,at Last,as an FTO”,Lawfare,Sep.7,2012,http://www.lawfareblog.com/2012/09/the-haqqani-network-to-be-designated-at-last-asan-fto/.
(22)“Talk:Insurgency in Jammu and Kashmir”,http://en.wikipedia.org/wiki/Talk%3ATerrorism _in _Kashmir.
(23)“104 Armymen punished for HR violations in JK:Gen Singh”,Deccan Herald,Oct.24,2010,http://www.deccanherald.com/content/107095/104-armymen-punished-hr-violations.html.
标签:塔利班论文; 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论文; 中国巴基斯坦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恐怖主义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南亚历史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穆斯林论文; 武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