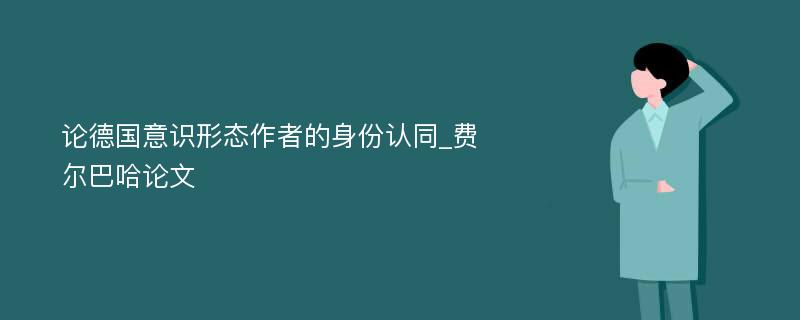
再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身份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意志论文,意识形态论文,身份论文,作者论文,再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08)05-0058-05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写作分担问题(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身份问题)是由日本学者广松涉挑起的。笔者在《国外学者论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学术关系》一文的“结论”部分已从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角度批驳了广松的“恩格斯主导说”,并许诺将以MEGA2发表的新材料为基础进一步论证“马克思主导说”。本文就是按此思路,以最新的国际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成果和MEGA2新发表的材料为基础,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做实证的分析和考察而得出的三点结论。
结论一:正像《神圣家族》那样,《费尔巴哈》章手稿正文的绝大部分内容是马克思写作的。
首先,“大束手稿”第二、三部分([30]-[72])可以肯定是马克思写作的。这是因为,“大束手稿”第二、三部分是从第三章的两处离题部分抽出来的,而第三章基本可以肯定是由马克思写作的。
理由1:由MEGA1/I/5第553-559页《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三章手稿编码表可知,有14张即56页手稿(具体来说是(1)、(2)、(3)、(4)、(20)、(21)、(22)、(23)、(27)、(28)、(43)、(44)、(45)、(75))是由马克思编码、魏德迈抄写的;由MEGA1/I/5第559-560页《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手稿编码表可知,署名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第四章《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施特版),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共14张)是由恩格斯抄写的,而现在已被判定是赫斯作品的第五章《“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共3张即12页)则是由魏德迈抄写的。由此可见,根本不能从笔迹来判断作者身份。
理由2:第三章多处提到“参看”某某作家的著作,这些作家的著作马克思之前都做过读书笔记或有该著作的藏书,而除个别例外(艾金和伊登),恩格斯并没有做这些著作的读书笔记,也没有证据表明恩格斯读过或藏有这些著作。
例1: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3卷第66页提到“参看艾金”,并引用了平托的两句话“贸易是本世纪的嗜好”,“从某个时期开始,人们就只谈论经商、航海和船队了”。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第5笔记本中简短地摘录了艾金《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记述》[1]323,而引用平托的两句话直接来自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第4笔记本的两处摘录[2]287-288。
例2:第74页(即“大束手稿”第三部分的[64])提到舍尔比里埃,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中登记了舍尔比里埃的名字。
例3:第193页提到“参看”勒瓦瑟尔的“回忆录”、巴莱尔的著作。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MH笔记本中对勒瓦瑟尔的“回忆录”有5页摘录,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登记的藏书中有巴莱尔的著作(第78)[2]6。
例4:第193页提到“自由的两个朋友”,这是克伟索和克拉夫廉的笔名,他们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用这个笔名在巴黎出版了多卷集的著作《1789年的革命史》。[3]75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登记的藏书中有该书。[2]5
例5:第193页提到博利约、贝尔蒂埃和雷尼埃。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登记的藏书中有博利约、贝尔蒂埃和雷尼埃的著作。[2]7
例6:第216页提到了配第、布阿吉尔贝尔、柴尔德。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B26笔记本对布阿吉尔贝尔的三部著作做了摘录,在《布鲁塞尔笔记》第4个笔记本中对柴尔德的著作做了摘录,[2]297-314在《曼彻斯特笔记》第1个笔记本中对配第的著作做了摘录。[1]8-22
例7:第217页提到迈尔西埃、马布利。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关于《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出版计划的草稿中列有马布利的名字,在《1844-1847年记事本》第69页记有迈尔西埃著作的书名(是带有布鲁塞尔图书馆书号的书名,也就是说不是马克思的藏书)。[2]24
例8:第217页提到了兰格、布里索。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第6个笔记本中做了兰格、布里索著作的摘录。[2]427-429
例9:第220页提到“参看:西斯蒙第、威德的著作等等”。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的第1和第2笔记本中摘录了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在《曼彻斯特笔记》的第5笔记本中摘录了威德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
例10:第225页提到《平等论者》杂志,第236页提到《博爱》月刊。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关于《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出版计划的草稿中列有这两家杂志。[2]14
例11:第231页提到了约翰·瓦茨。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第6个笔记本中对瓦茨的著作做了摘录。[2]430-433
例12:第241页提到伊登的《穷人的历史》第1卷和基佐的《法兰西文明史》。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的第5笔记本中摘录了伊登的《穷人的历史》第1卷,[1]302在《1844-1847年记事本》中登记的藏书中有基佐的《法兰西文明史》。
例13:第251页、第252页引用了特拉西《意识形态的要素》第4册和第5册《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16、17、18、19和22页的几句话。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B21笔记本做了《论意志及其作用》第16、18、24等页的摘录。虽然引文与摘录笔记并不吻合,但完全有理由相信,马克思正是因为做过特拉西著作的摘录笔记,因而对摘录笔记内容上下文的内容有较深印象,因而在写到这个地方时,马克思直接从特拉西著作中引用了相关内容。[2]5
例14:第344、452页提到米·舍伐利埃。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登记的藏书中有舍伐利埃的著作。[2]5
例15:第351提到“参看沙尔·孔德《论立法》”。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登记的藏书中有孔德的《论立法》。[2]9
例16:第416页提到了杜沙特尔。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登记的藏书中有杜沙特尔的著作。[2]9
例17:第417页提到西尼尔。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的第4笔记本中摘录了西尼尔的著作。
例18:第469页和第482页提到葛德文的《论政治正义》。马克思在《1844-1847年记事本》中登记的书目中有该书。[2]12
理由3: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11月决定针对《维干德季刊》第三卷发表的鲍威尔文章《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进行批判,并很快写出了一篇长文,准备交给正在创办中的《季刊》。在写完上述文章后,马克思决定继续对施蒂纳进行批判。马克思对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逐章进行批判,并且越写越长,甚至陷入细节而不能自拔。这种写作风格很像马克思写作《神圣家族》时的情形,而与恩格斯精练的写作习惯有很大差异。
理由4:正如聂锦芳指出的那样,施蒂纳的书出版前,恩格斯看了校样,写信给马克思,说书中有很多荒谬的东西,要对其进行批判。[4]马克思收信后的回信没有保留下来。但恩格斯又写信给马克思,说:“由于我和施蒂纳的私人关系,我低估了他的思想的影响,你的评论是对的。”而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1889年说过一段关于施蒂纳的话:“我和施蒂纳很熟,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远不像他在他的书里表现得那么坏,他只不过是稍稍带点学教气,这是他在教书的过程中养成的。”由此可以推断,恩格斯不大可能对施蒂纳写这种苛刻、充满讽刺和挖苦的论战性文字。
第二,“大束手稿”第一部分([1]-[29])也可以肯定是马克思写作的。
理由1:巴加图利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对比了《提纲》和《费尔巴哈》章的文本,发现了许多类似之处。
例1:《提纲》1,“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提纲》5,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对照《费尔巴哈》章“大束手稿”[10]的两段论述: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其中“全部活生生的”是马克思补写的;“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也是马克思补写的。
例2:《提纲》3,“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对照“大束手稿”[25]:“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再对照第三章:“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会不再是‘旧人’,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坚决地去改变这种环境。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3]234
例3:《提纲》6,“费尔巴哈……不得不……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对照“大束手稿”[10]:“他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
例4:《提纲》9和10把旧唯物主义即“直观的唯物主义”与市民社会相联系,把新唯物主义即“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相联系。对照“大束手稿”[8]“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以及[10]“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说法。
理由2:除巴加图利亚列举的上述文本外,笔者这里进一步提出一些文本对比的例证。
例1:对照《提纲》3:“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与“大束手稿”[20]:“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例2:“大束手稿”[20]有这样一段论述:“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对照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相关论述:“从前的目的论者认为,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动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同样,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即证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了思辨的高见: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5]100-101再对照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相关论述:“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大家知道,英国工业的发展使苏格兰地产获得了新的价值。而英国工业则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然把耕地变成牧场。要实行这种改变就必须集中地产。要集中地产就必须消灭世袭租佃者的小农庄,使成千上万的租佃者离开家园,让放牧几百万只羊的少数牧羊人来代替他们。这样,由于耕地接连不断地变成牧场,结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如果现在你们说,羊群赶走人就是苏格兰地产制度的天命目的,那么,你们就创造出了天命的历史……认为以往各世纪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产资料等等都是为实现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这首先就是用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来代替过去各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否认后一代人改变前一代人所获得的成果的历史运动。”[6]150-151
例3: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把自己的共产主义称为“现实的人道主义”[5]167-168,以有别于“抽象的人道主义”。对照“大束手稿”(10a)被删去的一段话:“至于谈到革命的这种必要性,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不论是法国的、英国的或德国的,早就一致同意了,而圣布鲁诺却继续心安理得地幻想,认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即共产主义所以取代‘唯灵论的地位’(唯灵论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只是为了赢得崇敬。”
例4:“大束手稿”[24]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市民社会理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对市民社会的重视是马克思特有的,是马克思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后就关注的话题。
例5:“大束手稿”[25]论述了实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因素”:“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对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说法:“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6]11区别只在于,“物质基础”还只是指“无产阶级”,而“物质因素”有了更全面的内容,除了“革命群众”即无产阶级外,还包括“一定的生产力”。
例6:“大束手稿”[26]谈到了德国历史编纂学,并有马克思的边注:“所谓客观的历史编纂学正是脱离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反动的性质。”这里马克思所批判的,正是著名的兰克“客观史学”。而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第4册笔记中对兰克的著作进行了摘录。
第三,“小束手稿”也可以肯定是马克思所写。
理由1:从“小束手稿”的形成过程来看。我们已经知道,“大束手稿”的三个部分是马克思分别从批判鲍威尔的文章(即为《季刊》准备的稿子)和批判施蒂纳的手稿中抽出来的,马克思在抽出三部分内容后,还给它们编了从1到72的页码。显然,把涉及“费尔巴哈”和“历史”(即唯物史观)的离题内容抽出来单独形成一章,必然存在上下文衔接以及内容重复等问题,因此在已有内容(即[1]-[72])基础上重写第一章,就是马克思必然的选择。既然我们已经证明“大束手稿”为马克思所写,重写第一章理所当然就是马克思份内的工作了。
理由2:从“小束手稿”的内容来看。
例1:“小束手稿”(3)论述了历史上的三种所有制(即财产)形式: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根据莱文的考证,马克思关于三种所有制形式的知识主要来自尼布尔和蒲菲斯特的历史著作。[7]部落所有制和古代所有制的说法来自尼布尔,而关于封建所有制的论述则来自蒲菲斯特的《德国史》和法的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胡果的说法。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第5册笔记中对蒲菲斯特的《德国史》做了摘录,而在《巴黎笔记》的B26笔记本有一个简短的古罗马编年史摘录,[2]69-83所依据的正是尼布尔的《罗马史》。恩格斯尽管也对历史学有浓厚的兴趣和精深的研究,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关于三种所有制形式的论述来自恩格斯的历史学学习和研究。
例2:“大束手稿”和“小束手稿”都强调研究要从“经验的事实”和“经验材料”出发,要运用“经验的方法”,但同时也特别强调“实证”方法:“德国人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他们的历史思辨所以特别热衷于这个‘史前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粗暴事实’的干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创立和推翻成千上万的假说。”[6]79-80“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6]73然后接着批判“抽象的经验论者”只做“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这里所谓的“抽象的经验论者”是指兰克的“客观史学”方法。既强调“经验”,又强调“实证”,并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批评“抽象的经验论者”只做“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这只可能是马克思而非恩格斯。我们知道,恩格斯长期在英国生活,深受英国经验论的影响,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运用经验论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产物。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强调“经验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到恩格斯成功运用经验论研究英国现实问题的影响。但马克思在接受经验论的同时,也对经验论的不足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受孔德实证哲学的影响,马克思对研究方法的强调逐渐转向“实证”。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登记的藏书中有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2]17,马克思1843年底至1845年初呆在巴黎期间,孔德的实证哲学刚刚开始流行,马克思购买并阅读《实证哲学教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恩格斯身在英国,法国此时流行的实证哲学大概不会很快感染到他。因此,从对“实证”方法的强调来看,“小束手稿”也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马克思所写。
结论二:虽然《费尔巴哈》章手稿正文的笔迹不能作为判定作者身份的依据,但后来插入、补充或修正的内容则可依据笔迹确定作者身份。
根据汉译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我们很容易确定哪些后来插入、补充或修正的内容是马克思写的,哪些是恩格斯写的。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做具体展示。
结论三:不论是“大束手稿”或是“小束手稿”,都是恩格斯在之前的草稿基础上抄录的。这里笔者提出一个大胆推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事先讲好了他们之间分工合作的方式,即先由马克思写第一稿,然后由恩格斯在誊写的同时进行补充和修改。
第一,根据陶伯特的说法,第二章即《圣布鲁诺》被删去的第5节“圣布鲁诺乘坐在自己的‘凯旋车’上”[3]115很可能是魏德迈的作品,但最后送出版社时被删去了。如此看来,最初批判鲍威尔的文章(即为《季刊》准备的稿子)也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工写成的,但马克思从中抽出的内容(即“大束手稿”第一部分)肯定是马克思所写。由于抽出的内容原位于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因此可以推测前3节是马克思所写,而第4节“与‘莫·赫斯’的诀别”很可能是恩格斯写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圣布鲁诺》章是“大束手稿”第一部分被抽出后恩格斯所做的最后誊清稿,也就是送到出版社去的付印稿。在此之前,恩格斯已经做了一次誊清,也就是说,马克思先写了前三节,然后由恩格斯在誊写的同时进行补充和修改,恩格斯接着写了第4节。
第二,批判施蒂纳的手稿完全是马克思一人所写。在两处离题内容(即“大束手稿”第二、三部分)被抽出后,恩格斯和魏德迈做了誊写,这就是送到出版社的付印稿,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内容(即《圣麦克斯》章)。与《圣布鲁诺》章的情况一样,“大束手稿”第二、三部分被马克思抽出前,恩格斯就对马克思的手稿做过一次誊写。恩格斯在誊写时做了相应的修改。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大束手稿”的(21d)(即后来马克思标的页码[35]),有一段不短的恩格斯栏外新稿。[8]可以想象,这是恩格斯在基于马克思的批判施蒂纳的手稿基础上誊写(21d)时随手做的补充。当(21)被马克思抽出来后,(21c)被全部删去,(21d)的绝大部分内容(包括恩格斯的栏外新稿)都被删去,但这些被删去的内容在恩格斯做最后誊清(即送到出版社的付印稿)时又被重新利用。
第三,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以及不久之后的《哲学的贫困》写作方式大都是按照论战对象的章节条目逐章逐条进行批判,因而篇幅很大而且冗长。马克思直接长篇地阐述自己的思想,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而到《资本论》第一卷则已经很娴熟。但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马克思还不习惯于直接长篇地阐述自己的思想。因此,在重写第一章时,马克思进行得并不顺利,曾经三次起草第一章的开头,恩格斯也相应地誊写了三次开头。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恩格斯先誊写了(1?),马克思又做了修改,如对第一句话“正如我们德意志意识形态家所断言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变革”,马克思删去了“我们”,又删去了“断言”而代之以“宣告”,在“变革”前面还加了“空前的”修饰语。马克思所做的这些修改都完整地再现于恩格斯所做的誊清稿(1)中。这再次印证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手稿进行了誊清,当然必要时也会做修改和补充,[28]和[29]恩格斯的长篇栏外补充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不论是第二章、第三章或第一章的“大束手稿”和“小束手稿”,虽然都主要是马克思写作的,但恩格斯在誊写过程中确实贡献了思想,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产物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当然恩格斯起的是“第二提琴手”的作用,绝非像广松所夸张的那样是“恩格斯引导了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