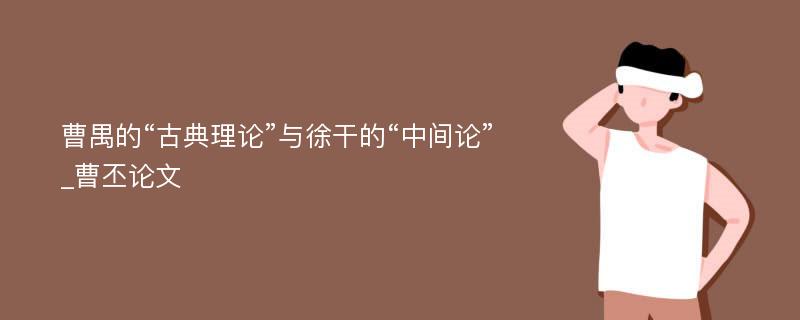
曹丕《典论#183;论文》与徐干《中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曹丕论文,论文论文,中论论文,典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曹丕《典论·论文》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徐干《中论》则为名理学的代表作,所属学科不同,二者有什么关系呢?笔者多年以前读《典论·论文》,即思考其结尾何以特书一笔:“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又读曹丕《与吴质书》,颇叹丕对徐干之评价独与应玚、陈琳、刘桢、王粲、阮瑀诸人不同。评价后述诸人,基本从文章风格角度略加评述,评价徐干则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典论·论文》与《与吴质书》何以都甚推重徐干《中论》,盛赞其“成一家之言”呢?曹丕在写作《典论·论文》时,似有徐干《中论》始终浮现于脑海,为什么会如此呢?
一
欲明《典论·论文》与徐干《中论》的关系,必须先明暸《中论》在建安时期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于建安时期政治思想的变化,学术界讨论者甚多,而以陈寅恪先生数十年前的见解最具史识。寅恪先生迻录曹操求才三令,指出东汉外廷之主要士大夫,多出身于儒家大族,欲以其修身治家之道德方法推及于治国平天下。曹操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寅恪先生进一步指出:“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44-45页。)东汉后期,清议流弊泛滥,人物品评中名实不符的现象相当严重,王符起而强调“苟得其材,不嫌名迹”(注:《潜夫论·本政》。)。王符的呼声虽然微弱,却成为建安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强调名从于实的先声;曹操三令则如石破天惊,成为讲求实效、力斥虚名的政治宣言。
就在曹操发布求才令的时期,徐干正好先后充任曹操的幕僚和曹丕的文学侍从,即任司空军谋祭酒掾属和五官将文学。这位于学无所遗的知识分子,马上成为曹操政策的理论宣传者。建安七子中,王粲、应玚、刘桢、陈琳、阮瑀和徐干,都是曹氏父子的幕僚和文学侍从。从《典论·论文》可以看到,此六子中,唯徐干长于宜理的论,虽然徐干的辞赋“时有齐气”,虽然这种舒缓的风格有时可能成为诗赋之累,但形之于宜理的论,却有助于说理的有条不紊。此六子中,徐干是起而宣传名从于实的理论的最佳人选。庞朴先生曾指出,徐干《中论》所表现的精神态度,“无不钤印着曹操政策的痕迹”(注:《名理学概述》,载《历史论丛》第一辑,齐鲁书社1980年版,141页。),诚哉斯言。不过,我们还应进一步看到,徐干《中论》是一部系统讨论名实关系、强调名从于实的理论著作,它不仅要宣传曹操的政策,还要凭着它的系统性去影响曹氏父子,尤其是影响五官中郎将曹丕。
也许有人要问,徐干《中论》动辄援引儒家经典之言及先王周孔之事,俨然醇醇儒者,怎么可能与使奸弄诈的曹阿瞒站在同一战线?是的,徐干于《五经》可悉载于口,但却不是抱残守缺的腐儒。他在《中论》第一篇《治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其思想与东汉经学思想,已判然画界。一部《中论》,凡提出一种观点,往往引儒典圣迹为证,似皆从儒家道德立场出发,其实处处取古为今用的原则,利用儒典圣迹,以说明名从于实这“大义之所极”。《中论·智行》:“曾参之孝,有虞不能易;原宪之清,伯夷不能间。然不得与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其用意明显在强调才而忽诸孝与清。又:“子贡之行,不若颜渊远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闻一知十。由此观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颜渊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悦)。”直谓德行未必服人,盛才最能服人,其与曹操三令如出一辙,而理论性更强。
明白徐干完全可以和曹操站在同一思想战线,再来看徐干《中论》名实论的系统和针对性,我们行文时,便有了些“论其世”、“知其人”,“以意逆志”的自信心。
徐干的名实论有鲜明的针对性,批判的锋芒直指东汉后期以来流俗所为:“苟可以收名而不必获实,则不去也;可以获实而不必收名,则不居也。”(注:《中论·考伪》。双鉴楼藏明刊本。)这种风气混淆视听,成为培育欺世盗名者的土壤。“非辩而谓之辩者,盖闻辩之名而不知辩之实。”(注:《中论·核辩》。)由此可见:“则时俗之所不誉者,未必为非也;其所誉者,未必为是也。”(注:《中论·审大臣》。)这种是非混淆的局面,在历史上具有普遍性:“故名实不相当也,其所从来尚矣!何世无之。”(注:《中论·审大臣》。)
有鉴于此,徐干高扬起名从于实的理论大旗:“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注:《中论·考伪》。双鉴楼藏明刊本。)徐干《中论》处处利用儒典圣迹宣传其主张,而孔子强调名分,徐干加以调和说:“仲尼之所贵者,名实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夫名之系于实际也,犹物之系于时也。”(注:《中论·考伪》。双鉴楼藏明刊本。)围绕名实问题的讨论,归根到底是为曹操的用人措施张本,所以徐干《中论》常把哲学的命题转变为政治的话题,其中《爵禄》、《考伪》、《谴交》、《审大臣》等许多篇,都围绕或涉及这一政治话题。徐干认为:“凡明君直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已心,而徒因众誉也。用人而因众誉焉,斯不欲而治也,将以为名也。”(注:《中论·审大臣》。)以“徒因众誉”为为名,主张明君“悟乎己心”以用人,使曹操的用人措施有了有力的理论根据。曹丕称美徐干《中论》,根本的原因似在于此。
二
曹丕是一位深爱文学的政治家,他称美徐干《中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关于名实问题的讨论,起于对东汉后期清议活动名实不符风气的批判,清议活动的重点是品评人物,而徐干《中论》的系统性远胜于王符《潜天论》关于名实问题的主张,亦优于同时的刘廙的政论,无疑能给当时的人物“月旦”,提供新的思维方法。凭着其学术素养和睿达之资,曹丕把徐干的名实观,运用到了对文学和文学家的批评态度上,实现了由运用名实观批评政治到运用名实观批评文学的过渡。
曹丕《典论·论文》开宗明义,对文人相轻的陋习提出批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又:“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是站在批判的立场发言,徐干《中论》则常站在省身的立场立论。《中论·虚道》:“故君子常虚其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视彼犹贤,自视犹不足也。”这一番话,正可用曹丕《典论·论文》“盖君子审己以度人”一句来概括。传本《中论》古序称美徐干说:“君之交也,则不以其短,各取所长。”古序作者,曾侍坐于徐干,故其论徐干的交友,语意心迹全同于曹丕之志,的为深知徐干与曹丕关系者。
曹丕《典论·论文》在批评建安七子之后,提出文体论和文气说之前,插入一段议论:“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这段议论与上引开篇议论遥相呼应,仍紧扣在名实问题上,实乃告诉读者:名从于实的思想,是贯穿《典论·论文》全篇的沛然之气。前面分述建安七子之长短,是秉持着审己以度人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后面提出“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等崭新的文学主张,也是尊重文学创作的自身规律这个“实”,丢开传统的诗教说那个“名”。而曹丕的这段议论,显然也与《中论·谴交》:“名有同而实异者矣,名有异而实同者矣。故君子于是伦也,务于其实而无讥其名。”君子的“务于其实而无讥其名”,与常人的“向声背实”态度正相反,不正说明曹丕与徐干思想的默契吗?《中论·修本》:“明莫大乎自见,聪莫大乎自闻,睿莫大乎自虑。”与曹丕批评常人“暗于自见”相对照,不正可想见曹、徐二人的灵犀相通吗?或许有人会对此问题提出质疑:汉代桓谭、王充都曾对贵远贱近,尊古卑今的陋俗提出过批评(注: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典论·论文》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164页。),曹丕的议论只是由桓、王的议论所触发。 然而,我们结合《典论·论文》全篇语意来细加考察,尤其是想想曹丕为何特地在文末写上“唯干著论,成一家言”这一笔,便不难明暸:曹丕至少是由徐干的名实观联想到了汉人桓谭、王充的议论,桓、王之说是曹丕思想的远源,徐干的名实观是曹丕思想的当世之缘。
曹丕在讨论了文气问题后,用较长篇幅讨论了文学的价值和作家的创作品格问题,这与名实观有无关系呢?窃以为曹丕提出文章不朽说,看似重名,其实其意在于:文章之名能立,在于作家之实能立。何谓作家之实?“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此其一。“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此其二。罗根泽先生认为:“作者的寄身翰墨,见意篇籍,是为的‘声名自传于后’,则其重文缘于‘名’而非缘于‘实’。”(注:《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版,125页。)似未达于作者之旨。 结合前后文可以明晓,曹丕要说明的是:“声名”是后世之人通过作家的篇籍之“实”而自得之,不是从“良史之辞”得之,也不是从“飞驰之势”得之,其意正欲去不实之“声名”,崇系之实的“声名”。由此可见,此段“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两句颇堪注意,正陆机《文赋》所谓“警策”是也。《中论·谴交》:“故无交游之事,无请托之端。”徐干讲的是政治品格,曹丕讲的是创作品格,但言异而心同,其间关系,讵难见乎?曹丕与徐干的这种心灵相应,不独见诸《典论·论文》。《中论·谴交》认为君子的基本品格应是:“心澄体静,恬然自得。”而曹丕在《与吴质书》中称赞徐干“怀文抱质”,“恬淡寡欲”,“可谓君子矣”。曹丕之于徐干,可谓知己。
综上所述,可以想见:徐干逝去,曹丕怀其人而读其书,《中论》的系统性极强的名实观,深惬丕心,遂成为贯穿《典论·论文》全篇之思想脉络,故曹丕于一篇之中,屡致意焉,深怜徐干之情,溢于言表。
三
曹丕《典论·论文》虽深受徐干《中论》影响,但亦非对《中论》亦步亦趋。一方面,徐干先后为曹操的幕僚和曹丕的文学侍从,其在《中论》中阐述的主张,或有秉意于曹氏父子者,或有曾与曹氏父子谈论者;另一方面,徐干年十四始读五经,“发愤忘食,下帷专思,以夜继日”(注:《中论》传本古序。),学术途径和素养毕竟与曹氏父子有所不同,所以《中论》中表露的思想也会有与曹丕思路不同者。更重要的是,《中论》是谈政治思想的,而曹丕是通过《典论·论文》来张扬其文学主张,自然在如何看待文学这一基本问题上,与徐干确然画界。
徐干《中论》二十篇没有专门讨论文学的,这固然决定于其书性质,但他对文学价值看得不高,仍可从《中论》中依稀见到。《务本》一篇,强调人君当务大事而不可崇尚技艺,他所说的大事,都是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没有提到文化,更没有文学的影子,盖文学在他说的技艺之列。这种观念,与曹植“辞赋小道”,“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注:《文选》卷四十二《与杨德祖》。)之说相若。曹植说的可能是希图建立奇功而不能的愤激之言,徐干则是在向曹氏父子进忠言,则其文学观念尚不如其政治思想进步可知。
汉末建安时期,关于夭寿问题的讨论较为热烈。据《中论·夭寿》,荀爽认为所谓夭寿,是形体夭而德义寿,即强调立德。孙翱则认为,仁者寿之说,不过是“诱人而纳于善之理”,乃教化的手段。徐干则主张:“以仁者寿利养万物,万物亦受利矣,故必受也。”是徐干重在万物之受利,实偏向立功之论,这与曹操的思想比较接近。夭寿问题在他们那儿,都没有与文学发生关涉。
作为魏王世子的曹丕显然有意要提高文学的地位。他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提升为人君当务的大事,而不是视之为小小技艺而已。称文学为“不朽之盛事”,似乎直接针对徐干的《夭寿》篇,所以曹丕更明确地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以形体和荣乐为夭,以文章为寿,是以立言为上。曹丕作为提出文学真正价值的第一人,没有忘记自己的创获与徐干的关系,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他与徐干看法大不相同,他特地在《典论·论文》之末称徐干《中论》“成一家言”,是亦以其为不朽。这正是“审己以度人”的态度。
正由于曹丕能在徐干《中论》的启发下,变政治的思路为文学的思路,所以其能出于《中论》而又超越《中论》,持审己度人之心,求文学创作之实,旗帜鲜明地提出“文本同而末异”、“文以气为主”等前无古人的文学主张,为汉魏之际的文学批评开一新生面。
从曹丕《典论·论文》与徐干《中论》的关系,我们看到:文学批评思想,实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思潮密切相关。文学批评思想兴废渐变之迹,似不应孤立地就文学批评史本身作考察,而应结合历史、思想史作综合的研究,唯如此,庶几能免于皮相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