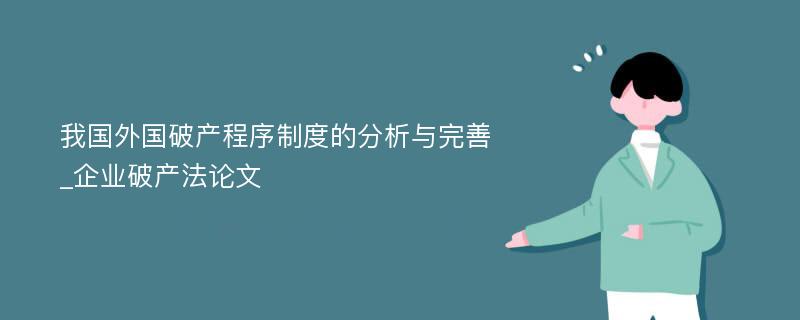
我国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制度的解析及完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域外论文,效力论文,外国论文,制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企业破产法》有关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规定的解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5条第2款规定:“对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破产案件的判决、裁定,涉及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财产,申请或者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裁定承认和执行。”
上述规定在我国的立法中首次确定了承认外国破产判决、裁定的主要原则。同时,《企业破产法》第4条规定:“破产案件审理程序,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所以,对外国法院的破产判决、裁定的承认,在考量《企业破产法》本条规定特殊适用条件的同时,还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对外国法院的判决、裁定承认的一般性条件与程序。
目前我国破产法这一规定的内容显然还不够具体,未能提供足以指导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规则。因此,需要对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破产判决、裁定的特殊条件进行适合国情与国际惯例的研究解析,并且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企业破产法》的司法解释中加以具体规定,笔者建议其主要内容可以包括:
(一)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优先顺序与审查标准
在实践中,有时会遇到不同国家对债务人同时或先后启动多个破产程序,并且均向我国提出承认其破产程序效力申请的情况,这时就需要确认承认不同外国破产程序的优先顺序与审查标准。笔者认为,鉴于我国《企业破产法》第3条在确定债务人破产案件管辖权时采用了住所地标准,为了与其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我国法院在原则上应优先承认债务人住所地所在国开始的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此后,如果非债务人住所地所在国的破产代表申请我国法院承认该国的破产裁决,在依法应予承认的前提下,原则上不得给予其多于债务人住所地所在国之破产代表所得到的救济权利,除非其能证明这种限制是不公平的。
在债务人住所地所在国的破产法不主张该国的破产程序具有域外效力,或债务人住所地所在国尚未开始针对债务人的破产程序时,我国法院可以承认非债务人住所地所在国开始的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而在债务人住所地所在国的破产代表申请承认该国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并获得我国法院承认后,应修改已经给予非债务人住所地所在国的破产代表的各项救济权利,使其原则上不得多于债务人住所地所在国破产代表获得的救济权利,除非其能证明这种限制有不公平之处。
(二)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承认方式与溯及力
在对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承认方式上,有的国家规定无需启动本国法院程序,在立法或司法实践中直接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在本国的效力即可。但我国的立法与此不同。依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我国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需要启动本国的法院承认程序。而对这种承认裁定是否具有溯及力,即能否约束在外国破产程序开始后、得到我国法院承认前,在我国境内发生的债务人对财产的处分行为与债权人的个别受偿行为,立法没有提及。
依据一般之法理,承认外国法院的裁决就是承认其所确定的法律关系。既然这种法律关系是依据外国破产裁决产生的,对其承认的效力自然应当溯及至裁决生效之日,即法律关系产生之日。
但如确认对外国破产裁决的承认具有溯及力,则债务人在外国破产程序开始后仍对我国境内债权人清偿债务的,那些善意债权人的受偿利益就可能由于清偿无效或可以被撤销而受到损害,这是有失公平的。不过另一方面,从债务人外国破产程序开始,到外国破产代表使该破产程序开始的裁决在我国法院得到承认,必然有一定的时间差。如果对此时间差中债务人的个别清偿行为或财产处分行为等完全不加干涉,又难免会出现破产欺诈行为或偏袒性清偿行为。由此出现保护本国债权人正当权益与强化跨境破产合作、避免债务人等的欺诈行为之间的冲突。这一矛盾即使是在跨境破产问题上合作水平较高的各国也同样存在。
综上,笔者认为,在跨境破产的国际合作没有对此冲突形成一致的解决办法或国际惯例时,我国可以考虑从以下两种方案中择一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种方案是否认对外国破产程序开始之裁决的承认有溯及力。同时,在我国没有建立授权法院给予外国代表临时救济权力的制度前,为了保障公平,可以采取对外国破产程序裁决从速承认的原则。本方案可以优先保护我国债权人的利益,并且与《跨境破产示范法》的默示规则保持一致。
第二种方案是,确认对外国破产程序开始裁决的承认有溯及力,但善意①债权人的受偿可以豁免于此溯及力之外。对债权人是否为善意的举证责任,由外国破产代表承担。本方案虽然有些“超前”于跨境破产国际合作的目前阶段,但更为公平,也更有助于破产法公平清偿之核心价值的实现。
(三)依据国际条约或互惠原则的审查
1.依据国际条约进行的审查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审查外国破产裁决的依据是国际条约或互惠原则。由于我国尚未缔结或参加任何承认外国法院破产裁决的国际公约,所以此处的国际条约主要指我国缔结的民商事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截至2006年8月14日,我国已与法国、波兰等30多个国家②签订有已生效的民商事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其中与新加坡的司法协助条约不包括互相承认法院裁决。对于上述国家法院的破产裁判,我国法院应按照条约中规定的条件审查是否承认外国破产代表提出的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申请。审查条件一般包括:第一,合适的管辖权;第二,裁决的终结性与执行力;第三,审判程序具备最基本的公正性;第四,在我国无冲突裁决或诉讼;第五,公共秩序保留。对上述五个条件,笔者在本部分只分析前两个条件的解释问题。第三个审查条件在承认外国破产裁决时没有特殊意义,因为破产程序本身不是一个审判程序,而对破产程序本身的公正性要求可以列入公共秩序保留的范围。第四个条件依据破产程序优先适用的原则就可以解决。第五个条件将在后文中另行论述。
第一项审查条件是“合适的管辖权”。《企业破产法》没有具体规定承认外国破产案件裁决时的管辖权条件。目前,各国普遍承认的具有完整域外效力的破产程序,仅限于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法院或其住所地所在国所启动的破产程序。据此,一般情况下,我国可以只承认债务人住所地所在国开始的破产程序具有域外效力,这既符合国际破产合作的精神,也符合《企业破产法》中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法院专属管辖的规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债务人住所地所在国的破产法不对外主张其域外效力,即主要破产程序不具有域外效力时,也应当考虑承认债务人营业场所或财产所在国开始的辅助程序的域外效力。
第二项审查条件是“裁决的终结性与执行力”或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如前所述,考虑到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特殊目的和要求,所谓裁决具有终结性与执行力或曰“发生法律效力”,应解释为发生破产程序开始的效力,并不限于已经作出破产宣告。因为在破产程序的启动上,案件受理裁定的法律效力与破产宣告的裁定完全相同,都会产生剥夺债务人对财产的管理与处分权,转由管理人控制债务人的事务及财产,禁止债权人、债务人的个别清偿行为,中止针对债务人的诉讼等效力。如果狭隘地将破产案件受理裁定排除在具有终结性或执行力的裁决之外,不承认其域外效力,将无法防止在案件受理至破产宣告期间内债务人的欺诈逃债和债权人的个别受偿行为,使得跨境破产案件的国际合作在最关键的方面失去效用。
2.依据互惠原则的审查
对于没有与我国签订生效的民商事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的国家,《企业破产法》规定人民法院应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是否存在“互惠”一般是依据先例认定的,而在没有先例时如何认定就需要研究了。我国的立法与司法解释从未对“互惠原则”作出过明确定义,或指明其评判适用方式。国际私法学者根据对最高人民法院一个批复的研究,认为我国采取的是在没有相反证据时推定不存在互惠的态度。③如果上述推断成立,在承认外国破产裁决时,何种事实可以构成“相反证据”就显得非常重要。
从各国的司法实践看,在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上的“互惠”,一般是指本国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在相同情况下也会得到该外国的承认。因此,如果一国在立法中确立了与我国相近似的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规则,或规定了更为宽松的条件,就可以视为在此问题上实行了对我国的法律互惠④,构成“相反证据”。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在承认外国破产裁决上设置了比较严格的审查条件,因此所有基本上采纳了《跨境破产示范法》的国家以及在本国破产法中规定了与我国承认外国破产裁决相似条件的国家,都应当可以通过法律互惠的审查。
(四)公共秩序保留的解释与适用
《企业破产法》中还规定,申请或者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外国破产裁决,必须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际间设定的此项法律规则,在我国国际私法学界一般称为“公共秩序保留”,也有的国家称为“公共政策”保留。目前我国对“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应当如何理解与执行研究得较少,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也比较混乱,因此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制度与成熟经验。
需要指出的是,承认外国破产裁决较之承认外国普通民商事裁决,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于普通的外国民商事裁决,我国法院如果不予承认,并不会断绝申请人在我国寻求司法救济的全部途径——申请人可以在我国有管辖权的法院就同一事项另行起诉,寻求司法救济。但如果外国开始破产程序的裁决被我国法院以公共秩序保留为由而拒绝承认,那么外国破产代表往往难以在我国申请其他可以达到其目的的司法救济。因为《企业破产法》第3条规定,对债务人的破产案件管辖权属于专属管辖,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若据此立法文义分析,将排除我国法院依《民事诉讼法》第4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第24章“管辖”所规定的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适用。所以理论上讲,只要债务人在我国境内没有住所,我国法院就不能对其破产案件行使管辖权,外国破产代表也就无法在我国开始破产程序,以阻止债权人的个别受偿或债务人对其在我国境内的财产行使管理处分权。
综上,笔者认为,虽然适用公共秩序保留的具体情形要由法院在实践中掌握,但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标准应当从承认外国破产裁决的结果考虑,只有在承认的结果直接有悖于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时,才能以公共秩序保留为由拒绝承认。法院不能仅仅因外国破产法或相关法律与我国立法存在不同,就借公共政策排除其适用,而要从“法律的基本原则”的高度来审视这种不同是否存在适用公共秩序保留的必要性。为了防止外国破产代表丧失在我国《企业破产法》下取得救济的机会,必须防止滥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外国破产开始程序对债务人在我国境内财产效力的现象。
(五)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理解
最后,《企业破产法》还要求被承认的外国破产裁决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对此要作出正确判断,首先就需要界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是什么,需要明确其产生的法律依据。
如果可以依法将债务人的住所地确认在我国境内,则我国法院对债务人的破产案件就有管辖权。此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是指其根据我国各项法律包括《企业破产法》产生的所有权益。外国破产裁决中凡是与我国《企业破产法》等立法规定不符的内容,都可能损害我国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如果确定债务人的住所地不在我国,则我国法院对其破产案件是没有管辖权的,我国破产法是不适用的。此时,我国债权人针对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只能是根据《企业破产法》以外的其他民事法律以及依据作出破产裁定的该外国的破产法所产生的相关权利。所谓外国破产程序损害我国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主要便是不能在该国破产程序中公平对待我国债权人,即我国债权人没有享受到该外国破产法所规定的权益。需特别强调的是,外国破产法规定的债权清偿顺序与我国《企业破产法》不同,不能视为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为我国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我国债权人本来就不享有我国立法所规定的各项权益,包括清偿顺序利益。而其例外是,如果我国债权人对债务人在我国的财产享有物权,如别除权、取回权等,则可以主张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即我国立法以维护其权益。
二、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制度的完善
与在跨境破产问题上国际合作水平更高的各国相比,我国《企业破产法》目前在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制度方面,主要是欠缺主要破产程序与非主要破产程序的区分及配套制度。
如前所述,主要破产程序是在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国开始的破产程序,只要该国破产法主张其域外效力,该程序的域外效力就得到在跨境破产问题上持国际合作态度国家的普遍认可。而非主要破产程序是在债务人营业所或财产所在国开始的破产程序,其效力是地域性的,仅及于债务人位于该国境内的财产。这两种破产程序的区分起源于1995年的欧盟《破产程序公约》。虽然该公约未能生效,但该区分制度被1997年的《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跨国境破产示范法》及2001年的欧盟《破产程序条例》所继承。欧盟《破产程序条例》第3条第1款规定,“对于公司或法人而言,如无相反证明,注册办事机构得被推定为其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跨境破产示范法》在其《立法指南》第72段中采纳的是与此相同的定义。
设置非主要破产程序的目的,主要是考虑承认外国破产裁决将使本国债权人必须参加外国破产程序才能获得受偿,不仅对当事人不方便,而且由于外国破产程序规定的清偿顺序可能与本国不同,也不利于保护本国债权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后,外国破产代表可能也需要本国法院来协助执行外国的破产程序,清算债务人在本国的财产,实际上也有启动本国破产程序的必要。因此,采用主要破产程序和非主要破产程序配合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协调并维护各方当事人之利益。
如果在跨境破产的国际合作中,我国可以启动非主要破产程序,就可以解决因与其他国家破产法在债权清偿顺序等问题上规定不同(如《企业破产法》第132条规定的职工债权的特殊清偿顺序)而产生的法律冲突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但在我国建立非主要程序制度还存在两个问题需要在司法解释中加以解决。第一,《企业破产法》规定破产案件属于专属管辖。若从立法文义上分析,只要债务人在我国没有住所,我国法院就不能对其破产案件行使管辖权,无权启动非主要破产程序。所以需要对管辖规定作一定的扩大解释。第二,《企业破产法》第5条第1款规定,“依照本法开始的破产程序,对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财产发生效力”,这与启动非主要破产程序仅具备地域性效力的要求不相符合,需要例外性地规定非主要破产程序的效力不及于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财产。
笔者认为,建立非主要破产程序是完善我国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立法的关键,一方面有利于更好地执行外国破产裁决,协助实现外国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维护我国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跨境破产示范法》提供了比较合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规则,可以弥补我国《企业破产法》这方面的立法空白。因此,可以根据国情采纳《跨境破产示范法》规定的一些基本内容,建立我国的非主要破产程序制度。采纳《跨境破产示范法》还可以表现出我国更为开放的国际破产合作意愿,树立国际破产合作积极参与者的形象,并确立我国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互惠原则,为我国管理人在境外主张我国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注释:
①即对债务人在外国被开始破产程序不知情。
②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tyfls/wjzdtyflgz/zgywgdsfxzyflhz/t267989.htm,访问日期2008年1月12日。
③徐宏:《国际民事司法协助》(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290页。
④王慧:《论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载《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第4卷第1辑(总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