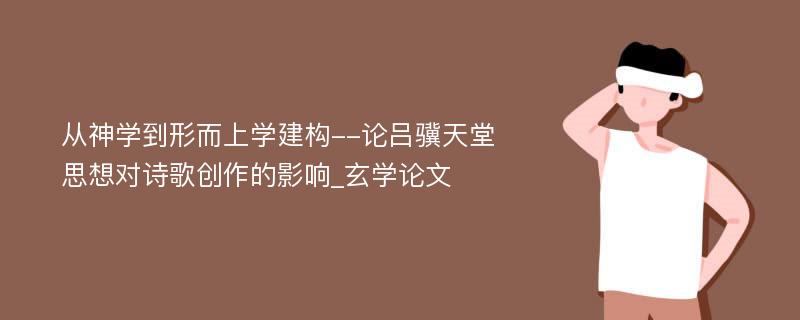
从神学到玄学的建构——试论陆机天道思想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玄学论文,神学论文,天道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陆机《文赋》主张的“诗缘情而绮靡”,历来被认为是中国诗歌理论对“诗言志”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然而陆机的诗歌却受到情感淡薄的批评①,与汉末建安诗歌悲凉慷慨的饱满的抒情性相比,陆诗的确更注重辞藻、对偶、用典等艺术技巧,而诗歌的抒情性则有所欠缺,这也说明了陆机诗歌创作,并没有完全实现其“缘情”理论,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点与陆机的天道思想有很密切的关系。与陆机前后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相应,陆机的天道思想也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吴国时期,其天道思想受吴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具有神学的性质;第二阶段为太康十年陆机入洛之后,在玄学思潮影响下天道思想的玄学化发展。陆机天道思想的发展历程,本质上可以说是从神学到玄学的建构的转变,这种转变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吴国时期:神学化的天道思想
陆机天道思想的神学性质,是在吴国特殊思想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正始期间何晏、王弼代表的北方玄学兴起之时,三国对峙的南北隔绝使吴国的思想保持了汉代以来原有惯性发展,故其思想以汉儒思想为主。汉儒天道观主要体现在《易》学上,《晋书·纪赡传》载纪赡与顾荣共赴洛阳,途中论《易》太极,顾荣批驳王氏“太极天地”之说,认为“太极者,盖谓混沌之时,蒙昧未分”②的一个宇宙构成阶段,顾荣的“太极”论其实是宇宙生成论,而王弼所讲的“太极”则与玄学中的“无”一样是形而上的本体,这是汉儒与魏晋玄学的本质区别。汤用彤《王弼大衍义略释》云:“王弼太极新解为汉魏间思想革命之中心观念,顾氏依旧说评判,宜其不为他所了悟。”这种“旧说”就是汉儒思想。纪瞻虽然支持王弼说,认为“王氏指向,可谓近之”,但他认为“太极极尽之称,言其理极,无复外形,外形极,而生两仪。”③可见纪瞻也仍然没有准确理解王弼的思想,他的太极论与顾荣所说的本质上一样,都是宇宙的构成论。顾荣、纪瞻的宇宙论其实是吴国盛行的“天体论”的反映。天体讨论从汉代开始兴起,三国时期这一思想只在吴国广泛流行,可见吴国对汉代思想学术的继承。④
另一点,在何晏、王弼将《易》与《老》、《庄》共同作为三玄之一时,吴国的《易》学却仍是象数之学。陆机的从曾祖陆绩即是《易》学大家,颜延之《庭诰》称其学术特点是“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⑤《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引别传载虞翻上《易注》,奏云:“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臣)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⑥虞翻易学出于家传,也就是传孟氏易,清皮锡瑞《经学通论》说孟氏、京氏“其言易亦主阴阳变异”⑦,这正是汉儒《易》学的路数,象数、阴阳变异之学与汉儒天人感应、谶纬思想关系极为密切。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陆机,其思想自不能不受到影响,《与清河云诗》⑧说“有命白天,崇替靡常”、“天步多艰,性命难誓”,即表现出对于个人之上的神秘的“天命”的恐惧。又如《豪士赋序》说:“借使伊人颇览天道,知尽不可益,赢难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则巍巍之盛仰邈前贤,洋洋之风俯冠来籍。”就是批评齐王同不懂天道的警示才会轻举妄动自取覆亡。这种神学性质是陆机天道思想的第一阶段。
从根本上说,阴阳变异与谶纬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迷信思想,神学意志对思想的控制往往就造成了诗性精神的缺位,对诗歌创作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所以吴国的文学状况也与东汉颇为相似,诗歌的创作是比较沉寂的。陆机现存的诗歌几全为进入北方后所作,入洛前的诗歌极少,可以说在吴国时期陆机的诗歌创作是不活跃的,这与吴国落后的文学状况相应,根本上说与吴国的思想环境乃有极大关系。吴国时期神学性质的天道思想对陆机诗歌写作的影响,是一种消极的、非自觉的关系。天道思想与陆机诗歌具有积极意义上的关系,是在入洛之后,陆机在玄学浸润下,其天道思想由迷信向理性自觉发展,从而对其思辨能力、思维方式以及诗歌题材的选择、诗风的形成产生主动性的影响时,才真正地确立起来。
二、入仕西晋时期:天道思想的玄学化
太康十年,陆机兄弟相携入仕西晋,在北方玄学思潮的影响下,其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晋书·陆云传》载陆云本无玄学,但夜遇王弼的鬼魂后“谈老殊进”⑨,这个故事又见于刘敬叔《异苑》,主角变成了陆机:
陆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师。时久结阴,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见一少年,神姿端远,置《易》投壶,与机言论,妙得玄微。机心服其能,无以酬抗,乃提纬古今,总验名实,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晓便去,税骖逆旅,问逆旅妪,妪曰:“此东数十里无村落,止有山阳王家冢尔。”机乃怅怪,还睇昨路,空野霾云,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⑩
这个故事包含了两层重要的含义:一、“妙得玄微”与“总验名实”,体现了玄学与汉学思维方式的歧异;二、“心服其能,无以酬抗”,表明初入洛时陆机与玄学家在思辨能力上的差距。这个故事本身虽不足信,但结合《陆云传》所说的“谈老殊进”,却很明确地表明了陆氏兄弟思想上的转变和进步,包括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和思辨能力的提高。(11)西晋玄学大盛,即使像张华这样的北方士人亦不能不时常表明自己“恬淡养玄虚”、“好师老彭”,以迎合时代的要求,陆机虽“服膺儒术”(12),但在玄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背景下,为争得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更不能不对自己的思想有所改造,改造的方向即玄学化,这亦是彼时思想之大势。对陆氏兄弟来说,道家、玄学思想的引入,实有一种思想解放的功效,这种思想之解放,首先冲击的就是汉儒阴阳变异的天道思想,这种神学化的思想不得不接受道家、玄学的重新阐释。清皮锡瑞《经学通论》说:“汉末易道猥杂,卦气爻辰纳甲飞伏世应之说纷然并作,弼乘其弊,扫而空之,颇有摧陷廓清之功,而以清言说经,杂以道家之学,汉人朴实说经之体,至此一变,宋赵师秀诗云‘辅嗣易行无汉学’,可为定评。……弼注之所以可取者,在不取术数而明义理;其所以可议者,在不切人事,而杂玄虚。”(13)魏晋人以玄虚取代汉人的解经之体,即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思想的玄学化潮流,玄学使魏晋表现出与汉代明显有别的学术气质,所以从“本无玄学”到“谈老殊进”,明确表明了陆机入洛后思想上的玄学化转变。(14)
玄学化对陆机天道思想的重构具有重要的意义。玄学摒弃了汉儒的宇宙生成论,而将天道由神学转变为形而上学。(15)陆机《列仙赋》云:“因自然以为基,仰造化而闻道。”这里“自然”、“道”即有本体的含义,也就是《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意思,《文赋》以老庄思想为指导(16),更可证明陆机受到道家思想深刻的影响。葛洪《抱朴子》载陆机临亡时说“穷通,时也;遭遇,命也”(17),《晋书》本传也载陆机在遇难前“神色自若”曰:“今日受诛,岂非命也!”这种“临难不惧”,即与《庄子·秋水》说的“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很相似。《遂志赋》云,“惟万物之运动,善纷纠而相袭”,《叹逝赋》说,“伊天地之运流,纷升降而相袭”,都是从汉儒的天道观之宇宙运动入手,但陆机在接下来说,“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遂志赋》),“谅造化之若兹,吾安得取乎久长”(《叹逝赋》),明显可以看出他思想上的进化,即从对天地运行的外在客观现实的具体认识,升华到对社会人生变化的必然性的根本性认识。这种思维方式即是从汉学朴实的“提纬古今,总验名实”向玄学的“妙得玄微”的转变,体现了陆机思维方式的变化和思辨能力的提高。《思亲赋》云:“天步悠长,人道短矣,异途同归,无早晚矣。”《叹逝赋》也说:“然后弭节安怀,妙思天道,精浮神沦,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即从对“天道”的理性思考中,领悟“大暮同寐”的必然性,从而也认识到不必“矜晚怨早”。这些都可以看出玄学重构之下,陆机的天道思想异于神学的理性内涵。
陆机将对宇宙永恒运行的认识,提升到对万事万物的普遍必然性的理解,可以说,他所理解的其实是一切事物具有的本体意义的“道”、“命”,所以“天道”也就带有本体的性质,这正是魏晋人的思想特点。李泽厚说:汉儒把原始儒家“以身作则”的道德论,提升为“天人感应”的帝国秩序的宇宙论,“它在意识形态和科学文化的两方面都上升了一级,也为下一步魏晋本体论和宋明心性论作了理论上的足够储备。”(18)陆机则在玄学的影响下,进一步将汉儒的“天人感应”提升到魏晋玄学的本体论阶段。陆机天道思想由汉儒发展到魏晋玄学,其实也是其现实经历与整个思想史发展结合的逻辑结果。陆机玄学化的天道思想本质上是把汉儒天道观哲理化了,把它从一种机械的宇宙模式和神秘的天人感应升华到形而上学,但这种提升并不是对汉儒完全的排斥和遗弃,而是援玄入儒、以玄释儒。陆机的天道思想仍保留着汉儒天人对应的形式,即“天道”与“人道”的对应,这种对应是形而上的“天人之际”的关系,是本体与客观事物的对应,与汉儒有本质的区别。可以说,陆机通过玄学将天道思想由神学改造成为形而上学,实现了对天道思想的重新建构。
陆机天道思想的玄学化转变,使天道思想由外在的迷信的神学,转变为内在的理性精神,成为对人生具有指导意义的世界观,这对陆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天道思想对陆机诗歌创作的影响
天道思想影响下陆机的思维方式与道家有很相似的一面,即把带有本体性的思想推广到对普遍事物的理解上,这对情感具有明显的自我消解作用,因此深刻地影响了陆机对诗歌题材的选择及对情感的表现。
陆机诗歌缺少对社会政治题材的表现,与其天道观思想有很深刻的联系。《与弟清河云诗》序云:
余弱年夙孤,与弟士龙衔恤,续忝末绪。会逼王命,墨絰即戎,时并萦发,悼心告别,渐历八载,家邦颠覆,凡厥同生,凋落殆半。收迹之日,感物兴哀,而士龙又先在西,时迫当祖载,二昆不容逍遥,衔痛动徂,遗情西慕,故作是诗,以寄其哀苦。
据《吴志·陆抗传》,从凤凰三年(274)秋,陆抗卒,陆机与晏、景、玄、云等兄弟分领陆抗兵,到太康元年(280)吴国亡,及稍后陆机葬其兄晏、景二人于先人墓侧,前后历时将近八年,就是诗序中说的“渐历八载”,所以这首诗当作于太康二年前后。(19)诗分十章,第九章云:
昔我斯逝,兄弟孔备。今予来思,我凋我瘁。昔我斯逝,族有余荣。今我来思,堂有哀音。我行其道,鞠为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亡。拊膺涕泣,血泪彷徨。
诗序和诗歌本身都袒露了那种国破家亡的深刻痛苦,我们所引的这一章,用《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句式,形成“今昔”对比的强烈反差,来表现诗人那种难以接受又不能不接受的深沉痛苦。这首诗可以说是陆机国破家亡的痛苦之情的一次激烈迸发,但是这种激烈深刻的情感在陆机入洛后的诗歌中是很少见的,其原因一方面与陆机作为亡国之臣入仕新朝的现实政治考虑有关,但其内因却须从陆机自身的思想来寻找,这就是入洛后陆机思想的转变。陆机玄学化的天道思想的理性思辨能力和将本体性思想推广到对普遍事物的理解的思维方式,对其情感具有很强的消弭作用,如《门有车马客行》:
门有车马客,驾言发故乡。念君久不归,濡迹涉江湘。投袂赴门途,揽衣不及裳。拊膺携客泣,掩泪叙温凉。借问邦族间,恻怆论存亡。亲友多零落,旧齿皆凋丧。市朝互迁异,城阙或丘荒。坟垄日夜多,松柏郁茫茫。天道信崇替,人道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
这首仍可以看作是陆机对国破家亡的感慨系之(20),但和《与弟清河诗》不同的是,《门有车马客行》不是无节制地表现那种一往伤情的“拊膺涕泣,血泪彷徨”,而是在抒发了悲怆的家国之思后以“天道信崇替,人道安得长”的说理来作结,实乃一巨大的转变。陆机很多诗歌都有这种情况,即用与此相似的诗句从理性上对所发之情做一个了结和消解,如《齐讴行》:
营丘负海曲,沃野爽且平。洪川控河济,崇山入高冥。东被姑尤侧,南界聊摄城。海物错万类,陆产尚千名。孟诸吞楚梦,百二侔秦京。惟师恢东表,桓后定周倾。天道有迭代,人道无久盈。鄙哉牛山叹,未及至人情。爽鸠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将复去,长存非所营。
诗的前部分用赋的笔法描写齐国之江山辽阔、物产丰富,为齐景公的“牛山之泣”造势,但对这种悲慨,陆机则以“鄙哉牛山叹,未及至人情”加以鄙薄,并用“天道有迭代,人道无久盈”来表明自己对于人生的必然性的理解,从而也自然地消解了齐景公式的悲叹。其他如《塘上行》“天道有迁异,人理无常全”,《遨游出西城》“迁化有常然,盛衰自相袭”,都体现了陆机以理化情的思想。
理性思想对情感的消解作用是很明显的,这一点中外思想家都有深入的论述。17世纪荷兰著名思想家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即明确地阐述这一点,其第五部分《论理智的力量或人的自由》命题六就说:
只要心灵理解到一切事物都是必然的,那么它控制情感的力量便愈大,而感受情感的痛苦便愈小。
在这个命题的附释里斯宾诺莎进一步解释道:
对事物必然性的知识愈能推广到我们所更能明晰、更活泼地想象着的个体事物上,则心灵控制情感的力量便愈大。……因为我们看见,一个人对于所失掉的有价值的东西的痛苦一定可以减轻,如果失者认识到所失掉的东西,在任何方式下都是无法保存的。(21)
斯宾诺莎说的将“对事物的必然性的知识”加以推广的思维方式,与我们前面说的陆机将本体论思想推广到对普遍事物的理解上是一致的。按斯宾诺莎的思想,思想对情感的控制是通过发现和理解事物的必然性而达到的,这其实就是以理化情的作用,也就是《庄子·人间世》说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正是这种理性力量消弭了陆机激烈的内心痛苦,使之缺乏一种悲剧感以及由此触发的更为巨大的诗歌创作力量。宗白华说:中国人从宇宙运行的节奏和谐中体验到的必然性,成了其文化艺术的一个基础,所以“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发挥,且往往被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发挥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22)固然对中国的文化艺术精神不能一概而论,但就陆机来说,却的确可以作为这种传统艺术精神的一个典型代表。陆机虽主张“诗缘情而绮靡”,但从《文赋》中可以看出,陆机并不认为“情”是文学的唯一要素,《遂志赋序》批评冯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即可看出他对激烈之情的不满。陆机对于“理”的强调甚至超过了对“情”的强调,《文赋》中说到“理”就有10处,“理”的含义很广,既有“事理”、“文理”等含义,也有本体论的意思,比如结尾部分说“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途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这里的“理”就有宇宙本原的含义,在陆机看来“理”比“情”更具有本体性的地位。合不合“理”是陆机诗学一个很重要的主张,这一点对陆机的诗风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钟嵘《诗品》评陆机的诗歌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气少于公干”(23),“气少”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情感郁积,对于陆机来说这正是以理化情的结果,陆机的诗歌不如建安诗人那样悲凉慷慨,也不如入北朝后的庾信悲怆沈郁,同样是经历了亡国之恨和流离之苦,陆机与庾信在诗歌题材、感情取向和强度等方面都差别巨大,这与他们的思想背景是有关系的。
陆机受天道思想影响的人生观和审美观,决定了其诗歌创作对社会政治等现实题材的疏离,以及在情感表达上的克制。陆机诗歌主要都是思乡怀人、感时伤物等日常化题材,情感的表现虽不能说不真实,却流于普遍化,既乏重大的题材也无深刻之情,所以无法达到曹植、阮籍这些伟大诗人那种由深沉的痛苦和孤愤创造出来的深广宏大的诗境。这与陆机玄学化天道思想对情感的消解是有很深刻的关系的,也是后人认为陆机诗歌创作与其“缘情”理论相矛盾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沈德潜《古诗源》说:“士衡以名将之后,破国亡家,称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词旨敷浅,但工涂泽,复何贵乎。”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更激烈地批评道:“安仁过情,士衡不及情。……故安仁有诗而士衡无诗。”
②③房玄龄《晋书·纪赡传》[O],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19页。
④关于这一点,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史论丛》)有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考。
⑤严可均《全宋文》[O],中华书局,1958年版,卷三十六,第2637页。
⑥陈寿《三国志·吴志·虞翻传》[O],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22页。
⑦(13)皮锡瑞《经学通论》[O],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1页、25页。
⑧郝立权《陆士衡诗注》认为此诗作于“太康二年”。沈玉成《〈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中的几个问题》也认为此诗当作于葬二兄于先人墓侧的前后(《文学遗产》,1992年第3期)。
⑨房玄龄《晋书·陆云传》[O],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85页。
⑩刘敬叔《异苑》[O],中华书局,1996年版,卷六。
(11)《文赋》中陆机在论述创作的构思过程时表现出很强的思辨能力,这一点与入洛后受玄学的影响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12)房玄龄《晋书·陆机传》[0],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67页。
(14)陆机《演连珠》其四二云:“臣闻烟出于火,非火之和;情生于性,非性之适。故火壮则烟微,性充则情约。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无伫立之迹。”这里性、情明显有高低褒贬之分,表明了陆机对“情”的根本态度,联系《演连珠》五十“足于性者,天损不能入”之说来看,“应代表着陆机入洛受玄学风气影响后的观念”(参考周勋初《文赋写作年代新探》,载《文史探微》)。这也表明了陆机思想上的玄学化转变。
(15)《世说新语·文学》载:“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这里说的“天人之际”已不是董仲舒那种具有神学性质的“天人感应”,而是玄学形而上学性质,这段话也表明了玄学对汉儒天道思想内涵的取代和重新构建。
(16)刘若愚认为《文赋》的结尾说的“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是“把表现宇宙原理看作是文学的基本宗旨”的“玄学论”的诗学主张。(参见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第2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文赋》论述创作构思时说:“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种“收视反听”的内视法,更是从庄子的“心斋”发展而来的。(参见《庄子·人间世》)
(17)金涛声《陆机集》[M],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9页。
(18)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页、166页。
(19)参见沈玉成《〈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中的几个问题》,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3期。
(20)《乐府解题》云:“曹植等《门有车马客行》,皆言问讯其客,或得故旧乡里,或驾自京师,备叙市朝迁谢,亲友凋丧之意也。”陆机此诗虽不出这个乐府主题,但联系陆机的现实经历,这首诗明显寄托了陆机对国破家亡的感慨。
(21)斯宾诺莎《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第243页。
(22)宗白华《美学的散步》[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4-95页、第97页。
(23)曹旭《诗品集注》[O],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标签:玄学论文; 天道论文; 陆机论文; 三国论文; 诗歌论文; 文化论文; 门有车马客行论文; 读书论文; 吴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