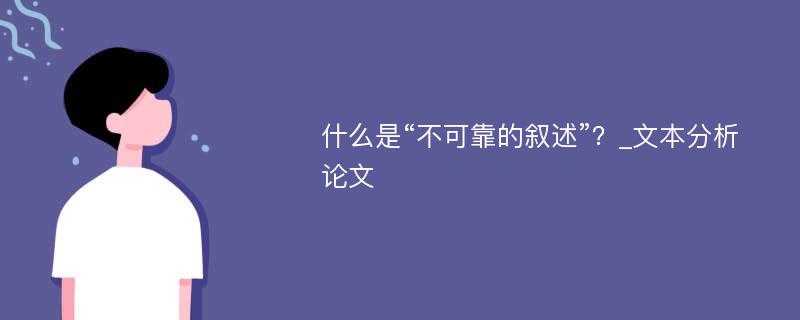
何为“不可靠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何为论文,不可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可靠叙述”是当代西方叙事理论中的“一个中心话题”,① 近年来,这一话题在国内叙事研究界也日益受到重视,频频出现于相关研究论著之中。针对“不可靠叙述”,有两种研究方法:修辞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对此,西方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认知方法优于修辞方法,应该用前者取代后者;另一种认为两种方法各有其片面性,应该将两者相结合,采用“认知—修辞”的综合性方法。笔者认为,两种方法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此外,两者实际上涉及两种难以调和的阅读位置,对“不可靠叙述”的界定互为冲突。根据一种方法衡量出来的“不可靠”叙述依据另一种方法的标准完全有可能变成“可靠”叙述,反之亦然。由于两者相互之间的排他性,不仅认知(建构)方法难以取代修辞方法,而且任何综合两者的努力也注定徒劳无功。因此,在叙事研究的实践中,我们只能保留其中一种方法,而牺牲或压制另一种。本文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消除混乱认识,廓清画面。
修辞性研究方法
修辞方法由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1961)中创立,追随者甚众。布思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标准是作品的规范(norms)。所谓“规范”,即作品中事件、人物、文体、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标准。②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布思认为作品的规范就是“隐含作者”的规范。通常我们认为作品的规范就是作者的规范。但布思提出了“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来特指创作作品时作者的“第二自我”。在创作不同作品时作者可能会采取不尽相同的思想艺术立场,因此该作者的不同作品就可能会“隐含”互为对照的作者形象。作者在创作某一作品时特定的“第二自我”就是该作品的“隐含作者”。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布思一再强调作品意义的丰富性和阐释的多元性,但受新批评有机统一论的影响,他认为作品是一个艺术整体(artistic whole),③ 由各种因素组成的隐含作者的规范也就构成一个总体统一的衡量标准。
在布思看来,倘若叙述者的言行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那么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倘若不一致,则是不可靠的。④ 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往往出现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布思聚焦于两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一种涉及故事事实,另一种涉及价值判断。叙述者对事实的详述或概述都可能有误,也可能在进行判断时出现偏差。无论是哪种情况,读者在阅读时都需要进行“双重解码”(doubledecoding)⑤: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离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构成正确的判断。这显然有利于调动读者的阅读积极性。文学意义产生于读者双重解码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与(读者心目中)可靠的作者之间的对照。它不仅服务于主题意义的表达,而且反映出叙述者的思维特征,因此对揭示叙述者的性格和塑造叙述者的形象有着重要作用。
布思指出,在读者发现叙述者的事件叙述或价值判断不可靠时,往往产生反讽的效果。作者是效果的发出者,读者是接受者,叙述者则是嘲讽的对象。也就是说作者和读者会在叙述者背后进行隐秘交流,达成共谋,商定标准,据此发现叙述者话语中的缺陷,而读者的发现会带来阅读快感。⑥ 在谈到叙述的不可靠性时,布思举了T·S·艾略特的《艾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开头为例。在普鲁弗洛克眼里,黄昏的天空就像是一个被麻醉的病人。倘若读者想要知道天气的真实情况的话,这样的描述无疑是不可靠的。⑦ 但此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我们面对的是象征性很强的现代派诗歌,而非现实主义作品。普鲁弗洛克眼中的天空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困境,体现了(隐含)作者对当时西方社会的看法,作者也无疑希望读者分享这一看法。的确,就文本的字面表层而言,普氏的叙述未能反映天气的真实情况,因此不可靠。然而,就文本的象征深层而言,普氏的叙述则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与作者对世界的共识,这也是作者邀请读者分享的共识,因此并非不可靠。
修辞方法当今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布思的学生和朋友、美国叙事理论界权威詹姆斯·费伦。他至少在三个方面发展了布思的理论。一是他将不可靠叙述从两大类型或两大轴(“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发展到了三大类型或三大轴(增加了“知识/感知轴”),并沿着这三大轴区分了六种不可靠叙述的亚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⑧ 就为何要增加“知识/感知轴”而言,费伦举了石黑一雄的小说《长日将尽》的最后部分为例。第一人称叙述者史蒂文斯这位老管家在谈到他与以前的同事肯顿小姐的关系时,只是从工作角度看问题,未提及自己对这位旧情人的个人兴趣和个人目的。这有可能是故意隐瞒导致的“不充分报道”(事实/事件轴),也有可能是由于他未意识到(至少是未能自我承认)自己的个人兴趣而导致的“不充分解读”(知识/感知轴)。⑨
应该指出,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并非未涉及“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叙述。他只是未对这种文本现象加以抽象概括。他提到叙述者可能认为自己具有某些品质,而(隐含)作者却暗暗加以否定,例如在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中,叙述者声称自己天生邪恶,而作者却在他背后暗暗赞扬他的美德。⑩ 这就是叙述者因为自身知识的局限而对自己的性格进行的“错误解读”。当然,费伦对三个轴的明确界定和区分不仅引导批评家对不可靠叙述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而且还将注意力引向了三个轴之间可能出现的对照或对立:一位叙述者可能在一个轴上可靠(譬如对事件进行如实报道),而在另一个轴上不可靠(譬如对事件加以错误的伦理判断)。若从这一角度切入,往往能更好地揭示这一修辞策略的微妙复杂性,也能更好地把握叙述者性格的丰富多面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费伦仅关注三个轴之间的平行关系,而笔者认为,这三个轴在有的情况下会构成因果关系。譬如上文提到的史蒂文斯对自己个人兴趣的“不充分解读”(知识/感知轴)必然导致他对此的“不充分报道”(事实/事件轴)。显然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两个轴上的不可靠性在一个因果链中共同作用。
除了增加“知识/感知轴”,费伦还增加了一个区分——区分第一人称叙述中,“我”作为人物的功能和作为叙述者的功能的不同作用。费伦指出布思对此未加区别:
布思的区分假定一种等同,或确切说,是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一种连续,所以,批评家希望用人物的功能解释叙述者的功能,反之亦然。即是说,叙述者的话语被认为相关于我们对他作为人物的理解,而人物的行动则相关于我们对他的话语的理解。(11)
也就是说,倘若“我”作为人物有性格缺陷和思想偏见,那批评家就倾向于认为“我”的叙述不可靠。针对这种情况,费伦指出,人物功能和叙述者功能实际上可以独立运作,“我”作为人物的局限性未必会作用于其叙述话语。譬如,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对在威尔森车库里发生的事的叙述就相当客观可靠,未受到他的性格缺陷和思想偏见的影响。(12) 在这样的情况下,叙述者功能和人物功能是相互分离的。这种观点有助于读者更为准确地阐释作品,更好地解读“我”的复杂多面性。
费伦还在另一方面发展了布思的理论。费伦的研究注重叙事的动态进程,认为叙事在时间维度上的运动对于读者的阐释经验有至关重要的影响,(13) 因此他比布思更为关注叙述者的不可靠程度在叙事进程中的变化。他不仅注意分别观察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在“事实/事件轴”、“价值/判断轴”、“知识/感知轴”上的动态变化,而且注意观察在第一人称叙述中,“我”作为“叙述者”和作为“人物”的双重身份在叙事进程中何时重合,何时分离。这种对不可靠叙述的动态观察有利于更好地把握这一叙事策略的主题意义和修辞效果。但笔者认为,费伦的研究有一个盲点,即忽略了第一人称叙述的回顾性质。他仅仅在共时层面探讨“我”的叙述者功能和人物功能。而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我”的人物功能往往是“我”过去经历事件时的功能,这与“我”目前叙述往事的功能具有时间上的距离。我们不妨看看鲁迅《伤逝》中的一个片断:
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领会地点点头。
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
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尔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
这段文字中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与两人爱情的悲剧性结局直接冲突,可以说是不可靠的叙述。这是正在经历事件的“我”或“我们”在幸福高潮时的看法或幻想,与文本开头处“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相呼应。也就是说,作为叙述者的“我”很可能暂时放弃了自己目前的视角,暗暗借用了当年作为人物的“我”的视角来叙述。“我”是一位理想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作品突出表现了其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现实中的幻灭之间的对照和冲突。这句以叙述评论的形式出现的当初的幻想对于加强这一对照起了较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中的“凝固”一词与前文中的“更新、生长,创造”相冲突,带有负面意思,体现出叙述自我的反思,也可以说是叙述自我对子君满足现状的一种间接责备。这种种转换、冲突、对照和模棱两可具有较强的修辞效果,对于刻画人物性格,强化文本张力,增强文本的戏剧性和悲剧性具有重要作用。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1)叙述者功能和人物功能的历时性渗透或挪用——当今的叙述者“我”不露痕迹地借用了过去人物“我”的视角。(2)叙述者本人采用的策略。 不可靠叙述往往仅构成作者的叙事策略,叙述者并非有意为之。但此处的叙述者虽然知晓后来的发展,却依然在叙述层上再现了当初不切实际的看法,这很可能是出于修辞目的而暂时有意误导读者的一种策略。诚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在回味当初的幸福情景时,叙述者又暂时回到了当时“宁静而幸福”的心理状态。若是那样的话,叙述者功能和人物功能则达到了某种超越时空的重合。(3)像这样的不可靠叙述之理解有赖于叙事进程的作用——只有在读到后面的悲剧性发展和结局时,才能充分领悟到此处文字的不可靠。
值得一提的是,布思、费伦和其他众多学者是将叙述者是否偏离了隐含作者的规范作为衡量“不可靠”的标准,而有的学者则是将叙述者是否诚实作为衡量标准。在探讨史蒂文斯由于未意识到自己对肯顿小姐的个人兴趣而做出的不充分解读时,丹尼尔·施瓦茨提出史蒂文斯只是一位“缺乏感知力”的叙述者,而非一位“不可靠”的叙述者,因为他“并非不诚实”。(14) 笔者认为,把是否诚实作为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标准是站不住脚的。叙述者是否可靠在于是否能提供给读者正确和准确的话语。一位缺乏信息、智力低下、道德败坏的人,无论如何诚实,也很可能会进行错误或不充分的报道,加以错误或不充分的判断,得出错误或不充分的解读。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诚实,其叙述也很可能是不可靠的。在此,我们需要认清“不可靠叙述”究竟涉及叙述者的哪种作用。A ·纽宁认为石黑一雄《长日将尽》中的叙述者“归根结底是完全可靠的”,因为尽管其叙述未能客观再现故事事件,但真实反映出叙述者的幻觉和自我欺骗。(15) 笔者对此难以苟同,应该看到,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涉及的是叙述者的中介作用,故事事件是叙述对象,若因为叙述者的主观性而影响了客观再现这一对象,作为中介的叙述就是不可靠的。的确,这种主观叙述可以真实反映出叙述者本人的思维和性格特征,但它恰恰说明了这一叙述中介为何会不可靠。
认知(建构)方法
认知(建构)方法是以修辞方法之挑战者的面目出现的,旨在取代后者。这一方法的创始人是塔马·雅克比,其奠基和成名之作是1981年在《今日诗学》上发表的《论交流中的虚构叙事可靠性问题》一文,(16) 该文借鉴了迈尔·斯滕伯格将小说话语视为复杂交流行为的理论,(17) 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来看不可靠性。20多年来,雅克比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并在2005年发表于的《叙事理论指南》的一篇论文中,以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为例,总结和重申了自己的基本主张。(18) 雅克比将不可靠性界定为一种“阅读假设”或“协调整合机制”(integration mechanism),即当遇到文本中的问题(包括难以解释的细节或自相矛盾之处)时,读者会采用某种阅读假设或协调机制来加以解决。
雅克比系统提出了以下五种阅读假设或协调机制。 (1)关于存在的机制(the existential mechanism)。这种机制将文中的不协调因素归因于虚构世界,尤其是归因于偏离现实的可然性原则,童话故事、科幻小说、卡夫卡的《变形记》等属于极端的情况。在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中,叙述者一直断言他的婚姻危机具有代表性。这一断言倘若符合虚构现实,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笔者认为,这里实际上涉及了两种不同的情况。在谈童话故事、科幻小说和《变形记》时,雅克比考虑的是虚构规约对现实世界的偏离,而在谈托尔斯泰的作品时,她考虑的则是作品内部叙述者的话语是否与故事事实相符。前者与叙述者的可靠性无关,后者则直接相关。(2)功能机制。 它将文中的不协调因素归因于作品的功能和目的。(3)文类原则。依据文类特点(如悲剧情节之严格规整或喜剧在因果关系上享有的自由)来解释文本现象。(4)关于视角或不可靠性的原则(the perspectival or unreliability principle)。依据这一原则, “读者将涉及事实、行动、逻辑、价值、审美等方面的各种不协调因素视为叙述者与作者之间的差异”。这种对叙述者不可靠性的阐释“以假定的隐含作者的规范为前提”。(5)关于创作的机制。这一机制将文中矛盾或不协调的现象归因于作者的疏忽、摇摆不定或意识形态问题等。(19)
另一位颇有影响的认知(建构)方法的代表人物是A·纽宁。他受雅克比的影响,聚焦于读者的阐释框架,断言“不可靠性与其说是叙述者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是读者的阐释策略”。(20) 他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隐含作者”这一概念进行了解构和重构,采用“总体结构”(the structural whole)来替代“隐含作者”。在A·纽宁看来,总体结构并非存在于作品之内,而是由读者建构的, 若面对同一作品,不同读者很可能会建构出大相径庭的作品“总体结构”。(21) 在1999年发表的《不可靠,与什么相比?》一文中,A·纽宁对不可靠叙述重新界定如下:
与查特曼和很多其他相信隐含作者的学者不同,我认为不可靠叙述的结构可用戏剧反讽或意识差异来解释。当出现不可靠叙述时,叙述者的意图和价值体系与读者的预知(foreknowledge)和规范之间的差异会产生戏剧反讽。对读者而言,叙述者话语的内部矛盾或者叙述者的视角与读者自己的看法之间的冲突意味着叙述者的不可靠。(22)
也就是说,A·纽宁用读者的规范既替代了(隐含)作者的规范,也置换了文本的规范。尽管A·纽宁也是一再提到文本的规范与读者规范之间的交互作用,但既然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文本的总体结构是由读者决定的,因此文本规范已经变成读者规范。
“认知(建构)方法”难以取代“修辞方法”
雅克比和纽宁都认为自己的模式优于布思创立的修辞模式,因为它不仅可操作性强(确定读者的假设远比确定作者的规范容易),且能说明读者对同一文本现象的不同解读。不少西方学者也认为以雅克比和A·纽宁为代表的认知(建构)方法优于修辞方法,前者应取代后者。(23) 但笔者对此难以苟同。在笔者看来,这两种方法实际上涉及两种并行共存、无法调和的阅读位置。一种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读者”的阅读位置,另一种是“隐含读者”或“作者的读者”的阅读位置。(24) 前者受制于读者的身份、经历和特定接受语境,后者则为文本所预设,与(隐含)作者相对应。修辞方法聚焦于后面这种理想化的阅读位置。在修辞批评家看来,(隐含)作者创造出不可靠的叙述者,制造了作者规范与叙述者规范之间的差异,从而产生反讽等效果。“隐含读者”或“作者的读者”则对这一叙事策略心领神会,加以接受。倘若修辞批评家考虑概念框架(conceptual schema), 也是以作者创作时的概念框架为标准,读者的任务则是“重构”同样的概念框架,以便作出正确的阐释。(25) 值得注意的是,不可靠叙述者往往为第一人称,现实中的读者只能通过叙述者自己的话语来推断(隐含)作者的规范和概念框架。可以说,这种推断往往是读者将自己眼中的可靠性或权威性投射到作者身上。面对同样的文本现象,不同批评家很可能会推断出不同的作者规范和作者框架。也就是说,真实读者只能争取进入“隐含读者”或“作者的读者”之阅读位置,(26) 这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由于修辞批评家力求达到理想的阐释境界,因此他们会尽量排除干扰,以便把握作者的规范,作出较为正确的阐释。
与此相对照,以雅克比和A·纽宁为代表的认知(建构)方法聚焦于读者的不同阐释策略或阐释框架之间的差异,并以读者本身为衡量标准。既然以读者本身为标准,读者的阐释也就无孰对孰错之分。雅克比将2005年发表的论文题目定为“作者修辞、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大相径庭的解读: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托尔斯泰的作品争议性很强,叙述者究竟是否可靠众说纷纭。雅克比将大量篇幅用于述评互为冲突的解读,论证这些冲突如何源于读者的不同阅读假设或协调机制。尽管她在标题中提到了“作者修辞”,且在研究中关注“隐含作者的规范”,但实际上这些概念与修辞学者的概念有本质差异。在修辞学者眼中,“隐含作者的规范”存在于文本之内,读者的任务是尽量靠近这一规范,并据此进行阐释。相比之下,在雅克比眼中,任何原则都是读者本人的阅读假设,“隐含作者的规范”只是读者本人的假定,也就是说,雅克比所说的“作者修辞”实际上是一种读者建构。她强调任何阅读假设都可以被“修正、颠倒,甚或被另一种假设所取代”,并断言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并非固定在叙述者之(可然性)形象上的性格特征,而是依据相关关系[由读者]临时归属或提取的一个特征,它取决于(具有同样假定性质的)在语境中作用的规范。在某个语境(包括阅读语境、作者框架、文类框架)中被视为‘不可靠’的叙述,可能在另一语境中变得可靠,甚或在解释时超出了叙述者的缺陷这一范畴。”(27) A·纽宁也强调相对于某位读者的道德观念而言,叙述者可能是完全可靠的,但相对于其他人的道德观念来说,则可能极不可靠。他举了纳巴科夫《洛莉塔》的叙述者亨伯特为例。倘若读者自己是一个鸡奸者,那么在阐释亨伯特这位虚构的幼女性骚扰者时,就不会觉得他不可靠。(28)
我们不妨从A·纽宁的例子切入, 考察一下两种方法之间不可调和又互为补充的关系。在修辞方法看来,若鸡奸者认为亨伯特奸污幼女的行为无可非议,他自我辩护的叙述正确可靠,那就偏离了隐含作者的规范,构成一种误读。这样我们就能区分道德观正常的读者接近作者规范的阐释与鸡奸者这样的读者对作品的“误读”。与此相对照,就认知方法而言,读者就是规范,阐释无对错之分。那么鸡奸者的阐释就会和非鸡奸者的阐释同样有理。一位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也就会随着不同读者的不同阐释框架而摇摆不定。不难看出,若以读者为标准,就有可能会模糊、遮蔽、甚或颠倒作者或作品的规范。但认知方法确有其长处,可揭示出不同读者的不同阐释框架或阅读假设,说明为何对同样的文本现象会产生大相径庭的阐释。这正是修辞批评的一个盲点,修辞批评家往往致力于自己进行尽量正确的阐释,不关注前人的阅读,即便关注也只是说明前人的阅读如何与作品事实或作者规范不符,不去挖掘其阐释框架。而像雅克比、A·纽宁这样的认知批评家则致力于分析前人大相径庭的阐释框架。倘若我们仅仅采用修辞方法,就会忽略读者不尽相同的阐释原则和阐释假定;而倘若我们仅仅采用认知方法,就会停留在前人阐释的水平上,难以前进。此外,倘若我们以读者规范取代作者/作品规范,就会丧失合理的衡量标准。
“认知(建构)方法”对“认知叙事学”主流的偏离
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以雅克比和A ·纽宁为代表的“认知方法”是“认知叙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若仔细考察,则不难发现,他们的基本立场偏离了“认知叙事学”的主流。认知叙事学是与认知科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旨在揭示读者共有的叙事阐释规律。认知叙事学所关注的语境与西方学术大环境所强调的语境实际上有本质不同。就叙事阐释而言,我们不妨将“语境”分为两大类:一是“叙事语境”,一是“社会历史语境”。后者主要涉及与种族、性别、阶级等社会身份相关的意识形态关系;前者涉及的则是超社会身份的“叙事规约”或“文类规约”(“叙事”本身构成一个大的文类,不同类型的叙事则构成其内部的次文类)。为了廓清画面,让我们先看看言语行为理论所涉及的语境:教室、教堂、法庭、新闻报道、小说、先锋派小说、日常对话等等。(29) 这些语境中的发话者和受话者均为类型化的社会角色:老师、学生、牧师、法官、先锋派小说家等等。这样的语境堪称“非性别化”、“非历史化”的语境。诚然,“先锋派小说”诞生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但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并非该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关系,而是该文类本身的创作和阐释规约。与这两种语境相对应,有两种不同的读者。一种是作品主题意义的阐释者,涉及阐释者的身份、经历、时空位置等;另一种我们可称为“文类读者”或“文类认知者”,其主要特征在于享有同样的文类规约,同样的文类认知假定、认知期待、认知模式、认知草案或认知框架。不难看出,我们所说的“文类认知者”排除了有血有肉的个体独特性,突出了同一文类的读者所共享的认知规约。(30) 我们不妨区分以下两种研究方法:
(1)探讨读者对于(某文类)叙事结构的阐释过程之共性,聚焦于无性别、种族、阶级、经历、时空位置之分的“文类认知者”,或关注读者特征/时空变化如何妨碍个体读者成为“文类认知者”。
(2)探讨不同读者对同一种叙事结构的各种反应,需关注个体读者的身份、 经历、阅读假设等对于阐释所造成的影响。
大多数认知叙事学论著都属于第一种研究,集中关注“规约性叙事语境”和“文类认知者”。也就是说,这些认知叙事学家往往通过个体读者的阐释来发现共享的叙事认知规律。与此相对照,雅克比和A ·纽宁为代表的“认知”方法属于第二种研究,聚焦于不同读者认知过程之间的差异,发掘和解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并以读者的阐释框架本身为衡量标准。有趣的是,有的“认知”研究从表面上看属于第二种,实际上则属于第一种。让我们看看弗卢德尼克的下面这段话:
此外,读者的个人背景、文学熟悉程度、美学喜恶也会对文本的叙事化产生影响。譬如,对现代文学缺乏了解的读者也许难以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加以叙事化。这就像20世纪的读者觉得15或17世纪的一些作品无法阅读,因为这些作品缺乏论证连贯性和目的论式的结构。(31)
从表面上看,弗卢德尼克考虑的是读者特征和阅读语境,实际上她是以作品本身(如现代文学)为衡量标准,关注的是文类叙事规约对认知的影响——是否熟悉某一文类的叙事规约直接左右读者的叙事认知能力。无论读者属于什么性别、阶级、种族、时代,只要同样熟悉某一文类的叙事规约,就会具有同样的叙事认知能力(智力低下者除外),就会对文本进行同样的叙事化。而倘若不了解某一文类的叙事规约,在阅读该文类的作品时,就无法对作品加以叙事化,阅读就会失败。这与雅克比和A·纽宁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照,因为后者是以个体读者为标准的。
西方学界迄今没有关注“认知(建构)方法”的独特性,这导致了以下两种后果:(1)雅克比、A·纽宁和其他相关学者一方面将叙述可靠性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个体读者,一方面又大谈读者共享的叙事规约,文中频频出现自相矛盾之处,这在A·纽宁的《不可靠,以什么为标准?》一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将“认知(建构)方法”与沿着修辞轨道走的“认知方法”混为一谈。A·纽宁的夫人V·纽宁就是沿着修辞轨道走的一位“认知”学者。她在《不可靠叙述与历史上价值与规约的多变性》(2004)一文中,集中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所采取的不同阐释策略。(32) 但她的立场是修辞性的,以作者创作时的概念框架为标准, 读者的任务是重构与作者相同的概念框架。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不同社会文化因素会影响读者的阐释,形成阐释陷阱,导致各种“误读”;读者需要排除历史变化中的各种阐释陷阱,才能把握作者的规范,得出较为正确的阐释。这是以作者为标准的认知研究,与A·纽宁等以读者为标准的认知研究在基本立场上形成了直接对立。西方学界对此缺乏认识,对这两种认知研究不加区分,难免导致混乱。笔者的体会是,不能被标签所迷惑,一个“认知”标签至少涵盖了三种研究方法:(1)以叙事规约为标准的方法(认知叙事学的主流);(2)以读者的阐释框架为标准的方法(“建构”型方法);(3)以作者的概念框架为标准的方法(“修辞”型方法)。在研究中,我们应具体区分是哪种认知方法,并加以区别对待,才能避免混乱。
“认知(建构)—修辞”方法的不可能
在2005年发表于《叙事理论指南》的一篇重新审视不可靠叙述的论文中,A ·纽宁对修辞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的片面性分别加以了批评:修辞方法聚焦于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无法解释不可靠叙述在读者身上产生的“语用效果”;(33) 另一方面,认知方法仅仅考虑读者的阐释框架,忽略了作者的作用。(34) 为了克服这些片面性,A·纽宁提出了综合性的“认知—修辞方法”。这种“综合”方法所关心的问题是:有何文本和语境因素向读者暗示叙述者可能不可靠?隐含作者如何在叙述者的话语和文本里留下线索,从而“允许”批评家辨认出不可靠的叙述者?(35) 不难看出,这是以作者为标准的“修辞”型方法所关心的问题,没有给“建构”型方法留下余地,而A·纽宁恰恰是想将这两种方法综合为一体。 建构型方法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读者不同的阐释框架如何导致不同的阐释,或不同的解读如何源于不同的阅读假设。这种“读者关怀”难以与“作者关怀”协调统一。纽宁不仅在理论上仅仅照顾到了修辞方法,而且在分析实践中,也仅仅像修辞批评家那样,聚焦于“作者的读者”这一阅读位置,没有考虑不同读者不尽相同的阐释,完全忽略了读者不同阐释框架的作用。(36)
如前所述,这两种方法在基本立场上难以调和。若要克服其片面性,只能让其并行共存,各司其职。在分析作品时,若能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就能对不可靠叙述这一作者创造的叙事策略和其产生的各种语用效果达到较为全面的了解。
人物—叙述的(不)可靠性
叙事学界通常将“不可靠性”仅仅用于叙述者,不用于人物。而笔者在发表于美国《文体》杂志上的论文中,(37) 则聚焦于叙述层上不可靠的人物眼光对人物主体意识的塑造作用。笔者认为,无论在第一人称还是在第三人称叙述中,人物的眼光均可导致叙述话语的不可靠,而这种“不可靠叙述”又可对塑造人物起重要作用。让我们看看康拉德《黑暗的中心》第三章中的一段:
我给汽船加了点速,然后向下游驶去。岸上的两千来双眼睛注视着这个溅泼着水花、震摇着前行的凶猛的河怪的举动。它用可怕的尾巴拍打着河水,向空中呼出浓浓的黑烟。
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为船长马洛,他无疑不会将自己的船视为“河怪”。不难看出,他暗暗采用了非洲土著人不可靠的眼光来叙述,使读者直接通过土著人的眼光来看事物,直接感受他们原始的认知方式以及对“河怪”的畏惧情感。由于土著人的眼光在叙述层上运作,因此导致了叙述话语的不可靠。这种不可靠叙述的独特之处在于人物的不可靠和叙述者的可靠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和由此产生的反讽效果可生动有力地刻画人物特定的意识和知识结构。这种不可靠叙述在中外小说中都屡见不鲜。值得注意的是,在有的作品中,这种人物眼光造成的不可靠叙述较为隐蔽,且难以当场发现,回过头来才会发觉。让我们看看曼斯菲尔德《唱歌课》中的一段:
梅多思小姐心窝里正扎着绝望那把刀子,不由恨恨地瞪着理科女教师。……对方甜得发腻地冲她一笑。“你看来冻——僵了,”她说。那对蓝眼睛睁得偌大;眼神里有点嘲笑的味儿。(难道给她看出点什么来了?)
曼斯菲尔德在《唱歌课》的潜藏文本中对社会性别歧视这把杀人不见血的尖刀进行了带有艺术夸张的揭露和讽刺。(38) 梅多思小姐被未婚夫抛弃后,一直担心社会歧视会让她没有活路。在上引片段中,从表面上看,括号前面是全知叙述者的可靠叙述,但读到后面,我们则会发现这里叙述者换用了梅多思小姐充满猜疑的眼光来观察理科女教师。后者友好的招呼在前者看来成了针对自己的嘲弄。“眼神里有点嘲笑的味儿”是过于紧张敏感的梅多思小姐的主观臆测,构成不可靠的叙述(理科女教师其实根本不知道梅小姐被男人抛弃一事)。这种将人物不可靠的眼光“提升”至叙述层的做法不仅可生动有力地塑造人物主体意识,而且可丰富和加强对主题意义的表达。(39)
这种独特的“不可靠叙述”迄今未引起学界的重视。这主要有以下两种原因:(1)在探讨不可靠叙述时,批评家一般仅关注第一人称叙述,而由人物眼光造成的不可靠叙述常常出现在第三人称叙述中。(2)即便关注了《继承者》这样的第三人称作品大规模采用人物眼光聚焦的做法,也只是从人物的“思维风格”(mind-style)(40) 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没有从“不可靠叙述”这一角度来看问题。其实我们若能对这一方面加以重视,就能从一个侧面丰富对不可靠叙述的探讨。
不可靠叙述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对表达主题意义、产生审美效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一叙事策略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十分热烈的讨论,也希望国内学界对其能予以进一步的关注,以此帮助推动国内叙事研究的发展。
注释:
①(33)(34)(35)(36) Ansgar Nünning,“Reconceptual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Synthesizing Cognitive and Rhetorical Approaches,”in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edited by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Rabinowitz,Oxford:Blackwell,2005,p.92,pp.94—95,p.105,p.101,pp.100—103.
②③④⑥⑦(10) Wayne 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pp.73—74,p.73,p.159,pp.300—309,p.175,pp.158—159.
⑤ 这是笔者从文体学研究领域借用的一个词语。参见拙文Dan Shen,“On the Aesthetic Function of Intentional‘Illogicality’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of Fiction,”in Style 22(1988),pp.628—635。
⑧ James Phelan,Living to Tell about I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pp.49—53;James Phelan and Mary Patricia Martin,“The Lessons of ‘Waymouth’:Homodiegesis,Unreliability,Ethics and The Remains of the Day,”in David Herman ed.,Narratologies,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9,pp.91—96.
⑨(25)(26) James Phelan,Living to Tell about It,pp.33—34,p.105,p.49.
(11)(12)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82、83页。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和“人物”是第一人称叙述中“我”的两个不同身份,我们应该谈“我”作为“叙述者”或“人物”,而不应像费伦那样谈“叙述者……作为人物”。
(13) 参见申丹《多维·进程·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载《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第3—11页;王杰红《作者、读者与文本动力学—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的方法论诠释》,载《国外文学》2004年第3期,第19—23页。
(14) Daniel Schwarz,“Performative Saying and the Ethics of Reading:Adam Zachary Newton's Narrative Ethics,”in Narrative 5 (1997),p.197.
(15)(22)(28) Ansgar Nünning,“Unreliable,Compared to What?:Towards a Cognitive Theory of Unreliable Narration:Prolegomena and Hypotheses,”in Transcending Boundaries:Narratology in Context,edited by Walter Grunzweig and Andreas Solbach,Tubingen:Gunther Narr Verlag,1999,p.59,p.58,p.61.
(16) Tamar Yacobi,“Fictional Reliability as a Communicative Problem,” in Poetics Today 2 (1981):113—26。也请参见Tamar Yacobi,“Narrative and Normative Pattern:On Interpreting Fiction,”in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3 (1987):18—41;“Interart Narrative:(Un) Reliability and Ekphrasis,”in Poetics Today 21 (2000):708—47;“Pachage Deals in Fictional Narrative:The Case of the Narrator's (Un) Reliability,”in Narrative 9(2001):223—29.
(17) Meir Sternberg,Expositional Modes and Temporal Ordering in Fiction,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p.254—305.
(18) Tamar Yacobi,“Authorial Rhetoric,Narratorial(Un)Reliability,Divergent Readings:Tolstoy's Kreutzer Sonata,”in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edited by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Rabinowitz,Oxford:Blackwell,pp.108—23;参见申丹《关于西方叙事理论新进展的思考——评国际上首部〈叙事理论指南〉》,《外国文学》2006年第1期,第92—99页。
(19)(27) Yacobi,“Authorial Rhetoric,Narratorial(Un)Reliability,Divergent Readings,”pp.110—112,p.110.
(20) 纽宁新近从“认知方法”转向了下文将讨论的“认知—修辞方法”。此处的断言是他在近作中对自己曾采纳的“认知方法”的总结(Ansgar Nünning,“Reconceptual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in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edited by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Rabinowitz,Oxford:Blackwell,p.95)。
(21) Ansgar Nünning,“Deconstructing and Reconceptualizing the Implied author,”in Anglistik.Organ des Verbandes Deutscher Anglisten 8(1997),pp.95—116.
(23) 参见Bruno Zerweck,“Historic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Unreliability and Cultural Discourse in Narrative Fiction,”in Style 35.1(2001),p.151.
(24) 参见Peter J.Rabinowitz,“Truth in Fiction:A Reexamination of Audiences,”Critical Inquiry 4 (1976):121—141.
(29) 参见Mary Louise Pratt,Towards a Speech Act Theory of Literary Discours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7;Sandy Petrey,Speech Acts and Literary Theory,London:Routledge,1990.
(30) 参见拙文Dan Shen,“Why Contextual and Formal Narratologies Need Each Other,”in JNT: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35 (2005),pp.155—157;申丹等著《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08—309页。
(31) Monika Fludernik,“Natural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Parameters,”in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edited by David Herman,Stanford:CSLI,2003,p.262.
(32) Vera Nünning,“Unreliable Narr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Variability of Values and Norms:The Vicar of Wakefield as a Test Case of a Cultural-Historical Narratology,”Style 38 (2004):236—252.
(37) Dan Shen,“Unreliability and Characterization,”Style 23 (1988):300—311.
(38)(39) 详见申丹《选择性全知、人物有限视角与潜文本——重读曼斯菲尔德的〈唱歌课〉》,《外国文学》2005年第6期。
(40) 参见拙文Dan Shen,“Mind-style,”in Routle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edited by David Herman et.al.,London:Routledge,2005,pp.311—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