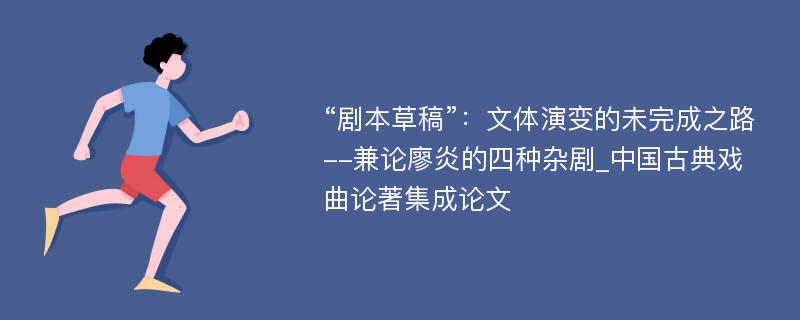
“拟剧本”:未走通的文体演变之路——兼评廖燕《柴舟别集》杂剧四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别集论文,杂剧论文,之路论文,四种论文,文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杂剧在经历了极其繁荣的历史时期之后,至明末及清时虽仍有“场上之曲”问世,但总体上说已为强弩之末,创作上出现一股所谓“案头之书”倾向。在这种倾向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不少剧论家就予以了抨击,力图刹风;而一些作者却仍然我行我素,似乎对这种批评全然不睬,依旧写他们的“案头之书”。甚至有作者(如清代的廖燕)暗示,自己压根就不在乎笔下的作品(如《柴舟别集》杂剧四种)能否搬上舞台,其本意就是在写案头之“书”。就是说,作者实际上是有意模仿剧本的样式,而进行具有别一种特色的文学创作。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这种“案头之书”是否真的一无可取呢?长期以来,这一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即从创作实际出发,对这一模拟剧本样式的文学创作加以探讨。在此,不妨借鉴学界对白话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拟话本”创作的命名方式,将这一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学品种称之为“拟剧本”。
一
杂剧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元代时演出盛况空前,总体说来,其剧本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舞台性与文学性得到了有机结合。而入明之后,北杂剧却逐渐式微,以至在明后期已经极少有人能够演出了。明王骥德在《曲律》中说:“迩年以来……北词几废”(注:王骥德《曲律·论曲源第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集第5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8月版)。 据说明正德年间一位在北京教坊学习过北曲遗音的老艺人,怀艺50年,直到临终前才有幸遇到一位知音。可见当时北杂剧已不大流行(注:何良俊《典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 集第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8月版。)。入清之后,虽仍有一些文人创作杂剧剧本,但用于演出者相当稀少;时或有以南曲演唱杂剧(即所谓“南杂剧”)者,而这已经不是杂剧舞台之正宗,传唱的机会与范围总是有限的。近人王国维曾说:“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注: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原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2月版。)他所看重的是北曲, 而北曲的演出在明清时的确趋于衰落。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则说:“……今歌场中,元曲既灭,明清之曲尚行,则元曲为死剧,而明清活剧也……”(注: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原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2月版。 )这里所谓“元曲”有北杂剧的意思在,而“明清之曲”则主要指传奇。两人的观点不同,但在一点上似乎并无二致,即认为明清时期杂剧舞台相对说来比较死寂。
明以后的杂剧文学创作沿两路发展,一是艺人化,一是文人化。前者便于演出,即所谓语涉“当行”,但一般说来文学性偏低;后者则过于讲究文辞的雅致,剧本有脱离舞台的倾向而成为所谓“案头之书”,即主要供文人阅读。文学性不高,剧本读来索然无味,不会吸引人们欣赏;而“案头之书”难以作为舞台演出底本,则不免失去了戏剧的本色。明王骥德在论及剧本创作时说:“……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上之上也;词藻工,句意妙,如不谐里耳,为案头之书,已落第二义;既非雅调,又非本色,掇拾陈言,凑插俚语,为学究,为张打油,勿作可也!”(注:王骥德《曲律·论曲源第三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集第13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就是说,戏曲剧本既要有文学性,又要有舞台性;离开了舞台性,也就难称地道的剧本了。他不赞成“案头之书”,古今凡以舞台性去衡量“案头之书”的剧论家也都不赞成。
尽管“案头之书”不被剧论家首肯,却依旧有人锲而不舍地去创作这“落第二义”的作品。这似乎是件奇怪的事情,然而其中自有它的原因在。
“案头之书”的出现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作者创作剧本的本意是供舞台演出,但由于对戏曲创作原理与技巧不能谙熟,故写出的剧本难以搬上舞台,而只能作案头作品阅读了;(二)作者原本就不是为演出而作,而只是借剧形式讲故事或抒发胸臆,他们本来就是写“书”,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剧本。以往论者比较多的注意前一种情况,而对于后一种情况往往忽视。其实,假若从文学的角度而非单纯从戏曲表演艺术的角度来看,这后一类创作更值得玩味。
明末徐爔作有一本《写心杂剧》系列剧,其自序云:“《写心》剧者,原以写我心也。心有所触则有所感,有所感则必有所言,言之不足,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能自己者,此予剧之所由作也。”(注:《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1012页。)这里包藏着一点信息,就是说他创作《写心杂剧》就如同写作别一种诗歌一样,目的是抒写自我。实际上也正是这样,该剧共18节(折),其主人公均为徐爔本人,写他的遭际,抒发他个人的感情。于是“杂剧”竟然成为带有抒情性的“自传”了。很显然他不过是把剧本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加以运用,作为一种立传、写心的叙事、抒情的载体而已。既然如此,那么类似于“写心”剧这样的剧本为“案头之书”也便不足为怪了。
二
文艺的价值是多方面的。除审美价值、风教价值、美育价值外,其认识价值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拟剧本中那类“写心”作品恰对我们了解作者的心态提供了相当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这里我们不妨以廖燕的《柴舟别集》杂剧四种作为个例,通过它来透视一下作者特定的心态,这或者对窥探清代士人心态都将是有益的。
廖燕(1644—1705),初名燕生,别号柴舟,韶州曲江(今属广东)人,以教馆为生,有《柴舟全集》。他所创作的杂剧《柴舟别集》包括《醉画图》、《诉琵琶》、《续诉琵琶》和《镜花亭》四种。四剧全以作者本人入戏,这是从徐爔《写心杂剧》那里学来的。四剧一方面对作者的窘境做了精细的描写,另一方面则层次分明地展示了他的处世哲学。
《醉画图》这出独折戏把廖燕的内心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剧中的廖燕满腹文章,更满腹牢骚,因为满腹文章没有使他功成名就;他棱棱傲骨,却偏生贫骨,因为富贵与他无缘;他志气激昂,绝不愿被“头巾”束缚,可仍不免流露出一股酸气,因为尚未摆脱俗事缠绕。主人公想把心中的积怨发泄出来,竟寻不到说得话的朋友,只好孤单单地对着书斋中的四幅画像(即杜默哭庙图、马周濯足图、陈子昂碎琴图和张元昊曳碑图)饮酒独语。他称杜默的落第乃“天下不平事”而深表同情,这实际是对自己遭际的不满;他对马周的“布衣上书”颇为羡慕,其实是要哀叹自己无此际遇;他对陈子昂“碎琴赠文”大加赏识,看来亦想有此一举;而他以为张元昊“此邦不用人,又去他邦”的做法是“英雄志在四方”的体现,则表明他为实现自我竟无视声名的极端想法。剧中的廖燕自始至终都在醉酒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借酒糊涂”。其实这是一句“谎言”,应该说他一直处在清醒之中。当家童劝他少吃一杯时,他是这样回答的:“你那里知道我饮酒的意思;知道我的,除非是壁上画的这几位相公。”在[尾声]中他唱道:“画中人,真吾党,岂是无端学楚狂。我只是颠倒乾坤入醉乡。”表明他把画中的杜、马、陈、张作为自己的楷模,甚至是替身;他不是为古人“代言”,而是借画中人来宣泄心中的郁闷,抒发胸中的激忿,表达自己“有才不遇”的失落感。
然而这只是他心态发展的第一阶段,到他写作《诉琵琶》时情形发生了一些变化。《诉琵琶》中廖燕因贫病加身,只好以卖唱为名,托朋友黄子涯到其他文友处帮他乞食。该剧把“穷”幻化为“穷鬼”形像,把“病”幻化为“疟魔”形像,在二鬼夹攻下,廖燕已家贫如洗。此种情况使他的思想开始产生一定程度的转变。他唱道:“……豪怀徒在醉里慢凝眸,说甚伊周事业,对妻孥冷落已堪羞。”([引子·满庭芳])这正是对他在《醉画图》中所持思想某种程度的否定。在“自报家门”中他又说:
……几日来米坛告匮,谈文岂可疗饥;酒盏俱空,嚼字那堪软饱?
……生平弄笔墨,争夸满腹文章;此日问经纶,那博一家漫饱?在穷鬼和疟鬼面前,“豪怀”显得那么空虚,“事业”又显得那么飘渺。可以看出,贫病逼迫得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面对现实,这可以说是廖燕心态发展的第二阶段。不过在这出戏里,廖燕并没有同头脑中的痼疾彻底决裂,即使在米坛告匮、全家温饱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他仍然担心“尽费前工”。所谓“前工”,是指他长期以来为仕途、事业所做的准备。既然对于前工不肯“尽费”,那也就表明他对富贵和官场并未彻底绝望。他甚至在讨饭时都不能放下文人的架子,仍然奢谈什么“文人贫甚亦风流”。若仅就文人的这股“酸”态而言,同《醉画图》时期又并无质的变化。
《续诉琵琶》含“逐穷”和“悟真”两出(折),除仍有前剧既已出现的穷鬼、疟魔之外,又把“诗”幻化为“诗伯”,把“酒”幻化为“酒仙”,最后还有太上真人上场,矛盾便在人、魔、鬼和神仙之间展开。在这出戏中,廖燕虽靠酒仙将穷鬼驱走,却自知无法从贫穷中挣出,不能实现所谓“饿出王侯”的愿望,于是他的思想出现了某种变化,他唱道:“……生平心事从来落落难俦,消我牢骚诗几首。……从此好歌讴,且慢怀笑傲王侯。”([二郎神]曲)这里一改前剧中对富贵地位的追求,而表现了对仕途的轻蔑态度。酒仙还转述了廖燕这样的话:“且使我望做进士、举人,听人去取,何如现做圣贤仙佛,任我主张,何等自由自在。”显然,廖燕已从名利的桎锢中得到初步解放。“同学诸公”的“眉批”云:“‘听人去取’四字,是活地狱;‘任我主张’四字,是妙天堂!”(注:廖燕《柴舟别集》的《醉画图》、《镜花亭》题前均标有“同学诸公评定”字样,但并未提及“同学”的姓名,推测“眉批”为廖燕本人所题,而托“同学诸公”虚名而已。)这大概是对廖燕心态第三发展阶段的最为准确的注脚,即仕途之路是险恶的,何必去自投罗网呢。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才对太上真人关于“不可因诗酒忘却本来”的点化有所体悟。
太上真人的出现推动廖燕思想向第四阶段发展,他开始识破红尘。这一阶段心态一直延续到《镜花亭》一出,“物外闲游”乃是他心迹之旅的最终归宿。
《柴舟别集》四种杂剧分开各自独立为一剧,而合则衍成完整的剧目。就是说,每剧抒写诗人的一种特定心态,四剧恰好表现了他心态的发展流程。但也应该指出,廖燕的心态有其发展的阶段性,却并不一定呈现为线性发展,在每个阶段中似乎都有其复杂的一面,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即使《镜花亭》一出,廖燕还时不时地表现出一种难以排遣的自怜心理。
三
廖燕《柴舟别集》是较典型的“拟剧本”。关于廖燕是在借用杂剧的形式来抒写自己的内心世界,《醉画图》一出中便透露出这一信息。廖燕这样唱:
[彩旗儿]向丹青闲称奖,借纸笔诉衷肠。那里知醉醉醒醒皆成谎,怪怪奇奇未可量。所谓“借纸笔诉衷肠”,就是指以《醉画图》的编写来表达内心的情怀。这便把他借剧本的样式而进行“写心”的意图交代出来了。当然这不是说《柴舟别集》作为“拟剧本”就一定不能演出,正如白话小说“拟话本”可作为说话的底本由说话人在书场演出一样,“拟剧本”也是可以上演的,只不过它的观众不会太多,演出的效果不会太好而已。但这对于廖燕来说并不重要,他需要的是以剧本形式抒写心灵,并不一定以舞台为媒体将其心灵转达给别人。我们从《诉琵琶》(即《乞食》)一出也能察觉出这一点。这出戏演廖燕为生活所爱,仿陶渊明《乞食》篇而编数首“新词新调”,把它们做为“募疏”以图朋友的周济。《诉琵琶》一剧的主旨便体现在这几首“新词新调”中。剧中人廖燕就说道:“我想,文人唱曲,岂效优人伎俩?把手拍桌子应腔就是了。”显然,他并不在意剧本演出与否,而只是就便借一种现成的传统文体供人吟咏或阅读而已。
那么,作者作为一位诗人,为什么不纯用诗歌形式而还要采用戏曲形式来抒写胸臆呢?这是因为在表现人物命运和感情发展历程方面,戏曲具有明显的优长。如前所述,《柴舟别集》便较成功地把廖燕的人生心迹有层次地展示出来了。
其次,戏曲还善于表现人物之间复杂的矛盾冲突,这便为表达作者内心的复杂面提供了某种可能性。比如穷鬼、疟魔同诗伯、酒仙之间所展开的矛盾,便艺术地表现了廖燕的借酒浇愁(穷、病以及仕途无望)的无奈心理,其中还包含着主人公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而太上真人对他沉湎于诗酒的玩世态度则给予了批评,这实际是廖燕内心矛盾的艺术折射。很显然,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来反映作者的自我矛盾,则使内心世界更具直观性。
再次,作者可以充分利用戏曲“逆向”代言的特性,将自己的思想寄予剧中人身上。通常我们说戏曲是一种代言体制,是指作者为剧中人代言,这是从创作方法而论的;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在为剧中人代言的同时,剧中人身上也便融入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应该说,戏曲的代言功能是双向的,即作者和剧中人互为代言。在《柴舟别集》中为作者廖燕代言的无疑是剧中的廖燕形象,但这不是唯一的;剧中的几个幻化形象,如诗仙、酒仙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代言;不仅如此,即使是他一心想驱逐的“穷鬼”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说话”。我们不妨读一读《续诉琵琶》第一出“逐穷”中穷鬼的一篇大论:
……我的功劳,若说起来亦好大哩!你看自古英雄豪杰,除了这班纨绔膏粱用我不着,若是从布衣白屋崛起的,那个不是我帮衬他来?就如伍员吹箫、韩信乞食、吕蒙正寄居破窑、范仲淹断韭萧寺,这几个古人后来都□封侯拜相;若不是老穷先下一激之力,焉能到此地位?所以太史公常叹我的功劳,说:“不困厄焉能激乎!”……这还不打紧,还要因我一激之力竟做了皇帝的:汉昭烈不因织履营生,做不得后汉皇帝;宋刘裕不因耕田糊口,做不得开国英雄……穷鬼援引古人的发迹史说,“穷”才可以“熬成名士,饿出侯王”,他嘲笑今世之人不能因穷而“发奋”,宣称“富贵要从贫贱中挣出来”。这是廖燕借穷鬼的口讲述穷的“妙处”。可以看出,他的“逐穷”不是简单地欲摆脱穷,而是亟想从贫穷这一母体中“挣”出而得以发迹,这是廖燕“逐穷”时隐藏在心里真实想法,所流露出的仍是文人的那种“酸”气。不仅如此,廖燕还通过穷鬼之口为自己未曾高中进行说词。诗伯问:“……你才先说,柴舟先生有甚好处,怎么不会中?”穷鬼答道:
那里在此较论?孔夫子不曾中得,难道不尊他做圣人?你看自古英雄豪杰,那个是朝廷法度所能笼络得他来的?岂不闻唐朝以诗取士,以杜子美、李太白这样大才,何曾中了?这举人、进士难道中了的,才学好过这二人不成?这莫不是廖燕的口吻?不过语出自己之口显得有些狂妄,于是安排穷鬼去说,觉得较为平和。廖燕的“同学诸公”对上述一段话的“眉批”是:“数语写出英雄磊落襟怀,原是柴舟自道。”这就一语道破天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穷鬼的“代言”功用。在这个荒诞剧中,人鬼神仙乃是廖燕心态流程的“物化”,分别代表着他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
最后,以戏曲形式代言可以把作者不便于说的话以隐蔽的方式说出。我们说《柴舟别集》具有明显的写心意图,但这并不等于说廖燕之所思所想全部都是率直道出的,在清代文字狱极甚的背景下,有些避嫌的话只能取较隐蔽的方式说,戏剧形式为此提供了某种方便处。比方他对造成自己怀才不遇的根源,公开的说法是“堪伤绝妙文章,却遇冬烘”(注:见《续诉琵琶·悟真》(降黄龙)曲。),把它推到不识才学的考官身上;而他骨子里所不满的是清朝的昏乱,这样的话在当时自然不能随便说,但又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便借酒仙的话说:“因见晋室昏乱,所用□[的]皆贪婪小人,所摈的皆正人君子,只是致政……”(注:见《续诉琵琶·悟真》酒仙的自报家门。)这里采用的是文人善用的“影射”法,以晋朝来影射清王朝。酒仙还说:“争奈诗伯到底是个文人出身,斯斯文文去向他讲,这厮那里肯听?就如宋朝那班卖国的奸臣、明季那班误国的书呆,遇到了强盗,动不动就去与他讲和就抚,这样见识,岂不误了朝廷大事?”(注:《续诉琵琶·悟真》酒仙的自报家门。)这里又是借明代事来影射清王朝。
综上所述,在文学史上确实存在一种以传统的杂剧样式为载体,以抒发自我为主旨的创作现象。由于这种创作成品更多的是为供给文人们阅读的,比较脱离普通的观众,所以具有案头之“书”的倾向。
然而,如果我们突破以纯剧本尺度衡量它们的传统思路,从创作实际出发,将其视为文学的一种特殊品种加以品评,就会发现它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优长:融诗歌艺术的抒情性、戏曲艺术的叙事性和双向代言性为一体,较为充发地发挥“写心”功能,形象而又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利于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等等。可以说,“拟话本”属于一种“边缘性”文体,尽管它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与拟话本在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同,拟剧本这一体式始终未能走向独立和成熟,虽然直至近现代文坛上还曾出现类似的创作,如鲁迅就创作过《过客》、《起死》等(注:《过客》,最初发表于1925年2月9日《语丝》周刊第17期,后收集于《野草》,见《鲁迅全集》第2集188—1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起死》《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集,469—479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但终究不能蔚然成风。因此,它在戏剧史上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法与曾对推动白话小说深化进程起到极大作用的拟话本相比的;然而,它在创作实践中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其长于发挥“写心”功能的优长,应当得到正确的认识和一定程度的肯定。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应该进入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
标签: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论文; 廖燕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