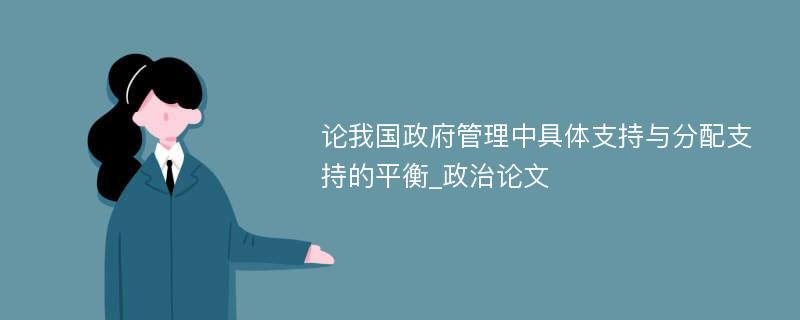
论我国政府管理中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的平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我国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政治系统理论是当代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但我们对其认识似乎仅仅止于此,真是这样的话,实在是对该理论的一种浅层次认识。笔者认为,它不仅是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学理论,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政府管理理论,其中大量有关政府管理理论与方法的经典论述,对当前我国政府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指导意义。可以说,它既是一种有关“一切政治系统是如何设法在稳定和变化的世界上持续下去”① 的一般性政治理论,也是关于使当代政府消除或减轻压力、保持持续和良性运作的理论与系列方法。这一点往往为我国学界所忽视。在当前政府管理理论还很不完善,管理方法亟须改进的我国,有必要重新认识与发掘政治系统理论关于政府管理的价值,通过对该理论的深入研究,从中吸取能为我所用的东西,提高我们的政府管理理论水平,指导我们的政府管理实践。政治系统理论所论及的政府管理理论和方法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该理论最重要代表人物戴维·伊斯顿有关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的论述,分析当前我国政府管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政府管理中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的平衡。
政治系统理论中的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
政治系统理论由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首创,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1965年)一书中,伊斯顿系统阐述了政治系统理论,因此而成为该理论的开创者和最重要代表人物。
在政治系统理论中,输入和输出是政治系统与环境发生相互关系的两个关键变量。伊斯顿认为,作为政治系统理论关键变量的输入和输出,是政治系统与其环境的互动,输入表现为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刺激或影响,输出表现为政治系统对环境刺激的反应或对环境的反作用。② 政治系统正是通过不断进入输入—输出,才得以持续。
政治系统有两个输入项:“要求”(demands)和“支持”(supports)。“要求”就是意向的表达。它具有确定的方向,无论“要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们都是直接向当局提出的。系统的成员总是尽量明确地表明其“要求”,以便获得必要的支持。但是,“要求”本身只是政治系统的原料,仅仅只有“要求”输入并不足以驱使系统运转,而“支持”则是驱使政治系统运转的动力源。③
“支持”指的是对特定政治对象的认同。“在A以B的名义从事活动,或者在A对B表示赞同的时候,我们就说A支持B。”④ 对于政治系统而言,“支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至少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没有对政府的一定“支持”,“要求”输入就不能转换成输出;其次,没有“支持”,就不可能保证管理规则和政府的某种稳定性,而“要求”输入正是通过后者才能够转换成输出的;最后,只有通过必要的“支持”,才能保证政治领导内在的一致性。⑤ 而“支持”的取向对象有三个:政治共同体(public community)、制度(regime)和当局(authorities)。⑥
作为输入项的“要求”和“支持”既是政治系统得以维持的动力,也是政治系统的压力之源。“要求”输入和“支持”输入作为最重要的压力源时都会对政治系统产生压力,政治系统若要正常运行就必须消除这些压力。如何消除压力也就成了政治系统得以持续的前提条件。伊斯顿着重论述了三种消除压力的方式,其中的两种方法即方法二与方法三就是关于散布性支持与特定支持的,它们分别是:通过支持的积累产生对系统的散布性支持和通过制造输出以激发对政治系统的特定支持。⑦ 可见,散布性支持和特定支持对系统压力的消除亦即政治系统的维持具有重要作用。
1.散布性支持(diffuse supports)
伊斯顿指出,政治系统要想持续下去,必须通过支持的积累产生对系统的散布性支持。对当局和体制的散布性支持主要来自系统成员的合法性信仰。这种合法性表现为,对系统成员来说,“承认并服从当局、尊奉制度的要求是正确的和适当的。这种情况反映了下列事实:成员以某种明确或含蓄的方式把这些对象看作是与他们自己在政治领域的道义原则和是非感并行不悖的”⑧。来自系统成员的这种支持构成了一个友好态度或善意的蓄积池,它将帮助成员承认或容忍那些反对的或认为会有损其愿望的输出。⑨ 这是系统不必为成员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支付直接利益的一种支持,成员可以从那种使他们的系统发达起来的承诺中得到满足,甚至有意制造出来的感觉中知足,以为自己是一个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该进程要求成员为了政治系统这个他们开始完全为之认同的一个实体的长远利益而约束眼前的要求。因此可以说,散布性支持是与对系统的信仰、忠诚、情感相关的,而与系统中得到的直接满足无关。正如伊斯顿所说:“尽管从理性道德的角度来看,输入的最高水平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形式,但是,散布性支持的蓄积仍可能会被一种对当局、制度或共同体的愚忠感情所增加。这种死心塌地的忠诚反映了一种依附,除了认同或服从一个高尚事业或目标的精神满足以外,人们不指望从中得到任何具体好处。”⑩ 如果说特定支持的获得主要是来自对成员要求的直接满足的话,那么,散布性支持的获得则主要是通过对成员精神上的满足,如向成员灌输爱国主义思想等意识形态的东西。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通过对成员的精神承诺而获得大量的政治好感,从而诱发了牢固的政治情感,并且不会因输出失败而轻易耗尽。因此,相对于特定支持而言,散布性支持或许更具持续力,而且无需政策输出。
2.特定支持(specific supports)
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的持续,除了通过支持的积累产生对系统的散布性支持,还必须通过制造输出(政策)以激发对政治系统的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主要来自成员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信仰有所不同,特定支持是与输出密切相关的。在某种意义上,对任何政治对象的支持从长远看取决于说服成员们相信,输出实际上是符合他们的需求的,或是使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指望输出在相当的时间内会满足其需求。即只要支持的输入可以与那种由特定的输出中所得到满足密切相关联,就是特定支持。(11) 正是通过制造政策输出而激发对政治系统的特定支持,系统的压力才可能得以消除或缓解。
例如,工会要求提高最低工资的幅度,并劝说立法机关同意其要求;农民呼吁更为灵活地制定农产品价格并以法律加以保护实施;公众要求政府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要求改善社会治安,保护私有财产等。当局或政府为此作出相应的决策,制定适当的法律规则,即通过政策输出以满足公众需求,从而赢得公众的特定支持,使政府达到减轻由于输入而造成的压力,以提高政府的合法性与公信力。这种满足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可能带来较高水平的政府好感,如果成员不断看到他们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被满足,他们对所有政府对象的忠诚自然就会增强。但特定支持也有明显的不足,因为上述反映不可能永远出现,在改变政治系统的条件下,人们至多可以指望新系统要优于旧系统。(12)
散布性支持与特定支持的区别与联系
虽然伊斯顿没有专门阐述散布性支持与特定支持的关系,但在理解了这两个概念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剖析这二者的关系。通过对这二者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来自公众的支持的两个方面,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首先,二者的功能不完全相同,合法性主要建立在散布性支持而非特定支持之上。特定支持是由于政治系统的输出(政策)给予系统成员某种具体的满足而形成,即特定的政策绩效所带来的受惠者的支持;而散布性支持则不同于特定支持的功利性,它独立于具体的政策输出,如前文所言,它是对政治系统的“善意”情感,并构成一个“支持蓄积”,从而使公众承认或者容忍那些与其利益相悖的政策输出,如为了特定的政治理想而放弃眼前利益。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的、结构的和个人的来源主要是和散布性支持相关。所以,在伊斯顿看来,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更主要是来自散布性支持而非特定支持,“如果不得不或主要依靠输出,指望用人们对特定的和可见的利益的回报来生成支持的话,那么,没有任何一个政体或共同体能够获得普遍认同,也没有任何一组当局人物可以把握权力”(13)。可见,合法性不能仅仅建立在特定支持之上,而更主要的是建立在散布性支持之上的。
上述二者功能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政治系统可以无视特定支持,而不致力于满足系统成员具体的需求。特定支持对于政治合法性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一个政府长期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难以想像这个政府会有多大的合法性。正如C.贝伊所言:“政府存在的理由基础,决定其权威施用的合法范围,以及人民服从与忠诚政府的幅度,就取决于其能否满足人民的需要。”(14)
其次,二者的支持对象有所不同。散布性支持的功能主要是形成系统成员对政治共同体和体制的合法性信仰,其支持对象更主要的是政治共同体(主要是民族国家)及其体制,也就是说,当局(主要是政府)以散布性支持获得公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信仰,即取得国家层面的合法性认同。特定支持在对象上与散布性支持有所不同,其主要是赢得公众对当局(政府)的支持或合法性认同。当局(政府)只有通过政策输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良好的政策绩效使公众直接受惠而获得支持。明白这一点对每一个政府及其管理都非常重要,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这两种不同功能的支持的独特作用,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争取公众对不同层面的支持。
再次,二者主要适用的时期有所差别,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并不完全一样。在革命时期或政局尚未稳定等非常时期,来源于意识形态或政治动员式的散布性支持或许更为有效,通过这种方式往往更能调动公众对特定当局或制度的认同与支持。但在和平建设时期,通过制造输出(政策)以激发对政府的特定支持则更为可靠,可持续性更强。因为此时的公众往往是比较理性的,他们的需求更为现实而多样化,他们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些需要的愿望转化为要求进入政府决策系统,并希望政府能够以输出的形式予以满足。
最后,散布性支持与特定支持又是有联系的,作为政治系统中支持的两个方面,它们往往表现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特定支持以政策输出的有效性为基础,而散布性支持则依靠政治社会化获得,形成一种符合特定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二者相互促进,通过其“合力”消除输入对整个政治系统的压力,使“政治系统能在稳定和变动的世界中持续下去”(15)。
我国政府管理中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的失衡及后果
在政治系统理论中,伊斯顿将散布性支持和特定支持的输入分别作为政治系统消除压力的三种方式之一,并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用二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进行论证,强调二者对消除或减轻政治系统压力同等重要的作用,通过二者的平衡达到系统的平衡,政治系统才能不断地进行输入—输出—再输入—再输出……从而使政治系统无限延续。
在我国政府管理中,理论上还没有正式使用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这两个概念,但其行为方式尤其是为了获得公众的支持的一切所作所为,无不表现在这两个方面。如主张广开言路,并在决策过程中采纳民众意见,制定符合民众需求的政策法规,从而获得公众的特定支持;通过政治承诺、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政治动员等方式赢得人民的散布性支持等。
但从现实看,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管理在理论上并没有区分来自公众的这两种不同功能的支持,从而导致在实践中不能有效地做到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的平衡,更为普遍的情况是,我国政府管理更多地依赖于来自人民的散布性支持,以获得对国家的合法性认同,而对特定支持重视不够,二者长期处于明显的失衡状态。可以说,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失衡,过于依赖公众的散布性支持而对特定支持重视不够,一直是我国政府管理的重要特征之一。如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精神文明”建设一直是占主导性地位的,以对美好的平均主义世界的终极目标承诺与不断革命的革命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政府更多的是通过对公众灌输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未来的美好以及资本主义罪恶等意识形态而获得支持,从而达到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合法性诉求。尤其是从“大跃进”至“文革”期间,我国政府主要是通过一种高度的意识形态及其教化功能,同时辅之以全国性的政治动员甚至个人崇拜获得公众支持,达到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高度控制。历史证明,这种方式在我国物质极其缺乏的时期,对树立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号召全国人民克服困难,是行之有效的。正如伊斯顿所言,在特定时期,“不断灌输合法感或许是控制有利于制度和当局的散布性支持规模的最有效的手段”(16)。但是,散布性支持是有限度的,长期依赖于散布性支持来支撑政治系统或政府的合法性并不可靠,国内外历史均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国“文革”的发生及其灾难性后果的产生,与我国政府长期过于依靠以意识形态为主要支撑的散布性支持是分不开的。事实表明,一味地依赖散布性支持而忽略特定支持,往往容易滋长政府与公众的浮夸心理、民族主义情绪及非稳定心态。如果散布性支持与特定支持长期处于失衡状态,输入给系统造成压力便不可避免。我国政府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近年来我国之所以突发性群体事件急剧上升,官民关系相当紧张(17),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散布性支持的过分依赖,不重视培育同民众利益直接相关的特定支持,有着紧密关系:重思想教育与控制,轻民众参与;政务不公开、不透明,不加强民众参政渠道建设,甚至有意堵塞民众参与渠道;决策欠透明、欠科学、欠民主,不反映民众直接需求,拍脑袋决策,置国家、民众利益于不顾,大搞政绩工程,损民利己等,这种让民众长期不能满足要求的感觉,必然导致输出失败,输入转化为压力。压力长时间未能得到缓解或消除,便会转化为冲突,从而严重威胁系统或政府的存亡。
其实,这也是我国政府行政人员尤其是行政领导在管理与思想上仍然固守传统观念、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一种典型表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至今,政府不少管理者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革命时期,在管理过程中还一味地强调革命年代大搞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式的管理理念与方法。显然,这与时代潮流不相符合。从这一点上说,进一步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在我国政府管理中仍然任重道远。
概而言之,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管理中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的失衡主要表现为重散布性支持而轻特定支持。过于依赖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的灌输而不够注重制度建设,输出(政策)不能充分反映民意、满足民众直接需求为其具体表现。其后果是导致输出(政策)失败,从而导致国家尤其是政府的认同危机,政府压力增大,民众与政府矛盾深化,甚至直接导致官民冲突。
政府管理过程中如何做到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的平衡
可见,在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管理在理论上未能区分来自公众的两种不同功能的支持,即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而在实践中却出现二者的明显失衡,过于依赖公众的散布性支持而对特定支持重视不够的情形下,正确区分这两种支持,把握二者的平衡,实在是当前我国政府管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充分利用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不同的功能并通过二者的“合力”将整个政治系统的压力降到最低。这对正处于公共危机频发期的我国而言,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做到二者的平衡至少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首先,需要厘清二者的关系和功能,并在正确处理其关系的过程中把握二者的平衡。诚如前文所言,散布性支持主要来源于由对公众的精神激励和政治动员而形成的对国家的政治好感和合法性认同,特定支持则是源自对公众需求的直接满足而产生的对政府的认同与支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由散布性支持而获得的公众对共同体(在当前我国主要是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好感与合法性认同最终需由因当局(政府)的输出(政策)而赢得的特定支持来维持。而在当前,我国公众的核心需求是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及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需要,所以,如何通过政策输出即良好的政策绩效满足公众的这些需求以赢得公众的特定支持,便成了当前我国政府管理的主要工作和任务。但是,在此过程中,也不应该忽视获得来自公众的散布性支持。因为特定支持的功利性较强,一旦政策绩效不佳,政治系统就容易丧失公众的支持,而问题恰恰在于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始终如一地保持良好的绩效,这不仅是因为政府施政难免存在失误,而且由于经济周期自身的变化也使政策绩效时有起伏。即使能保持一定的政策绩效,受益群体也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均匀,不可能使所有社会成员都满足。因此,一个政治系统必须注重培养散布性支持,以补偿在政策绩效不足时所带来的特定支持虚空问题。(18)
其次,充分利用二者的不同功能,通过发挥其“合力”作用达到二者的平衡。从前文有关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关系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二者的功能与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充分利用二者的不同功能,发挥二者的“合力”作用,对在实践中准确把握二者的平衡具有重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形成新的更加符合时代需求、更具吸引力的全民族认同的信仰价值,以发挥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作用而获得公众的散布性支持,树立与巩固国家的合法性认同。如前文所言,散布性支持的主要对象是政治共同体,这对当前我国而言,可以说主要就是国家,对国家的认同往往并不需要政策输出,其成本相对而言也要小得多,而散布性支持恰好能做到这一点。我国政府可以通过不断创新的方式,改变以前的革命型意识形态,建设发展型意识形态和更具社会终极目标和普世价值的新型意识形态,通过发挥意识形态的凝聚作用而获得公众对国家的散布性支持,从而维持公众在新时期对于国家的合法性认同。伊斯顿提出了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赢得民众的散布性支持的具体方法:“那种不直接与具体的物质报酬、满足或是强制相连接的支持,可以通过下面三种反应产生:第一,努力在成员中灌输对于整个体制及在其中任职者的一种牢固的合法感;第二,乞求共同利益的象征物;第三,培养和加强成员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程度。”(19) 当然,我们不能把散布性支持理解为对政治权威的“愚忠”或把政治社会化等同于搞愚民政策。这只是通过意识形态更新和适当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以减轻由于“要求”和“输入”给政治系统带来的压力,保持国家和政府的正常发展。近年来我国“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提出及其所强调的社会价值,是从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向执政党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步骤。这些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已经摆脱了阶级斗争与平均主义的终极理想的价值标准,在探索、形成社会新的价值目标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可以看作是执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寻求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资源的努力。(20)
二是通过大力发展经济与教育,促进社会公平等方式,创造更好的政策绩效,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以赢得公众对当局即政府的特定支持。如果说政治共同体或体制的合法性认同主要是通过输出便可获得的散布性支持的话,那么,当局即政府的合法性则主要来源于公众的特定支持,而特定支持主要以政府的政策输出即良好的政策绩效为基础,这往往是政府赢得合法性的最主要方式。正如李普塞特、林兹、戴尔蒙德等西方著名政治学者所言,合法性的最佳获得方式来源于持续的效能,这种效能是政府的实际绩效及其对公众与主要利益集团基本要求的满足程度。(21) 因此,通过大力发展经济与教育,促进社会公平等方式,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创造更好的政策绩效,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当前我国政府赢得公众支持的最根本途径。
再次,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代表代表民意、反映民情的作用,让民意能真正进入政府决策系统并能转变为相应的政策输出,从而满足公众需求,以改变以前过于依赖散步性支持的状况,加大特定支持的培育力度。一味地依赖于散布性支持而不注重特定支持,即过于依赖政治动员或精神激励,而不重视扩大人民权利,改进公众参与政治的途径,满足公众的现实要求,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长了,就相当于一种精神透支,而让公众在心理上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从而导致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而在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今,人们期望本身的增长比转变中的社会在满足这些期望方面的能力的提高要快得多。结果,在人们的期望与现实之间,需求的形成与需求的满足之间,以及期望的功能与生活水平的功能之间,形成了差距。(22) 这种差距会造成社会挫折感和不满足感。(23) 这种挫折感与不满足感很容易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近年来我国之所以各类突发性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并呈明显上升趋势,使得我国政府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疲于应付,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紧密相关。因此,在大力发展经济与教育,满足人民不断增加的经济需求的同时,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利益表达与沟通渠道,满足人民的利益表达要求,在决策过程中广开言路,加强公众参政渠道建设,做到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以进一步赢得人民的特定支持,能够改变长期以来我国过于依赖散布性支持而对特定支持重视不够的状况,从而达到二者的平衡。
最后,要求政府行政人员尤其是行政领导提高政治素质,掌握一定的政治技巧与管理艺术。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做到散布性支持与特定支持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门艺术,需要政治技巧和管理艺术。所以,政府及其行政人员除了努力做到上述要求之外,还需要加强自身政治素养和管理水平,因为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对政府的作用往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局的变动而不断变化的,对于在一定时期二者孰重孰轻的把握,需要行政领导人具有高超的政治素养与技巧;而如何通过对二者的准确把握,在现有条件下获得公众最大限度的支持,还需要领导人具备一定的管理艺术。例如,何时需对公众进行精神激励或政治社会化以及如何进行,何时应该适当采纳公众的意见,满足公众的直接要求以及如何满足、需优先满足哪些人或集团的要求等,均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技巧和管理艺术。
作为消除政治系统压力的两种重要方式的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并没有引起我国相关人员的足够重视,尤其是我国政府管理在理论上没有将二者加以区分,而在管理实践中却出现二者的明显失衡,不能充分发挥二者的作用,从而导致我国政府难以更好地赢得公众的支持。正确区分来自公众的两种不同性质与不同功能的支持,并在实践中准确把握二者的平衡,是当前我国政府管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充分利用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各自的不同功能并通过二者的“合力”将整个政治系统的压力降到最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公众的支持。在实践中要做到二者的平衡,需要厘清二者的关系和功能;需要充分利用二者的不同功能,发挥二者的“合力”作用;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代表代表民意、反映民情的作用,让民意能真正进入政府决策系统并能转变为相应的政策输出,从而满足公众需求;还需要政府行政人员尤其是行政领导提高政治素质,掌握一定的政治技巧与管理艺术,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注释:
①②③⑤⑧⑨⑩(11)(12)(13)(15)(16)(19)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0、43~44、183、335、329、330、322~323、331~332、323、20、335、333页。
④Easton,D.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Prentice Hall,1965,p.173;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⑥伊斯顿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他指出,政治共同体指的是政治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是由政治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政治系统则是由政治成员组成的;制度是政治系统第二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指政治系统运行所依据的一系列根本法则,它包括政治价值、政治规范和权威结构;作为支持的第三个基本对象的当局就是权威角色的承担者,通俗地说是当政者或政府。参见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261页。该书将英文regime翻译成“典则”,笔者认为将其译为“制度”更加符合此处regime的意思,因此本文统一将其译为“制度”。
⑦参见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579页。其方法之一是调整机构以减轻政治系统的分裂。伊斯顿认为,通过修改制度、改进利益表达机构和代议机构、改善政党机制等途径,可以有效提高整个政治系统的政治整合程度,减轻由政治分裂引起的支持性压力。
(14)Bay,C.Needs.Wan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1.No.3,1968,p.241.
(17)根据胡鞍钢的研究,在我国,目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群关系、政府和人民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严重侵蚀和削弱了党的执政基础和合法性基础。参见胡鞍钢《对挑战与危机的回应: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与危机管理》,载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编《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页。
(18)胡伟:《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
(20)萧功秦:《从转型政治学看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特点》,《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
(21)Lipset,Seymour Martin.Political Man.Expanded ed,Baltimore,MD:Johns Hopkins,[1960]1981,pp.64~70; Lipset,Seymour Martin.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Revisited.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4,Vol.59( February ),pp.1~22; Linz,Juan J.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rgimes:Crisis,Breakdown and Reeguilibrium.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78,pp.67~74; Linz,Juan J.Legitimacy of Democracy and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In Comparing Pluralist Democracies:Strains on Legitimacy,edited by M.Dogan:Westview,1988,pp.79~85; Diamond,Larry,Juan Linz,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eds.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ompating Experiences with Democracy.Boulder,CO:Lynne Rienner,1990,pp.9~16.
(22)Karl W.Deutsch.Social Mobilis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No.55,1961,p.493; James C.Davies.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No.27,1962,p.5; Chrles.Wolf.Foreign Aid:Theory and Practice in Southern Asi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296.
(23)这种差距的程度被认为是衡量政治不稳定的一个可信指数。参见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