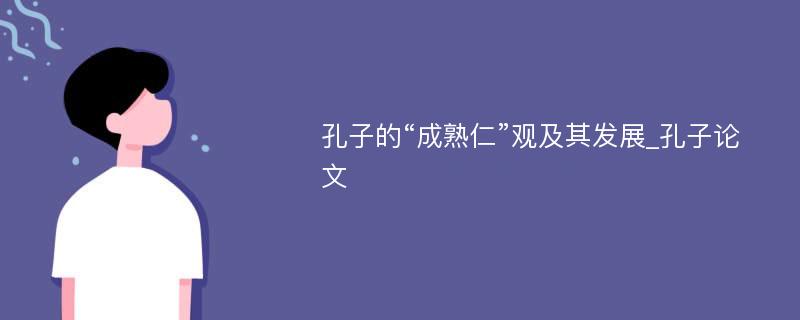
孔子“熟仁”观及其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熟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627(2006)01-0072-11
“熟”,是中国文化一个极富意蕴的概念。特别在儒家,有个一以贯之的“熟仁”观念,而其辨识渊源于孔子。观之于孔子的“熟仁”观及以后诸新儒多有的阐释和发微,其意义相彰更突显“熟仁”之实践境界——成人之道的独特理解——的优先地位,况且孔子的“熟仁”观念,奠定了后儒对于熟、对于熟仁的检讨,勾勒出一种基本向度。
一、孔子的“熟仁”观念
“熟仁”字之考义,见于《孟子·告子上》:“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清儒王夫之释其谓“荑稗,艸之似榖者,其实亦可食,然不能如五榖之美也。但五榖不熟,则反不如荑稗之熟;犹为仁而不熟,则反不如他道之有成。是以为仁必贵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种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难熟,而甘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则熟。’”(王船山《四书训义》卷三十五)在孟子看来,美、熟之间,是美在熟中,有熟则有美;光有美而无熟,则是“徒恃其种之美”而“难熟”,是不利于“求仁”的。故王夫之引尹氏“日新而不已则熟”而发挥孟子的“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训其义而谓:“孟子曰:学者入德之事,求仁而已矣”(《四书训义》卷三十五)。于此观之,孟子的“入德之事”在“求仁”,似锁定于君子之学,也谓成人之道的真实性把握。如此有一点须挑明,观乎孟子的“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至于王夫之的由美向熟的“求仁”,正是本源于孔子的熟仁之辨识。
熟仁观念源于孔子,在《论语》有三段话记得显著:《里仁》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不以其道,得之不去。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名实相符,是以仁衡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成君之道“必于是”,是在“无终食之间违仁”,表明君子必以其道的,恰以仁之熟而辨,这就是“无终食之间违仁”。如孔子期望的:“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君子善恶之别,恰以仁熟而辨。
按王夫之释孔子的志于仁而无恶:“其无恶可必矣。由是而熟焉,则纯乎善而不见天下之有恶”(《四书训义》卷八),于此王夫之训得其理中之熟仁义:“夫子曰: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者,仁而已矣。仁者,此心之存焉者也。顾其或存或去之几,必审之于早;而一存不复去之效,必待之于熟。审之早者,为取为舍之分也;待之熟者,为存为养之功也。取舍之分,因于欲恶之情,则求仁之大辨,于此有定力焉。”(《四书训义》卷八)
“求仁之大辨”,此番“定力”锁定的是“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是谓君子,无论处于何种“急遽苟且之时”,还是“倾覆流离之际”,盖君子总是不丢失仁于须臾片刻,哪怕在富贵与贫贱之间的取舍。这就是一种“定力”,“用力”也无非于此在“无终食之间违仁”上,因而得到的是:此番“用力者勉之于一日,而后相因以渐至于熟”。“渐至于熟”,也构成衡量君子存养功夫的内涵:“君子之必如是也,然后存之养之,密而无间,以熟其仁,则性焉安焉于天理之中,欲恶之几,必无妄动,取舍之辨,不得迟回,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乃于斯焉成矣。故学者勿轻言存养也”(《四书训义》卷八)。“勿轻言存养”,关键在尽早发现“熟其仁”中的“几”因素,识得“欲恶之几”,恰是君子成善的内在“存养”,而此“几”恰为心之存仁而涵养之熟,展开来看,就是“存之养之,密而无间,以熟其仁”的功夫,对于这番熟仁之存养,如王夫之识得辨清:“君子始终于仁之全功,其可忽诸?”(《四书训义》卷八)意思是说,识得“以熟其仁”之“几”,是绝对不可忽视而遗忘,尤其对成君之道而言,更是如此。清儒王船山的此番发微,是深得孔子“里仁”之精蕴的。
熟,精熟;熟仁,有精到之功。宋儒朱熹释得微义妥切。所引《里仁》那段话,朱子以为它可作两段看,“‘富与贵,贫与贱’,方是就至粗处说。后面‘无终食之间违仁’与‘造次,颠沛于是’,方说得来细密。然先不立得这个粗底根脚,则后面许多细密工夫更无安顿处。”(《朱子语类》卷二十六)这就是说,熟仁进行,须有个先后安排,立前段为粗,打根基;立后段为细,精到工夫,“须是先说个粗,后面方到细处。若不是就粗处用工,便要恁地细亮,也不得。须知节节有工夫,剥了一重又一重,去了一节又一节。”(《朱子语类》卷二十六)这是一种渐渐而习熟的工夫。似乎朱子看出“无终食之间违仁”中的“间”字深义,熟仁,须从“间”字上看,这“间”字真意就在显示渐渐而习的熟仁功夫。朱子评论“夔孙录此下云:然必先‘无终食违仁’,然后‘造次、颠沛必于是’。”又,“如孟子言‘善、利之间’,须从‘间’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决,孔子之言详缓,学者须就这上著力。”(《朱子语类》卷二十六)何谓这“间”字上“著力”?朱子点明:“既把得定,然后存养之功自此渐渐加密。”(《朱子语类》卷二十六)于此朱子道出的是,于“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中的“著力”功夫,即是一种熟仁的“细密工夫”、“存养之功”,它是始终于己,时刻不息的。宋儒朱熹的此番发微,尤是对这“间”字上的“著力”发挥,注入了一层熟仁之于“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的特定理解。
然试问孔子这般“熟仁”功夫又何以能显现、何以会实现其仁?由王船山、朱熹挑明的熟仁之功夫(“定力”、“用力”、“细密”、“存养”),可以在孔子那里得到某种渊源性解答。《论语》中的另一段话似乎勾勒出一种积极导向。
《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这段话虽为孔子弟子子夏所言,但也体现其教师的熟仁思想,可以看出,这段话是对“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的发掘。据子夏所言,始终的“仁在其中”,是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的习熟结合。譬如,一种“好学”的习熟工夫,内在贯穿在熟仁之中,“好学者日新而不失”,这是对“仁”的“日新而不失”,子夏做过一种说明:“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论语·子张》)王夫之释其谓:“其能月无忘也,非便习之已熟也,乃必能之志不懈于经月,不自谓已能而见无余味也。非好学而如是乎?”(《四书训义》卷二十五)熟仁而好学,恰是一种习仁而至熟的实践。这点亦如朱熹所挑明的相致。朱子学生杨至之问朱子:“明道谓:‘学者须当思而得之,了此便是彻上彻下底道理’。莫便是先生所谓‘从事于此,则心不外驰,而所存自熟’之意?”于此朱子答道:“然。于是四者(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中见得个仁底道理,便是彻上彻下底道理也。”(《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在这里,朱熹道出的“熟”观精义,即深入于这学、志、问、思之中的,应“见得个仁底道理”,使心中“所存自熟”,所熟在见于仁、习于仁、彻头彻尾,自始至终。
那么,在孔子那里,这“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中何以能“见得个仁底道理”呢?此番见习仁而熟,也取向于孔子另一段名言。
《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有感其“熟仁”有道,他自己从十五岁至七十余岁,历经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的熟仁之习,至于七十余岁,才有“不逾矩”之熟来,这里借朱熹的解释可看得此理:“三十而立之时,便是个铺模定了,不惑时便是见得理明也。知天命时,又知得理之所自出。耳顺时,见得理熟。从心所欲不逾矩时,又是烂熟也。”(《朱子语类》卷二十三)基于孔子这段话的本义到朱子的释义可看到,孔子的“志于学”、“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不逾矩”,其内核是贯于“仁”的,其整个进程就是习仁之熟的渐化。亦如王船山对孔子“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熟义时刻意挑明:“至于六十……因反而循之,熟而尝之,至于七十,则理之在万物者,吾可以任吾心而任之矣。”(《四书训义》卷八)这是心之而熟,这是有志于仁的贯乎通一,始志于学,故有成熟品性的锻炼,于此王船山挑明“志于学”所具备的仁之习于始终的成仁成性的熟仁过程化:“十五之所志,早有一从心之矩在吾规量之中,此吾之始之也,有若是者。三十以后之所进,不舍所志之学,而不敢期从心之获,以渐成之,吾之中之也,有若是者。七十之从心不逾,尽协乎吾志之所求,博通于所学之大,知与行自信诸心,天与物不在乎外,吾之终有若是者。则诚(仁)哉,性之不可恃,而学乃以尽其性也。吾之学如是,凡与我共学者,其亦尚如是乎!”(《四书训义》卷八)尽性成熟,有个“志于学”于其中,而自三十至七十,始终不失足于“志于学”,因为在“志于学”中,已内在积淀对于仁的往后追求的向度,更进一步看,成性成仁而成熟,是蕴涵在“志于学”的,或者反过来说,“志于学”,应具备往后发展的熟仁一切。
二、熟仁之实践境界
透过“熟仁”,首先看到孔子对“仁”的理解是有独到见识的。而这一见识的真底蕴是聚焦于一种实践之中的境界辨识。
综观《论语》,有十余次论及“仁”。但有一事须提出,《子罕》记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段话要准确理解。朱熹释得颇妥切:“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朱子语类》卷三十六)在朱子看来,孔子不是不言利、言命、言仁,而是言之有方术。以“言仁”来说,朱子以为,“罕言仁者,恐人轻易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朱子语类》卷三十六)于此观之,孔子看待“仁”,有“仁在学者力行”的一番实践之中的“熟仁”过程。也就是说,孔子把握“仁”,更注重习仁的实践意蕴,即如朱子所言的,“仁在学者力行”(《朱子语类》卷三十六)。看一下孔子有关“习仁”的实践辨识:
《雍也》:“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述而》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泰伯》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颜渊》云:“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其言也讱也。”
《宪问》云:“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应该看到,孔子对“仁”的原则设定,赋予其强烈的主体性行为取舍。行为是仁在其中的,这叫“依于仁”。此实践境界有三层意蕴:
其一,仁不在远处,就在人的身边。孔子感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人而不仁”,犹如身体有病,行为有乱。其二,仁在其中,可谓是“为仁由己”的。孔子引古诗“唐棣”强调仁在由己(本身)的努力而不在外面:“‘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哉?’”(《论语·子罕》)唐棣,一种植物;“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含有“捉摸不定”的意思。孔子借唐棣之喻,想要表达的是,真的想到仁,仁会遥远吗?此段文义似与孔子“仁,远乎哉?”有相同旨趣。杨伯峻先生对“唐棣之华,偏其反而”的释义于此颇有相通。杨释谓:“‘夫何远之有’可能是‘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意思。或者当时有人引此诗(这是‘逸诗’,不在今《诗经》中),意在证明道(即仁——引者注)之远而不可捉摸,孔子则说,你不曾努力罢了,其实是一呼即至的。”(杨伯峻《论语译注》)“仁”是一呼即来的,只看他本身是否努力所至。孔子赞扬管仲“如其仁”的实践努力,似乎也在指证这样一种观点,即“仁至”在实际生活中是可以做得到的,习仁不在于能说会道、能言善辩,而在于力行;圣人事事有仁至而来,全是按“仁之方”来左右自身言行,而且是时时刻刻,须臾不离身的。其三,实践仁道的体用。何谓“仁之方”?在孔子看来,实践仁道的方法,首先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使别人也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使别人也事事行得通。再者,能设身处地的一步步行仁术,那就是实践仁道的最好方法了。据朱熹、王船山释义,孔子“仁之方”中所含熟仁蕴意有体用发微,即熟仁是体用一致。按王船山训义:“知仁之体,识仁之用,无终食之间可违也。”(《四书训义》卷十)熟仁取“无终食之间可违”,就在“仁之为体固然也”,以仁之为“体”,则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用(《论语·雍也》)。按朱熹释义,一者谓仁之本体,“圣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指仁之本体。盖己欲立,则思处置他人也立;己欲达,则思处置他人也达。放开眼目,推广心胸,此是甚气象!如此,安得不谓仁之本体!”(《朱子语类》卷三十三)二者谓有此仁之体则有此仁之用。所谓“强恕而行”,“能近取譬”,则是“仁之方”,而此“方”恰是仁之体用,可见于熟。朱子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也;能近取譬,恕也。”(《朱子语类》卷三十三)在朱子看来,仁有等分,有圣人之仁,有贤人之仁,贤是“仁如酒好”,圣是“仁如酒熟”(《朱子语类》卷三十三),当然是圣优于贤、“熟”优于“好”。孔子赞赏管仲“仁之功”,也赞扬颜渊“三月不违仁”,然而管仲和颜渊均为贤仁而未达到圣仁,或许也是欠熟、功夫未至而就。以颜渊为例: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
朱熹评论谓,“仁是全体,如‘日月至焉’乃是偏。”(《朱子语类》卷三十三)有人向朱子提问:“三月不违仁,三月后亦有违否?”朱子答谓:“毕竟久亦有间断……过便是违仁。非礼勿视听言动四句,照管不到便是过。”(《朱子语类》卷三十三)在朱子看来,习仁是一以贯之的,是处处以礼衡之,至少是孔子对礼达于仁的一种表述或洞见。孔子指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只有“如‘克己复礼’,致谨于视听言动之间,久久自当纯熟,充达向上去。”(《朱子语类》卷四十一)这才是圣者所熟,颜回(渊)不及至孔子,也只在这“间”字上,“圣人之心,直是表里精粗,无不昭彻,方其有所思,都是这里流出,所谓德盛仁熟,‘从心所欲,不逾矩’。”(《朱子语类》卷四十一)亦如伊川曰:“此颜子于圣人未达一间者也。若圣人则浑然无间断矣。”(《朱子语类》卷四十一)“浑然无间断”,其中深藏着一个功夫力度是否足。《里仁》记道仁在实践中的用力,看到仁的熟在由身于己:“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也’。”于此朱熹看得透,“孔子言仁处,皆是用力处”,须戒“力不足者,中道而废”,这是“成德之事”,即安仁于好仁,也是利仁,功夫方到于此,便有那“利仁之熟”,即“到这里是熟”,才见得“用力足处”(《朱子语类》卷二十六)。王船山依难、易之见识得此理:“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奋然用力于仁,则我又未见其力有不足者。盖为仁在己,欲之则是,而志之所至,气必至焉。故仁虽难能,而至之亦易也。”(《四书训义》卷八)这一说法似乎也证得《雍也》中指谓的“仁者先难而后获”的实践境界。说到颜渊“未达一间者”,其中意境无非指向圣境,成为圣人,如曾国藩探孔子“熟仁”观所挑明:“即颜渊未达一间,亦只是欠熟耳”(《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13页)。相较孔子和颜渊,孔子有“无终食之间违仁”之圣境、之熟仁,故成为圣人,而颜渊“未达一间”,亦只是欠熟于“研几”,故曾国藩十分同意朱子学者倭仁(艮峰)所言:“‘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至熟)也。”(《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13页)无疑,研几至熟,似乎又归之于孔子十五有志、学志问思的习熟之中了。
值得提及,深入地看,仁之习熟,内蕴一个德性积淀。熟仁于学,学在践履务本(“仁之本”)的德性蕴生。其中看出孔子对于“仁之本”的一种独特见识。《论语·学而》记载孔子弟子有子说了一段“仁之本”,也足以照观出孔子熟仁于学的独特语境:“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仁之本”的要求,是“孝”德的承传。关于“君子务本”,朱熹肯定,“凡事专用力于根本。”至于“孝弟为仁之本”,朱子断言:“这个仁,是爱底意思。行爱自孝弟始。”“亲亲、仁民、爱物,三者是为仁之事。”“孝弟固具于仁,以其先发,故是行仁之本”。仁之本,是万事万物的发源处,习仁寻个根始个发,于此,朱子又喻“仁”为树根:“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叶繁茂”,“但有本根,则枝叶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叶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所谓“培植本根”,便是一番“为仁之本”的“生意”努力(《朱子语类·学而篇》)。对于《学而》这段话的释义,按王船山有与朱子同发感慨:“为仁”为行仁,认为“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人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学者务此”,王船山悟出熟仁之底蕴、之底据。孔子说“学而时习之”,是“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这是“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而不已”的熟仁之本根要求(《四书训义》卷五)。
王船山讲的“学之正”,是符合孔子“学”观的。《雍也》记载孔子的语录:“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意思是说:君子学欲其博,实欲其要,动必以礼,而守规矩,是以不背离(“畔”)道的。这是熟仁于学的根据之一。习仁而熟,原委于“合于道”,这是孔子对“博学于文”的别样看待,犹如王船山释此段文字而言明:“夫子曰:君子之为学,以求合于道也。……文皆载道之文……礼皆修道之事,于其切于身者,尤体道之实也”,联系仁之实践境界的“仁不远乎哉”,王船山阐发“道”也有如此境地:“月尽其身心之力,依乎道之所著,而道岂远乎哉!”(《四书训义》卷十)熟仁,是有“道”之底据的。
三、熟仁之《诗经》照观
孔子的熟仁于学中,对于“学”的熟之辨识,其中有个《诗经》照观,颇有意蕴。《论语·泰伯》有言: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于此,王船山释得其中“熟”观:“兴于《诗》”,是“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立于礼”,是“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成于乐”,是“故学者之终,所以至於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四书训义》卷十二)这里讲的“之初”、“之中”、“之终”与孔子讲的十五有志于学而至七十而不逾矩,有相同旨趣。如王船山以《诗经》辨其熟仁之功夫:“始以兴,继以立,终以成……即以至善端其始教,极至于圣功将熟之候,而《雅》《颂》之所,威仪之则,尤穷理尽性之所不离。”(《四书训义》卷十二)
《雅》《颂》系《诗经》中的篇章目。孔子十分注重《诗经》对于熟仁精义的锻炼的特殊意义。在《论语》多有记载孔子对《诗经》的倾注:
《学而》云:“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也。’”
《为政》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八佾》云:“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关睢》为《诗经·周南》一篇)
《述而》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泰伯》云:“子曰:‘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罕》云:“子曰:‘吾自卫反于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子路》云:“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哉?’”
《阳货》云:“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邵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周南》、《邵南》为《诗经·国风》篇目。)
所列并不是为了某种凑合,而是蕴含一种熟仁观念的。《尔雅》释“如切如磋”为“道学也”,释“如琢如磨”为“自修也”。似乎其中《诗经》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内蕴一种义精仁熟的主体性倡导。关于这段文字出自《诗经·卫风·淇澳》:“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个文雅有德性的君子,好像牛骨象牙经过了切磋,好像美玉宝石经过了琢磨。)王船山挖掘其中的“熟”义并比附于孔子的熟仁观:“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四书训义》卷五)有如此熟境,所以孔子对子贡说,“方可以与你讨论《诗经》了”。此番《淇澳》中的为学之理,也是被孔子看好的所谓“义精仁熟”,由王船山道个明白:“《诗》云‘如切如磋’,言乎学道之精也;‘如琢如磨’,言乎去私之密也。必其如是既切而复磋,择理之精也;既琢而复磨,治欲之密也;则纯乎理之存于中……而无非道乎?则无谄无骄者,以其自守之志操而从事于学修,以期进乎中和之德,其《诗》之所以言君子自治之功之谓与?”(《四书训义》卷五)王船山以为,孔子以《淇澳》尽熟之蕴,乃有个“涵泳”和“通”,这是“合于道”的熟仁之中,它不以贫富而左右。王船山继续释义:“切磋琢磨之功,非为贫富言也,而涵泳有得焉,则夫人之学必于此,天下之道尽于此矣。推而广之,于处贫富而尽其道,引而伸之于学修而知其通,以此言《诗》,三百篇皆身心之要矣。”(《四书训义》卷五)
学而有思。孔子熟仁于学,离不开一个“思”字,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于此也从《诗经》学得。在孔子看来,《诗经》三百五篇,可以归纳为三个字:“思无邪”。朱熹释“思无邪”谓“此《诗》之立教如此,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朱子语类·为政篇》)关于“思无邪”之中蕴生的“熟仁”之精义,朱子看得清:“圣人须是从《诗》三百逐一篇理会了,然后理会‘思无邪’,此所谓下学而上达也。今人止务上达,自要免得下学。如说道‘洒埽应对进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洒埽应对进退’之事。到得洒埽,则不安于洒埽;进退,则不安于进退;应对,则不安于应对。那里面曲折去处,都鹘突无理会了。这个须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贯通。到这里方是一贯。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习而但求察。”(《朱子语类·为政篇》)朱子看出“今人”有缺乏习仁之熟的坚韧和彻底,对大事小事、进退应对均无理会,是缺乏把握其中所潜藏的天道生意,即有个仁在贯穿,只有“须是去做”,到得熟了,便自然贯通其中的天道生意,这似乎是点明在习而至熟。《诗经》三百首,恰在教人思仁而贯穿在习仁的贯通,《诗经》教得常人应如是对待自己的心身言行。
孔子要求其弟子们好好学《诗经》,也正是领悟到《诗经》具有的特殊习仁之境。孔子感慨:弟子们何不学《诗》?因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这就是“可以用”王船山极力阐发其熟仁境界:“学之识之,而物且不能辨也,则何莫学夫《诗》乎?……《诗》之泳游以体情,可以兴矣;褒刺以立义,可以观矣;出其情以相示,可以群矣”(《四书训义》卷二十一),于此,孔子谈出他自己对于《诗》的至用性感悟,并希望其弟子们要注重其识辨:“吾学焉,而知《诗》之用广也;小子(弟子)学焉,当亦知其用之广矣。”(《四书训义》卷二十一)
至于《诗经》中何以见得有熟仁之广用,古人看得如是,清人唐甄《潜书》似有此番一席感悟:
《五经篇》:“于《诗》观美恶。”
《得师篇》:“由学致也。成王嗣位于冲年,周公无日不以君臣父子长幼之道训于王,其戒惩之言,具于《诗》、《书》,成王闻之熟矣。”
《食难篇》:“学《诗》《书》,明《春秋》,而身合乎古人之义,人皆称为君子,可谓贤矣。”
《善施篇》:“《诗》云:‘心之忧矣,之子无服’,交友之道也。”
《良功篇》:“《诗》曰:‘绥万邦,屡丰年’,是能尽性也。”
《有为篇》:“《诗》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言有待也,君子爱身之谓也。”
《潜书》此番《诗经》之感悟,着墨于君子之道,引《诗经》发微其习仁大义,是十分形象且具体,仁总是化在具体行动之中,成性于其中,于《诗》中别生一番熟仁之境界:“于《诗》观美恶”,“戒惩之言,具于《诗》、《书》”,“学《诗》、《书》,明《春秋》,而身合乎古人之义”;习仁言行,从《诗经》中可知得有仁熟之境,于此联系孔子从十五有余至七十的“不逾矩”,《诗经》似有内容上的实质性蕴含,看《潜书》的继续发微:
《知行篇》:“凡求道者,患在道之无从;既知所从矣,患在身之不至。《诗》曰:‘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溯而上之而道阻焉,不知所在也;溯而下之而宛在矣,知所在而未能即也。夫不惮身劳而上下往反,其求道可谓勤矣。”
《思愤篇》:“求道不与器界同,用力不与手足同。求道在我,绵力在心,弱则斯弱矣,强则斯强矣。《诗》云:‘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岂敢惮行,畏不能趋。’周道坦坦,夫何所畏;吾志必往,谁能沮之。”
《用贤篇》:“《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朊,或哲,或谋,或肃,或艾。’此五者,人之恒德。”
《敬修篇》:“《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非徒慎也,将以求涉济也。吾闻之:习心太约者,不可以致远。”
所引这几段《诗经》,《潜书》于此突显的主旨是学问思辨的精神性规则,求道在我,用力于勤;吾志必往,人之恒德;如临深渊和薄冰,习心慎思而致远。这是求道习仁,这是习心求熟的正直。义精仁熟亦于其中的锻炼。《诗经》中虽未有“义精仁熟”四字出现,可蕴生于其中的义理经过相关的阐释有某种熟义发微,如《潜书·去名篇》有圈点:“与终身勤修老而不遇者,具劳逸得失何如哉!《诗》云:‘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不耕得谷,不猎得兽,好名者之捷得如是。此后生之所奔走,正直之人或不免改行者也。”这里,《潜书》引《诗经·魏风·伐檀》四句,象征其中的意思是,“终身勤修”是得名至要,得仁也离不开此理;不播种不收获(“不稼不穑”),怎么能得到谷粮呢?又怎么称得上是“正直之人”所为呢?于此《诗经》也倡个“恒德”于其中。不仅如此,《诗经》对“思”的规定,给予一种熟仁的忧患和保持,《小旻》说“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如履薄冰”,其中始终蕴含个慎思和忧患的意识,而且在保持熟仁的行动中,这种慎思和忧患,无疑成为其中的应有氛围。
值得指出,汉人韩婴的《韩诗外传》,似乎对《诗经》中的“熟仁”观念基于孔子儒学的精神实质作了一种特殊的发微。
《韩诗外传》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熟仁在内的“治心”而不外求。《韩诗外传·卷一》说:“德义畅乎中,而无外求也。信者,贤者之不以天下为名利者也!《诗》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藏。’”《韩诗外传·卷二》说:“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恶,适情性,而治道毕矣……四者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诸己而存矣。夫人者说人者也。形而为仁义,幼而为法则。《诗》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求仁习仁,《韩诗外传》似乎找到由心向外的扩张力,认为在《诗经》甚有此义的渊源。《韩诗外传》发挥孔子的“学”观,并结合《诗经》点评道:“孔子曰:君子有三忧:弗知,可无忧与?知而不学,可无忧与?学而不行,可无忧与?《诗》曰:‘未见君子,忧心惙惙。’”(韩婴《韩诗外传》卷一)成君之道,有心之习仁而求熟,尚存学、行、知的结合,这是君子的品性;有学知行为一,是“不去仁”,而它在“素行”,《韩诗外传·卷一》继续理喻,“就仁去不仁”是存乎心身的“素行”,有“谓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亲之。故独居而乐,德充而形。《诗》曰:‘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其处”、“其久”在不去仁,心身(“素行”)于仁有熟,故能“独居而乐”、“德充而形”。同样,仁分层次,有“圣仁”、“智仁”、“德仁”、“磏仁”,而“四仁”均有熟境各辨,习此四仁各有其价值。《韩诗外传·卷一》有辨:“仁道有四,磏为下。有圣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磏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时;下知地,能用其财;中知人,能安乐之:是圣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时;下知地,能用其财;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宽而容众,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时:是德仁者也。廉洁直方;疾乱不治,恶邪不匡;虽居乡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汤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赏;疾乱世而轻死,弗顾弟兄;以法度之,比于不详(祥):是磏仁者也……《诗》云:‘亦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磏仁虽下,然圣人不废者,匡民隐括,有在是中者也。”按屈守元笺疏:“唐本眉批云:‘磏与廉同。’周(霁原)云:‘磏,古廉字。’赵(亿孙)云:‘磏盖苦节过中,以自厉为仁者。’”(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第85页)此段引《诗经·邶国·邶门》一篇,韩婴借喻发微:仁有圣、智、德、磏四种等级,但不管怎样,贯于其中的仁却是“素行”的品格,即便磏仁为下,圣人也不废;熟仁是“素行”的品格,是“切瑳而不舍”。《韩诗外传·卷二》指出:“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切瑳而不舍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熟仁精义,是一种锲而不舍的努力;有圣仁有智仁有德仁有磏仁,盖也属“切磋而不舍”。于此归结到的仍是知行又学治的统一,《韩诗外传》感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犹之贫也。”此乃也视其为君子修身立命之道:“夫士欲立身行道,无顾难易,然后能行之。欲行义白名,无顾利害,然后能行之。”《诗》曰:“‘彼已之子,硕大且笃。’非良笃修身行之君子,其熟能与之哉!”(《韩诗外传》卷二)这里仍以《诗经》肯定“硕大且笃”,表达出老实勤恳地修身习仁义,才是最大的行道有余。于此韩婴读《诗》,叹喟个“熟”观于其中。
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不究。不足故自坏而勉;不穷故尽师而熟。由此观之,则教学相长也。子夏问《诗》,学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贤乎英傑,而圣德备。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诗》曰:“日就月将。”(《韩诗外传》卷二)
这里韩婴借孔子言《诗》而发微其义来转述“熟”的感悟。学道而师道,重任而在肩:“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故太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尊师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师之谓也。《诗》曰:‘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韩诗外传》卷二)这里《韩诗外传》从师道而熟观的透视熟仁于学道之中:是以熟仁,务为学道,也为君子之德。《韩诗外传》引孟子“仁,人心也”提出“故学问之道无他”,只在习仁于人心,如《诗经·小雅·隰桑》的“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称其谓“求其放心而已”,并说明“习(仁)使然也。夫习之于人,微而著,深而固,是畅于筋骨,贞于胶漆,是以君子务为学也。《诗》曰:‘既见君子,德音孔胶。’”(《韩诗外传》卷四)习仁于心,日夜继之,不以忘之,如《诗》言“日就月将”,则有习仁于学道之中,这就是一种熟仁的践履。
《诗经》中的照观,还有一点须指明,即《诗经》中的熟仁精义观念,朱熹看得有一,即在熟读《诗》中有“玩味”,并在“玩味”的情绪中识得《诗经》中的熟仁之蕴义。朱子在《朱子语类·论读诗》一节里说得多是:
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元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
再三熟看(《诗》),亦须辨得出来。
须先去了《小序》,只将本文熟读玩味。
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者,意思自足。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此是读《诗》之要法。看来书只是要读,读得熟时,道理自见,切忌先自布置立说。
“读得熟时,道理自见”,意味的是《诗经》读到熟时,方是见得其中之理,这是熟中自有道理见得。朱子在回答“诵《诗》,每篇诵得几遍?”的问题时评价:“只觉得熟便止”,须是熟读了,文义都晓得了,涵泳读取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怪。见公每日说得来干燥,元来不曾熟读。若读到精熟时,意思自说不得。如人下种子,既下得种了,须是讨水去灌溉他,讨粪去培拥他,与他耘锄,方是下工夫养他处。今却只下得个种子了便休,都无耘治培养工夫。(《朱子语类·诗一·论读诗》)所谓“耘治培养工夫”,实是一种熟之功夫。于此,朱子道出一种读书、读《诗》之法,也在熟中探得其义。《论读诗》有言:
大凡读书,先晓得文义了,只是常常熟读。
如《孟子》,也大故分晓,也不用解他,熟读滋味自出。
读《诗》全在讽咏得熟,则六义将自分明。
这是朱子的看法,也是孔子的观点,其仁熟之侠义,透过朱子一席“玩味”辨识,亦可领略孔子熟仁观之心灵深处。或许在《诗经》的照观中比照出孔子的熟仁观及其发微的具体性和深刻性,至少在成人之道上。
标签:孔子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儒家论文; 孔子的名言论文; 国学论文; 诗经论文; 朱熹论文; 王夫之论文; 邵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