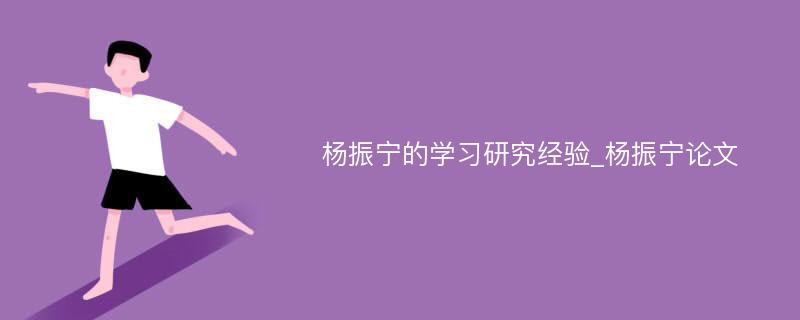
杨振宁的学习与研究经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杨振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二人成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2012年4月18日,已经90岁高龄的杨振宁先生做客中国农业大学名家论坛,讲述了自己大半生的求学与研究经历,展现了一位著名物理学家的风采。他在演讲后走下讲台,弯腰倾听年青学子提问的瞬间更感动了现场观众。
本刊刊登本次演讲实录,限于篇幅,有删节。
《神秘的宇宙》开启对物理的兴趣
我1929年到清华大学,当时7岁,就读清华大学里的成志小学(编者注:清华附小的前身),我父亲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
4年后进入北京城里的崇德中学,现在叫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在宣武门附近。学校很小,差不多300个学生,有一个小图书馆,我喜欢到里面浏览书籍。初中二年级,我在图书馆发现一本翻译过来的书,叫《神秘的宇宙》,描述1905年物理学大革命、1915年相对论和1925年量子力学,这不只是20世纪物理学的大革命,也可说是人类知识历史上非常重大的革命。我当时并不太懂其中的内容,不过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与我后来学习物理有密切关系。
1937年夏天我刚刚读完高一,抗战就开始,我们全家搬回合肥老家。后来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我父亲到昆明就职,1938年春天,我们就到了昆明。当时中学生流离失所的很多,教育部就规定不需要有中学毕业文凭也可以参加高考,我当时高二,算“便宜”一年,参加高考就进入了西南联大。
高考考试科目中有物理学,我高中并没有学习物理学,就借了一本标准教科书,关门念了一个月,原来我非常喜欢物理,觉得更合我的口味,所以就进入西南联大读物理学,而我起初报考的是化学。
与同学讨论是深入学习的极好机会
1942年我取得学士学位后,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读硕士。我在研究院的同班同学有黄昆(编者注: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和张守廉(编者注:著名电机工程专家)。我在黄昆70岁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描述当时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物理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所争论的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从喝茶开始辩论,到晚上回到学校,关灯上床,辩论仍没有停止。现在已经记不清争论的确切细节,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蜡烛,翻看海森堡的《量子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辩论。
根据我读书和教书得到的经验,与同学讨论是深入学习的极好机会。多半同学都认为,从讨论得到的比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还要多,因为与同学辩论可以不断追问,深度不一样。
芝加哥大学感受中西教学方法差异
1944年我研究生毕业,教了一年中学。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经印度到美国纽约。到纽约后我请求进入芝加哥大学。
在物理学习方法上,芝加哥大学与国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国内是推演法,在书上学到一个理论,按定律推演到现象。芝加哥大学正好相反,不是从理论而是从新的现象开始,老师和同学脑子里整天想的就是这些新现象,能不能归纳成一些理论。如果归纳出来的理论与既有理论吻合,那很好,就写一篇文章;如果与既有理论不符合,那更好,因为那就代表既有理论可能不对,需要修改。
整个气氛与国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中国使用推演法,打下一个非常扎实的根基;到美国,学会多注意新现象,由新现象归纳出理论。
中国教育哲学讲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就是说你得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与不知道的东西分清楚,不能够乱七八糟。有些东西你是知道的,有些东西你不知道,都要想得清清楚楚,这个才是真正的学习。这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很重要,有很大好处。
可是这种教育哲学也有很大坏处,事实上有许多知识不是这样学来的,比如一个小孩学讲话,并不是按部就班,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学会,他在一个不太清楚的时候,就弄出来。关于这一点,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叫渗透性学法,渗透性学法是中国传统不喜欢的。
事实上,很多东西第一次听不懂,第二次再听,还是不懂,可是就比第一次多懂了一点,等听到很多次以后,就忽然一下子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与西方教育哲学一个很大区别。我上学时就觉得西方学生没有把东西想清楚的习惯,可这并不阻止他们做出非常重要的工作,尤其是非常聪明的年轻人,用渗透方法吸取知识的能力很强。
永远不要把所谓不言自明的定律视为必然
1948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留校教书。1949年就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的研究所不大,没有学生,大概有20个教授,四五个研究领域,一二百个博士后和访问学者,是一个纯研究性的象牙之塔,非常成功。
我到研究所的时候,那里大师云集。爱因斯坦刚刚退休,我们年轻人没有人去骚扰,都很尊敬他。有一天我带着大儿子在路上看见他,就照了一张照片,我自己从来没有与爱因斯坦合过照。
1956年夏天我和李政道合作,检查宇称是不是真正守恒,做了3个星期的多种计算后,我们很惊讶地发现,所有过去的β衰变试验中并没有任何宇称绝对守恒的根据。好几百个β衰变试验一致认为证明了宇称守恒,但这些结论都是不对的,我们从而提出怎么样做实验能够测定β衰变中宇称不守恒。这些实验比以前实验要稍微复杂一点,提出来以后学生都不肯做,第一,这些实验都不简单,他们说不值得去做;第二,没有人相信宇称是不守恒的。
只有吴健雄(编者注:美籍华裔女物理学家,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愿意去做这个实验,她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现象,既然还没有实验证明,那就应该去研究。吴健雄与其他专家合作,在华盛顿做了半年实验,得出结论在β衰变中宇称是不守恒的。结论出来以后震惊了整个物理学界。后来更多实验证明,不止是β衰变,在所有的相互作用中宇称都是不守恒的,也就是说左右不完全对称。
1997年吴健雄去世,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吴健雄的工作以精准著称于世,但是她的成功还有更重要的原因:1956年大家不肯做测试宇称守恒的实验,为什么她肯去做此困难的工作呢?因为她独具慧眼,认为宇称守恒即使不被推翻,此一基本定律也应被测试。这是她过人之处。”吴健雄自己曾说,永远不要把所谓不言自明的定律视为必然。
我讲的这些,基本上就是把我过去的学校、研究经历归纳一下,得出的结论,也许这些结论对年轻人会有些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