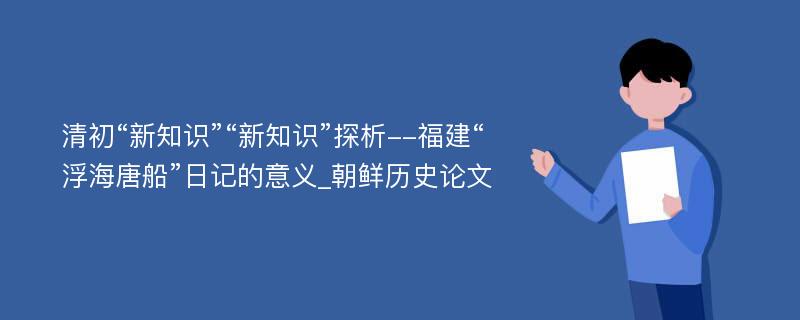
《清客新话》:日本对马藩尉探问清初“新知”——福建“漂海唐船”日记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客论文,清初论文,福建论文,日本论文,新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3)01-0064-08
明清之际,一些中国“唐船”往来于中国福建与日本长崎两地进行贸易,直接促进了中日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对其中“漂海落难唐船”文献个案进行研究,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学术效应,保存在日本的中国清初“唐船”“财副”郭育龄所编《清客新话》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清初漂海对马岛福建“唐船”与《清客新话》“问答”
日本贞享三年正月(1686),中国福建船主郭斗悬等在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附近遭遇海啸巨浪,迫不得已,就放任“唐船”顺流漂泊到对马岛港湾里,得到了对马岛止斋陶山救助。船主郭斗悬为何人?根据《清客新话》所载郭斗悬之弟郭育龄“自叙”的一段话知道:郭斗悬原籍为淮阴,属于“家世书香”门第,照理来说,也应该与郭育龄一样,是一个饱读诗书之士,但从后面的记载情况来看,郭斗悬并没有多少文化。①
对马藩主及其属臣在款待和照顾郭斗悬等之余,就清初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敏感问题向郭育龄进行了“探询”。郭育龄用汉文日记记载了这个过程。郭育龄把日记和郭斗悬等与船员来往书信合编,就称为《清客新话》。
日本学者大庭修编辑《江户时代日中关系资料〈兰园鸡肋集〉——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五》时,依据サブタイトル《兰园鸡肋集》收集而影印。大庭修说,《清客新话》应该作为日本对马藩的“每日记”资料被保存着,但因为日本对马藩的“每日记”资料只有贞享四年九月(1687)以后的资料,所以,这个“漂着事件”并没有被“每日记”文献记载,由此,这个资料显得十分珍贵。
在《清客新话》中,郭育龄交代了笔谈的人物、时间、地点。其中有:“大清福建人漂着对马藩平田茂左卫门尉笔谈,同三月二十三日归唐”字样。日本对马藩主派出家臣平田茂左卫门尉接待了郭斗悬等人。平田茂左卫门尉具有一定汉学修养,问答正文所涉范围很广。最后部分是郭斗悬等在岛上与在船上人往来短信,即“修归楫之际船岸分居来往短札”合编。“短札”涉及购买食品、器具、用药,互赠礼品、唱和诗作等事宜,内容非常丰富。
《清客新话》平田之“问”与郭育龄之“答”。原文是:
1.问:清皇帝定天下之后,其典刑税敛欤?答:清皇帝定鼎之后,省刑罚、薄税敛,凡老叟少童无不被其恩泽,可称为再生之尧舜禹矣。至于边浦寒村,既已心服,而所着者焉得又有内外之分?2.问:今世以道学明于世者,其姓名为谁?答:徐越、沈荃、冯普、张鸿烈、胡简敬、李蔚、杜立德、王义以上纂修之弘文,其余难以枚举。3.问:尝闻朝鲜通于贵国,倘夫奉万物而有朝觐之礼乎?且以为附庸之义乎?其年号制令从贵国之命乎?答:朝鲜国自明季以来,两国通舟。在明季曾闻有封,不记年代久矣!于今朝鲜不时入觐,时有土产之物进之。朝鲜人每每贸易在北京,出入不禁。4.问:清皇帝姓赵,但在夷无此姓,清帝先人乃中原之产乎?答:清皇帝原是元朝之后,在中原有年。自清皇帝入关以来,原无姓。进关之后,则从百家姓,措第一姓为姓,即姓赵。5.问:唐茶之制?答:此茶名松罗。茶产于南京徽州者佳。其茶树不逾人高。在二月则发芽,二月半后,采老为芽尖,三月则放大。采者类制之芽尖稀少,其价高,类制则次之。至制法,将叶采成,去其尖并根蒂后,以法蒸卷成,又用火炙成茶。6.问:三国魏吴挑战于合肥之地,夫合肥者属于今何地方?答:合肥,今之江浦是也。此地居于南京之对江,而北岸离江口有七八里远。江南地方乃吴地也,江北地方乃魏地也。江南水路多过江之地,陆路水路并通。7.问:一些词语的意义如何理解?比如哨探、梆子(要求图以示焉)、朝里壁、(关羽)重枣、搦战、穿(战袍)、日本饮酒量多称为“上户”,量少称为“下户”,中国与之对应的名词。答:哨探者,乃以小卒之哨其虚实也。梆子者,乃木制,乃传事之梆也。衙门用梆,传事于内外,又有巡守更夫用梆敲响,以警夜。此梆制法,用枽木者,声响。长二尺五寸,粗一尺七八寸,为圆其中,开一长逢,方能出声响耳!朝者,向也。里者内,乃向内壁之说。(关羽)重枣,乃称面赤丰满之意。搦者,索战也。(穿)即与着字同。(中国)饮少者为浅量,饮多者为巨量。
平田与郭育龄“问答”,可以分为几类内容来看:第一类,关于清康熙时代法律与赋税问题。郭育龄所说康熙时代“省刑罚、薄税敛”,是否符合实际?
一是“省刑罚”问题。章梫《康熙政要》提到,康熙初期,“法制未定”成为“时事最急者也”。根据大臣“参以古制,酌以时宜,勒成会典,颁示天下”建议②,康熙皇帝为维护国家统一,消灭分裂割据势力,恢复和发展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以及抗击外来侵略,以“禁暴止奸,安全良善”为立法准则,建立健全国家和地方行政法典,《康熙会典》就是集中体现。[1]具体“刑罚”规范,比如,清帝入关之后,最初沿用明代“旧典”不少,但对带有浓厚之满洲习俗特点的习惯刑罚法也进行了若干规范,比如革除贯穿耳鼻之刑。由此,满汉律例不断融合,渐次精密,刑制方渐趋正规,终至列入法典之内。比如1644年9月,刑部右侍郎提桥启奏:“五刑之设,所以讦奸除乱。而死刑有二,曰绞,曰斩,明律分别差等,绞斩互用。我朝法制,罪应死者俱用斩刑。臣以为自今以后,一切罹于重典者,仍分别绞斩,按律引拟。至于应笞之人,罪不至死,若以板易鞭,或伤民命,宜酌减笞数,以三鞭准一板,庶得其平。伏恳敕下臣部,传示中外,一体遵行。”朝廷准奏。康熙时代更是规范化,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刑罚简省”。但实际上,进入到了雍正乾隆时代,则越来越严苛。由此,郭育龄所说康熙时代“省刑罚”是大体符合实际的,但在表述上,以“规范而简省”则更为妥当。
二是薄税敛问题。以钱粮蠲免为内容的减免赋税,学者们认为是康熙时代盛世气象的重要表现。但何平认为,康熙帝在位的不同历史阶段,针对特定的政治经济形势所推行的钱粮蠲免政策,其着眼点和具体形式表现出差异。康熙初期,从政策条例和实践来看,为应付战争的需要,保证财力的扩大,清政权实行的是被动、严苛的蠲免政策。中期,康熙政权把宽赋和蠲免作为“育民之道”的关键环节,推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主动积极的钱粮蠲免措施。后期,在普遍蠲免基础上,清政府仍继续推行因时因地的蠲免政策。不同时期赋税蠲免政策效果为不同的因素所制约,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康乾盛世的内容之一加以理想化。[2]所以,郭育龄所说康熙初期“薄税敛”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大有粉饰康熙“盛世”之嫌。
与《清客新话》所记类似的情况,还可以在朝鲜燕行使闵鼎重《燕行日记》附录《王秀才问答》(1734刊行)中找到。[3]1669年,闵鼎重被朝鲜朝作为燕行使派往清朝正使而出使北京。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康熙八年(1669)阴历十二月十八日)和回国途中(康熙九年(1670)阴历二月初一),受到了直隶玉田县秀才王公濯的接待。闵鼎重和王公濯进行了笔谈,其闵鼎重“问”与王公濯“答”构成了《王秀才问答》的主体内容,闵鼎重以日记形式保存着。闵鼎重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和康熙有关的是第26条:
问:民间颇称朝政之善,而京里多以宫室石役游猎,国储渐竭为忧。猜疑积中,以察为明,用法太酷,人人畏诛,朝绅亦有分裂之渐云。此言信否?答:此具切时弊。然宫室之役,在旗下,不在民间,虽有田猎之苦,而廉贪屡有黜陟。独是逃人条例甚严,且弊窦百端,乃民不聊生之大者。朝绅党附从来有之,况今日乎?非妄言也。
“民间颇称朝政之善”,是闵鼎重所见所闻实情,和郭育龄所说康熙时代“薄税敛”相吻合。但对“时弊”问题不回避,因而一再追问。王公濯认为“官室石役游猎,国储渐竭”情况主要限于“八旗”,即清朝上层。而民间的情况不是这样。但还是指出了“逃人条例甚严”弊端,和郭育龄所说康熙时代“省刑罚”有些出入。郭育龄从总体上是肯定的,而王公濯则是对具体的一些“刑罚”有所否定,不过,总体评价上还是正面的。二者一致性很大,可以视为此条记载的佐证。
第二类,关于清康熙时代德艺才学而知名的人士。关于这几位人士,在文献上记载比较翔实,比如徐越、沈荃、张鸿烈、胡简敬、李蔚、杜立德。但有关冯普、王义情况,文献上记载的不多。这些知名德艺才学之士,各有其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清初德艺才学的群体形象。
第三类,清政府与朝鲜关系。平田之“问”表明,他们对当时中朝关系十分关注。郭育龄解答了“奉万物而有朝觐之礼”,谨慎地避开了敏感的“附庸之义”关系定性和“年号制令从贵国之命”问题。学者们对这一段朝鲜“朝天使、燕行使”研究成果很多,成了目前中韩日三国学术热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韩国林基中《燕行录研究》、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徐东日《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日本学者夫马进《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等。[4]所谓“附庸之义”,就是朝鲜朝国王对中国明清两朝奉行的是“事大”政策,以明朝为正宗中华文化的代表,相对于明朝,朝鲜朝就是“小中华”。而对于清朝,表面上是顺从,其实是对清朝以野蛮民族文化视之,而以朝鲜朝为正宗中华文化的中心自居。所奉年号,以明崇祯为准,而不是施行清朝皇帝年号,得到清政府默许。平田以为所奉年号是清朝皇帝年号,肯定是误解。
第四类,关于中国历史地理与茶文化。比如认定“三国魏吴挑战于合肥”的具体方位,在方法上,讲求古今对应,即立足于古今区域行政区划的变迁而确定合肥,就是今之江浦,还进一步描述具体的地理环境和交通优势。对唐茶之制中的松罗茶说明也是如此,从产地,到种植,到具体的制茶工艺,一一道来,可为当时郭育龄版的《茶经》妙典。
第五类,关于词语意义理解的,属于汉语词汇学内容范畴。具体解说方式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图示:梆子和朝里壁;二是具体词义描述和用同义词解释:哨探、搦;三是比较,抓住中日对应词的特点进行比较说明。比如:日本/中国、上户/巨量、下户/浅量、着/穿(战袍)。这当中,“着”的穿义,今天日语还保存着,即“着ゐ”。有意思的是,郭育龄是用“着”来解释的。“着”是中国十分通行的“穿”义动词。比如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二刻拍案惊奇》“说着了小服,从西门进来了”。两个“着”,都是“穿”义动词。
二、《清客新话》“短札”所透露的各类信息
《清客新话》“短札”即“修归楫之际船岸分居来往短札”部分,计30封信。只有第一封有确切的日期,即二月二,其他的没有日期,只有二月字样。但看得出来,基本上是郭斗悬等人在岸上与在船上人的往返短信。
这些“短札”所涉及的内容是:第一类,是在船上人请求在岸上的郭斗悬等人送来所需食品、日常用品等事项的。比如名字叫以中的来信:
自本船赠岸上。来字,乞发山泥两担,若得练就付来尤妙。此乃修灶致用也。立待蜡烛,再付九对来。如即雄野鸡,要买一只。黄四爷要小烛半斤,丘子云(要)大鱼四尾。
第二类,是在船上人向在岸上的郭斗悬等人汇报吴德等人生病医治情况,及征求吴德死后处理问题意见的。比如:
乞见字,拔冗即到船上来一看,以便下药,万不可迟。病人粥饭不食,寒热难遏,速速带药并三官。即来再闻,并药引、生姜、葱,船上亦无。
第三类,是在船上人向在岸上的郭斗悬等人汇报修船等事宜。
大爷,收白。见字,即可照样钉十只,钉大桅面梁用。外要鱼二尾,系顾正此。来熟土已收。承教,即遵法制度搪灶耳!此复!
第四类,是郭斗悬等回复船上人来信,称为“回”、“自岸遗船”、“呈本船”。
二月回。接来字。已知吴德之故停安,令船俱喜,所谕不可付。印上岸,自当遵命,所来之物,俱炤账为说;所取之物,亦炤账奉上。其水将有一舱;其小菜亦不必多付下来。外可买苍术三四两,醋一二斤,黄豆三五升。船上诸事,有良志炤看。不必大爷挂念。专此奉复!
应该关注《清客新话》“短札”所透露的信息。表面看来,这30封“短札”,似乎都是些“唐船”上人和岸上郭斗悬等人鸡毛蒜皮之事,没有什么可叙及的。但透过这些零散的事例,可以挖掘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其一,虽然是同一个“唐船”上的人,但船主和船员之间物品来往,是以“炤(造)账为说”的。往来账目要清楚,反映了船主和船员之间财务出纳制度的关系。在“短札”中的这种“收账”、“开账”、“林开文入账”、“物以炤账收讫”字眼时而可以见到。另外,还有所谓的一整套程序。比如有:“鹿肉尚有三腿,如要,即写字来取刻下来,物以炤账收讫。各兄在岸上,倘得暇,可将花名册并货册钉写,恐到时,未能所立就。其三位,可到时再议,或花不写亦该钉,每头序写便往回数次地,名曰期。亦免临时思索。”记载得很详细。表明了“唐船”财务制度的严密性。
其二,从30封“短札”的礼仪形式来看,“唐船”内部等级森严。在称谓上,有“郭大爷”、“黄四爷”、“育老原兄大人”、“二爷”、“王四爷”、“三爷”等,这种礼仪形式背后蕴含着严格的“唐船”内部等级制度,不可不关注。
其三,船上人向在岸上的郭斗悬等人汇报和建议,体现着“唐船”内部管理基本方式。郭斗悬是船主,称为“船头”。我们看“短札”,标明写给“大爷”的有5封,其他虽然没有标明,但大多数是写给他的。重要的事情首先要由他来决定。郭育龄作为“财副”是第二把手。看得出来,郭育龄因为有文化,也是该“唐船”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比如在“短札”称他为“育老原兄大人”;还写作“育黎”,应该是育龄的音讹;要让他给生病的船员“扶病”。有记载说,他回到船上也生病了,但后来在船上掌事。而最初,即郭斗悬受邀于岛上之时,名叫良志的管理船上的具体杂事,有“船上诸事有良志炤看”可证。名叫以中的人是船上的文化人,传达船上人的要求和信息。还有林开文(管理入账之事)、金兆威(称为教弟)、“王四爷”(托笔致谢)、金贵官、明光、潘、严二司(应该是管理修整船上之事)、丘应龙(称为教弟)、吴德(死者)、张见远(有文化)、钱大爷等,各司其职。金兆威、丘应龙对郭斗悬称为“教弟”,是不是和当时流行在福建“八闽大地”的天主教有关,也未可知。但用酒“敬神”似乎与此无关。
其四,敬神。比如:“初二日敬神,已无酒可用”;“明日致神之事,亦以领悉”;等等。所敬之神为何?这里没有清楚说明。据学者们研究,古代福建的海神信仰是多种多样的,有天妃、临水夫人、龙神、拿公、陈文龙、苏臣诸神等,都担负着“慈航普渡”的庇护任务。明清两朝很多出使琉球的福建人崇敬“海神”。齐鲲描述:“国朝册封琉球,向例请天后、拿公神像供奉头号船,请尚书神像供奉二号船。”这是说,要虔敬地迎供祀奉在船上的各种海神。等到册封之船抵达琉球后,又“涓吉鼓乐,仪从奉迎船上天妃及拿公诸海神之位供于上天妃宫内,朔、望日行香”。当册封使们完成使命回到福建后,还需“奉安天后行像,拿公于故所”,才敢各自安歇。可见,明清奉使琉球诸使节对供奉海神非常重视。[5]而前往长崎港进行贸易的这艘福建“唐船”船主和船员是否也有这种“海神”信仰呢?从这里的记载看,肯定是有的。
其五,“唐船”所遵循的“丧葬”习俗。围绕着丧事处理,也存在着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封“短札”记载了吴德“丧事”处理问题:
1.其吴德之尸,昨夜头目验过入棺,停在橹后撬头前。令通船客人要写连名呈状,求此处君上将吴德棺木在此入土,未知可能知诸客之愿否?乞否兄与?2.所来各项具已点取明白,(吴德)其棺已合,专候验过入验(殓)也。3.其棺材已完成入棺,不知可要本地头目看过否,乞示下,以便入殓。4.承谕吴德之故,昔夜入殓。即日即着人将船内收拾干净。又将炭醋苍术熏灼压之。又拨四人在仓睡卧,不必再费清思矣。棺上用绳因未来耳接教,即令顾正料理也。5.吴德之尸今已七日,口内流出血水。乞船主如何永王上速速上岸入土,再迟一二日,恐船上不堪此闻。
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是“在此入土”为何要“求此处君上”?二是为何要“本地头目”“验过入验(殓)”?三是吴德之尸入殓已七日,还不见船主将之“上岸入土”?这些问题恐怕与“唐船”所遵循的“丧葬”习俗及与对马岛的“丧葬”习俗是否吻合有关,是很值得研究的。
其六,日本对前往长崎港进行贸易的“唐船”出台一些限制措施。《呈本船》记述到:
呈本船,长崎之使船已到。其来文着即回唐,不许漫往长崎等语。适间已求过再三,难以作主。到此处,令人魂飞而魄散矣!究竟不知如何结果,先此报闻。
郭斗悬等人落难漂流到了对马岛,受到了对马藩主等热情接待。在完成休整之后,他们是打算继续回到长崎港进行贸易呢,还是打算回到自己的祖国?如果是打算回到自己的祖国,为何得到日本长崎之使船送来的“公文”而“魂飞而魄散”?清初施行“海禁”政策出于各种目的,对沿海正常的日中贸易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6]但此时清朝已经“开海禁”。这一点,郭斗悬等人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可能另有原因。看来,郭斗悬等希望回到长崎港进行贸易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的问题是,郭斗悬等人落难漂流到了对马岛,为何日本长崎方面如此之敏感?日本德川幕府在1633-1639年实施“锁国”政策,不许日本人出海,长崎成为唯一贸易通道。江户幕府为防止走私,对前来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实施种种限制措施。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出于日本和清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敏感关系的考虑吗?对马岛是历来相关各国觊觎和必争之地,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
三、研究《清客新话》“问答”及“短札”的意义
研究《清客新话》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对研究清初日本和中国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意义。明末清初,虽然政府实行“海禁”政策,但中日民间贸易往来亦是不断。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明清篇”谈到了清初中国“唐船”到长崎的贸易的数量,其中,仅在1659年为60艘、1660年45艘。[7]但1681年前后只有10艘左右,原因是1661年实施“海禁”的重要一步“迁界令”。直到1684年“开海禁”,情况才有所好转。郭斗悬等人是康熙“开海禁”政策直接受益者。《清客新话》所记“问答”及“短札”,也正是真实记录了清初日本人和中国人文化交流的历史,由此,对马藩尉的“探问”就具有了了解中国清初“新知”的意味。而郭斗悬等人所受到的热情接待和“救助”,也可以说是两国民间友好交往的真切写照,福建人郭斗悬等“落难”漂流对马岛,也就成为一个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
其二,对研究清初“唐船”管理、商品买卖情况及输往日本货物品种常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清客新话》“短札”所提供的“唐船”内部管理的方式是比较科学的,等级、财务、出纳、分配等一系列制度,井井有条,非常规范,说明,近代意义上的商船管理制度已经萌生。非常值得研究。《清客新话》“短札”涉及一些商品买卖情况也引人瞩目。
1.雄野鸡要买一只。2.大鹿后腿要买两只,豆三升。3.外可买苍术三四两、醋一二斤、黄豆三五升。4.要用鱼亦买来。5.但公司仓小菜可过三二日买。6.司二爷查收入账。所问蜡烛,乃芥子油浇成也,来烛五对并查收。其锅铲已达成价,要四钱,不敢付来。前来熟土二石,价钱一两五钱也。7.君上可否每一套(廿一史)有来?字乞。买鱼四尾,付下为感。
这主要是向对马岛方面购买商品具体价格情况,但“廿一史”似乎是赠送给“君上”,即送给对马岛藩主的。
清代福建省“唐船”输往日本货物品种,冯佐哲《从〈日本灯词〉看清初的中日文化交流》[8]引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提到:书籍、墨迹、绘画、墨、笔、纸、布、葛布、白丝、褶绸、绫子、纱绫、八丝、五丝、柳条、纱紦、罗、捻线绸、闪绸、天鹅绒、南京绡、丝线、棉布、绫条布、砂糖、甘蔗、橄榄、龙眼、荔枝、天门冬、明矾、绿矾、花纹石、鹿角菜、牛筋、天蚕、瓷器、美人蕉、线香、铸器、漆器、古董、扇子、针、栉蓖、蜡、降真香、茴香、藕粉、鱼胶、丝绵、茶、蜜饯、花生、药物、化妆品等。
在《清客新话》“问答”及“短札”载有货物食品用品名称:蜡烛(芥子油浇成)、晋茶、茶叶、木套、橘饼、针线、烟、酒、酒桶、鹿肉、豆腐(付)、雄野鸡、苍术、黄豆、生姜、葱、蓬帐、红毡包、葡萄、炭、熏灼。凉帽、锅铲。《呈本船》称:“接来字,送到,拣好一色上白丝十包,计重五百觔(斤),乞点收明白。”丘应龙说:“本船上载有廿一史,全部共四十五套,乃唐山至重之书,珍之加宝外,有料丝中围屏灯一架,并奇花大缎大红绉纱要贡。”
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密话》谈到“唐船”所载商品,丝是运往日本或曰日本进口的第一商品。所以郭斗悬福建“唐船”所载白丝十包是很珍贵的。其次是纺织品,比如缎子和纱。药材输入量较多的品种就有苍术。砂糖也是需求量很大的。书籍比重较低,主要是南京船和宁波船,而且,输入后需要经过书籍检察官审查。但郭斗悬福建“唐船”载有四十五套廿一史数量确实很大,令人惊讶。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记载1711年11月中国“卯五十一番船”运到长崎的书目,见载于宫内厅书陵部《舶载书目》第九册上,有86种,1100多册,装在40只书箱中,算是数量比较大的一次。但如果我们把《清客新话》所提及的四十五套廿一史换算成册数的话,数量就很惊人了。一部明嘉靖刻本廿一史卷数就达2879卷,40套达115160卷,远远超过1100多册的数量了。[9]印制如此多的廿一史,如果不是日本市场有巨量需求的话,运送这么多的书籍实在是不可想象。很显然,这些是用于当时日常生活必需重要物品。与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所记载福建省“唐船”输往日本物品可以相互参见。
其三,对研究清初“唐船”海洋文明与文学艺术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涉及文学,主要是郭育龄的诗作,其中最为重要的见之于郭育龄《自叙》,说道:“上命客余兄与余,于馆舍安荐陈菜田,复晤大全庵先生、眛轩平先生暨诗公览昆玉,不弃寒微,错爱而有所不至,朝夕盘桓,非更阑而不辍契。余骨肉数十年之知己,虽至岁良朋,未若是也。”由此赋诗一首:
遥瞻山岛之为带兮,其绕类弇潮水之川流兮,其去复洊苍松之盘曲兮,其形如龙台榭之层叠兮。
郭育龄是有感而发,把对马岛比喻作为玉带缠绕,大有“通感”的通灵效果。而称为“云间林薳”的《次辙藏主原韵呈眛轩平先生并祈教政》五言诗则另有一番景致:
偶挹诸名胜,禅宗忽尔逢。词源郁至理,诗旨识音容。海外风光异,天涯花柳浓。论交因坐久,不觉夕阳舂。
这是首典型的中日学人唱和之作。因其在特定的对马岛上,就具有了更为深刻的蕴意。这是“唐船”海洋文明“对接”带来的结果。
其四,对研究清初官话词汇史及对外汉语教学历史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前面“问答”涉及的词义解释内容之外,在“短札”部分最后,还可以见到郭育龄称为“前文字义”的解释词语意义内容(数字符号是笔者加的,表明次序):
1.验过,即看明。2.撬头前,乃披水。3.蓬帐,乃帆。4.云章,乃客。5.两担,担者,石也。6.一顿,乃一食。7.公司仓受用,乃公中之用。8.启者,乃牍也。9.拨冗下船,偷闲而下舟也。10.蓆垫好贮,竹席垫,船未放上。11.潘司,乃木面也。12.套言不叙,乃闲言不说之义。13.花名册,乃本船之人册也。14.货册,乃货物之册也。15.木套,乃泥套。16.号三年唐当即写明,死者吴德棺上年庚写错了,乞正。17.酸痛而抖,抖者,即颤也。
对这些词语的解释,郭育龄力图通俗化,简明易懂,比如说,抖,就是颤的意思;蓬帐,就是帆。但有的解释把本来已经通俗化的词语却用文言来解释,效果适得其反,比如:“一顿,乃一食”。还有的解释不确切,比如:“木套,乃泥套”;“蓆垫好贮,竹席垫,船未放上”。解释方法有问题,说明郭育龄的语言素养不高。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认为,郭育龄的解释还是很有意义的,面向外国人讲汉语词语意义,比较意识初步显现,这是很珍贵的。此外,《清客新话》文本所提供的各类白话语言形式,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清初官话词汇史和语法史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比如量词就十分丰富,已经具有了现代汉语量词的多种用法。
对《清客新话》“问答”及“短札”文献价值的揭示,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如果我们突破中日关系视界,把它转移到明清时代整个东亚“漂海落难”事件书写的广阔空间认识会更有所收获,比如朝鲜官员崔溥《漂海录》(1488),记录的是自己“漂海落难”到中国台州之后的经历,[10]则与此构成内在相似性的关联,此是后话。
收稿日期:2012-10-20
注释:
①大庭修编辑《江户时代日中关系资料〈兰园鸡肋集〉—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五》上,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第九卷第五册,关西大学出版部1996年版,第135-147页。《清客新话》原文写本依据サブタイトル《兰园鸡肋集》收集而影印。大庭修考证,该文献末尾有“松冈图书”印章,是松冈玄达(1668、1746)的旧藏品。
②章梫《康熙政要》卷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略云:“《康熙政要》二十四卷(宣统二年排印本)。此书仿唐史吴兢《贞观政要》之体,撮录清圣祖嘉言嘉行,良法美峥,分类排次,为四十二篇。今核全书,尚能自守其例,且附注出处,尤便稽考;此编萃而录之,得见全盛,可谓不苟之作矣。”《康熙政要》又有1969年台北华文书局版。
标签:朝鲜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