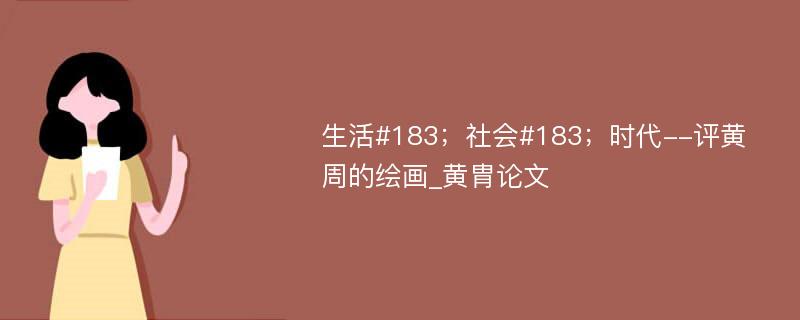
生活#183;社会#183;时代——评识黄胄之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时代论文,黄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黄胄——中国现代人物画大师
记得五十年代,我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工作时,看到一篇文章写道:一位西方学者批评中国画家不会画人物,后来他见到敦煌壁画,改变了这一偏见,但又说那是古代而非现代。四十多年过去,这一批评仍使我耿耿于怀。是的,我们中国画多以山水花鸟为主题,即使有人物,也多是千篇一律的高士策杖与千人一面的宫妃仕女。人物画的确是中国绘画的薄弱之环。但是,这已经成为过去。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反映多彩的社会风貌、烙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中国人物画,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当代中国画史上留下如此浓重一笔、为中国绘画的发展开辟了这样一个崭新阶段的代表画家,当推黄胄。
其一,绘写生活、社会、时代,是黄胄绘画创作的主题,标志着中国人物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黄胄是我们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画家,是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新中国火热的社会生活,锻造了黄胄,造就了黄胄艺术的成功,使他能够成为描绘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新社会的艺术家。
之所以说黄胄为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黄胄的人物画,具有成功描写新中国的生活、社会与时代的史诗特征。黄胄画人物,不是画孤立的人物,不是画简单的人物的相加组合,更不是在画肖像,而是在画我们这一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为了生活中的美好理想而积极、努力地改造着客观世界的活生生的人物。从《苹果花开的时候》、《葡萄熟了》,到《于阗歌舞》、《载歌行》,从《迎良种》、《检修农具》,到《庆丰收》、《积肥模范》,无论是《幸福的一代》、《我爱北京天安门》、《忆苦会上》,还是《火车来了》、《在广阔的天地里》与《欢腾的草原》,黄胄既描绘了《雪地驴驮》、《瑞雪迎春》与《人勤春早》,也图写了《牧鸭》、《喂鸡》、《育羔》与《驯马》,既歌颂了《高原子弟兵》、《亲人金珠玛米》与《边防巡逻队》,也记录了《帐篷小学》、《拉萨女学生》与《母女学文化》;黄胄的画笔,从《高原初春》画到《白洋淀上》,从《瑞丽街头》画到《南海朝霞》,从新疆戈壁画到蒙古草原……不用说优美多姿的《塔吉克舞》、《彝族舞》与《维吾尔舞蹈》,更不要提热烈、紧张的《打马球》、《较力》与青年男女相爱的《草原逐戏》,即便是《看我们画画的黎族小朋友》与没有人物的《西沙群岛出土文物》,黄胄都深情地运用他独具的形神兼备的淋漓泼墨一一绘写。纵观黄胄的绘画,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幅幅单张的作品,而是人民共和国缔造后,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团结、奋发,用勤劳的双手,在天山南北,在青藏高原,在云南边陲,在南海渔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壮阔的历史画卷。这样一部描写解放了的人民“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长卷,其艺术成就与美学感染力、震撼力,完全可与一部数百万言的文学巨著相媲美。
有人说黄胄的绘画不能免俗。黄胄绘画的“俗”,正是民俗、世俗与社会风俗,是构成整个社会与时代的人民生活的反映。正是黄胄笔下的这些“俗”,使人物画脱离了只画古人、神仙、佳人贵妇的俗套,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正是黄胄笔下的这些“俗”,一扫旧文人画无病呻吟的俗媚,表现了健康奋发向前的时代风貌,成为绘写新中国的生活、社会与时代的“画史”。
黄胄的绘画,不仅在绘画题材上开辟了人物画成功表现社会与时代的崭新阶段,而且在绘画思想上把人物画升华到史诗般的境界。
其二,从生活出发,用全新的笔墨,成功地创作出不落传统人物画技法窠臼的、雅俗共赏的大量作品,是黄胄绘画艺术的重要特征。
格尔木的风雪漫天肆虐,巍峨的驼峰似也不堪这高原风寒。然而,新中国的地质尖兵,却在风雪中挺进,使荒原酷冬,勃发出强劲的生机。在黄胄的这幅《洪荒风雪》图中,传统的“十八描”虽然踪迹几无,但中国人物画最高境界的生动气韵,流溢纸外。难怪此画荣获1957年国际青年艺术节的金质奖章。为什么这幅中国画笔墨传统痕迹甚少的作品,却有着如此突出的艺术成就呢?因为黄胄正在用时代的精神熔铸着自己的笔墨。“人物画不重写生,全凭印象意趣或摹拟古人,终不过入黄慎、改琦之流,逐年衰落。”这是黄胄题在1987年3月云南写生稿上的一段话。这段话不仅反映着黄胄对于传统人物画笔墨的态度,而且点出黄胄绘画艺术成功的秘诀——重视写生,走向生活。
在黄胄看来,人物画笔墨表现的基础,源泉在于生活。
黄胄认为:“我看画总不能离开内容、离开生活、离开社会需要,单纯搞形式是搞不出好作品来的。”“单纯搞形式,往往把人搞糊涂了。我看不要过多地考虑方法、技巧,要努力表现生活,画出自己的真情实感。”黄胄的这些认识,是其全新笔墨得以形成的理论基础。
用新笔墨,描绘生活、社会与时代,不落传统技法的窠臼,而又能够雅俗共赏,是黄胄大量作品的基本特征。《春兰》与《巴扎归来》,一写一工,一反映旧社会,一描绘新生活,是可以对读的两幅作品。春兰席地而坐,以指代笔,认真地在地上写着“革命”二字。虽只有春兰的一个侧面,但少女凝重的神思与心态,足可以代表三十年代全中国向往新生的妇女。画家的用笔,概括而肯定,渲染轻巧而简明,笔墨设色,一望而知描绘的是旧社会;几只啾啾相伴的雏鸡,仿佛正试图将春兰从沉思中唤醒,不但使春兰静思的情境恍若眼前,而且更映衬着春兰的青春气息,赋读者以深思与同情。彩墨辉映的《巴扎归来》则与此判然而异。不管是老人矍铄而喜悦的双眼,还是少女们天真而灿烂的笑颜,画家都以兼工带写的笔法作了反复的皴染与精心的勾画,用墨干中见湿、湿中含燥,设色冷暖相兼、关系明确——既有西画的素描关系,又见国画的渲染层次。赶集归来的轻松与欢愉,少女的稚趣与童真,负重力行的毛驴,忠诚相随的家犬,都使新生活的洋洋喜气,盎然纸上。这两幅作品,既没有“高古游丝”,也不见“吴带当风”,既非唐六如,也不是陈老莲,但笔墨气韵,生动袭人,真正是雅俗共赏、“笔墨当随时代”的杰作。不言而喻,黄胄笔墨之随于时代,源于他所置身的社会与生活。
其三,摆脱中国人物画临摹入门的传统,由写生到创作,黄胄敢于开创新路径,提供了人物画家成功的范例。
生活,是黄胄绘画技法形成的关键所在。
黄胄曾说:“我开始学画时没有临摹,这也有它的好处。我一开始就在生活里‘闹’,主要是画速写,一边观察一边画,边画边学,以后才学传统的东西。”他的这种艺术道路,打破了传统人物画临摹入门的路数,在中国人物画史上有着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独特意义。
有“枯柴皴”的形态,又有“折带皴”的意味,笔起笔落,兼及“斧劈皴”的笔势,然而读者看到的并不是一幅笔力劲健的北派山水,而是三位少女袅娜而行的娉婷背影。笔势刚拔的线条,勾写出少女柔美的身段,这样的艺术效果,绝非伏案临摹所可能成就;没有长期的写生功力,毫无可能臻此佳境。这幅1987年的速写上题道:“无论用何种描法,以能够较好的表现形象为本;可以借鉴,不可墨守成规。”既主张学习传统,又反对墨守成规,把自己独特的成功之路,用极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在另一幅德昂族少女的写生图上,黄胄题道:“所谓铁线、游丝、兰叶诸描法,都是运用了线描的表现力,也是画家匠心的结晶。”这无疑是画家对自己多姿多彩的线描人物中丰富的线条形态的定性;“匠心的结晶”数字,也是画家对自己由写生到创作、通过长期的写生实践来发展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这一艰难历程的自述。
“在生活中起草稿,在生活中练功夫,在生活中寻找技巧,个人风格自然可以形成。这不同于为了追求某种风格而生搬硬套。”这样的一种艺术实践,使黄胄的作品,真正地来自生活、描写社会、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可以说,观赏黄胄的画作,就是在读一部描写我们新时代的文艺著作。
二、艺术思维、科学思维、哲学理念的统一
说黄胄的笔墨源于生活,这里的生活并不是指画家自己的生活,而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深入生活、深入社会、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这不但是绘画技能得以提高的过程,也是画家的人生观、世界观得以提高、绘画思想得到升华的过程。黄胄是自学而成的画家,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画家。在生活中学习,在生活中独立思考、提炼,因而他的感受总是新鲜的,因此,黄胄的绘画往往有着一种崭新的意境和壮阔的气象。
“成教化,助人伦”,是中国绘画道德教育的传统。黄胄画驴,腕下的笔墨,写就的已经是一种道德标准与道德评判。在1985年的《群驴图卷》上,画家题道:“老黄牛和毛驴于人的贡献半斤八两,小驴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人们赞美人为老黄牛则可,或曰黄牛精神,或俯首甘为孺子牛等,而无人愿当老毛驴者,或俯首甘为孺子驴者。吾为毛驴鸣不平。”“其形偃蹇,其质戆憨,不事笑脸奴颜,哪能长舌呢喃,引吭啸傲人间,粗粝不厌,高栖不攀,坎坷其途,任重道远。”如果我们知道,“文革”期间,黄胄赶驴三年,与驴相依为命,我们对于黄胄笔下之驴的品鉴,就不会停留在画家笔墨的精到与毛驴结构的准确之类,而是会看见满纸的甘苦炎凉。黄胄的驴,笔墨称绝,而调和笔墨的,却是画家心中之泪,“平生历尽坎坷路,不向人间诉不平”。不仅如此,黄胄绘画中的哲学意味,显然又在对其道德指归作进一步的超越。例如,在一幅《骆驼图》中,黄胄题道:“骆驼在大城市被看为稀奇的怪东西。由于它失去了需要,只能在动物园作为展品。在大西北之大戈壁或沙漠中,特别显得高大有生气。因此品到内容决定形式的道理。”来自生活的感受,发为朴素的话语,却使得一件艺术品成为一种哲理的形象表现;黄胄的绘画,也是这样一种哲学的艺术。
邓拓曾以“人物新,意境新,手法新”这“三新”来形容黄胄的绘画艺术。生活的感染与孕育,固然是黄胄绘画得以“三新”、形成自己独有风格的重要因素,而画家富于科学精神的提炼,也是其艺术成功的关键。
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也是一种科学,艺术与科学有着共同的基础,那就是人类的创造力,因为两者都是探求人类真善美的一种手段。黄胄的绘画艺术与实践,实际上贯穿着一种科学思维——追求与表现真理的普遍性。黄胄的绘画,不论人物、动物,都是在提炼生活中最常见而又是最美好的形象,用新手法去唤醒读者意识中或潜意识中既已存在的情感。这种唤醒的手法越新,反响越强烈、越普遍,科学性就越深刻,艺术也就越优秀;黄胄的绘画,又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优秀的艺术。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非常欣赏黄胄的绘画。当看到黄胄的《奔马图》时,他说:画上的马,从任何角度看,都在向你奔来;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是统一的。李政道博士的话,自有深刻的内涵,但从中也可见黄胄绘画透视表现的功力。六十五岁以后,黄胄更重视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辩证结合,他说科学领域也应该是绘画的一个题材。这是他在炎黄艺术馆聆听李政道博士关于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报告,并多次与他交谈之后,在艺术思想上的一个新跃进。
黄胄善于画气势磅礴、数十平方米的巨幅大作。巨型图画的绘制,需要的不只是艺术家博大的胸襟、非凡的天分与深厚的功力,其严密的构图需要画家具有科学家的精细,需要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融会。其实,作为画家的黄胄是具有作为科学家的天分与才能的——雄伟壮观的炎黄艺术馆,总策划、总设计就是他自己,从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都浸润着科学思想与审美情趣的结合。
1995年9月,黄胄应邀到巴黎举行个人画展。在巴黎停留期间,在卢浮宫、毕加索艺术馆等各个展馆的参观,都激动着画家充满创造力的心灵。他按捺着心潮的起伏,激动地对法国朋友说:这次来巴黎的参观学习,鉴赏了西方各代大师的名作,平生梦中的追求得以实现;数日的参观,可谓“胜读十年书”,将会促使自己思考如何把创作再推上一个层次。再上一个层次,那将是怎样的境界?黄胄成功地描绘了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历史长卷,他又要绘制中国人民这第二次解放新长征的历史画卷。不幸的是,黄胄病逝了,但我想,他为我们留下的艺术财富是丰厚的,他留下的思想与创作之路更值得我们去认识、去思考、去汲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