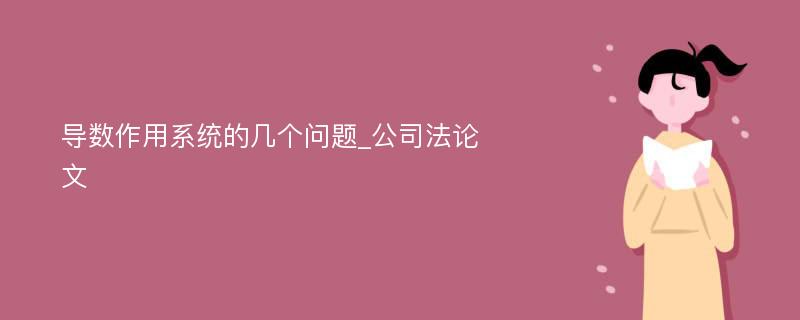
派生诉讼制度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小股东权益的事后救济,我国《公司法》第111条作了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这意味着股东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有权提起无效之诉和撤销之诉。但这两种诉讼的性质属股东直接诉讼,且诉因范围极其狭窄,对其他大量的控制股东或董事会、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小股东或少数股东仍然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创设新的诉讼形式——派生诉讼就成为必要。派生诉讼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有诉权的股东身份的具备。
有诉权的股东身份的具备是指作为股东在什么情况下方可为公司提起诉讼,即原告资格的确定问题。《美国示范公司法》§7.41规定:一个股东不可以开始或持续一项派生的程序,除非该股东:(1)在程序中被控诉的作为或不作为发生时是该公司的一个股东或者在上述时间中虽然不是一位股东,却从在上述时间中该公司的一个股东依法转让得到该公司股票而成为该公司的一个股东;以及(2)在要求强制行使公司的权利时公正地和充分地代表了公司的利益。《日本商法》第267条规定:“(1)6个月前起连续持有股份的股东,可对公司以书面方式请求提起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2)公司收到前项的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时,前项的股东可为公司提出诉讼。”联邦德国《股份公司法》第147条——损害赔偿要求的提出之(1)规定:“……,对于少数股东的要求,只有当构成少数的股东能够使人相信,在股东大会前的至少3个月他们就已经是股票持有人时,才予以考虑。……”。该条之(3)规定:“为了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股东大会可以任命特别代表。如果股东大会已经决定提出赔偿要求,或者是一个少数股东要求这样做,那么法院要根据那些其股份合计已经达到基本资本的1/10,或者其股票票面价值已经达到200万德国马克的股东的申请,任命其他人作为公司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的代表,……”我国台湾省“公司法”第214条规定,对董事提起诉讼的股东,必须继续一年以上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5%以上,才能以书面请求监事人,为公司对董事提起诉讼。
从上述国家和地区来规定来看,有原告资格的股东必须持有一定数额的股份,连续持有股份达一定期间。目的是防止部分小股东滥用诉权。“但考察各有关国家或地区设此资格要求的实际效果,其实并未达到预防滥诉的目的,反倒是将一大批小股东排除于原告之外”。结果是很多小股东仍然无法借助派生诉讼获得救济。现代股份公司股权日益分散,从股权平等以及鼓励股东行使诉权的角度出发,我国在创设该种诉讼形式时,不必对原告股东的持股比例作出要求。哪怕只持有一股,只要他认为董事、经理的故意或严重过失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进而损害了他的利益,他也有权起诉。这既可以催醒小股东依法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又可对董事、经理们起到一定威慑作用,使之不得不谨慎从事。对于连续持股期间的要求则可以规定,因为该诉讼制度的创设应侧重于保护投资股东的权益,如果不对连续持股期间作出要求,则难以避免一些投机股东滥用诉权。
2.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
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也称穷尽公司内部救济原则,是指股东在提起诉讼前,必须曾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监察人提出要求其对违法当事人进行追究。只有当董事会、监事会或监察人接到该请求后,经过一定期间不提起诉讼或对此不作答复,股东才有权提起诉讼。《美国示范公司法》§7.42规定:“要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股东才能开始派生的程序:(1)已向公司提出权利要求,并要求采取恰当的行动实现此要求;以及(2)从权利要求提出时起已经过了九十天除非已早被公司通知其权利要求已被排斥,或者除非是等待九十天期限结束的结果是公司会遭受不可补救的损害。”《日本商法》第267条和我国台湾省“公司法”第214条均规定了此项制度,即公司受到股东以书面形式请求提起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之日起,30天之内未提起诉讼时,股东可以为公司提起诉讼。
规定前置程序是由派生诉讼的本质决定的。因为,诉讼的原因在于公司的利益因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受损,公司应为真正的原告,只是由于代表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等拒绝起诉或怠于起诉,股东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起诉才是必要的。因此,规定前置程序是有其合理性的。我国《公司法》在增设派生诉讼制度时,应规定诉讼的前置程序,以符合派生诉讼的特征。当然,如果因前置程序的存在而使公司利益遭受更大程度的损害时,则可绕过该程序,直接提起诉讼。
3.对股东滥用诉权的防范。
派生诉讼制度的确立,固然为保护股东、特别是保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利的保障,但如果股东滥用诉权,则会使相关董事等穷于应对,势必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进而影响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所以,为防止股东滥用诉权,应规定对股东滥用诉权的防范措施。
(1)受指控行为的限定。被小股东提起派生诉讼而受指控的行为必须是董事、经理等的欺诈或重大过失行为,这种行为给公司进而给小股东造成了损失。换言之,并非所有的使公司蒙受损失的董事、经理的行为均可被提起派生诉讼。在英国判例法上有两个比较有名的判例是关于受指控行为的限定的。一个是库克诉狄克案(Cook v.Deeks)。该案中,某董事代表公司签定一项契约,但后来把这一契约变为己有。由于该董事在公司中拥有75%的股份,因此便在股东大会上通过决议追认了这一行为。公司少数股股东对此向法院提起了派生诉讼。对此,法院判决:由于董事战胜契约的行为本身已构成侵犯少数股股东权益的欺诈行为,所以,少数股股东有权起诉。另一个是但尼尔诉但尼尔案(Daniels v.Daniels)。该案中,公司共发行股份3000股,A、B和C共拥有1400股,E及F共拥有1600股。1970年F以4250英镑的极低估价(gross under-valuation)购入了公司的地产,1975年F将其转售时获得120000英镑。1978年,当A、B、C发现这一事实后便起诉控告E及F合谋使F获得非法利益。法院判决:多数股股东及董事E、F的行为虽然不构成欺诈,但董事F以使公司蒙受损失的行为使自己得到了115000英镑的利益,从而构成了严重过失,因此,少数股股东有权起诉。上述判例中所确定的原则对我国引入派生诉讼制度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因为,董事、经理等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会遇到正常的交易风险,当公司由于正常交易风险而遭受损失时,小股东就不能对董事、经理等提出派生诉讼。否则,则会导致小股东滥用诉权,而这又会产生以下后果:一方面会使董事、经理等穷于应对而有碍公司的正常运营,另一方面也会使董事、经理等在履行职责时缩手缩脚,不利于公司的发展。所以,我国《公司法》在增设这一诉讼制度时,应限定被指控行为的范围,可以限定为董事、经理的欺诈行为和重大过失行为,具体对董事而言,就是违反了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的行为。
(2)原告股东败诉时诉讼费用的承担。对此,各国法律作了相应规定。《美国示范公司法》§7.46规定,如果法院认为该程序没有合理的诉因或有不正当的目的,就可以命令原告支付任何一个被告为在该程序中辩护而发生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用)。联邦德国《股份公司法》第147条——损害赔偿要求的提出之(4)规定:“如果是少数股东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而且公司因在诉讼中全部或部分败诉而需要承担诉讼费用时,这些少数股东有义务向公司偿还这笔费用。如果公司完全败诉,那么这些少数股东还有义务向公司偿还根据第(3)款第3句任命特别代表所造成的法院费用以及给特别代表支付的补助和报酬。”关于原告股东败诉时诉讼费用的承担问题,笔者认为不能绝对地以成败论英雄。要看小股东起诉时是否有主观恶意,如果有,则所有费用应由原告股东承担。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抑制小股东滥用诉权的作用。此外,《日本商法》第267条之(4)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时,法院可以依被告的请求,命令提供相当的担保。这一点,也可为我国立法所借鉴。
我国现行《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均未对派生诉讼作出规定,但在实践中已有法院依照派生诉讼法理审理案件,而且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就个案以“复函”的形式作出过解释。诚然,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民事诉讼的制度创新功能。但法理毕竟不等于法律,我国作为制定法国家也没有遵循先例的司法习惯。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也仅对个案有效,不具有普遍遵行的效力。若不迅速改变这种无法可依的状况,则各法院对股东代表诉讼案件的处理非但不能建立先例,相反却是司法无序的表现。而最高人民法院的个案处理只是一种应急措施,不能对每一个该种案件一一“复函”,因为这不仅程序烦琐,而且降低了我国法制的透明度,影响了对投资者保护的可预见性。因此,在目前时机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在修订《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时,应将派生诉讼的机制纳入其中,以对小股东尽周延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