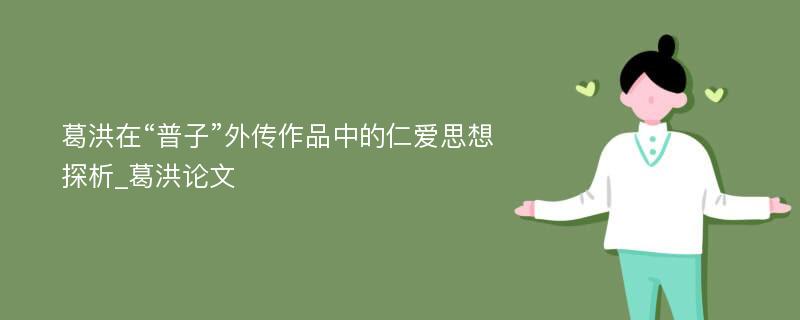
葛洪《抱朴子外篇》仁明思想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篇论文,思想论文,抱朴论文,葛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5;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09)06-0092-07
葛洪是两晋之际著名的道教学者。在其重要著作《抱朴子外篇》中,他对儒家的仁明观进行了重新阐释,主张明先仁后、舍仁而用明。这种诠释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颠覆。葛洪的这一思想是如何构成的,它的思想渊源又在何处,在儒学式微的时代这一思想给当时的思想界产生过多大影响?这便是本文要论析的三大问题。
在论述葛洪的仁明思想之前,有必要对传统儒家的仁明观点作一点辨析。
众所周知,仁是儒家思想中富有根本性的理论术语。儒家认为,仁是人最为重要、最为本质的特点,是内化于人心之中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并非没有差等,而是在家庭、血缘、伦理基础上由近及远,“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重视日常伦理与道德教化使之逐步渗透到人们的行为之中,乃是儒家思想借以开展的途径。但是,仁并不止于内在修养、道德品格,它还必须遵守一系列行为规范并外化为有效的实践动作,即“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仁意味着去成就与之符合的事业。仁是非常高的准则,从积极意义上讲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即推己及人,不但使自身完满,而且也使他人完满;从消极意义上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感同身受,不把自己不喜欢的强加于人。仁是人能为人的标尺,是全面提升人格的准则,也是最后衡量人们事业的依归。
明在儒家那里是表示智慧与才能的意思,如:“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论语·颜渊》)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诗经·大雅·烝民》)、“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礼记·中庸》)之明同义。儒家之明与智之义近似,都是说人的智能,如:“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
在儒家思想里,仁与明的关系非常明确,就是仁与明(智)可以配合,明(智)以辅仁,“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智是仁之有效补充。但是儒家又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则仁可以包括智而占有主导地位。儒家认为,两者都有积极价值,但是仁主明辅的主从与本末关系是恒定不变的。
在对待仁明关系的问题上,葛洪提出了一个与儒家大异其趣的观点,这就是明先仁后、舍仁而用明。在《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七《仁明》篇中,葛洪具体阐述了他的仁明观。葛洪把仁与明作了细致对比,然后断言:“以义断恩,舍仁用明,以计抑仁。仁可时废,而明不可无也。”葛洪并且用大量经典来证明自己的看法:
孔子曰:“聪明神武。”不云聪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传》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书》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叹上士,则曰:“明白四达。”其说衰薄,则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为仁由己。”斯则人人可为之也。至于聪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见赤子将入井,莫不趋而救之。以此观之,则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间,而聪明之分,时而有耳。①
葛洪引证儒家经典以及《老子》的论说,认为圣人以明为首,而仁非常易得,圣人不将其放在首要地位。葛洪扬明抑仁的用意极为显豁。葛洪不论引用儒家仁还是《老子》有关明的资料,均为单独论列,如孔子说“聪明神武”,《春秋》讲“明德惟馨”等,都是单讲明而未讲仁。葛洪认为单讲明未讲仁就是不重视仁,这显然犯了逻辑错误,偏离了文本的原意。再者,葛洪所举关于明的例证,大都是形容词,如“明王”、“明哉”,这些明不在主词位置,不是经典所要论述的中心。所以,葛洪关于仁明的观点与儒家经典相违背。葛洪此处对经典的理解多取一面,曲解处不少,当为“六经注我”,这说明大多数的阐释往往是对经典的重新解读,阐释是常释常新的,也是新思想得以形成的途径之一。
为了论证明先仁后、舍仁用明的思想,葛洪通过例举以阐明有仁无明的危害,并以之彰显明之作用强于仁,肯定明先仁后的正当性。葛洪说汤武讨伐桀纣,虽有不仁之实,但因其明以建不世大功;而徐偃王专修仁德却无明识,最后破家亡国,有仁无明的教训实在深刻。无明之人,很难辨别真伪、善恶,更不能适时采取对策以因应形势,不但自身难保,所谓的济物救生之谈亦属幻想:“夫心不违仁而明不经国,危亡之祸,无以杜遏”②。通过这种对比,葛洪益发明晰地阐述了明之功用。不仅止于此,葛洪进而指出,有仁无明对社会的进步几无作用,他认为只有“大明”之人方能发明创造从而推动历史发展,比如燧人氏发明火、神农氏改进稼穑、黄帝制作衣服、仓颉创作文字等等。这些圣人有大明之才,改善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提高了人类文明程度,因此功不可没。而这不是专务仁德之人可以做到的,明之功用远大于仁。以此对比,葛洪把明的地位与作用提升了起来。明显可见,葛洪的观点与传统儒家仁主明辅的思想背道而驰,并且与之形成极大的理论鸿沟。
后世学者对葛洪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尤以清代学者俞樾的抨击最为激烈:
要皆曲说也。抱朴固非经生,于经义所得殊浅,其实明不得先仁在。《论语》固有明证。何也?孔子论令尹子文、陈文子皆曰:“未知,焉得仁?”则知浅而仁深,知卑而仁高,大可见矣。《释文》曰:“知,郑音智。”《汉书》人表引此语,师古注曰:“智者虽能利物,犹不及仁者所济远也。”师古此意,必是康成旧说。抱朴不知此旨,故以明居仁之上,殊非正论。岂当时何晏之《集解》已行,学者已不知有郑义乎?③
从儒家思想本身来说,俞樾的驳难完全可以纠正葛洪的观点。不过,他怀疑因为魏晋之际何晏《论语集解》太过流行导致郑玄的《论语注》湮没无闻则是不确的。《晋书·荀崧传》载,东晋初建置郑氏《论语》、《孝经》博士各一人,足证魏晋之际《论语》郑氏义还在传授。二十世纪以来,敦煌、吐鲁番地区先后出土了多件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都说明当时学者并非不知《论语》郑义。葛洪之目的不在解释经义,“葛洪对于‘仁’字所以有新的估价,无关乎郑注的存亡,最主要的因素,是在于当时的局势,已非‘仁’字可以统括”④。
葛洪的仁明思想因为与儒家大异其趣,所以益显独特。但这种思想的提出却不是无源之水,其与东汉王充和徐干的思想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王充在《论衡·问孔》篇中说:
智与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为仁之行?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也。五者各别,不相须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礼人、有义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礼,礼者未必义。
王充认为仁与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人们往往只具有其中的某项要素,很难全备,仁不必智,智不必仁。《论衡·定贤》进一步论述道:“有高才洁行,无知明以设施之,则与愚而无操者同一实也。”王充此处论述与前相比显然更加深入。这种论断强调了“知明”的作用,对“高才洁行”的仁德反有贬损之嫌,造成明高于仁的态势。王充把仁与智作了分疏,明晰了各自的范围,指出仁非万能,智也有仁难以企及之处,这就为明先仁后的提出打开了理论缺口。而徐干在《中论·智行》篇中所论已经与葛洪很接近,他说:
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则可取乎?”对曰:“……夫君子仁以博爱,……智以辨物,岂可无一哉?谓夫多少之间耳。……是故圣人贵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于世矣。……四皓虽美行,而何益夫倒悬?此固不可同日而论矣。”
徐干指出,仁德人人具备,只是多少有别,因此并非异常重要,而才智却能立功益世,最为人所宝贵,因之仁德不能和才智相提并论。徐干所述完全拉开了才智与仁德的距离,明确表示了才智高于仁德的意见。徐干也是以经典为论据的,如他说《易·离·象》称“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尚书》以“钦明为先”等⑤。徐干认为儒家经典都推崇明之作用,明之先于仁非为无据。徐干也论及有仁无明的弊端,他列举历代帝王如徐偃王等因为只修仁义而没有才智终于害己覆国的事例⑥,从反面证实了有仁无明的危害。因此仁义与才智谁者为高、如何弃取,已经分外清楚。
从以上分析可知,葛洪明先仁后的思想显然受到了王充与徐干的启发以及直接影响,其间的继承脉络异常明晰。葛洪推崇王充及其《论衡》,认为王充“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⑦,所以他从《论衡》中吸取于己有利之思想应属合理。当然葛洪也采择了徐干的观点,他的论述也多援引经典为根据,其思路与徐干一致。葛洪指出了有仁无明的危害并以徐偃王为证,这也与徐干相同。只是葛洪把两人未明言、未具象的思想明确地以明先仁后、舍仁用明归纳了出来,并给以更加细致深入的论述。
葛洪对仁明二义进行详细的分疏,还应该是受到魏晋之际才性论的影响。大体来说,才指个人才智能力,性指个人道德品性,两者如何协调,在汉晋之际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汉晋选官制度如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等比较重视乡论清议,因此很看重士人在民间的声誉与名望,在传统中国社会里道德品性极容易被作为评价士人誉望的标准。但是,实际的政治需要才智能力,有德无才对于推动政治毕竟无益,所以士人的才智能力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这样一来,如何处理才智能力与道德品性的关系,两者孰轻孰重,就成为士人热烈讨论的题目,随之形成一定的理论解释,促成了才性论的开展。东汉尚名节,则论人较为倾向于道德品性,因之士人互相品题、激扬名声渐增,以致选人出现背实向虚的风气。曹操掌权,力图清肃此种风气,鼓励选人不必全倚道德品性,即使“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被举⑧。这种重才倾向无遗是对东汉重德性风气的反动。徐干在《中论·智行》篇中宣扬智优于行,智就是才智能力,行就是道德品性,这样说来徐干也是重才一派,与曹操正同。曹操掌权时,徐干为司空军谋祭酒、五官将文学,与曹操、曹丕关系密切,他提出与曹操相同的重才观点实属必然。对才性论的讨论,魏晋之际更为活跃,产生过傅嘏的才性同、中书令李丰的才性异、侍郎钟会的才性合、屯骑校尉王广的才性离等诸多理论⑨。才性论竟然可以发展出同、异、离、合四种不同的观点,可见时人对之研究愈加细致与透彻。至于才性四本论的具体内容,因文缺难以详考,但不外乎论证才性如何搭配以及哪一方面更加重要。葛洪对仁明二义进行分疏也受到当时流行的才性论思潮以及方法论的影响。他说:
夫料盛衰于未兆,探机事于无形,指倚伏于理外,距浸润于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恻隐于昆虫,虽见犯而不校,睹觳觫而改牲,避行苇而不蹈者,仁之事也。尔则明者才也,仁者行也。⑩
葛洪认为,明为才,指可以见微知著、预料形势以采取对策的能力;仁为行,指具有恻隐之心、容忍胸怀的品性。葛洪明确以才称明、以行名仁,这分明是探讨才性问题,由此可知葛洪是利用了才性论来探讨仁明关系。前文葛洪提出“以义断恩,舍仁用明,以计抑仁。仁可时废,而明不可无也”,这就把仁、明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两者作用不同,不能相互替代,而葛洪更加重明。从才性论上讲,葛洪的观点就是才性不同,不能混淆,而更加重才。这个观点与徐干一致。葛洪吸取了徐干的智行论,在才性论上也与徐干相同,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曾春海先生曾对四本论有一种解释,他认为才性同指性之外用为才或者是才发展成熟规定了性;才性异指才性领域不同,机能各异,互不相干;才性合指才性分属不同领域,相互配合始能成器;才性离指才由性发展而来,但后天的发展反而隐蔽了性(11)。依据曾春海先生对才性四本论的分析,则明显可以看出葛洪的才性论倾向于才性异一路。
葛洪的仁明观引起后世学者的瞩目。贬之者仍以俞樾所谓“曲说”视之,如蓝秀隆先生认为“智者虽能利物,而不能达道”(12)。褒之者则认为葛洪仁明观乃是主张仁明兼具,并不与儒家思想冲突,如尤信雄先生认为葛洪的主张“只是基于乱世特殊环境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权宜手段,实在无损于他对儒道的虔敬”(13),曾春海先生也认为“就基本要求而言,葛洪认为理想人格应兼具‘仁’与‘明’两种内在条件”、“葛洪这论点契合孔子‘智者利仁’观点”(14)。诸家之论见仁见智,如何评价葛洪的仁明观确为一重要问题。
首先应该明晰的是葛洪之仁明思想并非主张仁明兼具。葛洪明言“以义断恩,舍仁用明,以计抑仁。仁可时废,而明不可无也”,这表明葛洪是把仁明看作两个不同的范畴,其作用各不一样,因此在葛洪那里,仁明并非有平行的价值,而应该是以明超仁、以明包仁,这是葛洪仁明观的落脚点。其次,葛洪仁明观之明解释为儒家之智,不能全面含括葛洪的思想。上引王充《论衡·问孔》篇、《定贤》篇是“智”和“知明”与“仁”并举,徐干《中论·智行》篇是“智”与“行”并列。“知”与“智”通,“行”指道德品性也就是“仁”,而葛洪继承了二人的论述以“明”、“仁”对称,这样看来以“智”释“明”有一定道理。但是,仅仅以“智”释“明”已经不能包含葛洪所说“明”的完整意义。葛洪言“《易》曰:‘王明,并受其福。’‘幽赞神明。’‘神而明之。’此则明之与神合体,诚非纯仁所能企拟也”,“以为仁在于行,行可力为;而明入于神,必须天授之才,非所以训故也”(15)。“明与神合体”、“明入于神”就不是单纯的“智”所可以解释,此处之“明”已经包含有体道而行的意思,掌握了事物的运行法则就可以明了万物而不惑,行动自然无所阻滞。因此,葛洪所说之“明”实含有很强的形上意味,而具有“明道”的涵义(16)。那种认为葛洪的仁明观没有“达道”以及符合儒家思想的说法,似都未能切中肯綮。
从更深层次来看,葛洪的仁明观与其一向主张的道本儒末思想一致。在他看来,儒道两家的思想方法与分析问题的途径颇不一样。儒家是从日常人伦引申出自己的思想,是关注现实的态度,而道家认为伦理道德、礼乐制度并非天然存在,它们只不过是失道之后的一种人为状态,反而破坏了道的和谐与完整,如果按照道的要求行事,不但治身容易,就是治国也不难。两者比较,道为本儒为末。这一思想的源头来自《老子》,其第三十八章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老子》视仁义等为失道之后的堕落状态,道为本源儒为支流,以道御世无物不可统,儒道是本与末、器与用的分别。魏晋之际儒学式微,老、庄之说盛行,道家执一统众、以简御繁的思想更为玄学家所吸取,所以有得意忘言、得鱼忘筌之说,从而使道本儒末的思想带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葛洪作为一名道教学者也继承了道本儒末的思想与方法。他说:“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17),“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18),这是从本末、器用上看待儒道关系。葛洪谓“明之与神合体”、“明入于神”,显然不是儒家所说明白事理的意思,而更与道家之明相合。《老子》第十六章言:“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第二十二章言:“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庄子·骈拇》也说:“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庄子·庚桑楚》又说:“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此处道家之明是见于不见、体道而行,而儒家之明是才智能力、见于所见,两者有很大不同。葛洪所说之明与老、庄之明多相吻合,葛洪用道家之明置换了儒家之明。因此可以进一步肯定,葛洪所说之明当为明道之意。明为明道,而仁不过是一种形下的状态,按照道本儒末的思想自然可以得出明先仁后、舍仁用明的观点。这是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向,葛洪是在以道释儒、以道统儒。
魏晋之际,两汉以来日益繁琐化、谶纬化的儒学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儒学的独尊地位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史学、子学、文学逐步摆脱经学的束缚而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经学笼罩下的道德与伦理意识已经不能为思想界提供更加新鲜的东西。而史学、子学、文学主体意识的增强,无疑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增添了更加丰富的知识,为当时的思想界注入了活力,这就是“礼失而求诸野”。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儒家仁的学说既然益加滞碍与僵化,那么诸子百家之学的知识就有必要救济其弊,从而创造出新的思想体系。葛洪生当其时,他博学多通,广泛吸收诸子百家之学的知识,奠定了批判性吸收儒学思想的基础。仁的核心是道德,明的要义是知识,明先仁后、舍仁用明就是用诸子百家之学的知识改造儒家的仁义道德,把知识提高到主导地位而吸纳伦理道德。这就等于完全颠覆了儒家的仁明观,而重新塑造了知识(明)与道德(仁)诸要素,以形成有利于时代发展的、崭新的知识与道德思想体系。因此,葛洪的仁明观与魏晋之际学术发展的态势紧密相关,这就是葛洪仁明观在当时思想界的意义。
总之,葛洪提出明先仁后、舍仁用明的主张,是因为魏晋之际的现实情形需要他对之作出新的阐释。葛洪的仁明观颇受王充、徐干思想的启发,也与魏晋之际才性论思潮以及方法论的影响有关。同时,葛洪的仁明观还与其道本儒末思想以及当时的学术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注释:
①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4-235页。
②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第227页。
③李天根辑:《诸子平议补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2页。
④林丽雪:《抱朴子内外篇思想析论》,台北,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146页。
⑤⑥[东汉]徐干:《中论·智行》,见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7,289页。
⑦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第423页。
⑧《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⑨《世说新语校笺》卷上《文学》,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6页。
⑩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第227-228页。
(11)曾春海:《玄学及〈抱朴子·外篇〉中的理想人格》,载《哲学与文化》(台北)1999年第7期。
(12)蓝秀隆:《抱朴子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
(13)尤信雄:《葛洪评传》,台北,文津出版社,1977年版,第29页。
(14)曾春海:《玄学及〈抱朴子·外篇〉中的理想人格》,载《哲学与文化》(台北)1999年第7期。
(15)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第233、236页。
(16)章义和:《正郭与弹祢——〈抱朴子外篇〉汉末名士评议》,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7)(18)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8,184页。
标签:葛洪论文; 儒家论文; 抱朴子论文; 老子论文; 论语·颜渊论文; 论衡论文; 国学论文; 徐干论文; 论语论文; 孔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