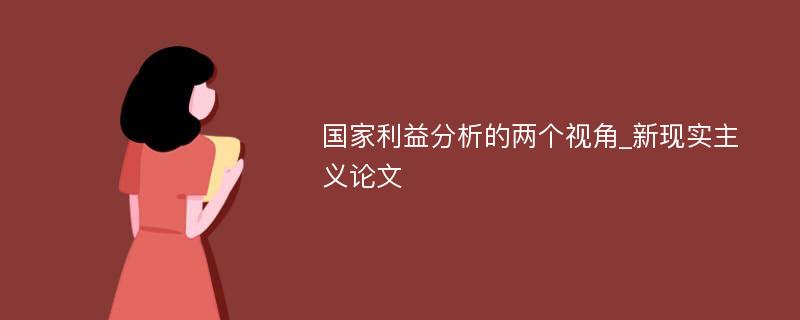
国家利益分析的两种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国家利益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历了三次大争论后,国际关系理论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深度扩展时期。(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些概念、命题和假设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国家利益的概念就是其中之一。从目前看,对国家利益的考察,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形成了两个明显的理论视角,即经济学(理性主义)和社会学(建构主义)的视角。
一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古典现实主义者摩根索那里,利益被确认为权力。(注:[美]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7页。)国家就是争夺权力、维护权力和显示权力。所有的问题都可归结为权力问题。国家行使权力的行为就是追求利益的行为。国家力量的大小决定国家利益之所在。不过,他对国家利益的分析主要来自于对人性的洞察和历史的领悟。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发展了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认为权力只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他从国际体系结构的角度来解释国家的行为,认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是一个自助的体系。在自助体系下,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由于对国家的现实威胁或可能的威胁随处可见,无政府状态只能使国家处在安全困境中。华尔兹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使用的是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在新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国际政治理论》中。他在描述国际政治结构时是通过与市场经济结构相类比来实现的。从排列原则上看,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相当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国际政治的单元国家类似于理性的经济人。“国际政治的体系,就像经济市场一样,是由重视自身利益的单元的共同行动而形成的,国际政治的体系,就像经济市场一样,从根源上说是个人主义的,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有意的。在允许自助原则上,国际政治和市场经济在结构上是相似的。”(注:[美]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正如经济学家以公司来界定市场一样,我以国家来界定国际政治结构。”(注:[美]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结构是根据单元之间的力量分配来界定的。公司和国家都是类似单元。结构的不同,不是由于单元在特征和功能上的差别,而只是它们力量不同罢了。市场结构是根据公司的情况来界定,国际政治的结构是根据国家的情况来定义。“这些理论问题要求我们把公司看成公司,把国家看成国家,而不理会公司之间或国家之间的差异,然后,就通过考虑各单元在它们系统中的地位,而不是通过研究它们的内部性质,而得到解答。”(注: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通过国家与公司间的比较,国家利益这一模糊不定的概念便清楚了。根据假定,经济人试图最大限度地获取预期利润,而国家则努力确保它们的生存。在分析国际体系的数目时,华尔兹从经济的角度认为两极是最好的小数。“当共谋和交易变得容易时,商业公司的财产和市场的秩序就会加强,随着参与者数目的减少,共谋和交易变得更容易。”(注: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在两极世界中,不确定性减少,计算易于进行。
新自由主义则通过引入合作和制度的概念来代替新现实主义的自助和安全困境的概念。它们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无政府状态的后果的认识上。不过,新自由主义对合作的起源和制度产生的分析仍然是经济学的视角。如果说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基欧汉还只是描述世界政治中的合作和制度的话,那么,在《霸权之后》中,他则用经济学的概念来打造自己的理论。(注: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102.)我们在这部作品中看到了交易费用、市场失灵、外部性、路径依赖、沉没成本、有限理性等经济学术语的借用。合作为什么在无政府状态会发生?理性选择理论给予了回答。作为理性的个人总是力图以付出尽可能少的成本,最大限度地增加某些价值和利益,作为人格化的国家,必须以最小的成本实现自身最大的利益。如果以武力冲突解决问题代价过高,以及合作使双方均能获利,国家间的合作就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可能方式。新自由主义强调,各国可以采取以牙还牙或者投桃报李战略,以一定条件为基础进行合作。如果囚徒困境能够重复,有条件的合作就容易实现,国家最终会发现共同合作是它们最好的长远战略。而要想实现合作,只能通过国际制度这一中介才能达到。“为了在世界政治中的合作不只是在临时的基础上进行,人类必须使用规则。”(注:James Der Derian,InternationalTheory:Critical Investigati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291.)国际制度为什么能起到这种作用呢?基欧汉把科斯定理运用到国际制度分析中。因为制度影响了交易费用,具体地说,制度减少了不确定性,改变了交易成本,在不存在等级权威的情况下,制度提供了较充分的信息和稳定的预期。如果交易成本可以不计,那么就不必创建新制度去促进互利的交换,如果交易成本太高,制度的建立也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世界政治中,主权和国家的自主性意味着交易费用不可忽略不计,因为沟通和监管很困难,所以,只要沟通和监管的成本小于从政治交换中所获得的利益,制度就会出现。一旦制度形成,尽管从效率上看并不最优,但改变它并不容易。新自由主义从路径依赖理论对此作了解释。“如果新的模式不足以证明扔掉可以利用的资源更为有利可图,那么沉没成本(sunk cost)则倾向于维持原来的行动模式。国际制度就代表了沉没成本。”(注: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p.102.)新自由主义通过引入国际制度变量来分析国家行为和国家利益。
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双方都把国家利益最大化作为思考的前提,很少提到价值考虑;都承认国家是最基本的行为体,尽管在非国家行为体的相对重要性方面存在分歧;都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注:参见David Baldwin,Newrealism andNewliber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导论部分。)它们的分析工具是经济学方法,即从经济学的视角来透视国际政治。新现实主义主要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来理解国家行为。它所论述的结构(无政府状态)相当于自由放任的市场,国家类似于市场竞争的行为主体公司(主要是大公司)。新自由主义则主要以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中的制度。我们知道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个体主义的方法,以经济人(利益、效用最大化)为前提假设。在上述理论中,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假设,国家被假定需要权力、安全和财富。他们认为国家的偏好是无疑问的,对研究者非常清楚。国家的偏好可以从一个国家的客观条件和物质特征中推导出来。政策变化的偏好是其反应。他们在国家内部寻找变化的偏好,然后,把偏好和国内行为体的需求联系起来。物质条件的变化重新塑造行为体的利益,迫使它们改变政策。这样,国家利益的来源就被置于国家之内,而不是在国家之外。尽管权力分配的变化在国家之外,但安全偏好是国家固有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以上述假设为基础,主要分析三件东西:相关的行为体、行为体的能力和它们的偏好。华尔兹明确地把国家刻画为相关的行为体,以权力衡量能力,以能力的最大化刻画偏好。新自由主义也是如此。他们之间的争论主要是在偏好的内容(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绝对获利与相对获利和无政府状态的性质)。研究者通过分析还原的方法,就可打开决策者的黑箱,解剖国家利益。
二
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国家利益和国家行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偏好可能不是国家固有的,也不只局限于物质状况。相反,国家偏好具有弹性。偏好之所以具有弹性是因为国家并不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行为体,而是镶嵌(embedded)在全球结构之中。个体主义的经济学方法不可能让我们充分地理解国家与国际结构之间的互动。于是,国际政治学者就把目光转向社会学。20世纪90年代前后兴起的建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条分析国家利益的视角。按照温特的定义,建构主义是一种国际体系的结构理论,主要论点是:1.国家是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分析单元;(注:Matha Finnemore,National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Chapter One.)2.国际体系的关键结构是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而不是物质的;3.国家认同和利益是社会结构构成的重要部分,而不是由人性或国内政治对国家体系的特定外在因素所构成。(注:Alexander wendt,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2.June 1994,p.385.)规范、话语和认同是它的核心概念。在本体论上,它研究的是国际政治的社会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在方法论上使用的是社会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关注的是行动者(agent)和结构的互动过程而不是结构和行动者的分离。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构成的(constitutive)。“国家在互动之前,没有认同,没有期望,没有利益,互动过程决定了认同和利益。”(注:Jonath Mercer,Anarchy and Ident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2,Spring 1995,p.231.)建构主义通过引入规范的概念,来分析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不是把角色和利益看成是既定的,而是质疑它们,把它们作为分析的对象。所谓规范是指行为体持有的共同预期。它不仅是主体的,还是主体间的。“规范有两种作用,即构成作用和规定作用。规范或者构成认同,或者规定行为,或者两者兼有。”(注:Peter J.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Securit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5.)这样,行动者和结构的互动通过规范连接起来。行动者的利益不再是既定的,而是不断变化和构成的。国家利益也就不是先定的,等着去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的。国家利益不能只从国家内部的客观条件和物质状况中推导出来,作为社会结构的规范同样对国家利益构成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外在的,而是被内生化(endo-genized)到行为体中。它们不只是限制国家行为,更重要的是改变国家的偏好。国家偏好的来源可以在国家之外寻找。国家被国际社会社会化了。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建构主义者解释国家行为和利益变化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社会学中是指人们获得人格、学习社会和群体方式的社会互动过程。(注: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在建构主义看来,社会化是一种把国际制度和规范与国家或国家内的集团和行动者联系起来的机制。它是规范的内化(internalization)。在新现实主义那里,社会化至多只是影响行为体的战略。(注: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88页。)在新自由主义那里,规范只是合作的促进者,是一个干预变量。建构主义认为社会化还决定认同和利益。社会化过程实际上是国家利益变化的过程。“国家利益是根据国际上公认的规范和理解——什么是善的和合适的——来认识。规范的语境也随时间变化,当国际上公认的规范发生变化时,它们就引起体系层面上的国家利益和行为的相应转变。国家利益的再定义常常不是外部威胁和国内集团要求的结果,而是由国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所塑造。”(注:Ma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International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27.)
建构主义的新秀玛莎·费丽莫从国际组织的角度分析了国际社会结构的规范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注:Matha Finnemore,National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Chapter One.)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际组织的产生是为了解决交易成本、信息不充分和其他市场失灵的问题。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认为国际组织的创立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工具。他们对国际组织的分析集中在组织结构内的成员国通过战略互动而构成偏好的过程。因此,国际组织只是国际互动的附属现象。这架机器的规范和规则只是约束国家能够做什么,但机器本身是被动的,不是有目的(purposive)的行为体,它只是一个干预变量,没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而在社会学看来,国际组织不仅对其他的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体作出反应,而且也对规范和文化的力量作出反应。这种作用塑造了国际组织认识世界的方式。国际组织的产生可能不是因为它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它们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所体现的价值。它们可以变成独立于国家的自主行为体。国际组织的这种权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它们体现了理性合法权威的合法性。2.它们控制了技术专业人员和信息。(注:Michael N.Barnet andMatha Finnemore,The Politics,Power,and Pathologies of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53,Autumn 1999,p.707.)理性合法权威的合法性表明国际组织可以有一种独立于国家政策和利益的权威,尽管它们由国家创立。科层组织对信息和专业人员的控制表明它们不仅仅是执行政策,还可以塑造政策。
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国际组织的不同分析导致了对国际组织的不同认识。社会学把国际组织看成是一个有目的的行为体,可以对世界发挥独立的影响,因而,当我们在分析国家利益时,国际组织就不只是作为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物质结构约束国家,而且还作为一个具有自己规范的、有目的的行为体来作用于国家,把组织的规范传授(teach)给国家,并使之内化为国家的规范,改变国家的认同和利益,而不论国家是否具有这种内在的需求。也就是说,国家利益的来源不再是国家内部的事情,国家被国际社会社会化了。国家利益不是先定的,而是由行动者和结构通过社会实践所构成的。
三
通过上述对国家利益分析两种视角的梳理,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启示:
1.两种视角丰富了我们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也促进了我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
从目前来看,尽管经济学的方法仍然占主导地位,但社会学的方法已显示出强劲的势头。它不仅有理论的构造,还有案例的研究,(注:Ma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表明了这一点。)大有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迹象。20世纪80年代末期基欧汉对建构主义缺乏实证分析的评价已不合时宜。不过,两种方法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一种补充关系。库恩的范式理论不适合国际关系理论。(注:Ken Booth andSteve Smith,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day,Peen State Press,1995,p.16.)正如基欧汉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所言,“我们并不认为……复合相互依赖完全反映了世界政治的现实,恰恰相反,它和现实主义是理想类型,大多数情况是在这两端之间,有时,现实主义是准确的,或基本上是准确的,但经常是复合相互依赖更好地描绘了现实。”(注:Michael Brecher,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International Study Quarterly,1999,4,p.234.)费丽莫也说,“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性的。”(注:Matha Finnemore,National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27.)世界政治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实在(包括物质实在和社会实在),如果我们从多方面考察国家利益,在各种方法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我们就会对它有一个更准确、更全面的把握。
2.把行为体与结构的分析进一步结合起来
在主流政治科学分析中,行为体的方法占主导地位。分析一般以假定行为体具有权力和固有的偏好开始,不论这些行为体是投票者、国会议员、公司、社会阶层还是民族国家,宏观的结果就是微观之和。而结构取向的方法是把结构看成是分析的起点,从中推导出行为体的行为和利益,结构是原因。从上面两种视角看,行为体的分析主要是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的方法,结构的分析主要是社会学的整体主义的方法。实际上,国家行为主要受两种逻辑支配,即推论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和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注:两种逻辑的名称来自马奇和奥尔森,转引自Ma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International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29.)推论逻辑由行为体驱动,行为体对手段和目的进行计算,设计出效用最大化战略,规范和惯例只是这一过程的产物。适当性逻辑由社会结构驱动,社会结构的规范控制所要考虑和采取的行动。不过,在任何既定的情形下,两者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国家利益时,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
3.对国际组织需要加以重新认识
在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家一直是透视的焦点,国家中心论的色彩特别浓厚,对国际组织的认识以国家为参照系。在《国家间的政治》中,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只不过是大国控制的工具,反映了大国的意志,是战争的限制因素。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看不到对国际组织的分析。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组织的作用很小,受国家权力和军事力量的限制。在《霸权之后》中,国际组织是国家解决冲突、促进合作的方式。以经济学方法为主的主流理论把国际组织看成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国际组织只是约束国家行为的一种结构,这种结构还是一种物质结构(力量的分布与排列)。而在使用社会学方法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中,国际组织既是自主的行动者,又是结构(物质和意义的)。自主的行动者意味着有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追求。结构意味着对其组成的单元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仅是一种约束,它还可以使结构的规范通过社会化改变行为体的偏好,从而改变国家利益。当今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由国际组织编织起来的网,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国家不可能游离于国际组织之外,而是更多地卷入到国际组织中来。国家加入国际组织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利益计算,还有国际组织的规范扩散的影响。国家偏好的变化既是学习(来自国家内部的需求)也是传授(来自国际组织的规范)的结果。随着全球市民社会组织的兴起,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融入国际体系的国家来说,我们不仅仅应关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还要注意国际组织对自己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只限于物质结构的层面,还蕴涵着意义和价值结构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