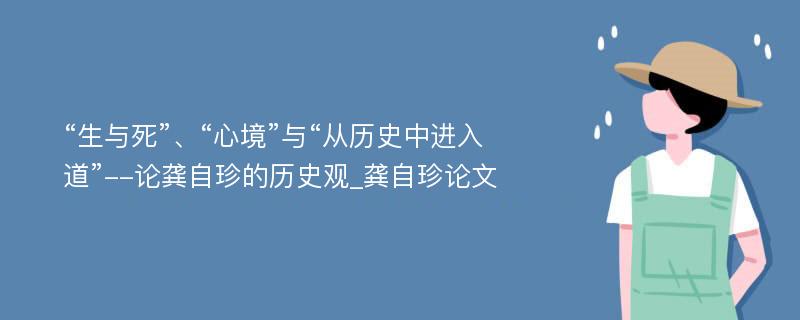
“始卒”、“心情”和“出史入道”——论龚自珍的历史观和史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史学论文,入道论文,心情论文,始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围绕龚自珍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学界同仁已发表了一些包含许多独到见解的研究成果。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如没有把龚自珍的社会文化发展史观与其人本史观有机联系在一起,未能将其有关历史的认识作为一个整全的历史观来阐发说明;对龚自珍所说的“道”以及“史”与“道”之间关系的阐释,似嫌不够周全;关于龚自珍历史观、史学观与其基本思想认识(如“童心”、“尊情”、“完者”即完全生命等)之间联系的探讨尚不够深入,等等。有鉴于此,笔者试图更加系统地阐释龚自珍的历史观和史学观,以推进龚自珍思想的研究。 一、“有始有卒”的社会文化发展史观 在《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中,龚自珍写道:“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①在这里,“造”,指创造,也指认识及命名(“造名字”)。龚自珍认为,“众人”建构(认识及命名)了自然世界,创造了文化世界;而“众人”的主宰是“我”(自我意识或主体意识),而非“道”、“极”等后人制定的学说、规则。龚自珍明确否定了历史是“圣人所造”的观念。 在《五经大义终始论》中,龚自珍阐述了“贵乎知始与卒之间”的“圣人之文”或“圣人之道”,亦即人类社会历史文化演变、发展的基本轨迹或基本逻辑:“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②。“有始有卒”的“圣人之道”,实际上就是“众人之道”(即“圣人”对“众人之道”的体察和认识——“圣者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作”③)。“众人”创造历史文化,首先从以“饮食”为核心的物质生产开始;继而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创制以“祭祀”为基本程序、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礼乐制度;最后,人们构筑了以“宾师”或“天下良士”为主要载体、以价值—思想或养德为中心的精神文明。在这里,龚自珍既指出了人类历史文化“三世”(“食货——据乱”、“祭祀——升平”、“宾师——太平”)演变、进化的纵向基本历程,又揭示了人类社会文化生成、存在的横向整全结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在《农宗》一文中,龚自珍阐释了“先小而后大”、“先有下而渐有上”④的社会文化发展史观。当然,龚自珍也有“圣人”创造历史的说法。例如,他认为:“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⑤“昔者人伦之始,五品之事,实大圣之所造。”⑥这种“圣人”创造历史的说法,表面上似乎与“先下后上”说(基于通史或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自相矛盾,实际上也可与“先下后上”说形成互补(因为“圣人”也参与创造历史甚至有时主导性地创造历史,特别是基于政治史及学术思想史视角进行观察时)。“圣人”创造历史的说法,在龚自珍的历史思想体系中,属于次要思想,并不是他的主流思想。龚自珍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化的。他说:“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人亦小天。古今朝市城邑礼俗之变,以有形变者也;声之变,以无形变者也。”⑦就某一特定朝代或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而言,存在着“蚤时”、“午时”、“昏时”的“三时”演变⑧,存在着“治世”、“乱世”、“衰世”的“三世”演化⑨;就社会文化史的长时段而言,“主张向前、向上的变化,也就是承认历史的进化、发展的思想”,这在龚自珍的历史认识中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⑩。在龚自珍看来,人类历史按“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的形式不断进化:“在所传闻世(引按:即‘据乱世’),人伦未明”→“在所闻世(引按:即‘升平世'),人伦甫明”→“于所见世(引按:即‘太平世’),法为太平矣”;“通古今可以为三世,《春秋》首尾,亦为三世”(11)。 二、重“心”尊“情”的人本史观 龚自珍认为,世界及其历史是由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或“众人”所创造的;“我”(自我意识或主体意识)是创造和推动世界的终极性力量。 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龚自珍写道:“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12)龚自珍认为,有记载以来的社会历史生活存在三种形态,即治世、乱世和衰世;而每一种社会历史生活形态的区分和转换,以人的发展状态(“才之差”)或“人才”(“才士与才民”)的生存状况作为根本标准甚至唯一标准。龚自珍继续写道: 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忧不才而庸,如其忧才而悖;忧不才而众怜,如其忧才而众畏。……三代神圣,不忍薄谲士勇夫而厚豢驽羸,探世变也,圣之至也。(13) 龚自珍认为,要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人才”的生存状况为依据,“探世变”,把握、区分社会整体的生存状态。龚自珍所谓的“良史之忧”,是仁人之忧(“良史者,必仁人也”(14)),是“去慰苍生六月天”、“夜闻邪许泪滂沱”、“三更忽轸哀鸿思,九月无襦淮水湄”的人文情怀,是“黔首本骨肉”的“悲辛”和“感慨为苍生”的“歌哭”,是“苍生气类古犹今”的“幽情”,是“九州同急难”的“怃然心”,是“攘臂定礼乐”的“血性”,是“既窥豫让桥,复瞰轵深井”的“剑侠”心或“江湖侠骨”,是对传承“前古之礼乐道艺”和担负“救弊”、“修废”、“革穷”等社会历史使命的“人才”生存状况的极度关怀——“忧不才而庸”和“忧才而悖”。龚自珍所谓的“良史之忧”,“不是等闲凄恨”(15),而是“无涯之忧”,是“总是忧道,非为冷热忧矣”(16)。龚自珍所忧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生活状态和基本生存之道,是“今中国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黄河日益为患”的社会生态大格局,是“才士与才民出,而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的不良社会文化习俗,是“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的压制人性的社会政治制度。 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初一日,龚自珍在《上大学士书》中写道:“自珍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17)。龚自珍认为,历史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创造或改造文化(特别在思想和制度层面上)依靠的是“人才”,历史创造活动是以“人”或“人才”为根本的。龚自珍“受三千年史氏之书”而后得出的结论是:“人才”或“人才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历史发展的标志,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理想价值。所以,龚自珍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写道:“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王者欲自为计,盍为人心世俗计矣。”(18)龚自珍认为,“人心”可以改变“世俗”,“世俗”可以转移“王运”。因而,从总体上看,龚自珍认为,历史变化的根本因素则在于人心(19)。龚自珍是一个极其崇尚“心力”的人,“把改造‘人心’看作是改造社会的根本,以为变法改制的关键在于提倡一种精神力量”(20)。笔者以为,龚自珍心目中的“人心”,可以包括“众人”之心或“民心”(21),但更主要的是“君子”、“人才”或“豪杰”之心。在《尊隐》等文中,他以“君子”、“人才”或“豪杰”的取舍、出处、穷达作为主要依据,来判断某一特定朝代处在“蚤时”、“午时”或“昏时”,来判定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处于“治世”、“乱世”或“衰世”。 龚自珍说:“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又说:“大兵大札,起于肉食。大亡大哀,起于莞簟。大薄蚀,大崩竭,起于胶固。”(22)在这里,龚自珍既从正面强调“心之力”、“哲人之心”的历史作用,又从反面说明“寄生精神”、思想—制度的僵化是社会历史大灾难的根源。 龚自珍大声呼唤“尊情”。狭义的“情”,是人们对外界事物的主观态度和内心体验;广义的“情”,就是“真”(23),就是完全的精神世界、完全的生命、完全的人生。龚自珍倡导“尊情”,即尊“真”,就是尊“真心”,尊“真我”,尊“真人”,尊“完全的人”;真的情,不限于理性,更不限于主流意识形态或官方正统学说,而应包括非理性,包括正统学说和官方意识形态(流行的支配性世界观)之外更加广阔的主体生命世界,以及主体生命过程中“我”与周围环境世界的真实、鲜活的关系。 龚自珍劝告人们要警惕重“事”轻“心”、重“迹”轻“本”的传统史学。他说:“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24)龚自珍吟道: 我读先秦书,莱子有逸妻。闺房以逸传,此名蹈者希。勿慕厥名高,我知厥心悲。定多不传事,子孙无由知。岂但无由知,知之反涟洏。羞登中垒传,耻勒度尚碑。一逸处患难,所存浩无涯;一逸谢万古,冥冥不可追。示君读书法,君慧肯三思?(25) 这里的“读书法”,即是读史法。龚自珍教给后人的“读书法”或“读史法”,就是要寻求历史中“名”或“事”等表象背后的真心、真情。 有学者指出:“对语言的不信任,是龚自珍的特性。”(26)被时人推为“天下善言文章之情者”(27)的龚自珍认为,人心深处最可贵、最美妙的感情,是无法用言语、乐器等外在工具来表述的。他说:“前哲有言,古今情之至者,乐器不能传,文士不能状,意者然乎?嗟嗟!感前修之易沦,眷华士之踵起,名满天下,才啬于命,情又啬于才。”(28)在人类生活历程中,“人才”是十分宝贵的;在“人才”的精神世界中,“真情”、“至情”、“异梦”、“春心”、“童心”,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人的内心世界、情感状态是极其复杂的,不是传统经学也不是既有史学所能完全涵盖的。 龚自珍十分注重历史长河中人类个体生命当下的直接体验——“心情”、“哀乐”。人类个体生命在特定历史时刻所表现的“心情”、“哀乐”,是人类历史生活内容的内在基本构成,是人类历史演化发展的内在主要动力,是人类历史演化发展的内在基本体现,也是人类历史理想价值实现的内在主要尺度。龚自珍吟道:“千秋万岁名,何如小年乐?”(29) “万千哀乐集今朝”、“歌泣无端字字真”的龚自珍向我们表明,完整的历史,既要见事,也要见心;既要见“迹”,也要见“本”;以史见“我”,即见“我”的“童心”,见“人”的真心或“哀乐万千”。这样的历史才是人的“心迹尽在是”(30)的历史,才能体现人类生命的完整轨迹,才称得上是人类生活全史,乃至人类的完全历史。 三、“出史入道”的史学观 通过阅读《古史钩沉论二》(道光五年初稿,道光十三年定稿),我们可以看到,龚自珍具有广义的文化史观,认为社会历史生活实践是人类文化的源泉,史学是民族文化的根本;“史”是“天”、“地”,各家学说是天体、江河。龚自珍说:“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31)广义的“史”,包括整个人类文化、社会文明。 在龚自珍看来,主观的历史(亦即历史学),既是对实际发生过的人类生活客观过程的记载和说明,也是对人类生活过程中蕴涵的文化精华、文明核心、“道”的探寻和阐发。 龚自珍说:“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诂训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32)“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含义丰富(33)。龚自珍所说的“圣人之道”,即是“众人之道”或“人道”(34),是“众人”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适当生活方式,是主体需求(需求的自觉则是理想价值)和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相作用、相交融的产物,是支撑人生实践、规范人生运行的理想价值、生存智慧(包含对人类历史事实及其因果关系的认知)、行为规范、合理制度,等等。 龚自珍认为,人们要“通乎当世之务”,发现生活问题,制定现实对策,探索“人道”或“万亿年不夷之道”(35),规划未来蓝图,必须借镜“前古之礼乐道艺”(36),依托人类历史文化中蕴涵的“富”、“寿”、“仁”、“和”等理想价值和“实事求是”、“穷变通久”等生存智慧,借鉴人类生活过程中生成的行为规范、合理制度等。 龚自珍诗中有语:“稽古有遥源,遵王无覂轨。”(37)他认为:“不有前事,圣将安托?”(38)即主张“史氏之书”是进行现实批判、理想阐述和实践创造的必要基础。 龚自珍写道:“史之百王,仁不仁之差,大端有三:视其赋,视其刑,视其役而已矣。”(39)可以说,“心仁事简”是龚自珍通过观察历史后获得的关于政治生活的根本理想价值。所谓“心仁”,就是“仰体上天好生之德”(40),“仁心为质,施于有政”(41),追求天下人民的安康幸福;所谓“事简”,就是统治者的施政措施要顺合民意,简便易行。 在龚自珍看来,“霸天下之氏……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的统治方式,“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的“霸统”,不可能给社会生活提供持续稳定的政治基础,必然会导致“一姓”王朝“胤孙乃不可长”的悲惨后果(42)。龚自珍认为,一个王朝之所以“兴”,是因为能够借鉴前朝之史、“豫师来姓”以“改图”、“革前代之败”,根据“万亿年不夷之道”以“自改革”;一个王朝之所以“夷”(衰败),是因为“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龚自珍写道:“《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为黄帝以来六七姓括言之也,为一姓劝豫也。”(43) 龚自珍在《平均篇》中写道:“有天下者,莫高于平均之尚也。……大略计之,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44)根据对历史客观规律的认识,龚自珍主张用文化手段(自改革)来调节(挹注)历史生活中的自发性及其偏差或弊端,“几于平”。 龚自珍认为,必须借鉴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农宗”、“宾法”等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来矫正、改革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为社会政治秩序的长久稳定打下牢固基础。龚自珍也讨论了以“律令”或程序为本而导致的“琐屑牵制”、“苛细绳身”、“无所措术”等弊端,要求借鉴“唐、虞、三代天下无不治”之历史,进行“更法”,以“政道”或“吾意”为本,“略仿古法而行之……以救今日束缚之病”(45)。 龚自珍说:“掌故不备,无以储后史;无以储后史,则太平不文致,重负斯时。”(46)在龚自珍看来,对人类历史事实及其因果关系、演化规律的认知,对人类历史生活中蕴涵的理想价值、生存智慧、行为规范、合理制度等的了解和理解,是人们探寻适当生活方式、构建理想社会政治制度的必要知识基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47)。“道”,是从人类历史生活中提炼概括出来的人类社会的适当生活方式(特别是其中蕴涵的理想价值和生存智慧),也是改革社会政治制度、改善人类现实生存命运的基本依据和主要根基。 四、探究完全历史与追求完全生命 显然,除了主张“史必须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48),要求历史研究“涉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49)之外,龚自珍还强调“史”必须反映人的原始真情、纯朴真心以及人性的丰富复杂性(50),展示人类历史生活主体生命广阔深邃、“哀乐万千”的精神世界。 在龚自珍看来,客观的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人类生活过程,不仅包括社会群体宏观的文化或文明演变过程,还包括个体的鲜活“声音笑貌”、当下的感性“哀乐万千”以及“众人”特别是“人才”的“心情”状态。我们可以把龚自珍的历史观概括为“人文史观”。这是一种以人(人生、人性)为本、以文(文化、文明)为体的历史观:既须努力说明每一时代“众人”特别是“人才”的丰富欲求情思、完整生命体验、完全生命过程,又要致力于探究作为人类社会生活载体、人类群体实践成果的“文化”或“文明”的古今损益、历史演变。 龚自珍一方面强调人类生活的客观性,尊重人类生命的多样性和人类生活的整全性,另一方面则高扬史家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强调史学应揭示“人道”以改善人类生存命运的社会实践功能。龚自珍认为,历史学或历史学家应该立足于历史事实的沃土中,积极汲取人类生命茁壮成长的营养,探索、阐明一条“引而上”、“引而之于旦阳”(51)的历史“大道”,发现、确认一条使世世代代的人的生命更饱满、更完全的历史“大道”。所以,在龚自珍看来,主观的历史(亦即历史学)应该“出史入道”,不仅记载和说明实际发生过的人类生活客观过程,还要探寻和阐发人类生活过程中蕴涵的“道”。 在龚自珍心中,研究历史,既为了说明历史真相(“善入”以著“实录”、言历史生活主体之“哀乐万千”),又为了确认、表达人生理想(“善出”以说明社会整体联系、点评历史人物表现、发表史家“高情至论”);既为了揭示人生的真理(“道”),也为了关注、改善人类的命运(“变通”、“挹注”、“改革”、“更法”、“救弊”、“修废”、“革穷”、治“病”、“请定后王法”;“被润泽而大丰美”,“宇宙愈清明”)。而全面深入研究历史和充分发挥史学功能的首要前提,是历史学家“自尊其心”,即高扬史家的主体性,确立史学的独立性。 龚自珍既强调“先小而后大”、“先有下而渐有上”、由“据乱”至“太平”的人类发展变化的客观历史过程,也注重说明以“人”为本、以“我”为主、以“心”为原、以“情”为尊的历史真实(理想)状态,特别重视追求历史中的“真心”,渴望探寻历史中的“至情”,珍视人的原始真情、纯朴真心,进而揭示人类的完全生命,还原人类历史的完全真实。 龚自珍十分注重揭示被“失其情,不究其本”的官学偏见或主流意识形态掩盖的历史真相。例如,在《京师乐籍说》一文中,龚自珍深刻地揭露了唐、宋、明等王朝专制统治者“箝塞天下之游士”的“私举动”、“阴谋”,揭示了普遍存在但“论世者多忽而不察”的专制政治之历史真相。龚自珍还指出,即使像商汤这样的“圣王”,“取天下……必有阴谋焉”(52)。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龚自珍揭去“盛世”或“治世”繁华的面纱,揭示了“衰世”降临且“乱亦竟不远矣”的19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历史生活真相,表达了渴望“改革”的强烈诉求。 龚自珍自称,“心史纵横自一家”,“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受三千年史氏之书”、“掌故罗胸”的他希望用一颗既真且爱的“童心”,去感受,去爱憎,涤除历史文明污垢,澄明人类生活的理想价值;凭借通古今之变的生存智慧、史家眼光,去观察,去明辨,探寻社会危机、国家衰亡和生活困境的解决方案。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历史环境中,龚自珍重新高举起“人道”理想大旗,以冲决社会文化的“束缚”网罗,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追求人的更完全生命,为中国近现代改革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53)。 “奇计定无宾客献,冤氛可顾子孙殃?”(54)龚自珍深刻地感受到19世纪前期中国全面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预言将会有“山中之民”之“大音声起”。面对深重危机,龚自珍极力倡导“尊心”和“尊史”,特别强调社会急需作为历史文化传人、社会文明种子、超越朝代世运的载道者、“王者”良好地履行职能之必备人才的“宾客”或“史材”(“宾”与“史”,“异名而同实者也”(55))的迫切性。 龚自珍认为,君子应该以“史”为“本”、为“根”,以“宾”自处。“宾籍阙”,是秦汉之后制度的重大缺失。所以,他倡导“尊宾”。“尊宾”,亦即“尊史”;反过来说,“尊史”,也就是“尊宾”。所谓“尊史”,就是尊重历史之生活真相、真实因果、客观规律,尊重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理想价值、基本生存智慧,尊重历史学家“实事求是”、“惟其是而已”的独立精神,即“向封建统治者争取史家应有的人格尊严与思想、言论的自由权”(56)。 虽然极力倡导“尊史”,主张史家应“自尊其心”,但在历史书写褒贬必须遵从帝王已定的“公论”(57)及大兴文字狱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避席畏闻文字狱”,“团扇才人踞上游”,“剑侠千年已矣”,龚自珍梦想的历史真相、历史规律和真理的尊严,追求的历史研究实践及史家精神之独立性,在实践中极难保持,只能“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师”(58)。龚自珍提出以“自尊其心”为核心的“尊史”思想,是对人类生存命运改善的高度期待,是对历史学自主发展的美好憧憬和坚定追求,也是对造成“万马齐喑”局面的专制制度的血泪控诉和理性批判。 虽然“苦不合时宜,身名坐枯槁”,内心充满“关山风雪怨”,但由于“铁石心肠愧未能”,生活在19世纪前期的龚自珍,一方面正视、揭露充斥“诈伪”的“衰世”现实,另一方面坚持“童心”,倡扬“白日青天奋臂行”的理想精神。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价值理想,在于破除妨碍每一个人发展的外在“束缚”,形成“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的“天地国家”,使每一个人都拥有更加自由的生活、更加完全的生命,使人的生存命运不断得到改善,每一个人都成为“全者”、“完者”。历史学家研究和撰写历史,应该有助于人类历史生活理想价值的实现。 由于社会公共空间基础的欠缺以及“诈伪”文化和专制制度的压迫,龚自珍对完全生命的追求最终“只梦堕天涯”。然而,龚自珍对人类社会“文致太平”(通过文教来实现太平)的美好前景的描绘,对养育完全生命的“天地国家”的憧憬,以及他追求的“求事实”、“探世变”、“知大道”、图“劻济”之“史”,大力倡导的“自尊其心”、“忧天下”、“志为道”具有“高情至论”、肩负“造就人才”崇高使命、推动养育完全生命的“天地国家”之形成的史家、史学,虽然不具备“诸国并立并争”、工业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追求等“近代”历史内涵,也不具有“国民史学”之类的“近代”史学特征,还不可能看到“史学近代化的轨迹”,但龚自珍的历史观和史学观针对人类生活和历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卓越见解,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对人类史学的发展,对拓宽历史学的领域,使历史学更富有人性,具有长远的借鉴意义。 ①《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页。 ②《龚自珍全集》,第41页。 ③《龚自珍全集》,第193页。 ④“先有下而渐有上之义”,是陈奂为龚自珍《农宗》所写批语。参见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43页。 ⑤《龚自珍全集》,第4页。 ⑥《龚自珍全集》,第100页。 ⑦《龚自珍全集》,第308页。 ⑧《龚自珍全集》,第86~88页。 ⑨《龚自珍全集》,第6页。 ⑩裴大洋:《试述龚自珍的社会历史观》,《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11)《龚自珍全集》,第47、48页。 (12)《龚自珍全集》,第6页。 (13)《龚自珍全集》,第7页。 (14)《龚自珍全集》,第334页。 (15)“不是等闲凄恨”是龚自珍词之属和者之语。参见《龚自珍全集》,第572页。 (16)《龚自珍全集》,第435页。 (17)《龚自珍全集》,第319页。 (18)《龚自珍全集》,第78页。 (19)蒋大椿:《龚自珍历史认识思想略探》,《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20)丁桢彦:《龚自珍历史哲学浅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3期。 (21)龚自珍1818年秋在应乡试的文章中写道:“我国家承平数百年,其所以蒙恺悌之庥,而奠灵长之福者,大都不越士气与民心二端而已。”他指出“民事不可缓”,“以民事为国本”,“不知亟民事,则国不立矣”;强调“民知忧则君忧其忧,则无倾”,“民知乐而君乐其乐,则弗替”(《龚自珍全集》,第601~602页)。 (22)《龚自珍全集》,第15~16页。 (23)“民生地上,情伪相万万”及“今……失金之情”中的“情”,就是“真”。《龚自珍全集》,第233、1页。 (24)刘逸生等注:《龚自珍编年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138页。 (25)刘逸生等注:《龚自珍编年诗注》,第258页。 (26)Shirleen S.Wong,Kung Tzu-chen,Boston:G.K,Hall & Co.,1975,p.87. (27)《龚自珍全集》,第199页。 (28)《龚自珍全集》,第200页。 (29)刘逸生等注:《龚自珍编年诗注》,第244页。 (30)《龚自珍全集》,第241页。 (31)《龚自珍全集》,第21页。 (32)《龚自珍全集》,第193页。 (33)韦政通:《中国哲学辞典》,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571~575页。 (34)龚自珍说:“先王以人道序天下。”《龚自珍全集》,第232页。 (35)《龚自珍全集》,第5页。 (36)《龚自珍全集》,第28页。 (37)刘逸生等注:《龚自珍编年诗注》,第296页。 (38)《龚自珍全集》,第103页。 (39)《龚自珍全集》,第235页。 (40)《龚自珍全集》,第312页。 (41)《龚自珍全集》,第228页。 (42)《龚自珍全集》,第20页。 (43)《龚自珍全集》,第5~6页。 (44)《龚自珍全集》,第78页。 (45)龚郭清:《价值重建与制度改革——论龚自珍政治改革思想》,《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46)《龚自珍全集》,第190页。 (47)《龚自珍全集》,第81页。 (48)陈其泰:《龚自珍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80年第6期。 (49)叶建华:《龚自珍史学理论述评》,《浙江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50)例如,“在龚自珍写给灵箫的情诗里,我们经常看到诗人同时扮演着经历私情的个体与自觉的史家这样双重角色”(孙康宜:《写作的焦虑:龚自珍艳情诗中的自注》,《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51)《龚自珍全集》,第232页。 (52)《龚自珍全集》,第124页。 (53)龚郭清:《传统与现代之间——论龚自珍的文化理想》,《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龚郭清:《用质真涤荡文明——论龚自珍“童心”的意蕴和意义》,《江南文化研究》第6辑,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95~105页。 (54)刘逸生等注:《龚自珍编年诗注》,第65~66页。 (55)《龚自珍全集》,第28~29页。 (56)牛春生:《龚自珍“尊史”思想初探》,《宁夏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57)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94~303页。 (58)刘逸生等注:《龚自珍编年诗注》,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