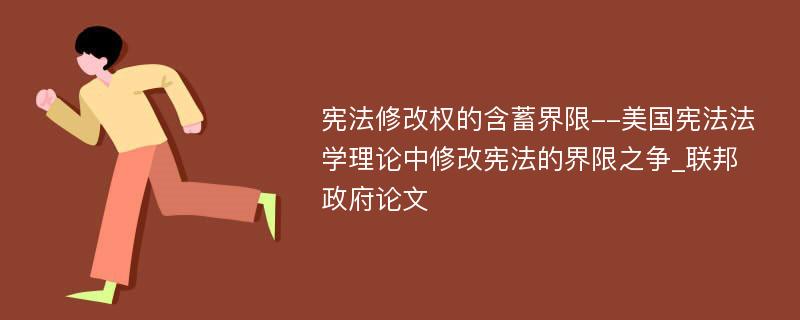
修宪权的隐含界限问题——美国宪法学理论关于宪法修改界限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法论文,界限论文,美国论文,修宪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导言
宪法修改是宪法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而修宪权的界限又是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它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① 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中文文献看, 学者们关于修宪权界限问题的探讨,大都以德国宪法理论为圭臬。② 不过值得充分注意的是,修宪权界限问题的理论渊源,其实并不在德国,而在美国。对此德国宪法学大师施密特也不讳言。按照他的研究,美国学者马伯里在191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③就提到了修宪权的界限问题。④ 事实上,远在马伯里的文章发表之前, 美国宪法学就开始了对修宪权界限问题的关注。
从宪法史的角度观察,美国1787年《宪法》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而且也是世界上首部规定修宪限制的成文宪法。按照美国《宪法》第5条的规定,在1808年之前制定的宪法修正案不得在任何方面影响本《宪法》第1条第9项第1节与第4节(这些条款主要规定了奴隶贸易不得被禁止的内容);而且无论何州, 未经其同意,不得剥夺其在参议院的平等投票权。从1787年制宪会议的情况看,美国宪法之所以在第5条规定了上述不得修改的事项,是由于各州(主要是各小州以及南部各州)对于联邦政府通过修宪侵犯州权之危险的恐惧。而从美国历史的发展看,至少从美国内战后第13宪法修正案的生效时起,联邦政府的权力日益扩张,各州自主权的范围日渐缩小,各州对于联邦政府通过修宪扩张联邦权力、“篡夺”州权有一种内在的不安。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关于修宪权界限问题的争论,无论在宪法理论上还是在宪政实践中,都异常激烈,争辩各方都提出了不少至今仍然具有理论意义的观点。
美国宪法理论关于宪法修改界限的争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并不是一场纯学术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表明态度的论辩,相反却有着极为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如果离开这个背景,就很难全面理解这场争论的意义。除此之外,美国宪法理论的这场论争与其宪政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场争论的发生、发展,并非出于某个形而上的价值或者某种先验的东西,也不是纯粹的逻辑推理,而完全是为了解决宪政实践中出现的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⑤ 因此可以说, 如果没有宪政的具体实践,恐怕也不会产生所谓的修宪权界限问题的宪法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这么说,美国宪法理论关于修宪权界限问题的争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宪法理论发展的重要启示。这或许就是研究、阐述这场争论的意义之所在。
二 奴隶制问题:修宪权隐含限制理论的初步提出
关于修宪权范围存在隐含限制观点的提出,与美国南部各州的奴隶制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这么说,美国修宪权隐含限制理论最初的出发点,就在于维护南部蓄奴各州的奴隶制度。
美国《宪法》规定的两项关于宪法修改的限制,主要反映了蓄奴州与小州的一种内在的不安。随着美国独立后的发展,南部各州的这种不安不仅没有任何消退,相反却日渐彰显。在联邦《宪法》开始运行的1790年,美国北部和南部的人口大体相当;到了1850年前后,北部人口已达1300多万,而南部只有960多万。 尤其是随着1830年前后废奴主义的出现,南部各州“对北部多数的这种担心像南部沼泽地中的植物一样迅速成熟起来”。⑥ 最令南部各州政治家们担心的, 就是随着北部各州实力的增长,使得他们能够争取到占全国四分之三的州,进而通过一项解放奴隶的宪法修正案,而这对于南部各州无异于“一种世界末日般的灾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治家、政治学家约翰·卡尔霍恩提出了为奴隶制辩护的州权理论,并且在为之论辩的过程中,初次提出了修宪权的范围问题。尽管卡尔霍恩关于修宪权存在隐含限制的观点还不十分明确,但他的观点的确是一个理论观念的开端,并在后来得到了宪法学家的进一步论证。
(一)卡尔霍恩关于修宪权范围的论说
卡尔霍恩是美国一个著名的奴隶制度的辩护士。⑦ 为了使南部各州的奴隶制度免受北方各州多数的干预,他又是州权理论的一个积极鼓吹者,这构成了其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美国早期的政治理论认为,合众国中存在一种分割的主权:各州在某些事务上享有主权,而联邦则在另外一些事务上享有主权,它们各在其领域内享有至高的地位。这个理论在美国制宪当时十分流行,而麦迪逊则是其卖力的鼓吹者。按照《联邦党人文集》的解释,联邦宪法的制定并没有把各州降低到省的地位,而是让它们拥有“某些独有的、非常重要的主权”,保有“一切未被宪法授予合众国的主权”。⑧ 这种理论也被联邦最高法院接受。在1793年奇泽姆诉乔治亚州⑨ 一案中,最高法院宣称:合众国对各州实际交出的一切权力享有主权;联邦每个州对所保留的一切权力享有主权。然而,对于卡尔霍恩而言,分割主权论是不可接受的,他认为分割主权就是破坏主权,主权要么完整,要么为零,一半主权一半非主权的州是不存在的。他认为,各州原来是,将来也是完全的主权者。因此,在美国联邦宪法之下,联邦政府虽然以主权国的资格行事,但它并不是主权国,它仅仅因为合法的主人——州——的默许才具有权威。⑩ 按照卡尔霍恩的观点,奴隶制是南部各州主权范围以内的事项,不允许联邦政府干预。如果联邦政府——实质上乃北部自由州——想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干涉南部各州主权范围之内的奴隶制度,那么,联邦政府就超越了权限。
在1832年8月28日给汉密尔顿将军的一封信中, 卡尔霍恩集中表达了他对修宪程序以及修宪权范围的观念。在他看来,修宪程序的一个主要功用就在于在联邦政府被授予的权力和各州保留权力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尽管他承认各州也有篡夺联邦权力的可能,但他认为联邦篡夺州权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联邦对州权的篡夺有违国家体制的基本原则——各州自治的权利。当联邦政府通过宪法修正案授予联邦一项有争议的权力时,卡尔霍恩认为,各州有权判定该宪法修正案是否源于修宪权的范围之内。如果该修正案超越了其范围,那么,各州就有权退出联邦。(11) 在卡尔霍恩看来,对宪法修改的限制,除了《宪法》第5条的明确规定外, 还有其他隐含限制的存在,而南部各州的奴隶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北部各州不能通过修改宪法来废除南部各州的奴隶制度,否则南部各州有权退出联邦。
美国奴隶制度的解决,最终依靠的是战争方式,这被称为“内战修宪”。不过,卡尔霍恩为维护奴隶制而提出的宪法修改隐含界限的思想,却并没有消失,相反得到了宪法学家的进一步论证和发挥。
(二)库利的理论
为了维护南部各州的奴隶制度,卡尔霍恩提出宪法修改不能无限制地进行。不过,在宪法理论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修宪权隐含界限概念的,却是宪法学大师托马斯·库利(Thomas Cooley)。库利在1871 年首版的《宪法性限制》一书中明确提出,修宪权有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不能通过修改宪法而废除政府的共和体制,因为这种行为带有革命的性质;二是任何对宪法的修改,都不能建立贵族名号,或者意图违反任何契约责任,或者通过溯及既往的法律剥夺公民的权利和财产,或者授权行使其他为联邦宪法明确和隐含禁止的行为。库利声称,如果权力机关滥用权力,进行了有违上述限制的宪法修改,那么,拒绝执行,以及进而将它们宣告无效,就是联邦或者各州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12)
1893年库利发表了《联邦宪法的修改权》的著名论文。他在文章中宣称,《宪法》第5条所规定的不可修改条款并不是排他性的, 因为还存在着其他对修宪权的宪法限制。这些宪法限制尽管没有被宪法明文规定,但它们实质上比明文规定的限制更加重要。在对美国《宪法》第1到第15宪法修正案的内容进行考察后, 库利认为,这些修正案的一个共同特征,就在于它们都在进一步扩展民主原则的大方向上,而民主原则是美国宪法的基础。因此,将来的宪法修正案必须符合这个大的原则。库利进而认为,下列四种所谓的宪法修正案实质上是违宪的宪法修正案:一是试图将部分从联邦整体分离出去的修正案;二是试图建立贵族制度的修正案;三是试图在各州采用不同税率的修正案;四是试图建立君主制的修正案。按照库利的观点,与其说这四种修正案是对美国宪法的修改,还不如说它们实际上是对“美国宪法的颠覆或者是革美国宪法的命”。按照库利的观点,这种关于修宪权的隐含限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即使宪法不将它们明文规定,它们的存在也是理所当然、不需要论证的。
库利打了一个简单的比方,解释制宪者当年为何没有明文规定这些更重要的、隐含的对修宪权的限制:“果树的所有者并不需要明确宣告,以禁止其雇员给苹果树嫁接金缕梅或毒漆树。这种禁止实是由一种更高的律法来宣布的,在这种更高律法的力量之下无须画蛇添足。”(13)
在这一时期,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由于它并没有具体判定任何一条实在的宪法修正案或修宪提案超越了修宪权的隐含界限,因而完全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辨。不过,在随即出现的有关美国第18、19宪法修正案效力的论战中,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第一次被运用到宪政实践之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 州权:美国宪法第18、19修正案效力之争论
20世纪的前20年,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时代”。在此期间,美国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联邦政府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在这些社会性改革运动中,禁酒以及妇女选举权运动似乎更为引人注目,因为它们不仅持续时间长久,并且最终写入了联邦宪法,成为全联邦的目标。
在美国,禁酒问题由来已久。在19世纪后期,酒精制品的泛滥已经成为令美国社会头疼的问题,禁酒运动应运而生。“一战”的爆发更助禁酒运动一臂之力,因为人们不希望士兵成为酗酒者,也不想让作为战略物资的粮食过多地转化成酒精。(14)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会于1917年12月18日提出了禁酒修正案,禁止在美国境内制造、出售、运输足以致醉的酒类,并提交各州议会批准。在国会提出修正案13个月后,该修正案得到了全联邦36个州议会的批准而宣布生效。而到1922年3月,除了伊利诺斯、印第安纳以及罗得岛之外的其他州先后都批准了该宪法修正案。似乎可以这样说,在美国当时,禁酒修正案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足以引起广泛争议的大问题。因为美国许多州都先后制定了禁酒的法律,有的还写入了州宪法之中,“禁酒修正案”不过是将各州的做法在全联邦推行而已。(15)
与禁酒运动相比,女权运动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更是风起云涌。实际上,“社会正义、禁酒和其他改革运动的大量推动力来自妇女”。(16) 1890年, 美国的劳动妇女只有400万,而1910年就增长到接近750万。妇女经济力量的壮大,使得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成为当时进步总震荡的重要组成部分”。(17) 在1900年,美国只有怀俄明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州给予了妇女选举权。而到了1910年,当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赋予妇女选举权时,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已是势不可挡。在1920年之前,美国已有多个州先后通过公民复决赋予妇女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18) 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力主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赋予妇女平等的选举权。1919年6月4日,投票权修正案终于得到国会两院的通过,提交各州议会批准,并于1920年8月26日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而生效。
作为“进步时代”的产物,就这两条宪法修正案的内容而言,它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然而,正是这两条从内容上看似乎并不起眼的宪法修正案,在主张修宪权隐含限制的学者看来,却显示了这样一种危险,即,相对较小但具有高度组织性和决心的少数,却可以促使各州议会批准有违于“国家多数人民情感与愿望”的宪法修正案。(19) 如果修宪权没有任何实质限制,那么,在《宪法》第5条的机制下,仅仅1300人就能够破坏这个国家人民的基本自由。(20) 为了消除这种危险,就必须对修宪权施加实质性的限制。在不长的时间内,不仅有不少学者撰文抨击这两条宪法修正案超越了修宪权的有效范围,而且还有人在法院对它们的合宪性提出了挑战,从而引发了美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关于修宪权隐含限制问题的论战。
在某种意义上,这场论战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禁酒或者妇女选举权问题本身,反对者实有醉翁之意。实际上,在反对者看来,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该不该禁酒,或者该不该赋予妇女平等选举权,而在于该不该由联邦政府宣告禁酒以及赋予妇女选举权。在他们看来,禁酒以及妇女选举权问题,都属于各州自治权的内容,不能由联邦政府干预。(21) 实际上,在1914年众议院第一次对禁酒修正案辩论时,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意见就是,禁酒问题属于各州自治的范围,由联邦政府管理禁酒有违于美国的联邦体制。(22) 同样,主张妇女选举权属于各州自治范围的也大有人在。实际上威尔逊总统以前就曾是一个妇女选举权的反对者。他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声称,妇女选举权问题是各州自主的事务,不应由联邦政府干预。(23)
更令州权主张者忧心忡忡的是,这两个宪法修正案将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及到它原来从未到达的领域,而这似乎是一个危险的开端。正像美国学者大卫·E.凯韦格所质问的那样,如果联邦政府可以被赋予干预诸如饮酒等极具私人性质事务的权力,那么它是不是能够和应当承担社会其他方面的责任呢?如果联邦政府可以干预选举中的性别歧视,那么它是不是也可以干预其他新的领域呢?宪法第18、19修正案的一个结果,就在于它们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联邦政府职责的重新界定和扩展问题。(24) 因此,州权才是实质之所在,州权才是目标,而修宪权界限不过是为州权辩护的一个论题而已。在这里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美国宪政史上的一个永恒话题:联邦与各州权力的消长与平衡。
为了论述的简便起见,本文将按照争论的具体内容,分别阐述修宪权隐含限制论辩双方的观点及其理由。
(一)美国宪法是否存在对修宪权的隐含限制
修宪权隐含限制理论认为,对修宪权的限制并不局限于《宪法》第5 条的明确规定,实际上,任何宪法修正案的内容都受制于两个方面:明确的限制和固有的限制。这种理论的一个观念是:修改宪法的权力,并不包括毁弃宪法的权力在内。按照《宪法》序言的表述,美国宪法的目的,就在于为了“建设更完美的联邦”,宪法的修改当然不能偏离这个方向。(25) 相反,假如修宪权没有任何固有的限制,只要四分之三以上各州愿意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很多荒谬绝伦的情形,比如说分割整个联邦、废除各州政府、废弃三权分立而将所有国家权力集于国会、改变国家的共和政体而建立君主体制、废除法院以及总统、任意合并各州或者从各州分离出新州、取消个人的权利及自由,等等。如果这一切出现的话,那将是整个宪法的毁灭。(26) 因此,任何对宪法的修改,都必须被设计用来更好地贯彻实施制定宪法欲以达到的目的。因此,不能说除了《宪法》第5条的限制以外, 修宪权就可以畅通无阻,实际上美国《宪法》自身就隐含了对修宪权的若干重要界限。
反对修宪权存在隐含界限的观点认为,除了《宪法》第5条规定的明确限制外,国会可以提出任何内容的修宪提案,各州也可以批准任何内容的宪法修正案,换言之,修宪权不存在任何所谓的隐含界限。这种观点认为,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不仅没有任何宪法上的依据,而且这种理论也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危险的。主张修宪权存在隐含界限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如果不对修宪权施加实质性限制,那么修宪权就可能被滥用。不过,这种推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任何国家权力如果到达其极端,都将导致荒谬和灾难性的后果。(27) 正像联邦最高法院反复宣称的那样,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不能被用来作为否认该权力存在的理由,比如说联邦征税的权力极有被滥用的可能,但它并不妨碍征税权的存在。同时,修宪权与其他国家权力有所不同。即使所谓的“滥用”发生,它也是发生在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组织、实质上也就是人民之手。除非认为美国人民不是主权者,他们没有改变其基本政治体制的权利,而且他们被一撮所谓的先知先觉们——他们知晓或自以为知晓美国人民的根本福祉——所竭力防范,否则,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人民享有修改宪法的全权,不受任何所谓隐含限制的制约。(28)
另外,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在于,给修宪权施加外在限制是非常危险的。主张修宪权隐含限制的人们常常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宪法的变动并不由简单多数,而是由四分之三以上各州的多数决定。毫无疑问,如果仅仅是由简单多数决定宪法的修改,那么法院可以对宪法修改的程序以及实质问题进行审查。但是,当四分之三以上的绝对多数通过仅次于革命的修宪程序表达其愿望之际,司法的介入是相当危险的。法院当然有执行法律之权,但法院也不会冒与立法、行政以及广大人民相冲突的危险,去宣布某条宪法修正案无效。(29) 实际上,由法院通过解释宪法的方法,挖掘宪法之中暗含的对修宪权的实质性限制,并进而对宪法修正案的效力做出判定是极不明智之举,因为这等于迫使法院进入了一个本质上是政治性问题的地带。(30)
(二)“修正案”的概念是否暗含着修宪权的界限问题
主张修宪权隐含界限的理论认为,“修正案”概念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界限。这种观点认为,修改宪法的含义,在于改变宪法中已有的条文,而不是增加新的规定。
这种关于“修改”概念的理解,实际上很早就出现了。在1909年,为反对第15宪法修正案,法官莫里斯就提出并阐述了“修改”与“附加”之间的区别。他认为,“修改”与“附加”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附加”是给宪法增添一种全新的、与原宪法文本不相关的东西;而“修改”是对宪法原有条文的一种变动或者改进。按照他的观点,第15修正案实际上并不是“修正案”,而是“附加案”。“修正案”的生效只需要得到全国四分之三州的批准,而“附加案”则需要得到联邦各州的一致批准才能生效。他质问说,假如一切对宪法的“附加”都可以假冒宪法修正案之名而进行,那么将何以保证各州的完整及其持续存在?(31) 这种观点为许多人所接受,在后来发生的关于第18修正案效力的争论中,该观点被一再引用。
在1920年罗德岛诉帕尔玛案(32) 中,罗得岛认为,在普通法中,“修改”是一个专门法律术语,特指“错误的修正”。因此,宪法修正案就应当局限于改正宪法中存在的错误之处。在斯韦茨诉俄亥俄州案(33) 中, 俄亥俄州最高法院法官沃纳梅克(Wanamaker)质问到,在“修正案”的标签之下, 如果出现一条提议放弃成文宪法,转而采用英国或者中国宪法而不是美国联邦方案的修宪提案,难道这个提案也可以被合乎逻辑地当作是符合制宪者原意的“修正案”,进而被有效批准吗?在菲贞斯潘诉博丁案(34) 中,上诉人认为,宪法修正案与普通立法在形式上是有区别的:对于禁酒这个目的而言,一条授权政府禁酒的宪法修正案与直接宣告禁酒的所谓“修正案”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前者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因而是宪法修正案的“适当形式”,而后者既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减政府的权力,因此它仅仅是一种直接的立法。《宪法》第5条只是授权国会以及四分之三以上各州通过宪法修正案,而不是授权它们直接立法。由于第18宪法修正案宣告直接禁酒,因而恰恰是一种直接立法,是无效的。
反对者认为,按照《宪法》第5条的规定,“修改”的概念并不是那么狭窄。在多数人看来,“修改”概念不仅包括改动已有的规定,同时也包括增添或者附加全新的、哪怕是与原宪法没有任何关系的规定。在前述菲贞斯潘诉博丁案中,新泽西州联邦地区法院认为,美国宪法中的词汇并不像通常的那样只有一种狭窄的、收缩的含义,相反却应当在一种宽广的含义上被运用。“修改”概念的含义,不仅包括修改已有的条文,而且也包括“附加”新的规定。按照有的学者的看法,如果“修改”的含义只是包括对原有条文的“变动”,而不能增添新的规定的话,修宪程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义。更有学者认为,在“修正案”的形式之下,国会完全可以提出一个全新的宪法草案。这看起来虽然有点特别,但似乎不存在国会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的法律障碍。因为《宪法》第5条并没有限定修正案的数目、性质以及是否具有可分性。(35) 不过,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就是,美国第一届国会提出的“权利法案”,实际上就是“附加”性的规定,而不是对宪法原有条文的变动,因为宪法原先并没有什么与“权利法案”相关的条文,而“权利法案”的效力是毋庸置疑的。(36) 这个历史事实说明,所谓“修正”与“附加”有别,进而主张“修正案”概念本身就是修宪权隐含界限的观点是不妥当的。
针对主张宪法第18修正案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直接立法,因而应当无效的观点,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休斯(Hughes)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认为,按照上述论点,宪法修正案只能等待法律的具体化后才可以实施;宪法修正案只能通过法律的具体化后才能影响个人的权利,这是荒谬的。实际上,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就是一条能够自我实施,不需要国会立法实施的典型,该修正案直接废除、而不是授权联邦政府废除了奴隶制度。(37) 既然《宪法》第13修正案是有效的,那就不能说第18修正案是无效的。
(三)各州保留的警察权是否构成修宪权的界限
主张修宪权隐含界限的理论认为,联邦政府无权通过宪法修改侵害各州的保留权力。具体地说,联邦政府不能通过修改宪法,把本质上属于各州警察权范围内的事项划归联邦管辖。为各州所谓的警察权进行辩护,实际上是这一阶段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鼓吹者的重要目的。在这方面,主张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的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他们认为,美国宪法的联邦体制不允许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改变各州与联邦之间的权力划分,更不许可单方面减少各州的警察权。在菲贞斯潘诉博丁案中,上诉人声称,在美国制宪当时,制宪者们所思虑并且为美国宪法所隐含的一个原则就是,各州具有主权并且在地方性事务上有自治权。因此,任何危及或者倾向于直接破坏各州地方自治权的宪法修正案,都与联邦宪法的意图和精神相互冲突而必然无效。在罗德岛诉帕尔玛案中,上诉人也主张,各州自主的警察权构成了修宪权的隐含限制,因此,“国会不可以合宪性地提议,各州议会也不能合宪性地批准任何事关各州主权之行使或者放弃各州主权的修正案”。
他们同时以州权为理由攻击《宪法》第18、19修正案的效力。他们认为,宪法修正案实质上分为两种,一是有关联邦机构变更的,一是关于人民自由与权利的。对于前者,各州议会可以做出有效批准,而对于后者,则必须由人民——通过州宪法会议——行使批准权。显然,第18宪法修正案并不涉及联邦机构的变更,而与人民的权利与自由紧密相关,并且,它是一个把人民保留的权利转让给联邦政府的修正案,实际上扩大了联邦的权力。而按照《宪法》第10修正案的规定,凡宪法未授予联邦,亦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一律由各州或其人民保留。制宪者当年将《宪法草案》提交各州宪法会议而不交各州议会批准,就在于制宪者认为各州议会无权把人民的保留权利转让给联邦政府。既然各州议会在制宪当时无权转让人民的权利,现在也就没有权力批准出让人民权利自由的修宪案,因此第18修正案是无效的。(38) 对于第19修正案,他们认为,按照美国《宪法》,各州是享有自治权的政治体,任何对宪法的修改都不能侵害到各州作为政治体的自治权。而第19修正案赋予妇女选举权,这是对各州选民条件的重大变更,使各州的选民大量增加,因此必须以各州的一致同意为前提,否则就是对各州自治权的严重破坏。基于以上理由,可以认为第19修正案也是无效的。(39)
反对者认为,各州保留的警察权不能构成修宪权的隐含界限。 他们指出, 在1787年制宪当时,在对修宪权界限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后,作为妥协,《宪法》将奴隶贸易以及各州在参议院的平等投票权作为不可修改事项写进《宪法》第5条, 而拒绝把各州警察权免受联邦干预的内容规定为不可修改事项。按照“明示其一则排除其他”的普通法格言,除了《宪法》第5条明确规定的限制外, 修宪权不应当有其他任何限制。同时,由于制宪者认为他们制定的宪法存在着种种缺陷,需要与时俱进加以修改,因此,制宪者实际上意在提供一个宽广的修宪权,而不是要为宪法修改设定若干隐含的界限。(40)
对于主张各州保留的警察权构成修宪权隐含限制的理论,反对者指出,联邦宪法的制定,实际上就是各州将其先前保留的一部分权力转移给联邦的过程,既然如此,宣称联邦不能再次从各州移转权力的观点就不能令人信服。更有学者认为,因为四分之三以上的州掌握着实质性的修宪权,约束着其余四分之一的州,所以很难说他们为什么不能通过修宪而废除某一个州、或者少数几个州、甚至整个联邦。当然,这个问题完全是个纯学术问题,不会实际发生。但应当强调的是,假如四分之三以上的州真的意图通过修宪而毁掉整个联邦,那将并没有任何法律障碍。(41) 既然各州都可以被修宪权“修掉”,各州保留的所谓“警察权”就更不在话下了。
在主张宪法修正案不应当干预各州保留的警察权的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站在反对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的一方,驳斥了认为第18、19修正案无效的观点。在合众国诉斯普雷格案(42) 中,最高法院认为,联邦与各州权利的划分,可以用修改宪法的方法予以变动。如果说第18宪法修正案涉及人民保留的权力,需要各州宪法会议批准的话,这不但于法无据,而且三个“内战修宪案”都是关于人民保留权利的修正案,同时也都是由各州议会批准的。既然“内战修宪案”的效力没有任何问题,那么第18修正案也应当是有效的。在利泽诉加尼特案(43) 中,最高法院认为,第19修正案与第15修正案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两个修正案的批准方法也是一样的。虽然有若干州反对,但第15修正案生效已达半个世纪。在这种情形下,既然第15修正案是有效成立的,自然不能说第19修正案是无效的。
(四)“权利法案”是否构成对修宪权的实质限制问题
主张修宪权隐含界限的理论认为,“权利法案”是修宪权的界限所在。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权利法案”以及宪法第14修正案就是被设计用来限定未来宪法修改的范围的。(44) 具体地说,就是联邦政府不能通过修改宪法而剥夺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主张,在合众国,所有政府的权力都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修宪权亦不例外。而在这一点上,宪法第18修正案的效力就值得疑问了。因为该修正案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即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试图通过宪法修改而限制人民自由的修正案。第18修正案的问题,实质上并不是酗酒与反酗酒之间的争端,而是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与政府绝对权威之间的斗争。如果个人饮酒的合法权利遭致破坏,那么整个国家的宪法也就被毁损了。实际上,对人民所保留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保护,是美国宪法恒久不变的原则,(45) 修宪权只能服从,而不是推翻这个基本原则。
反对者认为,尽管“权利法案”以及宪法第14修正案的意义重大,但它们仅仅是修正案,而不是宪法原初文本的组成部分。因此就像其他宪法修正案一样,它们也可以被一个新的宪法修正案所撤销,比如说宪法第18修正案就被第21修正案所撤销。而且,从法律观点来看,“权利法案”以及第14修正案并不比宪法文本的其他部分更加神圣。退一步说,即使承认“权利法案”是宪法原初文本的组成部分,它也并不必然构成对修宪权的限制,因为它并没有明示或者隐含地提及《宪法》第5条。实际上,《宪法》的其他条款从来没有被用以限制由《宪法》第5 条规范的修宪权。从各州法院的判例看,除了阿肯色州法院绝无仅有的一个判决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法院试图把州宪法中的“权利法案”当作是对修改州宪法的一个限制。不过,在上述阿肯色州的判决中,法院仅仅是宣告享有修宪权的州议会不能修改“权利法案”的条款,而享有修宪权的州宪法会议仍然可以这样做。这就说明,“权利法案”并不成为修宪权的隐含界限。(46)
尽管上述关于修宪权隐含界限的理论争论十分激烈,但实践却是“一边倒”的景况。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来没有宣布任何隐含限制的不存在,但在若干以修宪权存在隐含限制为由对第15、18、19修正案的效力进行合宪性挑战的案件中,最高法院毫不动摇地维护了上述三条修正案的效力。按照反对者的看法,这意味着最高法院对修宪权隐含限制理论的拒绝,也被他们当作是修宪权不存在隐含界限的一个重要理由。(47) 实际上,在修宪权隐含界限主张者的心目中,法院,至少是联邦最高法院应当成为发现、并且维护宪法隐含的修改界限的一个坚强支柱,不过,从相关的判例看,联邦最高法院的行动足以让他们感到沮丧。因为联邦最高法院似乎是一个“甩手掌柜”,它一再宣称有关修宪程序的案件都是政治性问题,司法机关不宜介入。的确,在1939年科尔曼诉米勒(48) 案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就基本上不再涉足宪法修改领域了。
四 宪法权利论:新一轮的争论
在经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争论之后,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一度沉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的终结。进入20世纪后半期,先后又有多名政治学家以及宪法学者再一次提出了修宪权的隐含界限问题,
其中尤其以宪法学者墨菲(Murphy)、罗森(Rosen)以及特赖布(Tribe)的观点引人注目。不过,在这个阶段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他们不再以修宪权的隐含界限来为州权做辩护,而是主张个人的宪法权利构成修宪权不可逾越的界限。为达此目的,“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宪法价值”等概念都被用来作为修宪权存在隐含界限的理论依据。
以个人的宪法权利作为修宪权的界限,并不是什么理论上的创新。在关于美国《宪法》第18、19修正案效力的论争中,早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观点。(49) 不过,在州权是一种主要的战斗口号和理论依据的情况下,以个人的宪法权利作为修宪权隐含界限的观点并没有占据主流位置。只是在现今,由于历史背景的变迁,在重提州权已显得不合时宜的年代,宪法学者们又拾起了个人宪法权利这根“稻草”,作为修宪权的隐含界限加以鼓吹。然而,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是,如果说前一阶段学者们关于个人宪法权利构成修宪权界限的理论多发自美国本土宪法学说的话,那么,在这一阶段,宪法学者在论争修宪权界限之际重提个人宪法权利,则更多的是受到了德国、印度等国家修宪权界限理论的影响,因而带有比较强烈的比较法意味。下面依次介绍他们的观点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关争论。
(一)作为宪法修改界限的宪法基本原则和价值
1978年墨菲发表了《宪法解释的艺术》一文,声称,宪法中的某些条款是如此根本、如此关乎人的尊严,因此试图将它们撤销的宪法修正案应当被法院宣告为无效。在墨菲看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具有这样的品格,不能被撤销,因而构成修宪权的绝对界限。墨菲推理如下:
(1)如果将《宪法》第1修正案植入第14修正案,其规定将有如下述:国会或者各州,无论是单独或者共同,均不得制定剥夺言论、出版、集会以及宗教自由的法律;
(2)宪法修正案是法律;
(3)因此,修改宪法以限制第1宪法修正案保护的权利就在国会及各州议会的权力范围之外。(50)
墨菲进而提出了三个论点为有限制的修宪权理论进行辩护。首先,墨菲借用了德国宪法法院的观点,声称宪法具有内部的统一性,每一个宪法规范受制于某些至关重要的宪法原则,因而具有从属性。在这里,对“人的尊严”的保护,是宪法价值的核心,在宪法修改时应当得到优先考虑。其次,在引述了印度法院的一个判决(51) 后,墨菲认为,美国人民所选择的宪政民主制将某些价值奉为神圣,而在这些价值体系中,“人的尊严”具有首要的重要性。与民主程序相比,“人的尊严”价值更加重要。第三,因为在宪法文本之上存在着上述重要的宪法价值、原则,因此,否认这些价值和原则的修正案必将是无效的,因为它与整个宪法体系的基本目的相互背离。(52)
特赖布教授在1982年也提出了基本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宪法并不是一个由互不牵涉的规则和标准组成的杂乱拼盘,也不是一个人们想往里装什么就可以装什么的空瓶。实际上,美国宪法体现了一系列的政治理念:代议制政体、联邦主义、权力分立、法律上的平等、个人自主以及程序公正等等。人们当然可以选择或者拒绝接受它们,也可以推翻它们,但是,只要人们还保持着对宪法的信念——只要人们是在修改宪法,而不是在废弃宪法——人们就不能简单地忽略上述宪法的基本规范和基本价值。实际上,作为整体的宪法结构和特性不仅提供了判断某一修正案是否恰当的标准,也为宪法修改施加了特定的限制。比如说,一条禁止无神论者取得联邦政府职位的修正案,就与宪法中至高无上的良心自由原则相互冲突,更不用说它在同等程度上也违背了宪法的政教分离条款。(53)
针对上述见解,反对修宪权隐含界限的学者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反对者认为,首先,墨菲关于《宪法》第1 修正案构成对修宪权的绝对界限的推理过程存在着很大的漏洞。理由十分简单,“宪法修正案”不是“法律”,修改宪法也不同于法律的制定。宪法修正案与普通立法的差异问题,联邦最高法院早在1798年的霍林斯华斯诉弗吉尼亚州案(54) 中就已经解决了。其次,在美国的宪政体制下,尽管法院有权解释宪法,但国会及各州议会或宪法会议有权“创造”宪法。而按照修宪权隐含限制理论的主张,法院将处于审查宪法修正案恰当与否的有利地位,这必将威胁到三个机关之间的微妙平衡。再次,毋庸置疑,从历史上看,代议机关的确有着采取极端措施威胁人的尊严的可能,不过,如果赋予法院实质性审查宪法修正案效力的权力,它也不是没有侵害人的尊严的可能性。回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可以轻易地找到与此相关的判例,比如说1857年著名的斯科特诉桑福德案(55),在该案件中最高法院荒谬地宣称美国宪法仅仅适用于白人——这与三个“内战修宪案”形成了鲜明对照。最后,至于所谓体现于宪法文本又高于宪法文本而存在的“宪法原则”或“宪法价值”,就简直是陷入了宪法争论的泥潭之中。即便承认它们的存在,它们也永远不能被转化为实在法的具体裁量规则,进而限定具有修宪权的国会和各州。(56) 另外,听任司法者作为“宪法原则”或“宪法价值”的保护者也是危险的,因为不存在任何办法来推翻法院因为误读“宪法原则”或“宪法价值”而做出的决定。实际上,所谓的“人的尊严”也不是绝对的,在很多情况下,至少在短期内,国家的统一要比“人的尊严”得到优先的考虑。(57)
(二)关于“焚烧国旗修正案”的违宪性的争论
美国国旗被当成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不过,在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58) 和合众国诉艾奇曼案(59) 中,联邦最高法院宣告禁止焚烧国旗的州立法违反宪法,因为焚烧国旗的行为属于“象征性言论”,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最高法院的判决立即遭到了美国国会以及政府的反对。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宣判的当天,国会参议院就以97∶3的绝对多数表达了其对该判决的不满, 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也马上发表讲演,号召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推翻法院的判决。之后不久,一条宪法修正案迅即被提交国会两院,它规定:国会和各州有权禁止物理性毁弃国旗的行为。不过,该提案没有获得两院的有效多数,最终未能提交各州批准。(60)
在国会内部展开对“焚烧国旗修正案”的讨论之际,院外有关“焚烧国旗修正案”违宪性的争论也进行得如火如荼。美国律师协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焚烧国旗修正案”将侵蚀表达自由这一最基本的权利,并将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61) 学者罗森认为,言论自由是人民保留的不可被剥夺的自然权利之一,人民不能把它转交给国家,作为人民代言人的代议机关更无权将它转交给国家。即使国会和各州议会通过一条新的宪法修正案,撤销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权利仍然受到《宪法》第9修正案的保护,并且可以由司法机关强制实施。因此, 如果某条宪法修正案侵犯了由第9修正案保护的未列举的权利,法院就应当宣告该修正案无效。(62)
反对罗森论点的人认为,罗森上述观点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宪法》第9 修正案保护的是人民未被宪法明确列举的权利,而言论自由相反却恰恰是被宪法明确列举的权利。假如罗森的推理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法院负有实施《宪法》第9 修正案规定权利的责任,那么,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法院负有强制实施其他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包括革命权的责任,而十分明显的是,革命权并不是一种可由司法机关实施的权利。(63)
反对者还指出,对于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而言,各州可能会是该理论的暂时受惠者,而该理论最终的得益者将是联邦最高法院。届时,联邦最高法院不仅将享有令人敬畏的司法审查权,而且还具有宣告宪法修正案无效的权力,即使该修正案的明确意图——就像若干生效的宪法修正案一样(64) ——在于推翻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如果这样,实际上就等于是将人民的主权移交给了法院,而这将有损于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原理。从长远看,法院的这种巨大权力必将使它脱离人民大众,而成为凌驾于它本来应当服从的制衡原则之上的太上机关。反对者认为,除了不能未经当事州同意剥夺其在参议院的平等投票权外,只要美国人民有所欲求,他们便可以进行任何方面的宪法修改。修宪程序的意义,在于防止国民因一时的情绪冲动,未经审慎思考而进行宪法修改。但是,假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民都处于一种狂热的状态,那么,即使给修宪权设置下某种障碍,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将迫使狂热的人民使用暴力手段,去取得本来可以通过宪法程序得到的某种宪法变革。在这个意义上,正像制宪者所宣称的那样,修宪程序实际上是革命的安全阀,为达此目的,如果人民意图经由通常的宪法修改程序而达其目标时,必须允许进行革命性的宪法变革。(65)
五 修宪权之隐含界限论:杞人之忧乎?
从美国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发生、发展的情况看,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各州保留的州权做辩护,成为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的一个主题。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这么说,美国宪法学关于修宪权隐含界限问题的论争,实际上不过是从美国制宪开始就发生的有关联邦与州权力消长与平衡论争的一个延续或者组成部分而已。(66)
美国宪法体现了建立强大的联邦与维护各州自主权力之间的一个平衡,美国宪法本身也不过是这两个矛盾之间的一个妥协。不过,正像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国家职能在量的和质的方面的增加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67) 美国的历史发展也呈现出联邦权力日益扩张的强烈趋向。在19世纪前期,联邦和州的双重主权理论还是美国政治理论的主流学说,卡尔霍恩亦强烈主张各州拥有对国会法令的废止权,他甚至认为各州有权退出联邦。然而,至少从美国内战之后第13宪法修正案生效时起,这些政治理论开始黯然失色。在1868年极为著名的得克萨斯州诉怀特(68) 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断然裁定退出美国联邦的要求违反宪法。或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各州自主权的范围日渐狭小,各州对于联邦政府通过修宪扩张联邦权力、“篡夺”州权呈现出一种内在的不安,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或许就是这种不安的自然流露。
然而,联邦权力的扩张毕竟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进程。与之相比,州权理论或许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为它辩护的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亦不免有反历史潮流之嫌。况且,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南部各州的奴隶制度密切相关,它充当了为南部各州奴隶制度进行狡辩的角色;另外,在是否赋予妇女平等选举权的争论中,该理论又一次被用以挑战赋予妇女平等选举权的第19修正案之效力。因此,似乎可以这么说,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潮;考虑到其为奴隶制辩解以及反对赋予妇女平等选举权的历史,以现在的眼光观之,甚至可以说它曾经扮演了一种或许并不光彩的角色。
大概正是基于这个缘由,在美国,反对修宪权隐含界限的理论是强有力的。按照瑞士宪法学家卡基(Kagi)的归纳,反对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的论据有下列四个:一是实证主义,也即否认宪法规范之中存在着上下位的位阶顺序,宪法规范中纵使明文规定有“不变”、“不可侵犯”、“永久”的禁止修改规定,对这些规定也是可以予以排除的。二是法律思想中的相对主义,也即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主观的,宪法中的根本规范只不过是相对的规范而已,它仅仅是特定国民的意思而已。三是进化思想,也即纵使要求刚性宪法的安定性,但用现在的规范及价值拘束将来的世代是不当的。四是国民绝对主权观念,也即认为国民的主权是无限制的。(69) 卡基归纳的第一、三、四点尤其符合美国反对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的基本观点。美国反对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的进路,一是几乎绝对的实证主义,认为凡是《宪法》第5条没有明文规定的,都不能作为修宪权的界限;二是就像杰佛逊所宣称的那样, “地球永远属于生者的一代”,认为死者无权限制生者的行动;三是绝对的主权观念,认为人民的主权是不受限制的。更有美国学者认为,“人民”的修宪权不仅不存在任何的所谓隐含限制,而且,“人民”更可以抛开既定的修宪程序,以全民复决的方式修改宪法。(70)
然而,美国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不光彩”的历史以及伴随它的强有力的反对理论,并不意味着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就是错误的,或者反对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就是正确的,而毋宁是说,反对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之所以强而有力,其主要缘由,在于美国独特的历史和社会环境。
美国民主制度的深厚历史和民情基础,使得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基本上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后得出结论说,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一是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二是法制,三是生活习惯和民情。在这三者之中,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只有美国人特有的民情,才是使全体美国人能够维护民主制度的独特因素。”(71) 在美国,很难想象通过宪法修改来废除联邦制度,或者建立一个君主专制政体,或者出现其他类似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主张者担心出现的荒诞情形。因此,通过明确或者隐含的方式,给修宪权施加某种外在的、实质性的限制以确保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多数美国学者看来,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庸人自扰,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最多不过是表达了部分学者的杞人之忧。
如果我们把美国和德国的情形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就更能发现问题之所在。在“二战”前的德国宪法理论界,由于《魏玛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任何宪法修改的限制,因此,尽管也有学者鼓吹修宪权界限的理论,但是修宪权无界限说则是一种占有支配地位的学说。在这种理论背景下,1933年,希特勒依据《魏玛宪法》第76条规定的修宪程序通过《授权法》,将《魏玛宪法》架空进而毁弃。基于《魏玛宪法》的惨痛教训,联邦德国《基本法》第79条明文规定联邦体制、民主、法治、社会国家秩序等是宪法的基本精神,不得予以修改。而在战后的德国宪法学界,基于战前修宪权无界限说客观上成了为希特勒毁弃《魏玛宪法》提供理论依据的事实,修宪权界限学说转而成为占有支配地位的宪法学说。(72) 德国宪法学理论的这个转变,并不是说修宪权无界限理论就是错误的,而仅仅是表示,修宪权界限理论争议的此消彼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国家的历史和社会事实。因此可以设想,假如美国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那么一段类似于德国《魏玛宪法》被毁弃的惨痛经历,今天美国关于修宪权隐含界限的争论或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注释:
① 参见韩大元:“试论宪法修改权的性质与界限”,《法学家》2003年第5期,第11页。
② 参见许宗力:“宪法修改界限的理论”,《宪政时代》第七卷第三期,第35页;[日]芦部信喜著,周宗宪译:“宪法修改界限”,《宪政时代》第十七卷第二期,第51页;董保城:“修宪界限之探讨”,《宪政时代》第十七卷第二期,第19页;姚中原:“我国宪法修改有无界限之探讨”,《法学丛刊》第189期,第83页。
③ Willian L.Marbury,The Limitations upon the Amending Power,33 Harv.L.Rev.223(1919).
④ 参见Schmitt,Verfassungalehre,S.106。 转引自颜厥安:“国民主权与宪政国家”,《政大法学评论》第63期,第54页。
⑤ 德国宪法理论关于宪法修改界限的争论就更具逻辑思辨气息。参见许宗力:“宪法修改界限的理论”,《宪政时代》第七卷第三期,第35页。
⑥ 参见[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崔永禄、王忠和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8页。
⑦ 1837年卡尔霍恩在参议院断言,奴隶制“并非邪恶,而是好事——是件十足的好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给劳动者如此多的份额,向他们索取得如此之少,而又如此悉心照料其生老病死”。参见[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崔永禄、王忠和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0页。
⑧ 参见[美]梅里亚姆:《美国政治学说史》,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34页。
⑨ Chisholm v.Georgia,2 U.S.(2Dall.)419(1793).
⑩ 参见[美]梅里亚姆:《美国政治学说史》,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46页。
(11) John R.Vile,The Constitutional Amending Process i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Westport,Connecticut London,1992,p.86.
(12) Thomas M.Cooley,A Treatise on the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5th Edition Boston:Little,Brown,and Co.,1883.The Lawbook Exchange,Ltd 1998,p.42.
(13) Thomas M.Cooley,The Power to Amend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2 Mich.L.J.109,119(1893).
(14) David E.Kivig,Explicit and Authentic Acts:Amending the U.S.Constitution,1776—1995,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p.222.
(15) 这是美国新泽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瑞尔斯坦伯(Rellstab)所概括的事实。参见Feigenspan v.Bodine,264 Fed.186(1920)。
(16) [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刘绪贻、王锦瑭、李世洞、胡志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17) [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刘绪贻、王锦瑭、李世洞、胡志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18) David E.Kivig,Explicit and Authentic Acts:Amending the U.S.Constitution,1776—1995,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p.227.
(19) Willian L.Marbury,The Limitations upon the Amending Power,33 Harv.L.Rev.223(1919).
(20) Selden Bacon,How the Tenth Amendment Affected the Fifth Article of the Constitution,16 Va.L.Rev.771(1929).
(21) 在美国,选举事务一直被各州视为完全属于州的自治权。196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威斯布雷诉桑德斯(Wesberry v.Saunders)案中宣告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原则后,共和党参议员德克森(Dirksen)在国会提出了宪法修正案,意图推翻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述裁决。德克森论辩说,既然美国的国父们赋予大小不均的各州在参议院的平等代表权,而没有顾及各州人口上的众寡,为什么各州不能有同样的权利去自主分配其议会的议席?参见Dirksen,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People,66 Mich.L.Rev.837(1968)。
(22) David E.Kivig,Explicit and Authentic Acts:Amending the U.S.Constitution,1776—1995,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p.221.
(23) David E.Kivig,Explicit and Authentic Acts:Amending the U.S.Constitution,1776—1995,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p.232.
(24) David E.Kivig,Explicit and Authentic Acts:Amending the U.S.Constitution,1776—1995,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p.217.
(25) Willian L.Marbury,The Limitations upon the Amending Power,33 Harv.L.Rev.225(1919).
(26) 奥菲尔德曾经详细列举了修宪权隐含界限理论主张者宣称的、如果修宪权没有了隐含限制将会出现的多达20余种的荒谬情形。参见Lester B.Orfield,The Scope of the Federal Amending Power,33 Mich.L.Rev.550,553(1930)。
(27) Wm.L.Frierson,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A Reply to Mr.Marbury,33 Harv.L.Rev.659,664(1920).
(28) Lester B.Orfield,The Scope of the Federal Amending Power,33 Mich.L.Rev.581,553(1930).
(29) Lester B.Orfield,The Scope of the Federal Amending Power,33 Mich.L.Rev.559(1930).
(30) W.F.Dodd,Amending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30 Yale.L.J.321,338(1921).
(31) M.F.Morris,The Fifteenth Amendment to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189 North Am.Rev.82(1909).cited from W.F.Dodd,Amending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30 Yale.L.J.321,330(1921).
(32) Rhode Island v.Palmer,253U.S.386(1920).
(33) Switzer v.State,103Ohio306(1921).
(34) Feigenspan v.Bodine,264 Fed.186(1920).
(35) Lester B.Orfield,The Procedure of the Federal Amending Power,25 ILL.L.Rev.418,428(1930).
(36) Lester B.Orfield,The Scope of the Federal Amending Power,33 Mich.L.Rev.575(1930).
(37) W.F.Dodd,Amending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30 Yale.L.J.333(1921).
(38) 正是以该观点为理论依据,并且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宪法教授科尔文(Edward S.Corwin)的支持,克拉克(Clark)法官1930年12月16日在合众国诉斯普雷格一案中断然宣告第18宪法修正案无效。参见United States v.Sprague,44F.(2d)967(1930)。这个判决震惊了全国,次日《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其长达20页的判决。不过,克拉克法官似乎预料到其判决会被推翻,他在判决的一开始就说:我希望它至少有这样一个效果,即促使人们将目光转移到长期被忽略的修正案的宪法会议批准方式。两个月之后联邦最高法院一致推翻了克拉克法官的判决。最高法院法官罗伯斯(Owen Roberts)在判决中指责克拉克法官抛弃了既存的司法惯例,而受到了那个时代“政治学”和“政治思潮”的影响。参见United States v.Sprague,282 U.S.716(1931)。
(39) 早在1909年美国学者迈臣(Arthur W.Machen)就阐述了这样的理由。美国《宪法》第5条规定,未经当事州同意,不得剥夺其在参议院的平等投票权。迈臣宣称,在美国《宪法》上,“州”的含义就是指一州的“选民”。《宪法》第15修正案赋予有色人种以选举权,从而在实质上改变了各州选民的构成,这是对州本身的彻底改造。在第15修正案生效前,罗得岛在参议院有两名议员,这两名议员代表了罗得岛的所有(白人)选民。在第15修正案生效后,罗得岛在参议院的议员所代表的,就已经不是原来的罗得岛了,而是一个新的罗得岛。“罗得岛”的名义未动,而实质却发生了转化。这实有违于《宪法》第5条,第15修正案因而是无效的。参见Arthur W.Machen,Is the Fifteenth Amendment Void? 23 Harv.L.Rev.169,174(1909)。
(40) Lester B.Orfield,The Scope of the Federal Amending Power,33 Mich.L.Rev.553(1930).
(41) Lester B.Orfield,The Scope of the Federal Amending Power,33 Mich.L.Rev.563(1930).
(42) U.S.v.Sprague,282 U.S.716(1931).
(43) Leser v.Garnett,258 U.S.130(1922)。关于上述两案的介绍,参见荆知仁:《美国宪法与宪政》,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433页。
(44) Lester B.Orfield,The Scope of the Federal Amending Power,33 Mich.L.Rev.566(1930).
(45) Everett V.Abbot,Inalienable Rights and the Eighteenth Amendment,20 Colum.L.Rev.183,185(1920).
(46) Lester B.Orfield,The Scope of the Federal Amending Power,33 Mich.L.Rev.567(1930).
(47) Lester B.Orfield,The Scope of the Federal Amending Power,33 Mich.L.Rev.579(1930).
(48) Coleman v.Miller,307 U.S.433(1939)。在本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宪法修改是“政治性问题”,其间的争议应当由政治部门解决,司法部门并没有立足之地。
(49) Everett V.Abbot,Inalienable Rights and the Eighteenth Amendment,20 Colum.L.Rev.183,185(1920).
(50) Walter Murphy,The Art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A Preliminary Showing,Essay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ed.M.Harmon(Port Washington,NY:Kennikat,1978),p151.cited from John R.Vile,Contemporary Questions Surrounding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ing Process,Westport,Connecticut London,1993,p.132.
(51) 印度最高法院曾经做出过几个有名的判决,认为宪法所确认的基本权利是修宪权不可逾越的界限。参见C.V.Keshavamurthy,Amending Power under the Indian Constitution-Basic Structure Limitations,Deep & Deep Publications,D-1/24,1982,p.55。
(52) John R.Vile,Contemporary Questions Surrounding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ing Process,Westport,Connecticut London,1993,p.133.
(53) Laurence H.Tribe,A Constitution We Are Amending:In Defense of a Restrained Judicial Role,97 Harv.L.Rev.433,439(1983).
(54) Hollingsworth v.Virginia,3U.S.(3Dall)378(1798).
(55) Scott v.Sandford,60 U.S.(19How.)393(1857).
(56) Walter Dellinger,Constitutional Politics:A Rejoinder,97 Harv.L.Rev.446,448(1983).
(57) John R.Vile,Contemporary Questions Surrounding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ing Process,Westport,Connecticut London,1993,p.1336.
(58) Texas v.Johnson,109 S.Ct.2553(1989).
(59) United States v.Eichman,110 S.Ct.2404(1990).
(60) David E.Kivig,Explicit and Authentic Acts:Amending the U.S.Constitution,1776—1995,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p.456.
(61) David E.Kivig,Explicit and Authentic Acts:Amending the U.S.Constitution,1776—1995,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p.458.
(62) Jeff Rosen,Was the Flag Burning Amendment Unconstitutional?100 Yale.L.J.1073(1991).
(63) John R.Vile,Contemporary Questions Surrounding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ing Process,Westport,Connecticut London,1993,p.141.
(64) 按照美国学者的研究,至少有四个宪法修正案(第11、16、26修正案以及第14修正案的一部分)的意图在于推翻联邦最高法院的有关判决。参见Walter Dellinger,The Legitimacy of Constitutional Change:Rethinking the Amendment Process,97 Harv.L.Rev.386,415(1983)。
(65) John R.Vile,Contemporary Questions Surrounding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ing Process,Westport,Connecticut London,1993,p.173.
(66) 不过,美国各州对于州权依然保持着敏感状态。1994年,在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两个有关联邦制度的重要判决后,有不少于15个州通过决议,重申《宪法》第10修正案的重要性。参见Henry Paul Monaghan,We the People[s],Original Understanding,and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96 Colum.L.Rev.121(1996)。美国《宪法》第10修正案规定:本宪法所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州行使之权力,皆由各州或人民保留之。个中意味,不言而喻。
(67)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2页。
(68) 7 Wallace 700(1868).
(69) 参见[日]芦部信喜:“宪法修改之界限”,周宗宪译,载《宪政时代》第十七卷第二期,第51页。
(70) Akhil Reed Amar,Philadelphia Revisited: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Outside Article V,55 U.Chi.L.Rev.1043(1988).
(71)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8页。
(72) 参见董保城:“修宪界限之探讨”,载《宪政时代》第十七卷第二期,第19页。
标签:联邦政府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宪法论文; 妇女选举权论文; 美国法律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联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