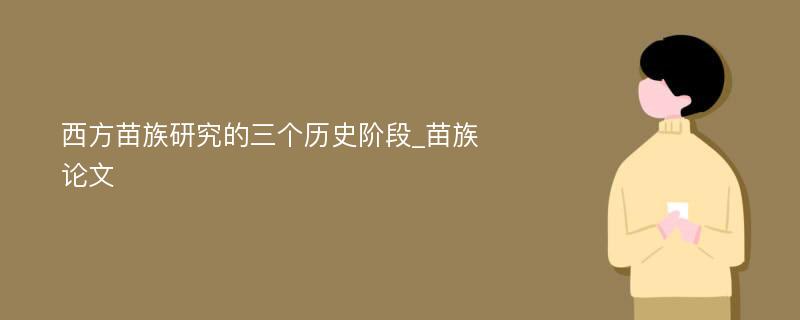
西方苗学的三个历史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段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早在17世纪初叶,一些西方传教士出于猎奇和探险而与苗族有过初步的接触了解,但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对这个古老的民族仍一无所知。直到19世纪,西方学者才在他们的著作中零星地提到苗族的有关情况特别是其种属问题。我姑且谓之为“早期西方苗学阶段”。这个时期的代表学者和作品有:1861年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关于中国的苗族或土著居民》,1862年英国军人布勒契斯顿《长江上的5个月》,19世纪80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德·卡特勒法热《人类种族通史》、韦尔努《人类的种族》和拉戎基埃《在越南北部的两年》,1894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克《中国西部的苗族和其他部落》等等。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人关于苗族的研究逐渐具体起来,涉及到苗族的历史、族源、社会组织、人生礼仪、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诸方面。它标志着“现代西方苗学阶段”的形成和成熟。主要有:1903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1917、1924年法国传教士萨维那《苗法词典》与《苗族史》,1950年德国语言学家乌德里库尔《苗瑶语历史语音学导论》,1954年美国民俗学家格雷姆《川苗的诗歌和传说》,1959、1960年苏联历史学家伊茨《苗瑶与蛮的族关系》和《苗族》1963年德国汉学家勃劳梯加姆《论白苗》,1967、1971年英国语言学家唐纳《白苗的变调与调变》和《苗瑶语的进一步关系》,1972年法国学者苏尔梦《18世纪的贵州》,1972、1974年,法国博士莱莫尼《苗族风水》与《苗族指路歌》。1972、1976年澳大利亚民族学家格迪斯《山地民族》与《泰国青苗的文化生态学》,以及1978年法国历史学家莫当《苗族史》等等。我之所以把这个时期西方人对苗族的研究称为“现代西方苗学阶段”,是因为其具有两大特点:首先,它已不同于“早期阶段”仅限于某个方面的一鳞半爪的介绍记述,而是针对苗族进行全方位或专题性的理性论述探讨;其次,它的作者阵容除了传教士这类准学者外,还有在各研究机构和大学任职的专家教授。
不过,西方苗学的“早期阶段”与“现代阶段”也有个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们的研究客体(对象)都在远离西方主体(作者)的中国和东南亚;研究的目的也主要是为有关学科积累文献资料,即“为学术而学术”。
这样,至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除个别学者外,西方人只有极少数人听说过苗族,就不足奇怪了。当他们听人说起老挝和越南山地从事水稻和鸦片生产的少数民族时,认为这个少数民族就是苗族,是一些在老挝和越南反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战争的勇猛的外国雇佣兵。至于苗族还分布在哪些地方,从哪里来,则是一片茫然。
80年代以来,苗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所认识知晓。1975年,由于老挝的动乱,聚居在泰国避难的10多万苗族的大部分——65000人,在泰国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署的安排帮助下,率先迁居到了美国。此后,陆续从泰国、老挝、越南移居美国的人数不下14万。他们以小聚居的方式分在美国50个州中的近40个行政州。在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威星康斯、圣保罗、利斯、底特律、明利阿、罗德艾兰、伊利诺斯、普罗维登斯、芝加哥、华盛顿、纽约、西雅图、俄勒冈、莫塞德、内布拉斯加等地区的70多个居民点中,大约有56个居住点不到1000人,仅有两个居住点达8000至10000人左右。
自1976年以来,又有部分苗族迁徙到法国、法属圭亚那、德国、英国、加拿大、阿根延、澳大利亚等4大洲的10多个国家。至此,世界五大洲都有苗民;苗族即成为一个世界性民族,为西方苗学的研究提供了活生生的直观的材料,使他们有可能有条件将苗学的研究推向深入的当代阶段。
与前述两个阶段相比,“当代西方苗学”的最大显著特点就是注重研究的针对性、实用性,以理论成果指导苗族实践,旨在解决苗族离开东南亚后在西方这新的生存环境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且研究队伍空前壮大,他们中有教育工作者、研究院研究员、大学教授、大学生、研究生、社会工作者、难民安置专家、联合国高级职员,医务工作者、艺术鉴赏家、苗瑶研究计划协调人,也有店主、地主、教徒以及邻里百姓。在研究课题上,他们由自发走向自觉,由过去的散兵游勇走向集群性的专题攻关协作。这种自觉,一是来自于10数万苗族在西方的存在——为能够在一种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各方面都与他们自己不同的文化中生存奋斗——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另是建立在寻求对苗族即时迁居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文化调适所进行的理性思考。于是,许多研究所、学会、协会、大学、难民安置机构都争相将苗族问题列入了自己的科研计划。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东西亚难民研究所与纽约移民研究中心等于80年代初期分别主办了“西方的苗族”和“苗族的变迁”两次专题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论文集。
此外,全美苗人协会、东华盛顿大学有关系科、加州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学研究所”等,在组织开展苗学研究上都颇有建树,成果累累。其中的全美苗人协会,系苗族移居美国后自己创建的一个学术性团体。它是一个国际性的混合文化的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和发展同苗族历史、社会组织、传统文化等背景有关的教育项目,同时组织开展学术研讨,以保护苗族文化,促进东西文化交流。
就我目前手头掌握到的有关苗族的英文版资料,当代西方苗学的主要著述有:1981年查尔斯·约翰逊主编的《ESL地区苗族民间故事集》,1982年第一版、1989年第二版的《西方苗族调查报告》,1986年版的《苗族的变迁》,1988年版的《苗族: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历史》,以及1988年美国博士路易莎·斯琴《美国莫塞德市的苗族居民》、《中国贵州苗族文化的复兴》等。另外,同期还有苗族博士杨道主编的专门介绍苗族情况的《苗族》杂志;法属圭亚那苗族出版的苗文版《婚俗》;明尼苏达大学东南亚难民研究所主编的《难民》杂志亦刊载有不少研究苗族问题的学术性文章,如1988年第一期发表的法人塔普《老挝苗族难民的文化变革》即是显例。
为促进对人类变迁和世界难民迁徙的社会人口统计、经济、政治、历史、立法、语言、文艺以及宗教诸方面进行研究,本世纪60年以来美国先后在纽约、明尼苏达等州郡创立了非赢利性教育机构——移民研究中心或难民研究所。《西方苗族调查报告》和《苗族的变迁》这两本大部头著作,就是这些机构和西方苗学家们在苗族那些方面的观点和意见。
《西方苗族调查报告》(《The Hmong in the West observations and repors》)是1981年10月2日至3日在明尼苏达大学召开的第一届西方苗族研讨会的文集,以英文计约40万字,共收录文章20篇。它分前言、导论、苗族文化与调适、苗族语言与通讯交流、语言学习的争论、困感与希望并存的美国苗族5个部分,向读者介绍论述了这个民族离开老挝的原因、经过,以及移居西方诸国所碰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语言交流、健康状况、就业安排、信仰冲突、再次迁居、婚姻丧葬、文化适应等等,是了解西方苗族来龙去脉不可多得的一本通俗读物。
《苗族的变迁》(《The Hmong in transition》)这本40余万英文字的著作,也是一本论文集,包括索引目录等附件在内共39篇。它以1983年11月17日至19日在明尼苏达大学召开的第二届西方苗族研讨会提供的背景材料为依据,洞察苗族的社会结构、文化特性;评价其在中国和老挝、泰国的状况;分析其目前在东南亚和美国的处境,提供在特定领域诸如语言与文字、健康与福利以及心理健康的研究成果。较之前本文集,这本书还给我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西方学者们把关于在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的苗族的研究引进了许多领域、拓宽了学术视野,反映了研究的多样化,证明了研究成果比以往更加成熟,达到了那个时候应有的水平。至于有关苗族居住社区资源匮乏以及迁移过程中面临西方文化的冲突与适应问题,该书亦包含了当时能够获得的最权威的资料,对于本书,我很是赞同史密斯大学教授罗伯特·I·罗斯在其出版说明中所作的中肯评价;他说书中的“文章言简意赅……不仅为专家学者,而且也为需要了解他们的新邻居和公众,提供了短小精悍的关于苗族变迁的课程”。
《西方的苗族》和《苗族的变迁》两书的主编者亨德雷克斯、道宁、邓纳德、奥宁都是卓有成就的教授、博士,分别供职于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系、语言系、小儿科系;他们同时也是两届西方苗族研讨会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在当代西方苗学史上功不可没。书中的作者既有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的专家教授,也有联合国负责难民事务的顾问和驻老挝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苗族: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历史》(《Hmong history of a people》)是美籍苗族历史学家凯瑟·昆西写的一本个人专著。该书约25万英文字,共有11章外加一篇绪论和两份文献索引。其中还有照片和图表25幅。作者的写作动机似乎不像上两本文集那样,出于对“苗族既能适应一种新的文化同时又保持自己传统”的思考,而主要是为他的妻子,是何缘故不得而知。与国内所见的汉文版的中国《苗族史》相比,这本英文版的苗族史可称得上一本世界苗族史。它以一种轻松活泼的笔调,娓娓动听地向世人叙述了苗族7000年漫长的艰辛历程:他们远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一带的祖源故土;他们穿越西伯利亚迁徙到中国的传奇经历;他们在中国历代社会中的消长变化;他们与汉民族3000年来的微妙关系;满清皇帝对他们的追剿征伐;他们怎样移居印度支那;他们在东南亚如何进行鸦片生产和贸易;他们与法国人貌合神离的结盟过程;他们在老挝国内战争中的态度;他们为什么寻求避难;他们怎样到了西方;他们在西方如何生存……但作者又不是那种追求文学效果的描绘,而是把观点和见解尽力溶入散文式的表述中,让人感到新奇的真知灼见随处可见。如关于苗族的祖源,国内苗学界只讲到4000年左右的九黎蚩尤时代就浅尝辄止了,而昆西则通过人种学、考古学、文化学、语言学的成果将之追溯到了7000年前欧亚大陆的高加索人种那儿。他认为,苗族的祖先就是5000多年前生活在西伯利亚的高加索的一个亚族,至公元前3000至1200年,苗族才离开西伯利亚到中国定居下来。因而他得出结论,苗族文化的主要特征在其移居西伯利亚前就形成了,并且这种文化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既反映出西伯利亚草原生活的因子,也适用于在山区生存的需要。虽然,关于苗族身上具有的高加索人种特征(“金发碧眼”、“窄脸型”、“鹰钩鼻”等,早为中西方学者洛克哈特、布勒契斯顿、卡特勒法热、韦尔努、拉戎基埃、克拉克、鸟居龙藏、萨维那、朱辅、范文澜、郭沫若等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所主张或注意,但真正在学术层面上进行探讨论证的恐怕只有萨维那和昆西两人。撇开其结论的真理性当有疑义不论,仅就这种科学上大胆探索的恢宏气魄而言,于我们的思路不无启迪,可供苗学界参改、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