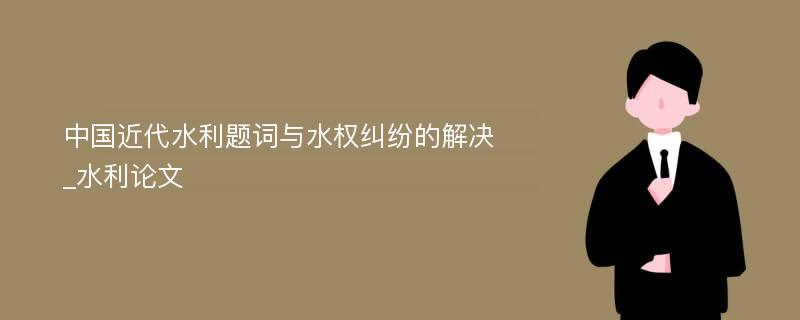
水利碑刻与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碑刻论文,纠纷论文,水利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06)03-0045-05
在水利史资料中,碑刻是最丰富,也是最有价值的原始资料。通过研究这些水利活化石,可复原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的概况和基层社会水权运行的细节。与水册的秘密性,非公开性相比,碑石很大程度上则是表述一种公开的事实。也就是说,公开、透明、显示权威是水利碑刻的主要特点。同时,与水册纯粹的民间自治性质相比,碑刻在强调民间自治的同时,允许官方力量的介入。以水权纠纷案件为中心所形成的官司碑,这一特点更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水利碑刻的意义不仅在于诉说,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开说教,提醒水权人注意其权利的界限,将纠纷消除于无形。因此,水利碑石是一种预防性的制度安排,它通过向人们陈述过去的纠纷及其处理结果,提醒人们维持业已存在的水权秩序,以免卷入新的纠纷,并因此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一句话,水利碑刻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具有强调、提醒的含义。
一
水利碑刻用料非常讲究,一般采用上好石料,甚至汉白玉,以体现水权的神圣和水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对一些重要的水利碑刻,人们还为其建立碑亭,以体现人们对碑刻无限敬仰之情。如陕西城固县五门堰所存《重修五门堰记》和《重修六堰记》两通明代水利碑,石材均使用汉白玉,显得雍容华贵,典雅庄重。水利碑刻一般由三部分组成:碑首、碑体和碑座。碑首一般雕刻狰狞威严的蟠螭,以显示碑刻的神圣庄严。碑体分为碑额和正文。碑额体现水利碑的类型,是官司碑,还是合同碑,或者其他类型。如《新开广惠渠记》碑,其碑额是“新开广惠渠记”六个大篆字,气韵极为生动,碑边镂刻龙云花纹,很有气势。碑体是水利碑主体部分,位于碑的正中央,一般用较多文字叙述水利工程的兴建、维修,水权管理的章程、乡规民约,水权纠纷发生的原因、经过、处理经过等。《重修广惠渠记》碑身通高四米多,宽一米一,碑文二十三行,每行六十四字。书法为行楷,端庄秀丽。碑座为一龟趺,高近一米,厚重而有力度。通碑看上去,简洁朴素,庄严肃穆。正文结尾有立碑人、书丹人、镌刻人姓名。官司碑刻有处理案件官员职衔、名称,以及中人名称。为了强调碑刻权威性,有些碑文就采用官方水权判决书。例如河津县《海公断案碑》,完整刻录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河津县长海鹏运审理干涧村宁典辰、原世英、史掌印等的刑事判决书。内容包括被告姓名、案由、主文、事实、理由、时间、审判员等。[1](P239-242)为了彰显某一水利碑刻的重要性,水权人会有意将互有联系的两个水利合同、判决等内容刻在一个碑的正反两面。如上述《海公断案碑》正面刻刑事判决书,碑阴刻《请求赔偿水利损失案碑》,即民事判决书。这是两个互相牵连的案件。民国二十四年干涧村与尹村发生了水权纠纷。河津县政府以民事第七零号判决书,令被告于涧村史平稳、史明智等十三人赔偿原告大洋七千八百元。尹村将这一判决原封不动地刻在了《海公断案碑》的碑阴,即《请求赔偿水利损失案碑》。[1](P242-244)
水利碑刻产生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重要水权事件或证据的记录,如水源地发现,水源变化等;第二是水权纠纷案件的官司碑,主要记录水权纠纷发生后,官府以司法手段介入,处理案件的情况,以及最后对水权归属的认定;第三是水利宗教重要事件的记录,主要记录水利神在护佑水源地方面的传奇、传说;第四是水权合同的记载,一个或数个村社就水权使用所做的制度安排,是一种特殊的契约。第一、二种水利碑刻,数量较多,地位也最为重要。一般放置在比较重要的场所,如公共活动场所、宗教祭祀场所,成为公共活动的主导性活语,也是宗教祭祀、信仰的对象。个别地方,官司碑就存放于审理水权纠纷的衙门,以示权威,并资遵守。如据《龚府尊供赵水利碑记》载,同治五年,护理巡抚王某审理洪洞县润民渠渠长上控赵城普安渠崔世珍于石埂新开泄沙口一案。案结后,“渠民禀请勒石,除查照原批事理,分别转行遵照,销案。并移霍州知照外,合亟饬令照卷勒碑,永远遵守,以息争端,可也。大清同治七年吉日勒石。此碑在乎阳府大堂滴水檐西墙根立,曾椎碑文数张,平阳府刑房卷内存一张,洪洞县刑房存一张”。[2](P206)
甚至一些地方,人们将一些重要水利碑刻安放在水利工程之中,使其成为水利工程的一部分,如四社五村就将确认水权的重要碑刻“金明昌五年霍邑县孔涧庄村碑”存放于孔涧村玉皇庙,供人们崇拜。每年祭祀时,与水利神一样,享受同等供奉。还是在四社五村,民众将特别重要的水利碑埋入水渠,以显示该碑与水利工程不可分割的关系。例如,孔涧村社首李德辛认为,把官司碑放在水里保存,就是防止将来再吃官司,他对我们说,“我把那个碑看了一下,(上面写了)各打六十杖,衙门还拿棍子打了(每村人)六十杖”,他还说,官司碑不能挖出来,“有问题再挖”。[3](P292)所谓“问题”是指水权纠纷。言下之意,如果不发生水权纠纷,就用不着挖碑;而如果发生了水权纠纷,就必须挖出水利碑,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碑刻对水权纠纷有一定抑制作用。笔者收集的河西民勤、武威、汉中、咸阳、渭南、临汾、洪洞、介休、灵宝等地水利碑刻,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官司碑。以武威市水利志收录的建国前水利碑刻为例,该志共收录7个水利碑刻,全部涉及水权纠纷。与水利有关的宗教祭祀碑一般存放于重要宗教场所,与水神共同构成了水利社会的宗教信仰。它一般以传奇、神话向世人讲述水源由来,以此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当然,一些最具权威性的水利纠纷碑石、合同、章程也会保存于宗教场所,供人们祭祀。合同是水权利益各方为水资源共享所达成的用水协议、章程等。它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合同或契约,但又不完全相同。相同之处,二者都是为了避免纠纷,或者在纠纷发生之后,双方签订的协议。不同之处在于,水权合同是双方纠纷解决后,为了避免日后再起争端,而订立的。它可能出于双方自愿,也可能是在官府压力之下,甚至以官府水权纠纷判决为基础而拟定的。由于它为双方所认可,因而可看作双方自愿签订的协议。以光绪元年武威怀六坝磨湾泉水利碑为例,该泉自明朝崇祯十一年发生水权纠纷以来,五坝、六坝一直你争我夺,相持不下。直到光绪元年,在县官审理下,“销毁私照,斩断藤葛”,“两造具结完案,更请给合同新照,彼此永远遵守,以杜争端”。[4](P381)水权合同碑虽然是以双方自愿认可为前提,但是,官府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官府以国家强制为后盾,以调解人身份介入纠纷,劝解双方,遵守协议。因此,水利碑刻的运作是民间性质的。但是,它解决纠纷过程中,始终和官方保持着密切联系,特别是当民间解决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时,水利组织与官方互动显得尤为重要。
二
水利碑刻是民间水利自治组织水权管理的产物,是基层社会水权运作的辅助手段。水利碑刻以庄严神圣的仪式,无可置疑的内容,确定水利社会权利义务关系的圣物。水利碑刻就其形式而言,是水利社会精神遗产的物化;就其内容而言,是水利社会千百年来先民水利知识和经验的总结,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通过水利碑刻运作,可避免纷争,实现水资源共享的理想。首先,碑刻强调以共享为原则,分配水资源。其表现形式是通过水利碑刻确认水源的公共属性或集体属性,如《新修洪山泉源碑》,记述了知县王正已因为洪山泉水不足,难兴大利。于是组织人员调查、勘探水源,挖出新泉七孔,引水利民。[5](P117-118)由于是官方主导的水利行为,所以水权必然为流域民众共享。一般而言,水源地都竖立有关于水源由来的碑刻,以确定水权归属。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这一形式向世人宣告那些人可以使用该水源,那些人不能使用该水源。四社五村水源地沙窝村龙五庙,除了祭祀水神,同时还供奉“清道光七年四社五村龙五庙碑”。该碑和龙王庙具有同等重要性。它把水利制度与宗教信仰紧紧地结合起来,将世俗水权与宗教的神权结合起来。这样,民众在用水的时候,不仅是使用普通的水,而是使用神水。同时,碑刻对用水原则也做出明确规定。山西四社五村、陕西泾惠渠、清峪河灌区,实行自下而上,轮流灌溉的用水制度。这一制度确立的前提就是流域水资源共享,否则,上游决不会答应下游首先用水,而冒自己无水可用的风险。为了强化这一原则的执行,在一些比较重要渠道、闸口,竖立碑刻,以警戒世人,不能随意截霸他人水资源。如《八复水夺回三十日水碑记》碑阴刻有会议章程六条,具体规定了贯彻自下而上灌溉制度的办法,以及违犯这一规定的处罚方法。山西《王官峪五社八村水规碑》也有类似规定:第一,“用水分村分浇也”,也就是说,灌溉按照一村一社的顺序轮流进行,第二,“各社分占水分定数也,东涧西涧占东渠十八分,西渠八分共二十六分”,也就是说,每一个村社的水量是固定的;第三,“各社用水先后次序也”,即规定各村用水的先后顺序;第四,“罚款各样各色也”,即规定堵塞渠道行为的处罚办法等。[1](P209-210)再例如,民国十六年(1927年)韩城《三村九堰公议规程碑文》规定,渠道维修,“每年挖渠,自下而上”:用水顺序,“轮水初挡日,准渗渠水通流三日,然后自上而下送富村八堰水一日,再轮富村水十日,再轮北村水六日,再轮南周村水六日,周而复始”,“泡蓝、沤麻,系已成庄稼,不论水轮某村,准三村同用”;如果“堰冲渠崩,准将分水日暂行停止。俟工成水归渠后,再看水轮至某村,另接续起”。①如果有人违犯水利规程,“任意截水浇地并私行盗水者,三村公议重罚”,“八堰浇地之日,准新开渠道经过之地先浇,余水始准以外之地再浇,不准乱浇,不准私开水渠引水,违者同工议罚”,也就是说,凡是违犯水规的行为都要受到相应的工役处罚。①该碑还对渠道经过土地补偿做了规定。其次,通过碑刻确定分水权,也是水利碑刻民间运作的重要职能。在这一点上,水利碑刻的功能与水册的功能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水册是以积极方式确认水权,而碑刻则以消极方式对水权做出排他安排。在水权涵盖范围方面,水册比较全面规定了水资源使用的所有细节,不仅有水程的详细描述,也有工程维护、工役补偿、违犯水规行为的处罚的具体规定,而水利碑刻则可以看作是由个案组成的水权管理片断。这是由水利碑刻的特性所决定的。因为碑刻记载内容的有限性,以及使用目的的单一性,使它不可能像水册一样,记载需要长篇大论的水利事件,而只能以简洁的形式,凝练的语言,表达较为复杂的内容。因此,在题材的选择方面,它只能是一事一碑,或一个类别一碑,不可能在一通碑上表达具有连续性的水利事件(如水权变化、水粮变化等)。规章碑只能反映有关水权运行习惯、章程等方面的内容,官司碑则只能反映某一发生的原因、经过及其最终的解决等内容,最多只能在反映案件解决基础上,在碑阴重申与纠纷有关的规章制度以及水权习惯。碑刻与水册对分水权规定,也有很大差异。水册不仅可以规定干渠的分水原则,还可具体到支渠、每一个村庄,甚至每一个水利用户。例如陕西省清峪河灌区《高门通渠水册》、《清峪河源澄渠水册》,其水程都具体到了每一个水利用户。而碑刻只能以抽象的语言,对分水情况做出概括性规定,例如山西洪洞与赵城两县的分水原则是“三七分水”,具体到每一个支渠、每一个村庄、每一个水利用户,应该怎么分,就语焉不详了。再次,通过对官司碑的公开展示,向权利相对人宜示自己权利,借此以警告对方,应该遵守业已形成的惯例,否则,可能要导致相应的后果。官司碑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官方管理行为的体现。如以渭南万盛堡□玉桥水权纠纷为例,县官“邓□绶断定,各守旧规,不许阔宽渠道,令将□玉桥前后断案勒石,永息争讼,庶不致弱之肉强之食也”。①这一碑刻的竖立,就是秉承县官命令而建立。目的使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产权明晰的目标。实际上,官司碑的运作是通过碑刻信仰、立碑仪式等外在形式对乡村社会施加内在影响,而不是对司法判决的说教或者宣传。另外,官司碑对内还有强化成员之间团结,一致对外,防止水权利流失的功能。清峪河灌区,常常因为不能很好地执行水规,导致水权流失的现象发生。《八复渠夺回三十日水碑记》记载了八复渠由于利夫不能维护自己权利,致使每月三十日一天水程被上游沐涨渠夺去。后八复渠通过诉讼,于光绪五年,又重新夺回了三十日水权。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八复渠于光绪七年四月立碑以为警示。[6](P104-109)因此,官司碑具有对内与对外双重作用。对外方面,以乡族观念为主导,鼓励村社成员为了共同体利益争夺水资源,即使付出金钱、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村社将争水牺牲的成员视为英雄、烈士,为其树碑立传,甚至将其神化,供奉在水神庙里。同时,给予其子孙后代享受用水优待之特权。清代道光五年(1825年),四川千功堰,西河之北坪,新冲出一河,水量湃入黑石河,引起西河淤积严重,致使千功堰无水可灌溉。邛崃、大邑、崇庆、新津四县用水户推选郭之新为长河堰长,率众前往修堰,与其他渠堰发生争执。郭之新为了灌区广大民众利益,据理上告。由于屡告不准,不得已拦舆控诉,被诬为“控词冒渎”而定罪,投狱90天。但郭之新毫不气馁,多次上诉到制台衙门。后经官府派员查勘,终于使湃走水量仍归故道,恢复了四县农田用水。民众感其功德,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以“功遍西河”匾额相赠。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政府旌表他为“正八品官”,并赠“寰宇煦春”匾额。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水利户在大邑县韩场镇建立石碑一座为,以示纪念。[7](P103-104)最后,重要碑刻所在地也是水权裁判场所。水碑一般都存放于公共活动、公共宴饮、宗教祭祀之所。这些地点,在中国传统社会往往都指向一个地方,如果是一个村社,可能就是水神庙,也可能是家族祠堂。如果是较大地域,则可能是当地集市所在地,或者共同宗教所在地。这些场所是公共活动的地方,是解决村社重大问题的集会地,自然而然,也是解决水权问题的场所。这些场所,是存放祖先牌位的神圣之地,也是存放历史记忆的场所。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对水神的祭祀,可强化人们对水利碑刻的历史记忆,从而将其升华为一种朴素的感情,最终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和自觉的行为。这些场所,往往是水权械斗时,聚集民众,进行战前动员,鼓舞士气的场所。也是械斗后,祭祀死亡者,将其英名写入族谱、碑刻的圣地。对内,是处罚那些不执行水规,浪费水资源,侵占他人水权的裁判所。在山西一些水利区至今还流传着“碑(庙)前打死,碑(庙)后埋”的谚语。[3](P306)其寓意是碑刻所在地就是神圣的裁判所,在这儿对不遵守水规,肆意用水,甚至恶意挑起事端者,均可实行这一古老缄言。因此,将有些不守水利法规的人打死,就像执行国家法律一样,不负刑事责任。实际上它是借助神灵神秘力量,教育普通民众遵守水规、章程的培训中心。从社会学家田野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家都津津乐道这一民间谚语的威力,但是,很少有人能够证明其实施过。不可否认的是,借助这些神圣手段,确实能够以较小成本维护水权规章制度的运行。另外,碑刻通过将社区民众对水利事业的贡献记录于碑石的方式,满足了人们将自己恩泽推及于自己后代的想法。在社会学家所做的水利调查中,每当自己祖先名字出现在碑刻上的时候,都会激发他们的自豪感。也许,他们仅仅为水利工程捐助了几元钱,但是,当这一简单数字,经过若干历史岁月,以碑刻形式重新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其性质完全发生了变化。它身上所承载的荣光,让后人感恩不已。事实上,这些碑石上留名人的后代,就是今天热衷于水利事业的社首、渠长。他们的付出,又会檄励其后代继续造福社区。这样,我们看到,治水社会的历史的责任在他们手里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
三
碑刻在基层社会水权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与水册一样是中国基层社会水利自治组织进行水权管理的重要手段。他们都是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流传,成千上万人经验累积而形成的精神财富。虽然,它所反映的内容是发生在过去的水利事件,其影响却及于今天。而且,它不仅反映了立碑时代的水权特点,也反映了水利历史长河中前人有益的水权管理经验。而且,毫无疑问,它将继续发挥对当地水利社会的影响力。今天,它们已成为中华民精神遗产的组成部分。不论是在灌溉农业区,还是在非灌溉农业区,碑刻都成为水权取得的重要证据。人们在碑刻周围生活,围绕碑刻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进行褒贬,从而成为地方社会公德良心的承载者。从立碑过程来看,它是官方、当事人三方行为互动的结果。碑刻,就其性质而言,具有一定官方性。因为大量官司碑,本身就是官方介入基层社会水权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碑刻的作用,不是简单教义式的宣讲,而是复杂的民间运作。它涵盖了诸如祭祀、民间舆论、乡村治理、民间自治等水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对水册、水利习惯的有益补充。它不仅是基层水利社会水权管理的工具,也是官方介入基层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它不是少数社会精英权力游戏的外在表现,而是基层社会民众的共同生活准则、共同信念、共同生活理想的外化。通过碑刻对为公众利益献身、牺牲的英雄人物的颂扬,形成乡村社会公认的价值观。②通过碑刻,可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建立跨地域的联盟。东南沿海、闽南、潮汕地区,通过对水利碑刻的共同崇拜,共同面对困难,建立了跨越血缘关系的联盟。
近代以来,碑刻数量有所减少,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如民国时期陕西省新建的“泾惠渠”水利工程,建有《泾惠渠颂》水利碑,汉惠渠建有《汉惠渠记》水利碑。甚至八十年代,安康防洪堤上新建洪水历史标志塔、宝鸡建冯家山水库时,都建有新型水利碑。这说明在新时期水利碑的独特作用仍是无法替代的。总之,水利碑刻是基层社会解决水权纠纷案件的物质表象,不仅具有预防纠纷的作用,而且,一旦纠纷案发生,又是处理水权纠纷的重要证据。
注释:
①引自渭南地区水利碑碣集注(内部发行),渭南地区水利志编纂办公室编,58-59,186。
②对维护地方水权利益做出重要贡献的英雄人物的颂扬不限于水利石碑,一些地方渠册也有类似记载。据山西《沃阳渠册》记载:“道光二十二年,皇天震怒,警醒下民,灵雨未降,不满一年,斯时古县、董寺、李堡三村,心生计巧,私淘新渠,盗五村北泉之水,浇灌伊之田地。于是吾村掌例范兴隆、苗文孝、范思有、左本治、左清风等,与古县、董寺、李堡三村理论。谁料伊等恃强,遂约数百余人与吾村相为斗殴。吾村人虽则不多,然而理直气壮,遂致误伤古县村吉广顺。于是两造人等,据亶在案。蒙陈老爷堂审问清,断北村吉士功、燕村堂到案,言伤人命之事。陈大老爷断谕,令吾村范兴隆等案定罪。以后各使各水,仍照古规,不许紊乱纷争,强霸横行。但范兴隆既为村了承案,是以公共之事,而不惜一己之命,真可为义气人也!吾村聚众遂议:范兴隆以为永远掌例,传于后辈,不许改移。伊之地亩,有水先浇,不许兴夫,以为赏水之地,永远为例。且于每年逢祭祀之时,请伊后人拈香,肆筵设席,请来必让至首座,值年掌例傍坐相陪,以谢昔日范某承案定罪之功。”载孙焕仑:《洪洞县水利志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