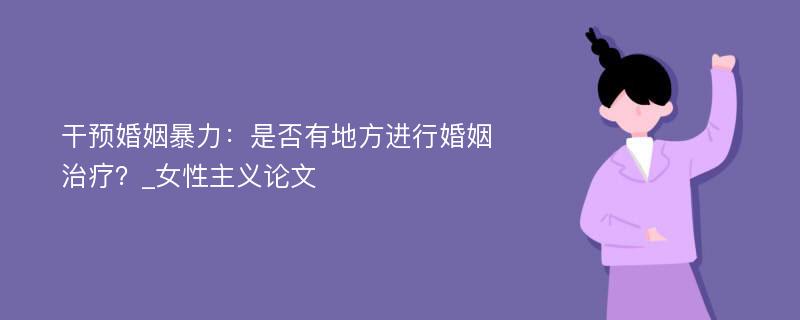
婚姻暴力的干预:婚姻治疗是否有一席之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婚姻论文,有一论文,之地论文,暴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8,R749.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2)009-0641-07
婚姻暴力是严重的公共健康、法律及社会政策议题[1-2]。婚姻暴力受暴者不仅遭受直接的身体伤害,也会承受重大的心理创伤[3];不仅是个人的伤害,所有家庭成员也都受到冲击[4-5]。调查显示,婚姻暴力的终生发生率为25%~30%,一年的发生率约为2%~12%[4]。中国全国妇女大会报告约40%夫妻在冲突中互殴,频率约为“几个月一次”,与十几年前的数字比较,年增25.4%[6]。
受女性主义观点的影响,美国对婚姻暴力采取施暴者与受暴者分开的双轨制(parallel track)干预模式[7],这种模式限制了婚姻治疗的使用。经过几十年来相关领域学者的努力,一些新的研究数据提示有必要调整对婚姻暴力的认识与干预的方式。因此,本文介绍了婚姻暴力的定义、施暴者的类型、婚姻暴力干预的现况、施暴者的标准治疗程序、成效研究的结果,以及实施婚姻治疗的优势与反对意见。
1 婚姻暴力的定义及施暴者的类型
1992年,美国家庭暴力预防与服务法案(The 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 Service Act)将婚姻暴力或称为亲密伴侣施暴(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IPV)定义为“任何发生在具有婚姻或亲密关系的暴力或胁迫行为,并导致身体伤害”。该定义未提及精神虐待,因此我们认为欧洲议会对家庭暴力的定义“在家庭的架构内,成员发生任何行为或是漠视,因而造成其他成员生命、身体、心理的完整或自由的侵犯,或是严重地伤害其人格发展”较为完整。
要处理婚姻暴力问题,对施暴者的了解是重要的一步。Delsol等[8]认为施暴者类型的研究确定了施暴者是异质性的,这解释了先前研究结论不一致的现象,建议日后的研究要基于施暴者类型累积研究结果和设计干预的方式。
Holtzworth-Munroe和Stuart[9]提出了对施暴者分类的3个维度:①暴力(生理、心理及性暴力)的严重度及频度;②广度,即暴力局限于家庭成员或家庭外的人,以及相关变量(如犯罪行为);③出现心理病理及人格偏差。他们依据这3个维度提出3种家庭暴力类型:①家门内(family-only),即暴力最轻微且局限在家人;②烦躁/边缘型人格(dysphoric/borderline),即暴力较严重,施暴者有边缘型人格偏差或情绪问题;③广泛的暴力/反社会人格(generally violent/antisocial),即暴力最严重,施暴者有反社会人格障碍,最常与外人发生冲突。Johnson[10]根据婚姻暴力关系的性别对称性(gender symmetry)提出以下类型:①寻常夫妻暴力(common couple violence),即暴力发生于某些特定的生活情境,夫妻因冲突相互激化而导致暴力,男性与女性的发生率差不多,与控制无关,受暴者不会感到普遍性的恐惧;②亲密的恐怖主义(intimate terrorism),即施暴者在生活各个层面广泛地控制配偶,大多是男性控制女性;③暴力抗拒(violent resistance),即受暴者用暴力反击;④相互暴力控制(mutual violent control),即夫妻旗鼓相当地相互控制。Gottman等[11]基于施暴者施暴时的心跳反应,将施暴者分为type I及type II两种类型。type I施暴者的心跳变缓,而type II则心跳会增快。也有学者将暴力分为表达性暴力和工具性暴力[12],表达性暴力发生于夫妻双方冲突时,暴力是愤怒与冲突的自然产物;工具性暴力通常是有目的性的、操纵的,常被用来作为权力与控制的工具,通常是夫妻中的一方加诸于其配偶。
以上施暴者的分类方式中,都有一种类型如Johnson[10]称为寻常夫妻暴力、Gottman等[11]归类为type II施暴者,而Holtzworth-Munroe与Stuart[9]则称为家庭内(family-only)婚姻暴力,我们建议称为轻型婚姻暴力,他们不具严重心理人格问题色彩,暴力多针对家人,而且暴力较轻微,多为表达性暴力。研究证实了这群施暴者的存在[13-14];而重型暴力施暴者则有人格偏差。此外调查发现,男性女性使用暴力的比例相当,都属表达性婚姻暴力[15-16]。轻型婚姻暴力可能是个案数目最多,而且是婚姻治疗师最常遇到的暴力形式[17]。
2 双轨制的干预模式
对于家庭暴力的探讨,始于1962年Kempe[18]发表关于儿童虐待的文章。20世纪70年代妇女团体陆续在美国各地成立受虐妇女的紧急庇护中心,与此同时学界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女性主义者亦积极游说立法,来影响干预家庭暴力的方式。婚姻暴力被界定为社会、法律问题;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的社工接获电话投诉或相关单位通报暴力事件时,公权力即进行基于女性主义观点设计的评估与干预。女性主义认为施暴者是受到父权思维的影响,对女性进行权力与控制,因此暴力都是施暴者的错,必须让他担负起全然的责任,同时也要保护受暴者不让她遭受二次伤害。如此形成夫妻分开干预的双轨制模式;对受暴者着眼于其安全,助其独立生活,提供庇护安置、心理支持、经济扶助、法律服务、住宅、就学以及就业服务;对于施暴者则依法提出伤害罪诉讼或申请民事保护令以防止违法行为。施暴者的强制性治疗计划都是经由法院要求进行的。基本上施暴者与受暴者的双轨干预不交叉,女性主义者并不赞成(或不提倡)夫妻共同接受治疗。
3 对施暴者的标准治疗程序
虽然目前美国对制定施暴者的标准治疗程序仍有些争议,但由于对治疗方式的质量和公共健康的监控的要求,以及对受暴者安全的重视,主张制定的一方占上风[19-20]。包括哥伦比亚特区的45个州制定了施暴者的标准治疗程序和/或管理规范,这比6~8年前的调查[21]在数目上以及在规定的详尽程度上都有增加的趋势。在干预的理论方面,美国95%的州采取女性主义观点,视家庭暴力为权力与控制的虐待形式,尽管心理学和心理病理学因素在某些标准里被视为可能的贡献因素[22],但35%的州禁止对施暴者采取基于精神科疾病模式、心理动力理论、冲动控制疾病、互相依赖、家庭系统或成瘾模式主导的治疗形式。最主要的理由是进行这些取向的治疗有可能让施暴者规避了该负的责任或危及受暴者[23]。目前最流行的两种治疗理论是女性主义和认知行为,女性主义理论通常是以男性团体治疗的形式进行的心理卫生教育,即所谓Duluth模式的性别平权的再社会化教育,参与者多为法庭判决的强制性治疗个案[24]。目前对许多社会而言,施暴者的心理卫生教育团体是首选,甚至是唯一合法的干预方式[25]。至于认知-行为治疗模式则企图改变施暴者对暴力行为的错误认知,并教导沟通和控制情绪的技巧。
不论任何取向,几乎所有的标准治疗程序都包含下列要点:①以受暴者的安全为第一考虑;②避免指责受暴者;③施暴者要为暴力行为负全责;④让施暴者了解他们必须学习非暴力的解决冲突的方式;⑤帮助施暴者学习替代的、非暴力的应对行为方式[21]。
4 婚姻治疗用于干预婚姻暴力的概况
美国98%施暴者的标准治疗程序认为团体治疗是首选的治疗形式[21],68%的州明令禁止在整个疗程里进行任何形式的婚姻治疗,其他32%的州则都限制只能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受暴者的安全无虞)才准予进行“非传统的婚姻治疗”(也有学者如Stith和McCollum[15]称为夫妻联合治疗)。
演变成双轨制模式的可能原因是:①婚姻暴力被定位为法律(婚姻暴力是犯罪)、社会(父权制度),而非治疗议题;②早期研究的样本都为庇护所的受暴妇女,或来自法院的施暴者,这造成婚姻暴力主要是男性对女性施暴的印象,并确立了保护受暴者的干预原则,因而限制了婚姻治疗的使用。限制使用婚姻治疗的立法形成恶性循环,它会让干预者即使对适合的个案也不进行婚姻治疗,因为女性常是较被同情的一方,干预者担心在治疗期间可能发生暴力所要负的法律及伦理责任。不实施婚姻治疗就无法积累经验、改善治疗的理论与技术,这会进一步限制婚姻治疗的使用,而且如此一来,要改变已然立法的干预模式就更不容易了。
5 婚姻暴力干预模式的成效
20世纪末,Rosenfeld[26]综述施暴者再犯率的相关研究,发现被逮捕而完成治疗的施暴者的再犯率(36%)与被逮捕而未完成或完全未治疗的施暴者(39%)相近。Davis和Taylor[27]将5篇研究的数据做了平均的效应量分析,结论是上述做法效果不明显(Cohen's h=0.41,P<0.50)。
21世纪初,Babcock等[28]查阅了22篇准实验(quasi-experimental)设计及实验设计的研究,发现减少暴力再发生的成效有限,参加完治疗者比未参加治疗者的再施暴比例只减少了5%。Feder和Wilson[29]进行的后设分析只纳入有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初始状态,或是有对照组的准实验设计的10篇论文,得到干预模式没有效果的结论。
婚姻暴力干预成效的文献中,为数最多的研究设计是单一团体治疗前后测比较[30],也有不少学者进行准实验设计的研究。准实验设计大多是比较完成治疗组与脱落或是未完成治疗者,这类研究最大的缺点是在方法学上,因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本质上的不同会得到有利于实验组的研究结果。本文只列举符合随机分组且有对照组的实验设计的研究,主要参考McCollum和Stith[31]、Eckhardt等[32]、Feder和Wilson[29]、Babcock等[28]、Feldman和Ridley[30]等的综述。其中,关于婚姻治疗的成效研究只有3篇,Stith等[33]发现婚姻治疗比夫妻团体治疗疗效差,Fals-Stewart等[34]发现婚姻治疗比个别治疗效果显著,Harris等[35]则发现婚姻治疗和婚姻团体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关于夫妻团体治疗的研究有Stith等[33]、Dunford[36]、O'Leary等[37],以及Harris等[35]的4篇,只有Stith等[33]文章发现夫妻团体的疗效优于婚姻治疗,其他3篇的夫妻团体的疗效均与比较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此外,愈后期的文献实验设计愈周详,除了暴力减除也逐渐重视治疗的间接目标,如Stith等[33]关注婚姻满意度及对暴力的态度。除了女性主义及认知行为外的其他治疗取向(如行为婚姻治疗、焦点解决取向)的研究也有变多的趋势。因为成效研究的篇数太少,对于婚姻治疗是否比男性团体或夫妻团体治疗有效的问题目前尚无定论。较为确定的是,对男性施暴者的干预模式在减少暴力再发生的效果有限[32],也没有证据支持基于女性主义的施暴者干预方案有效[28,31-32,38]。
6 主流干预模式的不足之处
目前主流的婚姻暴力干预模式是基于女性主义的双轨制干预模式,美国绝大多数州已立法制定施暴者的标准治疗程序或管理规范。经过几十年来相关领域学者的努力,一些新资料涌现,女性主义观点遭受严峻的挑战:①权力-控制策略与婚姻暴力关联性不大。权力-控制的策略,可能是某些,但显然不是所有婚姻暴力男性的特征,而且非婚姻暴力的男性也会使用这一策略[37]。②不是所有婚姻暴力都是男性对女性施暴。如Jose和O′Leary[39]报告36%~58%寻求治疗的夫妻,在前一年有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而37%~57%有妻子对丈夫的暴力;Whitaker等[40]对美国11370名18~28岁的成人调查发现,24%在关系中有暴力,其中一半是相互暴力,在单向暴力中超过70%女性是施暴者;此外,施暴者分型的研究[9-10]显示有各种施暴者,限制只能用单一模式治疗所有的婚姻暴力夫妻是不明智的[41],况且所限定使用的干预模式并未被证明有效[31-32,38]。
所以,已然立法的干预典范可能妨碍了某些方面的发展:①过于强调受暴者的安全、让施暴者负起暴力的完全责任,而阻止受暴者接受治疗,因而限制了婚姻及个别心理治疗的发展[21]。②过于强调女性觉醒,而忽略了提供孩子更稳定的生活环境。③用法律手段强制干预家务事,并未顾及许多受暴妇女不想与施暴者分开的主观意愿,这也激起施暴男性对干预的抗拒。传统团体治疗在开始的前3个月的脱落率高达40%~60%[42],以致司法强制治疗的效果相当差[29]。④现行的双轨制干预模式显然没有设置男性受暴者的庇护所,也没有针对女性施暴者的治疗。
7 实施婚姻治疗的优势
对婚姻暴力中施暴和受暴者双方经由处理关系中无效、甚至造成问题的互动模式可以预防再发生暴力[43],有助于所有家庭成员的心理成长。但并不是要对所有个案实施婚姻治疗,而是要谨慎地筛选。建议标准如下:①夫妻都有意愿参与治疗;②属于轻型婚姻暴力;③夫妻双方都有停止暴力、改善相处关系的意愿。
女性主义论者反对受暴者参与婚姻治疗,最主要的理由是治疗不公平地暗示着受暴者要负起暴行的责任。婚姻治疗师认为施暴和受暴双方应各自负起责任,前者要负起不使用暴力的责任,而后者要负起面对自己处境的责任;婚姻治疗师期待选择维持婚姻关系的受暴者勇于面对婚姻问题,为了自己及所爱(包括孩子或其他家人)的幸福,接受专业协助,处理相处的问题,因为用司法手段隔开双方,不足以解决婚姻暴力的关系问题。
支持实施婚姻治疗的论点包括:①学界迄今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男性施暴者的干预方案有效,相反,已有一些符合实验设计的婚姻治疗成效的研究[4,31];②既然施暴者并非同构型的[44],应针对施暴者或夫妻的不同特性施予治疗[31,45],我们相信应有某些夫妻适合用婚姻治疗;③目前美国普为施行的评估与干预都基于女性主义观点,这并不符合许多夫妻的生活经验,这会忽略婚姻暴力夫妻真正的需求[46],例如,有研究发现50%~70%的受暴女性重返暴力关系[47-48],在完全脱离暴力关系前,她们平均来回于庇护所和施暴者之间七八趟[5],可见受暴者希望结束的是暴力而不是关系;④受暴者仍与施暴者同住(或密切接触)的情况下,如果只处理施暴者,而未处理夫妻每天面对的子女管教、家务或是经济问题所引发的冲突,则不足以避免暴力再发生,因为典型的亲密关系暴力发生在夫妻相互争执的氛围中[49],男女两性使用暴力的频率相当[16,38],而且是双向的[50],促成配偶同时停止使用暴力较有机会成功地停止婚姻暴力[16,31,51];⑤婚姻失和是最强的暴力发生的危险因子[52],因此借由婚姻治疗促进夫妻和谐相处应能降低暴力再发率。
婚姻治疗优于其他治疗形式:①婚姻治疗师从夫妻的互动中很快就能看出施暴者控制的手段,以及控制在夫妻关系中的功能,这在男性团体和个别治疗中无法看出[53];②治疗师对受暴者的了解与支持,能让一时无法离开暴力关系的受暴者产生自信和能力,让她更有能力处理暴力关系;③婚姻暴力夫妻常犹豫于维持婚姻关系,婚姻治疗可以评估夫妻能否共同生活,或是协助夫妻平安地分开[54];④治疗师可阻断男性因受伤而使用暴力,强化他在关系中不使用暴力的承诺[55];⑤治疗中可以放慢动作检视夫妻的互动,并提供停止夫妻间不良互动的实际演练,增强施暴者的自我觉察、设身处地的共情能力和选择不使用暴力的能力,也可以增强受暴妇女保护自己和影响配偶使他发生适切行为的能力[56]。
婚姻治疗可弥补当前防治措施的不足:①有些夫妻不愿通报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因为他们担心公权力进入家庭的后果。这些夫妻可能因为冲突、痛苦或抑郁寻求精神科门诊或婚姻治疗的协助[57],接受婚姻咨询的夫妻中50%~65%有过至少一次婚姻暴力[58-59],由此可见婚姻治疗门诊是婚姻暴力防治重要的一环。②即使受暴者有保护令,甚至离婚也无法杜绝暴力,特别是有孩子的夫妻[60],因为许多持有保护令的妻子仍与施暴者同住,而且有许多惨剧发生在她拿到保护令时,因为保护令代表夫妻关系已经质变。如果受暴者拿到保护令的同时,能有治疗师与施暴者保持接触,关心他的利益,评估并处理他的情绪,受暴者的安全应更有保障。③夫妻关系痛苦与暴力的发生呈正相关[45],因此在持续的相处中,不提供夫妻服务对于选择留在关系中的妻子相当不利。④施暴者团体治疗中并未触及支持暴力持续发生的互动模式[61]与关系动力。⑤施暴者单方面接受治疗可能对配偶及婚姻关系造成负面效果。如,施暴者实践所学到的“离开现场”的技术,如果配偶并不知情,可能会觉得那是另一种控制或是惩罚的方式。⑥施暴者的强制治疗结束后,若没有专业人员协助夫妻磨合,无异于让受暴妇女处于危险中[62]。
总之,我们主张婚姻治疗最主要的理由是它符合某些婚姻暴力夫妻的需求;若未提供婚姻治疗,对那些仍旧留在原来的家庭环境的妻子相当不利,也无法帮助施暴者完成强制治疗后仍想共同生活的夫妻。何况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建议审慎考虑婚姻治疗的适用性[46],也有愈来愈多文献显示婚姻治疗的疗效并不亚于传统的男性团体治疗[7,32,34,37]。对婚姻暴力夫妻施行婚姻治疗必须严格筛选个案,在选案时,治疗师会考虑安排跟夫妻分开会谈,除了留意受暴者会不会害怕和施暴者一起谈话,也要留意施暴者对暴力的态度,及其停止使用暴力的动机强弱。在进入婚姻治疗之前,治疗师要跟夫妻签订“非暴力契约”,约定如果在治疗期间发生暴力的处理方式。一般约定若发生暴力,治疗师会详细了解暴力事件的始末,并分别跟夫妻讨论是否继续治疗,包括治疗师在内的三方中,只要一方不愿意就停止治疗,然后治疗师要作适当的通报或转案。在整个治疗历程中治疗师必须对权力敏感,也要对暴力再发生提高警觉。至于婚姻治疗同时处理夫妻双方,是否能比双轨制更有效、更节省社会资源,是非常值得后续研究探讨的问题。
8 结论与建议
婚姻暴力是社会法律也是医疗实务的问题。美国对婚姻暴力的干预是从无到有、由下而上发展起来的[63],但立法却由上而下地限定干预的方式,这不仅压制婚姻治疗及其他心理治疗理论使用于婚姻暴力的干预,减少经由实务经验的反馈而调整干预方式的弹性,也造成强加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于发生暴力的丈夫与妻子的弊病,以致未能以受暴者及施暴者本身的需求为主要考虑,亦即,不是问夫妻要什么,而是认为他们应该改变成什么。这种情形下最不幸的结果在美国发生了,那就是法定的干预模式效果不佳的同时却难能改变现行制度。因此我们建议尚未法定施暴者标准治疗程序的社会,应将婚姻治疗纳入更大的干预模式中,优先对有意愿共同生活、改善关系的轻型暴力夫妻施行婚姻治疗,积累实践经验并实验设计成效研究,以制定更合乎婚姻暴力受暴者及施暴者需求的政策。
2011-08-09收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