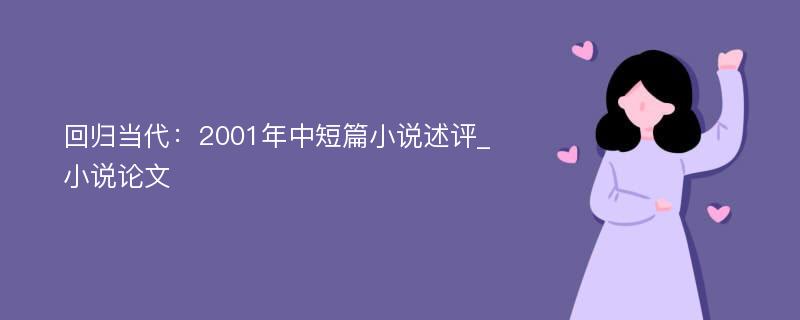
重新回到当代——2001年中短篇小说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短篇小说论文,年中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末”是缠绕过去十多年文学的一个阴影似的概念,当人们走出世纪末沐浴在新世纪 阳光之下,发现“世纪末”的情绪是何等的脆弱和矫情。摆脱“世纪末”的阴影,在新世纪 文学的浪潮中重新树立文学的理想精神、重新确立文学的当代意识,重新建立文学的审美价 值,使成为2001年一种新的小说意识。
时间不是没有重量的,从世纪末到世纪初,人们的生活会有一种重新开始的感受,而中国 社会在国际地位的变化,申奥成功、加入WTO等一系列新世纪带来的新气象,为当代生活的 意识无疑增添了新的内容。作家的当代意识无疑在这种变化的当代生活中得到了强化和补充 ,其价值取向和审美视野也逐渐发生位移,因而2001年的中短篇小说便呈现出一种与当代生 活同悲欢、共命运的格局。
与当代生活同悲欢、共命运
2001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有意识地拉近了与当代生活的距离,当代生活的丰富多姿与变化 多端在作家们的笔下得到真实的迅捷地抒写,池莉的《看麦娘》、方方的《新杀夫记》、张 者的《唱歌》、许春樵的《一网无鱼》、刘心武的《京漂女》、汪淏的《从夜晚开始》、 申维的《第六代》、唐颖的《告诉劳拉我爱她》、程青的《艾琳访谈录》、东西的《我为什 么没有小蜜》等都重新再现了文学的鲜活感,在他们的小说中,都能感受到当代生活清新的 气息和可以触摸的实感,都能感受到当代生活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动荡。
池莉是这几年当中值得注意的作家,如果早在80年代末期,池莉便从《烦恼人生》、《不 谈爱情》等小说成为新写实的探讨一种“零度写作”的可能的话,那么近年来的池莉小说则 进入了自由写作的状态,她对当代生活的关注,不只是对普通人群生活状态的关注,不只是 还原他们的原生态,还关注他们心灵的波动、情感的涟漪。《看麦娘》和《过着声名狼藉的 日子》都是池莉以独特的视角来观照当代生活变迁的优秀之作,将当代生活的喧嚣与繁杂巧 妙浓缩在一个女性的视角之中。《看麦娘》显得尤为突出。“看麦娘”是一种植物,当地老 百姓俗称“狗尾巴草”,因为“看麦娘所有的草穗子都会护着麦地,无论日出日落”,所以 这个本来从欧洲过来的植物就有了非常中国化的名字。“看麦娘”成为整部小说的一个经典 性意象,“于世杰曾经陪我去父亲的麦地里散步,当我满含泪水,试图告诉他这些貌似相同 植物的细微差别和不同名字的时候,于世杰频频地看手表,然后失去耐心地插话道:‘还不 就是狗尾巴草吗?’”。小说中“我”和于世杰的冲突,不只是夫妻情感的冲突,而是两种 价值、两种人生的冲突,小说围绕寻找失踪的女儿容容展开了一系列当代生活图景,而“我 ”和丈夫于世杰的貌合神离,已不是婚姻意识上的破裂,而是不同价值观的碰撞。“我”留 恋的生活,热爱的理想是与“看麦娘”一系列意象相关的,与麦地、田野、星夜、理想这些 美好的记忆相关,于世杰则是活在现实之中的人,他关心的是金钱、地位、时尚和虚荣,当 “我”死心塌地要去寻找养女容容时,于世杰怎么也不能理喻。
《看麦娘》属写实类的作品,但池莉却能写出境外之境,意外之意来,小说的主人公找女 儿容容,但容容并不是记忆中的看麦娘,容容因经营负债失踪,容容是一个比于世杰还要于 世杰的混世小魔女,这让我“我”的寻找带上难以言清的悲剧色彩。小说中另一个意味深长 的人物是上官瑞芳,这个惟一能和“我”沟通并达到心灵默契的人是容容的生身母亲,但她 却生活在精神病院之中,因为她生活在昨天。艺术和幻想之中,容容和上官瑞芳都是两个极 端的人,而“我”和于世杰都仿佛是他俩影子似的活着。在小说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作家与 当代生活的切身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加入生活的合唱,而是带着真实的感受去抒写,带 着疑虑、困惑甚至拒绝来看待生活。池莉将“我”的名字取为“易明莉”,更表明作家对这 个人物的认同倾向,也表明作家从“新”写实走向“心”写实。
许春樵的《一网无鱼》可以作为《看麦娘》的“男性版”阅读,小说里的主人公是个乡村 的诗人,来到城市打工,看不惯俗世的浑浊和虚伪,他就到网上的虚拟世界去寻找慰藉,也 不肯在现实生活中妥协。这个倔强的诗人显然是作者精神的一种虚构,也是一种寄托,以拒 绝的态度来面对当代生活。不只是一种观念的排斥,而是心灵的回避和抵抗,正是当代文学 的另一种心路的历程。
进入当代生活的多种方式
描写当代生活是当代文学的一个传统,但这个传统曾经受到了挑战,一度时间也受到了作 家的冷落。当代文学反映当代生活,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历史上虽然不乏写旧的生活的经 典之作,但在任何时代的文学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无法不正视当下生活,无法不面对当代生活 的变迁。在80年代曾经出现过描写古老、描写蛮荒、描写原始的“寻根文学”潮流,远离了 当代生活。这与我们当代生活的观念化单一化可能相关,为什么会出现“伤痕文学”、“反 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些主潮流的思潮?因为它们确实是当时生活的最重要的内容,而 现在的当代生活进入了丰富多彩的正常状态,已经很难用一种概念或一般思潮形容我们的当 代生活,当代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为作家的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在如此丰富的生活面前, 作家不会简单依附于某种思潮,也不会只是一个时代的传声筒。
张者的《唱歌》是他校园系列中的精彩的一篇,这是反映大学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实小 说,其格局有点似钱钟书的《围城》,一个法学教授与一群研究生,在市场经济浪潮的袭击 下,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动荡,因而上演了一出出人生的悲喜剧。90年代中期曾经讨论过 “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可当我们在《唱歌》中看到一群兴高采烈在世俗之境中狂舞的师 生们,就愈发觉得知识分子的脆弱是值不得夸耀的。汪淏的《从夜晚开始》,也属于困惑 类的小说,主持人尤扬可以在电台解决很多听众的心理的问题,可尤扬的心理困惑却无人能 解。尤扬按照今天的知识分子分类法,该属于“传媒知识分子”,但无疑是“学院知识分子 ”,还是“传媒知识分子”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悖反,就象高明的理发师能够帮别人理出各 式各样的发型却无法面对自己的发型一样。知识分子的这种当代困惑,不只是面对生活的动 荡变迁之后的困惑,而是人文主义者永久的困惑。
唐颖《告诉劳拉我爱她》是2001年让我读后大感意外的小说,当更多的作家去试图理解生 活,且阐释生活时,唐颖却以她独特的思维方式告别人们,生活不是拚搏,而是心灵的平静 ,是对生活美的享受。这或许与唐颖旅居海外的生活感受有关,可她至少为我们开启了生活 的另一扇窗户,在另一个层面上与当代生活息息相关。陆离的《到佛罗里达》按照流行的文 学分组法,该属于“留学生文学”的范畴,可陆离好像不在意“留学”与“非留学”的概念 ,也没有夸张地表现中西文化的冲突,而是隐隐地写到经济对人的制约和影响,把“贫贱夫 妻百事哀”那种人性的切肤之感写得微妙而传神。
刘心武的《京漂女》、申维的《第六代》、程青的《艾琳访谈录》是介入当代生活的另一 种方式,这些作品都属于描写“他者”的小说,而且又是描写“圈内”生活的小说,因而他 们在叙述时都保持着某种客观,或者说做出某种客观状,因为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可能是作者 的朋友,也可能是熟视无睹的一些人,当然还有《京漂女》那样的采访对象式的熟人。这些 艺术家或准艺术家的生活状态或许更能体现当代生活的种种变迁,《艾琳访谈录》中的那个 艾琳我们曾相识,她的发迹是一个当代神话,而那个落泊的第六代导演丁建成,又是当代艺 术生存情境的一种写照。刘心武的《京漂女》中的“京漂们”,已经成为北京文化的建设者 ,而这正是作家没有意识到的。
北方的《四如意》是2001年小说中的别调,他对风尘社会的描写以一种白描式的零度叙述 ,因为缺少批判的力度而会引起人们的不满。虽然作家的主观情绪过于暧昧,但不能不承认 ,《四如意》所展现的当代社会那段阴暗而龌龊的人生,虽然只是残余地存在着,但如果我 们把《四如意》和《看麦娘》比较起来阅读,便会发现它们是当代生活的正面和负面,就像 一个镍币一样。当“妓女文学”“妓女电影”被传媒争论不休时,《四如意》不动声色地展 现了另一种世俗风情画,我们可以鄙夷,可以摒弃,但无法不承认它是生活的千分之一,或 万分之一或亿分之一。
审美不拒绝“零距离”
“零距离”是2001年的关键词之一,这个由中国足球传媒圈引发出的概念,正在广泛地使 用,申奥成功——中国与奥运会零点距离;加入WTO——中国与世贸组织零点距离;中国队 冲 出亚洲——中国足球与世界杯零点距离;……等等。而文学与生活的距离也慢慢地拉近,这 种拉近不是人为的,这种变化是两方面作用力的结果,一是前些年“个人化写作”的思潮让 一些作家从历史的记忆,寻根的古趣中走向当下生活,而个人生活仄逼让他们把视野投响更 广阔的生活领域,二是读者的呼吁和制约,这些年读者冷落文学的原因,是因为当代文学缺 少当代生活的鲜活和迅捷,当所有作家都去经营传世之作时,读者宁可去读那些经典的传世 之作。前几年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对广大读者和文坛的冲击,更加说明当代 生活的变迁,当代人心灵的波澜仍会引起文学的“轰动效应”。刘恒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某种 “零 距离”的体现,一是与当代生活的“零距离”,张大民的“房子问题”是北京人的问题,也 是全国人的问题,它是社会的热点,而另一个“零距离”,则是小说与作家的血肉联系。刘 恒告诉我,他在写这部小说时曾经几次号啕大哭,不能自己。而池莉近期的小说也不时融进 自己的经历和心态,这种“零距离”的尝试,说明文学的“我”(不只是主人公)永远是其他 载体无法替代的心灵使者。
审美理论上有一种“距离说”,意即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要保持适当距离才可能发现美, 同时才能表现美。因而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便有一种贬新扬旧的批评倾向,理由就是有了距离 才能过滤掉生活的杂质,有了距离才有比较,因而美不在当代,不在现实。其实,这是一种 以偏概全,是一种古典主义的美学理想。现代美学的概念,并不是建立在距离的长短上,尤 其电视的“现场直播”的方式出现之后,更新了审美的时间方式。我们在看奥运会、维也纳 新年音乐会等节目时,都是由电波及时传递给我们,我们感受到的并不只是新闻价值,还有 很多的审美价值。而当代艺术强调介入性(比如行为艺术)之后,审美不只是历史主义的旁观 和远视,也近距离或无距离地置身其中。
当然文学上的这种“零距离”表现在叙述上要更为复杂一些,这里就张者的《唱歌》和申 维的《第六代》作一些说明。《唱歌》是用第一人称写作的小说,因为小说里时时出现“我 ”,是“我”在叙述,但这个“我”与池莉的“我”不同,池莉的“我”不仅担负叙述故事 的任务,“我”还是一个重要人物,“我”甚至就是小说的主人公,而《唱歌》的“我”只 是快乐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中的生活是没有距离的,但小说生活和人物又与“我”没有 关系,这种“零距离”其实是一种距离,是一种“无我”的距离,因而《唱歌》中的那些人 物和故事既亲切,仿佛在身边,又生疏,“我”并没有介入。这种审美上的两种距离就像小 说里的两种事件一样具有张力和变化。而申维的《第六代》是一篇无“我”的小说,但小说 里那种对人物近距离和无距离的叙述,又让你感受到“我”无时不在。《第六代》里的主人 公丁建成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因为真实,显然作者始终用小说虚构的笔法来遮蔽这种纪实性 ,但遮蔽本身就产生了与人物的亲密性,你会感到作家与丁建成的“零距离”,因为那些生 活细节、那些细微的感受,并不是体验和想象的结果,而是由作家这个叙述人转述出来的。 转述本身又产生了距离,这使得这篇小说在叙述上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苏童的《女同学们 二三事》也有类似的叙事特点,这位描写女性的“红粉圣手”写的虽是女同学的旧事,但他 的笔端不经意地把她们拉到当下生活之中,当代生活的变迁,人物命运的无常便自然呈现出 来。
描写当代生活,正视当代生活,并不是从2001年开始,也不会从2001年结束。文学表现当 代生活,什么时候都会是一个挑战,什么时候都会有优劣高下之分,我欣喜地看到,当代作 家认清这个文学的基本原理,并勇敢地接受这种来自生活的挑战,也是对文学的单一、文学 的冷落的挑战,当文学不能成为传声筒也做不了象牙塔时,文学与当代生活的联系就比任何 时候更加密切了。我想用《看麦娘》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述评,也许是合适的:
“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无论太阳从东边或者从西边升起,无论我们的女儿什么时候归来, 上官瑞芳,我们都更要力争平静度过每一天。只有我们自己的生命,在轻轻生长过程中的那 些感受,那些只有我们俩人领会到了却永远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它将与我们的终身如影 随行”。
2001.12.14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