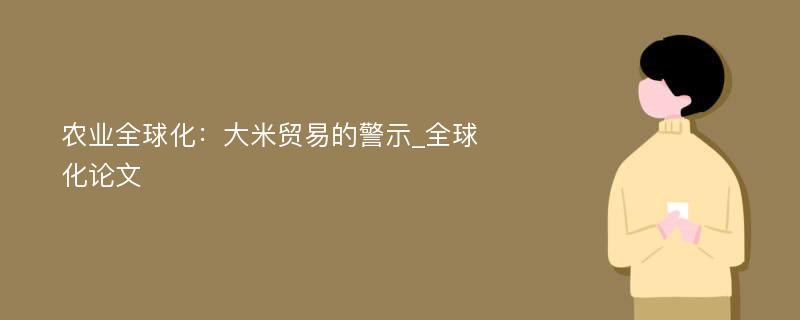
农业的全球化:大米贸易的警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米论文,农业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全球化”概念已在政治领袖、新闻记者、权威的评论员和大学教授中成为极其流行、极具影响并广泛谈论的术语。尽管大学教授们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显得较具训练、谨慎和有眼力,但“全球化”大体上依然是一个漂浮不定、难以捉摸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本身的发展历史还不确定。本文的目的是试图为“全球化”定位:界定这一概念并使其专门化和历史化。我将采用一个两重的叙述方式来实现本文的目的:第一,我将审视过去各类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并提出我自己的理解;第二,我将通过对农业的一个案例——世界一体化大米市场的形成——来捕捉和表达存在于真实世界中而非图书馆、办公室和沙龙里的与全球化相关的各种机会和问题、可能性与局限性。
在深入讨论之前,让我先把我的整个看法列成以下四个要点。第一,“全球化”并不新颖,它已有很长的历史;第二,在全球化的要旨、主张、议题、争论、问题和恐惧等诸方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全球化正似乎是在重复和再现很久以前农业全球化时所导致的现象;第三,如果大米贸易的案例具有启示性,那么全球化将会产生复杂的结果;第四,至少从经济上来说,全球化并不是不可避免,或只有单向度发展和不可逆转。
(一)
鉴于本文是“全球”经济史论文,因此,我想先就本文的方法和其它表面看来相似的“世界”和“国际”经济史的方法做一区别。我认为,全球经济史的方法在于它具有全球整体的有机性、跨文化性和关联性,其它方法则只具有全球整体进程中的板块性、定点性和附带现象的性质。“世界”和“国际”经济史的方法通常趋向于以比较狭窄、孤立和双边的方式来研究历史问题,甚至是重大的历史问题。用经济学的一个形象描述来说,世界和国际经济史的方法是“部分”而非“整体”均衡的方法,没有部分与整体间反馈的回路,更不显示部分与部分辫状交织为整体的螺旋。基于以上的简短描述,我们可以开始检讨两个议题:全球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大米市场的形成、后果和意义。
在过去几年里,含糊和捉摸不定的“全球化”概念在新闻界和学术界导致了一些富于启发性的二元形象,举两例来说:“流线车与橄榄树”,“伊斯兰圣战与美国化世界”。(注:文中所提出的形象取自于两本最近出版、广受注意的论述全球化的书名:Thomas L.Fa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New York:Frrar,Straus and Giroux,1999);Benjamin R.Barber,Jihad us.McWorld(New York:Times Books,1995).)并且,在作为“进程”的全球化和作为“感性”的后现代主义接踵而至时,一批晦涩、如果并非全然不可理解的二元形象的“替代表述”也浮现出来。例如,对罗兰德-罗伯荪来说,全球化意味着一个“普遍中的特殊性和特殊中的普遍性的双重进程”。(注:Roland Robertson,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2),pp.177-178.)更晦涩的表述来自于高深莫测的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在他看来,全球化是“在它的部分之间加剧二元关系的一个不具有整体性化的整体。它的部分——主要是民族国家、但也包括地区和社群,仍然继续通过‘民主国家实体’这一模式来表达它们自己(但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其它模式,例如,社会阶级?)”。无论这有多令人迷惑,詹姆森还只是刚来劲:“尽管这些二元关系、或者说点与点对应关系已经不同于复杂整体中的地域之间或部分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仍需为这些二元关系们加上一些含蓄的界定:它们最首要的是紧张与对抗,但不是完全排斥;每一元都是借助二元中的另一元来按自己意志而努力表达自己……”(注:Fredric Jameson,"Preface,"in Fredric Jameson and Masao Miyoshi,eds.,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p.xii.)詹姆森继续说,假如以上的表述也可以被称作“全球化”——用克莱尔·露斯准确的、并且经济学家保尔·克鲁格曼也如此采用的术语,那么我认为以上的表述至少显示了“全球化”概念的一些具有同一性和分析性价值的东西。(注:Paul Krugman,The Accidental Theorist and Other Dispatches from the Dismal Science(New York:W.W.Norton,1998),p.73.)
广义来说,我们都本能地知道或至少认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全球化,但问题是如何从分析的语言为这一概念定位。我们当然也很难从路易·阿姆斯特朗那儿得到启发——这位伟大的爵士小号演奏家在被问到什么是爵士时回答道:“如果你需要问,那你将永远不知”。让我们离开对概念满是云雾的转述,从具体化开始。我们实际上有过一些关于全球化及其后果的非常有用的著述。例如,有一部著述这样写到:全球化者“使得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具有全球性”,结果是: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催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的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以上的引述虽然语言上有些文学化,但它们值得敬重。它们不是出自于威廉·葛雷德尔或爱德华·鲁瓦克的新近名著,而是出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50年前的《共产党宣言》。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者”的确抓住了全球化的精神,虽然使用的是不同的术语:我称之为“全球化者”的群体,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
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以“摧毁”全球化的——或资本主义的表面“覆盖物”之描述性语言多么有力,但其它更严格、或至少更具证明性或因此而更具证伪性的方法也是可能的。例如,在界定全球化时,我们可以强调变化与进程,把重心放在跨国界的劳工、资本、产品、服务等的流动、以及它们绝对规模的增长;或者更有效地从“相对”重要性来衡量这些流动的增长。克鲁格曼就经常研究世界贸易增长率和世界生产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以它们作为衡量全球化的方法:即当前者持续地高于后者,那么所谓“全球化”的进程正在发生。(注:Krugman,The Accidental Theorist,p.73)虽然还用不着我来批评这一方法的定义上的简明性——我在原则上也很吝啬使用批评的语言,但把全球化简化为一种计量的比例对我来说也还是有点格格不入。我较赞成从世界贸易的相对重要性角度来诠释长期增长。例如,把这相对重要性的长期增长视为:经济生活结构、组织、运作中一些更深层、更复杂、本质上更有意义的“计量”变化的体现和表达。
正是遵从于这样的原则,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把全球化定义为:“产业和服务业行为(比如,研究和发展;投入、生产和分配的资源的使用)和跨国界的公司网络(比如,通过合资和共享资产)的地理扩散”。(注:Graham Bannock et al.Dictionary of Economics(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98),P.176.)这一定义可能不典雅,但它具有很强的描述力,甚至剖析力。从这一角度出发,社会理论家曼努尔·卡斯特尔斯强调相互依赖性、规格、服务、同步性,把全球经济定义为“基于一个星球在真实时间里运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注:Manuel Castells."European Cities,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and the Global Economy,"New Left Reuiew,Number 204(March-April 1994),P.21.)托马斯·弗里德曼也是这样强调计量性:当“每一个人”感到世界贸易重要性的相对增长给他们带来了压力、限制和机会时,而技术、金融和信息也在同步“民主化”时,那么全球化已经出现。(注: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ue Tree,p.59.)弗里德曼这里采用了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弗尔南德·布罗代尔在分析资本主义起源和扩张时的同样方法。在《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及其他著作中,布罗代尔强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一个地区有足够的人受到“资本主义”市场、行为、观念的影响,而使得“其它”市场、行为、观念日益不再重要、不再富有意义、甚至过时之时,那么资本主义已经出现。(注:Fernand 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1400-1800,trans.Miriam Kochan(New York:Harper & Row,1973),pp.xi-xv and passim.)我们能用“全球化”替代“资本主义”、“全球的”替代“资本主义的”吗?可能不行。但是,把一定的量的比例综合在一起——某一些或另一些事物的量在一段相当长时间内跨国界流动的相对增长——然后使用前面提到过的一些计量“方法”,我们能够从脉络上把握——如果不是完全地——难以驾驭的“全球化”概念怪物,而不是毁了它。
(二)
我下面要做的,是把上述有关全球化的概括议论与全球大米贸易的“具体事实”联系起来。这些具体事实显示了全球化的复杂性——如果不是它的矛盾性,因为当今世界大米市场的特点是“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白热化的出口竞争,而它们生产稻米的方式又是非常、非常地不一样。两个简洁的例子可以使我的论点明朗。
1996年6月我去了阿肯色州几周,就美国的稻米业做档案和实地的研究。在那儿,我花了一周时间在当今美国稻米业的中心:阿肯色州中东部的“大田野”地区,访问了德维特、福斯特城等地方,特别是著名的水稻试验区所在地斯图嘎特。在斯图嘎特我与一些土壤学家、植物基因学家进行了交谈,并与美国最大的稻米合作组织“稻田食品”的前主席斯特瓦特·杰苏普一起度过了很多时间。我访问了朴实、但在许多方面都很吸引人的斯图嘎特农业博物馆,并且也与一些农具商进行了交谈。这些访问使我学到了很多,但更多地学到的却是在田野里。斯图嗄特是世界上最先进、最资本集约化的“水利农业系统”的所在地。它是一个广袤的水利灌溉世界:播种和撒肥都由飞机进行(1996年美国基梯伊公司斯图嘎特的电话指南上登录了27家飞机撒播公司的号码)。它也是一个由摇控拖拉机、耕播机、收割机组成的自动化世界:使用卫星指令的全球定位技术、分布距离计算机、爱荷华州阿姆斯市梯尔思实验室研制的激光测控系统来进行管理,能根据土壤的需要、过去的产量、可能的潜力把化肥按需要量和不同配方精确地投撒到每两三英寸土地。最令人感叹的是,它还是一个没有人的世界:在广阔的田野上,两个农业工人可以轻易地耕种750英亩的土地(注:1英亩=6.07亩,1英磅=0.908市斤——译者注。),平均每英亩收获5500英磅净米。的确,如果不是这儿一座铝棚、那儿一座灌站,它简直没有生命的痕迹,它造出了一种奇怪的不现实的陌生文化的大地景象,使我更多地联想起小说家唐·德里罗或弗里德利克·巴瑟尔密,而不是撰稿作家文德尔·贝里为我们所描绘的田野风光。我在斯图嗄特的访问中学到了许多。(注:请参考另一项对阿肯色州“高技术”农业的描述:John Fraser Hart,The Land That Feeds Us:The Story of American Farming(New York:W.W.Norton,1991),pp.301-314.)
1997年6月我访问了缅甸,这是我1993年以来四度访问过的国家。1997年的这次是我第二次被允许利用一个档案馆:仰光的大学中心图书馆里的专门档案。更重要的是这次我访问了一个村庄——固平朝(Go-Pin-Chauk),距三角洲低地勃固行政区的比林大约两小时汽车路程,在比林的南面。我会见了村长:一个制作手推车的匠人,并由他引见,在紧挨着村边稻田的一座高跷草屋楼下会见了十几个谷农,在一起的还有两个缅甸语翻译、一群各色各样的孩子、一匹马、两条奶牛和一条水牛。我向这些20多岁至80多岁的谷农们提问,倾听他们挨个地回答。
固平朝远不是斯图嗄特可以想象的。大部分缅甸的农村没有电(当然也没有全球定位技术),只有很少几条铺过的道路,基本没有农业机械,只有原始的水利控制。“绿色革命”的一揽子计划——高产种子、商业化肥、农机设备等曾经被断断续续地尝试过,但固平朝的大部分稻作依然仰仗于人力工具、水牛和季风。(注:实地笔记,Go Pin Chauk,Bago District,Lower Division,Myanmar,January 1997。关于今天缅甸农业的相对落后状况,请参阅:Peter G.Warr,"The Failure of Myanmar's Agricultural Policies."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00(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0),pp.219-238.)
尽管斯图嗄特和固平朝在形象上和事实上具有天壤之别,但它们今天无可选择地在全球大米市场上成为竞争的对手,正象它们过去也是对手一样。美国和缅甸,加上泰国,如今再加上越南,是世界上四个主要的大米输出国。虽然斯图嘎特和固平朝各有一些“富有”的农民,但缅甸今天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而阿肯色也是美国最穷的地区之一。如果把斯图嗄特、固平朝以及其它大米输出地区放在一起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将向我们展示一段几百年前就开始了的既有趣又有意义的历史。我在这段历史的研究上已出版了很多著述,不应在这儿再重复自己。我想做的是:简洁地回顾一下大米贸易的历史,然后向读者警示全球化可能为我们创造怎样的一个未来世界。
(三)
为了理解大米全球市场的形成,我们首先必须把它嵌入一段范围更广的历史之中:资本主义的扩张和精致化。资本主义的成长可以说是过去五百年世界史上最重大的发展。长期以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做了长期和艰苦的研究,以解释资本主义的成长以及它内在的动力。虽然学者们在细节和侧重点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都认为:资本主义(或更广义地,市场社会)的演进使土地、劳力、资本从“传统的”或非市场性的压抑下获得了进步性的解脱,并使这些“生产因素”相应地个性化、连接化和商业化。但由于这些生产因素转型的过程在时间上不平衡,尖刻的学术辩论一直集中在西方以及非西方“传统”和市场”的社会何时分野问题上。这些辩论也许都不切要点,因为更重要的不是分野时间的准确性,而是理解市场社会长时段进程本身的力量和性质。这一长时段进程或许始于12或13世纪,但在17世纪,这一进程在西方肯定已经开始,并在20世纪早期得到完成。(注:有关这些问题更完全的讨论请参阅:Peter A.Coclanis,The Shadow of a Dream:Economic Life and Death in the South Carolina,1670-192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13-15,190-192.)我们可以通过对一个整合的全球大米市场形成的进程进行分析,以了解资本主义进步的一个有限、但有启示意义的方面。这一分析至少可以部分地展示资本主义的“本质”或以亚里士多德在“话语时代”之前的术语来表示的“生命原理”。
虽然大米贸易在亚洲许多地方已有千年多的历史,但这一谷物只是在17世纪才在“西方”成为一项具有重要市场意义的商品。(注:底下的内容大多出自于我即将出版的一部关于国际稻米贸易的书。如果想看实例研究,请参见:Peter A.Cocianis,"Southeast Asia's Incorporation into the World Rice Market:A Revisionist View,"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4 (September1993):251-267;Coclanis,"Distant Thunder:The Creation of a World Market in Ri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it Wrought,"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8(October1993):1050-1078;Coclanis,"The Poetic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The U.S.Rice Industr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Agricultural History 69(Spring 1995):140-162.如果想了解其他的有关世界大米贸易的计量数据,请参见:H.J.S.Cotton,"The Rice Trade of the World",The Calcutta Reuiew 58(1874):302;V.D.Wikizer and M.K.Bennett,The Rice Economy of Monsoon Asia(Stanford,Calif.:Food Research Institute,Stanford University,1941),pp.320-327;Norman G.Owen,"The Rice Industry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1850-1914",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59(July 1971):75-143;A.J.H.Latham and Larry Neal,"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Rice and Wheat,1868-1914",Economic History Reuiew 36(May 1983):160-180;Randolph Barker et al.,The Rice Economy of Asia,2 Vols.(Washington,D.C.:Resources for Future,1985);A.J.H.Latham,Rice:The Primary Commodity(London and New York:Poutledge,1998).)它在西方的出现值得重视并非因为大米贸易的量对西方早期近代的影响,而是因为在这一时代中欧洲人开始雄心勃勃地扩展、控制、重塑大米贸易,使其在日后成为“全球”和“常规”的贸易,不再象从前那样是地方或区域间的间歇式或非常规化的贸易。
断言大米贸易在17世纪的西方开始变得重要并不意味在此之前大米贸易不存在于西方。我们已确知在早期近代以前,大米贸易就存在于地中海沿岸,并在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来来往往,但贸易的市场是很有限的。在17世纪,欧洲其它地区人口的增加和收入的上升导致了整体需求的增长,这必然并足以巨大地扩展和深化了西方的大米市场。北欧,特别是日耳曼诸王国急速增长的大米需求不仅成了欧洲大陆大米贸易的焦点,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成为西方大米贸易的焦点。
从大米在亚洲的优越地位来看,欧洲的大米贸易显得奇怪,甚至有点异乎寻常。尽管17世纪大米有着市场收益,但大米从未吸引过西方的消费者。在东方世界,这一谷物的力量是日常食物的全部;但在西方,大米只是日常食物的一种多功能和便宜的替代品或补足品。它特别被用于喂饱游民群体——士兵、孤儿、海员、监狱犯人、穷人等等,补缺或替换更合口的食物。准确地说,大米还有其它用途:它常常被用来喂养动物,还具有多种工业用途。但很清楚,在西方,大米从来没有被视为赖以生活的物品。
因此,不象小谷(小麦、大麦、黑麦、燕麦)那样为欧洲人所钟爱,大米注定了是可有可无的。其次,也不象糖、烟草、棉花等在早斯近代崛起于欧洲市场的商品,大米有许多近似的替代物。如果上述的特性限制了大米的力量,那么它们也同样使大米在西方的每一处都具有销售性。我们最终发现大米商品在一个广袤的地区被大量交易:从秘鲁和阿根廷直到黑海的沿岸。尽管大米的力量有限,但西方的大米市场是如此的有力,以致于它在1700和1920年间足以塑成和摧毁好几个经济实体。我们下面会看到这些例子。
在18世纪之前,欧洲的大米贸易大多起源于意大利,主要在波河上游肥沃的冲积谷地,即皮蒙特和伦巴第。一些西班牙的大米也找到了途径进入欧洲市场,还有一些不时地通过地中海群岛而抵达的印度大米。这些地区都不依赖于大米贸易,国际上对大米的需求量也不影响它们的经济状况。但在下两个世纪中,由于欧洲资本主义扩张和精致化,一些新供给者被卷入欧洲大米市场。这些新供给者的经济命运紧密地和国际上对大米的需求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似乎不相干的南卡罗来纳州和低地缅甸、乔治亚州和暹罗会在经济上联结起来。
18世纪以后,欧洲大米市场越来越成为所谓“边缘地区”的产物,显示出老与新的大米帝国不断地在将希望变为事实。无论倾向于以“相对优势”或“都市主宰”的方法来解释国际贸易的范型,我们都会发现南卡罗来纳、乔治亚、低地缅甸、暹罗、印度支那——18和19世纪西方大米的主要供给者——与教科书中的出口外向型、单一生产经济体的案例非常一致,几乎就是教科书案例的拙劣的翻版或模仿。如果这些地区的出口情结是根本性地由欧洲资本和资本家所创造,那么欧洲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边缘地区的商业主动合作者和他们的继承者所鼓励和诱使。
与某些学者的想法相反,这些经济实体形成如此的结构,并非它们有天生的缺陷。事实上在某些时候,基于单一生产和出口的经济战略可以导致持续的增长和发展,毕竟,按照艾尔伯特·赫希曼著名的“非平衡增长道路”理论来找出一些相应的地区和国家的例子并不难。(注:See Albert O.Hirschman,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uelopmen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如果想看最近的对“非平衡增长”模型的重新建构与提炼,请参见:Paul Krugman,Geography and Trad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1).)然而,就我上述提到的经济实体来说,单一生产却导致了不同的后果,这正是我所希望解释的现象。
上述的每一个经济体最初都从外向型的稻米生产专业化中受益。例如,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的稻米区——建于1700和1750年间,依赖于奴隶劳动力的一个种植庄园群——可以说是1770和1820年间世界上最富的农业区。此外,英国人所鼓励的“缅甸三角洲”转型曾把这一地区从疆野转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地带,至少,在1855至1900年间增长了缅甸农民耕作者的收入。甚至爪哇——曾经一度成为西方大米的又一个主要供给者——在19世纪上半期荷兰人对这个岛的经济渗透加强时似乎也偶尔从大米出口增长中获益。
然而,上述每一个地区的长期发展——以及意大利、巴西、孟加拉、西班牙、印度支那的大米出口地区——最终都因面向西方的出口专业化而受挫,在西方,大米只是一项次要的、具有弹性价格的商品,它有许多相近的替代品。大米,象今天的许多农业产品一样,已被证明是一宗为发展而押错了的宝。上述每个地区都有过各自的“市场时代”,但随着技术创新促进了市场的整合和加强了竞争,每个地区都又依次地眼看着自己的市场时代消逝。
鉴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无情”逻辑和每一时代国际大米市场的限度,这些因素决定了只有最廉价(或最优化连接市场)的供给者才会繁荣。因此并不奇怪:大范围的竞争优势一旦失去之后,上述的每一个经济体都陷入了停滞和衰落。上述的每个经济体都曾追求它的短期“相对优势”,但一个短期框架中所具有的经济学家们信任的“经济理性”并不必然对长期发展最为有益,或者甚至有助。
在西半球为大米生产和出口建立起“工作平台”的一个世纪之后,欧洲资本家不仅成功地进入了即有的亚洲大米贸易网络,还成功地组织起他们自己的南亚和东南亚的大米生产和交换网络。奠定和促进了19世纪面向亚洲供给者的“转向”是技术的创新、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蒸汽轮船的崛起、跨洋电报的出现等,甚至在这些技术创新前,亚洲大米的廉价(一开始是孟加拉和爪哇)已经让亚洲的供给者们在与西方大米出口地区对手的竞争中取胜。
在19世纪下半期,低地缅甸、暹罗、印度支那成了全球大米市场的主要角色。1900年前后,市场的整合——按所谓单一价格法则来衡量——已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大米的价格越来越与整合的步伐一致,并在所有国家中也越来越在日益狭窄的范围内变动。尽管有着这样的全球化证据——用卡斯特尔的术语来表达:大米市场清晰地运作为“一个整体”,并且肯定地许许多多的人象弗里德曼所定义的那样感到了大米贸易“重要性的相对增长带来的压力限制和机会”,但世界市场的大米主要供给者们几乎没有见证到他们福利的持续增长。从世纪交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过剩的生产、人口的压力、租佃和负债问题象温疫一样传染着东南亚的供给者们;新的技术突破和美国的(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和阿肯色州)资本集约化大米生产方式导致了“相对优势”告别亚洲;世界大米市场的不稳定性更限制了东方实现其“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利益。
具有讽刺(或辩证)意味的是:为全球市场而采取的大米出口专业化使得亚洲的每一个主要供给者都恰好落入这一市场“早期进入者”的同一命运,即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州等在它们失去了相对优势后所落入的命运:贫穷、僵硬、非平衡的经济体,被发展经济学家们不恰当地或有些委婉地称之为的“因素扭变”和“经济非对称”所摧毁。不幸的是,这些结构性特征从此一直制约着上述每一地区为发展而做出的努力。(注:泰国是一个大米出口国,并且它的上一代人享有了发展的成功。但即便是泰国,大多数学者认为它的发展不是因为稻米部门,而恰恰是轻视了稻米部门。)虽然东南亚的主要出口国还能够保有世界市场的较小一端,并且相对地把它们的中心移向亚洲市场,但大米所创造的发展性“工作平台”已被清楚地证明不足以支持,更不可能促进长期增长。
大米的案例表明:经济发展和全球化都不必然是单向度的进程。的确,两者都似乎各自呈现为一个含有内部矛盾的进程,但它们都重负着历史的包袱。我们应该认识到:全球化能够给予,但它也能轻易取回。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正象一批学者近来所认识到的那样:在1870和1914年之间,世界经济在许多方面比今天更为整合。(注:Paul Krugman,"The Loc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in Krugman,Pop Internationalis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6),pp.205-214;Kevin H.O'Rourke and Jeffrey G.Williamson,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The Eu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0),pp.1-28 and passim.)如果更贴切地指向本土,人们只要做点研究就会记得:在过去20年的狂增猛长之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也只是在最近才达到了它在1920年代的水平。(注:"The Real Leap Forward",The Economist,20 November,1999,p.25.)这些事实,连同大米贸易的近代史,至少应该能让甚至是对自由贸易、全球整体、世贸组织等的最热情和最勇猛的支持者们也暂停一下思考。
(本文译者为美国威明顿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