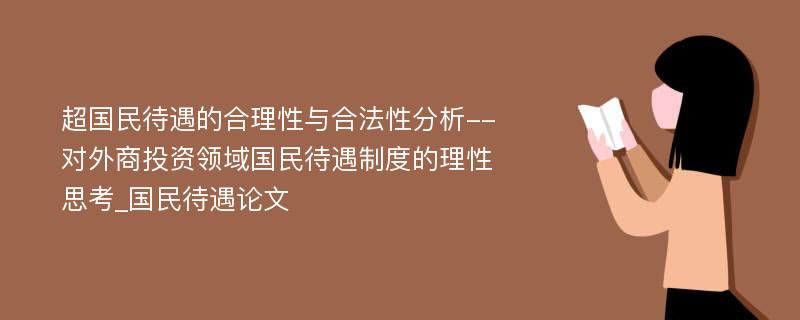
“超国民待遇合理合法论”评析——外商投资领域国民待遇制度的理性思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论文,待遇论文,合理合法论文,思辨论文,外商投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08(2004)02-164-07
经过历时15年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获得了WTO的入场券。尘埃落定,需要冷静思考的是,告别“世”外桃源的中国如何以积极、负责的态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按照WTO规则及中国作出的承诺,我国已基本完成了对以外资法为核心的现行中国法律的“废、改、立”工作。审视中国现行外资立法,与WTO所倡导的透明度、废除数量限制等原则明显不符的法律规定与相关政策已不复存在,惟独没有触及依法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一系列优惠待遇。在中国入世谈判的进程中,有关外商投资企业享有的优惠待遇是否有悖WTO奉行的国民待遇原则,一直是国际投资法领域研究的热点,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我国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对外资基本上采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形成了事实上的“超国民待遇”与“次国民待遇”并存的倾向,构成了对国民待遇原则的双重违反[1](P.18-23)。为缩短与国民待遇的距离,中国政府在调整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注:1993年12月31日,中国颁布了《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对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统一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同日颁布的《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取消了工商税与工商所得税之间的差别,并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选择工商税与工商所得税中较低者纳税的特权。1996年1月1日,中国又颁布了改革进口税制的方案,逐步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资本性货物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按照该方案,自1996年4月1日起,逐步实行国民待遇,使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在进口设备、原材料方面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然而,中国入世后,学界对国民待遇的理解出现了歧义,一些学者认为,“超国民待遇”与国民待遇是兼容的,在国际法上不存在禁止东道国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规定,并且有学者撰文论证“超国民待遇”的合法性、合理性[2]。“超国民待遇”是耶非耶?莫衷一是。鉴于这一问题事关我国入世后遵守规则、履行承诺的大事,直接影响我国外资立法与政策未来发展的导向,有必要正本清源,从理论上予以澄清。笔者认为,“超国民待遇”固然有助于我国维持现阶段吸收外资的区位优势,但于法无据,于理相悖,“超国民待遇合法合理论”值得商榷。
一、对“超国民待遇合法论”的质疑
主张“超国民待遇合法论”的人士认为,有关投资领域国民待遇的概念有两种表述:第一种表述是,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应“等同于”(as the same favorable)其给予本国投资者的待遇;第二种表述是,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应“不低于”(no less favorable than)其给予本国投资者的待遇。如GATT1994第3条第4款将国民待遇表述为“一缔约方境内产品在进入另一缔约方境内时给予的待遇……在优惠上不得低于原产于本国的相同产品的待遇……”按照“超国民待遇合法论”的推理,GATT1994只是规定了缔约方不得将“低于”本国相同产品的待遇给予本国境内外国产品的义务,并未禁止缔约方行使将“高于”本国相同产品的待遇给予本国境内外国产品的权利,因而国民待遇与“超国民待遇”是兼容的。笔者认为这种逻辑推理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有关国民待遇的定义学术界早有定论,并无二致。国民待遇是现代国际法确立的有关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基本制度。国内外法学界对于国民待遇内涵的理解约定俗成。我国著名国际法学者韩德培教授认为,“所谓国民待遇是指内国给予外国人的待遇和给予本国人的待遇相同,即在同样的条件下外国人和内国人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相同。”[3](P.116)姚梅镇教授认为,“国民待遇要求一国以对待本国国民之同样方式对待外国人,也即外国人与本国人享有同等的待遇。”[4](P.299)王铁崖教授认为,国民待遇是指“国家在一定范围内给予在其领土内的外国人以本国公民所享受的同等的待遇。”[5](P.248)美国权威法律辞书将“国民待遇条款”(National-treatment clause)表述为:A provision contained in some treaties,usu.commercial ones,according foreigners the same rights,in certain respects,as those accorded to nationals[6](P.1047)。可见,权威学者一致认为,国民待遇要求内国给予外国人享有的待遇与内国国民相同,所谓国民待遇存在两种表述的提法依据不足。
第二,从法理上讲,外国人在内国不享有超越内国人的权利。国民待遇实质上追求的是内外平等,内国人与外国人一视同仁。从法理上说,主权国家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是最高的,国家只有在对本国国民负责的情况下,才对外国人负责[7](P.143)。按照国民待遇的要求,内国给予外国人的待遇固然可以不低于内国人,但不能高于内国人。根据现代国际法关于国家间主权平等原则及国家属地优越权原则,外国人在法律上与东道国国民享受同等待遇和同等保护,承担同等义务与责任,但不能要求不同于或更多于东道国国民所享有的权利,更不能处于特权地位,也不承担更多的义务[8](P.248)。显而易见,现代国际法不承认外国人在内国享有超越内国人的权利。当然,国民待遇只是就一般原则而言,强调内国人与外国人权利等同,并不意味着在具体民事权利上外国人与内国人完全一样。无论是有关国际公约还是各国国内立法,都将国民待遇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第三,对GATT1994第3条第4款的解读不宜望文生义,脱离国际法的范畴。GATT/WTO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并非创制性的,而是源自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制度,GATT/WTO的规定也无法改变或赋予国民待遇新的内涵。因此,应该严格按照现代国际法确定的国民待遇的定义和内涵解读GATT1994第3条第4款。笔者并不否认包括GATT1994第3条第4款在内的一些法律文件的有关条款采用了类似“不低于……”的字眼来表述国民待遇,这种规定虽不规范,但并无明显不当。因为“不低于”不等于可以“高于”,两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追本溯源,GATT/WTO及其法律制度一直将非歧视原则(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奉为一项首要的基本原则,而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则是体现不歧视原则不可缺一的两翼[9](P.38-39)[10](P.139-140)。因此,GATT/WTO实行国民待遇的本意是杜绝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使一缔约方的产品经清关后,与另一缔约方的产品享受同等待遇,而非意欲使一缔约方的产品在另一缔约方享受“超国民待遇”。令人堪忧的是,在我国WTO研究领域,非法律界人士望文生义,随心所欲解读有关条款的现象时有出现,而有关媒体以讹传讹,以致谬种流传,贻笑大方。这种现象在国际上并不是孤立的,在以往GATT运行过程中曾出现过排斥法律工作者的现象,“左右GATT的政府人士,成功地把法律工作者排除在谈判会场外”。(注:see John H.Jackson: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of the GATT-MIN System:Reform Proposals for the New GATT Round,Ernst-Ulrich Petersmann and Meinhard Hill edtion; The New GATT Round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1991)P.4-5.)GATT为此付出了代价,陷入有法不依,规则失灵,法纪废弛的境地。面对具有强制法律约束力的WTO规则,非法律界人士应当走出望文生义,任意解读WTO规则的误区。
第四,“超国民待遇”并非法律概念,与国民待遇不应混为一谈。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超国民待遇”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没有确切的外延和内涵,所谓“超国民待遇”具体表现为外资在东道国享受的待遇“超越”国民待遇标准的状态,充其量是一种与国民待遇标准不符的不法现象。因此,“超国民待遇”并不是享受国民待遇是否“过当”、“越位”的问题,在理论上并不存在“超国民待遇”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超国民待遇”与国民待遇不是量的区别,两者有质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也许持“超国民待遇合法论”的人士会质疑:既然“超国民待遇”不合法,WTO规则或其他法律规范为何不明文禁止?WTO相关机构对中国进行过渡性贸易政策审议时对中国存在的“超国民待遇”现象为何视而不见?笔者认为,WTO有关条款在作出类似“不低于……”的规定时,并无必要作出“不能高于”的禁止性规定,因为法律对于显而易见的法律常识通常无须明文规定。这就如同制定规范性的法律文件时,立法者没有必要规定该法律文件是有约束力的。因此,不能因为WTO规则没有明确作出“不能高于”的禁止性规定,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可以高于”的结论。鉴于目前在中国从事直接投资、享受“超国民待遇”优惠的外国投资者大多来自发达国家,由这些国家占主导的WTO相关机构对中国进行过渡性贸易政策审议,对“超国民待遇”现象视而不见的缘由是不言而喻的。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法律的天平向经济利益倾斜是不难理解的。外资在缺乏法律根据的情况下享受“超国民待遇”,无疑是一种“不当得利”。然而,一方慷慨给予,另一方坦然接受,何乐而不为?!
二、对“超国民待遇合理论”的质疑
持“超国民待遇合理论”的人士认为,我国现阶段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在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计划经济体制仍有一定影响的情况下,国家在工资、价格、物资供应、信贷方面给予国有企业以特殊的支持,给予外资一定的优惠,是对外资所遭受“损失”的一种“补偿”[2]。笔者认为,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笼统地讨论“超国民待遇”是否合理的问题。
第一,对我国长期实行的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应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为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我国实行了鼓励与限制相结合,以鼓励为主的外资政策,这种鼓励主要表现为给予外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方针,赋予外商投资企业减免税、低税率、加速折旧、亏损转结、纳税扣除、再投资退税、投资抵免、延期纳税等优惠待遇,使外资在事实上享受“超国民待遇”。这些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是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应该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这一政策是合理的。对这一政策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利用外资的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其一,从经济上看,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我国现行的外资优惠政策是在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下产生的,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我国资金、技术匮乏,产业结构严重失调,急需吸收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国内企业能从国家计划渠道中获得种种有利的经营条件,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因种种限制而处在不利的经济环境中。因此,实行优惠政策既是对外资的一种激励机制,同时又是对事实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外商投资企业加以弥补的必要措施。
其二,从法律上讲,主权国家有权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外资政策。对外资的鼓励措施属于一国国内法规范的范围,在与本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不相冲突的前提下,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可能,独立自主地制定本国的外资政策。与此同时,在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束前,投资措施尚游离于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之外,国际社会并无规范投资措施的国际法规范。因此,在当时情况下,我国赋予外资优惠政策合情合理合法。
其三,从外资法的发展规律来看,发展中国家无不将对外资的鼓励措施作为其外资法的核心内容。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相对落后,急需吸收外资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又无其他吸引外资的条件,只得不惜给予外国投资者种种优惠待遇,而这种优惠又以减免税收作为主要形式,因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有“税收天堂”之称。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既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外国投资的普遍做法,又是发展中国家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途。
其四,从我国利用外资的实践来看,优惠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实行对外开放政策25年来,由于我国成功地实施了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披露,200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连续第二年减少,比上年减少1/5,降至6510亿美元,为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中国却以创记录的530亿美元流入量,成为2002年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首次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显示,2003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为302亿美元,月均超过50亿美元。专家预测,按照这个发展趋势,2003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将突破600亿美元大关。实践表明,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使我国多年来始终保持了吸收外资的区位优势。
第二,中国入世后调整外资优惠政策的必要性。如前所述,我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在利用外资的实践中曾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时过境迁,经过20多年的变迁,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有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已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对外资实施优惠措施的法律依据也受到了挑战,对我国现有的外资优惠政策进行调整,从根本上改变外国投资者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状况已势在必然。
其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外资优惠政策已失去其合理性、公平性。市场经济实行经济关系契约化,市场竞争秩序化,政府行为规范化,强调市场主体的平等性,市场主体在同一规则下公平竞争既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又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内在条件。1993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经过10年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基本形成,并且正在不断完善。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特殊支持已不复存在,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已处于相同的市场经济环境,外资优惠政策已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再给予外商投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不但违反优惠政策的本意,而且势必使既不享受国家计划保护,又不享受优惠政策的国内企业处于明显不公平的竞争地位,这显然违背国民待遇原则。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投资者更加看重整个宏观经济决策与投资环境的稳定与完善,中国巨大的市场对外商的刺激作用和吸引力远远超过具有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优惠政策。可以说,以税收优惠为主的外资优惠政策已完成了历史使命。
其二,在新的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下,外资优惠政策已失去其存在的法律基础。1994年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束,《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以下简称TRIMs协议)正式诞生,并被纳入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之中,“国民待遇”、“废除数量限制”、“透明度”等一系列适用于国际贸易的法律原则被引入投资领域,使传统的国际投资法发生了深刻的变革。TRIMs协议第2条第1款明确规定:在不损害GATT1994项下其他权利与义务的前提下,任何成员方不得实施与GATT1994第3条第4款(国民待遇)或第11条第1款(废除数量限制)的规定不相符的对贸易产生限制和扭曲作用的投资措施。在TRIMs协议附录部分的解释性清单中列举了与“国民待遇”与“废除数量限制”不符的5种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11](P.34-38)。可见在新的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下,对贸易产生限制和扭曲作用的“超国民待遇”已被明文禁止。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享受的待遇优于国内企业,这种“超国民待遇”实际上对外资起到了补贴作用,扭曲了平等的竞争环境,显然违反TRIMs协议。调整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使我国外资立法与政策同TRIMs协议协调一致,与WTO规则全面接轨,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加入WTO后我国遵守规则、履行承诺的必要措施。
其三,在利用外资的实践中,外资优惠政策的负面效应已日趋明显。外资优惠政策如同一把双刃剑,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现阶段,其积极作用已逐渐消退,而被“超国民待遇”扭曲的不完善的外商投资环境已成为我国进一步引进外资的主要障碍,外资优惠政策的负面效应愈来愈为人们所关注。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不但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挫伤了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威胁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影响了外资政策的稳定性,扩大了地区差异,扭曲了外资流向,助长了“假外资”的蔓延,同时也使外商投资的战略动机出现错位,使外资不能深入地参与我国市场竞争,最终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与质量。
三、对“超国民待遇”现象的理性思考
在新的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下,“超国民待遇”的合法性、合理性受到严峻挑战,对此,我们应以理性的态度,冷静思考我国利用外资领域存在的“超国民待遇”现象。加入WTO后,中央适时提出了12字的应对方针:“遵守规则、履行承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贯彻这一方针的核心是如何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行使多边贸易法律制度赋予我国的权利,并将入世后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笔者认为,解决投资领域“超国民待遇”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在“遵守规则、履行承诺”的前提下,正确把握好“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第一,以理性的态度,积极探索WTO体制下外资优惠政策新的形式与内涵。对于加入WTO对中国外资优惠政策的影响,存在两种极端的倾向:一是所谓“超国民待遇合法合理论”,认为中国外资法只须解决外资待遇低于内资的“次国民待遇”问题,至于“超国民待遇”,则符合WTO规则,不须作出调整;二是主张取消所有对外资的优惠待遇,认为在WTO体制下不存在外资优惠政策的空间。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对于“超国民待遇合法合理论”前文已作评析,不再赘述。后一种观点在理论上也亟待澄清。加入WTO并不意味着需要取消所有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从多边贸易法律制度的要求来看,TRIMs协议所禁止的只是对正常贸易产生限制或扭曲作用的投资措施,并不妨碍成员方在不违反国民待遇的条件下实施鼓励外资的优惠政策。即使对那些有违于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TRIMs协议也允许成员方在一定的过渡期内暂时适用。(注:TRIMs协议第3条规定,GATT1994项下的所有例外均应适用于本协议的规定。第4条又规定,发展中国家根据GATT1994第18条(关于维持国际收支平衡)、GATT1994收支协议以及1979年11月28日采纳的“为收支实施的贸易措施的1979年宣言”规定的范围和方式,有权暂时背离TRIMs,协议第2条所规定的义务。)因此,当务之急应是以理性态度,积极探索WTO体制下外资优惠政策新的形式与内涵。
第二,以高度务实的态度,对“超国民待遇”作柔性化处理。对“超国民待遇”的合法性、合理性提出质疑,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顾中国改革开放和利用外资的实际状况,断然取缔外资在中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鉴于“超国民待遇”利弊参半,对于现阶段“超国民待遇”的利弊得失应作实事求是的评估,并采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趋利避害,作出柔性化处理。为“遵守规则、履行承诺”,应该慎言“超国民待遇合法合理论”,原则上应不再出台明显有违国民待遇的外资政策和法律。在利用外资的实践中,则应以高度务实的态度,积极贯彻“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灵活运用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从国际社会利用外资的实践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投资已成为影响一国竞争力的国际资源,我国周边国家对外国投资的争夺趋于白热化,甚至展开了优惠政策的竞赛[12](P.5)。笔者认为,在“超国民待遇”尚未亮起红灯的现阶段,拟将“超国民待遇”视为WTO领域的“灰色区域”,充分利用这一时间差,保持现阶段我国吸收外资的区位优势。因此,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我们对“超国民待遇”现象应持低调的态度,既要慎言“超国民待遇合法合理论”,同时也不宜轻言取消“超国民待遇”。
第三,以渐进的方式,有步骤、分阶段地消除“超国民待遇”现象。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关外资享受的优惠政策是从沿海逐渐向内地扩散的,我国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起步较晚,现阶段仍需要依靠以税收优惠为主要内容的优惠政策吸收外资。有鉴于此,对于历史形成的“超国民待遇”现象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方法予以消除,而应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伴随着条件的逐步成熟,从经济特区、沿海地区渐次向内地推进。
四、重塑外资优惠政策的思路
鉴于“超国民待遇”反映了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引导外资的不规范行为,消除“超国民待遇”现象,重塑外资优惠政策已势在必然。在现阶段,重塑外资优惠政策总的思路应是以国民待遇原则为指导,逐步消除目前“超国民待遇”与“次国民待遇”并存,对国民待遇原则双重扭曲的局面,确保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在同样的市场环境、同一市场规则下公平竞争,以营造利用外资的良性循环。为实现这一目标,应以积极探索WTO体制下外资优惠政策新的形式与内涵作为突破口,为此,宜采取以下几项调整措施:
第一,以国民待遇为指导,促进外资优惠政策与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外资优惠政策与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相互脱节,是导致“超国民待遇”现象的原因之一。为此,应采取积极步骤,加强外资优惠政策与外贸政策、外汇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的协调,加快步伐取消国内企业进出口经营审批制度,统一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持汇和用汇制度,彻底改变“内外有别”、“抑内让外”的状况。
第二,逐步弱化具有让利性质、补贴性质的各类税收优惠政策,代之以功能性、产业结构性的优惠政策。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形式单一,难以摆脱税收优惠的窠臼,地方政府在所得税的减免方面更是乐此不疲,几乎倾其所有,甚至超越法律规定对外商作出承诺。当务之急应是尽快走出税收优惠的误区,赋予新形势下外资优惠政策新的形式与内涵,强化功能性、产业结构性的优惠政策,加强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和科技导向,大力扶植基础设施项目、进口替代的原材料项目及高科技项目,积极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为有效制止“超国民待遇”现象,应防止新出台的优惠政策单方面向外资倾斜的倾向,只要符合产业导向、地区导向的要求,内外资企业在享受优惠政策上应一视同仁。从长远来看,我国应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势,实现立法观念的转变,从优惠型立法转变为审查型立法,从强调中国特色转变为注重与国际标准接轨。
第三,加强外资立法与政策的统一性、稳定性。追根溯源,滋生“超国民待遇”的直接原因是我国在外资立法的模式上采取内外资有别的“双轨制”,这种国内经济立法与外商投资立法并存的现象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不但影响了我国法制的统一,同时导致了内外资企业享受不同的待遇,进行不平等的竞争。与此同时,以往那种对外资法“小修小补”的局部修改使我国外资立法难以摆脱捉襟见肘的困境。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对国民待遇双重扭曲的“超国民待遇”与“次国民待遇”并存的现象,改变“双轨制”立法模式不啻是一种治本之举。笔者认为,在我国利用外资工作历经25年,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逾10年,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WTO的情况下,中国外资立法与政策所面临的国际背景与国内背景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塑我国外资立法体系的条件已渐趋成熟。我们应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契机,积极推动外资立法与政策统一化的进程,建立和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外资法体系。为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形式到内容,对以外资优惠政策为核心的现行外资立法作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以全国统一的外资立法与政策取代目前从沿海到内地、多层次的、名目繁多、内容各异的外资优惠政策,以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典取代利用外资的各种单行法规、地方法规和行业规范,最终达到外资立法与国内经济立法的完全统一。
标签:国民待遇论文; 外商投资企业优惠政策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投资论文; wto论文; 法律论文; gatt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