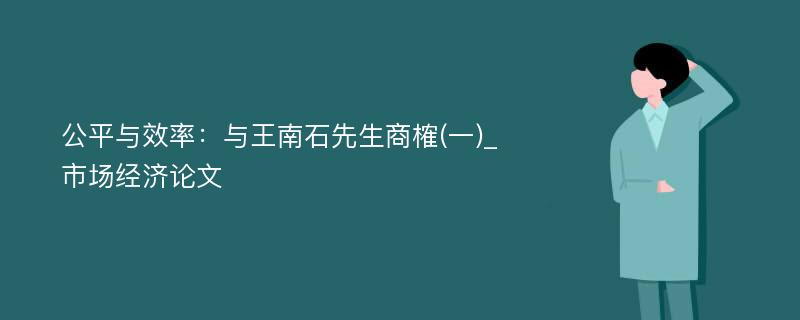
论公平与效率——与王南湜诸先生商榷〔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平论文,效率论文,王南湜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平、效率是健康社会必须关注的问题。我国论者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对论及的所有问题仍然没有定论,但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则是大有裨益的。本文是商榷文章,那就只好通过跟随被商榷者的思路去漫游而展开笔者的观点,以此就教于王南湜诸先生。
一:效率与公平的含义
效率与公平范畴的界定,学界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所以如此,问题不在于效率与公平两个范畴的内涵怎样确定,而是它们的外延被学界同仁忽视。大多数人在谈论效率时,一般都是从经济领域出发的,认为效率就是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率,但效率的本义应是单位时间内完成工作量的大小即劳动效果与劳动量或工作效果与工作量的比率。那么不光是经济领域存在效率问题,其它社会领域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能仅仅限于在经济领域对此进行探讨、争鸣、界定。关于公平的范畴,同样如此,有政治上的公平,有经济上的公平,有伦理学上的公平。如果就其存在的状态分,还有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结果的公平。角度不同,结论就不一样。公平的本义应是公正、公道、合理、正义。至于有人认为公平是人们对某种社会现象的一种道德评价,是某种社会关系的观念表现(王锐生、陈勇等先生持此观点),是一种社会规范价值,其功能在于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财富的分配关系,是客观上存在的价值等等(石梁等持此观点),笔者认为这些结论是“定义过宽”,但不能否认这些结论的深刻性和必要性,只是问题本身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权衡公平与效率两个范畴的复杂程度,为了澄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我国学界的是是非非,笔者想强调一下公平的问题。我们在探讨公平及其相关问题时,一定要区别公平、平等、均等、平均主义等概念,在论述问题时,不能犯“偷换概念”的错误。在王南湜诸先生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起点的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等概念,要知这些概念与“机会均等”、“结果均等”是不一样的。这正是笔者主要地想跟王南湜先生商榷的地方。
公平、公正、平等三个概念的意义是相近的,所以“起点的公平”、“起点的公正”、“起点的平等”可以互用;“过程的公平”、“过程的公正”、“过程的平等”也是相近的;同理,“结果的公平”、“结果的公正”、“结果的平等”也就可以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公平、公正、平等就是人与人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相同的权利。它有权利平等(或公平、公正)——即国家承认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机会平等(或公平、公正)——即社会应该为每个公民追求自身利益、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平等地公平地提供必要机会和条件,如“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语)、结果平等(或公平、公正)——即主张社会的价值物对所有人实行按劳分配的、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原则进行平等的公正的分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公平、公正、平等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们就必须承担各尽所能的平等义务和享有按照劳动取得报酬的平等权利。即使是市场经济,只要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就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点。不能因为社会主义还不完善,还处于初级阶段就否认人们最起码的公平、平等的要求——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要求。这与由于劳动者的体力、智力、家庭负担等不同所导致的现实的不均等所希望的那种均等是不同的。前者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的,后者则是不可能的。均等和平均主义是同义的,它要求全体成员平均享有社会的一切财富,主张消灭一切差别,在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物质分配和个人需要等各方面绝对平均。“起点均等”、“过程均等”、“机会均等”、“结果均等”就是这个意思。如:“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语)、“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王小波语)、“等贵贱、均贫富”(钟相语)、“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洪秀全语)。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绝对平均是不现实的,而且直接违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具有落后性和破坏性。社会主义要的不是这种均等和平均主义,而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公平要求。
所以“起点的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与“起点均等”、“机会均等”、“结果均等”是根本不同的。在论述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我们不能混同两类概念,尤其是不能混淆“结果的公平”与“结果的均等”。
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王南湜先生在《探索公平与效率的具体关系》一文中(见《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讲述了这个问题, 笔者理解他的观点如下:
1、文明时代以来的社会有两类即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的社会, 并且市场经济社会一般地是相对于生产力水平较发达的状况的(王文没有直言,但明显地包含这样的意思),是迪尔凯姆称之的“有机团结”的社会;而非市场经济社会则一般地是对应于生产水平不发达的状况的,是迪尔凯姆所谓的“机械团结”的社会。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经济活动不必再为了保证社会秩序而受制于政治活动;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则是以政治为中心的。所以效率、公平与自由分别为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域各自的内在价值取向,以政治活动为中心必然导致以公平为主导性价值,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则必然导致以效率为主导性价值。还认为起点的公平从保证社会效率着眼主要是市场经济社会的,而结果公平从保证社会秩序着眼主要是非市场经济社会的。
这些观点乍一看来,好象与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无关,实则不然,笔者认为这是认清两者的理论基础,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就决定了你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持一种什么样的观点。王先生的上述观点,也就决定了他思想中的公平效率观。
应该说这些观点是深刻的,但笔者不同意王先生的观点。一是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社会的划分不利于对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的具体分析。笼统而论,往往得出不准确的结论。如市场经济社会一般地是相对于生产力水平较发达的状况,而非市场经济社会则是相对于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那么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是指经过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之后的状况)、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吗?其次,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效率”为主导性价值,固然不错。但并不是说经济活动不必再为了保证社会秩序而受制于政治活动,或者说追求效率不必再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而受制于公平;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也不光是,或者不会是纯以“政治活动”为中心,以“公平”为主导性价值。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应该是政治与经济的有机统一,既要追求效率,又要密切注意公平,在公平的基础上追求效率,在效率带来的新的结果之后再创新的公平。在现实的社会,特别是当今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不能人为地将政治与经济、公平与效率分开,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都得注意这个问题。否则导致的后果是社会的畸形发展。第三,王先生认为起点的公平从保证社会效率着眼主要是市场经济的,而结果的公平从保证社会秩序着眼主要是非市场经济社会的。这也是不正确的。前已述及,公平与效率是任何社会必须关注的,有史料记载的社会都证明如此。不存在有的社会注重公平,有的社会忽视公平。王先生将公平分为起点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韩志国等先生也这么看),笔者主张在两者之间加入过程的公平,只有如此才更有说服力,之所以如此,主要的是因为在整个公平的大过程中,如若只注意起点的公平、结果的公平,往往与事不利。因为在实际的运行中,或者说在从起点的公平到结果的公平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现实的复杂性,特别是由于主体的主观性、趋利性,就极易出现过程的不公。所以为了从起点的公平到结果的公平顺利发展,有必要加入“过程的公平”。另外,也不是像王先生所言,将起点公平与结果的公平带着各自的功能分属两个社会。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结果的公平在现实社会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一公平都有这样的动态过程,主观地对其分割是形而上学的作法。再说,并不是只有起点的公平才能保证社会效率,结果的公平才能保证社会秩序。实际上,结果的不公给社会效率的提高会设置巨大的障碍,当然也不能保证社会秩序;起点的不公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样会有极大的破坏,自然也不能保证社会效率。总之,笔者认为,只要是公平的,就会给社会效率以极大的提高,就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反之,就会阻碍社会效率的提高,就会破坏社会的安定。如此之后,自然就引出了下述问题:
2、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完全统一的。 公平只与不公平相对立,与均等、与平均主义相差别。只要是公平的,即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结果的公平的有机统一,就会导致效率的提高,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被扭曲,那就意味着公平的缺失,意味着不公平的出现,其结果必然导致低效率或无效率。同时社会的不安因素也就因此而产生。而王南湜先生认为,只有起点的公平与效率才是统一的关系,起点的公平才是达到高的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和手段。而结果的公平则与效率的关系呈现三种状态即一致关系、对立关系和介乎两者之间的既非一致又非相斥的弱一致、弱相斥关系。从政治与经济共同作为人类活动的两个不可缺的方面看(实际上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如此:政治与经济永远不可或缺),经济活动所着力追求的高效率不能离开为结果的公平所保证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一个缺乏秩序的社会,是不会有效率的,同时经济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增加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增进,一个没有效率的社会,公平是可怜的、可悲的,故两者存在一致关系;结果的公平若施之于经济领域,则不可避免地使起点的公平成为无意义,而妨碍效率之提高;同时若坚持效率至上,坚持起点公平,则机会均等和竞争(应是机会公平,因为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则必然导致结果公平的缺失,故两者有对立性;但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又存在起点的公平并非完全是经济领域的价值导向,结果的公平并非完全是政治领域的价值导向的第三种关系即弱一致、弱相斥关系。很明显,王先生只钟情于起点的公平,对结果的公平是厌弃的。字里行间也可看出他对我国经济落后的担忧,所以想尽快地使效率有一飞跃,但性急吃不得热豆腐,而且社会是一系统工程,公平与不公平就是其中重要一环。要想在当今我国使经济发展,效率提高有众星拱月之势,无论是起点公平,还是结果的公平都不可忽视。当然王先生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据的根源是将结果的公平等同于结果的均等或者平均主义,如果谈结果的均等、平均主义会妨碍效率,则人人无异义了。因为按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结果的均等、平均主义实质上就是不公平。但结果的公平作为公平的一种或者一个发展阶段,则与效率是完全统一的,只有不公平方与效率抵触。人们追求公平的状态,就象追求平等、民主、自由等的状态一样,应是每一健全社会给予保证的。公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是理想的、完美的、正义的社会状态。一个社会实现了公平,那么它为该社会处于良性运行状态就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为效率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平与效率是完全统一的关系,但不影响公平与效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国家有孰先孰后或者孰重孰轻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关系和谐,社会秩序稳定,而且经济不怎么发达,可以视效率为主导价值,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参考王锐生先生的观点);反之,则以公平为主导性价值,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当然现实的国家在施政方针中究竟何者优先,应该是内政,不容干涉。但为了人类的进步,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我国现在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则应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点。不然我们追求的公平就象王南湜先生所言则是“可怜的、可悲的。”追求的效率,如果稍不留神,时刻有导致两极分化的危险。
张晓明先生明确指出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两者的关系是矛盾关系。许多学者实质上也是持此种看法的。笔者也不同意这种观点。公平与不公平,效率与无效率才是矛盾关系。但公平与效率则不具备这种关系,它们之间是一种统一关系、条件关系。矛盾关系具备统一关系、条件关系的特点,但不能反推,不能说具备条件关系、统一关系的东西就是矛盾关系。学界所分析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对立关系,实质上不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而是不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不能偷换概念。
三:对其它一些观点的不同看法
1、共同富裕的理想不能掩盖不合理的贫富悬殊。
共同富裕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是理想的、完美的社会状态,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我同意刘润葵先生的观点)。王锐生先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共同富裕是解决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的行为导向的手段,不是目的,不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他预言在中国实现小康水平的时候(即21世纪初)中国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不必等到共产主义的实现。笔者认为,手段和目的是相对的,问题在于各自的论域不同,即使相同的论域,手段和目的也是极难区分的。将共同富裕视为手段,还是视为目的,这并不重要,我们关心的是怎样在中国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能否实现,什么时候实现等这样一些问题。在现实的中国,应该说存在“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的危险性,而且富的只占少数,贫穷的占绝大多数。那么先富的地区和个人能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和贫困的人吗?在多大的可能性、多大的规模上去给予支持、帮助呢?能从根本上普遍地解决贫困问题吗?从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再说依靠国家政策的倾斜等走向富裕的地区和个人自然是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去这样做,但那些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劳耕耘而走向富裕的人也有这个义务吗?另外,我们区分开了勤劳致富者和不劳而获者吗?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没有弄清,空谈共同富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国12亿人都强烈渴望共同富裕的状态早日实现。但理智的人应该积极地去探讨实现这一状态的具体途径。
时下,我们千万注意,不能因为我们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发展、提高效率这一中心任务上,不能因为我们在为共同富裕而努力奋斗中,不能因为我们反对平均主义,而无视、忽视不合理的、不公平的、非法的、罪恶的贫富悬殊,对那些权钱交易者、贪污受贿者、偷税漏税者、剥削农民者等等,应该绳之以法。为国人走向共同富裕开辟平坦的、康庄的大道。
2、不公平之恶只能是人类历史的破坏力
王锐生先生不同意刘润葵先生的观点,笔者持异义。王锐生先生引用黑格尔之“恶”以及恩格斯评价黑格尔的观点来反驳刘润葵先生,笔者认为是“偷换概念。”因为黑格尔之“恶”正象恩格斯所言,是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是对陈旧的、过时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是罪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等。但与不公平之“恶”是根本不同的,黑格尔之“恶”是历史的必然,而不公平之恶则是社会的扭曲、变形,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即使恶劣的情欲之“恶”也与不公平之“恶”不一样,马尔萨斯早就论及了物欲和情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生理基础,情欲即使恶劣的情欲当然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之一。不公平之“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永远只是提供“教训”,它本身并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而只能是糟蹋历史、蹂躏社会。
3、改革的代价由谁承担?
王南湜先生将改革的代价区分为两种即模式代价——社会注重效率而使公平受到损害,是市场经济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和过程代价——新旧模式之间的“秩序真空”而滋生的权力与金钱相交易等的腐败现象,从而使社会公平受到损害的代价,这是极为深刻的观点。因此,改革的代价由谁承担的问题,应分为两种答案:一是模式代价,它必须由我国的全体公民承担,不能将其只归于农民、工人。应该是所有公民特别是富裕的地区和个人应主要承担这一代价,其中尤其以依靠国家政策倾斜而致富的地区和个人为重;二是过程代价,这是某些人(其中有大量的党员干部,甚至国家级干部)的“钻空”、“投机”等导致的,那么,责任自然由他们承担。笔者不同意王南湜先生的这一提法:在新旧经济秩序之间“秩序真空”里,不可避免地滋生出腐败现象。现实中存在的东西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呢?既然不可避免,我们又怎样克服腐败现象呢?结论很清楚。王先生认为对过程代价的补偿只能是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只有釜底抽薪,才能解决问题,这是笔者深为赞同的。对过程代价的补偿,如果象模式代价那样,由全体公民作出一点牺牲来补偿、承担,那既不是扬汤止沸,更不是釜底抽薪,相反,那是姑息养奸,是纵容腐败。所以过程代价坚决由腐败者承担,承担之后,还必须给予法律的制裁。
